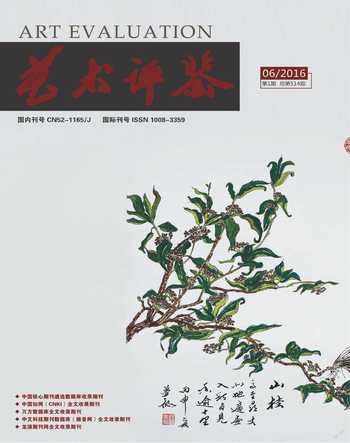画家的艺术品收藏
2016-05-30张芙蓉郭昕
张芙蓉 郭昕


参与、举办画展:1985年,系列版画参加“立交桥版画展”;1986年,参加第九届全国版画展览,并在《美术》《画家》等杂志发表画作:1988年,国家文化部授予“民间美术工作开拓者”称号:1994年,系列民艺藏品参加“中国民间艺术一绝”大展(中国美术馆)获金奖;1996年,在北京当代美术馆举办“颜新元藏湖南水陆道场画展”,中央电视台“书坛画苑”栏目进行专题报道;2001年,合作大型油画组画《升》《腾》被中国银行收藏:2007年,被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导师:2008年,创办北京“庄子湾”画廊(北京酒厂国际艺术园);2009年,在北航艺术馆主办“国风新语·颜新元当代艺术新民间实验展”,并参加“牛转乾坤”(北京)艺术创作邀请展;2010年,参加“第3届当代艺术邀请展”(北京);2011年,策划的“2011北京——中国民俗艺术国际论坛”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由著名学者田青、王鲁湘担任学术主持,其200件民俗艺术个人藏品参加此次论坛之“移动的古代祭祀壁画展览”,并配合此次论坛在北航举办“东风绘本”展览:同年,参加《第3届中国齐白石国际艺术节——当代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杜大恺师生展》;2012年,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大观园》栏目首播王鲁湘对颜新元的访谈节目《神鬼之祭》;同年参加《欧洲行写生作品展》《第四届当代艺术邀请展(北京)》《北京油画学会作品展》《名人画名山·山水画展》;2013年,与杜大恺等参加在马来西亚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展》以及《走进自然——杜大凯师生作品青州邀请展》《意象的超度》《八面来风》等画展,并随国际频道环球奇观摄制组南非采风写生;2014年,举办《花鼓墨韵·颜新元戏剧小品展》《一家人画画》展览:参加《梦想·蓝天》6·5世界环境日主题艺术作品展、《融合·建构》当代艺术邀请展(双年展,北京)以及广东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站在世界屋脊,托举生命希望”西藏采风写生创作活动;2015年举办《宋庄职业画家作品展》《自由的表达·一家人画展》《忘却陈规·一家人画展》《言下之意·一家人画展》《画外之音·一家人画展》《本真之理·一家人画展》;2016年,湖南省新闻出版广播局、湖南妇女联合会授予“书香之家”牌匾、国家新闻出版广播总局、全国妇联授予“书香之家”牌匾。
发表专著:《中国当代“新民间”艺术》《湖湘文库·湖湘民间绘画》《湖湘文库·湖湘民间木雕》(与龙全合作)《民间鬼神画》《中国现代陶艺家》《十九世纪中国风情画》《名师点化·名师访谈》《东风绘本一1》等。2015年先后在《十月》《名作欣赏》作专题发表。
作为中国民俗艺术的知名藏家和研究专家,颜新元的藏品曾获“中国民间美术一绝大展”金奖,还被国家文化部授予“民间美术工作开拓者”称号。对于他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下,与民俗艺术结缘并开始收藏民间艺术品的问题,笔者充满好奇。于是,借此机会,听他娓娓道来:
“早先,我就住在乡下,一直在老家生活,三十多岁才离开农村。那个时候我曾经设计自己的未来,就觉得我可能应该注意到潜在于我的脑海里的我自己都可能没有意识到的记忆或者说是曾经有过的某些感觉与经验,这种潜在的经验应该主要是与民间艺术,或者说与民俗艺术相关的。有一个理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规划以后,我就有意的关注本地的、外地的甚至世界的民俗艺术。最初关注‘民间只是觉得一个画家如果要想具有世界性,你首先要具有自己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一个民族和地域的个性,其实也是由许多个体的个性形成的一个共性,这种共性放在全人类文化的餐桌上,它的文化食品口味就是民族和地域的个性。从画画的人的立场出发,怀着寻找自己民族的根的动机,从找到自己的作品的文化依托与个性的目的出发,才进行了长时间的民间艺术和民俗艺术的收集、整理、出版,到这一系列工作的后期,直到大学的讲堂对其进行传授,在绘画创作中的应用。这是一个不容我自己选择的时代约定。因为这些工作必须要有人来做,我的这种意念与动力的产生,一定是我所在的特定的时间与特定的空间文化自律的因果。我的家乡湖南、益阳、桃江,是一个民俗艺术和民间艺术特别浓郁的区域,这个区域它必然要养育一大批为它动情的人吧,我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个”。
颜新元自身的艺术境界高度使他在收藏艺术品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衡量标准。他收藏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并不同于多数买家那样,首先考虑藏品会增值几何,买进之后他也不急于出手。他会综合的关注一件艺术品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在这种种的价值里面,他首先想到的是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文化与艺术优先的这样一件文物评判规则,不仅在私人收藏家中极为罕见,甚至在世界上的众多博物馆都不多见。人们优先考虑的往往是历史价值或经济价值。而颜新元关注的却是一件藏品在造型艺术创意等方面体现的智慧,以及制造艺术品的个体怎么样表达当时的真实的个人性情怀,怎样表达这个地域的这一群人的某种意识。
尽管颜新元热爱艺术、痴迷收藏,但他严格遵循反对掠夺性收购的原则。在民间看到心仪的艺术品,大多情况下,他只是拍张照片记录下来。如果所有者主动要求出售,他也会先规劝其自己保存,一代代传承下去。因为,他坚信不应该断炊的民俗艺术烟火,最好是继续在它的自然语境中传承下去,它应该在那个原生态的域境里自由发展,而不是被“囚禁”于收藏家的仓库之中。基于这个原因,他的大多数藏品,首先是来自于市场的。
通过三十多年慢慢的积累,颜新元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优质藏品。这个质与量综合起来的状态,正符合了他本人的收藏目标和收藏态度。逐渐地,这些质量兼优的藏品,对他和他的夫人与子女绘画创作产生了积极作用,可以说,这种间接或直接地对深藏在暗处的一种理念的借鉴,趣味的影响,都带来了好处。
颜新元对民俗艺术的热爱,绝不止步于民间艺术品收藏,还通过多种方式去研究和挖掘民俗艺术。在他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生命力最强,对整体的支配力最为恒远的内容应该莫过于民俗艺术。因为,它都能成为习俗的组成部分,成为习俗支配的元素,一定有特别的理由让它不容易灭绝,或者说它会有特别的活力,特别深层的生存必要性。颜新元说:“我一般喜欢用‘民俗艺术这个词汇来归纳我所关注的这个学术板块。我以为,在民俗艺术的宝库里面最为重要的就是视觉的东西,因为视觉的东西它很直观,是一代代、一辈辈的记忆,通过艺术劳动的转换,把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人们看不见的东西转化为视觉的东西,它是智慧和劳动的转换结果”。
颜新元注重视觉的部分,还因为他的自我定位是“做视觉艺术的人,是画画的人”。他希望跟画画很贴近的一些优秀传统的造型艺术能够得到更多的了解。他能够找到的每一件单个的作品,绘画也好,雕刻也好,刺绣也好,皮影也好,对他来说,其实都只是在一些有趣的村子的地下捡到的有趣的动物的毛,而且是一根一根的毛。颜新元如是说:“我把它捡起来,放在掌心。这时就会想,如果能够把这些毛种到它的皮肤上,又能推测的看到这个皮肤是以什么样的形状附着在一些动物的身上,然后这些动物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村庄里面,或者说在树林里面怎么样运动,怎么样生存,动物跟动物之间是怎么样处理关系的等等,那该有多好。这提醒我不要割裂的只看每一件作品的美——我们在博物馆看的往往都是毛发的零散的碎片,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找到这些碎片哪怕是以一种虚拟的,或者以追忆的、印证的方式,让它归附到原来的话语体系,归附到一个相对整体的体积感上。基于这个理由,我比较留心古代的文字手抄本,拿手抄本与同时期的绘画对照。他们画的是什么内容组合,挂在哪儿,怎么挂,手抄本里面就会提到。比如说祭祀绘画就会有很多的神灵的组合,如果你同时得到了手抄本,里面就会有一些唱词,这些唱词往往会提到什么神,这些神都是有归类的,一组一组的。这样,我们能够有机会了解这些原来我们可能没办法找到的姓名与群组的归属这么一些文化内容。这样的绘本与手抄本的对照,给我解开了很多的难题。在文字手抄本里面,它会有方方面面的启示,让你得到可能想都想不到的一些文化与社会方面的感知。因为,我们能找到的这些文物,很多是远离了它产生的时间和地点的,我们要找到更多手段来印证它产生与存在的理由。印证的手段除了我说到的一些手抄本,木板印刷本,还有特别宝贵的民间口头的述说,比如当地的老人,他们唱的,他们说的,包括一些神话、故事、传说。从中,你会得到一些绝对很快就会流失的记忆,口头的东西比文字的东西更加宝贵。这样一个经过百年新文化运动,尤其经过可怕的“文革”之后,来自于真正口头传承的古代经典显然是极少的,极宝贵的。为了记录这些口头的东西,我曾经专门买录音机,一家一家地去采访。我采访的东西可能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比如,我这边刚采访一些传统的祭祀的法师,过会儿又采访一些老太太唱她们少女时期唱过的民歌。我觉得,这一些娱乐的口头传颂的东西和文字传下来的东西,一些信仰与生活间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对应,能让你找到一些相关的、立体的映照”。
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魅力,能够让一位艺术家对它充满如此激情?颜新元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当下,在诸多的文化内容、文化形态之间,民俗艺术,或者说民间艺术,首先就是特别的朴实,特别的富有人种的血脉基因。这种血脉和基因的宫含量,也是我们看到它特别朴实和可信的一个来路。它来自于本土。这个本土包括地理、气候,包括创造力,最深层的内容包括哲学。当哲学通过艺术品表达出来,它无形中就包含了物侯历法等等一些基本的原委。特定的物产,来自特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特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又造就了这个地区的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人的一些理解事物的方式、表达事物的方式、储藏历史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承,显然是这个地域和这个民族地方的人的一个极大的损失。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了解这种记忆的重要性呢?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跟之前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在之前的农耕文明时代,祖祖辈辈他有一个有序的记忆链条。工业文明潮水般突然来到这个地方之后,突破国界,突破地域的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无趣的文化雷同性,或者说单一性,通过模仿、复制来传播,大大地伤害了这个世界文化未来丰富多彩的可能性。而我深信,丰富多彩的基因是必须由我们这一辈人把它传下去的。而且,只有传下去,这个传统才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只有是活的传统,我们学它才会有意义。我们这一辈能够拿出什么叫传统的东西交给我们的后人,一千年以后,两千年以后,我们的后人还能够找得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他们祖上的传统,而不只是民国或清代的传统,魏晋、唐代、宋元明清那样的传统。在所有的‘传统的份额里面,必须要有我们当下的传统。我特别关注怎么样把我们收藏的东西转化为我们的理解之后的一种吐故纳新,怎么把新的东西吸纳进来,转化为一种包含着优秀传统的一种感觉,一种创造品”。
事实上,颜新元如此热爱民间艺术还有一个理由——由于农耕时代交通的不便,信息沟通方式的不便产生的丰富多彩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会产生趣味的个性化、趣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区别于我们当下所得到的文化饲料的配给,像我们今天“文化麦当劳”“文化肯德基”这样的文化饲料的配给。“当然我也不主张狭隘的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在这样一个文明过渡的时代,尤其在我们提倡程式化的这么一个趋势下,来自于乡野的,也包括来自于过去都市的、街巷的底层民众的艺术,无疑更包含着一种粗犷的野趣,而这种野趣至少是对被我们夸大的所谓的‘现代文明的一种补充。野趣是生命整体中间最为宝贵的东西,因为它往往是群体模式教育之外的,来自于生命本体的追求,是气质层面的东西。过去时代的集体的无意识和集体的有意识,形成了反复锻打、反复修炼、反复补充的一个经典历练的过程。往往我们看上去一个好随意、好奔放的东西,甚至有一些偶然性的东西,其实它是经过祖祖辈辈一点一点补充、一步一步完善积累而成的。一些我收藏的我以为最好的刺绣里面的桃源刺绣、雪峰山脉的刺绣和雪峰山脉的木雕,一种活泼的野趣的外表是蕴藏着很多很多经典的。其实,从这些很好的刺绣和木雕中,也能看到一定的程式化的一种传承,明代的、清早期的、清中期的、清晚期的,它可能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个作者不同时期的,同一个地域不同作者的,它都会有微妙的气质性的表达。同样的构图,一个柜子上的木雕组合,刀马人的组合,有的马头昂起来,马尾巴甩过去,或者说猛一扭头的姿态,会有一些群体对马的共同记忆。对一个整体空间布局的讲究,可能也保存着一个群体的习惯性特征,但是,与当代机器文明的单一性不同的是,传统‘民间绝不会丢失个人的东西。
或许,正是由于对民间艺术的珍视与热爱,使得颜新元的作品独具洒脱、自在又直白、可爱的个性,那么,他在绘画创作的过程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种个人独特的艺术绘画风格是怎样形成的?他又是如何评判自己的艺术风格?
早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民间美术系学习的几年中,他就产生了一些怎么样把民间的东西运用到创作中来的欲望和经验,尤其是当时一些前辈老师——杨先让先生、靳之林先生、吕胜中先生等传递的经验,他们都以不同的传统含量与当代含量,从不同的角度来吸收民族、民间的艺术精华。比如说,吕胜中先生更多的是把一些民间的符号拿来转化为当代艺术的一个哲学表达,他的哲学也继承了传统民间的一些理念,但是他的视觉形式就是非常的“当代”的:靳之林先生是更加表现在理论方面的一些建树,表现在对一些哲学层面的、文化层面的挖掘和归纳,这是他的一个极大的长处:杨先让先生则更多的是一种对整体的、社会教育构架所做出的贡献,包括对当年全国唯一的在高等美术学府的民间美术系的建立。
举家迁到北京以后,一些优秀的绘画导师和好朋友的影响,对颜新元的艺术创造走向成熟,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跟杜大恺、尚扬、戴士和、刘巨德、曹力、龙全、丁立人、田青、吕品田等人的密切交往,都是他从文脉接气的气场。学习来自于传统文物的东西,学习来自于民族、民间艺术的东西,最好的态度就是当自己把它用到自己的创作的时候,要规避造型的表面模仿和简单复制,而更多的应该在乎它深层情怀、思维方式的经验渗入。颜新元的水墨,讲究对即兴的、偶然性水迹、墨迹的尊重,他制造这种偶然性的机会,在中国特有的宣纸上,或者说类似于宣纸的其他纸张上,制造一种具有特别的奔跑速度和特别的墨水浓度和干湿度的音乐节奏,很享受。水墨,在特别的宣纸上奔跑的状态下,即兴想到的形放置在一个特定疏密关系的次序里面,怎么样控制,怎么样将错就错地把握偶然性的机缘,然后给它合理的收拾,都是一种挑战。由于有这些偶然性的机缘,这副作品与别人的作品,甚至与自己其他的作品,都会不一样。如此,他的纸张,他的布帛所记录下来的图样一定是包含着他即兴调控的智慧的。他愿意从这里面来找类似于民间的一些野趣,刚刚说到民间民族的东西很宝贵,它就是保存着个人的生命跟生命之间不同的那种气质性的野性的趣味。
对于颜新元所选择的风格体系来说,很机械地要把一个对象的形画得很具象,很写实没有更多的意义。把一样东西画得很准确,把一个场面画得很真实,以此体现他的写实能力有多高,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那么做,那不是他的目标。把一个绘画构成的次序感和节奏感建造出来,兼顾点线面的构成关系,疏密的构成关系,肌理的构成关系,最后形成一个气氛,而这个气氛包含着气质,这个气质紧紧地联系着自己所追求的人格指标,还体现着某种可资识别的具象再现信息,这就是他希望在作品里面强调的。比如说色彩,有时候颜新元会习惯用灰调子的色彩,但有时候,他也习惯用相对比较单纯、明亮、强烈的色彩,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色彩,选择是浓是淡,是高纯度还是低纯度,都会使他联想到家中所收藏的那些自以为是中国之最的那样的刺绣,那样的画着色彩的木雕,追求那样的既亢奋、既昂扬、既鲜明、既爽朗,同时也特别和谐优美的境界。当然,各个层面的艺术品,文人的艺术品和民间的艺术品它都有相对低档、中档或高档的存在,也肯定存在浅层次的东西,这要就靠人们的眼光和我们的水平来对它加以甄别,加以利用,加以改造,加以吸收。
在欣赏颜新元的作品时,我们总会感受到一种乡野的气息,这是他在着意表达些什么吗?颜新元如是回答:“我觉得艺术作品的风格是建立在你的情感和你的造型艺术的形式语言这个系统化语言之上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特别的一种感情的划定,然后通过我的一种包含着特别的造型,特别的节奏的布局所形成的一个特定气质来表达自我,比如说在画油画的时候我也会有意识的用到一些水墨的经验,但是我绝不会用油画去复制一种水墨效果。油画笔意要服从油画布的语言、油画笔的语言和油画颜料的语言,它们的语言是特定的。油画笔和毛笔是不一样的,我会强调在油画里面用到一种油画的线。比如说油画笔线的粗细,行走的快慢,和往下摁的力量,都会在画面上找到一种与毛笔不同的知觉,这种知觉一定不同于别人。因为整体知觉是多元素的综合把握,它不是单项的一种模仿。对象不一样,当时的体谅不~样,对事物的揣摩不一样,情感状态、情绪状态不一样,它终极的呈现就会不一样。由于它的元素不是单一的,所以它是无法复制的,甚至连我自己都是没办法复制的。没办法复制,这就是艺术的自由,这就是艺术的生动活泼。实际上,正是这种唯一性才决定了艺术创作的价值。这种唯一性不能建立在刻意做奇、刻意作怪的目的之上。我反感有些人满足于从异国他乡移植某种身边的人没有见过的把戏来当自创的新鲜玩意儿。我有让周边的人感到更为新奇的元素——可能在博物馆难以看到的宝物——渗透到我的作品里面去,它们会变成一种气质。只有当我的综合性的艺术气质变得很健康、很美好、很自如、很自在、很本色的时候,我的收藏离我的创作、我的创作离我的创作目的才会相对的靠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