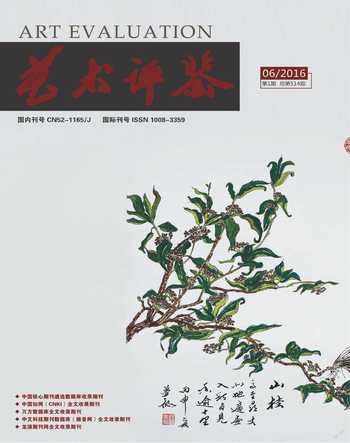真诚的述说
2016-05-30张芙蓉
张芙蓉

曾举办个人展览:《王王平作品展》(1991年,中国美术馆);《鱼》(1996年,美国佛蒙特中心画廊);LOVE(2001年,在美国纽约Ethan cohen Fine Arts画廊);《王玉平》(2001年,澳大利亚悉尼Ray Hughes画廊);《王王平》(2002年,北京红门画廊);《王玉平》(2002年,台湾观想艺术中心);《鱼》(2004年,瑞士日内瓦Leda画廊);《天光》(2005年,上海张江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年度提名展——2011王玉平》(2011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市井浮世绘》(2011年,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台北-北京》(2013年,台湾诚品画廊)。
曾举办联展:《首届中国油画展》(1987年,中国美术馆);《申玲、王玉平作品展》(1988年,中国美术馆);《新生代艺术展》(1991年,历史博物馆);《申玲、王玉平作品展》(1993年,中国美术馆);《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展》(1993年,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批评家提名展》(1994年,中国美术馆);《当代中国油画展》(1994年,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第二届中国油画展》(1994年,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作品展》(1995年,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第三届中国油画展》(1995年,中国美术馆);《首届中国油画学会展》(1996年,中国美术馆);《第四十七届威尼斯双年展》(1997年,意大利威尼斯)《98福州亚太地区当代艺术邀请展》(1998年,福州画院);《中国绘画50年》(1998年,日本东京日中友好会馆);《中国百人小油画作品展》(1999年,中国美术馆);《中国当代艺术展》(1999年,美国旧金山);《第一届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展》(1999年,沈阳东宇美术馆);《世纪之门·中国艺术邀请展》(2000年,成都现代艺术馆);《中国油画百年展》(2000年,中国美术馆);《第三届上海双年展》(2000年,上海美术馆);《Red Hot中国当代艺术特展》(2001年,北京红门画廊);《学院AND非学院》(2001年,北京艺博画廊);《迹象·未来》(2001年,北京艺博画廊);《首届北京双年展》(2003年,中国美术馆);《第二届北京双年展》(2005年,中国美术馆);《第二届美术文献展》(2007年,湖北省艺术馆);《十年一觉》(北京和静园艺术馆);《拓展与融合——中国现代油画研究展》(2008年,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素描60年》(2009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申玲、王王平作品展》(2010年,北京今日美术馆);《中央美院造型学院教师作品展》(2010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手头、笔头》(2010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时代肖像——当代艺术30年》(2013年,上海当代博物馆);《大阪双年展》(2010年,日本大阪);《中国新表现主义,(2014年,上海中华艺术宫);《第二届中国油画双年展》(2014年,中国美术馆)。
在我看来,王玉平是一位极其富有个性的艺术家,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就充满热情默默地投入进去。这么多年,他一直坚持着画画,因为他爱画画,画画能带给他幸福。他不会察言观色的去关注别人想要什么,而是用自己独特而又充满生活温情的绘画语言讲述着那些生活中的真善美。
王玉平一直坚持以写生的方式进行艺术创作,但是他却与传统的写实绘画不同。传统的写实绘画更多的是追求逼真地再现现实生活中我们肉眼可见的客观世界,通过对绘画对象本身的描绘来表达那种真实感。王玉平的绘画虽然没有刻意的追求那种逼真再现的描绘,但是他的画却能给人一种扣人心弦的真诚和真实感。就像他的夫人(艺术家申玲)在随笔里面写到的北京市民在看到王玉平写生画《铃铛胡同》的时候说的一段话那样“您说来咱这种楼画画的人每年可真不少,有好多学生,也有老师,可真就没他画的好,瞧着就那么真着,一看就知道是咱铃铛胡同,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这功夫下深喽。”王玉平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种真实感上的认同是因为他赋予了他的画面更多更深层次的东西,这种更深层次的东西就是他对真实生活的体验上升到精神层面的感悟与智慧,运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描绘出自己身边最真实的模样。有业内人士曾经说过王玉平的画是难得的雅俗共赏,接地气,又有国际范儿。他的画之所以受到大众的喜爱是因为他的画面所流露出的真情实感,是生活中一些真实真挚的东西,没有虚假美化,因为没有人喜欢谎言。以儿时的心态、今天的眼光创作就是王玉平的创作态度,正如他所说:“我拎着画具,在城里瞎转悠,像初学画画的孩子,不必有思想,也没有负担,哪儿都能画,怎么画都行,画好画坏无所谓。只是用这个方式温习着过去,打发着现在,又晒了太阳”。
正如王玉平的“画北京”系列作品,天空的颜色,看到的每一张都是不一样的心情,好像这些天气你都经历过一样。王玉平笔下的古建就像他在自己的随笔里描写的那样:“北京的古建从小已经看惯了,今天让我更感兴趣的倒是它们和周围现代因素共处一境,各种交通标志、信号灯、电线杆和上面交错的探头、墙上怎么也咔哧不干净的小广告还有伸向天空的树的姿态,实在是今天的北京才有的景象。”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画里面会有那么多横贯画面的电线,笔直的电线杆、路灯,各种颜色形状的标示牌,还有扭曲着伸向天空的各种姿态的树枝,因为他感兴趣的点在那里,这也正是他的画能够撩人心绪的原因。这让我想到罗丹的一句话:“当一个艺术家,故意要装饰自然,用绿的颜色画春天,用深红的颜色画旭日,用朱红的颜色画嘴唇,那他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丑的——因为他说谎。”王玉平正是从反面印证了罗丹说的这一点,因为他的创作是真实的,所以他创作出来的艺术是美的,大家喜欢他的作品。
王玉平还有一大部分的人物写生创作,其中很有意思的是《包办婚姻》和《老来伴》这两幅。王玉平还写了随笔《老来伴》来描述他的画面:
大妈姓可,大爷姓冯,他俩是一对老夫妻,家住在美院附近,退休了,闲着没事常来美院做做模特。
大妈精力好,爱聊天,听她说俩人的父辈早年在一块做生意,因为两家处的好,就给他俩定了娃娃亲,一直过到七十多岁,有一双儿女。
大妈说他们的婚姻是包办的,平时没话,不幸福。
每天来学校上课,他们也是各走各的,大妈说她愿意跟老头一块走,大爷不等她,吃了饭就早早一个人跑了。大爷性格内向,不言语,爱看书,经常抱着一本《中医药理》,或是翻看我画室的书架。跟大爷讨教点中医的知识,大妈在旁边嗤之以鼻:“他原来就是工厂医务室的,屁都不懂,甭听他瞎说。”也不见大爷生气,嘟囔几句,接着聊我们的。
有天中午休息,我跟大爷说:“您对大妈好点呗,给您养了儿女,做了一辈子饭,真要是大妈生气,不管您了,那您可就惨了”。
第二天见着大妈很高兴,说昨天晚上吃饭,大爷给她播了一筷子面,说“你吃吧”。大妈说她可高兴了,大爷从来没对她这么好过。
大爷大妈做模特认真,不偷懒。
王玉平画中的可大妈和冯大爷是他在生活中多次接触、多次感受过后经历艺术的提炼高度凝缩了的形象,画面上的两个形象不仅仅是一种单纯感知的结果,它还被艺术家赋予了一种真实的情感。这种真实的情感可以从他抽象的绘画语言中体现出来。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所以艺术也不能单纯的模仿现实生活,这就要求艺术家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去粗取精,提炼出最典型、最具表现力的东西呈现在画面上。罗丹曾经说过:“自然中认为丑的,往往要比那认为美的更显露出他的‘性格,因为内在真实在愁苦的病容上,在皱蹙秽恶的瘦脸上,在各种畸形与残缺上,比在正常健全的相貌上更加明显的显现出来。既然只有性格的力量才能造成艺术的美,所以常有这样的事:在自然中越是丑的,在艺术中越是美。在艺术中,只有那些没有性格的,就是说毫不显示外部和内在的真实的作品才是丑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王玉平笔下的人物形象从视觉方面来讲并不够美丽,人物面部五官是以一种表现性的线条来表现,面部的色彩也是以一种相对主观的色块组合而成的。这种通过艺术抽象出来的绘画元素或者说绘画语言有机的组合在一起。虽然这些绘画语言组成的艺术形象不像我们脑海中幻想的艺术形象那么美好,但是这种通过真实生活提炼出来的艺术作品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因为它是经过真实的生活的日积月累所进发出来的最为珍贵的东西,那就是情感。一些让人感到温暖善良的东西,一些让人感到生活美好的东西。用王玉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其实还是愿意体会比较温暖的东西,比较坦率的,让人觉得日子还挺美好的东西。”这是王玉平的个人性格与他的艺术气质达到的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
齐白石先生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王玉平的画就妙在这似与不似之间。这是一种最为理想和谐的状态。引用托卡莱尔的一句话:“美术一旦脱离了真实,即使不灭亡,也会变得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