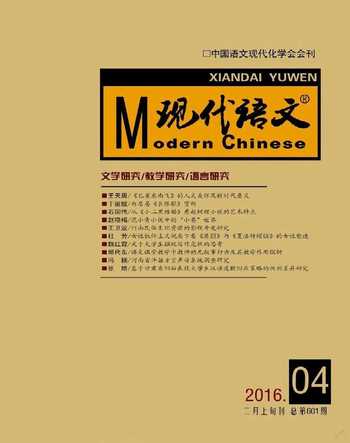论现代化语境下新乡土小说创作
2016-05-30张太兵高菲
张太兵 高菲
摘 要:《富矿》与《后土》是新乡土小说的重要作品,也是现代化语境下苏北社会生活变迁的风俗画,将叶炜的苏北新乡土小说与沈从文的湘西乡土小说比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从创作语境看,前者的创作语境是现代化,后者的创作语境是战乱;从人性书写看,前者侧重展示人性的假、恶、丑,人与人之间的倾轧,后者书写了现代化进程中人性的真、善、美,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从叙事风格看,前者是乡土写实,后者是田园牧歌;从创作主体看,前者对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后者对现实生活进行了审美过滤。
关键词:现代化 语境 新乡土小说 对比
新乡土小说和旧乡土小说是相对的。如果试图从宏观上概括这一创作现象,“新乡土小说”的概念应该包括以下两方面内涵:一是以农民为表现对象无疑承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形成的“乡土小说”的核心视角,所以仍然可以将之归入“乡土小说”的范畴。二是由于它所表现的对象往往在宏观社会经济变迁的背景下往返于城乡两域,其思想和行为展示着异质性文化价值的冲撞。从而使得这一创作在叙事空间、价值判断等方面体现出新的特点,所以,又须在“乡土小说”之前冠之以“新”。[1]《富矿》与《后土》是新乡土小说的重要作品,也是现代化语境下苏北社会生活变迁的风俗画,将沈从文的湘西乡土小说与叶炜的苏北新乡土小说对比,可以看出二者有相似的地方:创作主体都立足于自己的家乡进行创作,而且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创作产生了越界的影响;创作主体都来自农村,对农村的社会生活有深刻的体验,文本透露出对农村生活、农村发展、农民命运的思考,同时表现出了对农民的挚爱与同情;书写了农村的风俗,是不同时期的农村风俗画。但新乡土小说与旧乡土小说更有着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历史语境不同:现代化与战乱
《富矿》与《后土》创作于当下,当下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正在加速。《富矿》与《后土》以现代化为背景,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苏北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它以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冲突为主题。骨头是两种文明的冲突,肉是苏北农村的社会生活。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苏北、鲁南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农民致富的过程中,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对话与冲突中,农民内心的艰难、苦痛、挣扎,他们的希望与绝望、忍受与反抗、自发与自觉。《富矿》与《后土》同时揭示了麻庄社会生活的“明”与“暗”,以此来影射当下整个中国的社会生活。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麻庄也在进行着这种转变。在明处,我们看得见的变化很多,高速公路四通八达,高速铁路朝发夕至,铁路公路星罗棋布,开发区、新农村的建筑如雨后春笋,汽车像蝗蟲一样铺天盖地;与之相伴的是农村的青年人越来越少;影星歌星身上的衣服越来越少;清正廉洁的官员越来越少;清新的天气越来越少;而雾霾却越来越多,网络上惊世骇俗的新闻、图片越来越多,阴暗的角落越来越多,偷盗村、艾滋病村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包脓裹血的社会。《边城》完成于1934年4月19日,是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中所描写的茶峒地区原是“汉代五溪夷”,偏僻、蛮荒,为历史上犯人流放之地;苗族、土家族在这里过着原始的、自由自在的牧歌生活。至18世纪才开始推行封建宗法制度,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实行黑暗、罪恶的统治,残酷镇压苗民起义,大肆屠杀无辜的人民。青年时代的沈从文,经常目睹发生在家乡的饥荒、暴乱与杀人越货的情景,因此他从小就产生了厌恶暴力的人道主义思想。创作《边城》时,他虽然宣称创作的是“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但实际上却正是针对湘西的“现在”,为满目疮痍的现实所感发,呼唤着自由的、美好的、“牧歌”式社会的回归,并以此对湘西封建宗法制社会进行批判。作品所表现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悲剧,其实他是以一个真善美的边城,反照当时社会的黑暗、不和谐。沈从文说:我所写到的世界,即或在他们全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然而他们的宽容,他们向一本书去求取安慰与知识的热忱,却一定使他们能够把这本书很从容读下去的。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得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过去的伟大处与目前的堕落之处,以及寂寞地从事着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叶炜的苏北新乡土小说与沈从文的湘西乡土小说在创作语境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人性视角不同:假恶丑与真善美
《后土》的主人公王远是叶炜着力塑造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圆整”人物,这个人物身上集中的体现了人性的“假恶丑”。明着村民看见的是王远当村干部不拿工资,将工资捐献给养老院,暗地里王远却贪污了大量劳苦村民的血汗钱,明着王远帮助如意将她的丈夫从派出所“救出来”,暗地里他却用三千元钱买下了如意的身体供自己淫欲,在当下的农村,像王远这样趁人之危、逼良为娼、落井下石,往良家妇女流血的疮口上撒盐的村干部不少。农民在致富的道路上受到了无数这样村干部的侮辱、愚弄、蹂躏、践踏。作品以平静的口气将这些暗流呈现给读者,使我们联想起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老婆与狡猾的钱文贵。穿越麻庄,中国的社会生活亦是如此,前些年国有企业改制,明着是股份制改制破产重组,暗地里却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落入个人囊中,明着是进行新农村建设、开发区建设、高铁建设,暗地里却与王远一样在中饱私囊、破坏改革、破坏乡风民俗、败坏人心。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有打着“反孔”的旗号吃“孔子饭”的人,现实生活中同样有打着“慈善”旗号吃“慈善”饭的人,打着“改革”旗号,破坏“改革”,吃“改革饭”的人。王远是新时期乡土文学中典型形象的代表,王远的形象让我们想到的太多太多,这无疑是当代文学画廊中一个敢与《白鹿原》中鹿子霖形象比肩的形象,一个随着时代前进将会散发出无限文学魅力的典型。《后土》虽然写了阴暗的社会生活,但作家的思想却无丝毫的阴暗,《后土》延续《富矿》的思路,表现了对农民百年命运的深切关注,以此暗喻了百年乡土中国的发展进程。小说主要写了四代村干部带领群众建设家乡的艰苦历程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斗争。第一代村干部老支书和老村长是早期农村先进人物的代表,他们为建设麻庄付出了毕生心血,但因为时代环境使然,麻庄没能摆脱贫困。第二代村干部王远面对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和麻庄的现实处境,在带领群众致富的过程中,也不得不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和考验。以曹东风和刘青松为代表的第三代村干部更加具备改革麻庄以顺应时代要求的思想和能力。他们在带领麻庄群众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不得不与上一代思想保守的老人展开较量。而小说重点则在于展现了以大学生刘非平为代表的第四代村官的时代风采,塑造了新一代农民形象,有力地呼应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路。王远、曹东风、刘青松、大学生刘非平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但正是这些有血有肉的平凡的小人物,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生活的明和暗,看到了乡村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边城》中老船夫在人性上恰恰与王远截然相反,如果说王远身上体现出的是“假恶丑”,那么老船夫身上则表现出的是“真善美”。沈从文在《边城》中着重展现了人性的真善美。在老船夫身上,集中体现了边城人民古朴的民风,人性的优点。首先是勤劳、淳朴。船将拢岸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地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但不成,凡事求个心安理得,出气力不受酬谁好意思,不管如何还是有人把钱的。管船人却情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过渡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有时从神气上估计那远路人对于身边草烟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时,便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去,一面说,“不吸这个吗,这好的,这妙的,味道蛮好,送人也合式!”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解渴。管理这渡船的,就是老船夫。其次,老船夫宽容、宽厚。船总父子三人都因翠翠迁怒于老船夫。(大老)这时正想下河去看新船装货。老船夫见他神情冷冷的,不明白他的意思,就用眉眼做了一个可笑的记号,表示他明白大老的冷淡是装成的,表示他有消息可以奉告。他拍了大老一下,轻轻地说:“你唱得很好,别人在梦里听着你那个歌,为那个歌带得很远,走了不少的路!你是第一号,是我们地方唱歌第一号。”大老望着弄渡船的老船夫涎皮的老脸,轻轻地说:“算了吧,你把宝贝孙女儿送给了会唱歌的竹雀吧。”这句话使老船夫完全弄不明白它的意思。……老船夫搓着手说:“大老,听我说句正经话,你那件事走车路,不对;走马路,你有分的!”那大老把手指着窗口说:“伯伯,你看那边,你要竹雀做孙女婿,竹雀在那里啊!”老船夫抬头望到二老,正在窗口整理一个鱼网。回碧溪岨到渡船上时,翠翠问:“爷爷,你同谁吵了架,脸色那样难看!”祖父莞尔而笑,他到城里的事情,不告给翠翠一个字。“二老,二老,你等等,我有话同你说,你先前不是说到那个——你做傻子的事情吗?你并不傻,别人才当真叫你那歌弄成傻相!”那年青人虽站定了,口中却轻轻地说:“得了够了,不要说了。”二老想起他的哥哥,便把这件事曲解了。他有一点愤愤不平,有一点儿气恼。“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船总性情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这是很明白的事情。老船夫对于这件事的关心,使二老父子对于老船夫反而有了一点误会。船总想起家庭间的近事,以为全与这老而好事的船夫有关。虽不见诸形色,心中却有个疙瘩。 船总不让老船夫再开口了,就语气略粗地说道:“伯伯,算了吧,我们的口只应当喝酒了,莫再只想替儿女唱歌!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你是好意。可是我也求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以为我们只应当谈点自己分上的事情,不适宜于想那些年青人的门路了。” 老船夫被一个闷拳打倒后,还想说两句话,但船总却不让他再有说话机会,把他拉出到牌桌边去。以上所有的人物,都曾迁怒于老船夫,包括孙女翠翠有时也不能理解祖父,但是老船夫都能包容。再次,细心、慈爱。傩送爱上了翠翠,老船夫也小心试探。祖父用拳头把自己腿重重的捶着,且笑着:“翠翠,你人乖,爷爷笨得很,话也不说得温柔,莫生气。我信口开河,说个笑话给你听。你应当当笑话听。河街天保大老走车路,请保山来提亲,我告给过你这件事了,你那神气不愿意,是不是?可是,假若那个人还有个兄弟,走马路,为你来唱歌,向你求婚,你将怎么说?” 翠翠吃了一惊,低下头去。因为她不明白这笑话有几分真,又不清楚这笑话是谁诌的。 祖父说:“你告诉我,愿意哪一个?”翠翠便微笑着轻轻的带点儿恳求的神气说:“爷爷莫说这个笑话吧。”翠翠站起身了。“我说的若是真话呢?”在天保傩送兄弟俩到碧溪咀对岸为翠翠唱歌的那一夜晚,翠翠已经睡着了,可是老船夫一夜没睡,他听了一夜,一句不漏地记了下来,转唱给翠翠听。其用心之良苦,让人喟叹不已。此外老船夫身上还闪烁着坚韧、顽强、广结善缘、泽披后人等优秀品格。
三、叙事传统不同:乡土写实与田园牧歌
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形成了两大基本叙事传统:一是乡土写实传统,从鲁迅、赵树理、高晓声到韩少功,以知识分子立场、文化批判形成启蒙传统;二是乡土浪漫传统,从废名、沈从文、孙犁到汪曾祺、贾平凹,以知识分子立场、人性审美形成诗化传统。[3]叶炜是一伟非常关注现实的作家,在他的乡村书写中自觉的继承了乡土写实叙事传统,“他主张小说应该对现实生活有所启迪,对人们的思想进化有所帮助”。他说:“一段时间以来,我的写作一直努力围绕这个信条展开,无论是小说写作还是学术研究,我都企图在考察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对生活进行力所能及的干预。”他认为“文学干预生活的观点还不应该退场,至少在现在这个特殊的瞬息万变的时代,在大多数文学的受众群体还不能够很清晰地看透现实生活的丑恶之前,文学启蒙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富矿》与《后土》就是干预现实的书,现代的中国社会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变革,这个变革就是农村的城市化和农业的现代化,麻庄是整个中国农村的缩影,《富矿》与《后土》描写的是大变革时代农民唱出的交响乐,乐曲述说了农民离开土地时灵魂的挣扎,他们的欢乐与泪水、希望与绝望,对土地的背叛与热爱及留守农村干部的高尚与堕落,伪善与狠毒,倾轧与争斗。人灵魂深处的东西被作家撕裂,血淋淋的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如果你想了解农村,如果你想感受大变革时代农民的欢乐与苦痛,《富矿》与《后土》是你不得不读的作品。鲁迅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许杰、王统照、赛先艾、王鲁彦、台静农等“隐现着乡愁”的乡土作家,堪称现代乡土文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鲁迅是最早以小说的方式关照乡土的现代作家,其小说创作直接带动了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的风潮。他的小说创作多来自病态社会中疾苦不幸、麻木不仁的人民,先将他们的病痛找出,然后暴露在阳光底下,以引起救治的注意。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派以人文主义情怀和现代意识,确立起“改造国民性”的基本主题,对封建文化作全面决绝的揭露批判。他们怀着同情、忧愤与悲悯,以理性批判的眼光展现乡村的野蛮丑陋,挖掘农民的劣根性,试图以强大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力量拯救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中乡土国民的灵魂,以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后来的王鲁彦、许钦文、彭家煌、台静农是这一主题的承继者、发扬者。这种以鲁迅为标志,以知识分子立场、文化批判、启蒙主题为核心的乡土小说叙事传统,不仅成为20世纪乡土小说最重要的传统,也是“五四”精神的主要内涵。遗憾的是,它只在20年代乡土小说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中断半个多世纪后,才在80年代中期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派小说中薪火再传。寻根派小说全都取材于乡村,以知识分子身份立场,审视比鲁迅的“未庄”还要蛮荒、古朴的乡村社会,具有明确的现代追求和对民族文化的启蒙意识。批判与继承,以现代意识省思中国传统文化,是寻根小说对待本国历史传统的基本态度。他们省思的是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以及整个民族文化心理,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探寻,揭示这些传统的负面效应。“寻根”是对历史的一种梳理,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返照和省思。可以说,寻根小说完全切入了鲁迅传统,“在文化批判上深化了鲁迅精神”,而且“在现代叙事策略的探索方面,寻根小说也更进了一步”。[4]如果说鲁迅所表现的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麻木、愚昧的乡民,那么韩少功则是借麻木、愚昧的乡民省思中国传统文化,叶炜则是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农村现状的真实画卷,塑造出一群实实在在的农民形象。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他们的命运和遭遇、他们的生活和情绪,叶炜刻画的是社会主义当家做主的农民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在墨守“常”与应对“变”的过程中灵魂的挣扎,他们面对的时代环境是旧的伦理被抛弃,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灵魂无所归依的困惑,面对复杂的现实,他们无所适从,从文本中我们仿佛可以听见她们灵魂深处的叹息。沈从文的《边城》是乡土浪漫叙事传统的典型代表,《边城》充溢着牧歌气息。牧歌最早指古希腊人描写西西里岛牧羊人生活的诗。后来维吉尔写了著名的作品《牧歌》,也带典型的田园诗风格,人们便习惯称这一风格文类为“牧歌”。所谓“牧歌”指的是一种传统的诗歌,表达都市人对理想化的农牧生活的向往。文艺复兴后。出现一些专写古代田园生活的田园诗或散文,也是牧歌一类文体的引申。现代批评家常把那种偏于表现单纯、素朴生活,并常与现代繁复生活相对照的作品,都称作“牧歌式”的作品。刘西渭的《<边城>与<八骏图>》[5]一文中就认为《边城》是“一部idyllic杰作”。汪伟的《读<边城>》提到《边城》有“牧歌风”和“牧歌情调”,“《边城》整个调子颇类牧歌”。夏志清赞赏沈从文的《边城》是“可以称为牧歌型的”,有“田园气息”的代表作品。杨义说沈从文“小说的牧歌情调不仅如废名之具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是真正的“返璞归真”。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新乡土小说与旧乡土小说有着截然不同的叙事谱系。
四、主体关注不同:批判关切与过滤审美
叶炜在《富矿》与《后土》中书写了一种人生形式,就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农民在致富的道路上心灵的分化,先进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对保守、充满温情甚至有些落后的乡土生活的冲击。《富矿》与《后土》对农村生活的原生态进行了叙述,同样有着对人性之常的展示,叶炜笔下的“人性之常”与沈从文的“人性之常”有所不同。它包括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的嫌贫爱富、人的无法满足的欲望、人对贫乏枯燥生活的逃避、对现代文明和丰富精神生活的渴望及人与人之间的伤害。对于麻姑、笨妮、翠香、六小、曹东风、刘青松、王远等人来说,农村生活是“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常,生儿育女是常,麦苗、水稻、棉花、大豆是常,猪、马、牛、羊是常,鱼塘、沟坝、桃园、荒冢是常。机器是变,矿灯、矿靴、矿服是变,漫天黑雪是变,跳舞是变,发廊卖肉是变。《后土》与《富矿》同时向人们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些非常复杂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人们对罪恶的认同感,人们的欲望日益膨胀转变为恶望。比如胡列对女性的猎逐、老来对发廊老板的包养,蒋飞通与肖芳、麻姑的三角关系,李玉花和王远的私通。男盗女娼一直是我们道德上最抵触的东西,尤其是在乡土中国,但是在麻庄、麻庄矿,村民、矿工都习以为常。这折射出现代社会人们对罪恶的认同感的上升。社会越现代化人心越被掏空,在麻庄、在麻庄矿人们不再坚守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正如小说中叙写的“麻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时间在一点点改变她,她现在对一切都感到无所谓,她所做的一切都好像是为了打发时间。她的身体和灵魂都被生活掏空了,用文雅一点的词语来说,就是一切都忽然间变得虚无起来。”[6]像麻姑一样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日益模糊。作家对这些“变”充满了惶惑和担忧。穿越麻庄看现实更让我们感到害怕。一个大学生毕业时,没人看中你论文写的好坏,学会了哪些东西,而看中你就业时找到了什么好工作;评价一个姑娘,不看她有多少学识、人品如何,而看她找到了多好的男朋友,看一个小伙子不去看他有多大的事业心、读了多少书做了多少事,而看重他手里捏着多大的权力、钱包里装了多少钱,这已经成为我们今天一个普遍衡量成功的标准。到了文化圈、演艺圈,作为一个演员如果没有绯闻,几乎被认为是极大的失败,还要千方百计的去制造绯闻、丑闻。而且读者、观众、包括知名人士都对此认同,这就是社会的“变”,也是叶炜忧思的“变”。这难道不是当下社会的真实状况吗?人们从对美好生活的美望变为欲望的无法自禁,由欲望的无法自禁变为充满恶望。沈从文先生在《边城》中为我们展示了湘西世界的人性之常,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希腊小庙,作者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7]现实生活和自然界一样,既有风和日丽又有狂风暴雨;既有鲜花玫瑰又有蚊子苍蝇;既有和平时期的安逸闲适又有战争时期的血雨腥风;既有人性的真善美又有人性的假恶丑。必须指出的是沈从文在创作中对现实生活进行了审美过滤,他将现实生活中的狂风暴雨、蚊子苍蝇、血雨腥风、假恶丑都过滤掉了,单向度的歌颂人性美好的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作品的思想力度,但是恰恰是这种“削弱”造成了读者阅读中的“疏离”。读者把文本中的“艺术真实”当作“现实存在”来接受,作品和现实之间就缺乏“张力”与“弹性”。
五、结语
通过对苏北新乡土小说与湘西乡土小说的对比,可以看出它们的历史语境不同、人性视角不同、叙事传统不同、创作主体的关注不同,正是这些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艺术世界,而这些艺术世界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遐想、无限的思考、无边的感慨。必须说明的是,苏北新乡土小说的创作更加贴近当下的社会生活、更能让我们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更生动地展示了现代化语境下小人物内心深处的希望与失望、期待與无助、无奈与挣扎、艰难与苦痛。它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新乡土小说的对社会的干预能力及创作主体的社会人生思考。
注释:
[1]邵明:《何处是归程——“新乡土小说”论》,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8年04月25日14:31。
[2]沈从文:《沈从文为什么写边城》,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4月25日。
[3]白忠德:《浅析中国乡土文学内涵及其叙事传统》,作家,2010年,第6期。
[4]白忠德:《浅析中国乡土文学内涵及其叙事传统》,作家,2010年,第6期。
[5]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文学季刊,1935年,第3期。
[6]叶炜:《富矿》,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
[7]沈从文:《序跋集〈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5页。
(张太兵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200234;高菲 安徽滁州 滁州学院外语系 239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