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书闲话(五)
2016-05-23李庆西
李庆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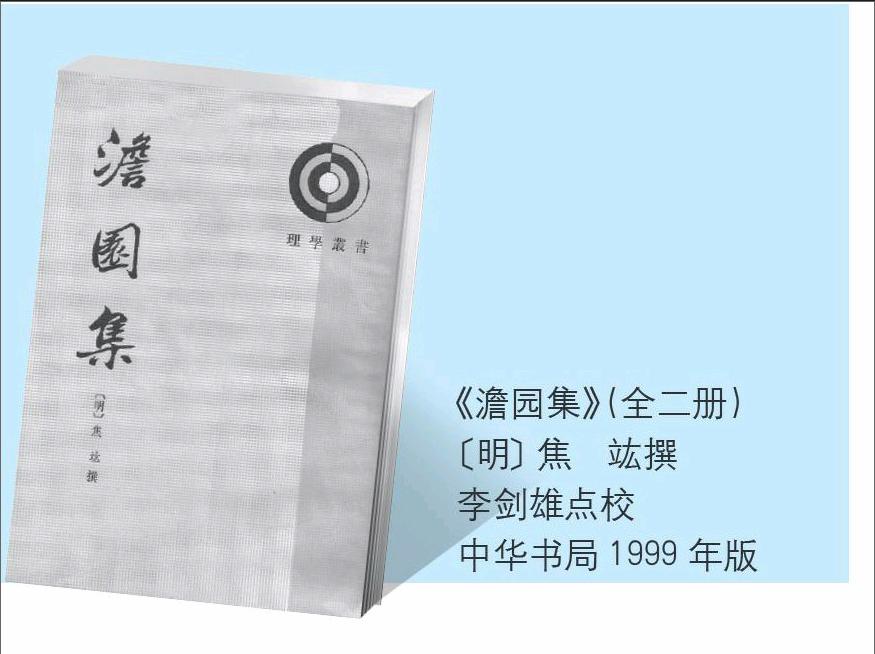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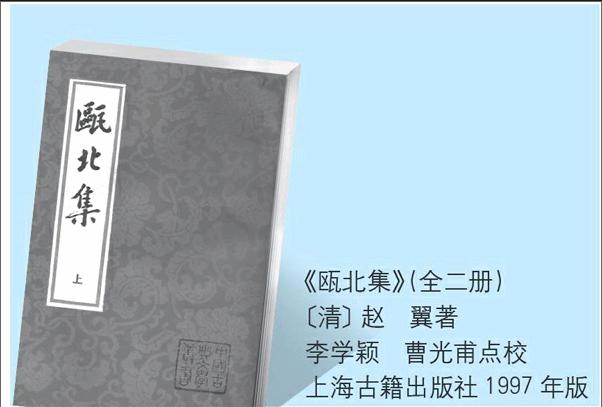
《瓯北集》
赵翼这个名字如今被人提及,主要是因其史学家身份,所著《廿二史劄记》《陔余丛考》等,都是治史者必读之书。作为清代诗人,赵翼不能跟王士禛、朱彝尊一类人物比肩,但也算颇有特色的一家,他主张“性灵”,与袁枚、蒋士铨并称“江右三大家”。这部《瓯北集》大率汇集其一生创作,收诗四千八百余首,数量之多,令人咋舌。
写得如此之多,或亦无暇细琢,学不来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不过,杜诗也有一千四百余首,何况人家只活到五十八岁,赵氏却有八十五岁高寿。其实高产诗人亦不乏佳者,南宋陆游更有九千首诗。问题似不在数量多少,好坏自须从作品本身来说。
平心而论,赵翼的诗通常显得直白,缺少某种蕴藉。“晴冲尘沙雨冲潦,经年两走长安道”,这是送别的调调;“中年渐爱逢场戏,此地聊堪对酒歌”,这是同人雅集的嘲唱;“白杨衰草黯孤坟,犹号前朝旧寝园”,这是凭吊怀古之思。赵氏做诗有点像时下玩微信。譬如湖堤散步,即口占眼前之景:“野色青于染,春流滑似膏。封鏖千树亚,浪卷半湖高。”就差将照片发到群里了。所谓“性灵”,不妨说就是心性活泛而敏感,随时都有一些小感触,些许小事便能触发滔滔诗情。家居无事,偶有所得,亦辄然赋诗:“日用而不知,凡事轻心掉。闲中试静观,无一非奇妙……此皆在眼前,格物有不到。一物一太极,谁能遍探奥。”古往今来,生老病死,天地万物,皆在吟咏之中。自然,朋友纳妾更要晒诗祝贺:“风情临老尚儿嬉,买得婵娟鬓已丝。”
“兴观群怨”的诗学传统到赵翼他们这儿显得老套了,从晚明公安三袁倡导“性灵”开始,心性随缘的近俗态度渐成时尚。这是颠覆义理的时代,自须摆脱唐人宋人的诗理与修辞。这就不难理解,学问丰赡的赵翼做诗何以造语浅近。“撑肠五千卷,纵目廿二史。”(《放歌》)故纸堆里都是当代史,雄迈之中不惮几许俗意。所以,“梨花体”与“羊羔体”破空而来,韩寒和郭敬明联袂穿越。赵翼心仪的诗人是白居易,因为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他在《泊舟琵琶亭作》一诗中写道:“香山四十六七岁,正是左迁江州日。我今亦以镌秩过,计年亦是四十七……”以白氏自况甚有逼格,不过这诗读来有些快板书的味道了。
前人评价赵翼诗,有“好见才”“好论驳”“好诙笑”之说(《瓯北诗钞》祝德麟序),自是洞中肯綮。不过,作为史学家和官员的诗人,这些并非仅仅出于情趣之好尚,他需要借助“他者”之存在表现自己的才学和诙谐。在一组描述民生疾苦的绝句中,他写道:“晓市声喧似涌涛,争营口食罄钱刀。共言米价如梯级,一步升来一步高。”(《米贵》)聆听窗外市井纷扰之际,嘲讽世态之笔付以津津乐道之情态描述,不啻是叙说众口铄金的街坊舆情。
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批评明代李梦阳等人论诗全凭耳食之论,如杜甫“全乎学力”云云,有谓“思力所到,即其才分所到”。这是注重气脉的说法。可是赵翼自己诗里差的就是这个,总是显得“才分”跟不上“思力”。
不过,赵翼诗作中却有脍炙人口的佳句,后人文章里引用率极高。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元遗山集》);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二联都以议论见长。
《晚翠文谈》
三十年前游走京师,在西坝河林斤澜府上认识几位北京作家,其中就有汪曾祺先生。当时与黄育海策划出版作家谈创作丛书,便向汪老约了这部书稿。编稿,出书,诸事顺遂,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此书出版后自己留存一册,插在书架上,不时会翻阅一下。
书中收录了汪老四十余篇文学随笔,有谈论自己的小说创作,也有评论别人的作品的,还有一些关于戏曲和民间文学的杂谈。此书结集之前,他的小说《晚饭花集》尚出版未久,许多读者从那书里的作品见识到这位新冒出来的老作家,不由拍案叫绝。其实,汪曾祺小说创作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年出过一本《邂逅集》),那时没有多大影响,八十年代初以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重返文坛,已是年逾六旬,却给人十分强烈的震撼。他那套叙事话语确实很特别,民国旧事,乡间异人,极富个性与温情。那里边没有几十年的憋屈,没有苦大仇深的火气,更没有此一时彼一时的政策方针。在谈到《受戒》的创作体会时,汪老说道:
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关于〈受戒〉》)
在《晚饭花集》自序中又说,他的小说跟那种低贱的花草一样“无足珍贵”。他不想走“高大上”一路。出语如此谦逊,内里却有十分坚韧的写作理念。显然,自重返文坛之日,汪曾祺就想着要摆脱流行已久的工具叙事(即便当时名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悲剧”写法,也还纠缠于过时的或是当令的宣传话语)。也许是出于艺术直觉,也许是蓄意而为的叙事策略,他甘愿置身“主流”之外,实在是心里另有标杆。他时常会说到他的老师沈从文,在寂寞中探索中国叙事之路径,试图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感叹道:“沈先生的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不知道为什么,多年来不被理解。”(《沈从文的寂寞》)他当然知道是为什么,这其中的原委若要讲得妥帖,须用曲折的理论语言来表述。其实不说也罢。
汪老不是那种精通文学理论的小说家,但他有极为深厚的艺术修养。他惯常从语言和审美趣味的角度来谈论文学创作。他认为语言是本质的东西,反映着对生活和表达的认识,实际上也是作家的风格与人格(《关于小说语言》)。他从沈从文的带有色彩和声音的文字里,感受到一种“摆脱浮世的营扰”的境界(《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他欣赏林斤澜的“文字游戏”,琢磨着“凭借语言来构思”的妙义,以及语言的陌生化效应,等等(《林斤澜的矮凳桥》)。其实在汪老看来,语言表达趣味各异的存在感。阿城的人物说:“待在棋里舒服。”汪老说:“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人之所以为人》)
谈语言,谈风格,谈小说的抒情性,谈传统与风俗,这些都是夫子自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的“文艺思想”要被人关注,直接谈思想就不太明智。那时候“现代派”也被认为是境外势力的别动队,汪老小心翼翼地跟卡夫卡之流作出切割。他不想招谁惹谁。在一次讲演中,有人递条子质疑他为什么写“无主题小说”,他矢口否认自己有这样的作品。他说他的小说都是有主题的,只是主题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不能讲得太死,太实,太窄”(《我是一个中国人》)。书中有一篇短文题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其中特意讲到,“有人说,用习惯的西方文学概念套我是套不上的”。借别人之口申明政治正确,乃将自己归入最稳妥的一拨。有道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躲避意识形态陷阱,逃离有争议地带,躲到一边写自己的人物。可是,将人物还原为人,不能说没有风险。汪老也忍不住要为自己专写旧人旧事作些辩解—“比如,社会主义新人,如果你看到了,可以随心所欲挥洒自如,怎样写都行,可惜在我的生活里接触到这样的人不多。”有些无奈,也很无辜,是大实话。
《饮水词笺校》
纳兰词婉丽、多情、率真,读来感触无已。三十年前,冯统一兄编校《饮水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受赐一册,闲来翻检好词好句,颇得其乐。后来冯兄与赵秀亭先生做了这个笺校本,不啻又疏通学习门径。这个集子好在有笺注、说明和辑评,可让读者了解纳兰词作的缘起、背景、修辞与用典,以及前人评析,等等。笺校者功夫做得很细,光是校订就采用了前人十五种本子参校。当然,笺注、说明、辑评俱见功力。卷二有《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一阕,唐圭璋评曰“柔肠九转,凄然欲绝”。原词见下: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这首悼亡词纪念故去的卢夫人,语词不费解。笺注引叶舒崇《纳腊室卢氏墓志铭》,谓卢氏亡于康熙十六年某月日,说明则据“三载悠悠”句,断定此阕作于康熙十九年。又举述顾贞观和作,继而说到明清时文人间“代赠”与“代悼亡”之习尚,诚以古人心肠辨述:
顾贞观《弹指词》亦有《金缕曲》“悼亡”一阕,词云:“好梦而今已。被东风、猛教吹断,药炉烟气。纵使倾城还再得,宿昔风流尽矣。须转忆、半生愁味。十二楼寒双鬓薄,遍人间、无此伤心地。钗钿约,悔轻弃。 茫茫碧落音谁寄。更何年、香阶刬袜,夜阑同倚。珍重韦郎多病后,百感消除无计。那衹为、个人知己。依约竹声新月下,旧江山、一片啼鹃里。鸡塞杳,玉笙起。”此词与容若词同调、同题、同韵,显为同时和作。卷一《采桑子》“谢家庭院残更立”阕,梁汾亦有和作。近人张任政云:“闺阁中事,岂梁汾所得言之?”似诧愕不得其解。实则言涉他人闺阁之诗古已有之,于生者有所谓“代赠”,于逝者有所谓“代悼亡”。明清之际,作诗为他人悼亡乃为文人一时习尚。如王彦泓《疑云集》有《为文始悼亡》诗;李良年有“为尤悔庵悼亡”《一丛花》词;朱彝尊则有“和梁尚书伤逝作”《凤凰台上忆吹箫》词。如此作品,数不胜数,惟代人发哀,难得其真情而已。容若词一往情深,血泪交融,真切动人;梁汾词则有“倾城再得”“香阶刬袜”诸句,非止轻俗,尤见唐突,岂容若所忍言。关于和友人悼亡诗,虽为当时习尚,然亦有非议之者。如朱慎即云:“友人妇死,而涕泗交颐,岂为识嫌疑者哉!”(见性德同时人张潮撰《友声》丁集)今学者钱锺书更讥之为“借面吊丧,与之委蛇”,“替人垂泪,无病而呻”,古之寻常事,固有难以理解者。
考订是学者功夫,理解心性、习尚则需要人情体贴。又,卷三《虞美人·为梁汾赋》一阕,盖因顾贞观不赴博学鸿词科,携《今词初集》南归镌刊,又与吴绮共编《饮水词》,性德乃作此词答之。词中以“黄九自招秦七共泥犁”与顾氏共勉,虽“堕泥犁”而不悔。笺校者说明按述:
作词而不畏“堕泥犁”,比性德略早之词人沈雄亦云:“泥犁中尽如我辈,便无俗物败人意。”(《古今词话》卷下)与性德意略近。然沈氏为放达语,意轻;性德则为决绝语,乃人生追求之郑重选择,寄意极重。
轻重之间极有分辨,非终日浸淫其间,不能有这等见识。
《澹园集》
焦竑是明隆庆、万历间士林领袖,一生著述丰赡。其作主要有《老子翼》《庄子翼》《焦氏笔乘》《焦氏类林》《玉堂丛语》《国朝献徵录》《国史经籍志》等。这本《澹园集》是他的诗文合集,包括奏疏、策问、序文、题跋、考论、书札、墓志、传状、诗赋及讲学语录等。其中经学、史学、文学无所不猎,且泛滥三教,出入百家。现在作为一般阅读,像帐词、寿序、墓表、祭文一类意思不大(对专门研究者可能是重要资料),书中这些文章甚多,可见作为名家大佬应酬写作亦颇受累(当然这类文字通常有润资)。奇怪的是,焦氏科名蹭蹬,宦途踬踣(五十入仕,六十弃官),何来这么大名声?其实,自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中间已有另一种价值标准,就是阳明心学之新思维。传统的儒学义理开始被重新解释,读书人醉心于各种异说,体制内的名位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
从焦氏若干文稿中可以看出,他的朋友圈(从师尊到弟子)尽是当时最有意思的人物:耿定向、王襞、罗汝芳、李贽、汪道昆、管志道、冯梦祯、邹元标、耿定理、耿定力、陈第、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周汝登、陶望龄、徐光启、顾起元、黄汝亨、陈懿典……等等。他们是那个年代的自由化分子,聚众讲学,四处串联,传播怀疑精神。焦竑是联结泰州学派与李贽一类异端人物之间的枢纽,故而声气甚广。他本人以博学著称,尽管思想学术标新立异,却未显现过激的叛逆姿态。
引佛入儒是焦竑改造儒学的基本策略,书中不少文章都涉及这方面话题。或许是要接入新的思想资源,或者干脆就想偷梁换柱,总之是要改变宋儒的原教旨孔孟之学。有曰:
学者诚有志于道,窃以为儒、释之短长,可置勿论,而第反诸我之心性。苟得其性,谓之梵学可也,谓之孔孟之学可也,即谓非梵学非孔孟之学,而自为一家之学,亦可也。盖谋道如谋食,藉令为真饱,即人目其馁,而吾腹则果然矣。不然,终日论人之品位,而未或一哜其胾,不至枵腹立毙者几希。(卷十二《答耿师》)
其谓“谋道如谋食”,乃以“心性”“良知”反求诸身,会通儒释,有如白猫黑猫之论。焦氏一再批评宋儒程颢之诋訾佛学,曰:“伯淳唯未究佛乘,故其掊击之言,率揣摩而不得其当。大似听讼者,两造未具,而臆决其是非,赃证未形,而悬拟其罪案,谁则服之?”(卷十二《答友人问》)又曰:“佛言心性,与孔孟何异?其不同者教也。”(卷四十七《崇正堂答问》)又曰:“内典所言心性之理,孔孟岂复有加?”(卷四十八《古城问答》)至于程氏之学,他是相当不屑,“然其学去孔孟则远矣”。他担心宋儒之僵化才是危机之由—
孔孟之学,至宋儒而晦,盖自伊川、元晦误解格物致知,至使学者尽其精力,旁搜物理,而于一片身心反置而不讲……学者为注疏所惑溺,不得其真,而释氏直指人心,无儒者支离缠绕之病。(卷十二《答友人问》)
焦氏对道家亦颇感兴趣,其辨说“老庄盛言虚无之理,非其废世教也”,认为道家之精妙在于不执圣人之迹。有谓:“仁义礼乐,道也;而世儒之所谓仁义礼乐者,迹也。执其迹而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卷二十二《读庄子七则》)以“道”与“迹”相区分,确是焦氏高明之处,相比今世之知识界人士显然更有智慧。
可惜焦竑的时代过于封闭,所能接触的知识还相当有限,真正能够利用的思想资源也主要是这儒道释三家。倘若三家有灵,实在用不着焦氏如此大费周章。
《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
本书收入六个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1935)、《虚构集》(1944)、《阿莱夫》(1949)、《布罗迪报告》(1970)、《沙之书》(1975)和《莎士比亚的记忆》(1983),总共七十篇作品。作为一位长寿作家,博尔赫斯(他活到八十七岁)小说数量不多,加上诗歌和散文,总的文字量也不算多。
当然也不少了。博尔赫斯小说带有浓厚的哲学和游戏趣味,可以让人反复阅读,而且很可能每一次阅读还有不同感受。博尔赫斯自己说过,他写这些故事,“旨在给人以消遣和感动,不在醒世劝化”(《〈布罗迪报告〉序言》)。这话有点半真半假,他极富智慧和性情的作品充满匪夷所思的幻象或是镜像,或是幻象的幻象,镜像之镜像。拐了许多个弯儿,却也是撄心之作。譬如,在《南方》《马可福音》《第三者》那些作者自己最得意的故事中,叙述法则往往就是精神与现实的错位,多半是什么顽冥不化的东西把人逼到了死角,然后就突然出现了雪崩式的变化。该解构的被解构了,不该解构的可能也被解构了。大作家注定要完成探讨命运的使命,调侃也好,悲悯也好,其心中自有承载。
《恶棍列传》中有一篇《蒙面染工梅尔夫的哈基姆》,说的是蒙面骗子的事儿。那个叫哈基姆的染工套上面具就成了先知,用一种侧供给的宗教手法将自己抬到神灵地位,然后作为上帝的“影子的影子的影子”,主宰天下大事。蹊跷的是,这故事假托来自一本阿拉伯手抄古籍,可是该书原本已经佚失,而一八九九年发现的手抄本被人认为是伪作。也就是说,骗子的故事来自于一个靠不住的文本。伪诈的伪诈是否搞成了负负得正的关系?你得自己去琢磨了。那个传说中的《玫瑰的摧毁》的阿拉伯手抄本,没准就是哈基姆本人的大作。
博尔赫斯无疑是最具颠覆性的叙述者,对传说或是见诸记载的人物、事件进行“重述”是其驾轻就熟的惯用手法,照他自己说就是“篡改和歪曲别人的故事”(《〈恶棍列传〉1954年版序言》)。其实,博尔赫斯“篡改”和“歪曲”的蓝本,往往并非实有其事的文本。他用这种文本性方式演绎事物的诸多可能,以表现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和多灾多难,于是时空的多维关系和现实的多重构成往往就呈现为迷宫式的画卷。“迷宫”和“镜子”是博尔赫斯小说里常用的意象,那些接连分岔的路径和多重折射的镜像似乎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的无限之意,但这里完全没有那种难以忍受的延宕,倒是花样迭出的变数让你应接不暇。
当然,“颠覆”和“歪曲”并不只是“重述”,博尔赫斯笔下更有别的套路。譬如,《刀疤》以人称转换颠倒英雄与叛徒的身份;譬如,《马可福音》中那个自由思想者竟播撒了造神之愿……这些反向逆求的手法不只使作品平添几分阅读趣味,更是将某些靳固不移的东西重新抖落了一遍。“颠覆”或是“歪曲”,说到底是一种批判意图。在《死亡与指南针》一篇中,博尔赫斯嘲弄世人迷恋规律的文化理念,断案者一味从犹太教的历史暗雾中去推究事物的因果关系,未料凶犯正是利用那些宗教传说布设迷障,而一切只是始于走错房间的偶然事件。其实,历史未尝不是走错房间之后的将错就错,面对那些因果倒置的文化诠释,博尔赫斯含而不露的微笑中永远带有哲学的沉思。在他最重要的作品《小径分岔的花园》中,无限中的偶然便是一个叙述主题,而如此形而上学的探讨竟采用侦探推理的悬疑手法加以表现,倒是十分有趣的文学实验。
J. M. 库切对博尔赫斯有着深刻理解。在《博尔赫斯的小说集》一文中,库切注意到博氏的文本性特点,注意到博氏的一再暗示:“说话人的自我其实并非真实的存在。”(《异乡人的国度》,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埃德温·威廉森《博尔赫斯大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谈到博氏小说,认为许多作品都带有自传性质,因而将其叙事意图归于疗救心理创伤—爱情创伤,政治创伤,想象力与情感创伤。如此而论,作者似乎要凭借那些“重述”和“重构”的故事去实现自我救赎。这种说法多少有些似是而非,因为根本没法解释博氏的仿拟手法跟他本人命运有何关系。这位滥用心理分析的牛津学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博氏的游戏态度,以及如何在游戏中颠覆现实法则—人家完全就生活在智性和文本之中。
二○一六年二月八日,丙申年正月初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