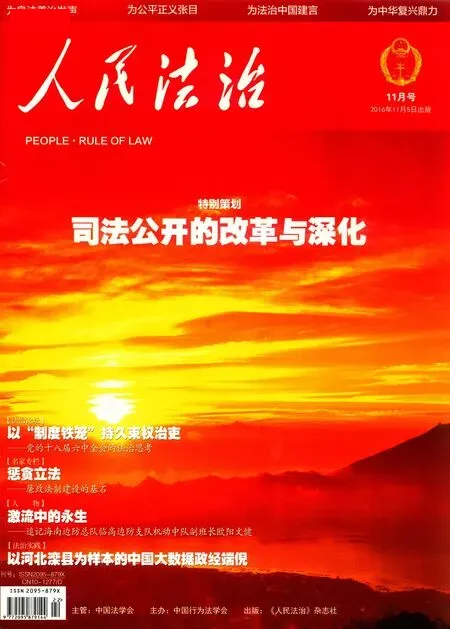加强司法透明度指数研究助推中国司法公开工作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主任田禾
2016-05-17吴燕张慧超
文/吴燕 本刊记者/张慧超
加强司法透明度指数研究助推中国司法公开工作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主任田禾
文/吴燕 本刊记者/张慧超
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院研究所的一项“拳头产品”,是一个团队精诚合作的产物。司法透明度指数的研发、评估,是法学学者走出书斋和庙堂,关注实务部门的工作、理论联系实际的成果。中国司法透明度成果直接推动实务部门不断改进工作,对于司法公开乃至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法治指数研究用数字这一最直观的形式向全世界展现我国法治的进步成果,有利于我国摆脱在法治、人权、公开透明领域长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有助于树立中国法学研究的理论自信,为施政公开的进一步推进和健康发展提供智识支持。
田禾研究员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主任、法治指数创新工程首席专家,《法治蓝皮书》主编,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她作为法治指数、实证法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接受了《人民法治》的专访。

记者: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是您带领的团队研发的,取得很大影响,可否跟我们介绍一下司法透明度指数的研发情况?
田禾: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是我们法治国情室、法治指数中心乃至法学研究所的一项“拳头产品”,是一个团队精诚合作的产物。该项目从2011年启动,连续五年向社会发布《中国司法透明度年度报告》。司法透明度指数的研发、评估,是法学学者走出书斋和庙堂,关注实务部门的工作、理论联系实际的成果。中国司法透明度成果直接推动实务部门不断改进工作,对于司法公开乃至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记者:您主导开展这项评估的初衷是什么?即推出这项指数研发和测评,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田禾:这项评估的开展,有着我对中国法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和考虑。改革开放以后,法治成为中国发展的核心关键词之一,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法学研究的重心在于引介和移植西方法学理论、法律制度。这种模式固然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实施效果大打折扣的现象并非少见。
对此,我一直在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法学研究必须要谋求创新和转型。如何进行呢?在研究对象上,要关注中国法治发展实际,研究并解决法治发展中的真问题。在研究方法上,我一直认为,有必要根据中国特色法学理论,借鉴西方的法学成果,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进行量化评估,用数字这一最直观的形式向全世界展现我国法治的进步成果,并结合实际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能够反映我国巨大进步的法治与人权保障机制与理论体系,这样可以使我国摆脱在法治、人权、公开透明领域长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树立中国法学研究的理论自信,为施政公开的进一步推进和健康发展提供智识支持。
通过设计和实施关于法治的科学客观指标,方便非法学背景的管理者和民众对民主法治做出简明、综合、具体的判断。相对于传统冗长复杂的报告、论文形式的研究成果,能显著降低理解认知难度,仅通过简单的指数、指标比较,即可全面了解中国法治现状与进步成果。我想,这也是我们推出的司法透明度等一系列法治指数测评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力、并为许多科研院所效仿学习的重要原因吧。
记者:据了解,您领导的课题组设计的指标体系得到了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广大法院的普遍认可。请问,你们是如何进行指标设计的?
田禾:的确,法治指数研究项目是跨学科、跨领域、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开放性的大型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工程。这一研究活动通过研发法治数量工具、指数与模型的设计,制定能够客观、全面反映中国法治发展进步与成就、问题与瓶颈的法治指数,为民主法治运行与发展过程中的实践与学术问题提供创新性的解决思路、科学的方法与可行的路径,并以此推动依法治国。
司法透明度指数的研发测评,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自2009年开始,我们已经在陆续开展包括政府透明度在内的一系列法治指数测评。在指数研发上,司法透明度与政府透明度指数,以及之后的检务透明度指数、高等教育透明度指数等相类似。首先,这一系列透明度指数,和我们正在实施的地方立法指数、研发的法院公信力指数等,共同组成中国国家法治总指数。其次,在指数研发上,相关之间也存在共通之处。体现了我一直强调的,要将社会学调查研究与法学研究相结合,将数量工具大规模引入法学学科建设中,致力于开发具有创新性和中国特色的法学定量研究。
当然,每个项目会根据自身特点、制度运行规律、发展阶段作出调整、完善。全国层面的司法透明度指数测评,由审务公开、审判公开、文书公开、执行公开、案卷测评、流程管理等板块组成。其具体内容,每年都会有所调整和完善。
记者:司法透明度指数的研发实施,要遵循哪些原则要求?
田禾:其原则可分为实体、程序两大方面。
在实体考虑因素上。我们在第一次司法透明度指数测评中就提出,指数设计的原则包括:一是依据法律和依据法理相结合的原则,即不但要涵盖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等对司法透明的具体要求,更要符合促进司法透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公众知情权的法学理论和基本规律。其次,指标设计坚持了客观中立的原则,即所有版块和具体指标的设定完全从是否符合法律与法理、是否有助于公众获取信息的角度考虑,且所有指标及测评方法尽量做到只测评相关功能或者相关信息的有无,而不测评其好坏,最大限度排除调研测评中的主观性。再次,贯彻了立足现状并有所前瞻的思路,即不但要体现中国法院在推进司法透明方面的实际状况,更要通过调研测评,提出司法透明发展的未来方向。
在程序上面,指标设计的程序,经过了多轮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我们组成调研组,充分研究了中国现行的有关司法透明的法律、司法解释等文件以及境外法院、中国各地法院的实际做法,并广泛征求了法官、律师、学者等的意见。最终根据法院的实际情况和公众与当事人对司法信息的需求层次,对测评指标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完善。
记者:在测评方法和实施上的特色,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田禾:与社会学相对更青睐主观性较强的满意度测评有较大不同,我们坚持使用客观数据,最大程度排除研究人员主观偏好的影响;以指标作为核心衡量手段。通过调研对象的网站,对网站信息公开形式以及重要领域的信息公开情况进行测评,为确保实证研究的客观性,尽可能精准地测评中国司法透明度,调研组摈弃了实证调研中较为常用的民调模式,在设计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法院网站的运行情况和公开内容和形式进行打分。
调研采取观察和验证的方法对有关法院网站的相关栏目和信息进行分析。调研中,为了慎重起见,凡是调查人员无法找到信息内容、无法打开网页的,均由其他调查人员利用互联网上的多个主要搜索引擎进行查找,采取更换电脑及上网方式、变更上网时间等方式进行多次验证。对于个别无网站的法院,调研组通过搜索引擎检索了其在相关媒体上发布信息的情况。
记者:这么复杂的指标、这么多的测评对象,测评工作应该有一个很大团队吧?
田禾:这是我们的理想(笑)。我们团队的人数非常有限,正式在编人员只有6人,却承担了大量的指数研发和第三方评估工作。凡是慕名来法学所交流的人,都对团队的工作量和团队的精神深感震惊,说这么大的测评项目,你们应该有一百来号人吧?司法透明度指数的测评,实际上就是三五个科研人员,几个学术助理,再加四五个学生,总共就十来号人。尽管大家都很辛苦,特别是到每年年底出成果的时候,大家忙得几乎都要崩溃了,但是一看到我们的成果对中国法治建设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家再苦再累也觉得是值得的,这种荣誉感支撑着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前进。当然,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我们也在想办法,比如向信息化要效率。通过建设法治指数的测评平台,训练成员应用好SPSS软件等措施,提高效率,保质保量完成测评工作。
记者:中国司法透明度测评这么多年,有哪些原则在坚持?是否也有些在悄悄变化?
田禾:这个问题很好,经过五六年的实施,司法透明度测评的“变与不变”,的确值得总结。
首先是“不变”,司法透明度测评,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讲,叫“不忘初心”。这么多年,司法透明度测评的设计原则不变,实施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没变,每年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是没变的——甚至可以说有增无减。其次“变”也是有的。在测评对象上,从最初的不包括自治区高院和自治区之下的较大市中院,到逐步将所有省级高院、较大市的中院全部纳入,再到将最高人民法院也纳入测评范围。这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司法透明在全国逐步成为共识,逐步消除“死角”。在指标设计上,逐步从形式考查过渡到实质考查。在我国法院普遍重视司法公开建设的背景下,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以往一些有用的指标,过两年看来,大部分法院都做得到,甚至比当年指标要求还要好。再去测评,意义就没那么大,甚至成为“白送分”。比如,第二年的测评就删去了如栏目设置、下辖法院的链接等形式要件,增加了法院预决算等财政信息指标,并增加了法院人员信息等指标的分值。这样反映出,我们考查司法透明度是全方位的,从形式到内容,从过程到结果,都属于测评范围之内。
记者:据我们了解,在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的基础上,你们还进行了一些地方司法透明度的研发,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吗?
田禾:是这样的。比较典型的有,浙江法院阳光司法指数、北京法院阳光司法指数、广西阳光司法测评等。另外,我们还对中国海事法院的司法透明度进行了年度评估,因此,我们研发的司法透明度指数评估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区域性的,还有专项的,是立体的、全方位的指数产品。
2011年,我们接受浙江高院的委托,开展浙江法院阳光司法指数的年度评估,对全省103家法院司法公开水平进行独立第三方评估,并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发布评估结果。其测评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沈德咏常务副院长的批示和认可,被认为是中国司法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必将载入中国司法改革史册,也有力推动了全国司法公开工作。相关研讨成果结集出版,形成《法治中国与司法公开》一书,产生了巨大影响力。
最有趣的是重庆市渝北区。渝北区法院听说我们的阳光司法测评之后,很感兴趣。要找我们进行测评。当时我们一口回绝,说一个法院,怎么测?测出来怎么排名?但他们特别诚恳,特别热情。经过反复沟通,他们提出说可以在整个三级法院中,把他们排进去。这样,启动了渝北区法院这“一支独苗”的测评。
今年启动的是广西全自治区法院的阳光司法测评,我们分了四个小组,深入各个中院以及随机调取的基层法院,进行实地调取案卷,这方面工作已经结束了。其他版块的测评正在进行中。
记者: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还有什么延伸的计划吗?
田禾:中国司法透明度的指数测评只是第一步。我不仅有一系列想法,并有一些付诸实施了。典型如:
一是基于司法透明度指数测评的调研、论证和境内外相关材料搜集,形成专著《司法透明国际比较》(李林、田禾主编,吕艳滨副主编,全书约340千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该书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泰国等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司法透明的情况进行了调研,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直观地展示境外司法透明的实践,分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分享了其成功的经验,并运用实证方法分析剖析了中国内地司法公开的进展和面临的问题,为法院加强网站建设、推动司法透明提供了重要参考,成为自最高人民法院到许多地方法院推进司法公开、司法网站建设,学术界研究司法公开的案头必备书。更进一步的,国际司法透明度指数的研发,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二是对法院工作更加全面深入、专题化的测评。包括正在进行的法院执行方面的测评,法院信息化建设的测评等。应该很快就能看到相关成果了。
记者:测评这么多年,司法透明度有很大的影响吧?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田禾:可以说,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是制度完善层面。基于司法透明度连续多年测评,已形成关于司法公开的多篇调研报告,对制定和完善司法公开的制度起到了极大的参考作用,获得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强烈关注、多次批示和深度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人民法院的司法公开》白皮书,以及一系列司法文件的制定讨论过程中,更是与我们团队进行了反复深入交流。
二是成果再研发层面。在司法透明度测评形成的大量客观数据基础上,结合法学原理已发表论文多篇,内部对策建言性质的要报、内参更是非常丰硕。
三是对外话语权方面。已有司法透明度引起了国际性的关注,美国大使馆、中国欧盟商会、法国使馆等国际性机构及组织先后就司法透明度相关的研究成果登门拜访,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交流。
最后是获奖,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影响力。2012年,作为中国司法透明度测评的第一次的年度总结成果——《中国司法透明度年度报告(2011)——以法院网站信息公开为视角》,一推出即获得第四届“全国优秀皮书报告奖”一等奖。中国司法透明度年度报告的重要载体,年度出版的《法治蓝皮书》,更是已多年在300多本蓝皮书中脱颖而出,连续多年获得一等奖,第一名也拿到了“手软”。
记者:田老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田禾: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司法透明度测评,以及关于法治的各项测评指标,为我国法治推动作出贡献,为中国法学话语权的形成作出贡献,也最终为全人类的法治完善作出贡献。
最后,也感谢《人民法治》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将中国司法透明建设的成果宣示于众,也期望你们立足“人民性”,为司法公开的纵深发展、司法改革的全面落实建言献策,提出宝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