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的“稿酬”
2016-05-14陈棣芳
陈棣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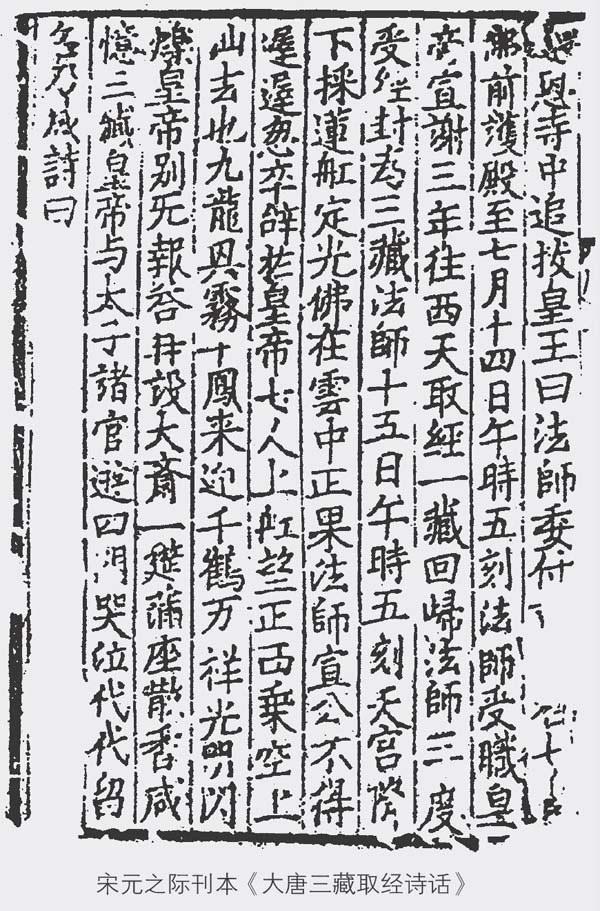
我国古代文人受人请托获取稿酬由来已久。“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这大概是我国较早有文字记载的作文受谢的例子了,“此虽无润笔字,而实为润笔之始也”,故宋人王楙在《野客丛书》说:“作文受谢非起于晋、宋……此风西汉已然。”而为这一现象定名,则是在隋代。明人彭大翼在《山堂肆考》中说:“分纪草麻,润笔自隋唐有之。”《隋书》卷三十八《郑译列传》有 “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之说。而后,润笔即成为文人稿酬的代名词。宋代文人的稿酬,又叫“润毫”“濡毫”“濡润”。
宋代文人的稿酬,根据其来源可以分为官家和私人两种。有资格接受官家稿酬的人,并非一般文人,而是翰林学士、知制诰之类的“词臣”。欧阳修《又论馆阁取士札子》云:“今两府阙人,则必取予两制。”注:“翰林学士谓之内制,中书舍人知制诰谓之外制。今并杂学士、待制,通谓之两制。”南宋赵昇《朝野类要》卷二“称谓”类云:“翰林学士官谓之内制,掌王言大制诰、诏令、赦文之类;中书舍人谓之外制,亦掌王言凡诰词之类。”
词臣接受润笔,太宗时成为定制。沈括《梦溪笔谈·内外制润笔物》:“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则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驺皆分沾。”苏耆《次续翰林志》:“先帝 (太宗)以公(指苏易简)久在内署,虑经费有阙,特定草麻(即诏书,以黄白麻纸书写)例物,朝谢日命阁门督之。既得,因以书进呈。自是无敢有阙者,迄今以为定制。”但是并非词臣的所有制词都有润笔,在宋代一般正四品以上官员受封或晋升才可以送润笔。《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文臣待制、武臣横行副使及遥郡刺史以上除改,自来亦送舍人润笔。”润笔的多寡,视被任命官员的品级而定,即所谓“旧制辞皆有润笔,随官品定数”。可见,有资格送润笔也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了。至于润笔的形式,不限于钱财,马匹、缣帛等贵重物品皆可充为润笔。
欧阳修《归田录》说:“王元之(禹偁)任翰林,尝草夏州李继迁制,继迁送润笔物数倍于常。” 继迁所送“润笔物”为五十匹马。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三记此事曰:“太宗时,禹偁为翰林学士,尝草继迁制,遗马五十匹以备濡润,禹偁以状不如式,却之。” 杨亿草寇准拜相麻,“其间四句曰:‘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之器,不露锋芒,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胸中事。例外别赠白金百两。” “白金百两”既是“例外”,常例必定尚有所赠。按照南宋惯例,册皇后时,“先一日,宣押翰林学士锁院,草册后制词,赐学士润笔金二百两”。
受封或晋升的官员往往不自觉送润笔,这一现象在宋代似乎司空见惯。苏耆《次续翰林志》:“草麻润笔,自隋唐以来皆有之。近朝武臣移镇及大僚除拜,因循多不送遗。”对乞文吝馈、督之不送者,草词官往往自己出面索要,并且,索者、送者均不以为怪。《蔡宽夫诗话》亦载:“其后有当送而不至者,往往牒催。”《归田录》卷一:“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为怪也。”
词臣所得润笔,并非草词者专享。王珪《免学士院润笔札子》:“学士院故事,凡润笔,并与见在院学士均分。”《梦溪笔谈》中也载“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驺皆分沾”。然而,润笔与“见在院学士均分”成为定制,则是在杨亿之后。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十 “杨文公辞诰润笔与同列均分”条:“杨文公亿,以文章幸于真宗,作内外制。当时辞诰,盖少其比。朝之近臣,凡有除命,愿出其手,俟其当值,即乞降命。故润笔之人,最多于众人。盖故事,为当笔者专得。杨以伤廉,遂乞与同列均分。时遂著为令。”这说明,在杨亿之前,润笔是执笔者一人专得;自杨亿开始,才与同列均分,此后成为惯例。
沈括《梦溪笔谈·内外制润笔物》:“元丰中改立官制,内外制皆有添给,罢润笔之物。”但实际上润笔并未彻底罢弃。哲宗元符二年九月七日晚,翰林学士蒋之奇草刘妃为后制,“翌日,降制讫,遣中人赐对衣、金带银五百两于学士院”。王宇《玉堂赐笔砚记》记其为学士时曾夜召至禁中草拜免宰相制,“翌日,入侍经筵。上曰:词颇逮意。既退,遣中使至玉堂,赐臣笔砚等十三事,皆当日殿中所设,上所常御者:紫青石方砚一,琴光螺钿匣一,宣和殿墨一,斑竹笔二,金笔格一,涂金镇纸天禄二,涂金砚水虾蟆一,贮黏麴涂金方奁一,镇纸象尺二,荐砚以紫帕,匣以黄方……” 周必大记南宋时受赐于禁中的情景说:“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滴之属,几二百两,既书除目,随以赐之。隆兴初犹用此例。乾道以后,止设常笔砚而已,退则有旨:打造不及,例赐牌子金百两。立后、升储倍之”。能受到皇帝笔砚赏赐,是翰林学士最引以为荣的,所以王宇说他自己“幸以词命为职,乃被赐人主所御笔砚,则知翰苑职亲地近,非他要官比”,是“词臣之极荣也”。在士人们心中,这种润笔的意义,显然是一般润笔远不能比的。
翰林学士受命作碑铭也可得润笔。王珪受诏撰卫王高琼、康王高继勋神道碑,获“银绢各五百两匹,金腰带一条,衣一袭”。周必大为书写韩世忠神道碑,其子韩彦古送“金器二百两充润笔”,周必大觉得“义有未安”而不受,并向孝宗上《辞免润笔札子》陈情,结果皇上御笔批复:“依例收受,不须恳免。”
宋代文人受人请托作文,也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润笔。当时请人作诗,是要送润笔以为酬谢的。宗室赵士暕请陈师道题《高轩过图》诗,后来赵氏“赠以十缣”。宋末方回,凡有人请其写诗序,都需得钱入怀后才肯动笔:“市井小人求诗序者,酬以五钱,必欲得钱入怀,然后漫为数语。”蔡君谟(襄)既为《集古录》书序,欧阳修亦 “以鼠须粟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为润笔”。北宋著名学者李觏曾为某僧撰《新成院记》,僧以“十千润笔”。古代铜钱以千钱为一贯,十千钱也就是十贯。因润笔太过低廉,友人为之抱不平,写诗说:“田翁不知价,只得十千钱。”
宋代墓志碑铭润笔,相当丰厚,这可能与民间树碑风气盛行有关。北宋元祐间赵挺之曾对黄庭坚说:“乡中最重润笔,每一志文成,则太平车中载以赠之。” 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三“埋铭”条:“陆经多与人写埋铭,颇得濡润。人有问:‘子履近日所写几何?启曰:‘近日写甚少,总在街上喝道行里。”可见陆经从事此道,平时获利甚多。周邦彦曾为大臣刘昺的祖父作墓铭,刘昺“以白金数十斤为润笔”。宋末元初赵孟頫为“罗司徒奉钞百锭,为先生润笔”,请胡汲仲为罗父作墓铭。宋曾慥《高斋漫录》:“欧公作王文正墓碑,其子仲议送金酒盘盏十副,注子二把,作润笔资。” 张端义撰《贵耳集》载,吴傅朋为席大光母写碑铭,大光“以文房玩好之物尽归之,预储六千缗而润毫”。孙觌常应邀“为人作墓碑”。晋陵主簿丧父,请觌撰碑铭,并许诺“文成,缣帛良粟,各当以千濡毫也”。觌欣然落笔,极力褒美。不料墓志刻成后,“遂寒前盟,以纸笔、龙涎、建茗代其数”。但孙觌还是因为常为人撰墓碑而家用丰饶:“孙仲益每为人作墓碑,得润笔甚富,所以家益丰。”
作文不收受润笔者也大有人在,且往往成为士林美谈。《容斋随笔》载:“曾子开与彭器资为执友,彭之亡,曾公作铭,彭之子以金带、缣帛为谢。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尽朋友之义,若以货见投,非足下所以事父执之道也。彭子皇惧而止。此帖今藏其家。”宋周密《癸事杂识》载,张孝祥知京口时,多景楼落成,张孝祥为大书楼匾,“公帑送银二百两为润笔,于湖却之”。 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云:阊门之西有姚氏,素以孝称。所居有兰瑞堂,东坡尝为赋诗,姚致香为惠。东坡于虎邱通老简尾云:“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遣,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与收留无异。实为他相识所惠皆不留故也。切为多致此恳。” 苏轼因从不受人润笔物,故托人还之。名臣范仲淹也不收润笔。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六十载:“范文正公为人作铭文,未尝受遗。后作《范忠献铭》(范忠献即范雍谥号),其子欲以金帛谢,拒之。乃献以所蓄书画,公悉不收,独留《道德经》而还书。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宝,仲淹窃为宗家,惜之毋为人得也。”范仲淹替人作碑志只收一本《道德经》,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相比那些声名显赫的文章大家,地位卑微、落魄的士子只能以“鬻文”自给。售卖诗文获得的收入其实也是润笔的一种形式。北宋时汴京有一位张寿山人,自言“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宋初苏州人许洞,曾卖诗还酒债:“许洞以文辞称于吴,尤邃《左氏春秋》,嗜酒,尝从酒家贷饮。一日,大写壁作歌数百言,乡人竞来观之,售数倍,乃尽捐其所负。”曹希蕴也经常卖诗,《桐江诗话》载:“曹希蕴货诗都下,人有以敲梢交为韵,索赋《新月》诗者。曹诗云:‘禁鼓初闻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梢。谁家宝鉴新磨出,匣小参差盖不交。” 吕惠卿知扬州时,扬州“有吕川者卖诗于市,句有可采者。常与吉甫赓和”。王炎在《双溪类稿》卷二十五《二堂先生文集序》中自谓“年十四五,学作举子文字”,“其后挟琴书鬻文以糊口”。同卷《南窗杂著序》亦称:“其不肖孤某,用先大夫之学侥幸登科。处则鬻文,以补伏腊之不给;出则随牒转徙,糊其口于四方。”刘斧《青琐高议》别集卷之一 “西池春游”条中云,潭州人侯诚叔“久寓都下,惟以笔耕自给”。 “笔耕自给”,即卖文糊口的文雅说法。括苍吴斯立 “客诸侯耳,方栖栖焉,鬻文以自给”,并赡养老母,时人真德秀称赞“此斯立之所以为贤也”。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贾廖碑帖”条曾记载婺州人王用和为贾师宪摹拓碑帖,“贾大喜,赏用和以勇爵,金帛称是”。宋末曾子良 “累任至建德府淳安令,甫三月,国事变,归隐山中,鬻文以自给”。
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文人的经济意识日渐增强,文章也和其他商品一样,可以随行就市自愿买卖,只不过从事这种营生的收入只够勉强糊口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甚至出现了专门卖售文字的铺面。陈藻在《赠故乡人》诗云:“我家已破出他乡,如连如卓方阜吕。岂料囊金随后散,一齐开铺鬻文章。”吴自牧《梦粱录》载:“衣市有李济卖酸文,崔官人相字摊,梅竹扇面儿,张人画山水扇。”“卖酸文”铺面的出现固然是宋代文人生活所迫,但也反映了文人商品意识的萌芽和社会对文人智力劳动成果商品化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