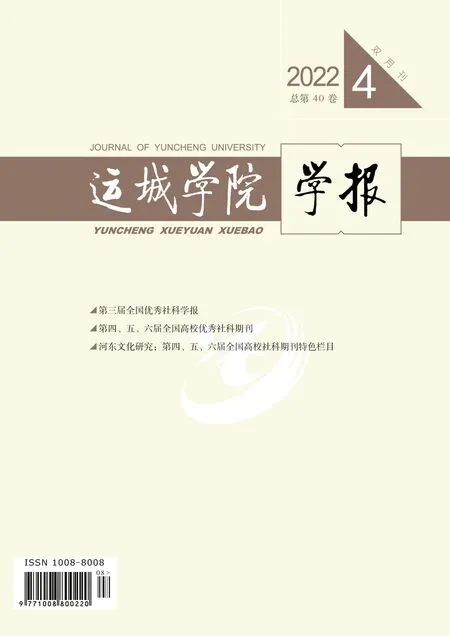中晚唐翰林学士权力运作方式与政治参与问题
——以德、顺两朝为中心
2022-03-17朱子豪
朱 子 豪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西安 710100)
在唐玄宗时出现,并在唐代中后期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翰林学士,是在唐初秦王府“十八学士”、弘文馆学士等基础上发展而来。唐初李世民在秦王府设置文学馆并设置学士以供参谋:“擢房玄龄、杜如晦一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直更,宿于阁下,讨论坟典”[1]6,秦王府“十八学士”在李世民即位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李世民即位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置了弘文馆学士:“贞观初,置弘文馆学士,听朝之隙,引之大内殿讲论文义,商较时政,或至夜分方罢”[1]7。武则天之时,又发展出“北门学士”以参议朝政。玄宗于开元初设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2]7834后又于开元二十六年另设学士院,由于与翰林院同在右银台门内,因此被称为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在唐代中晚期的中枢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免三公宰相、命将相,皆出于斯”[1]10,是唐代中后期政治的重要参与者,为历代史家所重视。德顺两朝更是翰林学士权力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应当关注。
对于德顺两朝翰林学士与政治的关系,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刘后滨从制书成立的角度出发,通过研究制书成立过程中不同官员的作用,认为翰林学士在中晚唐政局中与枢密使、中书门下组成新的中枢“三巨头”[3]。袁刚从唐代中枢决策体制演变的视角出发,认为通过德顺两代的发展,以翰林承旨学士的设立为标志,翰林学士在宪宗时与中书门下、枢密使共同构成了新的中枢行政体制[4]。毛蕾则以皇帝更替为脉络,研究不同时期翰林学士与中枢政治的关系。她指出在德宗前期翰林学士受到猜疑、迁转极慢;泾原兵变后则逐渐倚重翰林学士;顺宗时翰林学士地位有所下降[5]。对于宦官与翰林学士的关系,袁刚认为虽然反对宦官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与“甘露之变”最终失败,但还是对宦官产生了一定约束[6]。王永平考察了翰林学士与宦官既互相利用又矛盾重重的独特关系,而中唐之后日益加剧的朋党之争促使翰林学士逐渐成为拥有兵权的宦官势力的附庸[7]。赵雨乐指出在南衙北司之间的斗争中,作为一支新兴的对抗宦官的政治势力,翰林学士为宦官所不能容。宦官通过设置翰林学士院使,逐渐取得了对翰林学士的控制[8]。戴显群对唐后期中枢政治作了细致的梳理,并认为唐代翰林学士凭借学士院位于禁中的优势,在与宦官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9]。傅璇琮在对唐代翰林学士史料详细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研究唐代翰林学士的重点在于关注他们参与政治的方式和心态,并且应重视个案研究。他认为永贞革新是翰林学士与宦官集团之间的一场政治斗争,导致翰林学士最终失败的原因是他们不能齐心协力,虽然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却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10]。同时,傅璇琮也认为德宗朝是翰林学士职权演化的关键时期,并以陆贽为例来说明如何客观的分析史料,进而合理地判断翰林学士的权力,从而避免过高估计翰林学士的作用[10]。叶炜从翰林学士与宰相议政方式的差异这一角度入手,提出了皇帝在政务信息流通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进而明确了翰林学士对皇权的依附性[11]。许辉也对德宪两朝翰林学士与政治进行了论述,对德宗与宪宗时期翰林学士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探讨[12]。
对于翰林学士问题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以前,前辈学者主要对翰林学士的人员构成进行考证,以补充中晚唐时期史料的缺失。自80年代以来,学者主要研究方向转变为翰林学士在唐代政局中所起的作用,不过主要集中于翰林学士与宦官关系、翰林学士侵夺外朝权力等方面,对于理解中晚唐政治体系中不同于唐前期的新变化很有帮助,但是对于翰林学士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对于翰林学士这样一个群体,我们不应只关注于它的一个侧面,将翰林学士从中枢权力结构的整体中剥离出来,而应当将翰林学士权力发展变化的情况与中晚唐时期皇权寻求重振的大背景相结合,考察紧急事件下皇帝对政务处理的问题与翰林学士的权力运作方式。
一、肃、代两朝翰林学士权力的变化
唐玄宗设立翰林学士与当时日益变化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由于初唐时期严谨的法典化职官体系已无法满足治理需要,在以皇帝和宰相为代表的统治集团走向政务化的同时,唐王朝也采取大量任命使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受皇帝委派,直接向皇帝负责。翰林学士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设立的一个差遣之职。翰林学士在此时得到了重视,逐渐侵夺中书草诏之权。翰林学士权力的发展,与这一时期的社会动荡局面密切相关。
(一)肃宗朝统治危机对翰林学士权力发展的影响
安史之乱时,翰林学士草诏权的扩大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肃宗在灵武凤翔事多,草创权宜济急,遂破旧章,翰林之中始掌书诏”[1]15,由于肃宗于灵武仓促即位,在这种特殊时刻,内廷官员得以打破常规、委任要职,翰林学士得以“始掌书诏”。此时翰林学士所掌制诏权,主要针对于由皇帝从内廷直接发出的诰命,称为“内制”,内制用白麻书写,与由中书舍人执掌的用黄麻书写的外制相区别。自此之后,重要事务多由翰林学士草诏。“两制”的出现,是翰林学士对外廷中书舍人草诏权的侵夺。此时的翰林学士,已开始主动、积极地参与政治。如中唐著名文士苏源明,在天宝十五载六月安禄山攻陷长安后,不受安禄山伪职。苏源明的坚贞行为在肃宗回京后获得了嘉奖:“肃宗复两京,攉考工郎中、知制诰”[2]7161,在第二年即乾元元年五月,由考工郎中、知制诰正除中书舍人,不久即以中书舍人入为翰林学士[10]142。在翰林学士任上,苏源明积极参议政事“是时,承大盗之余,国用乏屈,宰相王玗以祈袴进,禁中祷祀穷日夜,中官用事,给养靡繁,昭应令梁镇上书劝帝罢淫祀,其它不暇及也,源明数陈政治得失”[13]5772。可以看出,苏源明的上书意味着此时的翰林学士已经不再只是起到备位顾问的作用,而是对时政积极参与,这是玄宗朝所未有的状况。
(二)代宗朝翰林学士权力发展状况
与肃宗时期翰林学士的发展相比,代宗之时翰林学士并未在政治权力的扩张中进一步取得优势,这或许与代宗由宦官拥立即位不无关系:“乙丑,皇后矫诏诏太子。中官李辅国、程元振素知之,乃勒兵于凌霄门,俟太子至,即衙从太子入飞龙厩以俟其变。是夕,勒兵于三殿,收捕越王傒及内官朱光辉、马英俊等禁锢之,幽皇后于别殿。”[14]286由于代宗在宦官拥立下即位,作为拥立者的宦官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等以拥立之功,加之掌控禁军,成为重要的政治集团;后鱼朝恩掌权时“凡诏会群臣计事,朝恩沽贵,诞辞折愧坐人出其上,虽元载辩强亦拱默”[13]5864,由于宦官凭借其掌握禁军的优势干预朝政,扰乱了正常行政体制,这一时期的翰林学士受其影响,权力受限,只能作为皇帝制衡各个政治集团的工具,代宗由于扶持外朝宰相元载以打击宦官而使得元载专权,在铲除鱼朝恩之后,为遏制其政治势力,代宗任命与元载不和的李栖筠为御史大夫:“以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14]300。代宗通过翰林学士内诏出命,提拔李栖筠为御史大夫,而外廷毫不知情“及白麻所出,内外震肃”。可以看出,代宗利用翰林学士草诏之权,绕过外朝体系任命李栖筠以制衡、削弱宰相权力。代宗凭借其政治手段不断扶持各方势力以达到政局的平衡与稳定,而此时的翰林学士,由于深处禁中、为天子近臣的关系,不断被皇帝利用。但是纵观肃代之际“台辅伊说之命、将坛出车之诏、霖洽天壤之泽、导扬顾命之重,议不及中书矣”[1]112,翰林学士的制诰之权依旧被认为不如中书舍人。在至德、大历年间政局的发展中,翰林学士多数情况下也只是谨守本职而已。
二、翰林学士权力运作形式对德宗、顺宗朝政治的影响
德宗朝是翰林学士权力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德宗朝初期,翰林学士权力与代宗时期相比并无显著变化。在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驾崩之后,德宗继位之初便启用张涉为翰林学士“德宗在春宫,受经于涉。及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访以庶政,大小事皆咨之,翌日,诏居翰林,恩礼甚厚,亲重莫比”[14]3577。德宗任命张涉为翰林学士,诸事都与张涉商量,但这更多的是由于张涉与德宗私交亲密,才能对时政频繁干预。张涉能发挥权力的前提,是德宗的信任,所以并不能说此时的翰林学士在政治上的作用有多么重要,但是德宗以亲信担任翰林学士,也体现了学士在皇帝心目中的独特地位。
直至建中四年的泾原兵变,翰林学士才真正在德宗朝的中枢格局中确立自己的位置。泾原之变是翰林学士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由于事发仓促,旧有的行政体系被打乱,翰林学士草诏权在这次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正是由于这次事件,翰林学士的行政能力得到了德宗的认可,逐步在中央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唐代中后期一个重要的差遣之职,最初设置翰林学士是使其充当政治上的参谋顾问,而在兴元元年德宗“诏翰林学士朝服班序,宜同诸司官知制诰”[13]347,明确了翰林学士朝服班次的问题,代表着翰林学士院发展的进一步制度化倾向。而以陆贽为代表的翰林学士也积极参与政治,但是关键在于,翰林学士是如何发挥权力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
(一)被动参与议事
从翰林学士设置的目的来说,被动型的侍从顾问是翰林学士主要职责,通过对皇帝提出问题的答复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应当是翰林学士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叶炜通过对德宗时期著名学士陆贽的文集分析,发现作为翰林学士的32篇奏状中,承问而对与皇帝知会类占25篇,主动提议类只占7篇[11]55。由此可见翰林学士参政的主要方式是对皇帝政务咨询的回答。被动参与议事的奏状占据主要部分,这也与翰林学士的信息来源有关,由于学士院“职在禁闱”,处于与外界相对孤立的状态,其信息来源必然受到一定限制,通过皇帝告知的信息必然是其主要信息来源。且肃宗时拥有直接奏事权的官员增多,对于这类奏状,如果没有皇帝的授予,翰林学士无法看到,也就无法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皇帝的询问便是翰林学士行使职权的重要一环,如《陆宣公奏议注》卷一《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
内侍朱翼宁奉宣进旨:缘两河寇贼未平殄,又淮西凶党攻逼襄城,卿识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陈利害封进者。[15]6
这是陆贽初任翰林学士时的一篇奏状,是德宗就朱滔、田悦、李希烈反叛,朝廷征讨叛军之事问于陆贽。“合有良策,宜具陈利害封进者”一句表明这是德宗通过宦官问策于翰林学士。在泾原兵变中,德宗长女唐安公主亡故,德宗欲造塔安置灵柩,宰相姜公辅上书,意在劝阻厚葬,德宗通过宦官将事情原委告知陆贽,希望得到他的建议,陆贽通过《兴元论解姜公辅状》和《又答论姜公辅状》为姜公辅分辨,认为“当问理之是非,岂论事之大小”[15]56,但德宗最后依旧未能听从陆贽建议,将姜公辅罢相。这是皇帝主动发问,要求翰林学士陆贽提出自己的意见。除此之外,皇帝主动发问的尚有《驾幸梁州论进献瓜果拟官状》:
右钦淑奉宣圣旨:自发洋州已来,累路百姓进献果子胡瓜等,虽其微细,且有此心。今拟各与散试官,卿宜商量可否者。[15]54
这也是德宗下诏询问陆贽对于奖赏进献瓜果者的看法。
以上几例是承问而对与皇帝知会类的奏议,从以上几例奏对中都可看出是皇帝通过宦官发问并提供信息,希望得到翰林学士的意见,而翰林学士作为提供参考意见的侍从顾问,通过奏状的形式提出建议。其意见虽不一定能全部实施,但德宗频繁地问对足以看出德宗时翰林学士在决策时所起到的影响。同时,皇帝通过对政务信息的控制,也使得翰林学士权力的发挥不得不依附于皇帝,翰林学士其实是被动地向皇帝提供参考意见,而并未主动干涉政治。
(二)主动参与议事
除了被动型议政,翰林学士还可以凭借身为天子近臣的优势,通过主动提议的方式发表对时政的意见:
俄而泾师乱,帝自苑门出,公辅叩马谏曰:泚尝帅泾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夺之兵,居常怫郁不自聊,请驰骑捕取以从,无为群凶得之。帝仓卒不及听。既行,欲驻凤翔倚张镒。公辅曰:镒虽信臣,然文吏也,所领皆朱泚部曲,渔阳突骑,泚若立,泾军且有变,非万全策也。帝遂之奉天。不数日,凤翔果乱,杀镒。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请为守备。卢杞曰:泚忠正笃实,奈何言其叛,伤大臣心!请百口保之。帝知群臣多劝泚奉迎乘舆者,乃诏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辅曰:王者不严羽卫,无以重威灵。今禁旅单寡而士马处外,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内诸军。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辅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3]4832
姜公辅在泾原兵变中,对于朱泚的动态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力劝德宗驻扎于奉天而不是朱泚旧部所在的凤翔。之后凤翔的动乱验证了姜公辅的判断,而之后姜公辅再次主动言事,劝诫德宗加强防备。这两次言事,均是姜公辅在翰林学士的位置上进行的主动提议。由于当时德宗仓皇出逃,无法维持正常的政务运转,因此姜公辅的行为虽然有所逾越翰林学士的职责,但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得到了德宗的认可。在统治危机爆发、外朝政治体系崩溃的情况下,翰林学士得以主动参与政治。这也正如陆贽所说:“奔播之际,道途或豫除改,权令草制”[14]5057,翰林学士权力的扩大,与统治危机的爆发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泾原兵变中,德宗仓皇出逃,府藏委弃,以致“服御之外,无尺绢丈帛”[14]3793,之后诸藩供奉至,德宗命入琼林、大盈两库,以做私用,这使翰林学士陆贽上疏,请罢两库:“臣昨奉使军营,出经行殿,忽睹右廊之下,旁列二库之名,惧然若警,不识所以”[14]3793,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两库状》中的这一句,清晰的展示了这是他主动搜集相关信息,向皇帝提议。在兴元元年陆贽奉命出使安抚李怀光后,力谏德宗将李晟与李怀光军驻地互换,最终“及贽屡陈怀光反状,乃可晟之奏,移军东渭桥”[14]3795。可以看出,在陆贽担任翰林学士时,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才能,陆贽已突破翰林学士原有的侍从顾问的职能,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当时的中枢政局之中。但是这种主动奏议只是少数、非常态的行为,陆贽本人也很清楚这种主动奏议是逾越了翰林学士原本的职权,在他的《论关中事宜状》中,他说:“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觉妄发,辄谕顾问之旨,深测幽微之端。此臣之愚于自量,而忠于事主之分也”[15]16,陆贽为自己辩解说是由于事主之心才“辄逾顾问之旨”。翰林学士郑絪在窦文场请以白麻任命其为神策军中尉时,上奏说:“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书、门下。今以命中尉,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遂著为令邪?”[12]5075这也是翰林学士认为制书形式不合常规而主动上奏的情况。
总体来说,由皇帝提供信息,学士承问而对的情况占主要部分,这也是由于翰林学士院位于禁中,学士值宿位于内庭之中,信息来源单一,皇帝通过对信息的控制,使翰林学士成为辅助自己处理政务的机构。但在面临特殊情况时,由于时间紧迫,翰林学士在此时反而更能就面临的情况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也是翰林学士主动发挥其议政职能,突破了翰林学士职责的限制。
由于在泾原兵变中外朝官员面对危机时的无力表现,使德宗不得不依赖于翰林学士、宦官等内廷势力:“乘舆每幸学士院,顾问锡赍无所不至,御馔珍肴辍而赐之。又尝召对于浴堂,移院于金銮殿”[1]13,德宗希望通过翰林学士来巩固统治,这使得翰林学士对政治参与相较于前朝显得更加频繁、主动。但是应当注意到,翰林学士在德宗朝政局的参与程度也与翰林学士的个人能力密切相关,陆贽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奉天时,陆贽便表现出了出众的才能:“旁吏承写不给,他学士笔阁不得下,而贽沛然有余”[14]4914,陆贽在之后受到重用,与他卓越的个人能力不无关系。而除他之外的其他翰林学士,如姜公辅、吴通玄、吴通微、顾少连、韦执谊、卫次公、郑絪等在德宗朝政局中主动议事的情况则不多见。而在德宗后期,翰林学士对政治的参与及其自身的权力发展又有了新的变化。傅璇琮认为:“在陆贽被贬后,翰林学士出现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10]50,在陆贽被贬后,虽然翰林学士在政局中的参与不如陆贽时频繁,权力却日渐提升“翰林学士韦执谊及渠牟皆权倾宰相,趋附盈门”[2]7575。翰林学士权力发展在贞元后期处于一种平稳的提升中,突出表现为翰林学士任职时间之长,如郑絪、卫次公自贞元八年入翰林学士院后,一直担任翰林学士直至德宗逝世[12]199。在这种情况下翰林学士的权力处于一种不断稳固并且持续上升的态势,以致于“贞元末,其任益重,时人谓之内相”[1]15。总体上看,德宗时期翰林学士对政治的参与形式,呈现出从被动到主动的趋势。
三、特殊办公场所对翰林学士权力发挥的影响
德宗时翰林学士主要作为皇帝的辅助来参与政治,其主要职责依旧是作为皇帝的顾问来提出意见,翰林学士参与政治的方式主要为通过奏状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在顺宗时,由于顺宗身体不适无法视朝,作为可以出入内廷的翰林学士,这时便可依靠这一特殊权力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参与政治。因此顺宗虽在位时间极短,但却是翰林学士参与政治的高峰期。
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时东宫疾恙方甚,仓卒召学士郑絪等至金銮殿。中人或云:“内中商量,所立未定。”众人未对。次公遽言曰:“皇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内外系心。必不得已,犹应立广陵王。不然,必大乱。”絪等随而唱之,众议方定。[14]4179
顺宗的即位本身便与翰林学士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德宗去世后,翰林学士卫次公等人的力谏是顺宗顺利即位的一个关键因素,而正因此,卫次公、郑絪等以功臣自居,与后进的王叔文、王伾二人产生了严重分歧。
王叔文与王伾二人早在顺宗为太子之时便与其亲近,顺宗即位后任命二人为翰林学士:“壬寅,以太子侍书、翰林待诏王伾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以前司功参军、翰林待诏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14]406。王叔文任翰林学士后“欲专国政,首引执谊为相,己用事于中与相唱和”[2]7729,对外以与之交好的韦执谊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借以掌控朝政;对内勾结侍奉顺宗的牛昭容与宦官李忠言:“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与李忠言、牛昭容议事”[2]7731。通过这种内外勾结,王叔文与王伾暂时掌握了大权,时人目其党羽为“二王八司马”。王叔文凭借翰林学士院位于禁中的优势,以及翰林学士出入宫禁的方便,得以时常面见顺宗,商量国事。此时由于顺宗无法面见外朝官员亲理朝政,而翰林学士由于地处禁中,相较于外朝官员,便代表了更进一步的皇帝意志,“时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亲奏对者。内外盛言王伾、王叔文专行决断”[16]5653。在顺宗时,除却二王外,尚有郑絪、卫次公、李程、张聿、王涯、凌准、李建等7名翰林学士[17]238。这七人中除凌准外,其余均为德宗朝老臣,这也为翰林学士内部的矛盾爆发埋下了祸患“顺宗立,王叔文等用事,次公与絪等多持正”[14]4179,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学士院内部的矛盾,而卫次公等人与王叔文党的矛盾为后来俱文珍勾结翰林学士打击王叔文等人提供了可能。
由于顺宗因病不能亲理朝政,沟通内外的翰林学士便显得重要了起来:“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于中书,俾执谊承奏于外”[14]3743,顺宗时的翰林学士,已经不仅止于侍从顾问之职能,而是真正成为了中枢决策之所在。由于王叔文掌握了实际的决策权,而郑絪、卫次公等人却有翊戴顺宗登位之功,这引起了郑絪、卫次公与王叔文一派的矛盾,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矛盾的爆发焦点在于立储问题:宦官俱文珍、学士郑絪等均为“先朝任使旧人”[2]7731,奏请立广陵王为太子;而王叔文等认为不宜早立太子:“中外危惧,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恶闻之”[2]7735。在政治斗争愈发激烈的情况下,俱文珍等人率先发难:“诏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太子诏”[2]7735。翰林学士的草诏权在立太子的程序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翰林学士可以在此时面见顺宗,恐怕也与翰林学士院位于内廷,较为方便出入宫禁不无关系,这也是翰林学士作为近臣的便利之处。俱文珍对王叔文的打击便主要集中于削夺王叔文与顺宗的沟通渠道上:“宦人俱文珍忌其权,罢叔文学士,诏出,骇怅曰:“吾当数至此议事,不然,无由入禁中。”伾复力请,乃听三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旧职矣”[13]5125,当王叔文被罢去翰林学士之职后,他与顺宗的沟通被切断,而顺宗又无法视朝,这就意味着他被排除出了决策机构,这使王叔文在面对政敌时毫无反抗之力,不久后,王叔文便被贬官。
王叔文的崛起,是翰林学士通过与皇帝沟通的特殊地位来取得决策大权的案例。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翰林学士的草诏与顾问的职责,而是翰林学士可以值宿禁中的特殊性。当然,这也有顺宗身体不便、无法正常处理政务的原因。翰林学士通过与皇帝沟通的特殊渠道,得以取得相较于外朝官员更进一步的与皇权的联系。办公地点离皇帝更近的翰林学士在皇帝无法与外朝官员见面的的特殊时刻,自然在政治上有着更高的权威性,而翰林学士权力运行的特点也是其独特的地位所导致。
结语
翰林学士的出现是唐代中后期政治制度变化的显著体现,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实行决策的体制在玄宗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后正式宣告瓦解。在中央决策体系的转型时期,统治危机的爆发使皇帝需要一个更为高效和便于掌控的机构来辅助皇帝统治。自玄宗安史之乱以来,由于行政体系受到战乱影响而无法正常运转,翰林学士便充当了临时行政机构的角色,积极参与政治[18]。
德宗顺宗时期是翰林学士发展的重要时段,正是由于在这一段时间中翰林学士表现出的独特的政治作用,才促使宪宗时翰林学士院制度进一步完善,出现了翰林承旨学士,前人论述多以为承旨学士的出现是翰林学士制度化的一次重大发展[19],但这是在德顺两朝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推动翰林学士制度在宪宗时进一步完善。翰林学士始终是一种差遣之职,其办公场所位于禁中之内[20],一方面限制了翰林学士对信息的获取,皇帝凭借对信息的管控,使翰林学士只能依附于皇帝;同时也压制翰林学士本官官品的升迁,严防翰林学士结交外臣特别是宰相,造成了翰林学士“荣滞相半”的独特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特殊的办公场所也使翰林学士拥有独特的发挥权力的方式。在中央决策体系中,翰林学士是作为皇权的依附来参与政治,以翰林学士掌内制,本质上是皇帝加强专制的体现[21],而就对政治的主动参与程度来说,翰林学士在一般情况下主要通过被动奏对的方式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参与朝政,而在面临突发危机时,翰林学士才能够突破被动议政的限制,主动参与决策,而在顺宗时,由于顺宗无法理政,导致了翰林学士能够在此时依靠其出入宫禁的便利主动插手外朝政局,这也是其特殊的办公地点带来的优势。
自顺宗以后,翰林学士在中枢政局中主动参与的程度逐渐降低[22],但是作为一个行政机构,翰林学士在中晚唐政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翰林学士的发展,整体上有从临时性质的差遣向职事官转变的趋势。它的出现,也反映出专制君主不断试图以内廷侍从削弱外朝权力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