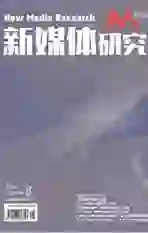基于拟剧论的视角探析日常朋友圈中“秀”的自我呈现
2016-05-14姚瑶
姚瑶
摘 要 利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的几个重要概念来研究微信朋友圈动态中个人对自我形象的塑造,以及为了维护表演在朋友圈中完美的呈现而使用的一些交往技巧。具体包括熟人圈中剧组与观众的互动模式,用户如何使用印象管理中的防御性艺术来防止表演崩溃,“秀”对他们在网络虚拟交往中起到了何种催化作用,“赞”作为符号在互动中的象征意义是如何可能的。通过这些传播学角度的分析,能够对移动互联网时代下新的人际互动交往方式有新的理解,最终理性认识传播及其技术如何嵌入且影响人的生活。
关键词 朋友圈;秀;自我呈现;拟剧论;互动交往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6)08-0026-03
1 从现实社会延伸到社交媒体中的“秀”
社交媒体时代,微信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一种社交工具,根据腾讯公司的相关数据显示,微信的平均日登陆用户为5.7亿,平均每天打开微信10次以上的用户,达到55.2%[1]。庞大的用户数量构成了一个基于网络虚拟环境下的社交圈。早起与晚睡的第一件事就是刷朋友圈。吃饭前先拍照,旅游时发风景照,女生化妆之后发自拍照,各种类型的照片充斥着朋友圈。除此之外,随时随地即时发表自己心情感想、动态及定位、生活琐事等文字内容也成了“秀”的一种表达方式。朋友圈不再是最初简单定义的“朋友”圈,而是各种秀和心灵鸡汤类杂糅的大杂烩。在这个拟态环境中,人们秀吃喝玩乐的行为就像是一场表演,为了使他人按照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看待自己,努力表演出与自己定义相符合的形象。
人们越来越热衷于“自我表露”,正如美国学者安德鲁所描述的那样,社交网络中的每个人都热衷于暴露自己——个人信息、位置、品味、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2]。从需求层面解释,人们通过“秀”来赢得他人关注;个性化前台的建立则用来标榜自我,获得身份认同;借“点赞”或评论的互动方式来维系人际关系。秀恩爱、秀富、秀颜、秀情调、秀品味等等一系列“秀”的符号共同构建了一个新的人际互动场域。
2 从拟剧论视角分析“秀”行为
戈夫曼的拟剧论认为人人都是社会这个舞台上的表演者,为了使他人按照自己呈现出来的内容看待本我角色,会通过各种印象管理技巧来操纵和粉饰自己的角色形象。这一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几个概念的学理阐释包括:角色扮演、表演舞台、演员与观众、表演剧本。下面笔者将根据这几个重要概念来缕析朋友圈中“秀”行为。
2.1 表演舞台
拟剧论中,前台是指个体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的使用的、标准的表达性装备。前台是表演者为了塑造自我而进行的理想化表演,后台则是表演者为了支撑前台的无误差表演而进行的其他表演工作。微信的表演舞台就是作为发布动态和分享内容的朋友圈,前台包括有微信头像、昵称、个性签名、封面照片等。
这些显性符号可被好友,即除本我之外的他者能直接观察到,可帮助观众或多或少的感知账号所有人的外缘信息。例如:一个朋友圈封面是卡通人物漫画的账号,其本人的年龄范围会是30岁以下;一个朋友圈签名是豪言壮志的账号,其本人应该是有进取心的或者说是想表现出自己是个进取的人。这些符号是“表达性装备中能使我们与表演者产生内在认同的那些部分”,并且由于符号之间具有关联性和前后一致性,所以前台表达出来可被直接观察的外缘信息都是稳定统一的,某个账号的朋友圈,不可能既表露出账号所有人性格深沉又传达出他幽默搞怪的特点。
与微博社交媒体的属性不同,微信是一种社交工具,其用户基数最初都是建立在实时交流的功能上,因此,朋友圈带有社会交往意义却又有其特殊性。一方面,朋友圈具有实名制性质,每一个好友都对应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个具象的熟人,且双方都知道对方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身份,这一定程度弱化了社交媒介带来的虚拟性。另一方面,由于观众与演员间无直接观察,导致互动交往中对方前台的表情动作等视觉性线索缺失。
2.2 演员与观众
朋友“圈”将账号所有人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人际脉络延展到网络上,相比于被大V占据的微博平台,我们在朋友圈中看到的新鲜事都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熟知的朋友、同事、同学等,因此,构成了双向交往关系,构成这个共同场域的人互为演员和观众。
笔者根据自己的观察对“秀”的表现进行了分类:分享体验型、标榜自我型、情感表达型。分享体验型是根据个人体验将所经历的事或物向他人分享传播,例如旅游时发的心情状态、吃饭时发的美食照片或对食物的评价等;标榜自我型是表达自我认同的诉求,包括观点、品味、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等方面,如女孩将高昂消费购物清单“晒”出来以期得到别人对她“富”的认同;情感表达型是发布动态仅是为宣泄情感或抒发情绪,例如某人为了宣泄愤怒而在朋友圈发表了大段吐槽文字。
但不管这些类型如何划分或被定义,在朋友圈“秀”无外乎都是为了得到他人关注或关注他人,因此只要使用朋友圈,那么人人都是观众也同时是演员。演员在朋友圈中即时分享着自己的动态,观众通过手机消费演员们的表演,并达成一种默契。尽管观众都知道表演者的形象是经过美化出现的,但由于观众在个人主页上也构建了一个自我表演的场域,因此,具有演员与观众双重身份的人会在互动中帮助对方完成自我身份想象而不会拆穿。
2.3 剧本
剧本就是“常规程序”,是表演主体“在表演期间展开并可以在其他场合从头至尾呈现或表演的预定行动模式”,剧本又分为一定的社会规范和个人的角色期望两个部分。在朋友圈秀场中,我们根据自己设置的剧本来进行表演行为,人们常常根据特定的情境定义做出相应的行为,尽管社交的方式被技术改变,但这种社会心理和惯性行为没有改变。例如:每到特定节日时,朋友圈就会涌现出大批“孝子”,父母生日那天也会被用来当作表演的特定情境,表演者会“秀”出自己如何为父母庆生或如何表达自己对父母的孝心。在上述特定情境中,表演者煽情的表达着自己对父母的爱意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向父母开口表达这种情感。一部分观众会对这种充斥着夸张渲染的内容感到不真实或反感,但却不会在评论里表达出自己真实想法,甚至还会出于礼节性的点赞。
在这一幕戏剧中,不管表演者是否出于真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表现出自己的孝心并且让他者认为自己有孝心。那么从个人角色期望来说,表演者对自己的角色定义中就有“孝子”这种形象并希望观众能以这种形象来看待自己;从社会规范来说,表演者在特定的情境中做出孝心和爱意的表达即使有夸张和修饰的成分,也是合乎主流价值观认可的。
另外,观众的反应行为也耐人寻味。也许某位与表演者熟悉的好友知道他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一个孝顺的子女,但他并不会拆穿表演甚至还会点个“赞”,这种表面的、虚饰的一致,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每个参与者都把自己的想法和欲望藏匿于他维护社会准则的表述之后[3]。共同处于这个表演场域中的每个人都会自觉遵守这种符合社会规范的剧本表演。
3 对朋友圈自我呈现表演的几点再思考
3.1 静态考察自我
尽管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来研究朋友圈中“秀”的行为。但这只是分析考察的一个端点,并不是最终方法。理论是用来分析和研究某种社会现象的,而不是通过对某种社会现象的研究分析来论证理论的正确性,因此在这里想通过朋友圈这个研究范本来讨论拟剧论并未涉及的
内容。
在微信4.0版本中,分组功能是最受好评的附加功能。你无法判断你的好友发布的动态是何属性,公开还是部分可见或是仅对他/她可见,这就为表演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表演者可以通过观众隔离分组分剧本表演。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有选择性的向不同群体塑造不同的自我形象。发布状态时设置“谁可以看”,于是观众被标签化,拟剧论中定义的面向所有观众的表演就失
效了。
另外,每个人的自我观念在不同的互动中是有所差别的,正如库利“镜中我”概念所表明的那样,我们通过他人对我们的看法了解我们自己,由于每个人对我们的看法都是带有主观性和唯一性的,因此和不同的人社会交往时,自我表现会区别呈现。某学生可能会在朋友圈中发表自己正在图书馆学习的照片,以博得父母或亲友的良好印象,而发表戏谑的段子脏话时会屏蔽亲友老师。这种典型的面具化表达随着自我的不同定义,自然也呈现出各异的状态。而拟剧理论在此是模糊的,演员似乎是某种稳定的永不变化的自我,这个自我在所有互动中都只是在尽可能制造最好印象,一切行为都被视作是表演的一部分。然而朋友圈中的表演并非全是失真的表演。例如:“我今天钱包丢了很难过”这类感情抒发型的内容,是纯粹的情绪表达而非角色扮演。
3.2 “点赞之交”:基于符码的互动模式
碎片化时代,人们对一掠而过的信息只能形成一个短暂印象。为了维系人际关系加深虚拟社交工具上的人际互动,人们不得不选择一种方式来反馈自己的知晓。“赞”作为一种符号文本,其核心价值在于能有效概括和汇聚“赞在特定情境下所替代与意指的想法、意义和观念,此时也就彰显出其具备的意指潜力[4]。我们可以把点赞看成是互动者主动性参与的一种情感表达,它的意义可以从赞赏、认同的层面外延到互动交往、舞台配合层面上。
从互动交往层面上来说,点“赞”包含着多种信息的流动与扩散,如各种意见情绪等。内容发布者在他人关注下体验到了自我的存在。从点“赞”的一方来说,这种互动方式可向被点“赞”者传达某些讯息:我在关注你,我赞同你的说法。这种示好行为实际上也是为了标榜自我存在,在“他者”的表演活动中加入“自我”的存在。从舞台配合层面来说,点“赞”似乎更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隐喻在双方的心理活动中。“我”为你点“赞”意味着“我”对你的关注和捧场,是对你理想化表演的认可或假装认可。那么同样的,在“我”进行表演活动的时候,希望你也能回馈以同样的互动让这场表演得以完成。这种情境定义下的点“赞”者与被点“赞”者之间维系的是礼节性的符号互动。
参考文献
[1]2015年微信平台研究数据报[EB/OL].http://mt.sohu.com/20151030/n424741512.shtml.
[2]安德鲁·基恩.数字眩晕[M].郑友栋,等,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4.
[3]2015年微信用户数据报[EB/OL].http://www.shichangbu.com/article-24563-1.html.
[4]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
[5]魏宝涛,王爽.朋友圈点赞文化与网络情绪传播[J].中原文化研究,2014(1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