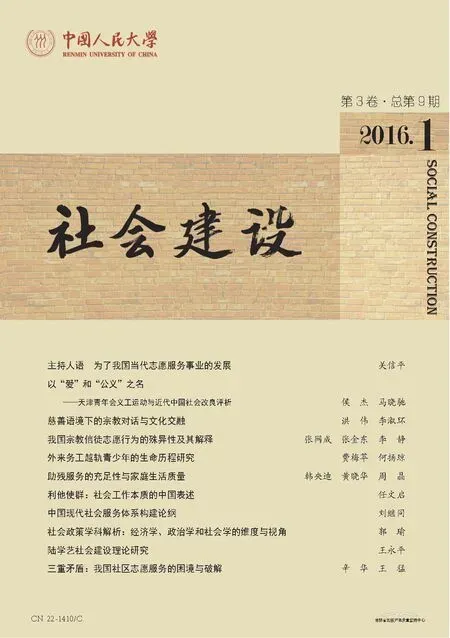我国宗教信徒志愿行为的殊异性及其解释——基于一项调查的实证分析
2016-05-05张网成张金东
张网成 张金东 李 静
我国宗教信徒志愿行为的殊异性及其解释——基于一项调查的实证分析
张网成 张金东 李 静
摘要: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基于通行的有/无宗教信仰二分法,我国宗教信徒未能呈现出比非宗教信徒更佳的志愿行为表现。通过借鉴“宗教市场”的概念,本文提出了“信仰市场”的概念,并将其三分为“现代信仰”、“宗教信仰”和“无信仰”。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一项跨省市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信仰对于个体志愿行为表现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世俗化优先”的宗教政策下,宗教信仰对信徒的志愿服务及慈善捐赠表现有显著性影响,宗教信徒的志愿行为表现虽好于无信仰人士,但远不如“现代信仰”人士。
关键词:宗教信仰;志愿服务;慈善捐赠;宗教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志愿行为(志愿服务、捐赠)是宗教信徒参与社会事务、表达和印证信仰的重要方式,在当代,也是宗教团体运行和嵌入社会的重要基础。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证明,世界各国(主要是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宗教徒(相对于非信仰人士)有着更高的志愿服务和捐赠倾向。①[美]马克·A·繆其克、[美]约翰·威尔逊:《志愿者》,魏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我国台湾地区的宗教信仰与志愿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被证实是存在的。②李丁、卢云峰:《华人社会中的宗教信仰与公共参与:以台湾地区为例》,《学海》,2010(3)。国内的相关研究不多,但研究结论也都倾向于支持宗教信仰对志愿服务③刘凤芹、卢玮静、张秀兰:《中国城市居民的文化资本与志愿行为——基于中国27个城市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和捐赠④何蓉:《当代中国宗教捐赠行为的初步研究》,《宗教社会学》,2014(2)。的影响存在。不过,这些有关宗教信仰对志愿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都是建立在有/无宗教信仰二分的基础上。⑤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的第A5题为例,调查对象首先要在“不信仰宗教”和“信仰宗教”中进行二分选择,选择“信仰宗教”的则要在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回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其他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及其他等11类宗教信仰中做选择。这样的问题设计显然不利于对信仰进行三分处理。通过比较不同宗教信徒的志愿参与水平及不同社会宗教信仰的构成,研究者试图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对不同社会的公民参与水平及社会信任度高低做出解释。⑥[美]罗伯特 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这种要么有要么无的二分法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它掩盖了无宗教信仰者内部的巨大差异:在无宗教信仰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宗教信仰但有其他信仰。宗教世俗化意味着宗教所控制的领域和权力向世俗政权和主体性个人转移,这是一个部分信徒宗教观念不断淡化甚至放弃宗教信仰的过程,但这也是一个反宗教的和非宗教的知识和信仰不断生成并逐步嵌入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的过程。在这个双向互动、彼此影响的过程中,经典世俗化理论所预言的“科学无神论”时代并没有到来,宗教仍然活跃在“信仰市场”上,但与此同时,历经几个世纪的启蒙运动中逐渐构建起来的“现代信仰”也成长为“信仰市场”上的重要选项,并且同样影响人们的志愿行为。因此,研究信仰对人们志愿行为的影响就不能仅仅考察宗教信仰,还必须考察“现代信仰”。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坚定地坚持宗教世俗化的立场,并一直给予“现代信仰”强大的政治支持,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信仰市场”结构。这一特殊的“信仰市场结构”对宗教信徒的志愿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笔者2010年主持的一项关于我国公民志愿行为的调查时已经发现,在将“现代信仰”纳入考虑范围后,我国宗教信徒在志愿服务和捐赠方面总体上并无突出的表现,甚至在有些方面还不如非宗教人士。①张网成: 《中国公民志愿行为研究(2011)》,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第39、53、87、91、102、116、124、133、149、169页。这与宗教信仰二分下的结论有明显区别。通过本文的进一步分析显示,与“无信仰人士”相比,无论是“宗教信仰人士”还是“现代信仰人士”其志愿行为表现都更佳,说明信仰对于人的志愿行为是有影响的,这与现有的研究结论又是基本相符的。笔者认为,这一特有格局的形成与我国宗教管理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二、理论框架
按照宗教市场理论,任何社会的宗教子系统都与世俗经济子系统完全类似,均由有价值的产品的供求互动构成。正如罗杰尔·芬克和罗德尼·斯达克所分析的那样:“宗教经济的构成包括现有的和潜在的信徒(需求)市场,寻求服务于这个市场的一些组织(供应者)以及不同的组织所提供的宗教教义和实践(产品)”②[美]罗杰尔·芬克、[美]罗德尼·斯达克:《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杨凤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44页。,“宗教需求长期来说是非常稳定的,而宗教变化主要是供应方面转变的产物”③同上,第238页。。不过,宗教供给会受到政府的影响。当宗教经济是无管制的和有竞争的时,宗教供给水平会不断提高,宗教参与总体程度也会随之提高;但当宗教市场因宗教管制或者宗教补贴偏离竞争而形成垄断或者寡头垄断时,宗教供给水平则会降低。④同上,第247页。为了使宗教市场理论更好地适用于解释中国宗教现象,杨凤岗提出了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理论。杨凤岗认为,斯达克等人的宗教市场理论忽略了非传统的和非制度性的宗教参与,因而得出了宗教管制会降低宗教参与的错误观点。在杨凤岗看来,“加强宗教管制的结果不是宗教信仰和行为的总体减低,而是致使宗教市场复杂化,即出现三个宗教市场,而且每个市场都有自身特别的动力学。”⑤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6)。
宗教市场理论是在否定宗教世俗化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断言宗教世俗化不会影响宗教参与这一点上,杨凤岗比斯达克等人走得更远。不过,将潜在的宗教需求都视为现实宗教市场的有效组成部分,还是有些牵强的。同时,否定宗教世俗化进程对于宗教市场的影响,也不符合事实。毕竟,与“祛魅化”之前相比,任何现代社会中坚定的无神论者都更多了。事实上,至少在现代社会,没有宗教信仰不等于没有信仰,宗教市场只是信仰市场的一部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在信仰市场上“消费”。在宗教社会子系统中,参与竞争的既有各式各样的宗教流派,也有各类反宗教的意识形态(以科学主义、进化论、人本主义、民族国家观为核心内容),还有多种多样的谈不上流派或学派的零碎的观点、见解、说教和示范。这些宗教的和反宗教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构成的“知识和规范的蕴藏之所”,本文称为信仰供给市场。宗教世俗化本身就意味着反宗教的意识形态成为信仰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和结构性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世俗化不会改变宗教市场的命题是不成立的。①张网成:《世俗化与政府管制对宗教市场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丹阳市居民宗教信仰状况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3)。据此,可以将现代社会的人口分为三个部分:信仰宗教的,反对宗教的以及超越二者之外的。
各国宗教管制政策所要调节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确定宗教信仰与反宗教的现代信仰之间的关系。“三自原则”是我国宗教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根据这一原则,信徒的奉献(志愿服务和捐赠)成为宗教组织的生存基础,有着不同信仰的宗教组织必须设法在相互竞争的宗教市场上成功“出售”自己的产品。就此而言,宗教市场理论应该是适用于解释我国的宗教现象的。不过,由于确认唯物主义和进化论教育仍是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②国宗发[1996]010号文件。,科学主义依然承担着树立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双重使命,而宗教被官方认定为“终究是要消亡的”③中发[1982]19号文件。。因此,在我国的信仰供给市场上,宗教与反宗教的意识形态之间并不是平等竞争关系,而是以“世俗化优先”为特征的。所谓“世俗化优先”,本文指的是确保唯物主义、进化论和科学主义等反宗教的思想和意识而不是宗教成为人们信仰首选项的一系列政策安排,具体由两个方面的政策构成:一是激励人们选择现代信仰的政策,包括畅通捐赠和志愿服务渠道并赋予财政扶持、税收减免和人事任用等优惠激励政策;二是抑制人们选择宗教信仰的政策。抑制宗教信仰选择的政策又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在信仰的宣传和传播上给宗教组织设置限制性条款,如规定宗教组织不能在合法的宗教场所之外从事宗教活动、规定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规定宗教不得干涉教育制度等;二是在社会资源的获取上给宗教组织设置制约性条款,如限制宗教团体设立基金会、不赋予宗教捐赠减免税收权利等。正是“世俗化优先”的信仰政策,形塑和固化了宗教组织在信仰市场上的相对弱势地位,削弱和限制了包括官方认可的“五大宗教”在内的宗教组织吸纳信徒及其奉献的能力。在这样的国情背景下,本文提出两个假设:一是信仰影响人们的志愿行为;二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士比较反对宗教信仰的人士更少志愿行为。
三、研究设计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笔者在2010年主持的一项关于“中国公民志愿行为调查”④该调查项目得到了友诚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在此表示诚挚感谢。。这次调查的对象是大陆地区18周岁以上的常住居民。样本选取采取了多阶段抽样的办法。首先,根据各地社会经济条件(以人均国民产值的高低为衡量标准)和社会组织发育状况(以万人平均拥有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多少为衡量标准),选择了北京、浙江、湖南、黑龙江、云南、甘肃等6个有代表性的内地省/直辖市。然后,参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在每个样本省/直辖市选取3个有代表性的区/县,分别代表省会或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地市级城市的一般城区和中等发展水平的县。此后,在每个区/县各选出1个中等发展水平、人口在5万左右、职业类型较丰富的街道/乡镇作为调查实施地。最后,在每个样本街道/乡镇中随机抽出了300个样本家庭供入户调查之用。六个省市最后共收集到5400份调查问卷,经严格筛选后剩5017份有效问卷。
问卷为调查对象设置了9个“个人信仰”选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人士、佛教徒、道教徒、基督教徒①本次调查问卷中只设立了基督教,而没有像CGSS调查那样将基督教罗列为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其他基督教四类,因为将基督教与天主教等并列的分类方法是存在逻辑问题的。调查中,确实发现不少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互不相认的情况。相信在调查员的解释下,绝大部分天主教调查对象都选择了“基督教徒”而不是“其他宗教信仰人士”。、伊斯兰教徒、其他宗教信仰人士及无信仰人士。题型设计为“单选”,目的要让调查对象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为了分析方便,这里将调查对象的信仰选择分为三类:一是“宗教信仰人士”,包括佛教徒、道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及“其他宗教信仰人士”五类;二是“无信仰人士”;三是既不信仰宗教也不宣称没有信仰的调查对象,本文称之为“现代信仰人士”,包括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民主党派人士三类。调查是在2010年10月份实施的,考虑到时间过长不利于调查对象准确回忆,问卷收集了受调查者在当年第三季度(2010年7月1日—2010年9月30日)从事(有组织的)志愿服务、提供个人无偿服务和进行货币和实物捐赠的情况。
志愿行为是公民亲社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调查中,志愿行为被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即有组织的志愿服务(正式志愿服务)、个人无偿服务(非正式志愿服务)和慈善捐赠。②张网成:《中国公民志愿行为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在统计调查对象在2010年第三季度的志愿行为表现后,本文将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别检验信仰是否影响人们的三类志愿行为。本文的因变量有3个:因变量1是调查对象在2010年第3季度是否有过捐款或捐物行为(捐赠过为1,未曾捐赠过为0);因变量2是调查对象在2010年第三季度是否参与过有组织的志愿服务(参与过为1,未曾参与过为0);因变量3是调查对象在2010年第三季度是否提供个人无偿服务(提供过为1,未曾提供过为0)。本文的自变量为调查对象的信仰类型,具体是一个三分变量:现代信仰人士/宗教信仰人士/无信仰人士。参照钟晓敏③钟晓敏、高琳、刘炯:《中国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及影响因素》,《公共财政评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罗公利④罗公利、刘慧明、边伟军:《影响山东省私人慈善捐赠因素的实证分析》,《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9(3)。、张楠⑤张楠、张超:《我国个人捐赠消费影响因素探讨》,《消费导刊》,2008(2)等人的研究结论,本文选择了8个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男/女)、年龄(18—34岁/35—59岁/60岁以上)、婚姻状况(未婚/已婚/其他)、学历(高中及以下/大专及以上)、月均收入(1000元以下/1000—4000元/4000元以上)、家庭收入自评估(很高及较高/一般/较低及很低)、社会信任度(很高及较高/一般/较低及很低)及职业状态(在业/学生/无业)。
四、研究结果
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见表1):(一)在参与有组织的志愿服务方面,宗教信仰人士的参与率和服务时长均低于中共党员等现代信仰人士,与无信仰人士相比,虽然宗教信仰人士的参与率要高一些,但季度服务时长却略少于无信仰人士;(二)在为非亲非友的他人提供个人无偿服务方面,宗教信仰人士无论在参与率还是服务时长上均低于现代信仰人士,仅在参与率上略高于无信仰人士;(三)在慈善捐赠方面,宗教信仰人士无论在参与率还是捐赠额度上均低于现代信仰人士,仅在捐赠总额上高于无信仰人士。总体来说,在志愿服务与慈善捐赠方面,宗教信仰人士的表现介于现代信仰人士和无信仰人士之间,说明“世俗化优先”的宗教管理政策只是部分削弱了宗教组织的动员能力。

表1 信仰与志愿行为表现(加权前)
为了纠正样本代表性偏差带来的影响,我们按照不同个人“信仰”的全国人口发布比例进行加权处理,并推算了各类志愿行为表现的全国平均数,结果如表2所示。从加权统计的结果看,现代信仰人士在志愿行为方面的表现总体上都好于宗教信仰人士和全国平均;宗教信仰人士在有组织的志愿服务和慈善捐赠方面的表现与全国大致持平,在个人无偿服务方面略差于全国平均。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将调查对象分为宗教信仰人士和非宗教信仰人士,那么就有可能看不到宗教信仰对志愿行为(志愿服务+慈善捐赠)的影响。这反过来证明,将个人信仰做三分处理是必要的。

表2 信仰与志愿行为表现(加权后)
三个二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分别是:1.信仰对人们在2010年第三季度是否曾经捐赠过在95%的置信水平上有显著影响,同时对捐赠产生显著性影响的还有学历、婚姻状况、家庭收入自评价、社会信任度、职业等5个控制变量;以无信仰人士为参照组,宗教信仰人士在该季度有捐赠行为的发生比为1.096,现代信仰人士捐赠过的发生比为1.282;2.信仰对人们在2010年第三季度是否参与有组织的志愿服务也有显著性影响,同时对志愿服务产生显著性影响的还有职业1个控制变量;以无信仰人士为参照组,宗教信仰人士参与过志愿服务的发生比为1.359,现代信仰人士参与过的发生比则为1.552;3.信仰对人们在2010年第三季度是否提供过个人无偿服务无显著性影响,对个人无偿行为产生显著性影响有年龄、学历和社会信任度3个控制变量。如果不考虑个人无偿服务,前文所提出的两个假设均是成立的。至于信仰为何不影响个体的无偿助人行为,本文无法提供非常合理的解释,只能猜测它与个人无偿服务的无组织特征有关。
为了证明现代信仰与宗教信仰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本文对于调查对象为哪些机构或通过哪些机构为第三方提供志愿服务作了梳理。从表3中可以看出,本次调查样本中宗教信仰人士提供的正式志愿服务占全部样本的16.13%,其中仅有1.31%留在宗教组织,占比8%。但宗教信徒依然是宗教组织志愿服务的最主要提供者,所占份额接近六成;无信仰人士提供的正式志愿服务占全部样本的46.17%,但宗教组织从中得到的志愿服务委托仅有0.58%,占比1.3%;现代信仰人士提供的正式志愿服务占全部样本的37.7%,其中仅有0.33%是提供给宗教组织的,占比0.87%。将政府部门、政协机构、人民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福利机构、社区组织、志愿者协会及基金会合在一起计算,可以发现官方及类官方的组织得到了近八成的志愿服务总额,说明政府在动员社会力量为己所用方面是成功和有效的。从三类信仰人士的志愿服务流向宗教组织比例看,现代信仰人士最低,仅约为无信仰人士的2/3,约为宗教信仰人士的1/9,说明政府的宗教政策虽然对不同人群的影响有差异,但总体上在管控和制约宗教组织吸纳生存资源方面是非常严厉的。这些数据上的反差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即在志愿服务市场上的竞争中,宗教组织是非常弱势的,而这种弱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的宗教政策造成的。

表3 信仰与志愿服务组织方(%)
同样,我们也对调查对象的捐赠接受对象作了梳理和分析,结果见表4。这些捐赠接受对象往往不是捐赠的使用者,而仅仅是筹集者。宗教信仰人士提供的慈善捐赠占全部样本的15.49%,其中留在宗教组织的仅有1.06%,占比6.8%,但宗教信徒依然是宗教组织慈善捐赠的最重要提供者,所占份额接近2/3;无信仰人士提供了全部捐赠的45.91%,但流向宗教组织的仅有0.43%,占比0.94%;现代信仰人士提供了捐赠份额的38.6%,流向宗教组织的只有0.13%,占比0.33%;宗教组织接受的全部慈善捐赠只占捐赠总额的1.61%,还不到个人接受慈善捐赠份额的1/5。相反的,现代信仰人士提供的捐赠占总额的38.6%,但官方及类官方组织却接受了近3/4的慈善捐赠。数据上的反差同样是鲜明的,同样反映了宗教组织在捐赠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从三类信仰人士捐赠流向宗教组织的比例看,现代信任人士最低,仅为无信仰人士的约1/3,为宗教信仰人士的约1/20,与志愿服务的流向相比,比例更低,说明政府对获取捐赠的管制更为严厉。

表4 信仰与慈善捐赠接受方(%)
为了了解慈善捐赠的实际流向是否符合捐赠者的本意,研究者还就最合适的善资使用者向调查对象进行了提问,结果见表5。宗教信仰人士中认为应该有宗教组织使用善资的比例高达15.3%,高于实际向宗教组织捐赠比例的1.25倍;现代信仰人士中认为宗教组织是最合适的善资使用者的比例为1.2%,远高于实际发生比例的2.64倍;无信仰人士中认为应该向宗教组织捐赠的比例为2.4%,高于实际发生比例的1.55倍;整体上,认为宗教组织是善资的合适使用者的比例为3.8%,高于实际向宗教组织捐赠比例的1.38倍。从这些数据的对比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宗教管制政策明显地抑制了包括宗教信徒在内的各类人士向宗教组织捐赠的意向,从而也削弱了宗教组织获取慈善捐赠的能力;二是宗教管制政策在现代信任人士中取得了更为明显的效果,说明宗教管制政策对不同人群的影响方式和能力是有差异的。

表5 信仰与合适的善资使用者(%)
五、分析与讨论
本文在借鉴“宗教市场”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信仰市场”的概念,并将其三分为“现代信仰”、“宗教信仰”和“无信仰”。基于此,本文分析了不同信仰对于个体志愿行为表现的影响。从结果看,宗教信徒的志愿服务和捐赠表现都要好于无信仰人士,宗教信仰与志愿服务及慈善捐赠之间同样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类似。但与西方国家及我国台湾所不同的是,我国宗教组织在信仰市场上吸纳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资源的能力十分有限。①中国人民大学最近发布的《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为本文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解。“报告”称,五大教教职人员的月平均收入为506元,大众印象中很有钱的佛教,其教职人员的月收入则为397元,属于苦行僧的类型。数据来源:中国国家调查数据库,http://www.cnsda.org/index.php?r=site/article&id=126。由此我们推测,在“世俗化优先”的宗教政策下,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宗教复兴”前景是有限的,宗教信徒很难成为社会成员中的多数,宗教组织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也很难在公益领域扮演主导角色。
爱因斯坦曾将科学与宗教的依存性关系形象地表述为:“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②《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第182-183页。事实证明,这是极有预见性的。当经典宗教世俗化的热潮过去,研究者发现,宗教信仰与现代信仰共存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我国目前的宗教管制体制是建立在宗教最终将消亡的观点基础上的,与经典宗教世俗化理论吻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动中国传统宗教顺利完成现代转型,将是宗教政策完善的一个方向。宗教组织释放更多的公益服务潜能将会对我国社会福利提供必要的补充。
本文从宗教信仰与现代信仰共存的事实出发,提出了“信仰三分”的概念,并以此对我国宗教信徒志愿行为的殊异性进行了分析。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比通常所用的“信仰二分”方法更加实用。笔者相信,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信仰三分”同样适用于分析其他国家。不过,在那些无神论者广泛遭遇来自宗教组织、政权和社会压力的国家,“现代信仰人士”是否在志愿行为方面有更好的表现,则不得而知。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未能就信仰的三分方法展开更充分的论证;二是未能就不同的宗教对其信徒志愿行为的影响差异进行分析。
(责任编辑:陈劲松)
□社会工作
The Heterism and It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Religious Believers’Voluntary Behavior:Evidence-based Analysis on a Survey
ZHANG Wang-cheng, ZHANG Jin-dong, LI Jing
Abstract:Unlike in western countries, Chinese religious believers have failed to present better performance on voluntary behaviors than non-believers.Inspired by the “religion market” concept, this paper proposed a new concept of “belief market”, on which the social member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modern believers” (communists and the like), “religious believers” and “non-believers”.Based on a multi-provincial survey, we found that the religious believers had made better performances of voluntary service and charitable donation than the non-believers, yet much worse than the “modern believers”, which was interpreted as consequences of “securalization bias” religion regulation policy in China.
Key words:religious belief; voluntary service; charitable donation; religious regulation
作者简介:张网成,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金东,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硕士生;李静,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硕士生。(北京,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