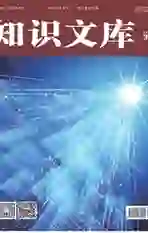另一个鲁迅在厦门
2016-04-29姚嘉敏
世人对鲁迅怀有景仰之情,但了解大多止于对其作品的解读。本文从《两地书》一书着手,深刻剖析鲁迅一段特殊的厦门岁月,从饮食起居、人情世故、幸福爱情、文学创作四个方面探讨他真实且生动的常人世界,还原一个饱满完整、有血有肉的鲁迅先生。
一、绪论
鲁迅,是一个大家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普通人熟悉的主要是教材中的鲁迅;而陌生则很可能是因为“鲁迅被严重地‘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了”。
《两地书》“大多的内容是倾诉别后的思念,爱的表示,相互的牵挂,彼此关心着对方的工作和生活,还有,就是倾吐块垒,抒发愤懑,甚至发牢骚等等”,如此内容的书信,我们能最大限度地去了解一个伟大思想家文学家的普通而平凡的个人世界。
二、鲁迅在常人世界里
1、饮食起居素婴郁闷
翻阅《两地书》,可以发现,鲁迅除以往的评论家笔下的高蹈远举、目光如炬之外,也有着难脱的锅碗瓢盘箸和吃喝拉撒睡之累。素为饮食起居的琐碎而郁闷的鲁迅,正是常人鲁迅的表现之一。
在厦门鲁迅时期的《两地书》涉及饮食起居内容的不少。给许广平的信中提到“校内的饭菜是不能吃的,我们合雇了一个厨子,每月工钱十元,每人饭菜钱十元,但仍然淡而无味”。于此可以看出鲁迅似乎开始对饮食环境不满。到已经决定离开厦大赴广州,鲁迅继续在信中写到“现在我们的饭可笑极了,外面仍无好的包饭处,所以还是从本校厨房买饭……一并买他毫不能吃之菜,以省麻烦”。对于厦大的饮食,鲁迅是颇有意见却又无奈的。
鲁迅另外一些生活琐事同样让鲁迅郁闷。比如“这几天而且更能睡觉,每晚总可以睡九至十小时;但还有点懒,未曾理发,只在前晚用安全剃刀刮了一回髭须而已”,较“懒”的生活让鲁迅“能吃能睡”“也许肥胖一点了罢”。鲁迅抱怨自己“懒”,而我们看来只是生活闲适。在闲适生活中鲁迅偶尔也会有些孩童般的举动。信中,鲁迅描述了这样一件事“楼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给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如此天真活泼、如此毫无顾忌、如此孩童稚气,恐怕在鲁迅的整个一生中都不多见。
关于“小解”的问题也有必要提一下。信中这样写道:“这里颇多小蛇……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磁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再伟大的人格也不至于为小解而冒大险,相较于“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冷峻,这样的先生尤为可爱。
此外,鲁迅在《两地书》中还聊到普通人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都会遇到的语言不通、气候不适应、住宿等方面的问题。买水果食物由于言语不通,当地人有欺骗外地人之嫌。对于气候环境,鲁迅讨厌蚂蚁,更是不习惯湿热气候。信中多次提到“这里的蚂蚁可怕极了……偶然忘记,则顷刻之间,满碗都是小蚂蚁”相类似的话语。鲁迅的住宿也是一个问题,在厦门短短的四个来月间,鲁迅搬过家,住过两个地方,而且所住之地都不是正常的宿舍。
这就是鲁迅在厦门大学时期的真实生活环境:吃不好,住不安心,再碰上生活设施不完善,小解一度成为问题。虽然期间可以稍“懒”一些,可以顽皮胡闹一下,但小事总是琐碎平凡,麻烦终究无日无之。一部《两地书》,使厦门鲁迅的常人世界在饮食起居方面得以最直观的呈现。
2、人际关系频生尴尬
鲁迅在厦大的135天里在人情世故方面消耗更多的精力和时间。鲁迅本来抱着“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想法,以期摆脱黑暗,奔向爱情和希望。但是当时的厦大埋葬了他的想法。在《两地书》中,有不少片段都描述了鲁迅对当时厦大人事上的失望。
鲁迅在厦大遇到的人,根据《两地书》中提到的可以大致这么分类:可以谈得来的好朋友一类,如林语堂、孙伏园;极其瞧不起与不满的胡适之“现代评论派”之信徒,如朱山根、顾颉刚;以及拜金、无聊甚至无耻的某些教授某种气氛;还有除此之外的一些无聊的应酬或不得不去的一些演讲。
对于好朋友,鲁迅是真诚的也是推心置腹的,偶尔也会对朋友的一些行为做法不满甚至发几句牢骚。鲁迅来厦大,可以说林语堂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了不为难林语堂,鲁迅坚持学期末才离开厦大。至于孙伏园,鲁迅在《两地书》及其日记中都常提及。在厦大期间,鲁迅与孙伏园可谓同甘苦共患难,吃一样的饭处一样的环境,鲁迅在《两地书》中对这个学生偶尔仍是有一些小意见,这体现常人相处的烦恼。
对于“现代评论派”胡适之之信徒的朱山根、顾颉刚之类的人事,在信中有过提及:“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朱山根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
鲁迅在厦大的人情世故中还有被鲁迅定论为“尊孔的”当时校长林文庆。鲁迅在10月16日的信中提到“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这里就是如此胡里胡涂”。这可以看出,鲁迅与林文庆也是不同道的人。
身为名人的鲁迅,粉丝多多,盛情难却。据《两地书》记载,有慕名而来听课的男女学生,有请他帮助筹办月刊、周刊,还有学校邀请“太虚”、马寅初要求去作陪,厦门其他学校邀请去做各种演讲以及会各类客人等,在《两地书》中都有提到,鲁迅实在是疲于应付。
厦门鲁迅的常人世界在《两地书》所描绘的人情世故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3、爱情日子温暖成熟
《两地书》能永恒,鲁迅与许广平的旷世爱情无疑是其重要原因。《两地书》见证了他们爱情成长成熟的历程。《两地书》中的鲁迅不是那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而只是一个处在热恋中并享受幸福爱情的普通男性。
在厦门时期的往来信件中,“他们不厌其烦地询问对方是否收到自己的信件,推算着邮件行走日程,猜测邮件迟到的原因;相互担心操心着饭菜合不合口,居住适不适应,工作累不累,身体是胖了还是瘦了”等等,无不显露着两人热烈而温暖的爱情。
“现在就只有我一人。但我却可以静坐着默念HM,所以精神上并不感到寂寞”,鲁迅不仅精神上不感到寂寞,在很多生活习惯上因为许广平的指正批评都有所改变。比如尽量少的吸烟,几乎不再喝酒,为了不让许广平不安,都不再半夜出去寄信也不轻易发牢骚,一个45岁的中年男性,在习惯已经定型的时候,竟然能做出这么多的改变,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
鲁迅用他的爱情他的《两地书》诠释了他作为常人却丰富的爱情世界。
4、有限著述无限珍贵
在厦大的130多个日子里,可以说是鲁迅一生中最纯粹的一段学院生活。就是这既短暂又纯粹的岁月,除了《两地书》,鲁迅还做了如下几个工作:整理完成两部学术论著《汉画像考》《古小说钩沉》;将1907年到1925年所写的杂文、论文23篇编成杂文集《坟》,并在最后附上《写在<坟>的后面》一文,以“驱逐自己目下的哀愁”;并将《上海通信》《厦门通信》(一、二、三)《<阿Q正传>的成因》《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等几篇《华盖集》之后的文字汇集成册以《华盖集续编的续编》出版;以及写下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5篇回忆性散文,以此完成散文集《朝花夕拾》的创作;并发表《奔月》《铸剑》等小说,后收入《故事新编》。
《朝花夕拾》、《坟》给了鲁迅在厦门孤独、寂寞时“淡淡的甜美”,《两地书》在成就了鲁迅与许广平旷世不朽的爱情之外,还呈现了一个厦门鲁迅的常人世界供世人品读,作品与书信中的鲁迅是平凡而普通的,也正是这一个鲁迅带给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滔滔财富。有意无意间,鲁迅的常人世界带给了这个世界太多的不平常。
三、总结
《两地书》的鲁迅不像以往教材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犀利深刻严肃革命的,且没有自己生活和情趣的伟大的不能接近的思想家文学家,而是一个在饮食起居上素婴郁闷、人际关系上频生尴尬、爱情日子温暖成熟的平常人。
(作者单位:广州华商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