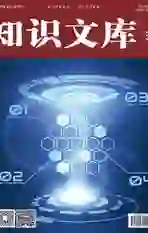唐宋时期浙江佛教概述
2016-04-29何勇强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的繁荣时期。当时佛教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伴随着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各种宗派纷纷诞生,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慈恩宗、律宗、禅宗、净土宗等。
南北朝时,佛教传播的态势是南方尚义学,北方重禅定。隋朝统一中国后,南北佛教渐趋融合,中国最早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浙江产生了。天台宗实际的创立者智顗深受陈、隋两朝皇帝推崇。天台宗以天台为其祖地,也因此得名。因以《法华经》为其主要经典,故又名法华宗。究其思想教理,主要是三点:在世界观上的“真如缘起”论,在认识论上的“一心三观”与“一念三千”论,以衣在方法论上的“止观”学说。除三论宗外,其他诸宗在浙江也有传播。如三论宗僧人乌凯曾在越州嘉祥寺开讲三论。
但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南北并峙相比,隋唐初期南方佛教明显落后于北方。天台宗虽然辉煌一时,但它实际上是南朝佛教的一屡余辉,到唐以后,其声势为新兴的慈恩、贤首各宗所掩,黯然不彰。华严宗的一代宗师澄观虽是越州山阴人,但他的活动基地却在五台山。
这种北强南弱局面直到唐朝后期才有所改变。唐后期至宋,佛教传播的基本态势是南禅北律。下面就以禅、律两大宗派的发展来看浙江佛教的状况。
唐朝的禅宗,初期主要是双峰道信、东山弘忍以及法融在润州一带创立的牛头禅系。弘忍门徒众多,而以神秀在当时的影响最大。由于得到朝廷的支持,以他为首的禅宗北宗被树立为禅宗的正统。弘忍的另一个门徒慧能则远走岭南,以顿悟传道,反对神秀渐修成佛的理论。这一宗派后来被人称为南宗。安史之乱以后,南宗的影响不断扩大,逐渐取代北宗成为禅宗传播的主流。当然,随着南禅自身势力的发展,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总括起来,不外乎两大宗系: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的洪州禅系与青原行思门下石头希迁开创的石头禅系。由此又产生很多支派,后人称之为五家七宗。所谓五家,即指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入宋以后,又从临济分出黄龙、杨岐二家,合称五家七宗。事实上,当时禅宗宗派之多且复杂,并不能仅用五家七宗加以概括。除五家七宗外,尚有德山、雪峰等宗派。沩仰宗是由沩山灵祐创立的,他的弟子仰山慧寂克绍其裘,将之发扬光大,主要在江西、湖南一带传播,声势极盛。临济一宗由黄檗希运的弟子义玄所创,创立之后长期就在河北地区稳稳扎根。沩仰、临济都出自南岳怀让的洪州禅系。德山宗由德山宣鉴所创,以朗州为中心,在湖南、荆襄一带传播。曹洞宗是晚唐时由洞山良价、曹山本寂师徒创立的,从时间上稍稍迟于德山、沩仰。它的传播中心也是在江西、湖南一带。以上沩仰、临济、曹洞、德山诸宗在浙江都有传人,但声势远不如江西、湖南一带。
这一局面直到慧能第七世后才有所改变,当时正值唐末五代,福建、两浙和岭南取代湖南、江西成为禅宗新兴的中心。在禅宗传播重心东移过程中,雪峰宗的义存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当时福建、两浙的禅宗僧侣几乎全部出自他的门下,他的首席弟子玄沙师备被尊为法眼宗的始祖,他的另一个弟子文偃南下广东,创立了云门宗。大约到五代的晚期,玄沙师备的再传弟子清凉文益创立了法眼宗。文益本是杭州余杭人,后来学道福建,传道江西,到金陵后被南唐政府尊为国师。他的继承人天台德韶又成为吴越国的国师。当时南唐灭了楚国,又与吴越瓜分了闽国,疆域达到极盛,法眼宗在南唐与吴越两国政府的保护与支持下在东南地区广为传播,迅速发展,成为禅宗传播的主流。而吴越国崇佛之盛,尤胜南唐。文益之后的两位法眼宗祖师,德韶、延寿,俱是浙人。尤其是延寿,他是禅宗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提出禅教兼重、性相融合的主张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在这一时期,浙江成为禅宗传播的中心。
唐朝律宗主要分为三派,一为相部律,法砺所创,以其盛行于河北相州一带得名;一为南山律,道宣所创,以道宣住终南山得名;一为东山律宗,怀素所创,以怀素居西太原寺东塔而得名。东塔宗主要在北方传播,相部、南山两宗后来都向南方发展,在东南地区声势蔚然可观。相部宗向东南地区传播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三个人物是崇福满意、龙兴法慎与越州昙一。南山宗向南传播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光州道岸。他门下弟子极众,在两浙地区者有越州法华寺玄俨、杭州华严寺道光、湖州大云寺子瑀等。但在唐朝后期,南山律宗的声势毕竟无法与相部律宗抗衡。
到五代后,随着玄唐末名僧玄畅的两大弟子慧则、元表入住越州,南山宗开始在浙江崛起,并逐渐取代相部律宗成的主流地位。入宋以后,中国佛教的传播基本上是南禅北律。当时浙江的律宗尽管在声势上远不如禅宗,但仍一跃成为全国的律宗中心。南山律宗振兴浙江的一个关健人物是慧则的弟子希觉。一则,他与吴越国的政府官员甚至吴越国王本人都有交往,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二则,他在学术上成就卓著,《增晖录》一书出笼以后即风行两浙,促进了南山律宗的传播;三则,他培养了一些佛教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僧人,如著名佛教史家、素有律虎之称的赞宁,又如对宋朝初年的天臺宗山家山外之争产生很大影响的僧人皓端等。
此外,元表六传至允堪。允堪普遍地注解了道宣的著述,达七部之多,所著解释《行事钞》的《会正记》尤其重要。他的再传弟子灵芝元照,原学天台宗,后采台宗之说讲律,注解了道宣的三大部著作。允堪、元照是唐宋时期继希觉──赞宁之后的又一高峰,也使杭州成为当时的律宗传播中心。
唐宋时期是浙江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五代、两宋尤称峰中之巅。其时佛教繁荣的一个标志即是各个宗派的聚积与融合。除上述禅宗、律宗外,浙江也是净土宗的传播中心。当时禅宗、天台宗僧人多兼修净业,禅宗僧人延寿且成为净土宗历史上的一代祖师。宋初省常效法庐山莲社故事,在杭州西湖集合僧俗结净行社,提倡念佛。类似的结社集会后越来越多,文人士大夫迭相模仿;有些寺院建筑了弥陀阁、十六观堂,专供念佛修行,促进了净土信仰在民间的推广,渐渐成为一种风俗。净土信仰虽然自晋以来一直存在,但并未形成固定宗派。至南宋,四明僧人宗晓编定《乐邦文类》,以莲社为专宗,确定善导、法照、少康、省常、宗赜上承慧远为净土教的历代祖师,净土法门作为一个固定宗派初具规模。
此外,立足于浙江的天台宗虽在会昌灭佛中受到巨大打击,一蹶不振,但到五代时它开始出现复兴迹象。天台僧人羲寂从高丽、日本取回会昌灭佛后佚失的法华典籍,在吴越国政府与法眼宗僧人的支持下,实现了天台宗的中兴。由于对这些天台教籍的理解、诠释不同,主要是围绕智顗《金光明经玄义》的广本、略本的争论,羲寂的弟子产生分化。一派以义通及其弟子遵式、知礼为代表,一派以志因及其弟子晤恩、源清及再传弟子庆昭、智圆为代表。后来知礼及其弟子一派学说逐渐取得天台宗的正统地位,他们自称山家,将晤恩一派贬为山外。山家山外之争犹如禅宗的南北宗之争,不但没有天台宗衰落,反而使它取得前所却未有的发展。南宋时四明僧人志磐编天台宗的纪传体史书《佛祖统记》,卷帙庞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宗派在两宋时期的兴盛。
又如华严宗,五代、两宋是华严宗相对衰微的时代。当时它的传播中心仍在两浙地区。其代表人物即是杭州报恩院的净源,被称为华严宗的“中兴教主”。
唐后期至宋,佛学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即是各种思想的融合。首先是佛教内部各宗派的融合,其次是佛教与儒学的融合。最具此种会通思想的代表人物,延寿和契嵩,都是来自浙江的僧人,都曾入住杭州灵隐。作为禅宗僧人,延寿主张禅教兼重,他的百卷巨著《宗镜录》即是为了调和天台、贤首、唯识诸宗争论而作。契嵩是云门宗僧人,他为对付北宋中叶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士大夫对佛教的抨击,尝试援儒入佛,如将佛教中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提并论,又如大力提倡孝道、盛赞中庸之道。所有这些,不仅对佛教的发展,且对当时儒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会通思想在浙江蔚然勃兴,领导中国佛学潮流,恐怕是与当时当地各种宗派汇聚提供了肥沃的思想土壤分不开的。
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佛教的世俗化、平民化趋势。浙江佛教在这方面领导了中国佛教的潮流。禅宗、净土宗在浙江的流行,就反映了这一趋势。因其简单易行,信奉者日多,使佛教从六朝时期的贵族宗教渐渐演变为平民宗教。此外,北宋时杭州白云庵僧人清觉创立白云宗,提倡素食、行善、念佛,同时允许僧人蓄发、娶妻。由于没有繁琐的教义,且比较容易实行,乐为下层百姓接受。白云宗对后来中国的一些民间秘密宗教有着很深的影响。
无论是各宗思想的会通,还是世俗化的趋势,实际上都表明了佛教逐渐中国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即是对佛教神灵的改造。一是把佛教固有神灵中国化,二是把中国历史人物改造为佛教神灵。在这方面,浙江都有比较突出的例子。把佛教固有神灵中国化的例子是观世音。观世音,其梵文为Avalokitesvara,在佛教中原是男身,到中国后渐渐演化为女身,融入中国的民间信仰中。我们不知道浙江人在其中起我多大的作用。但观音道场最后却落在了浙江的普陀山。据说是五代时日本僧人慧锷从五台山负观音像东渡,至梅岑山触礁,遂留像建寺,改梅岑山为普陀山。
把中国历史人物改为造为佛教神灵的例子则有布袋和尚弥勒佛与济公。弥勒与布袋船泊港内本是二神。弥勒梵文Maitreya,是佛教中的菩萨,因居西方极乐世界,随着净土信仰的普及,弥勒信仰也渐渐深入人心;又因佛预言他将继承自己的佛位,故称未来佛,常成为一些宗教团体造反作乱、企图改朝换代的工具,在中国民间的秘密宗教中有很深的影响。布袋和尚名契此,五代初期明州人。《宋高僧传》谓其“形裁腲脮,蹙镇皤腹,言语无恒,寝卧随处”。又说他常以杖荷布袋一只,沿街乞讨,每得酝酱鱼葅,一部分放入口中,一部分放入布袋,人号为“长汀子布袋师”。曾有偈云“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等句,人们因此怀疑他是弥勒下凡。据说,在他死后,还有人在其他地方见到他,背负布袋。发棺视之,惟见一舄。浙江一带对他非常崇拜,民间多图画其像,后来弥勒与布袋和尚便合而为一。济公是南宋时台州人,原名李心远,法名道济,在杭州如灵隐寺出家,后移住将慈寺。因嗜酒肉,举止疯癫,故人称“济癫僧”,后被人神化为降龙罗汉转世。类似契此、道济等浙江僧人被神化而进入佛教神仙谱系的事例反映了佛教的中国化倾向。
这一时期浙江对外佛教文化交流也非常活跃。在佛教初传中国时期,中西交通主要经由陆路。但自中唐以后,中国西北方面受突厥、吐蕃等少数民族势力侵扰;入宋以后,中西陆上交通又受契丹、西夏所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的佛教文化交流越来越依赖于海上交流。在佛教初传中国时期,中国对外佛教交流主要是主要学习佛法,翻译佛经,其交往对象主要是印度;而到宋以后,主要是外国僧人来中国学习佛法,交往重心也由印度转移到日本、朝鲜。浙江地处海滨,加上佛教文化繁荣,当仁不让地成为进行对外佛教交流的前沿。新罗、高丽、日本僧人大量来华,数量極多。以元代而言,来华的日本僧人,仅现在可知的就有220人之多,其中59人为浙江人,占全国1/4强。这些僧人对日、韩两国的佛教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举例言之:唐时日僧空海来中国学习密宗,从明州回国,创立真言宗。日僧最澄到天台学习佛法,回日本创立天台宗;宋时又从天台宗派生出日莲宗。日僧荣西宋时两次入华,到天台、阿育王诸山,回国后传临济宗。荣西的弟子道元,来华访天台、天童,开创日本曹洞宗。至今,日本的天台宗认国清寺为祖庭,曹洞宗认天童寺为祖庭,临济宗认杭州径山、天目山为祖庭。
当然,交流是双向的。日本、朝鲜佛教反过来也影响浙江佛教的发展。如五代、宋初天台宗得以中兴,便是靠武昌灭佛后散失的典籍得以从高丽、日本重回中国。高丽僧人义通还成为天台宗一代祖师。
当时浙江佛教的功德事业也极其发达。首先是大量修建寺院,数量之多,不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也远远多以当时其它地区。如五代吴越诸王崇佛,境内大兴寺院。仅杭州一地(不包括今杭州西部一些县市,当时属于睦州),仅《咸淳临安志》所记载的,就有近400座之多。此外,还大量修造佛塔、经幢,临安功臣塔、杭州白塔等,至今仍风声峙立于浙江境内。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杭州的佛教造像。中国的石窟造像和摩崖龛像,盛于晋唐之世,但当时的造像,大半集中在西北和华北地区;而且,到五代以后,凿窟造像的风气,开始衰微。但是,吴越国、宋元时期,杭州作为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佛像的塑造,蔚然成为风气,因此留下大量造像,不但数量丰富,而且可以和五代以前的北方石窟造像相衔接,成为造像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吴越、南宋定都杭州,凤凰山一带是其宫殿的所在,因此从凤凰山到慈云岭一带地区成为当时的政治重心,附近寺院林立,吴越国的佛教造像也多分布在这一带。此外,东到宝石山南坡,西到北高峰和天马山之间的飞来峰四周,也有大量的佛教雕刻和古迹。
当时浙江佛教的蓬勃发展与统治者的提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崇佛最甚者,当数五代吴越诸君。尤其是吴越国的末代国王钱俶,几乎将佛教作为吴越国的国教了。他为延寿《宗镜录》作序,云:“详夫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自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贶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惟此三教,并自心修。”可见,虽说是三教并重,钱俶却将释教置于第一位,佛教是儒、道二教之宗。当时崇佛的君主大有人在,但从无一人将佛教提到如此的高度。这使得吴越国成为浙江佛教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宋代诸帝也崇佛。尤其是南宋定都临安,使两浙之境为畿辅之地,集全国文化精华所萃,浙江佛教仍保持极盛之势。宁宗以制定寺院等级制度,全国有“五山十刹”,其中“五山”全在浙江,“十刹”中浙江也占了十分之六。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