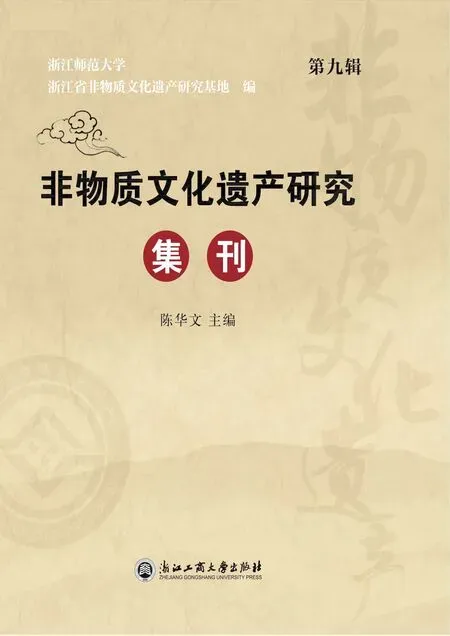略论孝亲传统对祝寿风俗与祝寿图像的影响*
2016-04-17程波涛
程波涛
(安徽大学艺术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9)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
略论孝亲传统对祝寿风俗与祝寿图像的影响*
程波涛①
(安徽大学艺术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9)
祝寿图像的生成,无疑经过了一个从精神信仰层面到图像符号层面的演变与转化过程,而这类图像更容易以感性的外壳去表现内在的生命祈愿和心理诉求。从符号学角度看,祝寿图像只不过是“能指”,而在图像背后则是丰富的“所指”,这种源自于星辰崇拜的古老习俗,不断杂糅进伦理、政治、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的意义表达,最终指向于一种图像化的呈现。而从祝寿图像的文化生成和发展脉络看,孝道和尚老传统是其产生并多样化的重要推动力,因此,从孝亲传统来把握祝寿图像,无疑是认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社会现实下,认识民俗艺术图像的有益视角。
祝寿图像 孝亲 尚老 生命伦理
渴望生命的长久存在是人类普遍的生存意愿。《庄子·在宥》中黄帝问广成子:“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答曰:“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黄帝真诚地向广成子探询长寿“秘方”,广成子的回答却给人以荒诞不经之感。人们对长生永在的理解经常受到神话和古代医书的影响。在古代的中国,特别是到了秦汉时期,人们渴望长寿的心理与神仙观念发生了紧密的关联,出现了一批方士、神仙家、养生家,而且很多帝王也热衷于长生之术,秦始皇和汉武帝等人都曾派人去东海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如在汉画像石和画像砖中,二十八星宿和羽化登仙主题的图像反复出现,反映的正是人们渴望长生永在的功利性心理。早期的那些神话故事,及其相关的图像意在表现长生和不死主题,更是后来祝寿图像的一个观念的来源。这类图像由于夹杂着浓厚的民间信仰观念的成分,故而神话的、幻想的以及巫术性色彩极强,给人以虚无缥缈、扑朔迷离之感,反映了在科技不发达时期,人们对于生命自身和自然现象缺乏系统而科学的认识。汉代的黄老之学兴起和《山海经》等带有玄幻色彩的著作出现,更是使一些人产生对不死仙乡和得道之人羽化而登仙的渴望与向往。而早期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也曾直接断言:“人寿当为一百至一百二十载。”正是因为有了各种传说和来自医学界的预言,给渴望长寿的人们以可能性与真实性的希冀。历代关于养生、重生的著作更是层出不穷,例如,梁代陶景弘的《养性延命录》、唐人孙思邈的《孙真人养生铭》、宋人陈直的《养老奉亲书》、元人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明人胡文焕的《寿养丛书》等,都体现了古人对于生命的能动思考和带有探索意义的实践。任何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由渴望长寿到尚老、重老,再到尊老和孝亲之间,构成了一个带有内在连贯性的文化逻辑。
一、孝亲传统对祝寿风俗的渗透
我国作为礼仪之邦,很早就有养老的礼俗制度,张亮采先生在《中国风俗史》中写道:“养老之礼始于虞舜,名曰‘燕礼’,夏曰‘飨礼’,殷曰‘食礼’,《记》称有虞氏养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①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22页。祝寿图像本身就是孝亲、尊亲、养亲实践的载体“再现”,从这一意义上说,认识我国古代的孝道传统,对于体认祝寿文化以及祝寿图像的生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百善孝当头”,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孝道就是其中之一。在社会中,对于每个家庭成员来说,孝敬父母、尊敬长上实为厚风俗、淳教化的良法,也是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孔子曾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汉代开始提倡并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伦理观念,汉武帝刘彻采纳儒家知识分子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统治思想,国家开始倡导和推行忠、孝等儒家伦理观念,并将其提升到治国和笼络人才的政治层面上来。“家国一体”的意识开始日益被更多的底层民众所认同,其后,在封建社会中的不同朝代的统治者们也积极效法和沿袭,并逐渐将孝道与忠君的伦理观念纲常化,成为统治和约束被统治者的隐形力量,从而使孝亲行为成为一种社会的、国家认可和倡导的行为准则。尤其是在用人制度上除了沿用先前儒家读书人治国之外,推行“察举孝廉”制度则是一个新的举措,客观上推动和加强了养老、孝老的社会制度的形成。事实上,“孝”也是“忠”的基础和必要的前提条件,汉以后封建时代的统治者无不把“忠”和“孝”联系起来,“孝”成为衡量一个人德行和立身的重要标准,并上升到一种政治的高度。乃至后来统治者更强调和注重“忠、孝、节、义”等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在汉代皇帝中,除了汉高祖刘邦之外,其他皇帝的谥号中都有一个“孝”字,如汉孝文帝、汉孝武帝等,而且,在汉代以后也有如晋孝文帝等,甚至入主中原的北魏皇帝拓跋宏,也被称为魏孝文帝,可见,孝道深受国人重视。国人很早就开始尊奉和践行孝道,由此,孝道成为一种获得积极认可和赞许的社会性行为,被视为不同阶层崇尚的正统社会伦理思潮的“风向标”。这种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带有浓浓亲情的伦理道德行为,足以体现一股具有感恩意识的社会文明风气在社会传播和沿传开去,孝道对于 “厚人伦、淳教化”的社会风气,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推动。《礼记·宓官》:“万舞洋洋,孝孙有庆。俾尔识有昌,俾尔寿而臧。”孝子贤孙的孝亲行为会赢得朝廷的认可和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这恰恰是我国尊老敬老风气的体现。也正是有了这样的风气和氛围,祝寿礼俗得以形成和兴起,并得到统治者的鼓励、提倡以及制度化的保障。
孝道风气和氛围的形成,离不开国家和社会多渠道的宣传、弘扬和塑造。经过较长历史时期的灌输和积淀,这种孝道传统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标准,其影响一直沿袭至今。
首先,文字和口头资料中关于孝道的论述与事例比比皆是。在对于孝道的弘扬方面,古代的蒙训教材、类书、文集、民间抄本等都有孝子故事;在艺术方面,民间说唱、美术、戏曲等也都曾对孝道传统和尊重老人的家庭伦理价值观做过积极的舆论宣传,并充分发挥过伦理教化功能。西汉王延寿作《鲁灵光殿赋》称:“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数,麻不载叙,恶以戒世,善以启后。”初唐的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序中写道:“其于忠臣孝子,贤愚美恶,莫不图之屋壁,以训将来。或想功烈于千年,聆英威于百代,乃心存懿迹默匠,仪形其余风,化幽微感而遂至飞游腾窜,验之目前,皆可图画。”正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宣传孝道,喻示人们见贤思齐,这才如春风化雨般地扩大了孝文化影响力。“二十四孝”正是社会对孝道的提倡和赞许,也是被强化了的道德观念。
其次,以制度和伦理规范孝道的推行。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那么,对于不赡养老人的人,除了乡邻的舆论讨伐和鞭挞之外,还有国家法律的多种制约和宗法制度下“家法”的惩罚,这使得“孝亲”成为特定历史阶段中,带有合理性、合法性和强制性的社会性行为。另外,除了在现实的制度层面外,还有精神层面的“警示”,那就是更为迷信而可怕的“天惩”,即对于那些不赡养和善待老人的逆子们,会被“天打五雷轰”,死后背上还会被“上天”书写有“不孝”二字,以“诫示”世人,从而使得很多人不敢或不愿突破“孝亲”伦理道德的底线,自律和自觉地恪守孝道传统。与不肖子孙受到“天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行孝本身也是积善的表现,在民间传说中,很多孝子都有“善报”,例如,董永卖身葬父的孝心义行感动了上苍,天界七仙女下凡,婚配董永,成就了一段天仙相配的美好姻缘。“善为德之本,德乃福之根。”这些故事最大的功用就是给善行者以心理的安慰。类似的劝善故事和“上天”奖励孝子的传说还有很多,无不给人以精神的鼓舞。子思曰:“大德者必长寿。”孝行除了是感恩的善举外,也是一种积德行为,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福运。这些带有应用色彩的文艺作品意在宣传“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因果观念。特别是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因果报应的观念深入人心,而与孝道有关的因果报应观念深深地影响到孝文化的稳定传承和祝寿风俗的持续发展。另外,像“仁者长寿”“善者长寿”的说法,都是对于善行和仁道的肯定。人们逐渐把“孝道”演化为一种必须强制遵守的道德行为,而且有来自“天”与人的共同监督,从而自社会层面到个人心灵层面共同编织了一种无形而又强大的舆论力量,对孝道文化进行强力灌输和推动。“事亲须是孝”①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9页。作为一种心理定式,成了封建社会中国人长期奉行的伦理价值标准。
再次,对于孝道的推崇,光有理论上的体现尚不足以充分表达其重要性,对孝道的表达需要物质化、仪式化,使其成为可感、可知的文化物象。诸如为孝子建祠堂,如山东嘉祥、长清等地的郭巨祠等;制作以宣扬孝道为内容的壁画和浮雕等文学和艺术等形式,对孝子进行表彰和扬名;还有反映孝道绘画,如《绘图二十四孝》、同治会稽俞氏刊本《百孝图说》,等等。祝寿之俗和祝寿图像无疑是实现对孝道伦理仪式化与物质化的重要途径。
二、尊老、孝亲观念影响下的祝寿图像
在孝文化浓厚的社会氛围中,出现了一大批孝亲的典范人物和感人的孝道事例,旨在教化世道人心,由此也催生了大量反映敬老、尊老方面的文学艺术作品。与“孝亲”相关的图像开始不断出现,如《老莱子娱亲图》《二十四孝图》等,以及赞美母仪、感恩慈母的陈洪绶《宣文君授经图》《三娘教子图》等。孝亲观念本是一种报答父母生身之恩、养育之劳的正常感恩行为表达。《诗经》有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而“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待”则无疑是一种令人顿足捶胸或“哀莫大焉”的沮丧、懊悔之事。表现积极乐生的生命意识之外,更易于被人们所忽视的是,祝寿图像中蕴涵的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的传统以及尊老乐群的人情观。对于老人来说,祝寿本身不仅是晚辈对其健康长寿的祝愿,更是对养育之恩和辛苦操劳的温情表达,因此,祝寿活动本身也就成为晚年生活的一种重要的心灵寄托;而对于每个家庭的个体成员来说,自己也会在岁月中变老,既是孝行的践行者,也是受益者,因为在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社会,敬老与被尊敬本是一体的。
尊老、孝亲是孝道传统的具体体现,也是祝寿图像产生的重要精神源泉。统治阶级首先为万民表率,通过政治权利体现尚老之义。在汉代,年过70的老人会被统治者授予“鸠杖”①鸠杖在汉代的意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鸠鸟被认为是“不噎之鸟”,赐予老人鸠杖,是希望高寿老者吃饭时能够“不噎”。这是一种通常的理解;第二,鸠鸟曾对于汉高祖刘邦有过“帮助”。王克谦《集解》引惠栋曰:“《风俗通》云‘汉高祖与项藉战京索间,遁丛薄中,时有鸠鸣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脱。及即位,异此鸟,故作鸠杖赐老人也。’”看来对于汉王朝来说,鸠鸟为“义鸟”和“祥禽”,曾于关键时刻无意间“救过”汉高祖刘邦的性命,才有后来大汉王朝的建立,因此,汉代的“鸠杖”礼俗具有特殊政治文化意涵。《艺文类聚》引《瑞应图》曰:“鸠,王者养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旧则至。”,并祭祀老人星,以体现对老者的尊重。如《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与国都南郊老人庙。”而且,统治者对于不同年龄段老寿星的加赐礼俗和待遇也不同。特别是“八十杖于朝”和“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赐就其室”,帝王亲自登门看望,年至九秩的人瑞们所享受的隆重礼遇程度,显然是非同寻常的,也是空前的。事实上,汉代所赐予老人的“鸠杖”,是一种来自统治阶层对于国内高寿老人的特殊礼遇,显示出汉朝统治者尊老的一种制度化表现,也是礼俗层面中很具有政治影响意义的行为。正是因为这种敬老、尊老的观念表现为一种社会性的意识和普遍心理,并上升为儒家文化传统下的理性认同和社会文化心理的隐形制约,包括敬老这样的礼俗在人们心目中被制度化和纲常化,逐渐成为祝寿文化的生成的社会心理基础。正是孝文化的浓厚氛围培育和滋生出祝寿礼俗,为祝寿图像创作提供了必要的仪轨和文化元素,也使得祝寿图像中蕴涵着丰富的人伦情感和孝亲思想。
《孝经》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在养老行孝的故事中,《老莱子娱亲》的故事最具有典型性。《太平御览》引师觉授《孝子传》曰:“老莱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著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因僵仆为婴儿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称老,为其伤老也,若老莱子可谓不失孺子之心矣。’”①[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四一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07—1908页。拟为三国时曹植的《灵芝篇》赞美老莱子:“伯榆年七十,彩衣以娱亲;慈母笞不痛,歔欷涕沾巾。”四川乐山东汉崖墓、山东嘉祥武梁祠、浙江海宁东汉画像石墓等,都有汉画像石《老莱子娱亲图》,画面主要是刻画年过七十的老莱子因“脚跌”,匍匐在父母面前,身穿七色彩斑衣扮作小儿状,并作婴啼的滑稽形象,取悦年迈的父母,以求父母不生“伤老”之感。由此老莱子成为“事亲至孝”的千古“模范”,后世的文学艺术中常以此来以喻示孝义,“戏彩娱亲”遂成为祝寿图和民间蒙训教育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与素材。老莱子成为祝寿题材中孝子的指代,明代画家唐寅在自己的《萱草图》中题诗:“北堂草树发新枝,堂上莱衣献寿卮。愿祝一花添一岁,年年长庆赏花时。”元代邹铉续编的《寿亲养老新书》中收录北宋陈直在谈到祝寿图像中老人喜爱的题材有“耕莘、筑岩、钓渭、浴沂、荀陈德星、李郭仙舟、蜀主访草庐、羲之会兰亭、陶渊明归去来、韩昌黎盘谷序、晋庐山十八仙、唐瀛洲十八学士、香山九老、洛阳耆英,古今事实皆绘为图,可以供老人玩……”②[元]邹铉:《寿亲养老新书》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四五册,第126页。可见这些题材是老人晚年生活所喜爱的,而创作这样的作品,显然也带有怡老、娱亲的文化心理和人伦情感。《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国人普遍相信善良能够引来福气,这种“福从善来”与“因善致福”的民俗心理,实则具有隐秘的文化内涵与助益人生的文化理念,而行孝则是积善和养德的一种重要手段。正是受到“孝亲”伦理观念及敬老、尊老的传统风气的影响,祝寿文化得以受到重视和发展。当然,不仅仅是汉代,在汉代前后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孝亲观都一直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被继承和发扬,体现了封建社会传统意识中家庭幸福观与和谐观的合理性一面,这也是祝寿图像能够长期存在的社会文化根源。古语:“家为邦本,本固国宁。”家族观念与家国一体、忠孝思想合体。在安土重迁的传统社会中,很多村庄大都是聚族而居,众多的男丁不仅是抵御外来势力侵扰的保障,也为农耕时代自给自足的家庭和家族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资源。而对于家族和家庭的老人来说,含饴弄孙亦是人生晚年的一件幸事。
从孝道伦理、尊老尚老的舆论造势,到祝寿风俗和图像化表达,这其中虽有统治阶级以孝道伦理之名行政治统治之实的意愿,但也确实培养、塑造了大批真正能够倾心于行善、尽孝的华夏子民,从而使得尊老敬老的风气蔚然成风,并成为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所秉承的一种优秀民族精神和传统。从功能和意义上讲,祝寿风俗本身就是重老、尊老的直接体现,有助于敦教化,助人伦。祝寿图像是祝寿风俗的形象载体,它承载着祝寿文化的精神内涵。祝寿图像背后的道德观,对于改善社会风气、增进人伦亲情、和睦乡里、改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净化世道人心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结语
就孝道传统和感恩文化统合来看,如果做深层的剖析,祝寿图像也能够衍生出新的道德价值体系。在祝寿图像的生成与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早期的寿国等精神信仰层面到孝道伦理层面的转换,而图像的意象构成和主题意涵的确立,基本上也是缘于此而展开。其中,孝道和尚老传统是祝寿图像产生并多样化的重要推动力。就图像本身来看,祝寿图像是具有精神意义的观念图式,其形成和传承皆以民俗背景为基础,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祝寿图像构成都是意在祝福生命,集中反映出国人对久寿、康宁、孝亲的现实渴望和积极乐生的生命意识。在我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祝寿礼俗中,国人一直注重孝道和尊老的传统,而作为一种文化折射,祝寿图像则可视为是以视觉艺术的形式
来图解与诠释孝道文化传统的某种“隐喻”。这种图像中所潜含伦理价值的现代意义与延伸价值在于:在频现信仰危机的当今世界,这类图像将有助于我们以新的视角审视民族精神和行为品质。
* 本文为教育部项目《民俗艺术视角下的祝寿图像研究》(课题号:14YJC760007)和安徽大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计划项目《安徽省民间美术教学实践》成果之一。
① 程波涛,男,安徽利辛人,艺术学博士,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民俗艺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