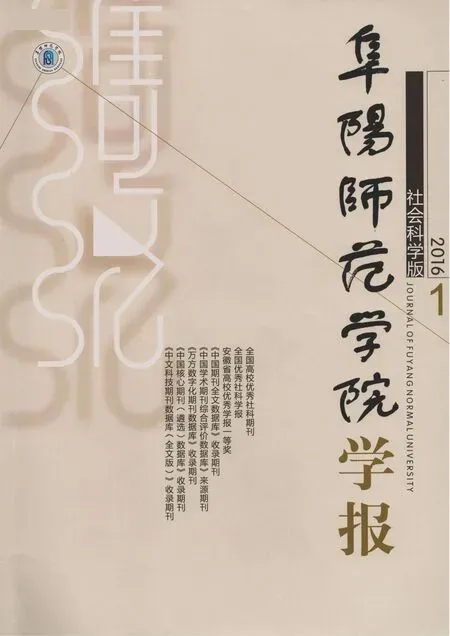楚地漆器纹饰与超现实主义绘画“梦幻”特征的比较研究
2016-04-16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100081
陈 莉(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楚地漆器纹饰与超现实主义绘画“梦幻”特征的比较研究
陈 莉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梦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而艺术是展示人类“梦幻”的重要渠道。楚地漆器纹饰云气流荡,事物处于瞬息万变之中,一事物可以幻化为他事物,人物或奇谲诡怪或飘然飞升,具有“梦幻”艺术效果。超现实主义绘画受到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影响,力求表现非理性、无逻辑的梦幻世界,也具有“梦幻”艺术效果。楚地漆器纹饰是人类对于宇宙混沌状态的集体记忆,体现了主客不分的原始思维模式和对世界的混沌体验。超现实主义绘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艺术家在倦怠于理性和秩序的生存状态下对于非理性世界的呼唤,是清醒的艺术家刻意制造的梦幻之境,折射出理性语境下人类的惶惑和恐惧。
关键词:梦幻;艺术;漆器纹饰;超现实主义绘画;比较
“梦幻”是人类的一种非理性生存状态,包括做梦、幻想、白日梦等。“梦幻”具有虚幻性、变化性、朦胧性、非理性、不可把握性等特征。“梦幻”状态体现在文学艺术中则成为一种艺术类型。这种类型的艺术具有如梦似幻的艺术效果。战国秦汉时期的楚地艺术与西方超现实主义艺术中都有着鲜明的“梦幻”色彩,折射出“梦幻”对于人类存在的重要意义,但这两类“梦幻”艺术又有着很大的不同。本文以楚地漆器和超现实主义绘画为比照对象,希望通过这两类艺术形式的比较能够更为深刻地认识“梦幻”与艺术的关系,也能对人类不同生存状态下“梦幻”在艺术中的不同表现有一定认识。
一
楚地主要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以楚国为中心,在地域上辐射到楚国的附庸国及周边诸侯国,在时间上延续到秦汉时期的文化概念。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长沙楚墓、曾侯乙墓、马王堆汉墓等一系列楚地墓葬考古工作的进展,辉煌灿烂的楚文化全面展现在世人面前,尤其是楚地漆器以瑰丽诡谲的色彩、惊彩艳艳的线条、如梦似幻的画面呈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
超现实主义是西方20世纪的一个重要艺术流派。这个流派以法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奥地利精神病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为哲学基础,力求摆脱现实映像,创造多义的梦幻世界。超现实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蓬勃发展,影响到文学、绘画、摄影等多个艺术门类。超现实主义绘画力图把梦境与现实统一起来,提倡写“事物的巧合”,倡导“自动写作法”,因而其作品具有梦幻感。代表画家有米罗、达利、恩斯特、马格里特等。
楚地漆器纹饰和超现实主义绘画虽然属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作为图像艺术它们同样创造了“梦幻”艺术效果。具体来看,这两种艺术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梦幻”特征:
首先,梦中的东西似乎都失去了份量,有一种虚无缥缈或飘然飞升的感觉。这一点在楚地漆器艺术和超现实主义绘画中都有很好的体现。在楚文化中有很多东西都如同云烟一样有着一种飘然飞升的感觉。如《庄子》和《楚辞》中就有不少餐风饮露、纵身一跃就能御风而行的飞升者形象。楚地漆器纹饰也常常给我们一种轻盈的,仿佛就要离开大地般的超脱感与升腾感。这种感觉首先是因为漆器上满布云气纹饰,具有云雾弥漫的艺术效果所造成的。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黑地彩绘棺上云气流荡,云气间又点缀着种种羽人仙怪、飞禽走兽,显得浪漫迷离。这种飞升感也来自漆器纹饰的线条化处理。甚至连各种动物也都要幻化为云气纹,因而在楚地漆器纹饰中几乎没有直线条,而曲线给人一种流动感,因而所有的漆器图案都给人以漫卷漫舒、云雾弥漫的感觉。如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彩绘凤鸟纹漆圆奁上,凤鸟被简化成没有份量感的线条。可以说,在楚地漆器上,我们几乎看不到有沉重感的物象。轻淡的云烟、具有流动感的曲线营造了一种如梦似幻的艺术境界。
超现实主义绘画中的景物也具有失去份量的感觉。如西班牙画家米罗的《哈里昆的狂欢》描绘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梦幻景象。在梦境中蜥赐、蛇、狗、蜜蜂等动物似乎都在分解、气化、上升以至在空中弥漫,一切都失去了重量,好像自由地漂浮在空中。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代表作品《天降》描绘了很多形态一致、但大小不一的男性,他们身着黑衣、头戴圆顶高帽,呈站立状,却像雪花一样漂浮在城市的上空。这些黑色剪影一样的人物也有一种失去份量的感觉。其实,在超现实主义绘画中这种失重感很多,巨大的石头会浮在空中,剪刀会离开了桌面炫富在空中,远山好像浮在海面上,等等,都体现的是梦中的情景。
其次,变形和幻化特征。这一特点在楚地漆器和超现实主义绘画也都有所表现。楚人认为,一切有形之体皆赖气化生而生成,整个世界中满溢着生生不息的气,生命也是一个气聚气散的过程,所以万物都没有固定的形体,万物之间可以变形、相互转化。龙凤的形象在楚地漆器最常见,但龙凤常与云纹或蔓草相互幻化,造成亦此亦彼的效果。如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三号墓出土的彩绘鸟纹卮,鸟的躯体和尾部幻化成蔓草的枝叶,造成动物和植物不分的梦幻感。1975年湖北凤凰山出土的豹纹扁壶,纹饰中的豹子根据需要被任意地拉长、弯曲、变形,幻化成似是而非的形象。任意变形是梦境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在超现实主义绘画中有更广泛的体现。如达利的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中有远山、峭壁,以及像面饼一样柔软变形的钟表,这些钟表有的被挂在枯树枝上,有的耷拉在桌子的边沿似乎很快就要坠落下来,有的贴在形状怪异的物体上。柔软的钟表形成了一种梦幻感。
楚地漆器纹饰和超现实主义绘画的重要价值在于超越日常生活和政治伦理构建了一种重要的艺术类型。春秋战国时期的北方中国已经经过了“天道远,人道迩”的反思,人的价值和理性精神得到了张扬。但是南方楚国地处蛮荒之地,依然有着浓厚的非理性思维。表现在艺术观念上则是北方中国已经在张扬“诗言志”的文以载道精神了,南方楚地艺术却离政治伦理教化观念较远,表达着对于世界的朦胧感受。如曾侯乙墓漆棺上绘有龙、蛇、鸟、兽、神人等近1000个交织纠缠、错综复杂的物象。尤其是无数条蛇纹穿插、缠绕、纠结在一起,大小不同的云纹彼此缠绕勾连,令人眼花缭乱,展现出一个神秘的梦幻世界。马王堆汉墓的黑地漆棺上,更是有似羊非羊、似虎非虎的神灵怪物若干,它们或骑马,或骑鹤,或奔跑,或拉弓搭箭,或嬉戏打闹,或玩弄活蛇,这些景象都具有超现实的特点。楚地漆器图案普遍具有各种植物动物交织并存、烟雾缭绕、缤纷多彩的特征。这样的纹饰与日常生活经验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以色彩和线条呈现了一个几乎是纯审美的世界。这种美几乎完全是符合康德关于美是无功利性的形式的定义。因而楚地漆器艺术有着较强的装饰性和审美性。
超现实主义绘画以摆脱日常生活经验和理性思考为出发点,努力挖掘人的先天精神本能,追求潜意识的情感流露和梦境般的视觉情景。如米罗的画中往往没有什么明确具体的形象,而只有一些按照感觉随意排列的线条和一些类似于儿童涂鸦的稚拙形状。他似乎什么都不想表现,什么都不想表达,只是随意地画出一种感觉而已。如米罗的《星空》中画了一些抒情性的线条,几只眼睛,一些零散的“米”字形图案,还有其他零零星星不知什么东西散布在画面上。作为接受者你几乎不能将这张画的标题与内容联系起来,你在这幅画中找不到有关星空的生活经验。这也许最符合超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受思想的支配但又不受理智的控制,超越一切美学或道德的成见。”[1]超现实主义力求不受理性的控制,不依赖于美学或道德偏见,用幻想和无意识去填补精神的空白。超现实主义画家甚至还倡导通过物象的任意堆积,形成令人惊讶的美,就像“在手术台上偶然发现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那样”[2]。这种奇异和梦幻的景象在理性世界是不可能的,但在梦境中却有着合理性。所以按照超现实主义的理论,你可以透过这些荒诞的画面去推测画面背后的潜意识,但不可以理性地分析这些画面所要传达的社会内容。因为潜意识是一种纯粹的心理活动,是自动产生的。艺术家所要做的就是忠实地记录通过自动流溢而偶然产生的种种想法。这样,艺术就表达了无利害关系的种种思想活动,而这一活动被认为真正体现或反映了人的本来面貌。作为一种生理现象,潜意识往往不包含深刻的社会内容,所以说超现实主义和楚地漆器艺术都创造了远离政治、伦理,远离日常生活的艺术范型。
“梦幻”是人类生存中的一种重要状态,人类存在虽然离不开对世界的理性分析能力,离不开算计,但人类不能过多沉迷于理性,正如人不能没有睡眠一样,人类不能没有混沌和梦幻状态。但很久以来“梦幻”状态却被人们忽略,直到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学才真正从理论上认识到非理性对人的重要意义,也是这些哲学家分析了艺术与梦幻的关系,指出艺术是人类回到“梦幻”状态的重要渠道。所以说,无论楚地漆器的“梦幻”,还是超现实主义绘画中的“梦幻”,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们以艺术的形式为人们揭示了“梦幻”生存状态,使人们深刻而全面地思考了人和艺术的问题。这样的艺术不是让观赏者回忆起日常生活,而是带观赏者进入一个虚幻的梦境。长期的理智和清醒,将会导致人的抑郁和疯癫。抛开清醒的理智分析,沉浸在某种没有目标的思绪中,做一个白日梦,或沉浸在这种作为艺术的白日梦中,对人类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享受,更是一种精神治疗方式。
二
虽然楚地漆器纹饰和超现实主义绘画都展示了“梦幻”艺术境界,但是它们却有着巨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不用专门去讨论的,但造成两种艺术“梦幻”不同的深层原因却是值得分析的。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楚地漆器纹饰所传达的情绪与超现实主义绘画所传达的情绪不同。稍微多了解一下楚地漆器艺术,就会发现无论是哪个墓葬出土的漆器,几乎都没有特别鲜明的个性情感,其中所体现的是一种比较模糊的情绪。因为几乎所有的楚地漆器纹饰都弥漫着云气纹,云气间点缀着形态模糊、朦胧的龙或凤,这些纹饰依照漆器形状均匀布置。因而,面对楚地漆器,我们找不到个性,也感受不到或抑郁或欢快的强烈情感。
虽然有很多超现实主义绘画中没有情绪,只有奇异的表现手法,但是在超现实主义绘画中,我们还是能够找到较为鲜明的个性和情绪。如前面提到的米罗的作品《哈里昆的狂欢》描绘了一场热闹的聚会,但蓄着胡子、叼着长杆烟斗的人却满脸忧伤地凝视着这欢快热闹的景象,透过房间的窗户所看到的幽蓝的夜空和风景,也透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内战的预感》是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代表作之一。在蓝天白云的背景下,画家运用细腻的笔法画了一个被肢解的人体,画出被肢解者痛苦的面部表情。如果说这是一个梦的话,那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梦。所以说,在很多超现实主义绘画中有着较为鲜明的个体情感表达。
同样在表现梦境,为什么楚地漆器云气纹表达了一种淡淡的思绪,却没有鲜明的情感,超现实主义绘画虽然也力求表达人的潜意识,但我们在这种潜意识表达中,还是能够找到较为明显的情感?我们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楚地漆器艺术是一种装饰图案,因而更加关注形式,而不关注内容,此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两种艺术形式恰好代表了人类生存的两个阶段。楚地漆器艺术出现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楚地,当时的江淮流域地广人稀,云遮雾罩,怪兽出没。这为楚人丰富的想象力提供了无尽的源泉。而楚人的想象中却隐含着人类关于宇宙的集体记忆。同样作为楚地艺术家的庄子在《应帝王》中讲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混沌的故事,说:南海之帝名叫儵,北海之帝名叫忽,中央之帝叫混沌。混沌待儵与忽甚善,儵忽为了报答混沌就用了七天的时间为混沌凿开了七窍。但七天之后,浑沌却死了。庄子讲这样一个故事意在告诉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本应如混沌一样不可被分析和理性切割。实际上这个故事也隐含着人类关于宇宙混沌状态的集体记忆。宇宙最初应当是一片渺茫望不到头的大海,或者是如同鸡蛋一样的混沌状态。这种关于宇宙最初状态的记忆隐约保留在世界各地的传说中。如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中也讲到了,很久以前,天地间混沌一片,如此混沌的世界运转了十万八千年,然后才有盘古开天辟地。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故事中都隐含着渺茫大水和混沌宇宙的记忆。《圣经》中也有洪水淹没大地,天地间一片茫然的记载。关于创世之初时间混沌的记忆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是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却被保存下来,且不断在梦境或艺术中出现。从《庄子》对于混沌的思维状态的崇拜,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得到楚文化与这种关于宇宙混沌状态的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同样,在楚地漆器纹饰上那些梦幻一般的纹饰并没有鲜明的情感表达。这是因为那些纹饰不是一种个体情感的表达,而是一种集体情感的表达。楚地漆器纹饰作为更古老的艺术门类所表现的是一个人类早期关于宇宙混沌状态的集体记忆。这种对于创世之初梦幻状态的回归,使人感觉到好像找到了自己的故乡,因而面对这种梦幻般的艺术——无论这种艺术是如楚地漆器一样散淡的云烟,还是一段没有明确表现内容的音乐——人有一种无思无虑,似乎又想了很多的感受。
超现实主义绘画虽然努力表现人的无意识状态,但是超现实主义画家是明确的创作个体,他们有着鲜明的个性和不同的生活经历,因而可能会将个体无意识和梦幻状态展现在绘画中,但由于他们有着太强的个体意识,对身边的生活有着过于清晰的记忆,因而不能与冥冥之中的力量对接,不能将潜藏在意识深处的集体记忆展现在绘画中。正如荣格在分析《浮士德》时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是一种超越了人类理解力的原始经验,它对艺术家的能力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唯独不需要来自日常生活的经验”[3],显然作家将较多的个性和日常生活经验带入到创作中,会影响集体无意识的表达。可能也正因为此,集体无意识主要出现在神话、传说等个性不是十分鲜明的集体创作之中。
其次,我们在楚地漆器纹饰中几乎完全找不到现实生活中的景象。那流荡的云气,那点缀在云气间的神灵鬼怪等等都不是现实生活景象的写照。但是超现实主义绘画不同,虽然它力求表现人的无意识和梦幻状态,虽然梦境中的景物会失去份量、会变形,但是我们依然能在超现实主义绘画中找到生活经验的表达,以及这些作品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所以说,超现实主义力求呈示一个梦幻的、神秘的世界,但超现实主义作品却不能完全带人进入一个温和的梦境。同样是对“梦幻”艺术境界的追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同的结果?
这是因为楚地漆器纹饰是身处梦境之中对于梦境的表现,而超现实主义绘画是身处理性状态的人类对梦幻状态的刻意追求。战国时期,北方中国理性思维已经相当盛行时,南方中国依然处于懵懂状态,还不能分清楚梦和现实的差异,或者他们不愿意分清楚梦和现实的差异。正如《庄子·齐物论》中所写的:“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4]101在这个故事中,庄周在梦中变为蝴蝶,翩翩起舞的蝴蝶适性而飞,并不知道自己就是庄周。庄周醒后不知是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周。在庄周的梦中,物我界限消解融合,梦和醒的界限消融,最终达到物我泯合的境界。楚人认为一切都是梦,连人生都是一个梦,“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4]95。这当是处于主客不分、物我不分、天人合一状态的楚人对世界的真实感受。这一感受虽不具有科学依据,但却符合心理真实。正如卡西尔所说:“虽然神话是虚构的,但它是一种无意识的虚构,而不是有意识的虚构。”[5]表现在楚地漆器中万物交融的梦幻境界是这种主客不分的梦幻哲学的图像化。可以说漆器纹饰是身在梦幻中的楚人对梦幻生存感受的再现,是梦中之梦。
但超现实主义绘画却不同,它产生于理性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中世纪的神灵隐遁之后,人成为世俗生活的主人,但人的物欲和贪婪也彻底摧毁了这个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社会弥漫着强烈的厌世、悲观的情绪。超现实主义者们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以及科学与理性信仰的危机,他们力求逃避现实,追求梦幻,以脱离现实的悲哀与残酷。可以说这是理性时代人类对于现实的逃避,对于真实内心的呼唤,但是身处孤独、恐惧和现代世界危机中的人们已经找不到回到宁静内心的路径。于是,超现实主义者们常常用一些非常离奇的方式寻找自己的潜意识。如达利不惜以忍受饥饿的折磨为代价使自己进入那种难得的幻觉状态。米罗则在鸡舍中插进涂满颜料的图板,让小鸡踩啄,利用其留下的痕迹,刺激自己的创作想象[6]。还有些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为了追求无意识书写,服用毒品致幻,让别人记录他无意识状态下的呓语。然而,这种寻找梦幻和本真自我的途径显得是那样的牵强。甚至超现实主义后继艺术家处心积虑地发明创造一些怪异、轰动的艺术创作手法,将庸俗、低级的因素引入艺术领域,最终使超现实主义沦为没有实际价值和意义的技术拼凑,成为无人能接受和理解的梦呓。所以说,超现实主义绘画是已经进入理性生活状态的人对于梦境的渴盼。但是在一个精神困顿的时代,人们非常倦怠,却回不到梦境中,灵魂得不到休憩。所以说,超现实主义绘画虽然希望表达超越现实的梦幻世界,但是他们的作品却更具现实性,折射着艺术家对于现实的认识。
神秘、恐怖是梦境中常有的感觉。这一点楚地漆器艺术和超现实主义绘画都有体现,但造成这两类艺术神秘、恐怖的原因却不同。楚地漆器的色调以红、黑两色为主,其特点是“朱画其内,墨染其外”,仅这两种沉寂凝重的色彩搭配在一起放在墓葬中就有一种神秘、恐怖的气息。楚地作为地处蛮荒之地的落后诸侯国,在战国时期依然有着浓厚的巫鬼文化。楚地文化中常见神灵鬼怪。楚地漆器无论造型还是纹饰都常常表现神灵鬼怪形象。如楚地墓葬中的镇墓兽大多口吐长舌、两眼圆瞪,头插巨大鹿角,全身髹黑漆褐色云纹,形象恐怖,体现楚人的灵魂不死观念。屈原的《招魂》中那“魂兮归来”的叫声充满了恐怖色彩。在曾侯乙墓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绘漆棺上都有神情诡异的巫师形象和怪神图案。所以说,楚地漆器纹饰中的神秘色彩的一个文化渊源是神秘恐怖的宗教。
超现实主义绘画中的恐惧不是来自神灵,而是来自人对悲哀和残酷现实的恐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欧洲经济萧条,世态炎凉,社会上弥漫着强烈的厌世、悲观情绪。战争摧毁了房屋,也摧毁了传统观念,一种推翻一切的思潮席卷而来,那也是一个宗教信仰遭到怀疑的时代。超现实主义绘画的画面常有一种失衡感,常表现血腥的内容。米罗在自己的画中把人的头、手、脚及肢体七零八落地分解开,改变身体各部分的比例,把比例夸张到极致,充满断裂和恐怖感。如《静物和旧鞋》中有旧鞋、酒瓶、插进叉子的苹果,还有一端变成一个头盖骨的切开的面包;背景是朦胧、模糊、捉摸不定的空间。整个画面让人感到恐惧和痛苦。超现实主义的理论批评家布勒东力求把毫不相干的事物结合在一起,产生尖锐冲突,显示极具张力的美感。这种形式被称作痉挛性的美。由于超现实主义创作了一个不合逻辑的变形、扭曲的世界,因此,超现实主义绘画不能带人进入一个曼妙的梦境,相反常常会令人焦灼、不安。《内乱的预感》构造了一个血腥的梦境,天空乌云密布,地上一片狼藉,惨不忍睹,画面中央是一个残破的身体,痛苦的面孔朝向天空,歇斯底里地嚎叫着,恐惧和不安笼罩在这幅作品上。
所以说,楚地漆器纹饰与超现实主义绘画都有着较为浓厚的神秘气息。但在这两种艺术中神秘气息的来源不同。楚地漆器纹饰的背后是神秘的原始宗教,超现实主义绘画则是神灵消失后,孤独的人对于世界的恐惧和神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的生存状态应当是理性与非理性、现实和梦幻的统一体。梦幻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一种状态。庄子的哲学和楚地漆器艺术为我们展现了人类早期的梦幻生存状态。这一梦幻状态折射出人类对于宇宙混沌状态的集体记忆,体现了主客不分的混沌思维方式。超现实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失去安全感和梦境的情况下,认识到了梦幻和无意识对人类的救赎作用,因而力求通过艺术的形式回到梦幻和无意识的努力,因而超现实主义绘画中充满了矛盾和张力,而楚地漆器艺术直接就在梦中,是梦还没有醒来时的混沌状态。
参考文献:
[1]金·格兰特.超现实主义与视觉艺术[M].王升才,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81.
[2]杰里米·沃利斯,琳达·博尔顿.立体派艺术家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M].王骥,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 79.
[3]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三联书店,1987:129.
[4]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15.
[6]鲍诗度.西方现代派美术[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326.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u Lacquer Ornament and Surrealist Painting
CHEN L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Min 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Dream" is a special way of human cognitive world.Art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to display the "dream" of human beings.The Chu lacquer ware is covered with cloud,there is a sense of fantasy.Surreal painting attempts to show the irrational,illogical fantasy world,but also has a "dream" effect.Chu lacquer decoration is the collective memory about the universe chaotic state,which reflects the primitive thinking mode.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the artists became weary of reason.They called for the irrational world,and expressed the subconscious in the art.
Key words:fantastic; art; lacquer decoration; surrealist painting; comparison
作者简介:陈莉(1969-),女,陕西咸阳人,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和中国古典美学的教学和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5
DOI: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1.012
中图分类号:J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310(2016)01-006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