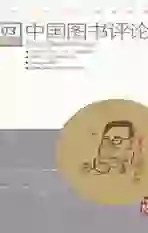从三种聚集形式看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境况
2016-04-15郎静
郎静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美]安德森,吴轈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理解大众文化》,[美]约翰·费斯克,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一些人偶然发现他们彼此站在一起,仅仅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们获得一个组织化群体的特点。一千个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的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群体。”[1]因此,在勒庞看来,“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2]也就是说群体的形成在于是否他们的情感与思想都关注于同一件事以至于独立的个人成为群体中的一个分子。而群体一旦形成便拥有了共同的群体心理,在群体心理的引导下,积极主动地朝着群体的既定目标前进。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青年,作为社会学与文化学意义上的群体概念,是伴随着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在儿童和成年人之间并不存在“青年”这一独立的社会和文化群体,一直到1789年撼动欧洲大陆的法国大革命爆发,青年群体积极响应大革命的号召,并作为历史的参与者投身到改造社会的大革命中。在近两个世纪以后的1985国际青年年,联合国才首次明确地将15到24周岁之间的人定义为青年。
19世纪中叶,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被迫打开国门,开启了畸形的现代化进程。面对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探求救国救亡的复兴之路。在他们当中,一大批有识的青年知识分子觉醒者在启蒙先导的指引下踏上了救亡图存的征程,为千疮百孔的中国带来了希望与理想。当我们谈到“新文化运动”、谈到“五四青年运动”时,就不能不提及启蒙思想的先驱者陈独秀,他在1915年为《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开宗明义地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强烈愿望。陈独秀写作这篇发刊词时已36岁,但面对民族危亡、社会动荡的局势,他依然怀有青年人的激情,与一切“陈腐朽败者”作斗争。他认为青年是历史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在《敬告青年》开篇就号召青年应“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并且应该与“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的伪青年,“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绝不作迁就依违之想”。他在文中响亮地提出“青年六义”,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以此进一步明确了“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在这里“敬告青年”不仅是唤醒“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告别千疮百孔的“老大帝国”[3],步入朝气蓬勃的“青年中国”的一封乌托邦理想的宣言书。
时至今日,整整百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的理想已经一一实现。1949年我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完成了民族救亡的使命翻身做主,成为国家的主人;1978年改革开放,使中国告别文革的阴霾,真正地打开国门参与到世界的竞争当中;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令世界瞩目。在这些巨大成就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前赴后继的结果。但是就目前出现的文化现象来看,青年这一特定群体本应具备的源于“五四”所承载的启蒙激情、个性主义、政治理想等精神在当代似乎相当程度地弱化了,而“消费主义”却发展起来。以目前的时间节点来说,当代青年指的是在1990年到2000年之间出生的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90后。本文选择了三个较为典型的90后青年聚集空间进行分析,从中似可窥见当代中国青年精神境况的某些面向。
一、电影院:娱乐方式粉丝化
据2015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显示,从2014年暑期档观众的年龄构成来看,18—24岁年龄段的观众所占比例最大,达到42.13%,24岁以下的观影群体占据总人数的51.54%;从暑期档观众的职业构成来看,学生群体和公司职员群体成为观影的主要人群,分别占观影人群总数的38.00%和37.60%[4]。由此,可以看出电影院是当代青年聚集的空间之一,而看电影也成为当代青年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
在2014年7月,即“国产电影保护月”暑期档上映的影片中,票房过亿的影片有六部,分别是《老男孩猛龙过江》(7.10)、《小时代3:刺金时代》(7.17)、《京城81号》(7.18)、《后会无期》(7.24)《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7.31)、《闺蜜》(7.31)。其中票房收入位于前两位的影片是《后会无期》(62946万元)和《小时代3:刺金时代》(52596万元)[5],这两部现象级的“粉丝”电影也成为2014年暑期最具话题性的影片,学界对于它们的讨论已经超越电影本身,而将其作为当下青年文化的一个折射,即娱乐方式粉丝化。
在约翰·菲斯克看来,在资本运作的条件下,大众不可能生产出自己的文化产品,而只能在消费环节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他认为,粉丝文化就是在工业化社会中出现的一种大众文化的“强化”形式,而粉丝则是一些“过度的读者”[6]。因此,生产环节的发出者,即我们所谓的“偶像”,其行动的出发点和动力就是如何最大程度地将以青年粉丝群为主的受众纳入其文化产品的运作中;而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得以聚集成为粉丝群,并获得暂时属于某一特定圈子的行为方式和集体心理。正如勒庞所说,“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7]
《后会无期》的导演韩寒和《小时代》的导演郭敬明是活跃在青春文坛上的领袖人物,有着强大的偶像魅力和小说积累的粉丝基础,他们不仅对青年流行文化和情感诉求有着精准的把握,而且谙熟文化产业运作的秘密。在对两部影片观看原因的调查中,位于《小时代3》观影原因前三的理由是:“读过原著小说”“观后可以吐槽”“与剧情产生共鸣”,分别占45.54%、42.33%和35.40%;《后会无期》则以“韩寒的号召力”(77.08%)、“与剧情产生共鸣”(50.00%)和“社交圈的重要话题”(47.92%)成为其高票房的保证。[8]加之,《小时代3》中主创演员超高的偶像号召力和《后会无期》中对主流话语的微抵抗,使得青年观众在景观建构的玻璃橱窗中相信“友谊地久天长”的神话,在戏谑与调侃中认定自由就是一场说走就走又无疾而终的旅行。在所谓的“情感至上”和“自由叛逆”的幻象中,粉丝群体再一次以票房完成了对“偶像”的朝拜,在膜拜中完成了社会裂隙的幻象性弥合。
二、学校:行为方式暴力化
如果说电影院是当代青年主要的娱乐消费空间,那么,毫无疑问,另一个大量聚集青年群体的空间就是学校。学校对于青年来说,是最重要的青春记忆场。
1986年4月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适龄的儿童和少年必须接受9年义务教育,这也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义务教育推行的近30年来,根据《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初中学校5.26万所(其中职业初中26所),招生1447.82万人,在校生4384.63万人,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3.5%,初中毕业生升学率95.1%;全国高中阶段共有学校2.75万所,招生1416.36万人,在校生4170.65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6.5%。[9]在教育改革越来越惠及广大青年的同时,暴力的因子在逐渐在校园中弥漫开来。纵观媒体上所披露的校园暴力事件,我们可以发现,校园暴力开始呈现出内转的趋势。校园暴力已经不局限于来自非青年学生群体对在校学生的暴力侵害,而更多的发生在青年学生群体的内部,尤其是在初高中学生群体中。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民族未来希望的公共空间,使得这个曾经是启蒙思想诞生的地方,会蒙上如此的阴霾?
近年来,媒体上所披露的校园凌辱暴力事件屡见不鲜,仅2015年上半年,引起强烈社会关注的事件有:贵州毕节中学生围殴惨案(2015年7月4日)、江西永新初中女生围殴事件(2015年6月22日)、河南信阳商城县数百中学生被曝在树林里赤膊群殴,堪比古惑仔(2015年6月26日)、广西南宁一名女生遭多名女生群殴暴力(2015年6月26日)、江苏宿迁初二男生遭多名同学殴打致死(2015年7月14日)、江苏高邮女生打人事件(2015年8月14日)、南京市浦口区陡岗中学初一男生遭学长狂殴吐血,被逼粪池添尿(2015年6月9日)、四川一少女遭围殴脱衣(2015年6月25日)。通过对校园暴力凌辱事件的梳理,我们发现在以往以男生为核心的校园暴力群体之外,“女生暴力”事件也频频发生。
2014年9月21日晚,在陕西省吴起县高级中学六名高二女生将几位高一学妹带到宿舍内进行了长达8个多小时的辱骂殴打,甚至强迫脱衣,拍摄半裸照片,欲强迫其“卖处”,并持刀威胁受害人不得将此事告知老师和家长。在被打的5名学生中,有4名学生受伤较重,其中2个被打成耳膜穿孔。
2015年6月22日,一则名为“江西永新县多名女初中生围殴女生逼脱衣合影”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在长达5分33秒的视频中,1名穿着牛仔裤的女生跪在地上面对着其余5名女生。这5名女生连番对下跪女孩扇耳光,用脚踹其后背,打人过程中嬉笑、嘲骂不绝于耳,而被打女生一言不发,上身挺直,双手护着自己的脸,最后,为首的女生要求下跪女孩自扇耳光。在长达5分多钟的围殴之后,其中三名女生逼下跪女生脱上衣自拍合影,负责自拍的女生面露微笑,另两名女生比出V的手势。
从上述的两个具体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校园女生暴力具有三个特点:首先,暴力的施受双方呈现出“多与一”的对立。施暴的一方以矛盾的直接主体为核心,向外扩散至朋友甚至是朋友的朋友;其次,女生暴力多与身体侮辱和性有关,主要包括言语辱骂、下跪、扇耳光、强迫脱衣等;第三,暴力与自媒体的结合。旁观者以冷漠、娱乐的姿态用手机拍摄视频、照片,上传至网络,在同学之间传阅,无形中给受暴者造成了“二次伤害”。而当网络舆论一边导向受害者之后,新一轮的网络言语暴力也降临在施暴者的身上。由此可见,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暴者都会被笼罩在暴力的氛围中,无一幸免。
在这些令人发指的暴力事件背后,我们需要拷问:是什么使这些处于花季或即将处于花季的少男少女们在人一生中最美的年龄,却成为同龄人眼中恶魔般的存在?是什么导致暴力在青年群体中悄然弥漫?在诸如完善法律惩罚制度、加强学校和家庭监管力度之类的后发的、强制的补救举措之外,是否应该回过头来反思校园暴力之核———施暴者,产生的社会根源?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资本话语、权力机制成为社会行动准则的语境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心智仍处于叛逆阶段的初高中学生更加迫切的需要他者的认同,而在消费社会中,他者的认同往往以主体所掌握的资本为先决条件。在学校的场域中,“唯分数论”的功利主义盛行使得学生被标签化为三六九等,金字塔最上端的是优等生,最下端被贴上了问题学生的标签。当问题学生无法在学校的场域中获得认同,又难以排解由此带来的不适“症状”时,他们就会想当然地诉诸于这样一种简单粗暴的“丛林强者的幻象”。在施暴者拳头的暴力背后,实际上是社会权力机制在校园中的微缩模型,折射出当前社会阶层上升渠道的失效和青年心理建设的缺失。
三、电子屏幕:思维方式平面化
20世纪30年代,拉康在重新阐释和改造弗洛伊德整个“无意识”领域的基础上,提出了富有独创性的“镜像阶段”理论。这一理论是主体心理发展最初的一个阶段———前语言阶段,处于“想象界”中。镜像阶段发生在6到18个月的婴儿生长期,此时,它只知道“他者”的存在而并不知道“自我”,但它已经具有将自己想象成整体的能力,因为它们知觉到的“他者”是一个整体存在。因此,当它被放到镜子前的瞬间,它第一次把对它来说相互分离的身体看作是一个整体,正是通过镜子这一他者的回应,“自我”开始呈现为人对自身的一种想象关系。如果说,婴儿通过镜子获得了想象性的自我整合,那么在象征界,通过对语言符号秩序的熟稔和网络媒介的推波助澜,青年则通过电子屏幕获得了一种幻象性的主体间性。因此,电子屏幕成为当代青年一种独特的聚集空间。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90后青年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网生一代”,因为对于80后来说,网络是作为一种新事物被接受;而对于90后来说,网络早已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根据《第3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以10—39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比例合计达到78.1%,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31.5%;从网民的职业来看,学生群体的占比最高,为23.8%;从网络传播来看,10—29岁的年轻人相对于其他群体更乐于在互联网上分享,尤其是10—19岁的人群,有65.9%的网民表示比较愿意或非常愿意在网上分享。在他们当中,青少年群体的网络舆论表达意愿更强烈,尤其是10—19岁网民网上发言积极性最高,有50.2%的比例;其次是20—29岁的网民群体,有46.6%的比例。[10]通过上述的数据,我们可以想象在时间的分秒之间,有多少青年正在聚集在电子屏幕前,低头专注于其中。QQ、微博、微信、人人、豆瓣、社区等微媒体的出现,不仅改变了青年参与社会交往的方式,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种网络化的平面思维模式。
网络思维,顾名思义,是在平面维度上的交错共生,通过表层交往联系在一起的能指符号,而能指符号间之所以能够不断滑动游移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在网络思维控制下,人通过“差异”的他者来确定自身的存在。既然如此,这里吊诡的是,我们如何来确定他者的意义?诚然是通过另一个“差异”的他者来确定,以此类推,我们发现在网络思维中,不存在“自己”,而只有“差异”的他者,我们一直在遵循着无数的“他者”为我们建构的话语系统来行事。在“他者”所建构的网络思维中,由于电子屏幕所代表的平面维度成为他者行事的准则,从而导致了世界垂直维度的缺失和平面化幻象的产生,因为在“变化的当下”,所有的“他者”看起来都可以通过电子屏幕确确实实又转瞬即逝地出现在每个地方。克里斯琴斯在《媒介伦理》中引述卡斯·R.桑斯坦的观点,“无限制的新闻和信息不能促进公共话语的生成,而是粉碎公共话语的‘噩梦。生活在这些加强自身观点的新闻节目、博客、播客和社会媒体中,公民倾向于过滤掉其他观点,生活在意识形态单一的‘个人日报中。”[11]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青年是“个人日报”的主要的读者群之一。网络看起来把世界联系成一个地球村,但在某些层面上,却造成了去公共的世俗化,从而导致更加严重的疏离和冷漠。
四、走偏:从想象的共同体到幻象的共同体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两种最初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的基本结构,就能明白何以这个转型对于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诞生会是如此重要了。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12]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鲁迅、沈尹默等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以《敬告青年》为第一炮,内容涉及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方面,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以其鲜明独特的对中国现状和问题的思考和表达,对中国青年和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青年》创刊之初多以综合性的评论文章和介绍西方作家作品为主,个人创作较少,因此销量不多,每期仅印一千份;1917年初,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正是揭开了“文学革命”的旗帜,除了正面宣传外,还有钱刘二人合演的一场“双簧戏”,可以制造论战,引起社会舆论和关注。此后,杂志的销量渐增,达到一万五千份之多,大专院校及中学生争先购阅,可谓盛极一时。正如安德森通过菲律宾民族主义之父荷赛·黎萨(JoseRizal)的《社会之癌》(NoliMeTangere)来解释“想象的共同体”是所言:
“从一开头就是这样的意象———数以百计未被指明、互不相识的人,在马尼拉的不同地区,在某特定年代的某特定月份,正在讨论一场晚宴。这个(对菲律宾文学而言全新的)意象立即在我们心中召唤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且,在‘我们会用一种现在也许还认得出来的方式来描述‘在安络格街上的一栋房子这段句子里暗示的‘认得出房子的人,就是我们—菲律宾—读者。这栋房子从小说的‘内部时间向读者的日常生活的‘外部时间的因果推移,犹如催眠术一般地确认了一个单一的,涵盖了书中角色、作者与读者,并在时历中前进的共同体的坚固的存在。”[13]陈独秀所提出的“青年六义”就是特定历史阶段共同体所想象的一种坚固的存在,在启蒙思想的引领下,进步觉醒的知识分子先驱将青年紧紧团结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号召青年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正是无数青年的前赴后继,成功地塑造了“青年中国”的现代认同,在改变自身的同时也改变着世界。青年,与个人而言,始终是处于变化中的群体,当“五四一代”青年结束其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成为当代青年历史书中的存在时,以启蒙为核心的想象的共同体在消费社会的转型中,转变为以资本-权力为核心的幻象的共同体。
想象的共同体与幻象的共同体,一字之差,却折射出当代青年的精神境况,即不知何为宏大而走向橱窗景观、不知何为理性而走向暴力、不知何为意义而走向虚无。在陈独秀所提出的“乌托邦理想”成为现实后,当代青年失去了想象的能力,进而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找到终极意义,而只能被异托邦幻象引导着去寻找那永在途中的、又转瞬即逝的意义。
青年似乎正在消失,绝对不是少数学者危言耸听的论断,而是在本雅明“救赎”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本雅明认为,“史学不是建筑在均质的、空洞的时间之上,而是建筑在充满着‘当下的时间之上。”[14]因此,对当代青年来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应该是一个从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中爆破出来的一个填注着当下时间的过去;但是消费主义的幻觉阻断了青年倒着跃向过去的辩证跳跃。因此,艺术批评必须扫清辩证跳跃道路上的障碍,将每一个“当下”重新拼装,恢复历史的记忆,使前辈们对当代青年有所言说。
注释
[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2]同上。
[3]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开篇即言;“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4]中国电影家协会:《2015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产业研究部编,世界图书出版社北京公司2015年版,第187—188页。
[5]同[4],第162—164页。
[6][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7]同[1],第14页。
[8]同[4],第195—196页。
[9]《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7-30/7437057.shtml。
[10]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3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5年1月,http://www.cac.gov.cn/201502/03/c_1114222357. htm。
[11][美]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媒介伦理:案例与道德推理》,孙有中、郭石磊、范雪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12][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轈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13]同[12],第25页。
[14]陈永国、马海良:《本雅明文选》,张耀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