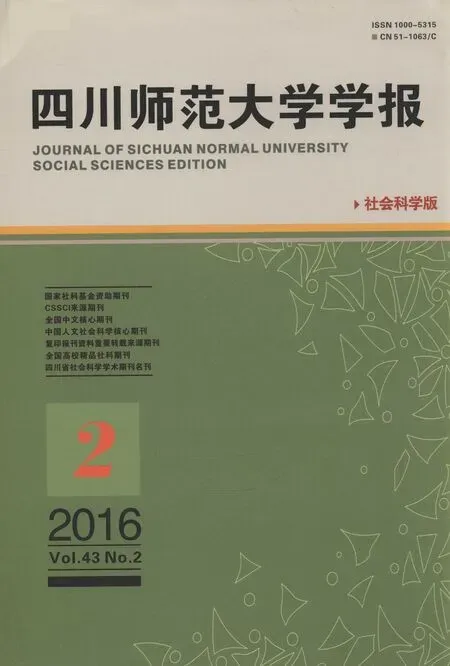“筑城固守”与“荆蜀相资”:晚宋川蜀防御政策的调整及影响——以钓鱼城战役前后为中心
2016-04-14彭锋
彭 锋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筑城固守”与“荆蜀相资”:晚宋川蜀防御政策的调整及影响
——以钓鱼城战役前后为中心
彭锋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晚宋钓鱼城战役可以放回到当时的川蜀整体防御布局当中进行考察,并可重点从“筑城固守”和“荆蜀相资”两方面探讨钓鱼城战役前后川蜀防御政策的调整,包括南宋朝廷中关于守蜀的争议和具体防御政策的落实,以进一步检讨强本弱末的国策惯性力对于川蜀防御及钓鱼城战役的影响。以钓鱼城战役为坐标节点,以运作其间的人事和制度互动为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钓鱼城的成功坚守与此前南宋政府做出的一系列调整策略有关,而最终之陷落也同样与这些策略的制定和施行紧密关联。
关键词:南宋;川蜀防御政策;筑城固守;荆蜀相资;钓鱼城战役
南宋对于川蜀的防御经营非常用心,宋高宗南渡敉平诸盗,稳住政权之后,即致力于川蜀防御体系的构筑,此后南宋历朝君主对于川蜀的防御经营也都非常重视。宋祚之持续,多赖川蜀地区军政防卫机制的正常运转,钓鱼城战役的胜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与对金作战不同,蒙古对宋分别从京湖、两淮和四川三路发动进攻,后更有“斡腹之谋”策略的施行。宋廷为避免各主要战区的割裂,协调各战区间守御战备,遂专门设置策应使司,其职多由居三边之中的京湖帅臣兼任,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两者的协调作战能力。余玠入蜀措置战守事宜,与京湖帅臣合力经营,重新构筑起川蜀防卫。长久以来,有关南宋时期川蜀军事防御机制的探讨不乏其人,也形成了较为可观的研究成果①。本文②则拟以合州钓鱼城战役之前的川蜀防御调整为切入口,探讨该防御机制的得失,又借此进一步检讨在南宋末期强本弱末的国策惯性是如何影响军事防御机制的正常运转,以及在此时期之内宋廷的防御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调整和这些变化调整对战局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一钓鱼城战役前川蜀守御战备
自端平元年(1234)蒙古灭金之后,宋蒙战端随之正式全面开启,宋廷企图乘蒙古灭金北撤之机收复旧疆,发动三京之役;蒙古则于次年以宋败盟为由沿边区兴兵大举攻宋③,马首所向,无不摧破,至“瞰临江口,有长驱之势,威震荆、楚”[1]400。端平三年(1236)九月二十九日,沔利都统兼关外四川安抚、知沔州曹友闻战死,蒙古军自此而长驱入蜀[2]13232。到十二月,“鞑靼国兵入普州、顺庆、潼川府,破成都府,掠眉州。一月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3]94。自此川北门户洞开,四川大部均遭陷落,所剩唯四川东部一带,“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尚在宋廷控御之内。高宗南渡之后苦心致力经营起来的川蜀防御体系,至此已遭重创,新的防御机制亟需重建。鉴于现实之种种形势,川蜀防线不断受压下移,由川西北往东推进已经成为现实之必然选择。
众所周知,军事防御的建立仰赖军需补给尤其是军粮的补给为多。原来宋军驻扎的川蜀地区,“自董居义丧蹙国,郑损弃五州并边,膏腴之地人莫敢耕,每岁官失就籴之粮七八十万斛,四大军岁给粮百五十万斛,其水运者裁三之一”,但“自绍定五年(1232)以后,官既失籴,而关之内外七十余仓皆为灰烬,所谓百万斛者既无从出,所仰给者惟一分水运耳”[4]卷十九《被召除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四札》。在这种情形之下,军需补给对于水运的依赖程度较之前加深。为避免水运失期,粮道阻绝,造成诸军乏食,宋廷一般都在大军驻扎地建造粮仓,以备不时之需。自蒙古侵入后,川蜀地区经蒙古军蹂躏殆遍,城镇空虚,仓廪如洗。川北大部分地区已经失陷,在军事上出现兵力耗散、士气不振、将心不稳的局面,之前较为严整系统的边区防线已经很难重新搭建起来。在这一大背景下,南宋朝廷众臣就如何部署蜀中防务展开了激烈讨论④。为尽量全面展示决策讨论及施行诸层面,以观其光影映照之处,下文就此分头论述。
嘉熙元年(1237),行都大火,也即川蜀大部失陷次年,牟子才应诏上封事,乘此言及蜀中防御的举措。他说:“蜀当以嘉、渝、夔三城为要,欲保夔则巴、蓬之间不可无以控扼之,欲保渝则利、阆之间不可无屯以遏截之,欲守嘉则潼、遂之间不可无屯以掎角之,屯必万人而后可。”[2]12357主张调重军屯守,扼住战略要害之地,成互为掎角之势,以便联合行动以防御蒙古军的分路进击。此后的守蜀策略大致循此一思路展布施行。在此基础上,牟子才复又言:“全蜀盛时,官军七八万人,通忠义为十四万,今官军不过五万而已,宜招新军三万,并抚慰田、杨二家,使岁以兵来助。如此则蜀犹可保,不则出三年,蜀必亡矣。”[2]12357牟氏提出增强兵力、绥抚边众夷酋的守蜀之策非常切合实际。但是,民兵用得好,可以助朝廷一臂之力,一旦“民兵散,不惟无以御寇而反为寇”[5]卷三《跋沈君迪丁酉上书》。事实上,尽管当时如牟子才之类奏言虽不在少数,但在朝廷中却仍然一度有弃蜀的论调出现,足见当时蜀事之艰难和棘手程度。
如南宋名臣、潼川府人吴泳,在端平三年(1236)上《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中言:
自丁卯曦乱兴沔而权臣已有弃蜀之说,自己卯寇入汉中而廷臣又有无蜀亦可立国之论,自辛卯敌兵破利入阆而襄阳帅臣复有扼均、房守归、峡之策。……何待蜀之薄如此耶?三京之师弃资粮如泥沙,至蜀饷科降则吝。北使之遣,捐金帛如粪土,至川阃奏请则啬。……然闻敌兵之入利路,诸司榛桩积已荡尽于广都劫船之日,根本扫地,公私赤立,似未可以虚文救之也。[6]192
据此,知宋廷中对于川蜀的防御态度一直存有异议,吴泳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他们对于弃蜀的论调嗤之以鼻,并主张加大对川蜀的财政支持力度,重新措置防御。弃蜀之论既遭否定,恢复蜀中守御的策略随即逐步着手施行,其中尤以筹备军粮、缮城自守为急务。
淳祐二年(1242),朝中论蜀事又愈急,《宋史全文》卷三十三对此有较详记载。为方便论述,兹录移如下:
四月癸亥,仓部郎官赵希塈进对言:“蜀自易帅之外,未有他策。”上曰:“今日救蜀为急,朕与二三大臣无一日不议蜀事,孟珙亦欲竭力向前。”希塈奏:“当择威望素著之人于夔峡要害处建一大阃。”上曰:“重庆城坚,恐自可守。”希塈奏云:“重庆在夔峡之上,虏若长驱南下,虽城坚如铁,何救东南之危。”上然之。
五月甲午,新知梧州赵时学陛辞,言吴玠守蜀三关,今胥失之,固宜成都难守。上曰:“嘉定可守否?”时学奏:“若论形势当守重庆。”上曰:“若守重庆,成都一路便虚。”时学奏:“重庆亦重地,可以上接利、阆,下应归、峡。”乙巳,尚右郎官龚基先入对,言上流事。上曰:“上流可忧。”基先奏:“施国之门户,荡无关防,(存)亡所系,岂可不虑?”丁未,右正言刘晋之言:“蜀祸五六年间,历三四制臣,无地屯驻,独彭太雅城渝为蜀根本,不然蜀事去矣。今宜于重庆立阃,庶可运掉诸戎。愿早定至计,料简边臣,俾往经理,则蜀可为也。”上然之。
六月甲寅,仓部郎官李鋂进对,乞广求备御之方。上曰:“秋风已近,去岁蜀事大坏,今当如何为策?”鋂奏:“陈隆之因成都城故基增筑,未为非是,第功力苟且,识者逆知其难守。臣尝问其方略,但云誓与城存亡而己。未几为田世显所卖,城门夜开,隆之衂焉。”上颦蹙久之。[7]2560-2561
据上可知,当时朝中对于守蜀的具体策略,尤其是四川置司治所有过讨论,理宗为此向臣下有过反复征询,以备求做出一较为合理的决定。理宗先是和仓部郎官赵希塈言守重庆,赵趋保守,且以东南安危为藉口,主张守夔峡;理宗和赵时学讨论时更进一步提出守嘉定,甚至言若守重庆则成都一路空虚;后听取右正言刘晋之意见,“于重庆开阃”,即在重庆府设立制置使司。从君臣奏对的内容中可窥知,理宗皇帝起初和孟珙一样态度较为积极,不欲一味退守,欲将守蜀力量的布置极力向前推进;最后综合考虑众人意见,做出设制置使司于重庆的折中决定。这里面当然也考虑到彭大雅所筑“重庆城坚”、“为蜀根本”的因素。从后来的战事发展来看,于重庆府设制置使司的意义是积极有效的,它对于统辖川蜀军务、加强川蜀防卫能力乃至于钓鱼城战役成功阻击蒙军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诚如学者已指出的,“为抵抗北方金、蒙长期以来的军事压力,南宋在巩固川蜀、荆湖、两淮边防线上,用力最深,成效也相当显著。然而,当蒙古选择采取夹击攻势,开辟西南战场,企图由云南进犯广西,迫使宋廷需采取紧急应变措施,来应付新的考验。”[8]225而在这三边之中,最关国势危亡的就是川蜀的防卫,因为它连接西南最近,是与蒙古推行之“斡腹之谋”策略直接相关的地带。上引牟子才奏言中,除了主张增屯兵力一项外,抚慰田、杨二家之议,亦实为深中肯綮之论。田、杨二家作为民夷领袖,长居思、播二州,此地又为“巴蜀之南鄙,近接珍、涪、南平、施黔,远通湖北之沅、靖及广右之雍、宜等处。乃国家藩屏”[9]5。在田、杨两家的经理之下,一度造就“蜀无雍塞之患,而六诏绝烽烟之警”的良好局面[9]2。况且,田、杨两家世结姻亲⑤,势力庞大,对于川蜀地区防御建设颇具影响,一旦“云南有北兵”,则“思、播当严为备”[3]210。史实证明,抚慰田、杨二家,充分发挥他们作用的举措,确实起到了积极效果。田、杨二家保蜀之功不可磨灭,他们同先后帅蜀之制臣合作无间,无论是赵彦吶、彭大雅、余玠、孟珙、李曾伯、蒲择之、吕文德、刘雄飞,还是夏贵,均曾得到杨氏的有力支持[10]352。其中,余玠帅蜀时期取得的成绩最著,得到田、杨两家的支持力度也最大。
余玠入蜀之后,依据险峻山势筑城,屯兵积粮,构筑其城池防御体系。淳祐四年(1244)五月,“利阆城大获山,蓬州城营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旧治,泸州城神臂山,诸城工役,次第就绪”[2]830。他接受田、杨二家及冉氏兄弟的建议献策⑥,将这种筑城固守的防御战术推广至所辖其他防御区域内,“凡地险势胜,尽起而筑之”[11]361,“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2]12470。淳祐六年(1246),杨氏又向余玠条陈保蜀三策:
连年虏寇如蹈无人之境,由不能御敌于门户故也。莫若进司利、阆之间,节次经理三关,为久驻计,此为上策。今纵未能□,莫若于诸路险要去处,众□筑城以为根柢,此为中策。至于保一江以自守,敌去敌来,纵其所之,此为下策。若夫意外之忧,近年西蕃部落为贼所诱,势必绕雪外以(图云南),以并吞蛮部,阚我雍广,窥我沅靖,则后户斡腹为患。[9]6-7
建言虽寥寥数语,实则抗敌之奇策。余玠取其中策守蜀,使“蜀相前后连筑诸城,若兵若民,始有驻足之地”。
综上所述,有关钓鱼城战役前的川蜀防御政策的调整,既有朝中君臣反复商讨抉择之层面,诸如制置使司设于重庆的确定等,也有制臣与地方酋领密切配合的层面。正是在这种多层面、灵活互动务实策略的制定之下,川蜀的军事布防体系才发挥其最大之功效。川蜀地区这种城池防御体系的构筑,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蒙军的继续深入,为宋廷的三边整体防御,尤其是为缓解长江中下游的防御压力带来了积极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战绩,即开庆元年一月(蒙古宪宗九年,公元1259年)合州钓鱼城击退蒙哥中路大军的战役。
二“筑城固守”与“荆蜀相资”策略的制定
川蜀地区长久以来都是中国财赋重地,向称“天府之国”,在宋代亦自有其特殊地位,经北宋以来百余年的着力经营,其人口财赋已渐称繁夥⑦。史载:“蜀中财赋,入户部五司者五百余万缗,入四总领所者二千五百余万缗,金银绫锦丝绵之类不与焉。”[3]141然而,“蜀自丁亥(1227)失关外,丙申(1236)残破之余,所存仅数州。既失蜀,国用愈窘”[3]141。淳祐九年(1249),帝问边事,郑清之谓:“天下之财困于养兵,兵费困于生券,思所以变通之,遇调戍边防,命枢属量远近以便其道途,时缓急以次其遣发。”[2]12421在这一时期,宋朝已经出现兵财匮乏的窘境。至南宋末,这一情况则更进一步恶化。咸淳四年(1268),当时皇帝以边患召沿江安抚使朱禩孙赴阙奏事,君臣对答之间无不显示出对川蜀地区的忧虑:
上曰:“卿此来,专欲以蜀事付卿。”禩孙奏:“臣职在驰驱,敢不东西惟命。”上曰:“当今财用甚为可忧。”禩孙奏曰:“祖宗时以全天下事力备西北二边,渡江以后半天下事力备三边,今日又以东南一隅之地备四边事,力可知。”上首肯。复问曰:“蜀中境土如何?”禩孙奏曰:“六十余州今止有二十余州,所谓二十余州者又皆荒残,或一州而存一县,或一县而存一乡。古人虽一成一旅尚能祀夏,未尝有不可为之事。然曰兵曰财一无所出,内则仰望朝廷科降,外则仰荆阃应援,内外脉络相通,臣方展布。”上曰:“然朕甚以蜀为忧。欲复版图,得以无负先帝付托,须卿一行。”禩孙曰:“陛下率宁人疆土忧顾如此,臣敢不鞠躬尽瘁,尽力以为报塞。至于成败利钝,虽诸葛亮尚书不能逆睹,臣亦岂能。自必惟知尽忠而已。”上曰:“云顶、清居如何?”禩孙奏曰:“顶已陷,并入成都,今惟清居最紧要。须是清居寇去,然后渠广无忧,夔路方可捍蔽。”上首肯曰:“卿为朕一行,旦晚便出命,凡有申请,卿可禀平章奏来,朕当从行。”[12]145
朱禩孙所言虽是南宋末年川蜀边防所遇到的棘手情状。其实,如上所言,在此之前,川蜀地区就已出现了“兵财一无所出,内则仰望朝廷科降,外则仰荆阃应援”的困窘局面。上引牟子才封事言辞中,就已发出蜀中兵力严重不足,难以抵挡蒙古兵锋,不增屯兵力则蜀中必亡的警示。针对这一危局,宋廷在此后应对中及时作出战略调整,最为明显的是专门协调兵力战备的机构“夔路策应司”⑧应运而生。除此之外,积极协调京湖,在兵力和财赋上予以支持。基于这些措施的综合落实,川蜀防务才得以勉力维持。
淳祐元年(1241),宋廷即命孟珙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路制置大使,以夔路隶制司,利、潼、成都三路隶四川制司”[2]823。次年(1242)六月,“诏以余玠为四川宣谕使,事干机速,许同制臣共议措置,先行后奏,仍给金子符、黄榜各十,以备招抚”;丁卯,诏欲玠任责全蜀,应军行调度,权许便宜施行[2]829。十二月丙寅,又以“权工部侍郎、四川宣谕使余玠权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7]2564。此时,孟珙仍“依前宁武军节度使、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夔路策应大使”,直到淳祐三年春乃“解夔路制置大使事”[13]5686。对于这一情况,李曾伯宝祐二年(1254)说得最为清楚:
以夔援则策司除授已久,以宣司兵力则发遣回戍已多。荆蜀之相资已非一日。嘉熙间尝命制阃兼蜀,宣以运掉非便,不数月而改兼夔路制置大使,又不便,改兼夔路策应。自是六七年间,声势上联下接,将士秋戍春还,荆蜀便之。癸丑(1253)之夏,公朝再建策应,臣叨恩兼领,敢不备殚救邻之力。去夏以来(1257),止缘紫金失、苦竹陷,庙堂仓卒,以蜀亡为忧,自策应改而节制,节制改而宣司,名称虽殊,气力则一。其实蜀已有制阃,奚必再建。旬宣夔当置策司,自可专任应接,盖宣、制并建,供亿徒繁,昔为一项费者,今为两项费,以承平之蜀且难,况破碎之蜀乎。臣与制臣虽是同心而共济,岂无掣肘于其间?设或误事,祗相委责。至于荆兵来赴蜀,戍出于策司所调,则帅在峡外,士卒知畏其主不敢有怠心,今之宣司虽是旧尝抚循士卒已视如客,岂能无去志,……兹幸公朝大柄,一新科琐,边吏莫此为急。罢宣司以専制任举,夔事以属策司,以一军心,以省邦费,此实上流先务,非臣私计也。[14]609
由于川蜀大部失陷,原本作为财赋重地的川蜀兵、财两项随着战事的深入,皆已渐显支绌,亟需寻求外力支援。宋廷对于川蜀一带防卫的系列调整,目的无疑在于将川蜀和京湖统合为一,试图利用京湖的兵力和财政支援川蜀防御的建设。史载:“余玠宣谕四川,道过珙,珙以重庆积粟少,饷屯田米十万石,遣晋德帅师六千援蜀。”[2]12379余玠守蜀最为得力,防御也渐成气候,守有余力甚至兴兵出击,“率诸将巡边,直捣兴元”,争取战果[2]12471。同时,余玠守蜀也得到了宰相郑清之的支持。郑清之再相之后,曾与余玠有私书往来,企图借其军功而固己之相位⑨。史载:“郑青山再相,因怂恿其(余玠)进兵,且以私书与玠,云:老夫只候此著为退身计。”[15]卷三《余樵隐》此时,川蜀对于京湖的支援需求逐渐减弱,颇成独立支持之势。史称:“蜀既富贵,乃罢京湖之饷;开边无警,又撤东南之戍。自宝庆以来,蜀阃未有能及之者。”[2]12473一方面,川蜀自身实力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即便在需要京湖支援的时候,京湖有能力也愿意倾力相助。
“荆蜀相资”,目的在于通融事力,但客观上却形成了分力局面。“荆蜀相资”此时更多而言是“荆资蜀”而已。既如此,则京湖自身兵力、财赋随之减去大半,极不利于京湖的防卫,孟珙遂有“彼若以兵缀我,上下流急,将若之何?珙往则彼捣吾虚,不往则谁实捍患”的浩叹[2]12379。事实证明,孟珙所言并非杞人忧天。李曾伯在《蜀边利害奏》中说:
孟珙尝谓非得三万兵不可入(蜀),去秋,臣离荆之始,兵犹半之,今日前除遣回外,荆旅仅存五千余人内,程大元二千五百余人尚戍阆州,七百余人随晋德守叙,其在重庆者,今不及二千,所谓宣司帐兵,川南各二百人耳。伎俩止此,有何威力。乃若宣司科降,则李埴、孟珙自有近例。今臣蒙科降十八界交二百万贯,银三万两,已拨付四川制总库交收,除去冬未到渝以前,资荆力支遣,今半年之间,节决共支,过金银钱引纽计第一料二十八千余万,计约元准科降几已支过前项第一料之数,是截日科降已无分文矣。资用如此,何能施为?……至于兵殚财乏,粮罄民空,而束手无措,将蜀不可为矣。[14]607
“荆蜀之相资”既非一日,“策应”之建也确实达到“救邻之力”,积极的效果业已显现,然而弊端亦随之而来。首先,就是事权的分割,将夔路事权分割给京湖制司,造成有关职能部门很难戮力同心于一事。对此,孟珙当时即表反对,称“蜀事病于事权之分”,主张“罢副司,权既归一,不当更分夔路”[13]5685-5686。其次,就是徒增财赋之负担。如李曾伯言:“其实蜀已有制阃,奚必再建。旬宣夔当置策司,自可专任应接,盖宣、制并建,供亿徒繁,昔为一项费者,今为两项费,以承平之蜀且难,况破碎之蜀乎。”[14]609再次,就是事权分割带来的人事渐趋复杂化,造成防御效能的削弱。“虽是同心而共济,岂无掣肘于其间?设或误事,祗相委责。至于荆兵来赴蜀,戍出于策司所调,则帅在峡外,士卒知畏其主,不敢有怠心,今之宣司虽是旧尝抚循,士卒已视如客,岂能无去志”[14]609。
事权分割又进一步造成人事的频繁变动,势必影响川蜀与京湖间的合力抗击。此后的京湖阃帅并不是都如孟珙一样愿意增援川蜀⑩。例如理宗曾下御笔命李曾伯调兵西援,李则在《回御笔手奏》中声称:
以上流之事尤深,或者之忧朝廷复建策司,俾任应援。此虽前比,非所敢辞。然边面弗同往时,而兵额不过旧籍,是必荆常无事,则力可相应。惟虑蜀或有警,而此亦弗宁,则将自为户牖之防,何暇复救乡邻之急。往闻督府增戍夔门,多亦调之江淮,非专藉于荆楚。[14]537
根据李曾伯的奏言,三边防卫,川蜀的防卫仰赖江淮和京湖支援为多,而此时西蜀已“渐成沉痼”,以京湖现有的防务力量,自救尚且不暇,更无暇西顾,防线重点也已渐次东移。这恐怕与蒙古重新调整进攻策略不无关系。郝经在《东师议》中对于钓鱼城战役前后之蒙古攻宋计划有详细论述:
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造舟为梁,水陆济师。以轻兵掇襄阳,绝其粮路,重兵皆趋汉阳,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则重兵临襄阳,轻兵捷出,穿彻均、房,远叩归、峡,以应西师。如交、广、施、黔选锋透出,门不守,大势顺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横溃潭、湘,以成犄角。一军出寿春,乘其锐气,并成取荆山,驾淮为梁,以通南北。轻兵抄寿春,而重兵支布于钟离、合肥之间,掇拾湖泺,夺取关隘,据濡须,塞皖口,南入于舒、和,西及于蕲、黄,徜徉恣肆,以觇江口。乌江、采石广布戍逻,侦江渡之险易,测备御之疏密,徐为之谋,而后进师。所谓溃两淮之腹心,抉长江之襟要也。一军出维扬,连楚蟠亘,蹈跨长淮,邻我强对。通、泰、海门,扬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备御坚厚,若遽攻击,则必老师费财。当以重兵临维扬,合为长围,示以必取;而以轻兵出通、泰,直塞海门,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骑上下,吞江吸海,并着威信,迟以月时,以观其变。是所谓图缓持久之势也。三道并出,东西连衡。[1]355
据此记载可知,此时蒙古的舟师水战能力已经得到大幅度提高,可成“水陆济师,三道并出,东西连衡”之势。蒙古分兵攻宋和“斡腹之谋”策略的制定,对宋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使得宋“以东南一隅之地备四边事”,财政上受到极大冲击,更对宋廷在军事防卫策略的设定采行上带来挑战。
宋廷给予帅蜀的宣阃制臣以“便宜行事”的权利。余玠为四川宣谕使时,“许同制臣共议措置,先行后奏”[2]824,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川蜀局势的确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然而,宋代“崇文抑武”的国策,加上朝廷政争,又给川蜀的防务带来消极的影响,使宋廷对于宣阃制臣很难完全信任。综合考虑到蒙古分兵攻宋、朝廷政争和旧有国策惯性力等因素,宋廷对于川蜀的防务策略也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时刻调整。大部分时间内,宋廷都将川蜀与京湖统合为一,但部分时间尤其是至宋亡前夕,又主张两相独立经营,各自措置防务。

徐清叟参知政事时,余玠专制于蜀,每交结权要及中外用事者,奏牍词气悖慢,示敢专制之状。上意不平之。徐清叟奏云:“余玠不知事君之礼,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上不答。清叟留班奏云:“陛下岂以玠握大权,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上乃从其言。[3]201
可见,朝廷对于余玠早已心怀芥蒂,伺机削夺其权。等到余玠一死,徐清叟再次奏云:“朝廷命令不甚行于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薨此玠,乃祖宗在天之灵,社稷无疆之福,陛下大有为之机也。”[3]201史料中记载的余玠:“久假便宜之权,不顾嫌疑,昧于勇退,遂来谗贼之口,而又置机补官,虽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于群小,虚实相半,故人多疑惧。”[2]12473后殿中侍御史吴燧又言:“故蜀帅余玠聚敛罔利,家有埒国之富。玠死,其子如孙一空币庾之积而东,宜薄录其财,以为蜀用。”[7]2638朝廷削夺其权,上述记载恐怕都是浅层次的原因,深层次的因素或许得从强本弱末国策的影响和晚宋的政争中寻求。开禧年间,吴曦降金事件也深深影响着此后南宋最高统治者对川蜀防卫决策的制定,成为宋廷挥之不去的阴影。
以上的论述,只是就关涉川蜀防卫的政策、人物、事件作了简单描述,目的在于提请研究者注意:川蜀防卫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不仅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相关,更有既定国策、人事斗争贯穿其间,这些对于川蜀防卫政策的调整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余论:南宋川蜀防卫政策调整之动因与后果
南宋晚期朝廷对于川蜀防卫政策的调整,其因素是多方面的。最实际的考虑当然是要合理分布调配各种资源,以集中最大力量抗击蒙古的进击。但是,面对这一棘手的现实情况,宋廷仍然未能完全排除干扰因素全力抗敌,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强本弱末这一历史力的牵扯,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川蜀防务起到消极作用;加上朝廷内部政争等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内耗,也进一步削弱了防卫力量。
本文选取钓鱼城战役前的川蜀防卫为坐标,通过对上述几个方面的论述,以运作期间的人事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为角度,探究钓鱼城之战前后川蜀防卫策略的变化及影响,并且将钓鱼城战役纳入整个川蜀防务大体系中进行考察,而不是进行孤立的探讨。众所周知,钓鱼城之战的胜利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城池防御体系的成功建设。但是,城池防御的弱点也非常明显,且易为研究者所忽略。川蜀地区的城池防御体系,受限于地理形势,是由多个据点相互应援构筑而成,其分布为点状,实际上各自为战的特点较为突出,对各自山形水势的依赖较强,其后勤补给一方面考验山城自己的独立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则对于水运舟楫的传送功能要求较高。随着蒙古军筑城技术和舟师水战能力的提升,一旦蒙军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切断城池与外部的联系,尤其是切断来自舟楫方面的支援,那么城池的坚守就非常艰难。合州钓鱼城抗击蒙古数十年,乃至与宋政权共存亡,所依赖的多为其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特殊险峻的地理形势以及钓鱼城自身强大的生产能力。逮至后来其他山城防御体系被各个击破之后,钓鱼城也很难独存,终于在外援丧失、内部资源消耗殆尽之后投降。从这个角度来看,将钓鱼城战事放入整个南宋晚期的军事防御布局中考察,将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钓鱼城保卫战的历史,也为我们研究南宋抗蒙坚持近半个世纪之由带来可资参考之视角。
注释:
①主要成果有:胡昭曦主编《宋蒙(元)关系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陈世松《宋元战争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李天鸣《宋元战史》,食货出版社1988年;《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以上专书中对于川蜀防卫多有论述,但侧重点不一,尤其是对于南宋中晚期的防卫调整关注不足。除上列诸书外,单篇论文的研究尚有不少。限于篇幅,此不赘列。
②本文曾以《筑城固守与荆蜀相资:晚宋川蜀防御政策的调整——以钓鱼城战役前后为中心》为题,在重庆市文化委员会、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西南大学主办的“二〇一五年钓鱼城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在论文撰写、研讨与评审中,承蒙上海师范大学戴建国教授、四川大学刘复生教授、粟品孝教授、西华师范大学蔡东洲教授、西北师范大学何玉红教授以及匿名评审专家等多位先生提供宝贵意见,在此,笔者一并致以谢忱!
③有关端平入洛,相关研究可参见:黄宽重《辩“端平入洛败盟”》,原刊《史绎》1973年第10期,后收入《南宋史研究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9-30页;陈高华《早期宋蒙关系和端平入洛之役》,载《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24页;王頲《端平入洛——收复三京与蒙、宋的开战》,载《西域南海史地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④有关晚宋边防的讨论,可参见:林瑞翰《南宋之边防》,《幼师学志》1970年第9卷第2期;黄宽重《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收入《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78年。对于守蜀的争议,书中着墨不多,尚有深入细化讨论之余地。
⑤关于田、杨两家姻亲关系,此处略作考证。淳祐七年(1247),《杨灿墓志铭》篆盖者即题“……军沿边都巡检使田庆裕”,查《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第4705页)职官六一之三十“以官回授”条载有:“淳熙十三年(1186)十二月二十一日,思州言:杨氏乞故夫田祖行在任酬赏回授与孙男田庆裕等补官。……乃诏田庆裕、田庆琪各特与补进义校尉。”又袁桷《资德大夫绍庆珍州南平沿边宣慰使播州安抚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上护军追赠推忠效顺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封播国公谥忠宣杨公神道碑铭》载:杨汉英“娶田氏,荣禄大夫义敏公谨贤之女。曾祖价……妣田氏,封齐安和政安康夫人、赠永宁郡夫人。祖文,宋任和州防御使、播州沿边安抚使。……妣田氏,封播国夫人,谥章靖。父即惠敏公,宋任左金吾卫上将军、安远军承宣使、播州沿边安抚使。……妣田氏,封播国夫人,谥贞顺。”(参见: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卷二十六,中华书局2012年点校本,第1276页)。由此而知,杨氏几代均娶田氏为妻,为世代联姻之家族,且在杨氏家族的部队中也有不少田氏家族子弟效力其间。详细情况可参见:贵州省博物馆编《贵州省墓志选集·南宋播州安抚使杨文神道碑》,贵州省博物馆1986年编印;宋濂著、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卷十八《杨氏家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2页。
⑥冉氏对于川蜀防卫贡献具见于史乘记载,尤其以建议筑城移治合州钓鱼山的冉琎、冉璞为最。材料显示,冉氏与田、杨二家也配合密切,共同为川蜀的防卫建设贡献力量。例如,在蒲择之任制臣期间,冉从周作为幕参,就曾深入诸蛮宣布上意,授以杀贼方略。见:贵州省博物馆编《贵州省墓志选集·南宋播州安抚使杨文神道碑》,贵州省博物馆1986年编印。
⑦学界有关宋朝对于川蜀云贵地区的治理研究,已积累了不少成果。较典型的,例如:Richard Von Glahn(万志英), The Country of Streams and Grottoes:Expansion,Settlement, and the Civilizing of the Sichuan Frontier in Song Time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88;葛绍欧《北宋对四川的经营》,《台湾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7期;林天蔚《南宋时四川特殊化之分析》,香港大学《东方文化》1980年第18卷第1、2期;John E. Herman,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Cambridg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刘复生《宋代羁縻州“虚像”及其制度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裴一璞、张文《拒绝边缘——宋代播州杨氏的华夏认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⑧有关夔路策应司的研究,目寓所及仅有喻学忠的两篇文章(《南宋夔路策应使设置时间考》,《重庆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夔路策应使考》,《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作为南宋末年出现的独特军事协调机构,策应使司不仅在夔路设置,在其他战区同样存在。策应使司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限于篇幅,俟另专文论述。
⑨有关郑清之与晚宋政治关系之研究,可参见:王德毅《郑清之与南宋后期的政争》,《大陆杂志》2000年第101卷第6期,第244-246页。
⑩如上文中所载,孟珙支援余玠在川蜀的防卫建设非常得力,在兵财用度的援助上都堪称积极。这恐怕与孟珙和余玠私交甚好有关。史载:“余玠宣谕四川,过松滋,公(孟珙)一见如故。”参见:《刘克庄集笺校》卷一四三《孟少保神道碑》,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86页。

参考文献:
[1]郝经.陵川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王瑞来.宋季三朝政要笺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
[5]吕午.竹坡类稿[G]//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9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6]吴泳.鹤林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G]//赵铁寒.宋史资料萃编:第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8]黄宽重.政策·对策:宋代政治史探索[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
[9]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墓志选集[G].贵阳:贵州省博物馆,1986.
[10]宋濂.宋濂全集.黄灵庚校点[G]//明清别集丛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11]阳枋.字溪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2]无名氏.咸淳遗事[G]//丛书集成新编:第11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13]刘克庄.刘克庄集笺校[M].辛更儒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14]李曾伯.可斋续稿[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5]刘一清.钱塘遗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6]蒋复璁.宋代一个国策的检讨[C]//宋史新探.台北:正中书局,1975.
[责任编辑:凌兴珍]
Fortification and Alliance of Shu and Jing: Adjustments and Influences of Sichuan Defense Policies in Late Song Dynasty
PENG F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study of the Fishing town batt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chuan’s whole layout of defensive strategies. The related post battle adjustments are then discuss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ortification and alliance of Shu and Jing, including conflicts on Shu’s defense and the implement of detailed defense policies, so as to review the impacts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es of “strong trunk versus weak branches” on both Fishing town battle and Shu defense. Finally, by studying Fishing town battle, and internal operating between human resources and system, this paper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both the beginning success and later failure of Fishing town’s defense tie to the series of strategies’ adjustment from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ichuan defense policies; fortification; alliance of Shu and Jing; Fishing town battle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2-0159-08
作者简介:彭锋(1986—),男,江西安福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古籍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宋史与历史文献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优秀成果培育项目(A-6001-15-001421)阶段性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5-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