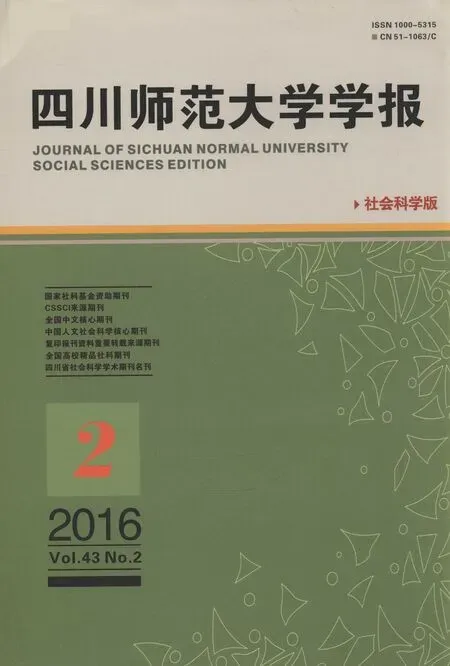论清代驻防成都满蒙八旗
2016-04-14秦和平
秦 和 平
(西南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成都 610041)
论清代驻防成都满蒙八旗
秦和平
(西南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成都 610041)
摘要:成都曾是清代满蒙八旗兵的防驻地。康熙末年,清政府移荆州八旗兵驻防成都,意在加强川西民族地区的控制,屏障西藏等地;乾隆后期,清政府特别设立成都将军,统领旗兵及汉土官兵,管理川西民族事务兼顾西藏地区,治理西南边疆意图更明显。当满蒙八旗兵进驻成都城区后,建筑“满城”,成都城市发展成一城三“城”格局。成都“满城”的便捷通道和独特院落及旗人生活习俗等,给成都城市文化赋予特别韵味,延续至今,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景点。从清中叶起,成都“旗学”兴起并持续发展,通过科举,涌现出不少人物,使满蒙旗人开始从“武”到“文”的转变;教育促进交流,消除“距离”,化解“疑窦”,使成都满、蒙、汉各族交往交融,“亲睦居然一家”,为清末保路运动暨辛亥革命时实现成都满汉和解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成都;驻防八旗;满城;“旗学”;化解“疑窦”
清代八旗兵驻防区中,成都是重要的地点,镇摄川西,影响滇藏;成都将军逾制兼理民政,管辖川西民族地区,调动满、蒙、汉等兵种,地位特殊。为什么清政府会如此决策呢?当八旗兵进驻成都“满城”,改变了成都城市建筑格局,影响至今,乃至“宽窄巷子”(胡同)成为享誉中外的著名旅游点,缘由何在?更重要的是,清代中叶,“旗学”得到快速发展,成都满蒙旗人崇尚教育,中举者众多,谋生门径拓宽,与川省士人、学子、民众沟通交往增加,满汉间的交流和融合增进,渐至“彼此毫无冲突,亲睦居然一家”[1]236之境,为辛亥革命时避免成都满城被屠悲剧之发生以及和平解决满蒙族旗人问题奠定了基础。为什么清末成都满、蒙、汉族民众能实现融合?要认识这些问题,必须研究清代成都满蒙八旗的由来、演变及影响。
关于清代成都满蒙八旗的由来、分布、构成、等级及俸银等,同治《成都县志》有较详细记载,且图文并茂。这与部分满蒙士子进入修志局,担任修撰、主修、参正、提调、协修或同修,或从事校正或校对,是分不开的。“满族驻防八旗在成都境,旧志只有节孝贞烈妇女数十口,其余事迹一切未载。此次奉督宪兼署将军吴发来八旗志稿,各类全备,编附县志,无敢或遗”[2]卷首,2,因而同治《成都县志》记载了关于成都驻防八旗的众多材料,是内地八旗驻防史的珍稀文献。
对清代以来成都满族蒙族史的调查研究,始于1959年10月辽宁省民委派遣李登弟、郑镇武来成都调查搜集资料。该次调查,历时月余,召开大小会议20余次,采访人数300人,调研的重点主要是成都满蒙族在解放前后的地位升降及生活变化。该调查资料,后来经傅乐涣、杨学琛整理润色,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出版[1]。20世纪60年代初,四川省文史馆动员相关人士撰写文稿,留下“三亲”资料,于是有刘显之撰写的《辛亥革命和平解决“满城”的回忆》[3]、徐孝恢遗稿《关于成都“满城”的回忆点滴》[4]以及四川省志近百年大事纪述编辑组编辑的《清代四川绿营、旗营和新军》[5]等文史资料发表,对清代成都满族蒙族及八旗的历史有所介绍。“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成都满蒙族史的研究被打断。“文革”后,1981年,陈一石发表《清代成都满蒙族驻防成都八旗概述》[6]一文,对清代满蒙族驻防成都八旗有所概述,但该文叙述简约,令满、蒙族民众深感遗憾。1983年,刘显之依据同治《成都县志》及口述资料等,整理并印刷旧稿《成都满蒙族史略》[7],对清代成都满蒙族历史尤其是驻防八旗的建制等做出详细阐述,丰富了陈文的内容;同年,陈一石发表《清代成都驻防八旗再探》[8]一文,对清代成都驻防八旗进行拓展研究。1993年,成都满蒙族人民学习会组织刘国源、何长明撰写《成都满蒙族志》[9],对外传播。此后,刘国源等人《我所知道的成都满族、蒙古族》[10]、张利《成都满族社会历史文化变迁》[11]、陈玮《清代成都满族旗人生活》[12]等文,对清代成都满族蒙族的历史、文化及生活有所涉及。2007年,万保君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辛亥前后成都满族研究》[13]及其《1911辛亥风暴下的成都满族》[14]、《辛亥革命成都满族问题的和平解决》[15]等文,解释了辛亥革命时成都为什么没有发生仇满排满的部分原因。此外,1993年出版的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16]一书,除引用了光绪五年(1879)成都地图说明成都“满城”八旗驻地外,对成都八旗驻防史基本上没作讨论。
本文拟采撷同治《成都县志》、《清实录》等相关资料及时人诗文,阐述清代成都驻防满蒙八旗的由来、发展演变、特点及影响,说明成都旗兵驻防特点及与川西民族地区的关系、“满城”布局结构,解释为何清代成都满、蒙族与汉族能实现民族融合、达到“亲睦居然一家”以及辛亥革命时成都未发生满汉冲突和屠满城悲剧之原因所在,以丰富对成都满蒙族历史的认识。
一成都满蒙八旗由来、组织及管理
(一)成都满蒙族旗人的由来及发展
满族蒙族入川始于清初①。顺治三年(1646),肃亲王豪格曾率领八旗兵入川攻打农民起义军。不过,战事结束,这些八旗兵就调离四川,奔赴其他战场。康熙二十一年(1682),四川提督何傅奏请朝廷调派满兵即八旗兵入川弹压战乱,稳定局势。当时,调派满兵入川,只是增强力量、平定局势。待形势稳定后,这些旗兵亦调离出川,未能留驻。
满蒙族旗兵能留驻成都,成为土著居民,与康熙末年西藏等地的形势密切相关。康熙五十七年(1718),西藏地区发生内乱,清政府调兵遣将,数路进军,平息叛乱。其间,都统法喇(喀)奉令率荆州3000名八旗兵借道四川进入西藏,参与平叛。不久,西藏局势得到安定,四川巡抚年羹尧奏请朝廷,请求在察木多(今昌都)、打箭炉(今康定)留驻满兵以加强控制,并建议将部分荆州八旗兵留驻成都,兼作后援:“川省地居边远,内有土司番人聚处,外与青海、西藏接壤,最为紧要。虽经设有提镇,而选取兵丁,别省人多,本省人少,以致心意不同,难以训练。见今驻扎成都之荆州满洲兵丁,与民甚是相安,请将此满洲兵丁酌量留于成都。省城西门外,空地造房,可驻兵一千。若添设副都统一员管辖,再将章京等官,照兵数量选留驻,则边疆既可宣威,内地亦资防守。”[17]卷二八○,8B-9A显然,宣威边疆、防守内地,实为年羹尧建议清政府用八旗兵驻防察木多、打箭炉及成都以维持川西民族地区稳定之意图所在。清政府接受了年羹尧的建议,从入川3000旗兵中选留1600人,保持八旗建制,留驻成都;同时,饬令1000名“披甲”作为余兵(或称闲散,候补旗兵)补录入荆州旗兵中,回防驻扎[17]卷二八○,9A。《成都竹枝辞》有云:“湖北‘荆州’拨火烟,成都旗众胜于前。康熙六十升平日,自楚移来在是年。”[18]76这样,成都就成为清代内地驻扎成建制八旗兵的地方,也是西南地区唯一驻防八旗兵的地方。
除康熙末年年羹尧奏请留200名旗兵于康定,后来雍正皇帝亦考虑拟留千名兵丁在察木多以增强力量、支援拉萨②外,乾隆年间清政府还调众多八旗兵入川平定大小金川乱事。有清一代,上至将军、下到知县的满族蒙族官员到川任职者为数不少,但受体制的限制,他们大多只是匆匆过客,没有定居,即没有增加川省满蒙族人口。故清代四川满族蒙族以康熙末年成都驻防八旗兵及家属为基础,逐年自然增长。康熙六十年(1721),1600名荆州八旗兵留驻成都,其后家眷陆续从鄂来川定居,在成都定居的满蒙人口逐年增加。据统计,雍正初年,成都旗兵及家属约2000余户、5000人;嘉庆五年(1800),成都八旗兵有2153户、10998人;同治十年(1871),成都有旗兵4500余户、13700余人[2]卷二,5。光绪九年(1883),成都将军歧元遵旨拣选100名余兵及家属约300余名,调至杭州填补该地旗兵[7]11。不过,因调离者不多,对成都满蒙旗兵人数的影响有限。光绪三十年(1904),成都将军绰哈布查核成都满蒙族旗人的册籍,共5100余户,男12000余人、女9000余人,合计21000余人[3]11。需要说明的是,在成都八旗兵中,有1/3是蒙古旗兵。也就是说,在上述各种数据中,约2/3是满族,约1/3是蒙族。
虽然清代成都满蒙族人口历年有所增长,但在近两百年间只增加了3倍,人口的自然增长是相当缓慢的。究其原因,主要有几点。一是战争损失。清代前中期,驻防旗兵随时出征,死伤量较大,影响人口增长。如乾嘉之际,为镇压川鄂陕白莲教起义,约1600名成都旗兵投入战斗,战死者多达700余人[7]16。二是受礼俗约束,旗人中寡妇再嫁者较少。当那些青壮年旗兵征战丧生后,受礼俗约束,这些家庭中的寡妇再嫁较少,多不能再繁衍后代,影响人口增长。比较前引嘉庆五年(1800)到同治十年(1871)的两次统计数,成都满、蒙族人口在七十余年间仅增加24%。相应的是,在成都满、蒙族中,守贞节妇多。仅据志书记载,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同治十年(1871),成都满、蒙族节妇达129人③[2]卷八,18A-25B。三是旗兵名额有限,影响生育。清代八旗兵员有定额、有饷银,但名额固定,不因人口(指男丁)增长而加增。在和平年代,旗人生育越多,意味无业者会增多,生活压力、谋生困难等影响到部分满蒙族妇女的生育观,大多不愿多生多育。
(二)八旗组织及管理
康熙末年,移防成都的八旗兵成建制,黄、白、红、蓝各正、镶旗都具备。因只有1600名旗兵,不得不压缩编制:每旗三甲(甲哇)两百人,成都八旗只有二十四甲,其中一甲、二甲是满洲兵,三甲是蒙古兵。各旗中虽有骑兵、委甲兵、炮手、匠役(铁匠、箭匠、弓匠)、步兵、养育兵、前锋、余兵以及幼丁等兵种,不过各兵种的构成往往随形势的要求或旗人的增多而有所变化,但主要增加养育兵或余兵(闲散),骑兵、委甲兵及炮手则增加很少。在八旗兵中,各兵种的地位及待遇均有差别,其中骑兵最高,余兵最低。
八旗兵有定数,遇有伤亡,出现空额,则根据旗兵的任职年限、“一骑三射”成绩等,适当考虑家庭人丁及经济状况,或由余兵补入,或依等级向上递补,按部就班,成为定制。清末成都旗人增多,但八旗兵额固定、不能扩张,难以解决多余旗人的生计问题。鉴于城镇防卫等的需要,成都将军崇实、裕祥及奎俊在八旗之外新建营旅,组建了“精锐营”、“振威营”及“新威营”,官佐及士兵近千人,换言之,就是吸纳了千余“闲散”旗人。稍后,依据朝廷饬令,将军绰哈布扩编这三营,健全机构,成为成都巡防军一、二、三营;他又借组建警察名义,吸纳闲散旗人为警察,解决其就业问题。随着环境的改变,八旗传统“一骑三射”的选拔模式也逐渐被新法操练所取代,刀枪、棍棒、弓箭等冷兵器也渐为“热火器”所替代,体力、灵巧训练变更为知识教育等等。
八旗是成都满族蒙族的基本单元,管理者有副都统1员、协领5员、佐领19员、防御24员、骁骑校尉24员以及笔贴式2员。这些管理者中,将军、副都统由朝廷委任派遣,协领及以下各员则依其任职年限、劳绩程度等,遇有空缺,依次升迁。鉴于西藏及川西民族地区的重要性,乾隆四十年(1775),清政府在处理金川事件时,决定添设成都将军,由其调防旗兵及时应对突发边事,“至成都满兵,必须移驻打箭炉,该处控制诸番,远抚西藏,实为扼要之地,并须添设将军镇守,声势方为尊重”[19]卷九八九,24B,控制“诸番”及西藏地方势力的意图十分明显。最初,清政府要求成都将军率部分八旗兵驻扎雅州(即现今雅安),“统兵镇守,节制绿营,并于两金川之地安设营讯,移驻提镇以资控驭”,就近处理藏、彝区突发事件,兼援助西藏;副都统则留驻成都,分兵防守,暨作后援,有效支持,待两三年后互换防地,平衡负担;不过,后来又考虑雅州地势逼仄,建筑“满城”困难,旗兵家眷难以安置,且将军与总督同住省城,便于商议,及时处理,于是决定将军仍留成都,与副都统同驻“满城”,各建衙门[19]卷一○○四,12B-13A。这样,成都将军既是成都八旗兵也是成都满族、蒙古族的最高管理者。与其他地方的将军不同,成都将军全衔“镇守四川成都等处地方将军、统辖松建文武、提调汉土官兵、管八旗事”。因此,四川布政使、按察使及提督等文武官员都是成都将军的属员,接受其领导;成绵、建昌两道,松潘、建昌两镇及阜和协还直接听命成都将军,凡涉及两镇道的重要事务,四川总督要与成都将军会衔奏请处理,不得遗缺,否则,不合体制,难以批准④[19]卷一○○四,25-26;成都将军还能“提调汉土官兵”,管理土司土目,调动土兵,监控西藏等地,凸显了清政府在成都驻防八旗兵的意图: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控制川西藏彝地区,屏障西藏。由于成都将军位高权重,副都统受此影响而地位降低,官印缴毁,变成“无印”都统;若要发公文,副都统只得借用将军印信加盖。
二成都满蒙八旗居住及生活
(一)聚居地特点
康熙末年,荆州旗兵移防成都,因职责所在,加以清政府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年羹尧选择成都城市西边原少城旧址圈划土地,筑墙封闭,集中驻扎,形成“满城”。满城“在府城西,康熙五十七年(1718)建筑,周四里五分,凡五门,官街八条,胡同三十三条”[20]42,集中安置满蒙旗兵及家眷。《锦城竹枝词》有云:“鼓楼西望满城宽,八道官街萃一团。老老将军能坐镇,驻防同领圣恩欢。”⑤[21]4B当时汉族及其他民族群众多生活在成都东面,俗称“汉城”;在满城与汉城之间隔“明蜀王城”,居民以回民为主。这样的民族聚居分布,将成都一城区隔为“满城”、“王城”和“汉城”三城。有竹枝词云:“‘鼓楼’西望‘满城’宽,‘鼓楼’南望‘王城’蟠。‘鼓楼’东望人烟密,‘鼓楼’北望号营盘。”[20]42又云:“本是‘芙蓉城’一座,‘蓉城’以内请分明。‘满城’又共‘皇城’在,三座城成一座城。”[18]75三城居民不同,习俗有异,特点鲜明。
成都“满城”四周为城墙环抱,形成封闭单元,有五个城门开关进出,其中东面两个门,即迎祥门、受福门,西面一个门,即清远门,北面有延康门,南面有安阜门。概括而言,“迎祥御街小东门,受福羊市小东门,延康小北门,安阜小南门,清远则大城西门”[2]卷一,2A。“满城”西部有金河,河水从水西门进入,从灵寿桥流出,流通满城,保障水源,再进入“王城”及“汉城”。因金河关系,“满城”南面墙下灵寿桥界于满、汉城之间,桥上砌墙阻隔,俗称“半边桥”。有竹枝词云:“右‘半边桥’作妾观,左‘半边桥’当郎看。筑城桥上水流下,同一桥身见面难。”⑥[20]57以城墙阻隔满汉民众交往,可见其封闭状况。
成都“满城”聚集八旗兵丁,是军事重镇。《成都竹枝辞》称:“不将散处失深谋,蒙古兵丁杂‘满洲’。四里五分城筑就,胡同巷里息貔貅。”[18]76聚散方便、调动自如,成为构建成都“满城”街巷功能的基本原则。具体而言,城南将军衙门为头,城北延康门为尾,长顺街为中轴,贯穿南北,联结首尾;长顺街东西两侧为各街道(官街)或各胡同(小巷);东、西城墙的内侧,从北到南,有顺城街,联结东、西两面的各条官街及胡同;将军衙门前,有金河街、祠堂街贯穿东西。这4条街道贯通满城的东西南北,8条官街及42个胡同形成严密的蜈蚣状的防守网,“将军府,居蜈蚣之头;大街一条直达北门,如蜈蚣之身;各胡同左右排比,如蜈蚣之足”[22]17,以便各旗满蒙将士集散快捷、调动方便、攻防兼备。
当旗兵移住“满城”时,按八旗划分防守(居住)位置,正黄、镶黄两旗居北,正白、镶白旗居东,正红、镶红旗居西,正蓝、镶蓝旗居南。各旗再按正、镶之标识,其住地分左右两翼,安置旗民,相互照应。在“满城”内,每旗有一街,集中旗衙门机构等,俗称官街;每甲旗人居住同一胡同各院落,三甲有三胡同,连同官街,共32胡同。其后,各旗人数增多,事务繁杂,又添加一些胡同。直到清末,八条官街依然保持,胡同则增至40余处。
旗人不交产,满汉不通婚。当朝廷决定八旗兵驻防成都时,年羹尧饬令下属,购置材料,调动人工,依据北方民房形式,并考虑成都的气候及建材特点,修建官房(衙门)和兵房(住房)等,安顿旗兵。兵房,按每兵(户)三间分配,正堂屋,两厢房;各兵房砌筑围墙,留有宅门,门前有下马石;墙内空地,形成独院;院内有高木杆,为祭天而设。旗人重礼节、爱清洁、好修饰,各家院内栽花种草、营建花园,各院落间无形竞争,彼此攀比,氛围特殊。于是,“满城”内树木繁茂,花草甚多,香飘四处。“‘满洲城’静不繁华,种树栽花各有涯。好景一年看不尽,炎天‘武庙’⑦赏荷花。”[23]67官街四通八达,胡同曲径通幽,院坝独立成院,花草繁茂芬芳,形成“满城”的特殊氛围,俗称“小北京”。这也是当今成都“宽巷子”、“窄巷子”旅游片区历史遗存的特色所在。
(二)旗人生活概况
毋庸解释,八旗兵当兵打仗,作战是其职责所在;清政府则发给饷银,分配房屋,养兵操练,戍守作战。康雍之际,成都八旗兵2000余人,按照任职的不同,分有不同等级,获得数量不等的饷银。旗兵中,高者如“前锋”,每名年支兵饷、口粮、马乾,折银95两;低者“余兵”,每名年支兵饷6两;再加将军、副都统的官俸及协领等大小官员的兵饷[2]卷五,1-10。据统计,光绪三年(1878)前,成都八旗兵年开支约18.9万两,接近20万两。这些饷银、马乾等均由藩库支付。“‘满城’城在府西头,特为旗人发帑修。仿佛营规何日起?康熙五十七年秋。”[18]76所谓“特为旗人发帑修”,就是指国家给旗人发饷银,养兵卫国。
清代前中期,国家强盛,银贵钱贱,成都满蒙旗人口不多,八旗中内有位置,亦能给养,其中骑(马)兵的待遇好、收入较高,据说每月收入可养人五口。斯时,兵饷能基本满足旗人家庭生活开支,衣食不愁。有诗曰:“吾侪各自寻生活,回教屠牛养一家。只有旗人无个事,垂纶常到夕阳斜。”[18]72表明旗人生活悠闲自在,令人羡慕。旗兵收入固定且有保证,致使旗人形成特别的悠闲文化。“旗人移往驻防兵,服食言谈另样精,今日出城闲逛逛,手提笼雀臂悬莺”[21]5A,就是其写照。少数旗人“绷面子”、好虚荣,在放饷时手上有钱,大吃大喝,挥霍之后,手中无钱,一些旗人则抵押衣物,甚至拆散房屋,贩卖梁木等,“‘西较场’兵旗下家,一心崇俭黜浮华。马肠零截小猪肉,难等关钱贱卖花”[20]47。一些商贾了解到此种情况后,就以发饷为限,变换商品价格,前贱后昂。“旗人喜务花,关钱后故昂其值。惟未关钱时,要零星买食物乏用,则贱卖之”[20]47,就是商贾利用特殊节点高出低进、伺机盘剥旗人的反映。不过,总的说来,成都多数旗人习俗简朴,恪遵礼仪,“冠婚丧祭,满洲、蒙古各遵祖法,节文虽异,皆不逾礼,宗族姻娅颇相亲睦,交游重义,酬答必丰,其俗俭约,不尚奢靡。其人戆真,不好私斗。巧于树艺,亦习诗书,骑射最精,果勇善战”[2]卷四,5,概括了成都满蒙旗人的习俗所在。需要说明的是,有清一代,成都满族蒙族人口不断增多,饷银、口粮及马乾等保持不变;到清代后期,僧多粥少,大多数满、蒙族人因收入短缺而陷入贫困境地,生活饥寒交迫,但其简朴规矩、遵礼守法的习俗未曾根本改变。
三成都满族蒙族的教育及科举
尽管清政府驻防旗兵在成都是出于控制川西民族地区、屏障西藏之用意,旗兵也以尚武为主,当兵作战,但在旗兵及其后代中不乏勤学之人,甚至弃武习文之人。不过,限于封闭的环境及教育经费的缺乏,康雍年间,“满城”还未建有学堂,只有家庭教育,父母兄姊口口相授、亲戚邻里引导而已。乾隆十六年(1751),副都统萨拉善利用旗兵马价息银及部分土地租金,每年约400余两银,用作师资薪金及学生学杂费,创办八旗官学[2]卷四,3A。乾隆三十五年(1770),副都统铁保鉴于满城已有数百孩童,官学仅一所,受教育者有限,于是便增加若干资金,再建一所学校,招收更多学生入学。乾隆四十八年(1783),将军特成额决定增加“满城”学堂,规定每旗必须设立一处学堂,选择40名子弟入学,总计320名学生;为鼓励外聘教师认真教学,特别给老师虚衔金顶等荣誉地位,“其训课优者,五年考满,遇有应升缺出,一体较拔”,授予实职,反之,到期解雇;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要求学生每月必须考试,优秀者奖励,对贫寒子弟则酌给笔墨费等[2]卷四,4A。其间,还设有八旗义学,各甲设立一所,“每年延师训迪及学生膏火,于各队兵摊助”[2]卷四,6,采取复式教学的模式,除教授满汉文字外,还传授弓箭、刀劈、骑术等技艺,随时考核,优秀者奖励。
从清中叶起,成都八旗教育得到快速发展。这固然与旗人勤奋好学有关,但当政者提高旗人层次、拓宽旗人出路的政策导向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嘉庆五年(1800),兵部曾要求成都将军禁止驻防旗人参加科举:“嗣后,各省驻防旗人不得应就近考试之例,遂荒清语、骑射本业。着该将军、都统等通行饬谕,各官弁等训课子弟,以清语、骑射为首务,其肄业者仍当娴习清语、骑射,务臻纯熟。”[2]卷三,3AB十几年后,当政者却转而鼓励旗人参加乡试。嘉庆十八年(1813),上谕旗人:“向来满洲、蒙古旗人俱准应文武乡试,复经停止。国家甄拔人材,文武并进。嗣后,满洲、蒙古与汉人一体,准于本省应文武乡试等因。”[2]卷三,3B希望驻防旗人不局限于学习满语文及掌握骑射技术,还应参加文武科举。该谕旨的颁布,极大地刺激了成都旗人学习汉语文、参加科举的积极性,加快了成都“旗学”的发展。这有竹枝词为证:“康熙移驻旗人来,嘉庆八年旗学开。《满汉四书》念时艺,蓝衫骑马泮游回。”⑧[20]52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谕称:“国家分设八旗兵丁驻防各省,立意至深且远。嗣因生齿日繁,披甲名粮,例有定额,势不能概令食粮当差。而各弁兵子弟亦有读书向上,通晓文义者,听其应试,以广取进之阶,所以造就人才,体恤旗仆者无微不至……应试之人,弓马如果娴熟,不患无登进之路。其应文试者,必应试以翻译,庶不专习汉文转荒本业。除本科各省文乡试,仍照例准其应考外,嗣后各处驻防俱着改应翻译考试,俾有志上进者咸知熟悉清文,不能悻邀拔擢,自必争相磨励,日益精通。”[2]卷四,7要求各省驻防旗人除学习汉文外,更应该学习掌握满语、骑射,并在传统武举、文举之外,为驻防旗人新开翻译进士科⑨,再辟晋职及分流的途径。
当政者的鼓励,不仅调动了成都八旗管理者兴办旗学的积极性,而且调动成都满族蒙族学子奋发学习和参加科举的积极性,促进了旗学的快速发展。据资料记载,副都统富勒洪额在任八年⑩,“时改试翻译,乃协同将军至官学训课,由是驻防多登科甲科者”[2]卷四,4A。同治十年(1871),总督吴棠兼任成都将军,特捐助银两,鼓励教学,“捐资数千金以作山长修脯、生童膏火。每月考校,给发经史奖励,殷肫教养旗兵,尤多惠爱”,修建房屋,提升办学层次,改八旗官学为少城书院[2]卷四,3A。他的鼓励带动影响部分下属纷纷捐款,募得银两5200余两,交商人作本生息,年息600余两,用于教师薪俸及学生纸墨费[2]卷四,4AB。光绪五年(1879),将军恒温捐献养廉银,扩大少城书院的规模,增添房屋,增加学生名额,增设奖项,鼓励教与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新学的发展,在官府的鼓励下,成都“旗学”调整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式;创办新式高小,培养人才;创办女子小学4所,资助女童学习;将24个牛录官小并为8个劝学所,以集中资源、提高效率;各旗还鼓励那些文化程度较高者离开“满城”,进入“汉城”的高等学堂、东文学堂、武备学堂、通省师范学堂及华阳中学堂学习,甚至出洋留学,以提高层次、促进交流[4]42。

四清代成都驻防满蒙八旗的作用及其对保路运动暨辛亥革命的应对
与其他地方的建制八旗相比较,旗兵驻防成都较晚。清政府之所以从入藏荆州旗兵中选择近两千名留驻四川,除增强川省的驻防力量外,还在于有此机动兵力,可及时应对藏彝地区突发事件,便于控制川西民族地区、屏障西藏等地,可谓用心良苦。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政府设立成都将军,加重军民事权利,管理成绵、建昌道及松潘、建昌两镇民事军务,节制各级属员,管理土司土目,定期巡视大小金川等地。清政府还曾考虑在康定、昌都等地驻扎旗兵,联络成都驻防旗兵,保障行动;饬令成都将军等介入西藏事务,等等。朝廷的意图明显,就是凭借八旗兵的忠诚之心、果敢性格、调动迅速等,及时应对及处理各类事件,加强对藏彝民族地区的统治。这是成都八旗兵及将军不同于其他驻防旗兵的特别之处,反映了清政府对藏区施以特殊管理的政策用意。

西南地区多系山区,崇山峻岭,八旗骑兵快速、密集冲击的战术受到限制,难以发挥应有作用。魏源说:“我朝骑射长于西北,故金川西南之役难于新疆,安南、缅甸之功让于西藏,将毋吉林、索伦之劲旅,其技不宜于南方,故事有难易,功有优劣与?若夫金川之始,温福、阿桂皆奏言:‘满兵一人费至绿营三人,不如止满兵而多用绿营。’川楚之役,勒保亦言:‘征黑龙江一人,可募乡勇数十人,不如舍远征而近募乡勇。’是则用兵变化,各视乎天时地利。”[24]卷十一,470-471的确,地形地貌、气候特产的不同,决定着战术调整及作战方式改变,更因新式武器的传入及运用,刀枪棍棒之类的“冷兵器”作用减弱,八旗兵威力下降,被团练、乡勇等私人武装所替代。影响所及,八旗兵成为“鸡肋”,训练疲软,斗志懈怠。之后,数位成都将军采取了创办“振威营”、“新威营”等城防军以收容闲散、选拔壮丁、新法训练等措施,试图解决八旗人多额少、生活困难等矛盾,重振八旗斗志,再显八旗威力,但收效甚微。

年底,“辛亥革命”爆发,影响成都等地,形势逆转。在压力下,赵尔丰考虑交权。在谈判时,蒲殿俊提出十一条协议,有两条涉及成都驻防旗兵:一、驻防旗饷,照旧发给,事后再为妥筹生计;二、自宣告之后,无论满、蒙、回与汉人一律待遇,不分畛域[25]505。赵尔丰提出并得到蒲殿俊同意的十九条中,涉及成都满人的有三条:一、不排满人;二、安置旗民生计;十四、旗军现练三营,统归陆军编制管理[25]504-505。经过协商,赵尔丰表示同意,移交权力,拟离开成都经营川边地区(今甘孜等地)。11月27日(阴历十月初七日),蒲殿俊宣布四川“独立”,成立军政府,担任都督,声称:“事事条持和平,力求宁人息事。外国人及教堂,我省行政官吏、满洲驻防人民,一律照常待遇……彼此共享太平,同尽国民天职”[25]512,道出了军政府对满蒙旗人的宽容。
新政权虽然愿意“照常待遇”驻防旗人,但处于“革命”时代,成都八旗兵“感着异常震惊,以为灭亡之祸,已迫眉睫”[3]37,他们以旗甲为组织,全副武装,准备死拼。周边汉回民众闻讯,惶恐不安……形势再度紧张。蒲殿俊、罗伦等拟考虑解决成都满蒙旗人问题,包括解除驻防旗兵武装,由兵变民。据说,罗伦多次到满城,与玉昆商谈解决方案;为表现诚意,罗伦将家眷送入满城,安置在赵荣安家中[3]37-38。
革命后的四川军政府虽已建立,形势却未稳定。赵尔丰听闻清廷尚存,后悔交权,阴谋复辟;军政部长尹昌衡及部分将领也密谋夺权,各种力量暗中较劲。1911年12月8日晚(阴历十月十八日),巡防军“骚乱”,打砸抢杀,秩序混乱,蒲殿俊隐匿不出,副都督朱庆澜离城外逃,尹昌衡伺机夺权,重组军政府,任都督。接着,尹昌衡拟处理赵尔丰以消除隐患,并利用袍哥关系,分化赵尔丰卫队,暗去其保护力量。12月22日(旧历十一月初三日)晨,尹昌衡派兵抓获赵尔丰,处死枭示,并发布安民告示:“十八之变,赵逆作俑。今日就擒,谢我万众。汉业光复,于兹巩固。七千万人,谣言勿动。”[25]516
赵尔丰是旗人大员(汉军八旗),其交权后突然被杀害,成都驻防旗人再受刺激,形势再次逆转。当时“满城”尚有三营兵力及“群众武装”,“满城”墙上列排火炮,火力不弱,如果借此与军政府对抗,后果难卜。虽然成都满蒙旗人倍感恐惧,却未选择对抗,而是派人联系都督府参谋部长王右瑜。“当由满族的日本士官同学文蔚卿来都督府向我表示,少城旗籍人员决无袒赵之意”,表达了容忍尹昌衡行动、承认其统治的意愿,这一选项站队再次转变了成都满蒙旗人的地位,“我(王右瑜)当报告尹昌衡,请其严令监督少城的军队,除收缴旗籍人员的武器外,不准随便开枪”[26]73,缴枪成为解决成都满蒙族的关键,决定他们能否平安。次日(阴历十一月初四),受尹昌衡、罗伦委派,徐炯、周紫庭进入“满城”调解,商议缴枪事宜。徐炯向旗人代表分析处境说:“成都非西安比,满汉素和,徒以嫌疑,故致纷纭。诸君试思之,汉兵多满兵数十倍,满兵能一战而冲出成都乎?能再战而冲出四川乎?即出四川,而距黑、吉尚远也,满人将无噍类矣!”[27]下,1964并说明引起满汉“嫌疑”的是武器,缴出武器,就能消除“嫌疑”,满汉相安。经过徐炯等人的规劝,在掂量力量对比及考虑出路后,旗兵们交出了武器,化“兵”为“民”。
随后,尹昌衡通告“兵变”及处死赵尔丰等情况,强调:“今者,赵尔丰已诛,满城枪械已缴,前此一切疑窦,本巳(已?)不解自消。”撇清满城武装与赵尔丰的关系,说明满蒙旗人的向背。接着,新政府告示全川,要求分清敌我、宽待满人:旗兵交出武器,军政府发六个月饷银;给满城旗人住房管业证,允许买卖;清理满城公家财产,交旗人共同管理;另再拨二十万元修建工厂(同仁教养工厂),接收贫苦旗民入厂学艺,解决生计;等等[3]39。于是,成都满蒙旗人在“革命”浪潮中未遭受打击,满汉“对立”得到“和平”解决。
辛亥革命时,成都满汉民众能保持“和平”状况,未发生西安、荆州、杭州等屠“满城”惨烈事件,旗人地位虽急剧下降但还有出路,这在当时内陆城镇是极其少见的。分析其原因,大致有如下三点。

二是领导运动的立宪派是不会采取“屠满”这一极端作法。辛亥革命前后,动员民众反清的宣传口号是反满,如望帝《四川讨满州檄》曾影响了多少民众。不过,领导保路运动及促成四川“独立”的是蒲殿俊、尹昌衡,而不是“革命”党人,他们是不会采取仇满行动的。前引蒲殿俊与赵尔丰达成的交权协议中,有对旗人“一律待遇,不分畛域”等条款。该协议公布后,即遭到重庆“革命”党人的攻击,称:“且蒲、罗诸人著名保皇宪政党,平日无排满复汉之思想,与民党之人显为反对。果如蒲、罗诸人之主张,我汉族断无有今日恢复之一日,而此等保皇助满无人格之人,乃竟因人成事,为此种祸全川、贻误大局之事。”[25]508重庆的蜀军政府还发表《讨满虏檄文》,表示率兵北上,“期获赵、端以燃脐,誓灭满奴而吮血”[27]上,142。不过,成都局势已定,蒲殿俊等建立并掌握政权,愿意“照常待遇”满蒙旗人,“革命”党人虽愤怒但无可奈何,“此吾所以不能不致憾于蒲、罗诸人,而欺成都独立之内容实腐败不堪言也”[25]508。其后,尹昌衡藉平息骚乱之机,夺取政权,担任都督,处死赵尔丰,消除隐患,树立威信。成都满蒙旗人在两次事变中均未反对,还撇清与赵尔丰关系,同意缴枪,消除“疑窦”,事实上支持了新政权。尹昌衡便藉仁义之名发布宽待满蒙旗人、化解排满仇满的告示:
我四川军政府,上顺天心,下从民望,应时成立。清督赵尔丰,知满清大势已去,率其所属,拱手退让。如再依满清略定江南之例,凡属清臣清兵以及满城驻防,例当草薙禽狝,杀戳无遗。而本军政府都督以及将校兵士,不惟不杀,且加保护。凡降顺者,一视同仁,待遇优渥……夫我大汉,应天光复,人心归附,兵力厚雄,如欲尽杀诸清臣及奸贼家属,未尝不可。而竟不为者,则以王者之师,首重仁义,苟非罪大恶极,不轻诛戳。非无满清入关时暴杀之能力,实鄙薄而不屑为也。[25]523

想当年,八旗驻防成都,为控制镇压,形成对立;忆辛亥,旗兵交出武器,变兵为民,消除“疑窦”,化解对立。在这转变过程中,教育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有人感叹:“成都旗人在蜀二百余年,与地方绅民久相往来,素敦交谊,用能于共和之际,彼此毫无冲突,亲睦居然一家!”[1]236盛赞成都满、蒙、汉各族民众间的亲密关系与交流交融。“居然一家”,这也是清代成都驻防满蒙八旗最积极的影响及归宿。
注释:
①宋末元朝,蒙古人曾进驻四川,任官或定居。但在明代,蒙古人或撤离,或融合,文献缺乏相关记载。本文涉及的蒙古族是清初进入四川的,特此说明。
②康熙末年,年羹尧曾奏请在打箭炉(今康定)留驻八旗兵;雍正初年,雍正皇帝亦考虑在察木多(今昌都)驻扎军队。但是,两者后来均未实行。原因在于八旗兵系单列的军事建制,由将军、都统或副都统领导,而要留驻八旗兵,势必要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派满蒙官员管理,“成本”太大。雍正四年,清政府划分川、滇、藏三地边界后,以川藏道路为官道,沿途设塘汛,留驻绿营兵控制保护,以八旗兵作为后备,待有重要行动时,清政府才派遣八旗兵上阵,如乾隆后期福康安领导抗击廓尔喀入侵的行动。
③同治《成都县志》卷八《列女志·节妇》说明:“自马甲德通妻瓜勒佳氏至色克通妻富查氏,共四十三口俱未请旌。”就是说,该志书共记载129名满蒙族节妇,其中受到朝廷旌表者有86人。
④清政府规定:“成都将军兼辖文武,除内地州县营汛不涉番情者,将军无庸干预外,其管理番地之文武各员,并听将军统辖,番地大小事务,俱一禀将军,一禀总督,酌量妥办,所有该处文武各员升迁被调及应参应讯并大计举劾各事宜,皆以将军为政,会同总督题参。庶属员有所顾忌,不敢妄行,而番地机宜,亦归画一。”
⑤诗注:“康熙五十七年以分防兵丁散住不齐,始于成都西角筑满城,官街八条,胡同三十六条,嘉庆十六年始立旗学,今支机石碑上载旗人自康熙六十年间由楚入蜀,云云。”此资料系成都淘书斋蒋德森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⑥诗注:“‘半边桥’在‘陕西街’后,‘满城’墙骑桥而筑,一桥中分,半在‘满城’,半在汉城,桥下水迤逦出城,达于锦江。”
⑦“武庙”指满城关帝庙,位于“满城”东南部,有荷花池。具体位置,见同治《成都县志》相关部分。
⑧诗注:“嘉庆八年(1803),始立旗学,钱宗师考,取得二名。”
⑨关于道光二十三年新开内地驻扎八旗翻译考试的由来及录取名额,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83年版)相关部分。
⑩富勒洪额于道光二十三年至三十年(1843—1850)任成都驻防旗兵副都统。








参考文献:
[1]辽宁民族调查组.四川省成都市满族社会历史调查[G]//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苗族傈僳族傣族白族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2]李玉宣,衷心鉴,等.成都县志[M].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3]刘显之.辛亥革命和平解决“满城”的回忆[G]//政协四川省委,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4]徐孝恢.关于成都“满城”的回忆点滴[G]//政协四川省委,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5]四川省志近百年大事纪述编辑组.清代四川绿营、旗营和新军[G]//政协四川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6]陈一石.清代成都满蒙族驻防成都八旗概述[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1981,(3).
[7]刘显之.成都满蒙族史略[M].成都: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1983.
[8]陈一石.清代成都驻防八旗再探[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1983,(2).
[9]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成都满蒙族志[M].成都: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1993.
[10]刘国源,等.我所知道的成都满族、蒙古族[G]//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成都文史资料:第三十辑成都少数民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11]张利.成都满族社会历史文化变迁[J].满族研究,2005,(4).
[12]陈玮.清代成都满族旗人生活[J].寻根,2009,(6).
[13]万保君.辛亥前后成都满族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07.
[14]万保君.1911辛亥风暴下的成都满族[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3)
[15]万保君.辛亥革命成都满族问题的和平解决[J].巴蜀史志,2010,(4).
[16]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17]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G].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吴好山.成都竹枝辞[G]//林孔翼.成都竹枝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19]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G].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G]//林孔翼.成都竹枝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21]任杰笙.锦城竹枝词[M].忠州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
[22]傅崇矩.成都通览[M].成都:巴蜀书社,1987.
[23]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G]//林孔翼.成都竹枝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24]魏源.圣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5]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G].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26]王右瑜.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G]//政协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
[27]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G].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28]刘放皆,等.张森楷挺身斗赵督[G]//政协四川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四川保路风云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29]蓉城家书[G]//丘政权,杜春和.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
[30]陶亮生.我所知道的徐子休[G]//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成都文史资料选编:辛亥前后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凌兴珍]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2-0167-10
作者简介:秦和平(1952—),男,四川成都人,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史。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2015-XWD-B0304)。
收稿日期:2015-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