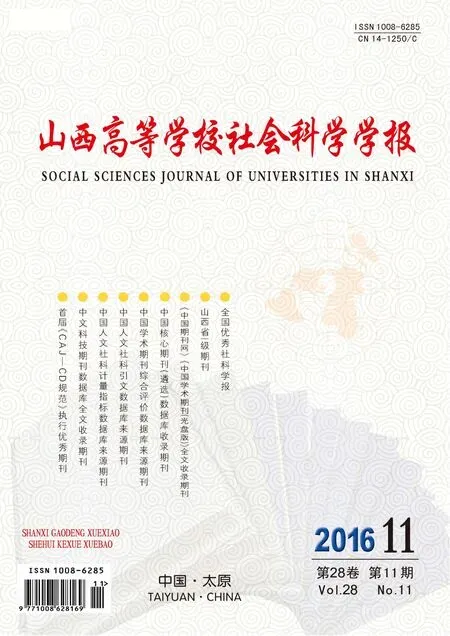网络舆情的偏差及引导策略研究
2016-04-13鲍善冰陶婷婷
鲍善冰,陶婷婷
(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网络舆情的偏差及引导策略研究
鲍善冰,陶婷婷
(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每一个网民都会受到网络舆情的影响,参与网络舆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如受众心理偏差、媒介传播偏差、网络舆情偏差等。网络受众表现出“负面偏向”和“从众倾向”;传播媒介倾向于“泛娱乐化”和“非权威化”;“网络暴力”和“网络谣言”时有发生。对此,学校、政府应高度重视,可以针对“群体极化”“近因效应”和“破窗效应”等网络现象,积极采取措施引导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偏差;媒介素养;引导策略
中国早已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8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3%[1]。微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上网变得更加方便,人们几乎每天都会参与网络活动。网络既是一个信息集散场,也是一个舆论的聚集地。网民在获取大量信息的同时也会参与网络舆论和制造网络舆情。
一、网络舆情存在的偏差分析
在互联网环境中,网络舆情的传播十分频繁,几乎每一个网民每时每刻都会受到网络舆情的影响,有些网民也不自觉地扮演了传播者的角色。在传播过程中,网络舆情在主体、媒介和客体方面存在着某些偏差,这些偏差使得网络舆论更加难以控制。
(一)受众心理偏差:“负面偏向”和“从众倾向”
网民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同时还是信息的接收者,而大多数网民扮演的是信息和舆论的接收者角色。网民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呈现出了“负面偏向”,尼尔森在调查了亚太地区用户习惯之后表明:“中国网民最喜欢发布负面评论,约有62%的中国网友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2]在面对正面社会事件时,有些网民会认为是在“作秀”;有些断章取义甚至编造的新闻却会引发大量网友围观。负面信息在网络舆论的传播过程中拥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与网民普遍存在的负面心理有关。因此,“网上各种舆论交锋,常常是负面评论压倒正面评论”[3]。
此外,网民在接受网络信息时还表现出了“从众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对某些网络舆论的“轻信”和“拒信”两种相矛盾的态度上。对于自己无法验证的信息,网民往往抱有“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轻信态度。这种态度往往会引发舆论风波,比如日本核泄漏之后的“抢盐风潮”。然而在谣言发生后,网民对专家出面辟谣却抱有“拒信”态度。这两种相矛盾的态度是由网民的“从众心理”引发的。在快节奏的网络时代,受众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冷静思考,最便捷的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态度作为自己的态度,以大多数人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这种“人云亦云”的态度也使得网络舆论环境更加复杂,“沉默的螺旋”等传播现象频发。
(二)媒介传播偏差:“泛娱乐化”和“非权威化”
当前的网络舆论呈现出了“泛娱乐化”的传播倾向。所谓“泛娱乐化”,是指当前的网络传播者无论是网民个人、还是网络媒体大都存在着将信息娱乐化的倾向,似乎任何事情都可以拿来娱乐、拿来消遣。有些公众人物为了“吸睛”将很多本该严肃对待的事情娱乐化处理。此外,在网络传播信息占主要地位的静态网页和动态视频上,主要传播的也是娱乐信息。维尔伯·施拉姆指出:“大众传媒主要被用于娱乐所占的百分比大得惊人。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在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4]网络这一新的大众传媒的“娱乐化”倾向则更加明显。公众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有关“娱乐圈”的最新信息,而对于国家政策信息、新法律法规的颁布等等国家大事,多数网站涉及较少或者更新较慢。
此外,网络环境下的舆情传播还具有“非权威化”倾向。在互联网中,权威的专家是信息的传播者,但绝大部分的网络信息传播者是“非权威”的。网络消减了专家和普通人的区别,给予了每一个参与者“话语权”。这些“草根”网民大都不具备相关专业的知识背景,却可以随时作为传播者引导舆论走向。“众多的网民向不计其数的读者提供了未经核实的信息,无知、误导和误报就这样不断循环往复。”[5]此外,很多网络媒体为了“吸睛”,对社会事件进行“断章取义”的报道也影响了舆论的正确导向。“媒介‘传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而是已经被选择和解释过的世界。”[6]网络不仅是获取新闻、搜集信息的平台,也成为了制造新闻和信息的媒介。
(三)网络舆情偏差:“谣言”和“网络暴力”
在网络环境中,每一件重大的社会事件都有可能成为谣言的温床,便捷的传播条件和众多的“草根网民”使得谣言的传播更加便捷,谣言大规模传播可能会引发舆论危机,甚至会造成“网络暴力”。近年来,以商业价值为目的而出现的“网络水军”频繁地以其规模优势转换舆论导向。他们被公关公司收买,为了经济利益出卖话语权,成为了“网络打手”。这些“网络打手”不仅是谣言的主要制造者和传播者,也是网络暴力的主要实施者。因此,“网络水军”又被媒体称为“网络黑社会”。此外,网民的“非理性”认知模式和“看客”心态也助长了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的产生。
网络谣言不同于现实社会中的谣言,它的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且影响深远。多数网络谣言披着“科学的外衣”,且言之凿凿。大多数网民缺乏相关知识,对这些谣言往往难辨真假,网络的快速传播也使得网民没有时间反问真相,很容易被蛊惑。同时,有些网络谣言也会引发网民过度“人肉搜索”,再加上“匿名心理”和“网络围观”,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很容易被侵害,他们的心理和人身往往遭受伤害。网络暴力是现实社会暴力的另一种形式,它表面上看来是没有杀伤力的,但其实网络暴力背后是血淋淋的。网络暴力和谣言是网络舆情存在的最主要的偏差,它们的存在使得网络环境变得污浊,网民极有可能成为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的参与者和受害者。
二、网络舆情偏差的引导策略
网络舆情是影响国民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让不法分子利用。因此,必须采用合理的方式引导网络舆情走向。针对网络舆情的偏差以及其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诸如“群体极化”“破窗效应”等现象,学校、政府可以创新网络舆情的引导方法。
(一)“群体极化”与培育青年网民的媒介素养
网络舆情在传播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即有关社会现象的态度、观点和情绪等舆情会呈现相对一致的现象。“群体极化”现象产生在网络舆情传播的中后期,它与“意见领袖”的表达以及“沉默的螺旋”现象有关。“群体极化”会产生两种相对立的结果,一种是形成一致的正确观点,另一种是使得错误观点更趋极端。这两种结果的形成与网民的整体素质密切相关。高素质的网民群体会促使正确的观点、态度趋向一致。因此,要引导网络舆情,首先应当提升网民的整体素质。
青年网民是网络舆论传播和接收的主力军,他们的素质决定了网民的整体素质。青年网民由于心智还未完全成熟,常常成为一些网络不法分子的利用对象。因此,必须对青年网民进行教育。学校和家庭是对青年网民教育的主要场所,而学校承担了网络教育的主要责任。当下,学校对青年的网络教育多关注的是信息技术、电脑维修等知识,而对于有关网络的法律法规、网络舆论的道德问题则不太重视。因此,学校要采用有效的方式培育学生的媒介素养。培育媒介素养的目的是增加学生对媒介如何运作、如何传递信息以及如何构建现实的理解和享受[7]。学校在网络教育上,要吸收新的网络知识和技术,更加重视有关网络法律法规及道德准则的学习,让青年网民学会健康地使用网络,而不被网络所伤害。
(二)“近因效应”与政府掌握话语权
“近因效应”是指相对于首次记忆和中间记忆,人们对一件事件、一个人物的近期记忆会更加深刻。它有利于产生正面效果,但也有可能发生负面效应,这取决于近期记忆的性质。在网络舆情的引导过程中,“近因效应”十分常见。一件重大社会事件引发网络舆论震颤后,政府及时发出声音,破除谣言,引导网络舆论,往往会取得良好效果。相反,政府对于网络舆论危机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网络谣言成为网民的近期记忆,往往会使网络舆情导向发生偏离。
在对网络舆情进行引导过程中,政府应当及时“发声”,掌握话语权。政府可以增加与网络媒体的互动,利用这些新媒体对政策作出解释,对政府行为进行公开,给网民以正确的思维导向,让网民能从正确的角度理解政府决策和行为。“将政府新闻主动喂给媒体,而不是让媒体到政府去搜集。”[8]此外,在应对网络舆论危机时,政府要及时公布事件真相,及时采取解决措施。网络舆论空间是有限的,正确的信息多了,错误的信息就会相对缩减。更多的网民将正面信息、正确观点作为近期记忆,负面的网络舆情、网络舆论危机就会减少。
(三)“破窗效应”与惩处网络违法行为
“破窗效应”是一个犯罪学理论,房间的一扇窗户被打碎后,如果没有及时修理,其他的窗户也会陆续被打碎。即放任一个负面行为就会引来更多人模仿,甚至会变本加厉。在网络舆情的引导过程中,如果不能对造谣者、网络暴力的恶意实施者及时惩处,就会诱发更多人仿效。
在网络中,每个人都享有表达自由,但这种“自由”却成为了谣言、诽谤传播的必要条件。当下,虽然网页、社交软件会对某几类不健康信息进行屏蔽,但是这种屏蔽的方法并不能有效阻止舆论的错误导向,这是因为恶意扰乱网络环境者很少受到法律的惩处。因此,惩处网络恶意实施者和传播者,对违法行为及时作出反应是净化网络环境的重要举措。对谣言的传播者、对网络暴力的操纵者、对“煽风点火”的网络水军等造成网络舆论危机的始作俑者,法律要及时给予惩处,避免由于“破窗效应”引发网民大规模的模仿。此外,还应该对网民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普及,网民只有知法、懂法,才能够自觉约束自身行为。网络不是法律的空白地带,网络上的自由是法律规范下的自由。只有规范网络自由,才能净化网络空间。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6-01-22].http:∥www.199it.com/archives/432626.html.
[2] 王江燕.冲击与重塑:网络文化下的政治向心力[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3):36-39.
[3] 曹桂华.论网络舆论引导中主流媒体作用的发挥[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4-27.
[4] 马媛媛.新闻的娱乐化不等于娱乐新闻[J].才智,2015(30):266.
[5] 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利弊的反思[M].丁德良,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0:4.
[6] 居延安.信息、沟通、传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84.
[7] 蔡帼芬.媒介素养[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66.
[8] 李跃华,李习文.简述我国对国外应对网络舆情危机做法的借鉴[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2(8):14-15.
Research on the Deviat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s and the Guiding Strategy
BAO Shanbing,TAO Tingting
(SchoolofMarxism,ShanxiUniversity,Taiyuan030006,China)
In the Internet era, almost every netizen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s and gets involved. But in this process,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s gradually demonstrate some deviations concerning public psychology, media publicity, and public opinions. Audience psychology shows the negative tendency and conformity; media have the tendency of over-entertainment, and non-authority. Violence and rumor occur in the Internet. In this situation, governments and school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t ,and use the Internet phenomena of "group polarization", the "recency effect" and "broken window effect" and take some active measures to guide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s.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deviation;media literacy;guiding strategy
2016-08-30
鲍善冰(1957-),男,山西应县人,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价值观。 陶婷婷(1991-),女,山西阳泉人,山西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生。
10.16396/j.cnki.sxgxskxb.2016.11.004
C913.4
A
1008-6285(2016)11-0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