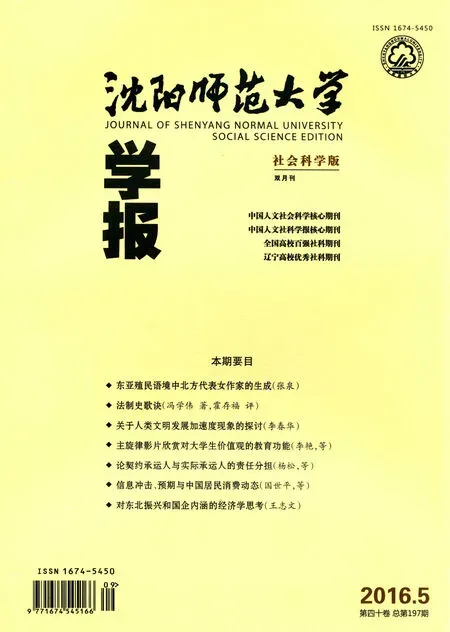红山文化面饰的艺术价值研究
2016-04-13刘海年
刘海年
(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红山文化面饰的艺术价值研究
刘海年
(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面饰种类繁多、材质多样,形象刻画以人物为主,制作手法也不一样,呈现出古代艺术非常强烈的表现力。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这些面饰,是还原红山文化时期原始艺术发展水平的宝贵文化遗存,具有文化历史价值及艺术价值。其面饰造型,简约、粗粝,充满了亘古的神秘性和“巫”的气息,传达了当时人类最纯粹的精神寄托,是中国原始艺术的一种表现类型,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溯源的组成内容之一。红山文化面饰,由于出土于各个不同地区,数量较少,附加的信息量弥足珍贵,是考证新石器时代古代艺术发展状况不可缺少的遗产资料。
红山文化;面饰;艺术价值
一、红山文化出土面饰概述
(一)根据《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装饰品种类不多,有穿孔蚌壳、刻画人面形穿孔蚌片,以及刻画后镶粘蚌片的穿孔人面石饰件等。”[1]出土的这件“蚌人面饰”长4.3厘米、宽3.5厘米,用浅阴刻线条刻磨出眼眶、嘴部与牙齿,以钻而不透的圆槽表示眼珠,造型单纯、简练。在前额头上钻有两个大孔,下颌处有一孔,可能是用来穿绳佩戴的需要。另外,兴隆洼遗址第一地点22号房址发现了一件石雕面具,这件石雕面具的嘴部贴有贝壳,可能是牙齿的装饰,脸部造型简单,眼睛部位有两个未钻空的大圆孔,上面有两个钻空的小圆孔,也可能是用来系挂方便。
(二)根据《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出土兽面牌饰1件。置于腹部正中。玉呈淡绿色。体扁平光洁,双面雕琢兽首形象。双耳大且竖起,镂空圆目及鼻孔,阴线刻出耳、眉际、鼻、嘴部廓线。吻部宽大,嘴角下咧,下颌窄尖,上有对钻二小孔,可穿系捆绑,有插磨使用痕迹。整体造型神秘庄重,线条简洁明快,表现准确。通高10.2厘米、最阔14.7厘米、厚0.4厘米。”[2]
(三)根据《洪格力图红山文化墓葬发掘报告》:“陶器2件。均为人面饰。一件泥质红陶,质地细腻,火候较高。正面外轮廓基本呈圆形。背面略凹呈平台状,深浮雕。额骨前凸,用两道相连的弧线形深(0.2厘米)凹槽表现出了高耸的眉骨。眼窝近似菱形,且正中央钻有深约0.55厘米的圆窝为睛。眼角处有明显的雕刻痕迹,眼角两内侧相接而成鼻梁显塌扁,鼻尖高凸,上钻有一圆窝。外眼角下与颧骨之间及鼻梁之颧骨间各刻有一道凹槽,表现出生动的脸部线条。口为一道横凹槽,嘴角处凹槽向上弯,并由深到浅连续至外边缘。顶部至背面对穿,钻出两孔,下颌至背面对穿一孔,可供佩挂或固定之用。下颌一侧表层残,长2.7厘米、宽2.5厘米、厚1.4厘米。另一件陶质及形制与上述一致。背面平坦,颧骨前突,眉为相连接的两道弧线状悬凹槽,同样表现了高耸的眉骨。钻有0.55厘米深的锥状深窝表现出圆形双眼,高鼻梁,鼻尖钻有一圆窝。颧骨两侧的斜凹槽与上述一致。口为一道横凹槽。顶部至背面对穿两孔。长2.1、宽1.85、厚1.2厘米。”[3]
(四)巴林右旗巴彦塔拉苏木苏达勒噶查遗址出土一件“玉浮雕人面”,长约4.3厘米、宽度约4厘米、厚度约1.1厘米,青玉质,玉面微凸、阴线刻画出脸的外轮廓和眼睛的形状,琢磨出鼻子、嘴和下颌。背面有一对钻的象鼻孔,可能是用来系、穿的部位。
这五件发现和出土的面具雕塑,材质不同,雕刻、装饰手法不尽一样,但是整体造型都是原始、朴拙,是当时社会面饰艺术发展状况的代表,而且这几件面饰的材料、制作工艺也都有所不同,呈现出当时社会面饰盛行的一面。由于红山文化出土的面饰遗存数量很少,为考证当时红山时期人类面饰的制作工艺、社会功能、面饰所具有的原始艺术基因给研究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猜测性,由此也越发显现出这几件面饰的珍稀性。
二、红山文化出土面饰艺术考古
(一)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蚌人面饰”小件,其面部轮廓简约,随蚌壳的形磨制出来,眼睛两个未钻空的孔代表了眼睛的瞳孔,周围的圆圈形状表示眼窝,没有鼻子的形状,嘴的刻画简朴概炼,只用两根线就抽象出嘴的形状,嘴下部有一个穿透的孔。这件4厘米左右的小型挂饰人面像,整体造型简约,只是用了最简单的造型语言就把脸部的特征表现出来,从艺术表现上达到了“以少胜多”、用最简单的语言表现了这件小型挂饰人面像的特征,是古代原始造型艺术的萌发阶段,是人类用艺术形象表达精神世界的开始,具有最直接、最率性的生命表现特征。“蚌人面饰”的出土,从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红山文化时期人类整体的生存状况和对自然、生命的敬畏,具有浓浓的“巫”的气息,是红山人类内心世界的诠释。另外一件贴贝齿石雕面饰,材质是石头,整体呈“甲”字形,眼睛的雕刻手法和“蚌人面饰”的雕刻手法几乎一致,整个脸部轮廓比“蚌人面饰”的外轮廓更加不雕琢,只是具有了五官的特征,嘴部凹下去的部位呈三角形,里面由贝壳装饰,造型抽象奇谲,充满神秘的远古气息。从钻孔工艺上看,当时的人类在石器上钻孔的技术已经有了进步,有了专门的钻孔工具。也由于当时人类的造型意识和造型能力受到当时生产工具的束缚,在材料雕刻上还满足不了当时的造物需求。钻孔技术的出现,满足了造物行为一定的功能性要求,如佩戴和悬挂的功能,但还不能完全达到对造型更深入的表现,如人物五官更形象、更细微的描绘,但从现在的审美角度来看,恰恰是因为这些物质条件的约束,反倒使这几件面饰具有了原始、质朴、粗粝、不过分雕琢和修饰的美学特征,具有极强的形式感和生命表现的远古象征,是红山文化初期人类造物活动的一部分内容。
(二)巴林右旗巴彦塔拉苏木苏达勒噶查遗址出土的“玉浮雕人面”,是用青玉材质结合线刻法雕刻出来的一件小型面饰。其脸的外轮廓、眼部用线雕刻,鼻子部分用琢磨的方法,造型简单奇异。这件雕刻面饰,由于是在玉质材料上进行刻画,显示了当时已经出现了雕刻玉器的工具和工艺,如线条的雕刻。该“玉浮雕人面”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与“蚌人面饰”雕刻手法的不同。首先是材料的选择上,选玉质材料来进行雕刻,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玉浮雕人面”的出土,确定了当时社会已经具有了采集玉石的能力,并且也具有一定的裁玉、雕玉、琢玉的工艺水平。对于为何选择玉质材料进行雕琢,在当时社会的环境下,应该具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如社会身份问题、尊卑问题、功能问题、造物形象问题、工艺问题等。这件玉浮雕人面像的出土,不仅是简单的材料上的变化,而且是当时社会功能等级的需求或是另外更复杂的原因所致。另外,由于选材不同,满足当时社会功能的需求不同,面饰从简单的石质材料到玉质材料的变化,可能是当时社会对面饰需求人的身份的变化,也就是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等级分化等原因,是红山文化时期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三)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出土的“兽面玉牌饰”,表明红山文化时期的雕刻工艺和艺术表现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从玉器材料的切割工艺、钻孔技术、琢磨水平上,红山时期的玉器制作都大大较兴隆洼时期的雕刻水平有很大改进。雕刻的艺术手法多样,钻孔镂空雕、线刻结合,在这件作品上体现的完美、高超,是红山时期玉器雕刻水平达到一个历史高度的体现。这件动物肖形首玉面具,做工精细,手法娴熟,刻画传神,对造型的把握准确,是玉器雕刻工艺上的提高,是写实造型能力的表现,是当时社会手工艺发展水平的体现。“兽面玉牌饰”出土的文化价值,在于它是红山文化发展到成熟时期信息反馈的载体;它的艺术价值,是熟练掌握了裁玉、切玉、钻孔、磨光等一系列制玉工艺。而且运用了线的雕刻手法,是浅浮雕艺术的表现形式,在雕塑的表现手法上是一种新的尝试,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性。并且在艺术造型上获得了更大的进步,刻画的形象传神生动。
(四)洪格力图红山文化墓葬发掘报告中出土的2件陶器,均为人面饰。“……该墓葬虽然没有发现容量器类的陶器,但发现了泥质红陶人面形饰件,丰富了其文化内涵”[3]20。这两件小型陶塑面饰像,用软质的陶泥作面饰,由于雕塑刻画的材质发生了改变,塑造手法和造型样式复杂起来,尤其是对五官、脸部的塑造,运用了很多装饰手法,面部的结构丰富,与“蚌人面饰”等石质材料的面饰有很大不同。
泥质红陶人面形饰件的出土,表明红山时期人类的造型活动已经不满足于对石头、玉石、蚌壳等材料的使用,开始使用更适合自身造型需求的材料。泥质红陶材料的使用,使当时的人类获得了更加自由、宽阔的造型空间,对物象的表现也越来越丰富,也是当时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能力增强的表现。由于红土和水混合成的陶泥,能充分展示人的造型能力,能灵活塑造出很多满足当时实用需求的生活用具、祭祀道具及其他精神世界需求的器型,能制造和创造数量更多、器型更丰富、能满足更多人使用的物品,极大地改变了当时社会造物活动的范围,显示出了当时红山人类的造物智慧和达到一定阶段的文明程度。“泥质红陶人面形饰件”的造型特征,从造型特征上与“蚌人面饰”“兽面玉牌饰”有很大不同。“泥质红陶人面形饰件”对面部结构、表情、比例的塑造,都较丰富和形象,显示出当时人类造型观念和造型能力的变化——开始使用合适的材料表现更丰富和更具象的造物行为。由于陶泥可以就地取材,使用方便,易于成形,干燥后或火烧后硬度增强。这种适合造型或造物材料的应用,极大地满足了当时人类社会的需求,成为盛极一时、用途广泛的造物材料。全国各地大量出土的陶罐、陶盆、陶钵、陶鬲、彩陶容器等,无不证明这种材料用途的多样性、数量众多性、传播范围宽广性等特征。相比较石头、玉石的材质硬度大、雕刻难度高、造型特征不容易把握,尤其玉石的开采比较困难,因此陶泥无疑是当时最普及的一种材料。正是陶泥的这种特性,也成为判断各个地区文化历史地域性的一种方法。
“泥质红陶人面形饰件”的艺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造型审美上的改变,也是当时人类为了表现对客观物象更具体、更直接、更写实基础上的一种造物意识或造物观念的改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人类造物活动的审美追求。
三、红山文化出土面饰艺术的精神表达
中国是世界上面饰艺术历史悠久、出土数量较多、雕刻手法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出土的古代红山文化时期的面饰以其造型古朴、稚拙、古代艺术感强烈而在世界面饰艺术领域具有重要的艺术考古价值。根据考古发掘和史籍记载,中国古代面饰的起源多与原始巫术、部落战争、狩猎活动、生命崇拜、自然崇拜等有着紧密的联系。“恐怖和敬畏以及力图对人类和自然现象做出解释的初始欲望促发了鬼神信仰的产生,并且有了充满巫术意味的原始宗教文化行为。”[4]红山文化时期的面饰是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原始宗教崇拜的意识形态发展的流变中产生的。从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的面饰造型形象可以看出,艺术表现原始、直接,雕刻技法逐渐提高,材质越来越丰富,雕刻工具越来越专业,造型手法由稚拙逐渐向夸张、变形、装饰、写实过渡。通过不同时期红山文化面饰造型的演变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造型艺术的发展线索:从对人物形象的模仿到写实手法的表达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也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逐渐变化有关系,也就是到红山文化玉器时代,红山文化的造型艺术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出土的诸件玉器的造型样式很直观地展现了这一特点。红山诸文化经过长达4 000多年发展演变过程,影响着辽河流域的诸多文化,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古代北方文化,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在红山诸文化中,是年代较早的一种,从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中国目前年代最早的玉器,石雕女神像则开了偶像崇拜之先河。红山文化后期,造型艺术高度发达,社会发展到了很高的形态,如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所说:“艺术的起源,就在文明起源的地方。”[5]红山文化的面饰艺术,在四五千年前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是古代中国发现较为原始的面饰造型艺术之一。它不仅是原始图腾的图像化,也是真实实物的象征,是远古时代人类的精神体现,是宗教艺术、民间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根植于原始民间,凝聚了漫长历史时期的审美体验,也是红山文化时期人类一种对生命本质、灵魂感悟的具象传达。红山文化面饰的功能,最初可能是作为人类对生命崇拜的物化,是人类对生命自我意识的一种象征,即原始人类认为人的死亡只是肉体的消失,灵魂依然存在,能保护本族或本人免于灾难,面饰是与灵魂沟通的工具或象征物。红山文化面饰无论是作为最初灵魂的替代物,还是后来祭祀活动中巫术的工具、崇拜的符号,以及神灵的象征等,都是古代艺术领域里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蕴藏着中国古代文化中民俗、生命意识、宗教和审美功能等精神内容。
四、结语
红山文化的面饰艺术作为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结合的文化遗产,具有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雕刻、绘画等多种人文学科的考古价值。红山诸文化的先民,在长期辛勤劳动中,用各种美石创造性地雕刻出无可计数的玉石工艺美术品,是中国古代玉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各类玉石器与当时的社会、氏族、宗教等活动维系着密切依附关系,并且享有一段时代特定的庄严辉煌的历史。
在2016年3月“十三五”会议期间,中国考古所王巍所长提出了开展“中华文明传播工程”的建议。也就是动员全社会用各种形式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成果①最新研究成果是:黄河中下游、长江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等,分别进入了初期文明——“古国文明”的阶段,史学界传统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开端的是夏王朝,并不是中华文明的肇始,而是由各地区域性文明,发展成为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四周地区施加强烈影响的新阶段,即“王国文明”的阶段。进行国内、国外的文化宣传,让世界知道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光辉历史,让十三亿中国人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都知道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悠远文明,让中国同胞增强对我们伟大民族的自信心,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华文明传播工程”的建议,是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后对中华文明进行文化全球化的一项具有追根溯源意义的提议。西辽河流域中的红山文化,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对红山文化的艺术价值进行研究,也是“中华文明传播工程”的一部分内容。出土的红山文化面饰,将和红山文化研究中的其他内容一样,成为中国古代艺术渊源的重要考古遗存资料。
[1]郭治中,索秀芬,包青川.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3(7):577-586.
[2]朱达.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7(8):9-14.
[3]苏布德.洪格力图红山文化墓葬发掘报告[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2):17-20.
[4]陈跃红,徐建新,钱荫榆.中国傩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75.
[5]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6.
Research on the Artistic Value of Facial Accessories in Hongshan Culture
Liu Hainian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The facial accessories unearthed from Hongshan culture relics have wide varieties and multiple materials,which were portrayed mainly by people with different production methods,showing the strong performance of ancient art.They are considered to be great cultural heritages reflecting art development in Hongshan Culture Period. Their cultural,historical and artistic values are also of great importance.The facial accessories are characterized to be simple and rough,mysterious and wizard.They presented people’s most pure spirit of that time.As a form of ancient Chinese art,they carried the historical elements of ancient Chinese art.Because of they were unearthed from different regions with a small number,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m tended to be of great value.The facial accessories from Hongshan Culture are indispensable for the research of art development in Neolithic Period.
Hongshan culture;facial accessories;artistic value
G 112
A
1674-5450(2016)05-0149-04
2016-07-02
沈阳市科技计划项目(F15-198-5-17);沈阳师范大学2014年重大孵化项目(ZD201425);沈阳师范大学2016年重大孵化项目(ZD201625)
刘海年,男,辽宁朝阳人,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美术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凤娥责任校对:赵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