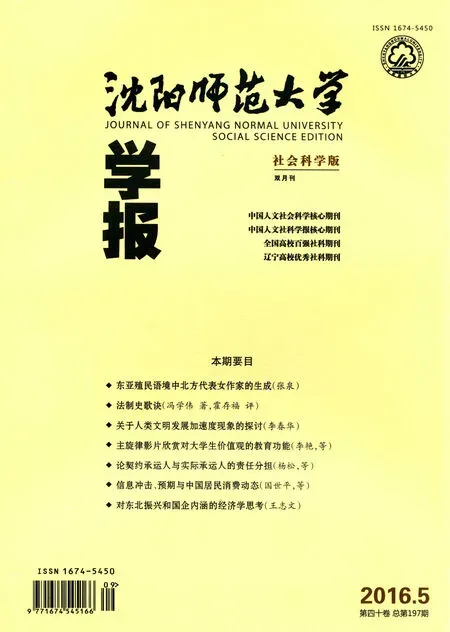社会历史发展观和人文关怀的融合——谈三重思想家威尔逊的文论批评
2016-04-13戴东新
戴东新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沈阳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辽宁沈阳110034)
文学综论
社会历史发展观和人文关怀的融合——谈三重思想家威尔逊的文论批评
戴东新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沈阳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辽宁沈阳110034)
美国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身兼社会学家、文论家和思想家三重身份,其文艺批评表明他作为“三重思想家”的特点:探讨领域的广博、独辟蹊径的观点、深刻的思想,以及犀利的言辞。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讨其价值:批评主体的大众化;文艺批评作为知性活动的功能;从艺术角度暗示作品复杂的主题和道德诉求;对按流派规定创作的作品虚构性的批判;作品的遗留价值和文艺批评的功用。旨在其对文艺批评的人文态度和社会历史张力融合做进一步研究,以期对其研究更为系统化补充一定的资料,为推动社会理想和社会进步而进行实践。直至今天,其文论批评都对于文艺领域学者的研究都会有所启示。
三重思想家;文艺批评主体;知性活动;道德诉求;遗留价值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Wilson,1895—1972年)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其著述丰富。《阿克瑟尔的城堡》(1931)向人们阐释现代文学大师叶芝、普鲁斯特、T.S.艾略特和乔伊斯等人的创作风格;《三重思想家》(1938)探讨了艺术家应该兼具思想家等多维角色,探讨了文学与公共生活的关系;历史巨著《到芬兰车站》(1940)按照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线索,探讨了法国革命思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书写辩证法,以及革命导师列宁到圣彼得堡的芬兰火车站领导十月革命,等等。正如威尔逊在《福楼拜的政治观》中说道:“一个艺术家仅有艺术这一维度是不够的,他的精神世界应该是多维度的,包括对社会意识形态、历史、哲学、心理等多方面的关照。”[1]
从这些文章中,读者可以通过对比和分析逐渐领会威尔逊这位文艺评论家的观点。本文对威尔逊的多维文艺批评角度和文化批评进行探究,这对他的文艺评论研究更加系统深入,为我国的文艺理论批评提供一定的支撑材料,让威尔逊的文学理论批评范例最大化地发挥“遗留价值”。
一、批判大众崇尚权威思想的倾向,重新定义文艺批评主体
作为文化批评思想家,威尔逊较为客观地对待大众批评,批评那些所谓的对作品不甚了解和感兴趣的学术批评。对一些批评家的批评具有一定权威性,代表批判精英这种观点,威尔逊对此进行了深刻解析。他非常犀利地指出了某些批评家施展所谓的才华,成功说服读者接受他们的权威,但他们实际上是江湖郎中,其批评技艺不过是昙花一现。真正懂得文学的有识之士犹如千里马,潜伏不露,他们尽自己所能把自己的观点通过机巧的语言介绍给那些对作品不甚了解的读者。文学批评绝不是某些对作品还不甚了解的编辑、教授或批评家的专长,而是来自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读者。这些具有一定美学品味的大众读者对某些天才的一流作家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一流的作家在市面上一直不被那些所谓的权威人士认可,或不合他们的审美情趣,可是他也许在有美学修养的大众中发现赏识其作品的伯乐。”[2]威尔逊较为客观公正地指出,对于作品中某些因素能让读者有一定的情感反应,往往是所谓的没有文学品味的研究者,但是我们对其引介别人的美学情感作为研究资料从而获得一定价值的成果不能坐视不理,加以否定。这充分说明了威尔逊尊重对文学有兴趣和品位的读者的情感反应,这些情感的本质实际上表明他们对艺术作品的赞许。我们可以这样进一步理解威尔逊的观点,只有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相遇或相互作用时,审美对象才会在我们的审美意识中呈现并展开,这也是文艺批评的出发点。
吴子林教授在其论文《菲洛克忒忒斯的神弓——当代文学批评的歧途与未来》中探讨了威尔逊为文艺理论批评家诠释的地位。“作为文学个体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纽带,文学批评家就得要有同情心和文学想象力,才能和艺术家站在同一个层面上来考察和理解作品”“批评家充当的是中介调停人的角色,调解艺术家个体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搭建艺术家和读者之间的沟通平台”[3]。吴教授就威尔逊对文艺理论批评家的定位进行评价,这种批评较为中肯。
二、重视人类知性活动的实际功用
威尔逊指出,文艺批评是人的知性活动,是为了让人更好地生存,这也说明了威尔逊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实践风范。需要特别注意一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1934年出版的《艺术即经验》一书中也提到了艺术的最终目的是恢复艺术经验与生活经验的关系,可以说这和威尔逊对文艺批评的功用有相合一致的地方。
威尔逊认为,人的知性活动有实际意义,它试图对我们的生活经历进行解读,通过对它的理解我们可以规避其中的不利因素。威尔逊曾使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和索福克勒斯戏剧创作的共性指明不同领域知性活动的共同目的——为人类生存服务。数学家欧几里得从抽象角度向大家解释了人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中距离之间的关系;而索福克勒斯利用戏剧暗示人的各种冲动之间的关系,它们混杂不清,彼此冲突,但后来都以命运出场,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平衡告一段落,这些冲动最终得以解决。所以希腊人在自然科学和艺术领域中,为我们理解生活树立了同一的典范[2]268。另外,威尔逊认为萨福的诗歌虽然没有太多的哲理性,但是可以帮助人宣泄情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诗人使用押韵方式,帮助自己和读者释放情感。人的经历由于时代不同不停地改变,一位超越先辈观点的作家一定会抓住以前未被解释的现象。人的知性活动可以是哲学和历史领域的,也可以是诗歌领域的,它会让我们心里充实,克服混乱引起的纷扰,减轻困惑不解的问题给人带来的压力。压力的减轻势必让人感到自己的力量,这种积极的情感反应证明我们读到了一部优秀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威尔逊并不把积极的情感反应和优秀作品的关系绝对化,他比较客观地指出,有些蹩脚的作品也会给人情感的慰藉。但威尔逊又指出:对于知性视野宽广、逻辑思维清晰的读者来说,还是那些功底深厚的作品让他们较为适中地释放压力。
三、道德诉求不应简单直观,而应从艺术角度含蓄地暗示
威尔逊只为在作品中表现出道德意义的作家写评论。“倘若文化不是不断地探讨赋予它意义的人类命运和价值,那么文化究竟是指什么呢?人类永远置于历史的批判之下,伟大的作家在某种方式上为人类做见证。”[4]威尔逊在强调伟大作品的道德诉求时,也从艺术创作角度对作品进行了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这篇文章中,威尔逊指出,即使一个人能够娴熟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实践,如果没有理解文学作品,对其中的道德主题就只会浅尝辄止。较高水平的作品主题不是简单、直露的信息,而是复杂的蕴含,它们往往是含蓄的;如果读者只从简单的社会道德角度去评判,而不是从艺术角度去把握,读者只会对此作品的创作感到困惑和怀疑。威尔逊引用恩格斯对几位作家的创作特点进行评价,进一步说明作家在作品中应该极力隐藏自己的道德诉求。恩格斯指出,作家愈是对自己的政治观点深藏不露,其艺术作品效果就会愈佳。他提到了巴尔扎克的价值等于多个左拉的价值。巴尔扎克认为自己是个正统主义者,谴责那个社会的堕落,但是巴尔扎克并没有言辞犀利地批判和挖苦,而是对那些贵族深表同情,这种讽刺更加尖锐和有力,起到了振聋发聩的艺术效果。海明威在《不能被打败的》这部作品中,向我们描述了斗牛士最终因受到被侮辱而丧命,但是展现勇气是他最大的胜利。威尔逊认为,海明威的成功在于他善写人的堕落和颓废,但是最成功之处莫过于海明威让读者深刻、含蓄地感受到每个人都要经历死亡。威尔逊的文艺观体现了“美在创造中”[5]。那种道德诉求中深沉的美和艺术作品的美相结合,会让人在美的感受中获得满足、愉快和幸福。
威尔逊这方面的文艺批评观和康德著名的论断“美是道德的象征”有同工之妙。康德在鉴赏判断四大契机中提出:美的分析应该把握质、量、关系和情状,美是想象力和知解力的和谐自由的游戏。我们可以凭此论点这样理解威尔逊的文艺观:作家的想象力和深厚的创作功底,加上读者对作品道德主题的深入领会,会产生美,道德象征的美。
四、合乎流派创作规定的作品和作家,有理想化和虚构性倾向
威尔逊指出,按某种流派定式进行写作的理想作品是不存在的,强调是先有作品,后来才有作品流派,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大家可以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学说在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去世以后才出现加以理解。文艺批评领域亦如此。威尔逊在文艺批评方面不受某一批评流派的限制,能利用自己在批评领域的实践和天赋,进行文艺批评大家的论述,所以才创作了主题深入、内容丰富的文艺批评作品,极力去除某些批评家纸上谈兵,仅靠想象得出的空谈。
威尔逊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学的研究是较为深入的,他在1935年申请了古根海姆奖金后,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旅行,接触了契科夫的《第六病室》的社会主义版本。“那时大清洗还没有开始,但五个月的所见所闻,让他领教了斯大林的本质,怀疑其苏联的制度。”[4]V他对苏联左翼文论家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左翼文论家总是对作品进行某种程度的检测,他们的工作莫过于在评判作品时给出详细的说明,用图表总结了一系列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应该具有的特点,而这些公式没有任何功用,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亦如此。威尔逊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当时苏联左翼批评家理想的作品特点,指出他们理想的文学模式应该满足如下要求:作品应该让无产阶级读者认识到自身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这就说明作品应描述:1.阶级斗争效果;2.作者必须让读者认识到他参与了上述活动;3.作者必须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角度出发,认识到自己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员。也就是说,完美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应该具备上述特点。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苏联这方面的左翼马克思主义批评,威尔逊回顾了1934年苏联举行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指出这次代表大会实质上将内容贫乏的作品请上舞台,而将真正优秀的作品清除出去,这无疑对文学创作是沉重的打击。所以,威尔逊提出:要发展艺术创作,就应该珍惜过去的文学大家,因为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今文学作品的劣势,我们应学会取其精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完全符合左翼批评家标准的所谓“文学大家”,否则在批评领域就会出现想象出来的文学名家。例如,人本主义者眼里完美的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社会现实主义批评家眼里完美的托尔斯泰。威尔逊对此言辞犀利,毫不留情。如果托尔斯泰按照这些批评家的标准去创造,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如果莎士比亚必须遵循这些批评家们要求的道德律令,莎翁也会休笔不耕。当时,共产主义批评运动中的希克斯(Hicks)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作家多斯·帕索斯身上,创造了想象中的帕索斯,说他是共产党员,擅长写无产阶级的作品,而后来帕索斯本人发行了一部作品,专门描述美国资本主义体制,而且还在《新共和》上宣布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后,谣言不攻自破。威尔逊非常冷静地指出:“理想中的多斯·帕索斯和没有胡须的高尔基类似,也就是说,高尔基在苏联的宣传下,形象经历了某些变化。但后来因为帕索斯对俄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些左翼批评家才否认了他被虚假化的美好形象。”[2]208
五、阐释作品的遗留价值和文艺批评的实际“功用”
威尔逊在他所处的时代就已经阐明:文化批评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虽然处于弱势,但“这并不是说文学家的边缘位置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提示社会转型在人的心理产生的看不见的影响。”[6]他对某些伟大作品的价值进行评论,同时也指出了文艺批评的实用价值。
威尔逊指出传承的艺术有其利用价值,但如果让艺术成为阶级斗争中的有效工具,艺术是武器,这未免教条。某些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为后世欣赏,并不都是因为它作为武器的工具性。威尔逊以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进行了解释:如果这些作品被当作工具,它们也是现代欧洲人摆脱中世纪的束缚用来作战的工具,凭借这种工具,他们认识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威尔逊认为用“功用”而不是“工具”会更为妥当。继而,威尔逊指出,文学效应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有长期效应的文学试图总结领域广阔和时间脉络较长的人类经验,从中得出一些普遍真理;而短期效应的文学是进行说教的,通过写小册子,从而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208。
在分析托洛茨基(Trotsky)的《文学与革命》这部作品中,威尔逊阐述了他对托洛茨基在书中提出的文学的“遗留价值”的理解[7]。在社会主义自由将要取得之时,野蛮时代和压迫时代的文学艺术有何价值?社会主义得以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将处于何等地位?是否存在着一种新型的无产阶级文学,以新的语言、特点和形式来表述新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和情感?托洛茨基不相信无产阶级文化会取代资产阶级文化,因为法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文化是在原有旧体制下发展成熟的,俄国目不识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不太可能产生先进的文化,未来亦不会。事实上,威尔逊批判了俄国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它割断了与传统文化的必然联系,把所谓的资产阶级文化(包括用词和句型)清除出去,结果让无产阶级观众费解,当时成了苏联作品标准一部分的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年)标准是这样规定的:诗人向资产阶级喊出“打倒你们的爱情,打倒你们的艺术,打倒你们的制度,打倒你们的宗教”,这其实反映了诗人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否定的抗争精神。后来,苏联也开始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建设经典文学,沿用外国的一些文化。当时的出版发行工作者引入了海明威和普鲁斯特的作品,这种做法一则证明资产阶级的堕落,二则丰富作家对生活的理解,提高自己的审美敏感性,丰富自己的情感,也就是说,引入国外文学具有师夷长技的功用。
六、结语
综上所述,威尔逊作为一位有独到之处的批评家,能从社会、历史和政治等方面对作品进行探讨和裁量,以一个社会学家的身份进行观察和论述的同时,也不会放弃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埃德蒙·威尔逊对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化因素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进行了具有人文关怀的评价,这也反映了他在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性。威尔逊所倡导的文学评论家所应肩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作品蕴含的道德诉求印证了他注重社会发展的历史性[8]。他在文艺批评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人文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融合态度,是其三重思想的有力证明。文艺评论家应该把握好文艺作品“人文——历史”的双重张力,在历史进程中把握社会进步,在文艺评论中体现人的良知和道德尊严。
[1]邵珊,季海宏.埃德蒙·威尔逊[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5.
[2]Edmund Wilson.Literary Essays and Reviews of the 1930s&40s:The triple Thinkers,The Wound and the Bow,Classics and Commercials Uncollected Reviews[M].New York,N.Y.: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Inc.,2007:267.
[3]吴子林.菲洛克忒忒斯的神弓——当代文学批评的歧途与未来[J].小说评论,2014(4):35-43.
[4]埃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M].刘森尧,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II.
[5]蒋孔阳.美在创造中[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7.
[6]赵勇.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童庆炳文学专题论集[G].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75.
[7]李辉凡.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J].苏联文学联刊:俄罗斯文艺,1993(3):50-54.
[8]梁建东,章颜.埃德蒙·威尔逊的城堡[M].上海:三联书店,2012:66.
Combination of Ideas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Humanistic Concerns——On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Triple Thinker”Edmund Wilson
Dai Dongx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110036;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110034)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Edmund Wilson presents his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style of Triple Thinker: wide subjects and horizon in exploration,peculiar opinions and shocking expression.The study mainly furthers the theme in five aspects:the popularity of the subject of criticism,the intellectual func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the complicated theme and moral appeal hinted in art form,criticizing the invention of those works create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literary schools,legacy value of literary works and the func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The essay aims at the systematic study about the combination of humanism and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rain in Wilson’s literary criticism,finally provides some materials for the domestic study about him.Furthermore,as a socialist,literary critic and thinker,he had social practices in order to realize his social idealism and promote social progress.It can still inspire the scholars in literature field today.
triple thinker;subject of literary criticism;intellectual activity;moral appeal;legacy value
I01
A
1674-5450(2016)05-0107-04
2016-05-06
戴东新,女,辽宁新民人,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艺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凤娥责任校对:赵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