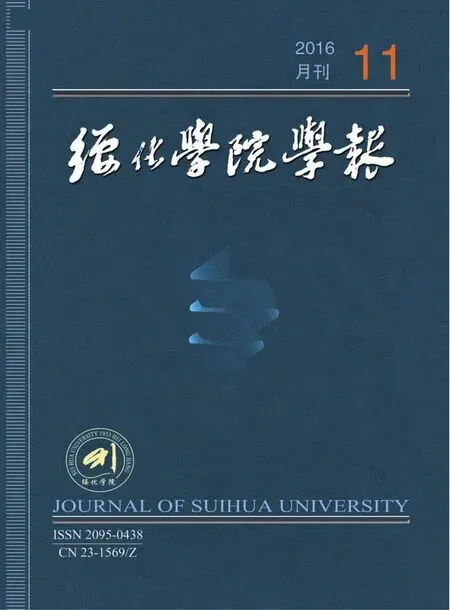浅析《哈姆莱特》中“疯癫”情节及其对主题的深化
2016-04-13李睿
李睿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浅析《哈姆莱特》中“疯癫”情节及其对主题的深化
李睿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文章从对“疯狂”的理解入手,探讨哈姆莱特“疯癫”情节的精神状态,从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中对疯癫的定义和精神分析的角度,解释哈姆莱特疯狂的真伪,并且探讨“疯癫”情节对剧本的升华,哈姆莱特在“发疯”状态下将主题引入的哲学思考。
哈姆莱特;疯癫;主题
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人们最推崇的是他的悲剧,而《哈姆莱特》作为悲剧中的代表作,受到了评论家的青睐。因为《哈姆莱特》不仅有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古今中外的评论家们不惜用浩瀚的笔墨对这部著作进行研究。
关于哈姆莱特“疯癫”情节,至今也一直存在争议,重点在于讨论他是否是“真疯”,目前存在三种说法:第一种如法国斯达尔夫人的观点,人物哈姆莱特的疯癫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的疯癫”,在她看来“剧本只是描绘了一幅人类精神在生活风暴超过了自己的力量而遭到毁灭时的最动人图景”,这一点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释地更为清晰。第二种是半真半假说,如我国学者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提到:“自己的悲痛和国王的怀疑使他一半真疯,一半装疯。”柯尔律治说:“哈姆莱特的疯狂只有一半是假,他巧妙的骗术来装疯,只有他真正接近于疯狂的状态时才能装得出。”海涅也说:“经过佯装的精神错乱投入了真正癫狂的可怕深渊。”[1]第三种情况是认为哈姆莱特自始至终是清醒的正常人,如陆协新在论文里写道:“他头脑清醒,富有智慧,思想敏捷,善于判断;对复杂而危险的形势应付自如,巨大的悲伤并没有使他丧失意志,愤怒的光焰也没有烧毁他的理智。”再如李鸿泉的论文里写道:“他思维清晰,应答敏捷,语言准确,逻辑性强。”[2]他们认为装疯是哈姆莱特复仇的一个手段。
一、哈姆莱特的精神危机
我认为讨论哈姆莱特“发疯”的真伪,首先要解决的是对“疯”的定义。《现代汉语词典》将“疯癫”定义为:“精神错乱;精神失常。”这个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被心理学家用精神分析的理论进行阐释。伯纳德·派里斯在《命运的交易》中用卡伦·霍尔奈的精神分析理论对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心理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揭示了人物的内心冲突、矛盾和焦虑。[3]从这个角度而言,哈姆莱特确实在剧本中呈现一种精神危机,虽然达不到疯癫的状态,但这种精神危机对他的语言、行为造成了很大影响,以至在他“装疯”的时候造成逼真的效果,让读者难以辨别。
霍尔奈把健康人的发展看作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把不健康的发展看作一种自我异化的过程。自我异化以一种对“基本焦虑”的防御开始,这种基本焦虑是孤独感、无助感、恐惧感和敌意感引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和模糊的疑惧感。”依据这个理论,伯纳德就认为哈姆莱特的难题在他遇上鬼魂得知父亲被谋杀,接受他复仇的使命前就已经开始。我们可以从剧本中可以发现,哈姆莱特在没有遇到鬼魂之前,他的精神危机就已经存在。对于一个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王子,他一直追求完美高尚的人格,然而突然面临自己父亲逝世、母亲改嫁的变故,他的惆怅和迷惘是不言而喻的。
“一切仪式、外表和忧伤的流露,都不能表示出我的真实的情绪。这些都是给人瞧的,因为谁都可以作成这种样子。它们不过是悲哀的装饰和衣服;可是我的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第一幕第二场)
父亲在哈姆莱特心中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父亲的突然逝世让他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第一次表达对生活的厌恶和现实的虚妄,甚至讲到“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溶解、消散,化成一篇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不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第一幕第二场)厌恶生活、甚至渴望死亡,还有内心被压抑的对克劳狄斯的敌意,让他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处于精神危机状态的人物。这些毁灭性的经历对于他的打击和创伤足以撼动他之前内心的完美图纸,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他推向深渊的临界地。
哈姆莱特和鬼魂交谈后,他又背负上了为父报仇的任务,这个任务促使他首先想出“装疯”的对策,他之后的遭遇都在“装疯”和精神危机的状态下度过。背负着复仇的哈姆莱特精神危机愈演愈烈,之前是突遭变故的难以接受,之后慢慢认清父亲被谋杀的事实,看清楚自己爱的奥菲利亚沦为试探他的工具,昔日好友也变成讨好国王的弄臣,甚至遭受被骗往英国险些丧命。经历了这个过程,哈姆莱特的精神几经崩溃。
伯纳德将哈姆莱特归为谦卑的或顺从的处事方式来迁就人们的一类,在剧本中尽管遭遇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的变故,但没遇到鬼魂之前,哈姆莱特还是说:“我将要勉力服从您的意志,母亲。”(第一幕第二场)这个类型处事方式的人往往以自我憎恨和自我毁灭为防御策略。
霍尔奈认为,自我憎恨是内心防御策略的最终产物,根本上来说,自我憎恨是理想化自我对我们实际的自我没能成为“应该”成为的自我感到的愤慨之情。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哈姆莱特的复仇上,这个任务显然加剧了他的精神危机。父亲的鬼魂要哈姆莱特为他报仇,但行为必须光明磊落,而且不能伤害他的母亲,“可是无论你怎样进行复仇,你的行事必须光明磊落,更不可对你的母亲有什么不利图谋。”(第一幕第五场)对于哈姆莱特而言,像战士一样公开宣战为父报仇的可能性极小,只能用一些手段甚至阴谋,而哈姆莱特一直想做到一个理想化的儿子、情人、王子和朋友。
当谦卑型的人遭受挫折后,除了自我憎恨,还会对自我毁灭感兴趣。这一点在奥菲利亚的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他一直顺从自己父亲和哥哥的教诲,当父亲被杀,爱人发疯,哥哥又不在身边,她从发疯走向了自我毁灭。而哈姆莱特在他的第一个独白部分开始考虑“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产生了逃离这个世界的欲望,是因为他不堪内心冲突的重负,命运的变故,复仇的纠结以致发展到考虑生死的问题。由于对死后生活的恐惧,他没有选择自杀“要是他只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这样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第三幕
第一场)他没有选择自杀,但他不时地表达对自我毁灭的思考和兴趣。这足以证明他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而这样的精神危机促使他更加理性的思考,探讨生死等终极话题。
二、哈姆莱特的理性发声
哈姆莱特在剧中确实存在不小的精神危机,但是他没有到达疯狂的阶段。这个疯狂的讨论我认为要追溯欧洲文学创作的传统。法国学者福柯《疯癫与文明》一书,通过对疯癫认识史的梳理,认为“疯癫”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疾病,更是文明或文化的产物,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4]在这本书里,福柯认为形容疯癫最恰当的词是“非理性”,在他看来,疯癫仅仅是一种由理性和非理性、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共同造就的纯粹功能。从这个角度而言,哈姆莱特在剧本中并没有失去理性,反而在极度的精神危机中思考人生、命运等关于终极问题,恰恰是一种理性发声。
哈姆莱特在遇到鬼魂之后立刻表示要装疯来保全自己:“我今后也学有时候要故意装出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第一幕第五场),他对自己的装疯有清晰的认识。之后利用“计中计”观察克劳狄斯的反应,后来又偷换送去英国的信函,让自己免于受害。从这一系列行动来看,哈姆莱特没有丧失理智,他利用自己的才智应对各种探测,设计计谋检验鬼魂的话,虽然他处于一种精神危机中,但他仍然具有清晰的思维和逻辑。
福柯对疯癫进行考古式研究,探讨了疯癫的知识和话语的历史建构过程。他认为中世纪末期到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作为一种标识尚未在社会完全确立,此时的疯癫是出现在社会领域中的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在文学作品里通常将疯人视为真理的化身。[5]疯癫因为其本身意象的不确定性,在文学艺术中被塑造异于常人的形象,这种形象以滑稽方式造成喜剧效果,或以呆傻语言说出事物的真相,可以在和理性的辩论中获得胜利。又由于疯癫本身所包含的流放元素,它也可以成为消除死亡威胁的力量。[6]
让读者容易认为哈姆莱特真正疯狂的是因为他的疯言疯语,这也使剧中其他人物迷惑以致不断的试探他。但细细品味哈姆莱特的疯言疯语,它不是简单的疯话,包含了很多真理性的探讨。在波洛涅斯试探哈姆莱特后,他也说:“这些虽然是疯话,确有深意在内。”“疯狂的人往往能够说出理智清明的人所说不出来的话。”(第二幕第二场)克劳狄斯也意识到哈姆莱特的疯狂并非因为恋爱:“他的精神错乱不像是为了恋爱;他说的话虽然有些颠倒,也不像是疯狂。他有些什么心事盘踞在他的灵魂里,我怕它也许会产生危险的结果。”(第三幕第一场)哈姆莱特的装疯并没有为他消除死亡的威胁,在与克劳狄斯的较量中,正是因为他在这些疯话中透露出的理性思考,被克劳狄斯捕捉到了危险的信号,因此要把他送到英国将其杀害。所以从福柯的理论来看,莎士比亚是遵从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疯癫形象的认识传统,借哈姆莱特装疯的语言传递他想要表达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与探问。哈姆莱特除了在装疯时期表达的语言颠三倒四,不符合当时的文明礼教之外,他的行为和判断是具有理智,符合逻辑的。结合文艺复兴时期的关于疯癫形象的文学传统,我们可以看出哈姆莱特装疯是主题升华,表达作者思索的必要情节,他并没有真正的发疯。
三、发疯情节对主题的深化
哈姆莱特“发疯”情节在整个剧本中处于核心的位置,它对整个剧的发展和主题的深化有很重要的作用。在情节层面,哈姆莱特背负起为父报仇的任务起,他就决定用装疯来躲避知道真相会引来死亡的命运,之后剧情的发展也都笼罩在他的“发疯”中,波洛涅斯用各种方式打探他发疯的原因,哈姆莱特装疯设计“计中计”刺探克劳狄斯,克劳狄斯察觉哈姆莱特装疯下的阴谋企图陷害他,哈姆莱特脱身完成复仇自己也走向死亡。从情节上看,“发疯”的情节作为一个引子伴随着整个剧情不断演化。
从主题层面来看,莎士比亚借助哈姆莱特的疯言疯语表达了自己对人类命运的终极追问,也将这部悲剧推上了一个拷问命运的哲学高度。最著名的就是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旁白,去考量反抗和顺应哪一种行为更高贵,这是一个人文主义理想的高贵英雄,与黑暗、丑恶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面临这样的挣扎和选择,将自己逼近一个最真实的世界拷问心灵,探寻活着的意义。
最能体现对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的是第五幕第一场,在奥菲利亚的墓地,小丑和哈姆莱特的对话。哈姆莱特的语言看起来是疯言疯语,没有逻辑,极富跳跃性。但隐藏在这些话语背后的是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他对话骷髅,取笑昔日能言善辩的弄臣,政客。连君王和自己也包括在内,“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霍拉旭!要是我们用想象推测下去,谁知道亚历山大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霍拉旭也认为这样的话未免太想入非非,哈姆莱特表达出无论生前多么辉煌的人物都会将结束自己的生命,化为尘土。这些疯话展开生死之思,引发死亡带给生命的虚无感,将“生命有何价值”这个终极追问的话题用这样疯癫的语言抛给读者。
通过上述讨论,我认为从精神分析角度,哈姆莱特确实存在精神危机,但他的行动和思维具有逻辑证实他并没有发疯,装疯的情节是作者用文学的“疯癫”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思考。[7]正因为哈姆莱特伴随严重的精神危机,矛盾、郁闷和纠结的心理,使他更接近于疯狂的状态,这种状态让他的“装疯”更加真实,也使他在这种危机中思考生死等哲学话题顺理成章。这个情节不仅引导了戏剧的发展,使剧情更加跌宕起伏,而且其中的语言深化了剧本的主题,将剧本的主题推向了生死、命运之思的高度。
[1]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戏剧选[M].朱生豪,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2]李鸿泉.哈姆莱特装疯新探[J].外国文学研究,1994(1).
[3][美]伯纳德·派里斯.与命运的交易[M].叶兴国,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4]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5]赤林.哈姆莱特“真疯”质疑[J].外国文学研究,1982(1).
[6]公风华.道德:理性专断的工具——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J].社会科学论坛,2009(1).
[7]黄晖.疯癫的沉默与理性的独白——解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J].法国研究,2010(1).
[责任编辑王占峰]
I106
A
2095-0438(2016)11-0079-03
2016-05-25
李睿(1991-),女,河南焦作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