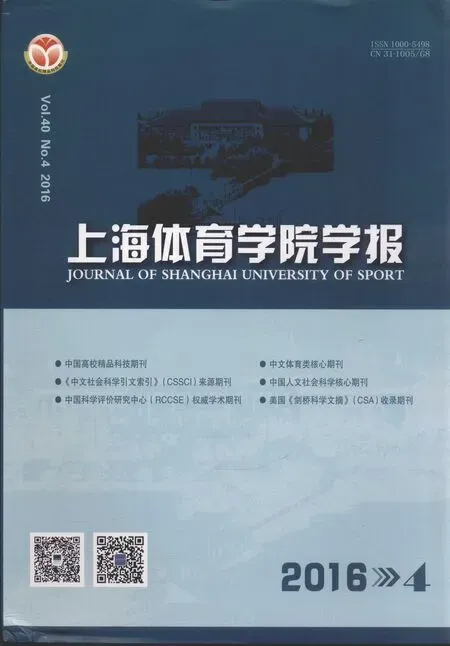体育自治与国家法治的互动
——兼评Pechstein案和FIFA受贿案对体育自治的影响
2016-04-13向会英
向会英
(上海政法学院 体育法学研究中心,上海 201701)
体育自治与国家法治的互动
——兼评Pechstein案和FIFA受贿案对体育自治的影响
向会英
(上海政法学院 体育法学研究中心,上海 201701)
摘要采用逻辑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对体育自治与国家法治的互动进行探讨。提出:体育自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国家法治,它们之间的互动主要表现为冲突与协作。通过评析Pechstein案和FIFA受贿案对体育自治的影响,进一步指出互动是体育自治与国家法治发展中的常态,也是促进体育自治、国家法治不断发展完善和实现体育善治的推动力。
关键词体育自治; 国家法治; 互动; Pechstein 案; FIFA受贿案
Author’s addressResearch Center for Sports Law,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701,China
多数人认识到体育法的存在是源于体育自治与公权力之间产生的冲突。1995年的“博斯曼案”使体育的特殊性得到了欧洲法院的承认,也让多数人认识了体育法。在此之前,许多法律工作从业者甚至都不知体育法的存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体育自治与公权力的冲突让人们进一步关注和认识了体育法,也促进了体育法的发展。针对不断涌现的有关欧共体法在体育领域适用问题,欧洲法院曾发表了著名的观点:“根据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在共同体内的重要社会意义,通过保持一定程度的平等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从而达到在俱乐部间维持均衡的目标……必须被承认为合法。”[1]体育的特殊性得到了公权力的承认。最近,德国慕尼黑高等法院的Pechstein案以及国际足联(FIFA)的受贿案件,又将体育自治与国家公权力干预的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那么,体育自治与国家公权力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国家公权力对体育的干预是否会影响体育自治呢?本文拟从国际、国内层面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对最近发生的Pechstein案和FIFA受贿案对体育自治的影响进行评述。
1体育自治与国家法治的冲突
1.1体育自治排斥国家司法介入
1.1.1体育组织规章的排他性条款自治组织拥有解决内部法律关系纠纷的排他性权力,即内部自治法律关系争议一般由自治组织系统内部解决而不诉诸国家司法机关[1]。从体育组织机构的章程看,许多体育组织章程均包含排除司法介入的条款。例如《国际足联章程》规定,协会应确保规定在协会内得到实施,如有必要对其成员施加义务。协会将对任何不遵守义务的当事人实施制裁,并且确保任何反对这些制裁的上诉均提交仲裁,而不是国家法庭。《奥林匹克宪章》第61条规定:“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发生的或者与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关的任何争议,必须按照《CAS仲裁条例》提交CAS仲裁。”[2]中国《足协章程》第61条规定:“本会会员协会、注册俱乐部必须保证遵守《国际足联章程》《亚足联章程》的规定,不将自己与国际足联、亚足联及其会员协会和俱乐部的任何争议提交法院,而同意将争议提交各方认可的仲裁委员会,并接受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这些体育组织的规章的排他性条款直接排斥国家司法的介入,并且达成一种共识。
1.1.2体育组织拥有自己的“类司法体系”体育组织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类司法体系”。从体育组织的纠纷解决体系看,成立于1984年的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简称CAS),已成为“体育最高法庭”。它就是为奥林匹克运动和国际体育争端提供专业、国际性的一致性解决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避免国家法庭由于不熟悉国际体育组织和规则而产生的不一致问题[3]。
体育组织为了成为一个有序的团体和增强凝聚力,在其章程和类似的纪律性文件中设立了相应的行为规范,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并由此对不服决定设计了救济程序机制。各体育协会根据章程的管辖条款行使对内部纠纷的管辖,该管辖权是一个开放性要约,通常不需要当事人签署[4]。多数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设定了多级纠纷处理机制。如FIFA的“司法机构”就是由纪律委员会、道德委员会和上诉委员会组成的两级处理机制。具有相关法律资格的纪律委员会主席,负责实施FIFA规则,也可以对国家协会、俱乐部、体育官员、教练员、运动员及成员的违纪或违反体育精神的行为进行处罚;上诉委员会主席的职责就是审理对纪律委员会提起上诉的案件。此外,FIFA还为各国足球协会制定了专门的《国家体育纠纷解决标准规则》,以加强协会成员的“司法权”和减轻自身纠纷解决的负担[5]。
随着ADR纠纷解决机制在体育纠纷解决中获得广泛认可,各国也纷纷建立了国家层面的体育纠纷解决ADR机制,排斥国家司法直接干预体育纠纷,并接受CAS管辖。如加拿大体育纠纷解决中心(SDRCC)、美国仲裁协会(AAA)体育仲裁小组、英国体育纠纷解决委员会(SDRP)、法国体育仲裁院(SDRCC)等。此外,各国内单项协会也成立了自己的纠纷解决机构,如中国足协的仲裁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体育大家庭内已逐渐形成由国内单项协会仲裁机构、国家层面纠纷解决机构、国际单项联合会纠纷解决机构和国际体育仲裁院组成的,具有层级的体育组织“类司法体系”。体育组织通过这一“类司法体系”的不断运作,逐渐强化“体育王国”的自治。
1.2体育自治法与国家法律对一些体育行为的调整存在差异体育自治法基于契约和组织而产生的规范力量,其效力来源于成员的承认。体育自治法属于选择性规范,体育协会或社团章程只适用于自愿接受章程管辖的人员,一旦成员退出协会或社团,章程就对他们不适用了。对协会或社团成员,体育自治法对其有特定的规范,甚至对于一些体育行为的规范与国家法律存在差异。例如,体育运动中的伤害不可避免,但有的上升为暴力行为,若不是发生在赛场上一定会受到刑法的规制。如1997年6月28日泰森与霍利菲尔德“世纪之战”拳王争霸赛中,泰森咬掉了对手的一部分耳朵,造成对手鲜血涌出,比赛中断。最后,泰森没有受到刑法制裁,而是由内华达州体育运动委员会对泰森进行了处罚(吊销拳击执照和罚款300万美元)。
此外,体育自治法尤其是超国家层面的全球体育法,在面对不同法系、不同国家法律时难免发生冲突。按照体育自治法,违反兴奋剂属于体育纪律问题,而按照有些国家的法律服用兴奋剂要受到刑法制裁。如在都灵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国际奥委会与意大利政府就因此产生了冲突。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使用兴奋剂者将被实施2年的禁赛处罚,而根据意大利《反兴奋剂法》使用兴奋剂的行为将受到刑事制裁(包括3年的监禁)[6]。最终,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及奥运会举办城市签署的协议,在奥运会期间,与奥运会相关活动应遵守奥林匹克规则而暂时“悬置”国家法律。
1.3国家法律在体育活动中适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体育的特殊性往往需要相关法律对体育的介入持谨慎的态度,国家法在体育活动中适用形成了一定的特殊性。作为体育市场活动的职业体育,具有一定的天然垄断性,但是作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对其调整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豁免或合理分析。如美国是最先出台反垄断法的国家,也是反垄断实践丰富的国家,其反垄断法豁免制度亦有近百年的历史,既有法定豁免,也形成了判例豁免原则。有涉及体育劳工的《克莱顿法》《诺里斯-拉瓜迪亚法》《劳工关系法》,还有关于体育转播权的《体育运动广播法》。这些反垄断法豁免制度及实践都对美国的职业体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7],也体现了国家法律在体育中适用的特殊性。
在欧洲,之前任何商业性的体育活动均属于欧盟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管辖范围,不存在所谓的“部分特殊豁免”;但是,体育的发展让国家公权力不得不重新对体育自治进行考量。2007年10月19日,欧洲非正式首脑会议通过了《里斯本条约》,其中第165条规定:“……欧盟应致力于提升欧洲体育议题,基于志愿活动为基础的结构和体育的社会和教育功能,考虑体育的特殊性。”[8]体育的特殊性得到了欧盟官方法律的认可。
在司法实践中,体育的特殊性促使形成新的法律原则理念和法理。如体育活动往往具有较高的受伤害风险,这种高风险逐渐通过司法实践形成了“甘冒风险”原则理念和法理。1992年的奈特诉朱厄特案的裁决告诉人们,不要把所有在体育活动中受到的伤害都起诉到法院,体育固有风险应被考虑在体育伤害侵权事件中[9]。受1981年考尼案的影响,针对体育比赛的暴力伤害行为,英国法院确立了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参赛即为同意”原则[10]。
1.4国家法庭对体育自治的质疑在体育活动的相关司法实践中,国家法庭对体育自治的质疑从未间断。德国司法机关对体育协会的态度就是一个典型。尽管德国大多数体育协会规定经过终局裁决后,不得向其他纠纷解决机构重开讼事,有的甚至明确规定不得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德国法院认为,协会内部裁决难以达到中立的标准,对此明确指出:“体育协会章程条款不能排斥法院的司法管辖权,禁止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的条款是无效的。”[4]
除了1995年的“博斯曼案”,还有不少上诉到国家法院的相关体育纠纷案例对体育自治提出了挑战。2008年7月,英国短跑名将钱伯斯向伦敦高等法院提起诉讼,以不合理限制贸易为理由质疑英国奥委会(BOA)章程的合法性。他因服用类固醇被禁赛2年,期满后,英国奥委会根据其章程第73条排斥他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因此,他因服用兴奋剂被终身禁赛。最终,伦敦高等法院以钱伯斯延误了申请等其他理由驳回了上诉,确认了他不能代表英国参加奥运会。同时,麦凯法官也表示了对BOA的质疑:“我不得不考虑BOA颁布法律说一名运动员被证明使用兴奋剂欺骗的相称性……是代表他的国家的不正确或不合适人选。”[11]
瑞士联邦法庭作为CAS的上诉机构,对体育自治起到了监督作用。2012年3月27日,瑞士联邦法庭以“违反瑞士公共政策”为由,驳回了2011年6月29日由CAS对球员弗朗塞里诺·马图扎伦反对国际足联决定的裁决。在此案中,CAS驳回了上诉人的请求,并确认了FIFA DRC的决定。瑞士联邦法庭指出:①FIFA的制裁体系是为了保护其成员的利益,然而在球员因违约赔偿时,对球员经济自由的保护不足;②FIFA的制裁在事实上不符合预期目的,如果球员被排斥出比赛,会导致他因丧失赚钱能力而无法支付裁决损失;③执行裁决的目标与有效性不平衡,过渡限制从事足球相关活动[12]。截至2015年6月,因不服CAS裁决上诉到瑞士联邦法院的130起案件中,有10起案件得到瑞士联邦法院的支持。
2体育自治与国家法治的协作
2.1国家法为体育自治提供了依据和保障
2.1.1体育自治的国家宪法依据在国家层面,一些国家宪法为体育自治提供了依据。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第124条规定了德国人民有:“有组织社团及法团之权,且此项权利不得以预防的方法限制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9条规定:“所有德国人都有结成社团和团体的权利。”《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18条规定,所有公民均有不经许可而自由结合之权利[13]。《西班牙宪法》第16条规定:“西班牙人民依合法宗旨并根据法律规定,自由地集会结社。”巴西的《联邦宪法》规定:“体育协会及体育实体的组织和运作是自治的,并受宪法保障,不允许政府对体育进行干涉。”[1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自由结社权。这些宪法中的社团权及结社权是体育自治合法性的根本依据。
2.1.2体育自治的民商事法律依据各国民商事法律对行业自治法的效力不同的规定,为体育行业自治提供了法律依据。例如《德国民法施行法》规定:“《民法》及本施行法所称法律指所有的法律规范,依照通说及实务,其形成途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法规等制定法以及习惯法和法官对法的续造。”[15]因此,德国的行业自治规章作为行政法的渊源之一,直接具有法定的强制性。体育自治原则被载入《德国基本法》第9条,其中明确规定国家司法应尊重体育领域内的自治权利。《意大利民法典》规定:“民法的法源包括法律、条例、行业规则和惯例,行业规则是指行业条例、集体经济协定、集体劳动契约和劳动法院作出的有关集体争议的判决,但不得与法律强制性规范和条例相抵触。在法律和条例的调整范围内,惯例在法律和条例引援的情况下发生效力,且行业规则的效力优先于惯例。”[16]《日本民法典》规定,有与法令中无关公共秩序相异的习惯,如果可以认定为行为当事人有依该习惯的意思时,则从其习惯。不违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的习惯,限于依法令被认许者或有关法令无规定的事项者,与法律有同一效力[17]。《瑞士民法典》规定:“任何法律在文字解释上,法律有相应规定适用的法律;法律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惯例;无惯例时,依据自己作为立法人所提出的规则裁判。在此情况下,法官应依据经过实践确定的学理和惯例。”[18]我国《体育法》在第48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在第49条规定:“在体育运动中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
此外,也有一些国家并不承认体育行业自治规章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如法国的行业规章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政府监督的,有的需要得到政府批准才能生效,有的只要呈报有关政府部门备案,没有遭到反对就生效[19]。美国的行业自治规章仅具有指导意义,须得到官方的认可才具有法律效力。
2.1.3国际公权力对体育自治的承认在国际层面,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是唯一在全球事务中享有权威的全球性政府组织。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71条规定:“经社理事会应与非政府组织就其职权范围的事项与之咨商。”这不仅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事务,具有国际法上的依据,而且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事务权利的保护,这为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奥委会的法律地位提供保护,也为国际体育自治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在2014年纽约举办的第69届联合国一般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指出:“大会支持体育的独立性与自治以及国际奥委会的领导奥林匹克运动的使命。”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指出:“体育是人类唯一真正实现全球普适法(universal law)的领域,而在全世界范围内适用这一普适法,体育不得不承担的自治责任,政治必须尊重这种体育的自治。”[20]
此外,体育的特殊性还在一些国际性政府组织的规范性文件中得到承认。如2007年在布鲁塞尔通过的《欧盟委员会体育白皮书》就承认了体育的特殊性。该白皮书认为,欧洲体育的特殊性主要包括2个方面:①体育活动和体育规则的特殊性。例如,男女分开比赛,参赛人数的限制,确保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保持各参赛俱乐部之间的实力均衡等。②组织结构的特殊性。包括尊重体育自治和体育机构的多样性,从基层体育到精英体育的金字塔式竞赛结构,不同层次不同运作者间的组织团结机制,以国家为基础建立体育机构,每个项目只有一个体育联合会的原则[21]。
2.2国家司法对体育自治的支持国家司法介入体育纠纷是谨慎的。如美国法院是尊重体育行业协会和仲裁机构裁决的,对其司法审查持慎重态度,在处理体育案件时遵循“司法救济以用尽体育行业内部救济措施”的原则及“当事人自愿放弃司法救济”,极少出现推翻体育行业裁决的情况。日本在2003年4月设立了体育仲裁机构(JSAA)[22],主要受理体育内部的纪律处罚纠纷案件,日本法院不直接受理体育纠纷,除非纠纷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民事权利。
国家司法对体育自治的支持在一些案例中也得到很好的体现。早在1977年,比利时法院在一个裁决中指出:“国际奥委会具有创造国际习惯法的权力,因为国际体育规则的效力超越彼此冲突的各国国内特定的政策和法律规则。”[23]在1984年的Martin案中,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九巡回审判庭做出了有利于国际奥委会的判决,指出:“国际奥委会有权力制定和补充《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则,在运用国家立法改变奥运会设项方面,法院必须谨慎小心。奥运会的组织和运作是依据《奥林匹克宪章》这个国际性的协议,这是全世界奥运会参与者都必须遵守的一个约定。”[24]1992年,甘德尔不服CAS裁决上诉至瑞士联邦法院,瑞士联邦法院驳回了上诉,并宣布CAS是“真正的、独立的仲裁机构”。在2003年的A.and B.v.IOC and FIS (Lazutina)案中,瑞士联邦法院在判决中公开宣布CAS是公正和独立的机构,指出:“CAS即将庆祝它的20岁生日,它已逐渐在体育王国建立了信任,被广泛承认,成为体育组织的重要支柱之一。”
2.3体育自治是国家法治的基础和有效补充体育秩序需要国家法治与体育自治共同发展和维护,体育自治在实现体育社会秩序健康有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国家法治的基础和有效补充。①体育自治法弥补了国家法的不足,丰富了国家法的内容。因为秩序的形成就是建立在实际有效的规则基础之上。体育自治法为国家立法不断完善和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泉,国家立法不断吸收体育自治法的内容,如前文所述形成的特殊法律原则,甚至直接采纳体育自治法的规定。如我国《体育法》在第34条规定“体育竞赛实行公平竞争原则”。②体育自治法是基于体育行业基础和成员的认同,较之国家法具有的国家性、普遍性和强制性特点,体育自治法具有自治性、专业性和契约性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事务分化日趋复杂,体育的行业性不断强化,体育自治法在调整体育事务及活动中更能贴近实际和反映体育的特点及利益,从而更有利于实际的体育秩序的调整。③国家法治成本高昂,而体育自治简便易行,能大大减少高额成本和负担。从人类法制历史看,行业习惯历来都是各国制定法的重要渊源。正如伯尔曼所说的:“所有的法律最终都依赖于行业习惯和惯例。”[25]
2.4体育自治与国家法治的协作在体育事务中有很好的体现
2.4.1反兴奋剂方面世界反兴奋剂体系就是体育自治与国家法治相互协作的一个典型例子[26]。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是非政府组织,《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属于私法法律体系,这个以私法主导的法律体系包含了明显的公法元素,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和其他国际性文件及国内的反兴奋剂立法、专门的国家反兴奋剂条例或法案。基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国际、国内的私法规则已迅速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和许多国家政府法律上的承认。2005年10月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截至2009年12月7日,《公约》已有130个缔约国。《公约》的目的是促进缔约各国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斗争”,并责成签署“采取适当措施”,其中包括立法、法规、政策或行政措施。《公约》意味着若要正确、有效地进行反兴奋剂斗争,法律和监管工作是必要的。国际奥委会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公约》就是在国际奥委会领导下,通过巨大的努力实现的,其宗旨为:在教科文组织体育运动领域的战略框架和活动计划框架内,促进预防并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最终消除这一现象。
2.4.2作为人权的体育权发展参与体育活动是一项人权,人权在体育中的发展通过体育组织和政府公权力的共同作用得到加强。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27条规定:“人人享有自由参加文化生活……。”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体育活动作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体育活动成为人的文化权利的一部分。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体育运动国家宪章》第1条规定:“从事体育训练和体育运动是一项基本人权。”1975年欧洲理事会通过的《欧洲体育运动全员宪章》和1992年修订的《新欧洲体育运动宪章》中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有从事体育运动的权利”,其中还有保护公民体育权利的专门条款。2007年版的《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参与体育运动是一项人权,人人都享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而不受任何歧视……”,2015年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也强调了人权的问题。我国2009年出台的《全民健身条例》,第1次以国家立法形式明确规定了公民有参加全民健身的权利。
2.4.3CAS权威性的发展CAS管辖权和强制力的发展得到了各体育组织与公权力的共同支持。CAS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得到了各国家奥委会、国际奥委会、国际体育联合会、反兴奋剂组织等体育组织的支持。在管辖权方面,《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明确规定:“任何产生或关联于奥运会的争议只能交给CAS按照《CAS仲裁条例》进行仲裁。”在悉尼奥运会期间的Baumann诉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案中,CAS仲裁庭指出:“IAAF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应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的规定,就与奥运会相关的争议接受CAS管辖。”[27]CAS奥运会特设仲裁庭明确表示:“本庭一致认为,根据《奥林匹克章程》第74条的规定,由各国际单项联合会隶属于奥运会整体框架,本庭拥有对他们的管辖权。”换言之,作为国际运动协会参与奥运会的必然结果,该协会必须接受奥运会章程规定的CAS仲裁条款。《奥林匹克章程》第29条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立场,该条款规定:“协会的地位、活动与实践必须遵守奥运会宪章。”[4]各国际体育协会章程中也有CAS的管辖权规定。如国际摔跤协会(FILA)章程的第28条第3款规定:“FILA与其成员之间,或其2个成员之间发生争议应提交CAS仲裁,不管相关国家在管辖权问题上如何规定;CAS作为最后一级上诉机构将管辖并裁决提交给它的所有上诉;上诉人必须遵守CAS章程、规章及其裁决。”国际足联(FIFA)章程的第64条第3款规定:上诉委员会宣布的决定为不可撤销的,并对所有当事人都有约束力,这一规定要求向CAS提起诉讼须经过上诉委员会[28]。通过此类的仲裁条款,各国际单项联合会的程序机制成为CAS的前置程序,CAS成为各国际单项联合会之上的终端救济机制[4]。
CAS还得到瑞士联邦法院等国家法院以及联合国的大力支持,如1998年的甘德尔案件,2003年A.and B.v.IOC and FIS (Lazutina)案件,瑞士联邦法院都公开宣布CAS是公正和独立的机构。CAS还与一些公权力机构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例如CAS通过兴奋剂案件的裁决塑造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而这又反过来形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家公约》的核心规则。由于CAS在任何地方的裁决属地均为瑞士洛桑,故在瑞士以外的裁决为外国裁决,其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是通过《纽约公约》的。CAS宣称“国内与国际权威共存……是典型的特点,国家政权不能抵制国际权威是公认的。”[29]
笔者认为,体育自治与国家法治一直都在冲突与协作中不断发展,这种互动已成为体育自治与国家法治的发展常态。
3Pechstein案和FIFA受贿案对体育自治的影响
3.1对体育自治产生巨大挑战,但不影响体育自治的根本Pechstein案和FIFA受贿案中国家公权力对体育自治的干预,会对体育自治产生巨大冲击,但并不影响体育自治的根本。FIFA受贿案使FIFA正经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在经历一系列极富戏剧性的事件后,于2015年12月21日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和副主席、欧洲足联主席普拉蒂尼被FIFA道德委员会处以禁止参加与足球相关活动8年的处罚。正如当年“博斯曼案” 中欧洲法院的介入,改变了足球转会制度,改变了足球领域垄断的状态,让体育自治不能完全游离在法律之外。这次的FIFA受贿案也使FIFA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针对德国慕尼黑地方高等法院关于Pechstein与ISU案裁决,CAS于2015年3月27日发表声明:根据德国竞争法原则(公共政策的构成部分),CAS与SFT在瑞士决定并没有阻止Pechstein向德国法院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上诉仲裁庭认为,让运动员参加比赛并根据协议进行仲裁并不是滥用支配地位,CAS仲裁也没有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的规定。上诉仲裁庭认为,为确保体育相关纠纷裁决的统一性,需要专设的国际性仲裁机构,而不是国家法庭。并强调,如果像Pechstein诉ISU案一样,仲裁协议被国家法庭认为是无效的,即使仲裁过程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国际仲裁的基本原则都将受到损害[30]。这一声明是CAS对德国国家司法机构介入体育纠纷以及对于体育自治质疑的反击。雅虎网于2015年3月27日对此申明发表《CAS在Pechstein案中捍卫了它的地位》的评论[31]。ISU于2015年7月9日发表了“Pechstein没有被恢复”的申明。在申明中强调,即使德国奥委会指定所谓的“独立公正的医疗委员会”审查涉案的医疗问题,并且随后发表他们的结果和报告,ISU都一直保留这种立场。
事实上,德国法院对体育自治的态度早在2000年的Dieter Baumann诉国际奥委会、德国国家奥委会、国际田联及CAS特设仲裁庭案中就已得到体现[28]。因此,在一定程度上Pechstein案是Baumann案的重演。ISU和CAS均通过申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且CAS正在与德国奥委会及运动员代表委员会进行协商和沟通,并打算探讨起草德国反兴奋剂法,为体育兴奋剂纠纷提供仲裁解决途径,而ISU表示会继续上诉德国联邦法院。德国国家法庭对体育自治的态度是否自此改变,可能还需要看事态的发展情况,但是CAS在Pechstein案和Baumann案中均未因为德国国家法庭的判决改变对他们的禁赛处罚,最终都维持了ISU、国际田联的禁赛处罚,以实际行动捍卫了体育自治。
FIFA受贿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育行业协会运作的最大问题是对自我利益的过度追求,并由此损害了社会利益。在体育自治体系的发展中,应兼顾和平衡社会利益。这个事件对于体育自治是否存在威胁?笔者认为,这一事件将在一段时间内引发各界对于体育自治的质疑;然而,从长远看,就像许多曾将“博斯曼案”看作是欧盟法律干预体育自治的威胁一样,它反而激发了体育世界与欧盟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和持久的伙伴关系。从此,欧盟尤其是欧盟委员会在调节欧洲体育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并没有侵害体育治理体系的自治。从FIFA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看,这次的受贿案也将进一步促进体育自治更加透明、民主和符合善治原则。
从社会发展看,虽然在有组织的社会历史上,法律作为人际关系的调节器一直发挥着巨大、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任何这样的社会中,仅仅凭借国家法律这一社会控制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一个自由的社会既是法治社会,又是一个自治社会。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体育社会实践,体育社会关系需要多种规范手段共同调整,体育自治将在体育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针对长春亚泰俱乐部不服中国足协的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事件,姜明安曾发表《法治的自治基础与自治的法治保障》的评论,指出:自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自治的保障[9]。国家法治的进步离不开体育自治的发展,体育自治的发展需要国家法律的保障,二者具有相依相辅的关系,它们的良性互动能进一步推进体育治理的合理化。
3.2促进体育自治的民主化国家公权力对体育自治的干预将进一步推动体育自治的民主化、法治化。CAS作为体育自治的“最高司法机构”,也是在国家法庭对它的不断质疑中发展和完善的。1992年的甘德尔案件促进了CAS在1994年进行了重大改革,建立了国际体育仲裁院理事会(ICAS)负责CAS的运作与财政管理,并修改了仲裁条例。2003年的A.and B.v.IOC and FIS (Lazutina)案推动了CAS在仲裁规则中设立回避措施。CAS于2012年和2013年对仲裁规则又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仲裁员提名、发展法律援助项目等,2015年12月24日CAS又发布了仲裁规则最新修订的条款。在Pechstein案中,慕尼黑法院Rainer Zwirlein法官在裁决中指出:对于CAS公正性的质疑是由于体育联盟具有指定仲裁员的优先权,而这一规定已经在CAS最新修订仲裁规则中得到修改。对此,CAS在2015年3月27日的申明中指出:“慕尼黑上诉法庭的指证是根据2009年实施的CAS规则和机构,并没有考虑到CAS组织机构的变化以及CAS程序规则的修改。”[30]从CAS的发展进程和CAS对Pechstein案的申明看,国家法庭对它的质疑,显然推动了CAS的民主化发展。
虽然FIFA受贿件仍处于发展中,但事实上,由于此次的受贿案,FIFA正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包括开始着手全面改革。2015年6月4日,FIFA主席布拉特指出:“我希望有一个全面的改革计划,且我清楚地知道只有FIFA可以实施这些改革。”体育组织自治的完善与发展,也只有通过体育组织自身的改革完成。FIFA也充分认识到这次受贿案件让FIFA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2015年12月2日的FIFA改革委员会提交给FIFA执委会的报告指出:“FIFA正经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当前的危机应当被视为FIFA复兴的独特机会,因此,为了恢复对FIFA的信心,防止腐败、欺诈、自我交易,使组织更加透明和负责,对其体制结构和业务流程的重大改革是必要的。最近的事件对FIFA造成了特别的伤害,其根本文化的改变需要持久的改革,使FIFA恢复声誉,从而让FIFA能专注真正的使命:促进全世界足球的发展。”为了恢复FIFA声誉,改革委员会报告的方案包括3个系列的原则:有效的FIFA文化领导改革原则、治理改革原则和促进FIFA更多协会成员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原则。
面对各种挑战和质疑,作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最高权威机构”的国际奥委会也正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发展和完善体育自治。2014年11月18日,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在瑞士洛桑公布了有关2020年国际奥委会改革规划的40条新建议,规划奥林匹克运动未来发展方向。在2015年9月25日华盛顿举办的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大会上,巴赫主席号召各国家奥委会和国际体育联合会推行善治,以保卫体育的信誉。托马斯·巴赫主席对各国奥委会和各国际体育联合会说:“没有善治,你们所有的成就都存在风险。”他督促各国家奥委会和国际体育联合会在所有活动中实施善治的原则和标准以保护奥林匹克运动的共同利益。
笔者认为,在Pechstein案和FIFA受贿案中,国家法治对体育自治的干预,对体育自治产生巨大影响,但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体育自治,而是进一步推动体育治理的民主化发展。国家法庭在一定程度上对体育自治的介入,可能直接导致体育协会在起草和运用规则和章程时,正确地规范自己和尊重法律。就像瑞士联邦法院为CAS程序提供品质保障一样,国家法庭为保障体育组织的成员和运动员基本权利提供监督[16]。
4结束语
在愈发错综复杂的体育社会关系下,不定时、各种方式的冲突与协作都将是体育自治与国家法治互动的表现,可能是在国家层面,也可能是在国际层面,且互动产生的影响又相互关联和彼此影响,甚至背后潜藏着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问题。目前虽不清楚Pechstein案和FIFA受贿案的事态最终将如何发展,但从长远看,通过互动,体育自治和国家法治都会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善治的原则,从而维护和促进体育社会秩序健康有序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圣甬.中国自治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19
[2]Olympic Charter[EB/OL].[2015-01-04].http://www.olympic.org
[3]张春良.论竞技体育争议的程序法治[J].体育与科学,2012(3):11-15
[4]Matthew J.Mitten & Hayden Opie,“Sports Law”: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Comparative,and National Law and Global Dispute Resolution[J].Tul L Rev,2010(85):269-322
[5]Ettore Mazzilli.国家层面足球的争议解决体系与仲裁[J].姜熙,译.体育科研,2012,33(6):19-20
[6]Schultz,Thomas,The lex Sportiva Turns Up at the Turin Olympics:Supremacy of Non-State Law and Strange Loop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6:7-10
[7]向会英.我国职业体育反垄断豁免制度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4):295-300
[8]陈华荣,王家宏.体育的宪法保障——全球成文宪法体育条款的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4:128
[9]郭树理.体育判例对美国法律制度发展的促进[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7(5):408-412
[10]曲伶俐,宋献晖.英美国家体育暴力伤害行为刑事责任初探[J].政法论丛,2007(2):85-91
[11]Louise Reilly.Introduction to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 & the Role of National Courts inInternational Sports Disputes,An Symposium[J].Journal of Dispute Resolution,2012(1):5
[12]Paolo Garaffa.意大利和国际体育法及判例制裁的比例原则[J].向会英,译.体育科研,2014(4):12-18
[13]汪莉.论行业自治的合法性[J].理论月刊,2012,225(11):93-97
[14]宋军生.论体育行业自治与司法管辖[J].体育科学,2012,32(5):71-77
[15]陈卫佐.德国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9
[16]费安玲.意大利民法典[M].丁玫,译.北京:中国大学出版社,1997:3-4
[17]屠世超.行业自治规范的法律效力及其效力审查机制[J].政治与法律,2009(3):65-74
[18]殷生根.瑞士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1
[19]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527-528
[20]Historic milestone:United Nations recognises autonomy of sports[EB/OL].[2015-04-08].http://www.olympic.org/news/historic-milestone-united-nations-recognises-autonomy-of-sport/240276
[21]EU White Paper on Sport[EB/OL].[2015-04-08].http://ec.europa.eu/sport
[22]江涛.日本体育仲裁与调停制度探析[J].体育科研,2013(2):17-19
[23]黄世席.论国际奥委会的法律地位:一种国际法学的分析[J].法学论坛,2008(6):43-48
[24]Martin V.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740 F.2d 670(9thCir.1984)[EB/OL].[2015-01-05].http://www.theplayersagent.com/uploads/knowledgecenter/article/27/attachments/50bcb57b6e5aa.pdf
[25]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贺卫方,高鸿钧,夏勇,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580
[26]Lorenzo Casini.“Down the rabbit-hole”:The projection of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beyond the stat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2014,12(2):402-428
[27]Arbitration CAS ad hoc Division (O.G.Sydney) 00/006 Dieter Baumann/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f Germany and Inter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IAAF),award of 22 September 2000 [EB/OL].[2015-01-05].http://www.jurisprudence.tas-cas.org/sites/CaseLaw/Shared%20Documents/OG%2000-006.pdf
[28]FIFA Statutes[EB/OL].[2015-06-05].http://www.fifa.com
[29]CAS/A/1149,CAS/A/1211.WADA vs FMF and Mr Jose Salvador-Carmona Alvarez.Cit[EB/OL].[2015-06-05].http://www.tas-cas.org/en/jurisprudence/archive.html
[30]Statement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 on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oberlandesgericht m ü nchen in the case between claudia pechstei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kating union (isu)[EB/OL].[2015-09-06].http://www.tas-cas.org
[31]CAS defends its position in Claudia Pechstein doping case [EB/OL].[2015-10-06].http://news.yahoo.com/cas/defends/position/claudia/pechstein/doping/case-
收稿日期:2015-12-28; 修回日期:2016-03-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4CTY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3YJA890026);上海政法学院院级课题(2016XQN09)
作者简介:向会英(1977-),女,湖南怀化人,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Tel.:(021)39227915,E-mail:xianghuiying@shupl.edu.cn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498(2016)04-0042-08
DOI10.16099/j.sus.2016.04.008
Interaction of Sports Autonomy and Rule of State Law——And the Comment on the Impact of Pechstein Case and FIFA Corruption Case on Sport Autonomy∥
XIANG Huiying
AbstractThe study used logical analysis and cas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of sports autonomy and rule of state law.It states that sports autonomy is conducted within the frame of state law,but contradicting the rule of state law to a certain extent through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The analysis of Pechstein Case and FIFA Corruption Case show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ports autonomy and rule by state law is the norm and impetus to achieve the sports autonomy and good governance.
Keywordssports autonomy;rule of state law;interaction;Pechstein case;FIFA corruption 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