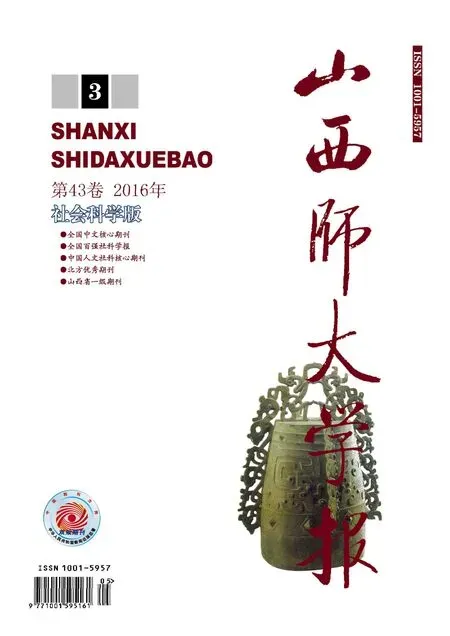胡风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传播的贡献
2016-04-13赵惠霞
赵惠霞,李 清
(西安石油大学 人文学院,西安 710065)
胡风终身致力于马列文论的研究和传播,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方面有很高造诣。他的文艺实践扩大了马列文论在中国的影响,使这一理论更加多元化和大众化。以往对胡风的研究不乏优秀成果,但是却更多侧重于研究胡风的理论本身。胡风的留学经历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联系成为胡风研究的盲区。本文将从传播学及留学生视角切入,把胡风作为留学生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中来,肯定了留学经历对他文艺生涯的影响,以及他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密切关系,着重分析胡风在译介马列著作、投身文艺评论、参与文艺论争、创办刊物等文艺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传播的贡献。
一、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五四”运动以后,马列文论著作也被介绍到中国。留学生成为译介马列文论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力军,胡风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在1929—1933年留学日本,在日本接触到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受到苏联文艺理论的直接影响。之后他又参加了日本进步团体的反帝运动,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认识,开始向中国译介马列文艺论著。“这一阶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的热潮”[1],胡风以翻译马列文论著作、从事文艺评论、创办刊物等多种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也积极配合了抗日战争。
第一,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
翻译马列文论著作是胡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途径之一。他翻译的作品有小说、回忆录、诗歌等多种体裁。1930年胡风应上海昆仑书店之约翻译出版的红色革命小说《在彼得格勒的美国鬼子》(简称《洋鬼》),开启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之路。1933年8月《文学》月刊发表了胡风所译的秋田雨雀的自叙传《我的五十年》,使读者对这位世界文化人有了更感性的认识。1934年12月翻译了恩格斯的《与敏娜·考茨基论倾向文学》,1936年翻译了匈牙利作家卢卡其的作品《小说的本质》,1936年1月翻译了高尔基的《文艺的课题》,这些译著向读者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名家的经典论著,反映了胡风在现实主义创作方面的具体倾向。胡风不断汲取名家的理论精髓,结合中国文艺实际,逐渐凝结成自己的文艺思想。1942年,胡风把之前翻译的众多短篇集成一书,题为《人与文学》,其中包括高尔基的四篇回忆录和托尔斯泰关于文学与艺术的语录。胡风对高尔基的回忆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珍品。……将更有助于读者从高尔基的表述中汲取某种精神营养”[2]321。对于托尔斯泰关于文学与艺术的语录,胡风则认为“这是从他为人生服务的恳挚的实践中留下的珍贵的经验”[2]322,值得作家学习。
胡风还把《送报夫》《牛车》《初阵》《山灵》等短篇,加进鲁迅的《译文丛书》,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不可否认,“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这些作品在读者中间有了相当数目的传播,起了对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的作用。”[2]320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这些作品,对于中朝人民的友谊结合,应该是起了一点作用的。”[3]44
第二,创办《七月》《希望》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新文学培植后备力量。
“1937年9月11日,《七月》周刊在烽火中的上海问世”[4]57。出版之后经历重重困难,先后多次停刊。1939年胡风在《七月》的复刊致辞中表达了刊物为抗战服务、与读者一同成长的愿望:
在神圣的战火下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
工作在战争的怒火里面罢!文艺作家不但能够从民众里面找到真实的理解者,同时还能够源源地发现从实际战斗里面成长的、新的同道和伙友。[5]565
《七月》在战火的淬炼中进步、成长,为抗日战争服务,“也以为新文学培植新生力量为己任……《七月》的独树一帜之处在于它青睐无名作家,是新作家成长的一块园地”[4]68。
之后创办的《希望》实际上是《七月》的延续,《希望》的支持者还是主要依靠当时《七月》的一些作家,如艾青、萧红、萧军、曹白等。胡风在《希望》的编后记中这样写道:“《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这发表在《希望》第一期,有的友人说它是《希望》的序言,也可以说是不错的。……我想指出文艺在民主斗争里面的任务不只是空喊。”[6]306在这两个刊物的致辞中,胡风道出了文艺在民主革命斗争中肩负的使命,他炽热的爱国热情激励着更多人加入抗日救国运动。文艺是他们拯救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创造新生活的武器。胡风的文艺实践,对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未来之路有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翻译马列文论著作,还是从事文艺批评,又或是创办《七月》《希望》等刊物,胡风都是围绕着爱国、救国的目标展开的。胡风通过文学作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猛烈的精神攻击,唤起广大人民群众对侵略者同仇敌忾的情绪,鼓舞人民的战斗热情。他是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灵魂工程师。
此外,胡风还为中国的新文艺培养新生力量,使中国文艺的发展拥有了更多宝贵的人才资源。著名作家侯唯动在青年时期就受到过胡风的指导和帮助,他说:“我在75岁高龄,回头看身后的脚印,庆幸自己在青年时代有了一个天大的机遇,遇到了胡风这位老师。”[7]369这不仅是侯老的心声,或许也是与胡风结缘,接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青年作家的共鸣。
一名优秀的翻译家不一定能够站在理论家的高度审慎地批评作品,一个文学理论家也未必有过兢兢业业翻译理论著作的经历。而胡风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极高理论造诣的翻译家、评论家、革命家、诗人,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也为战争年代铸就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和不懈的努力。
二、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虽然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却特别注重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胡风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运用到具体的文艺实践之中,不仅扩大了马列文论的影响,同时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推动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
(一)推动现实主义独尊中国文坛
以现实主义为特征的胡风文艺思想,“直接哺育出了在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戏剧、文艺评论等各个领域都有杰出成就的七月文艺流派”[8]。他们追随胡风在多种形式的文艺实践中,促进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也促使中国现实主义理论长期居于主导地位。
历史地看,“20世纪30年代,从苏联发展到世界各地革命文学运动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得到了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的广泛讨论,并且在东欧和中国出现了系统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9]胡风与周扬都曾在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坛有很大影响,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艺实际相结合,同时汲取西方现实主义理论之精髓,形成了两种同中有异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并且根据各自对现实主义中的典型问题、真实性原则,以及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理解展开了论争。周扬的现实主义似乎强化了文艺的政治色彩,胡风的现实主义则更加凸显了作家的主体性,他们二人的文艺论争也可以看成是现实主义发展中两个流派的论争。
1935年胡风在《文学》4卷6期上发表的《什么是“典型”和“类型”》,论述了有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周扬在1936年1月1日《文学》6卷1期上发表的《现实主义试论》中指出,胡风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解释应予修改。胡风紧接着在《文学》6卷2期上发表了《现实主义的一“修正”》,反驳周扬的批评,并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补充说明。自此,二人开始了关于典型问题的论战。很多青年作家也参与进来,在当时的文坛产生很大影响。这场论争,不仅把典型问题引入中国文坛,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最终随着中日战事逐渐拉开,以及左联内部关于“两个口号”问题的探讨,这场现实主义的典型论争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展开。“从总体上看,周扬与胡风典型论争是开创性的,对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的引进也是开拓性的,对我国典型理论建设及其历史意义(包括正面和负面的)都是必须肯定的。”[10]
典型性和“两个口号”的论争之后,又经过了“重庆论争”和“香港论争”,把文艺界有关现实主义的讨论也逐渐推向高潮。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家、理论家都参与其中,何其芳、邵荃麟等在重庆论争中把矛头直指胡风,但基本还是在学术范围内展开。与此同时,胡、周二人在现实主义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胡风相继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论民族形式问题》《论现实主义的路》等多篇有关现实主义的文章,不仅对文艺创作和发展中的多种理解和分歧展开了分析,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公式主义进行了批判,还清晰地展示了他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全貌,形成了与周扬相异的现实主义发展理路。
真理愈辩愈明,文艺论争促进了文坛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文艺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本身。胡风所参与的文艺论争,有助于厘清现实主义在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偏差,也有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健康发展。以胡风文艺思想为指导的“七月派”等文化团体,践行了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对现实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周扬文艺思想为代表的另一种现实主义则与政治发展紧密结合,逐渐形成了政治化的现实主义理论,曾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占有过极高的地位。
胡风文艺思想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也象征着中国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高度。经由胡风参与的一系列围绕现实主义展开的论争,以及有关现实主义的文艺实践工作,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现实主义的发展,促成了现实主义独尊中国文坛的局面。
(二)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大众化、多元化发展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一直注重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研究,包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两大主流派别的分立中,独具特色,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力。”[11]23胡风投入马克思主义文艺实践以来,通过创办刊物,参与多种形式的文艺实践,形成了个性鲜明的现实主义理论,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多元化发展。同时通过《七月》《希望》等刊物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播,扩大了这一理论在读者中的影响,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大众化。而在胡风的文艺实践中不断成熟的现实主义理论,也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更加丰富。
胡风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翻译、批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他的文本翻译大多取材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名家的经典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尔斯泰的著作。同时他的译著也注重了作品的丰富性和可读性,融入了控诉帝国主义侵略统治、反映无产阶级抗争的小说,例如苏联红色革命小说《洋鬼》、台湾作家吕赫若的《牛车》、日本普罗作家须井一的《棉花》等。这些译文的广泛传播,使马克思主义文论进一步渗透到广大读者中间。很多青年作家都是读了这些译文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读者中的影响。
胡风在1930年代就已经有很高的理论造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克服了左倾机械主义、主观公式主义等不良倾向的影响。胡风把托尔斯泰的文艺人生和厨川白村有关作家心灵欲求的表述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文艺评论当中,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如他对耶林、田间的评介,对端木蕻良的短篇《鴜鹭湖的忧郁》、罗淑的短篇《生人妻》的评介,都是抛开对作家的主观印象,对文本本身进行研究。1930年代写成的《林语堂论》和《张天翼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显现了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的极高造诣,称得上是作家论的典范之作。正是因为胡风在文艺评论方面,不以名家名作为导向,而是更多关注青年作者,才使他成为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作家的举荐人。在胡风看来“他们是属于人民的,直接地或间接地为了民族解放,有助于民族解放的”[3]48,同时也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引向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胡风创办的《七月》《希望》等刊物在读者中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胡风及其“同人”,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论,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论写作和文艺批评,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同时还在读者中发掘并培养了更多优秀的青年作家,形成了阵容强大的文艺团体——“七月派”。他们是胡风文艺思想的践行者,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大众化的重要力量。
胡风受托尔斯泰启发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服务理念,结合五四文艺传统提出了体现作家“主观战斗精神”、表现“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创作要求,他结合具体文艺实践提出了注重“主客体互动关系”的理论主张。这些文艺理念逐渐融合成为个性鲜明的胡风现实主义理论,不仅有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多元化发展,也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胡风文艺理论的追随者,也在实践中不断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朝着更加丰富多彩的方向发展。
三、对当今文艺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文艺实际的融合,是一种新文化的诞生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过程。但是,这种文化的融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胡风以及他的追随者们或许就是文化融合之路的殉道者,在文艺与政治的交错中险些被彻底“驱逐”。“胡风案”的发生到平反,引导着我们反思历史,重新思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也能使青年作家在老一辈文艺理论家身上感受到真正的文人气节和珍贵的学术品质。
(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文艺可以是辅助政治变革的武器,可以是弘扬正气传播正能量的工具,但文艺不可以机械地服从政治,也不能与政治完全等同。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12]93胡风案的发生,排除其个人因素,很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对文艺的过分干预和控制,以至于把正常的文艺争论、学术分歧上升为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
胡风曾经说:“真正的艺术应该是传达历史的要求,代言人民的愿望,艺术工作者应该用他的作品来争取民主运动的实现和胜利……怎样能够做到呢?这一方面要求艺术工作者抱着为人民服务的真诚深入到人民大众的生活里面,一方面要求艺术工作者在创作上艰苦地开拓现实主义的道路。”[13]206胡风的文艺主张符合当下文艺发展的要求,也有助于文艺工作者正确看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文艺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下的产物,如果受到政治的过分干预,文艺论争就很难在正常的范围内开展。这必然会破坏文艺发展的一般规律,影响文艺的审美要求,扭曲文艺论争的本来面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4]52这其实是强调了文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基本属性。但同时,“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总是呈现为政治观念、法律观念,宗教、哲学和艺术等各种具体形式,因此各种意识形态形式(如文学艺术)在具有意识形态的一般性质的同时,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质”[11]74。这实质上又强调了文艺与生俱来的独特性质。因此,文学创作既要考虑到具体的社会环境,也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要求,创作出更有益于时代发展和满足人民精神要求的优秀作品。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坚持政治信仰与个性化的文艺理论其实并不矛盾,若要避免文学沦为政治的传声筒,文艺工作者就应该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如此才能够创作出符合人民要求,顺应历史发展的作品。
(二)精神追求与治学品格的关系
胡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具体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其捍卫真理的学术品格对我们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胡风曾经说:“我很喜欢祖国的山河和各处的乡土,对于‘乡’字,有很多很多的感情。这不是指个人的乡,是指人民的深厚感情。”[15]725在胡风的文艺理论中,常常可以见到“为人民”的表述。他深信文艺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就应该代言人民的愿望。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胡风在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活中如何能够顽强勇敢地生存下来。雪后始知松柏操,诚如彭燕郊所述:“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对党怀着如此深挚、热烈的爱,对共产主义怀着如此坚定的山岳般不可摇撼的信念;也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受到如此巨大的误解,而他毫不怨尤,绝不摇摆。”[16]445然而,这就是胡风身上的珍贵品质,也是今天的文艺工作者缺失的,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胡风一生始终坚守文艺批评家的学术品格。对于凶险的文艺批判政治批判,面对文艺界一边倒的批评论调,胡风激动地怒吼:“我的理论是多年积累的,一寸一寸地思考的。我要动摇,除非一寸一寸的磔。我还要奋斗,我还要想办法。”[15]736这一寸寸的思考,包含了太多的心血与坎坷,是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文艺的向往,是他在远赴东瀛的岁月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挚诚与勤恳,是他在文艺批评上的艰难探索,是他在战火中对满目疮痍的旧中国最深切的感受。对于对手们的批判,胡风也曾竭力退让,当这种退让到达他的底线,他已经退无可退。这底线或许就是真理,就是文艺批评家应该葆有的品格。
胡风晚年“观点不变”的自信,让我们再次看到了老一代文艺工作者对文艺的执着和坚守,对真理的追求与向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道路上,胡风坚定信仰,积极探索实践,在还原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艺实际,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甘做泥土,以《七月》《希望》为阵地,为中国文艺发展培植新生力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 魏善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留学生为视角[J].吉首大学学报,2010,(7).
[2] 胡风.《胡风译文集》几点说明[A].胡风全集(第8卷)[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3] 胡风.胡风回忆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4] 周燕芬.因缘际会——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
[5] 胡风.愿再和读者一同成长[A].胡风全集:第2卷[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6] 胡风.《希望》编后记[A].胡风全集:第3卷[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7] 侯唯动.从读者中走向胡风[A].晓风.我与胡风(上)[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8] 蒋艳飞.胡风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比较研究[D].湛江:广东海洋大学,2014.
[9] 刘永明.20世纪30年代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三种理路.[J].赣州: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2).
[10] 叶纪彬.周扬与胡风典型论争及其当代评论.[J].沈阳:社会科学辑刊,1993,(4).
[11] 冯宪光.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2] 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3] 胡风.答文艺问题上的若干质疑[A].胡风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5]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A].晓风.我与胡风(下)[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16] 彭燕郊.他心灵深处有一颗神圣的燧石——记胡风老师[A].晓风.我与胡风(下)[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