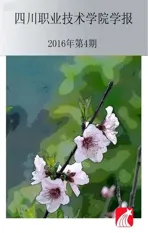探析莫言小说《红高粱》的叙事传播策略
2016-04-13蒙冬英
蒙冬英
(华侨大学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探析莫言小说《红高粱》的叙事传播策略
蒙冬英
(华侨大学文学院,福建 泉州362000)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在文坛上实属一部极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小说中许多场景和故事情节都深深地烙在人们脑海里而被铭记,这也是《红高粱》在具有极高文学价值之外的又一成功之处——运用了准确、有效的叙事传播策略,通过从创作构思到创作形式再到具体情节表现上传播策略和媒介化视角的运用,让《红高粱》在广大传播对象和文学领域中获得高度认可。
《红高粱》;叙事;传播;媒介
1 《红高粱》的传播媒介形式
在传播学著名的拉斯韦尔模式中认为,传播的过程必须由5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他们分别是传播的主体(who)、传播内容(saywhat)、传播渠道(in which channel)、传播对象(towhom)及传播效果(withwhat ef fect)。”①文学作品的传播亦是如此。《红高粱》的传播过程中,作家莫言即传播的主体,《红高粱》中的主要内容、中心思想等文学信息即传播的内容,而传播的渠道则是《红高粱》的不同传播媒介形式,对文学作品的传播效果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接受美学看来,每一个创作主体在创作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个“隐含读者”的存在,创作主体会在创作的过程中对隐含在文本之外的读者进行预设,让传播内容更好地被接受;而在传播学中无论是使用何种传播媒介,都是为了让传播内容在接受过程中不至于遇到太多的传播障碍,因此《红高粱》的叙事传播,就是传播文学作品信息的媒介表现形式。纵观《红高粱》的传播媒介形式,无论是其外部传播还是内部传播,都达到了内外兼修的效果,让文学作品在不同的媒介形式中,与传播的对象进行了对话交流。
1.1动静结合——外部传播媒介形式
创作主体在进行创作时,为了让自己的思想内容让传播对象接受,会慎重考虑到运用何种媒介传播自己的作品。传播过程中的外部传播媒介形式,简单理解其实就是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所运用到的媒介传播形式,直接服务于传播内容。莫言《红高粱》的传播,在外部传播媒介形式上,通过书籍、电影、电视剧的媒介形式,让文学作品的传播形成动静结合的效果。通过书籍的媒介形式传播,《红高粱》的文学信息通过一种静态的方式让传播对象慢慢品尝,体验高密东北乡红高粱的旺盛生命力以及高密乡抗日汉子的英勇粗犷,而书籍的媒介传播形式通过静态方式,让传播对象对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展开了无限的遐想,构造了迥然不同的红高粱世界;此外,书籍的媒介方式,让传播的内容得以大量复制而加快传播的速度,不断拓宽《红高粱》的影响覆盖面。另一方面,《红高粱》的外部传播媒介形式中还通过了电影、电视剧的传播,让文学作品在一个具有动态效果的方式下进行扩散传播。在电影、电视剧中,大量运用动态画面,丰富了莫言《红高粱》中传播内容的表达方式,这也是在文学不断媒介化的趋势中,文学作品《红高粱》迎合现代读者阅读要求和喜好的又一传播方式,让文学作品信息的传播呈现出动态的情境,覆盖更多传播对象。通过书籍、电影、电视剧的外部传播媒介形式,动静结合,扩展了《红高粱》的传播对象和提高了传播的效果。
1.2静中有动——内部传播媒介形式
文学作品在外部传播媒介形式中运用书籍媒介方式传播,属于静态传播,往往也会造成传播对象在接受传播内容过程中遭遇障碍,致使传播对象无法理解传播内容的精髓,因此传播主体会在传播过程中采取静中有动的传播方式,让传播对象更好地接受。
莫言的小说中,对于毫无生气的文本信息传播,也能通过精彩的声音媒介传播形式,让文本信息内容活灵活现,形成静中有动的传播效果。“高粱的茎叶在雾中嗞嗞乱叫,雾中缓慢地流淌着在这块低洼平原上穿行的墨水河明亮的喧哗,一阵强一阵弱,一阵远一阵近”②,抗日壮士在高粱地里穿行的情形,运用精彩的声音媒介传播方式,将红高粱地里的环境情景信息给人逼真、形象感受,通过静物的发声方式让传播对象在接受传播信息内容时获取更为有效的传递信息。“另一头骡子坐在地上,血乎乎的尾巴拂着大地,两腹厚皮抖得索索有声。两个时开时合的鼻孔里,吹出口上一样的响声。”③即使是牲畜,在莫言的《红高粱》中一样将声音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声音的媒介形式传播,让文本中的静态文字拥有了生命,产生了感情,静中有动,也让传播的对象在接受的过程中体会到声音的氛围营造,获得更为直观和深入的理解。
2 《红高粱》的感官化传播特色
强烈的感官化描写为莫言的小说贴上了鲜明的标签,这也是《红高粱》叙事传播中的一大亮点。利用感官化传播,让人们感受到恰似真实的文学描绘世界,传播了一种生命脉搏不断跳动的感受。在《红高粱》中,传播主体笔下感官化层面的描写,包括视觉、听觉、嗅觉等,都传递了不断膨胀的感官体验,并从感官体验中上升为红高粱土地上历史风俗、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冲突。
2.1视觉化传播
莫言笔下的小说,常常会给人带来一场视觉上的盛宴,经过语言艺术加工过的小说,让人在感受强烈视觉冲击之时,也给了传播对象一个思索视觉艺术和感受视觉美感的机会。作品中经过文字的描绘进行画面建构、意象营造,给人一种“造像效应”④的体验。而《红高粱》给人最大的视觉冲击力就是其中的红色意象渲染,通过一个又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让传播对象心生庄严而痛苦、神圣而战栗的感受,而非一种轻松淡然的阅感。无论是整个故事中的情节、人物、情景都被淹没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中,有金黄的红、辉煌的红、残酷的红、热闹的红、酱紫的红等。传播对象在传播过程中通过语言艺术的表达形成画面感,搭建作品和传播对象之间的沟通桥梁,让描绘的事物更加立体真实。“低垂的天幕,阴沉地注视着银灰色的高粱脸庞,一道压一道的血红闪电在高粱头上裂开,雷声强大,震动耳膜。”⑤这是我奶奶出嫁时路上的情景,闪电的血红透露着我奶奶在见到我爷爷英勇打死劫路者后的亢奋,人物的情绪也通过了给闪电的炸裂表现,血红的色彩更是给人一种喷涌而出的感觉,让我奶奶的亢奋之情跃然纸上;同时莫言也通过雷雨交加的天气预示我奶奶嫁到单扁郎家的厄运,必会引起血光之灾。在《红高粱》中,红色意象的使用比比皆是,“像一只赤红的大蝶”、“看到奶奶像鲜红的大蝴蝶一样”、“苍翠的脸上双唇鲜红”等,都通过视觉上的色彩运用,描述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画面,让人们可以在视觉化的传播过程中感受故事情节的变化以及人物情绪的起伏。
2.2听觉化传播
自然界中自古就推崇“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红高粱》中就营造了这么一个世界景象。茂密的红高粱在高密乡这块肥沃的土壤中,自由生长,吸收天地之精华,高密乡的人们也一样,直爽豪迈,不拘一格。莫言笔下的红高粱世界,人物的对话简短,但并不意味着语言的稀少会形成万籁俱寂的效果,而是通过大自然以及人们内心的发声,与传播对象进行情感沟通和传播,达到“大音希声”的妙处。
听觉化传播也许比不上视觉上的震撼和直观,然而听觉的魅力在于更容易触动心灵,引起共鸣。莫言笔下的红高粱土地上,风吹过高粱地而发出的阵阵犹如波涛般汹涌的海浪声、夜深人静各家各户骡马的嘶叫声、抗日勇士日夜兼程奔赴目的地的脚步声、高粱地里千万中蟋蟀虫子的窸窣声等,都形成了一曲曲动人的交响乐,也许人物间的交流少而简短,但却没有让人们感受觉得高密乡的安静,反而让人感觉在自然的声音中更好地传情达意。比起人物间的烦冗对话,《红高粱》中更注重突出高密东北乡上极具情感色彩的唱法,成为听觉化传播的典型。“青天哟——蓝天哟——花花绿绿的天哟——棒槌哟亲哥哟你死了——可塌了妹妹的天哟——”⑥突出高密东北乡女人的哭丧和唱歌一样,从其中也让人感受到了我奶奶在出嫁路上的凄凉之景,从简短的哭丧中就将其心中的悲怆刻画得淋漓尽致。“高粱熟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⑦歌声唱起,是一种感情宣泄,歌唱的声音,让传播的内容和对象形成情感的交流,源自心灵的声音,让读者心中激起情感的波澜。
2.3嗅觉化传播
人凭感觉而感知世界,感知自己的存在。人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而获得第一直观感受,因而在传播的过程中,需要对人的感官进行刺激,才能让人们顺利感受到描绘的世界。《红高粱》中在嗅觉化的传播上,尤其注重对嗅觉气味的描绘,让嗅觉的气味向读者传达环境周遭的信息,为情感的宣泄埋下伏笔。“我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红黄相间的腥甜气息”、“那股弥漫在田野的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都是我父亲对于血的记忆,通过人的嗅觉描写不绝的气息留在人脑海中的烙印,是深刻至极的,能在传播对象的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也是嗅觉化传播的好处。“河底下淤泥的腥味,一股股的泛上来”、“用螃蟹喂过的罂粟花朵肥硕壮大,粉、红、白三色交杂,香气扑鼻”,嗅觉的描写在《红高粱》中随处可见,也让传播对象更加容易和准确地捕捉到传播主体内心的细微变化。周围环境的描写,高粱土地环境杂乱,而淤泥的“腥”会让人的嗅觉受到强烈的刺激,对高密乡村子的环境进行了直接的情感带入;罂粟本身让人有所畏惧,可在莫言的笔下,螃蟹喂养过的罂粟,其气味的描写经过了嗅觉的传递会让人对罂粟产生一种不可抗拒、众不同的情感,牵动着传播对象内心的情绪,这也是嗅觉化传播的成功之处。
3 《红高粱》的传播媒介思维
为了让作品的内容传播取得良好效果,莫言不但注重文学作品在外部媒介传播形式的运用,而且在文学文本叙事过程中,也注重其内部媒介形式的传播,锤炼传播语言细节和描写技巧,将感官化的传播方式渗透在文本叙事中,形成传播之传播的效果。此外,莫言在作品的整体创作过程中,在作品创作内容及形式上,都渗透了灵活多变的传播媒介思维,《红高粱》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
3.1虚实相融的创作传播媒介思维
3.1.1“虚”——传奇性思维
在创作《红高粱》之时,莫言将故事发生的地点定在了自己的家乡——山东高密乡,这块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在这里,一直保留着古老的民间传统——流传着传奇性的神仙鬼怪故传说,这也培养了莫言对于叙述民间故事应具有的传奇性思维,“在民间口述的历史中,没有阶级观念,也没有阶级斗争,但充满了英雄崇拜感······”⑧因而《红高粱》中对于故事部分情节的虚构叙述,莫言可以将故事的传奇性发挥到极致,让故事中的人物、故事的情节都染上一层神秘性的色彩。《红高粱》其实讲述的就是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一段具有传奇性色彩的爱情故事和我爷爷余占鳌带领高密乡勇士抗日的英雄传奇历史,故事的发展游走于历史的边缘地带,为整个故事描绘上了传奇性的色彩,使传播对象对感叹爱情的浑然天成,崇拜英雄的英勇无畏。同时在故事的情节设置中,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场景、罗汉大爷被日军抓住生剥人皮的场面等,都经过了作者传奇性思维的加工,在民间传奇故事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让整个故事的叙述给了传播对象一股神奇的体会感,增加神秘性。
3.1.2“实”——新闻性思维
《红高粱》的文本故事内容在传播过程中,除了将传奇性的思维融入其中,还结合了故事叙述的真实原则,即传播过程中的新闻性传播思维,与其他文学形式最大的区别,就是新闻性的传播思维讲求真实。“新闻界的理想是毫无偏颇地追寻真相,然后不加修饰地把它讲述出来。”⑨让传播对象在故事的叙事传播过程中产生真实的阅感,增加作品在传播对象心里的接受程度。《红高粱》叙事传播过程中新闻性传播思维体现明显,在众多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中一味追求人物“高、大、全”的情况下,莫言却将高密东北乡上乡亲们真实的一面展现在读者面前。我爷爷余占鳌是抗日勇士,在伏击敌寇日军中英勇抗敌,是民族的英雄,在其抗日事迹中塑造的是我爷爷英勇高大的一面。然而莫言笔下的英雄形象也并非十全十美,率领东北高密乡村民英勇抗战的余占鳌其实只是一个土匪头子,在其抗日之前,也曾经杀人越货,做着土匪的勾当。甚至在其亲叔叔余大牙奸污了民女曹玲子的时候,余占鳌也只是说“睡个女人,也算不了大事”来搪塞任副官的质问,想为其亲人脱罪而不想执行“王子犯法,一律同罪”的军令。因此在主人公我爷爷余占鳌身上,也有着劣根性不符合英雄形象的一面,但却是其真实本质的一面,体现着真实化、生活化的整体个人。讲求真实的新闻性传播媒介思维,也会让传播对象在接受过程中对主人公更加认可。
3.2影视性的创作传播思维
莫言的《红高粱》在传播过程中,通过书籍、电影、电视剧不同的传播媒介进行传播,在不同的传播媒介中都引起了巨大反响。而从文本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跨越了不同的传播媒介界限,让作家出现“触电”现象⑩。毫无疑问,能让莫言的《红高粱》在影视中也获得如此高的赞誉,顺利完成文本到影视上的改编,也说明了《红高粱》中蕴含了值得被影视媒介表达和借鉴的东西,即《红高粱》在文本叙事传播中,融入了影视性的创作传播思维。
3.2.1蒙太奇手法的运用
“‘蒙太奇’的作用是把本不相连的镜头依据一定的逻辑和节奏剪辑在一起,目的在于让观众明白、了解剧情的发展过程”⑪,莫言在《红高粱》的文本叙事中,一样运用了蒙太奇的表现方式,将作品中的场景与自我的情感表达结合在一起,让传播对象更好地了解文本传达出的情感。“奶奶脸愈来愈白,奶奶的身体越来越轻飘,好像随时都会升空飞走······奶奶幸福看着高粱阴影下······奶奶想起那一年······花轿抬到单家大门时······奶奶躺着,沐浴在高粱地里清丽的温暖······”⑫对我奶奶中枪倒地的描写,场景中的镜头却进行了不同的转换,奶奶倒地时候的脸色特写,接着是切换到奶奶回忆嫁到单家的前三天,再接着是我奶奶和我爷爷的野合,最后又回到奶奶濒临死亡的现实场景。在不同的场景描写和切换中,将人物的临死的最后时光进行了距离的拉长,让整个故事的情节更加丰满,也将奶奶和爷爷的传奇爱情故事叙述完满,运用了蒙太奇的叙事传播手法。
3.2.2抽象语言具象化
文学的文本内容是通过文字进行传播的,传播的过程中会有一定的抽象性,比不上影视传播媒介中画面声音传播所具备的直观性,让传播对象在理解的过程中难度加大,因而文学的文本传播需要将抽象的内容具象化,让传播对象在具象化的内容中提炼内容的精华。《红高粱》中常常将抽象的内容具象化,“一群野鸭子从高粱上空飞来,盘旋三个圈”、“在杂草中高扬着细长的茎,开着紫、蓝、粉、白四色花”,莫言的作品中对事物进行描述叙述时,会花费较多的笔墨将事物进行具象化,避免语言的抽象和模糊的表述,呈现一个清晰的表达效果。野鸭子盘旋的圈数,一般在文字中会用概述表述,花朵的颜色也可以直接用色彩斑斓形容词进行形容,但在影视媒介传播中,这些信息都是直观表现出来的,毋庸置疑。因此《红高粱》中也选择了具象化表达传播方式,让抽象难以理解的表达对象变得具体、可观可感,减少文本文字传播的障碍和难度。
3.2.3声画合一的叙述语言
在《红高领》中有这样一段典型的描写:河里的水流到灯影里,黄得像熟透的杏子一样可爱,但可爱一霎霎,就流过去了,黑暗中的河水倒映着一天星斗。父亲和罗汉大爷披着蓑衣,坐在罩子灯旁,听着河水的低沉呜咽——非常低沉的呜咽。河道两边无穷的高粱地不时响起寻偶狐狸的兴奋鸣叫。螃蟹趋光,正向灯影聚拢。父亲和罗汉大爷静坐着,恭听着天下的窃窃秘语。⑬我父亲和罗汉大爷一起捉螃蟹时的画面描写当中,就蕴含了河水的呜咽声、狐狸的鸣叫声,高粱的晃动声音等多种声音,让整个情景画面就如同流动的图像一样在读者脑中闪现,形成了一个个声画合一的场面来完成信息的传递。显而易见,文学上的此类叙述方式也是契合了传播对象对声音和画面直观信息传递的需求,对影视媒介思维的借鉴和运用,让传播对象在声画传播下,接受双重刺激而加深对传播内容的印象和感受。
《红高粱》的整个文本描写中运用了多种准确、有效的叙事传播策略,将媒介化视角运用到文学内容的创作中,既丰富了文本的叙事方式,又加强了文本信息内容的传播,让传播对象与作品信息形成良好的沟通关系。
注释:
①张邦卫.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和文学理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3.
②莫言.红高粱[M].广东:花城出版社,2011:03.
③莫言.红高粱[M].广东:花城出版社,2011:35.
④付艳霞.莫言的小说世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19.
⑤莫言.红高粱[M].广东:花城出版社,2011:53.
⑥莫言.红高粱[M].广东:花城出版社,2011:46.
⑦莫言.红高粱[M].广东:花城出版社,2011:57.
⑧莫言.用耳朵阅读[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57.
⑨约翰·维维安著,顾宜凡等译.大众传播媒介[M].第七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94.
⑩刘文辉.传媒语境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82.
⑪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7.
⑫莫言.红高粱[M].广东:花城出版社,2011:72,77.
⑬莫言.红高粱[M].广东:花城出版社,2011:06.
[1]张邦卫.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和文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付艳霞.莫言的小说世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
[3]莫言.红高粱[M].广东:花城出版社,2011.
[4]莫言.用耳朵阅读[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5]约翰·维维安.大众传播媒介[M].顾宜凡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刘文辉.传媒语境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7]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周哲良
I207.42
A
1672-2094(2016)04-0062-04
2016-05-01
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编号:1400210019)。
蒙冬英(1989-),女,广西钦州人,华侨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