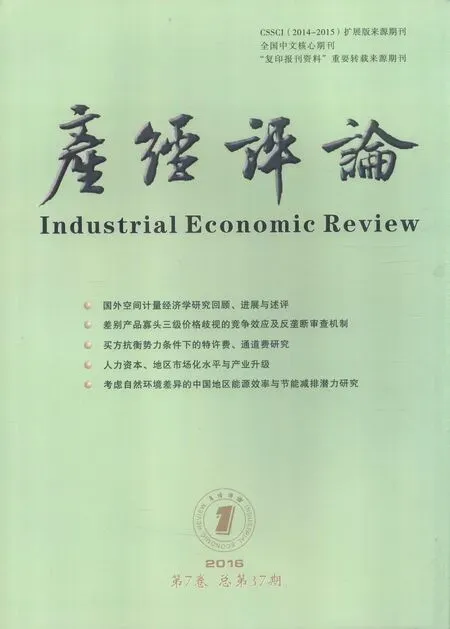腐败、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1997-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2016-04-13游士兵
游士兵 徐 涛
·国民经济·
腐败、投资与经济增长
——基于1997-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游士兵徐涛
[摘要]众多研究表明政府会通过多种途径对各类投资产生影响,包括政府公共支出效率、私人投资积极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和人力资本等。然而腐败是否通过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利用1997-2013年31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构建腐败、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的静态和动态模型,并运用GMM估计方法对动态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腐败通过降低企业投资积极性、削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效应。
[关键词]腐败; 投资; 经济增长
一引言
腐败问题一直备受学者、公众以及政府自身的关注,因为腐败无论是对宏观角度的投资、消费还是对微观角度的企业决策和企业成本都有深刻影响。腐败的经济学定义是指政府公职人员在未获取委托人授权的情况下利用公共权力在市场交易中谋取私利。腐败直接引起了市场上的寻租行为。根据微观经济理论,寻租行为导致市场失灵,降低了经济效率并使得资源配置偏离使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由于各方面的制度还不健全,监管不完善,腐败问题一般较为严重。根据透明国际最新公布的全球174个国家的清廉指数(2014),中国的得分为36分,在全球排名第100位。但近几年政府打击腐败的力度明显增大,每年检察院查处的贪污案件数量和人数,查处的县处级以上政府公职人员的数量都呈明显上升趋势。
腐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于腐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外文献大多关注腐败与经济增长和腐败与总投资之间的关系,结论则不一而论。Leff(1964)[1]认为腐败能从微观角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Mauro(1995)[2]的研究则表明腐败会降低经济增长效率。除此之外,国外的研究并没有指出腐败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而国内很多文献都探讨了腐败对各类投资的影响,包括政府公共支出的效率、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同时也有相关文献研究表明包括政府公共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在内的各类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国外的研究一般都针对市场机制完善、政治经济体制健全的国家。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政府掌握着大量资源以及分配资源的权力,腐败对经济增长和投资的影响和影响的程度会有所不同。因此,在中国,腐败是否通过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目前尚不明确,也就是“腐败—投资—经济增长”这一影响路径能否成立尚无定论。本文将沿着“腐败—投资—经济增长”的路径,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中国1997-2013年省级区域的腐败程度、地方投资以及经济增长面板数据,探讨分析企业投资规模是否是腐败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直观上,即分析腐败程度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显著。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是变量的选取与度量;第五部分是模型的设立与回归结果的分析;最后是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目前研究腐败与投资关系的文献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入手:一是研究腐败与政府公共投资的关系;二是研究腐败与对外直接投资(FDI)之间的关系;三是研究腐败对私人投资的影响。
(一)腐败与政府公共投资
国内目前有关腐败与公共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指出腐败对公共投资有负面影响。南旭光(2008)[3]构建了腐败、经济增长、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四个变量的联立方程组,该研究指出腐败虽然增加了公共投资的水平,但只有在低腐败的环境下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才是有效率的。杨飞虎(2011)[4]利用1980-2008年的数据构建了一个包含腐败程度、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他指出虽然在改革转型期,腐败能推动公共投资的增长和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腐败成为了公共投资增长的阻碍因素。谢地和丁肇勇(2003)[5]的研究也指出腐败不仅阻碍经济增长,而且对公共投资项目的决策、实施,对公共投资的效益和结构产生消极影响。
(二)腐败与对外直接投资
研究腐败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很多文献指出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高远(2010)[6]利用1988-2004年中国省级反腐信息和FDI的面板数据,证实了反击腐败力度的加大对FDI有相当的正面推动作用,靠打击腐败能有效地吸引FDI。程振源(2007)[7]根据世界106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腐败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二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随着打击腐败力度的增加,该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也会越大。但也有学者指出,当一国存在扭曲的激励制度时,腐败可能帮助外国投资者绕过本国设立的投资壁垒,腐败成为外国投资者的次优选择(胡兵等,2013)[8]。国外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Delgado等(2014)[9]建立了半参数模型研究腐败与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腐败对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有相当大的非线性作用,削弱外国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有效性和经济增长率,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减少腐败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也有学者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Okada和Samreth(2015)[10]利用130个国家1995-2008年的数据,研究表明如果只考虑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结论是不显著的;但是如果把腐败因素考虑进来,当腐败高于某个临界值时,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当腐败低于某个临界值时,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负面效应。
(三)腐败与私人投资
腐败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则比较复杂,有关认识还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腐败会抑制私人投资规模的扩大,主要表现为有关权力部门某些公职人员会特殊“照顾”行贿的企业,在进行决策时不会考虑到企业的未来发展能力和经济效益。这种特殊“照顾”一方面使经济效益不好、濒临破产的企业得以继续在市场上存活;另一方面,企业为了向有关权力部门某些公职人员行贿,不得不把部分利润让渡给这些公职人员,企业的正当合法利润受到剥夺,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会受挫,继而减缓投资的速度和规模(Svensson,2005)[11]。从另一个角度看,腐败和贿赂会增加企业的投资成本,抑制企业投资的积极性(Shleifer和Vishny,1993)[12]。国内也有学者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陈屹立和邵同尧(2012)[13]利用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腐败对私人投资积极性的影响,结论表明尽管腐败不是影响投资的决定因素,但是腐败的负面影响还是显著的,而且负面影响甚至超过了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
在研究早期还存在另外一种相反的观点,即认为“腐败能促进私人投资的发展”。腐败可以克服官僚主义带来的低效率,从而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时间的机会成本(Leff,1964)[1]。从这种观点出发形成了排队模型(Lui,1985)[14]和拍卖模型(Beck和Maher,1986)[15]。在排队模型中,众多企业在向政府获取审批时参与排队,每个排队者都有自己的时间成本,为了尽快获得政府审批,时间成本高的排队者愿意贿赂有关权力部门某些官员,时间成本越高的排队者贿赂有关权力部门某些官员的数额越大。这些官员会根据向自身行贿数额的大小,优先审批行贿数额大的排队者,这就相对降低了排队者的时间成本。拍卖模型认为政府掌握着审批这种市场资源,企业向有关权力部门某些官员行贿过程类似于拍卖,企业行贿的金额就是企业对审批这种资源的出价,有关权力部门某些官员最终把审批给出价最高的人。与一般拍卖不同的是,行贿拍卖是一种不公开的拍卖。但排队模型和拍卖模型本身也存在问题,受到了学者的质疑。除此之外,也有实证研究证明了腐败和投资之间的正向关系。Rock和Bonnett(2004)[16]利用中国、韩国等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其结论表明较高程度的腐败往往伴随着高增长和高投资。国内也有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经济发展与腐败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倪星等,2014)[17],即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遏制腐败。
已有研究显示腐败对投资的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腐败对包括政府公共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和私人投资在内的各类投资都有负面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腐败导致的寻租行为,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主动或者被动向政府行贿,行贿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降低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是另一方面,存在不少研究表明腐败对投资有正面效应。以私人投资为例,从排队模型和拍卖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向政府行贿可以降低单个企业在等待行政审批时的时间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企业投资。
关于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研究也主要从政府公共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出发。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18]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验证政府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的公共支出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效应。Borensztein等(1998)[19]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推动新技术的引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并利用6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证实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有重要贡献。
但是目前较少文献研究腐败通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也没有定论。本文基于投资角度,从理论和实证方面研究腐败如何通过影响投资来影响经济增长。
三理论分析
腐败程度影响企业投资的收益和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规模。有关权力部门某些公职人员存在腐败,企业就有向其行贿的动机和可能性,行贿的金额形成了企业的成本。但企业向有关权力部门某些公职人员行贿的同时也能获得相应的收益。政府掌握着部分市场资源分配的权力,腐败使得一些公职人员不会按照公平的市场竞争给予企业资源,而是根据企业是否行贿以及行贿额的多少来分配市场资源。行贿获得的市场资源就构成了政府腐败对企业投资的收益。从以上的分析来看,腐败对投资活动应存在着影响。下面构建具体模型探讨腐败、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模型
基于内生增长模型,本文假定经济体中只存在厂商和家庭。厂商在竞争性要素市场雇佣劳动,并在竞争性产品市场出售其产品,厂商在市场上追求利润最大化;家庭向厂商提供其拥有的劳动和资本,并在给定的预算约束条件下使自身效用最大化。具体模型如下:
1.厂商
厂商生产投入的要素为资本和劳动,并且假定其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因而t期的产出为:
(1)
其中,Y表示产出,K和L分别表示厂商投入的资本和雇佣的劳动。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资本是受腐败因素影响的资本投入量,也就是K满足如下关系:
(2)

产出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分配,每期的资本折旧为δ,因而t+1期的资本存量为:
Kt+1=Kt+Yt-Ct-δKt
(3)
根据一阶条件,可得t期厂商对劳动和资本的需求分别为:
(4)
(5)
2.家庭
假定经济体中有无数个相同且无限期存在的家庭,每个代表性家庭的效用来自于消费和闲暇。代表性家庭在每个时刻选择消费水平和劳动供给水平,家庭的最优化问题是家庭如何选择最优的劳动和闲暇时间以获得最大化效用。家庭的效用期望可表述为如下形式:
(6)
其中ct表示消费,lt代表家庭对劳动的供给,β为贴现率。家庭的预算约束条件为:
ct+it≤wtlt+rtkt
(7)
上式左边表示家庭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选择,而右边则表示家庭的收入来源,一部分来源于劳动供给获得的工资收入,一部分来源于投资获得的利息收入。
(二)模型求解
在竞争性市场中,家庭和厂商以及市场满足以下条件:
a.对家庭而言,在给定预算约束后,家庭通过选择劳动和闲暇时间的分配以获得最大效用;
b.对厂商而言,追求最大化利润;
c.市场出清,即有Ct+It=Yt。
为求得上述模型的均衡解,我们建立如下的贝尔曼方程:
(8)
对此方程求关于资本和劳动的一阶条件可得:
(9)
(10)
(11)
对式(11)更新一期可得:
(12)

(13)
将式(12)代入式(10)可得:
(14)
当经济达到平衡状态时,可得到如下最优解:
(15)
(16)
c-kαl1-α+δkk=0
(17)
联立式(15)、式(16)和式(17)可得出均衡时的投资、消费以及劳动供给量。从长期来看,投资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把式(2)代入均衡解中就可以得到腐败因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如果腐败抑制了投资增长,那么将间接地抑制经济的长期增长,相反如果腐败促进了投资,那么也将间接地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四变量选取与度量
(一)腐败的度量(COR)
腐败程度是很难衡量的指标,因为很多腐败都有隐蔽性。一个腐败案件在没有被查处之前,公众是难以知晓的。对如何衡量腐败,目前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许多学者会根据研究需要而采用不同的方法。在跨国研究中,一般用清廉指数来衡量世界各国的腐败程度。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简称CPI)是由透明国际向各国商人、学者或者分析人员发放问卷调查,然后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来衡量该国腐败程度的指标。在实证研究中,倪星和原超(2014)[17]利用当年检察院立案查处的贪污腐败和渎职人员人数除以政府公职人员的数量来衡量腐败程度。除此之外还有学者用其他指标衡量腐败程度。唐朱昌等(2014)[20]则是用检察院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数除以当地的总人口数。Goel和Rich(1989)[21]则是直接利用当地法院判处的渎职犯罪人数衡量一个地区的腐败。王传利(2001)[22]通过测度腐败频度来衡量腐败,他在研究中引入了“腐败黑数”的概念。
本文度量腐败的方法与倪星和原超(2014)[17]研究中采用的方法类似,利用检察院立案查处的贪污腐败和渎职案件数除以该省的公职人员人数,具体表示为每万公职人员中发生的贪污腐败和渎职案件数。

图1 中国渎职案件数和清廉指数(左图)与二者之比(右图)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一指标一直存在着争议:有学者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政府对腐败的打击程度(倪星和王立京,2003)[23]。查处的贪污腐败和渎职案件数与当地政府打击腐败的力度有密切关系。政府打击腐败的力度越大,查处的渎职案件数会增加。本文认为这一指标在我国更多地反映的还是腐败的程度。从图1中检查机关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数与透明国际公布的中国清廉指数来看,用清廉指数衡量的中国腐败程度与职务犯罪案件数是成反比的(中国清廉指数来源于透明国际)。
各省贪污人数及职务犯罪案件数原始数据从《中国检查年鉴》和各省人民检察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中获取;政府公职人员人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部分省份在部分年份只公布了职务犯罪的人数,本文根据当年全国的职务犯罪案件数与人数之比进行推算。
(二)经济增长和投资的度量(Inv)
本文用各省实际GDP增长率衡量经济增长,用各省实际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衡量投资增长率的指标。由于原始数据为名义量,本文用GDP指数对各省名义GDP进行调整,用各省的固定资产平减指数对新增固定资产进行平减,以1996年为基期。投资增长率和腐败程度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相关原始数据从《中国统计年鉴》上获取*西藏和部分省份较早年份的固定资产平减指数缺失,本文用当年全国的指数替代。。
(三)控制变量
本文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列入控制变量。这些因素包括各省公共支出增长率(PE),各省劳动人口增长率(WF)以及各省的开放程度(OPN)。

表1 变量统计性描述
政府公共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目前尚存在争议。刘勇政和冯海波(2011)[24]的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支出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然而Grier和Tulloek(1989)[25]的经验分析表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对GDP的增长有负面效应,但投资性支出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环境,因此对经济增长有利。庄子银和邹薇(2003)[26]利用国内数据同样也发现当政府公共支出存在很大的调整成本时,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是负向关系。根据已有研究,本文把政府公共支出作为模型的一个控制变量。劳动力是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数量上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同时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或者对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也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把劳动力增长率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经济开放度衡量了一个地区经济对外的开放程度,不少研究都表明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越高,对经济的增长作用越明显。范良(2005)[27]利用1982-2004年的数据论证了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尤其是商品和贸易的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采用和国内多数学者相同的方法,利用一个地区进出口总额与该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来衡量地区经济开放度,比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的开放程度越高。以上所有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五模型构建与回归结果
首先建立腐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静态模型。考虑到经济增长可能具有滞后性,下文进一步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深入分析腐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估计模型中的参数。
(一)静态模型
1.模型设定
根据数据特征和研究的需要,构建面板数据模型以分析腐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设立如下:
yit=α+β1Invit+β2Invit×Corit+β3Xit+vi+εit
(18)
其中,yit代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Invit代表各省投资的增长率,以每年各省固定资产投资表示;Corit代表腐败程度;Invit×Corit代表腐败通过影响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子;α代表常数项;Xit为控制变量,包括各省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PE),各省进出口增长率(NE),各省劳动力人口增长率(WF);vi是第i个省的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i代表省份(其中i=1,2,3,…,31),t代表时间(其中t=1997,1998,…,2013)。
2.回归结果
本文对静态模型的检验步骤如下:(1)采用Wald检验来检验模型的组间异方差;(2)采用Wooldridge检验来检验模型的组内自相关;(3)采用Pesaran’s CD检验是否存在横截面相关;(4)采用Hausman检验来检验数据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
Wald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存在很强的组间异方差; Wooldridge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存在组内自相关;Pesaran’s CD的横截面相关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存在横截面相关。Hausman检验的结果显示模型是固定效应。由于模型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本文采用Driscoll和Kraay(1998)[28]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修正,以保证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具体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2是使用Driscoll和Kraay(1998)[28]方法修正后的估计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10%和15%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2可以看出,在两种估计方法下,“投资增长率*腐败”的系数为负值且分别在5%和15%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腐败通过影响投资,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当政府掌握着市场资源以及资源的分配权时,如果政府存在腐败而且政府以企业向自身行贿数额的大小为依据来向企业分配资源,企业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需向政府行贿。企业向政府行贿付出成本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收益,从前面的理论分析中可以看出,行贿的成本和收益影响企业的投资规模。但从实证结果来看,这种影响效应是负的,企业行贿的成本大于收益,进而影响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抑制了企业的投资规模。
其他变量方面,投资增长率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预期相一致,投资增长能促进经济增长。两种估计方法的结果中劳动增长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劳动力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和开放程度在Driscoll和Kraay(1998)[28]的估计方法下并不显著,说明政府公共支出和开放程度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静态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和劳动力的增长。
(二)动态模型
1.模型设定
上述静态模型中的固定效应估计方法较好地解决了地区间的个体效应,Driscoll和Kraay(1998)[28]的修正方法使所得结论更加稳健。但相关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投资等经济活动具有滞后性或者惯性,也就是当期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当期的因素,同时也受前期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把自变量的滞后值放入模型,构建包含经济增长滞后变量的动态模型,以解决自变量所引发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建立如下动态模型:
yit=α+β1yit-1+β2Invit+β3Invit×Corit+β4Xit+vi+εit
(19)
其中yit表示人均GDP增长率,yit-1表示人均GDP增长率的滞后一期。
对于动态面板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法是不一致的,会导致动态面板偏差。因此,本文采用GMM估计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Arellano和Bond(1991)[29]在对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时,使用所有可能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这种方法称为差分GMM。其基本原理是对原模型进行一阶差分以消除个体效应,再用差分方程中的变量作为原变量的工具变量进行参数估计。但当变量具有很强的持续性时,差分项间的相关性很弱,差分GMM估计方法会导致弱工具变量问题,在极端情况下,差分GMM变得不适用。为解决上述问题,Arellano和Bond提出了水平GMM。Blundell和Bond(1998)[30]则将差分GMM与水平GMM结合在一起,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作为一个系统进行GMM估计。系统GMM方法能有效地克服模型中内生变量带来的估计偏差问题。相较于差分GMM,系统GMM的估计结果效率更高。对于GMM估计方法,有两个检验是必要的,一是扰动项的自相关性检验,另外一个是过度识别检验。
2.回归结果
本文分别用差分GMM和系统GMM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模型的具体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的模型参数估计值看,模型的扰动项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满足GMM估计方法的前提条件。Sargan过度识别检验值为1,所以我们强烈拒绝所有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原假设,即认为所有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整个模型满足GMM估计的条件,模型的估计结果是一致和无偏的。列(1)和列(2)是采用系统GMM方法估计的结果,列(3)和列(4)是采用差分GMM方法估计的结果。列(1)和列(3),仅把人均GDP增长率、投资及其滞后值和“投资增长率*腐败”作为解释变量,未加入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控制变量。列(2)和列(4)则加入了相关的控制变量,并且假定控制变量严格外生。
虽然差分GMM估计方法和系统GMM估计方法估计的腐败程度系数有差别,但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投资增长率*腐败”系数均为负数,与静态模型的估计结果一样,说明腐败通过投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

表3 动态模型估计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三)稳健性检验
虽然人均实际GDP从微观角度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状况,但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不仅与经济增长相关,而且还与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因素相关。然而腐败通过投资影响的是一个地区总体的经济增长状况。为了从宏观层面测度地区的经济增长,本文用地区实际GDP增长率替代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4 稳健性检验——以地区实际GDP增长率为因变量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从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应用Driscoll和Kraay的方法进行修正得到的稳健估计值,“投资增长率*腐败”的系数都是显著的(1%的显著水平),且符号与静态模型的估计结果一致。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从已有研究文献看,腐败对政府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都有影响,且研究结论多数倾向于这种影响是负面的。本文利用1997-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实证角度探讨了腐败、投资以及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静态模型本文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以及Driscoll和Kraay方法进行修正。对于动态模型,采用GMM的估计方法估计模型中的各参数。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也表明模型估计的参数是稳健的。
结果显示,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投资增长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明显趋向更高。但腐败通过降低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削弱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也就是说腐败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规模,更通过投资规模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这也说明投资是腐败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一个可能途径。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反击腐败有利于促进投资,进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这为当前政府的反腐工作提供了一个经济层面上的理论依据。
当然本文没有探讨腐败影响投资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一种可能的途径是由于政府掌握着大量市场资源的分配权,腐败引致投资者获取市场资源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寻租增加了投资者的投资成本,降低了投资的积极性。从经济角度出发,政府有必要限制市场上的寻租行为,但根本上,政府应以透明公开的方式分配市场资源,或者让市场决定资源的分配,从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参考文献]
[1] Leff, N. H..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Bureaucratic Corruption[J].TheAmericanBehavioralScientists, 1964, 8(3): 8-14.
[2] Mauro, P.. Corruption and Growth[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 1995, 110(3): 681 -712.
[3] 南旭光. 腐败对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 2008, (11): 19-24.
[4] 杨飞虎. 公共投资中的腐败问题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1980-2008年的实证分析[J]. 经济管理, 2011, (8): 162-169.
[5] 谢地, 丁肇勇. 公共投资、经济增长与腐败的相关问题研究[J]. 求是学刊, 2003, (1): 61-67.
[6] 高远. 反腐败与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的经验[J]. 南方经济, 2010, (2): 15-27.
[7] 程振源. 西方腐败经济学综述[J]. 国外社会科学, 2006, (5): 31-37.
[8] 胡兵, 邓富华, 张明. 东道国腐败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 (10): 138-148.
[9] Delgado, M. S., McCloud, N., Kumbhakar, S. C.. A Generalized Empirical Model of Corrup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J].JournalofMacroeconomics, 2014, 42: 298-316.
[10] Okada, K., Samreth, S.. How Does Corruption Influence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Economic Growth?[J].GlobalEconomicReview, 2015, 43(3): 207-220.
[11] Svensson, J.. Eight Questions about Corruption[J].JournalofPerspectives, 2005, 19(3): 19-42.
[12] Shleifer, A., Vishny, R. W.. Corruption[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 1993, 108(3): 599-617.
[13] 陈屹立, 邵同尧. 地方政府腐败会影响私人投资积极性吗?——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分析[J]. 南方经济, 2012, (2): 39-49.
[14] Lui, F. T.. An Equilibrium Queuing Model of Bribery[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 1985, 93(4): 760-781.
[15] Beck, P. J., Maher, M. W.. A Comparison of Bribery and Bidding in Thin Markets[J].EconomicsLetters, 1986, 20(1): 1-5.
[16] Rock, M. T., Bonnett, H..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Corruption: According for the East Asian Paradox in Empirical Studies of Corruption, Growth and Investment[J].WorldDevelopment, 2004, 32(6): 999-1017.
[17] 倪星, 原超. 经济发展、制度结构与腐败程度——基于2006-2010年G省2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4): 134-145.
[18] 郭庆旺, 贾俊雪. 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J]. 经济研究, 2006, (7): 29-40.
[19] Borensztein, E., De Gregorio, J., Lee, J. 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 1998, 45(1): 115-135.
[20] 唐朱昌, 霍明, 任品. 腐败会抑制市场化程度吗?——基于省际面板经验分析[J]. 南方经济, 2014, (4): 9-23.
[21] Goel, R. K., Rich, D. P.. On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for Taking Bribes[J].PublicChoice, 1989, 61(3): 269-275.
[22] 王传利. 1990年至1999年中国社会的腐败频度分析[J]. 政治学研究, 2001, (1): 38-56.
[23] 倪星, 王立京. 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J]. 江汉论坛, 2003, (10): 18-21.
[24] 刘勇政, 冯海波. 腐败、公共支出效率和长期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11, (10): 17-28.
[25] Grier, K. B., Tullock, G.. An Empirical-analysis of Cross-national Economic-growth, 1951-80[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 1989, 24(2): 259-276.
[26] 庄子银, 邹薇. 公共支出能否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验分析[J]. 管理世界, 2003, (7): 4-12.
[27] 范良. 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基于VAR方法对中国的实证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05, (11): 15-22.
[28] Driscoll, J. C., Kraay, A. C.. 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with Spatially Dependent Panel Data[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 1998, 80(4): 549-560.
[29] Arellano, M., Bond, S..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J].ReviewofEconomicStudies, 1991, 58: 277-298.
[30] Blundell, R., Bond, S.. Initial Condition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ofEconometrics, 1998, 87(1): 115-143.
[责任编辑:伍业锋]
[DOI]10.14007/j.cnki.cjpl.2016.01.011
[引用方式]游士兵, 徐涛. 腐败、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1997-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 产经评论, 2016, 7(1): 136-146.
Corruptio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7 to 2013
YOU Shi-bingXU Tao
Abstract:Many literatur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government has an impact on investment, including government efficiency in public spending, private investment enthusiasm, scale and human capital. On the other hand, some studies show that inve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Hence, does corruption have an impact on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investment? This paper, by using 1997-2013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constructs static and dynamic models between the corruptio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GMM estimation method is used to estimate the parameters in dynamic model. Conclusion implies that inve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corruption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investment.
Key words:corruption; investment scale; economic growth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298(2016)01-0136-11
[作者简介]游士兵,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徐涛,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国民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民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5-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