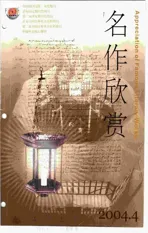批评作为精神实践
2016-04-13广东丨唐诗人
广东丨唐诗人
批评作为精神实践
广东丨唐诗人

唐诗人
很早的时候,我被人冠以“愤青”的名头,因为我的文章总是激愤,有所指、有所讽。可我慢慢感觉到,他们说的“愤青”与我关系并不大。网络上的愤青,普遍是情绪发泄、人云亦云,都有着强大的“网民”作为后盾,而我却是“孤胆英雄”。感觉蛮好,其实也不过是自我意淫。于是,我不再写杂文,甚至把它们全都删掉。我一头埋进了书斋。
可我于心不甘啊。在书斋里,我喜欢的是先锋文学,读的多是尼采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物的著作。阿多诺和德里达等人把我折磨得不行,可依然令我如痴如醉。这种充满强力性质的阅读,更加强化了我的反抗基因。然而,我又发现,操着这些意志之刀,我要刺向哪里?该怎么刺?有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有满腹的意志,面对的却是无物之阵。
于是,我重新拾起批评写作,但不直接行刺,而是用文学来刺。文学作品比单纯的意志刺得更好、更准,甚至刺得温柔美丽。我努力寻找当下还在刺着时代的作品,发现它们的利刃所在。
然而,当我想这么做的时候,却发现人们的批评兴趣早已从有所刺的状态中转移。他们戴着技术的帽子,不是刺向时代,而是冷静地扼杀着文学和批评写作自身的激情。他们欣赏温情节制的文学,主张理性规矩的批评。他们说批评介入时代,是对文学自足性的破坏,不可取。是的,我承认。可放弃介入的批评,它还有什么价值?沉浸于文本内部的规则考究,就为雕刻一类完美的作品?叙事上最具智慧的博尔赫斯都说,技术上完美的作品其实脆弱不堪,只有作品中伟大的灵魂才永垂不朽。不巧,我们的文学,却沉浸于追求完美,博大情怀和深广的批判,失却得一塌糊涂。
我知道,激情往往携带着某种乌托邦,还可能潜藏着血性,介入的批评很可能成为控制的力量。但有此历史教训也就表明,今天的介入要规避过去的样式。面对柔性而强大的消费体系和刚性的规约体制,介入的批评要在反思中展开,要寻找适合这个时代的有效的行刺方式。
这个时代,介入的批评是在文本、时代、自我与灵魂之间寻找平衡的支点。当美学文本擎起了乌托邦的时候,评论就要指出乌托邦进入社会现实时的希望与虚妄;当时代体制遏制了文学的自律时,评论则要强调文学自身的根本性指向;而当文学放弃时代指向、龟缩在文字游戏中时,批评就得唤起文化人的社会情怀;当一个时代的自由受到侵蚀、人心在沦陷时,批评更需要通过文学来发现人的灵魂,树立起自由和良知的价值。
或许,这是一种否定式批评,寻找差异或歧见,抵抗普遍化的符号统治,发现异质性力量,反抗媚俗与平庸。但这更是一种肯定式的精神实践:重申文学的价值和坚信良知的可贵。
作 者: 唐诗人,中山大学现当代文学方向在读博士研究生。曾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小说评论》《文艺评论》《山花》《文学报》《南方都市报》等刊物发表各类文章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