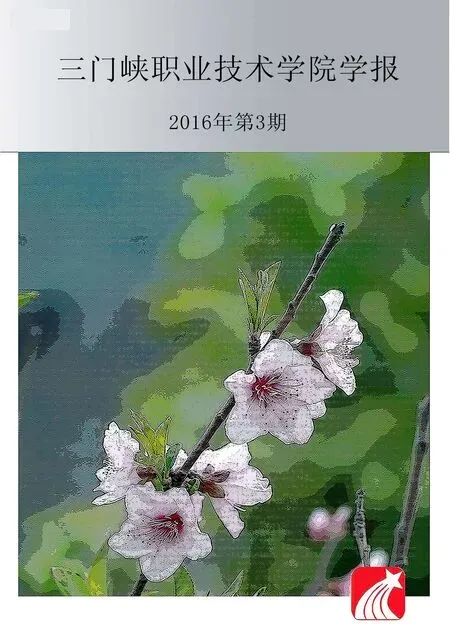古字新用
——对“六书”运用的研究
2016-04-12高正
◎高正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古字新用
——对“六书”运用的研究
◎高正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随着近些年人们交流信息的工具和交流平台日益的多样化,网络词语也随之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其中一些原本不为人知的生僻古汉字成为网络交流平台的“常客”,如最常见的“囧”、“槑”等字。这些字本是一些生冷已久的古汉字,但近来网民对这些犹如火星文的“怪字”推崇备至。从“六书”的角度对这些古字新用现象进行分类的同时,对它们意义的产生原因进行了研究,借此追溯这些网络汉字新意义的产生与传统造字法的传承关系。
六书;古字;网络用字
传统的汉字构造分析的方法就是所谓“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到了汉代,有三家解释六书,一是班固(《汉书·艺文志》),二是郑玄(注《周礼》引郑众语),三是许慎(《说文解字·叙》)。许慎不但阐释最详,而且也是第一个使用六书理论全面分析汉字结构的人,《说文解字》遂成为汉字形义分析的开山之作,许慎也被尊为小学大师。[1]三家之中,以许慎的说法最为详备,他在《说文·叙》中分别给六书下了定义,并举了例字。这是最早关于汉字结构的系统理论。此外,他又提出“亦声”“省形”“省声”“多形”“多声”等,[2]可以看作是对六书理论的补充。清代戴震把“六书”分为两类: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者为字之“体”;转注、假借二者为字之“用”。[3]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提到三书说,把汉字分成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三类。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认为这样的分类,眉目清楚,合乎逻辑,比六书说要好得多[2]。“六书”理论的随着汉字的发展演变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以解读汉字发展出现的新问题。近年来网络信息交流的普及使得汉字发展出现了“古字新用”的现象,这对“六书”的继承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古字新用”现象是指在网络上流行的日常不常使用的古汉字、生僻字,涉及的汉字部分被《康熙字典》收录外,还有部分是其没有收录的汉字。有些是古字又开始使用,意义并没有太大改变;但有些是古字“翻新”后,在网络交流中再创造后被赋予新的含义,如囧、烎、槑、兲、嘂、煋、靐、砳、嘦、嫑、玊、孖和圐圙等。笔者拟从前人的“六书”理论对这些古字新用现象进行分类,同时对它们意义的产生原因进行分类。从“六书”的角度来分析古字新义可以看出,这些网络汉字的结构与其使用意义产生的原因是有紧密联系的。
一、古字新用字的分类
从大量文献资料可以推测出古人并不是先有“六书”才造汉字。因为在商朝时汉字已经发展得相当有系统,但当时并未有关于六书的记载。“六书”是汉代以来的人把汉字分析后而归纳出来的系统。然而,自汉代有了“六书”系统以后,人们就都以之为依据造新字。就汉字的创造而言,汉字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前四书是孤立地分析每一个汉字得出的不同结构类型;后二书是揭示汉字发展使用的两种方式,即四体二用[4]。而随着汉字结构的演变由甲骨文到小篆、隶书、楷书,“六书”理论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三个元素:形、声、意。因此,这些网络上“复活”的古汉字也是网民以“六书”中的这三个要素为依据创新使用而形成的。综合现今网络流行的古汉字,大都具有象形、会意、形声的特点。
(一)具有象形特点的古字新用
“六书”中的象形是指字形摹写实物的形状,或用比较简单的线条来摹写事物的特征部分。《说文解字·叙》:“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5]古字新用中的象形与之有一定联系,人们为了特殊的需要会起用一些生僻字,也会根据“象形”即像字体本身的形态而与实际事物联系创造一些新义,以利于交流和文化传承。例如:
1.囧,“囧,〔俱永切〕,窻牖麗廔闓明。象形。凡囧之属皆囧。读若犷。贾侍中说:读与明同”。[6]“囧”字是骨刻文演变而来,古同“冏”。网民根据其字体形状,“八”像郁闷、尴尬、悲伤、无奈、困惑时向下垂的眉眼,“口”像一张嘴。因此“囧”被赋予处境困迫时的尴尬,为难。同“窘”一样表示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极为窘迫、尴尬的心情。这与“囧”字原意明亮的意思全然不同,网民因生活中的困境加上创新思维将其与字体外形联系,为它创造出一个新的意义,并引起大众共鸣而被广泛使用。
2.嘂,古文“叫”字。依《康熙字典》,【唐韵】古弔切【集韵】吉弔切,音噭。【说文】高声也,一曰大呼也。从,丩声。公羊传曰:昭公嘂然而哭。按今《公羊傳·昭二十五年》作噭而哭。又【尔雅·释乐】大埙谓之嘂。【疏】音大如叫呼声。【集韵】书作嘂[6]。网民根据其字形构造中的四个“口”字,将其联想成四张嘴同时叫,也就是大声叫,用以表现比“叫”字程度更深的情况。由此可见,“嘂”字自古就存在,意义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程度加深。
3.冇,是各地方言中用来表示“有”的反义词,因地区不同发音也有所不同,因字形与“有”相似,但当中少了两笔,被网友用来表示没有的意思。
网络流行的具有象形特点的新用的古字,因其字形特征而被网民创新使用,从字形角度与现实先联系,是对“六书”中“象形”造字法精髓的继承和创新。
(二)具有会意特点的古字新用
“六书”中的会意是指组合两个以上的字表示一个新的意义。《说文解字·叙》:“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5]而古字新用中的会意是这一理论的继承,因此这种情况的古字新用比较多,即用组合中的字的意义结合起来表示一个新的意义。六书会意有异体会意字(如:武)和同体会意字(如:从),古字新用中的汉字创新也有异体和同体之分。例如:
1.异体会意
(1)兲,古文“天”字。依《康熙字典》,【五音集韵】古文天字[7]。“兲”字结构由上“王”下“八”组成,因此网民将其自上而下连读为颇具暗讽特色的“王八”,但网络上依然使用着“兲”字的本义天的意思。
(2)烎,《康熙字典》里没有“烎”,只有一个与之相似的字,但上面的“开”是分开的两个“干”,原文为【集韵】夷针切,音淫。本作。詳字註。烎字原从幵作[7]。“烎”原义光明,将其自上而下读为“开火”,有一定宣战的意味。现在网民进一步引申,多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斗志昂扬、热血沸腾的精神状态,也可以用来表示惊讶的语气。可以看出网民已舍弃其原义而以其会意义代替。
(3)氼,古同“溺”,沉没;沉溺。《字汇·水部》“氼,与溺同。《字林撮要》:人在水上氽,人在水下氼,同。[7]这个字被网民自上而下解读为“水人”,在保留原本溺水意义同时,引申出会意义指专门“救火”的和事佬和什么都不懂的新人。
(4)炛,古同“光”。依《康熙字典》,【龙龛】同炚[7]。现也被网友分成“火”“化”两个字,表示这两个字组成的词语的意义,但此字用的相对较少。
(5)奣,天空晴朗无云。依《康熙字典》,【广韵】【集韵】乌猛切,音。【六书略】明也。一曰六合清明也。[7]现被网民用作“天明”,即天亮了的意思。
(6)勥,同“犟”。“迫也。从力强聲。古文从强。巨良切”[6]。顾名思义,将“勥”拆开,表达的其实就是强力,即某人某物强大,厉害的意思。
(7)圐圙,《汉语大字典》:“蒙古语指围起来的草场,多用于村镇名”。[8]网络义将两字的组成成分连读的,圐即“四”和“方”,圙即“面”和“八”连起来即是“四面八方”。
这些古字新用中的异体会意字大都是上下结构构成而进一步进行意义整合,由此而创新出新的符合交流需要的新意义。
2.同体会意
(1)槑,古同“梅”。依《康熙字典》:“【辰集中】【木字部】【玉篇】槑,古文梅字”。[7]但“槑”字由两个“呆”组成,“呆上加呆”。于是在网络语言里被用来形容人很呆,很傻,很天真。
(2)靐,原指雷声。《广韵·证韵》:“靐,靐靐,雷声也。”[7]现在被网友当做太雷了,比“雷”的程度更甚,惊讶到极点的意思。
(3)砳,象声词,石头撞击声。《玉篇·石部》:“砳,声。”《正字通·石部》:“砳,《六书略》:‘二石相击成声。’”[7]在网络上有时被作为“乐”的异体字使用。
以上四个例字,前两个同体会意意义所表程度随着组成部件个数而加深。后两个字则是组成部件作为同时出现的相同个体而产生的意义。
可以看出,具有会意字特点而产生新用法的古字,大都与其组成部件的意义有一定关系。古字新用的会意意义的产生在继承传统“六书”的基础上理解字义外,还使得这类古字的意义和用法呈现多样性,功能性也明显加强。
(三)具有形声特点的古字新用
形声,由形符和声符两部分组合成的字,其中形符表义,声符表音。《说文解字·叙》:“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古字新用中的形声是对其的发展,将古汉字的声符也赋予意义结合到整个字的意义中。如:
1.煋,《康熙字典》【集韵】桑经切,音星。火热也。【类篇】火烈也[7]。煋,“星”是声符,“火”是形符,而经网络“翻新”后,其声符也发挥其表意作用,把这个字当两个字用,一个火一个星,就是火星的意思。
2.恏,《康熙字典》引《张欣订正篇海》:“許皓切,音好。慾也。”[7]现网络取“好”字的音和“好心”的义,常用为“好”的通假字。
具有形声字特点的古字新用,在汲取传统“六书”理论中的“形声”造字特点的基础上,将声符的意义也整合进整体意义中,由此产生一个不同于本义的新的意义,是对传统造字法的追溯传承。
(四)兼具会意与形声特点的古字新用
古汉字还有一种切音造字法。它来源与商代的“合文”,即上古文字中,尤其是甲骨文中,合写在一起的两个字,如“组”就是“祖乙”两字的合文。后来“合文”逐步发展为“切音”造字法。这种造字法就是用两个字合起来拼出一字的读音,然后造出相应的汉字。如“诸”字,就是用“之”和“乎(于)”切音后造出来的。[9]裘锡圭先生也说:“汉字里还有少量不能纳入三书,合音字就是做偏旁的两个字反切而成的字。中古时代的佛教徒为了翻译梵音经咒,曾造过一些合音字,来表示汉语里所没有的音节,如(名养反)、(亭夜反)等。在现代使用的汉字里,表示“不用”的合音词“甭”……都既是会意字,又是合音字”。[2]如“朆”,从字音上看是“勿”和“曾”切音,字义是“不曾”,字形是“不”和“曾”合形。现今网络上最流行的两个这类字就是“嘦”和“嫑”。
1.嘦,《汉语大字典·口部》:“方言。连词,只要。”[8]从字音上看是“只”和“要”切音,网络字义是“只要”,字形是“只”和“要”合形。
2.嫑,《汉语大字典·女部》:“方言,不要。”[8]从字音上看是“不”和“要”切音,网络字义是“不要”,字形是“不”和“要”合形。
这类会意形声字既有会意的特点又有形声的特点。意义是由部件意义整合,读音这是两个部件前取声母后取韵,是传统“六书”理论为适应字形演变而发展出的新的理论。
从以上古、今汉字意义与字形的分析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古、今汉字意义之间具有明显的历史传承关系,即古字新的意义产生,是对传统造字法的继承、发展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二、古字新用现象的产生
我国古代对造字法有“六书”的提法,除了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还包括转注和假借。但严格说来这两种应属于用字的方法,是汉字意义多样化产生的原因,也是古字新用现象出现的原因。现在网络中流行中的汉字大都是古字的新用,意义大都偏离或决然无联系了。假借是一种不造字的造字法,只能是一个用字的过程,而非造字。因此,网络汉字特别是古字新用字是对假借用字法富有创意的发展,我们汉字的网络意义大多是假借产生的。
许慎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意思是说语言中的某一个词,本来没有替它造字,就依照它的声音假借一个同音字来寄托这个词的意义。假借字有两类:一类是本无其字的假借,另一类是本有其字的假借。古字新用不仅是在造字法对“六书”的继承与发展,在用字上也是承袭和创新,因此用字分为:
(一)本无其字的假借
在古代,某些词因原本并没有为它专门造字,人们就从现有的文字中选取某些同音字来记录。例如表示“没有谁,没有什么”意思的否定性代词,因原先没有为它专门造字,就借用与之同音的本义为昏暮的“莫”字来记录它。同样,在当今网络生活中,为了适应表情达意的需要,网民发挥创新思维,将想表达的意思赋予在一个可以“望文生义”的字上,这些古字大多假借为具会意和形声特点的新字,例如形声字“煋”,因其声符是“星”,而为适应信息交流需要经网络“翻新”后,把这个字当两个字用,一个火一个星,就是火星的意思。
(二)本有其字的假借
在古代,某些词已有为它专用的古字字形,但由于种种原因,另找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代替它。例如:早晚的“早”写成“蚤”。现在,处在信息交流平台上的网民并没使用本字,而是出于简省笔画,诙谐有趣的目的另找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代替它,这些字大多为具有形声特点的新字。古字新用的“恏”就是此类型:“恏”,现网络取“好”字的音和“好心”的义,常用为“好”的通假字。
(三)引申
依张桂光的《文字学简论》,字义的引申是语言中词义引申的反映,一般都与字形所体现的字面意义有关。[10]古字新用的“雷”和“靐”就是运用引申而产生的:“雷”,网友借日本动漫中的“受到强烈电波冲击”言语为“雷”,赋予雷“使人出人意料且令人格外震惊”的动词含义,这是从名词雷引申出来的。“靐”,网民则把它看成三个雷叠在一起,再结合网络汉字“雷”的“使人震惊”之义,那就是雷上加雷,太雷了,且用法也同“雷”。类似的字还有“槑”。
综上,古字新用的产生说明人们不仅对六书造字法进行了沿袭,而且传承了其用字方面的精华。当然,这也离不开人们对传统文化继承的积极态度,并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使古字也能与时俱进。
三、古字新用现象对汉字发展的影响
(一)古字新用现象是对六书造字法的继承和发展
综上可见,网民所用的网络汉字,特别是那些古字新用的网络汉字大多是继承六书的象形、会意、形声的原则进行能动再创造而产生其网络意义的。这与网民对于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是分不开的,与他们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是分不开的。一个个新的网络汉字的产生,一个个新的网络意义的出现,对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添砖加瓦、不断完善的过程。汉字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并辉煌灿烂,与这种海纳百川的气度是分不开的。况且语言和文字都有自我“扬弃”的能力,文字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系统,语言“约定俗成”的法则同样适用于文字,所以人们不必对源远流长、推陈出新的汉字发展过度担忧。
(二)古字新用现象对现代汉字的整理、规范和优化提出新的要求
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社会的发展给汉字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但事物的两面性使其也为现代汉字的优化整理带来了挑战。网络文化的不断发展要求以文字为载体的信息传递要具有多样化特点,但这导致一些不规范的汉字创造和使用,有些网民随意拆解和组合汉字来造新字,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大数目”“插播广告的最高境界”。因此,汉字规范既要继承传统、提倡创新,也要提高“规范汉字”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不仅提高网络信息交流的效率,适应计算机高速处理中文信息的需要,也要提高书面交际的效率。
从上文对古今汉字使用的传承关系分析中,我们应明确:无论是传统汉字造字法,还是网络用字对六书的创新使用,古字新用现象的对“六书”的发展,归根到底,都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大众的生活,都是来源于社会大众的实践。汉字使用的继承与发展只要是服从于社会发展需要,遵循科学可行的原则,人们就应该用包容万象的态度正确面对。这一点也是人们讨论汉字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
[1]韩伟.“六书”历史演变研究[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23-128.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戴震.答江慎修论小学书[C]//戴震.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黄天树.论汉字结构之新框架[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131-136.
[5]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8.
[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7]张玉书.康熙字典[K].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
[8]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K].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
[9]穆士虎.从“新造字”看汉字造字传承关系[J].铜陵学院学报,2009(3).
[10]张桂光.汉字学简论[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倪玲玲)
H122
A
1671-9123(2016)03-0102-05
2016-05-15
高正(1992-),女,山东枣庄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