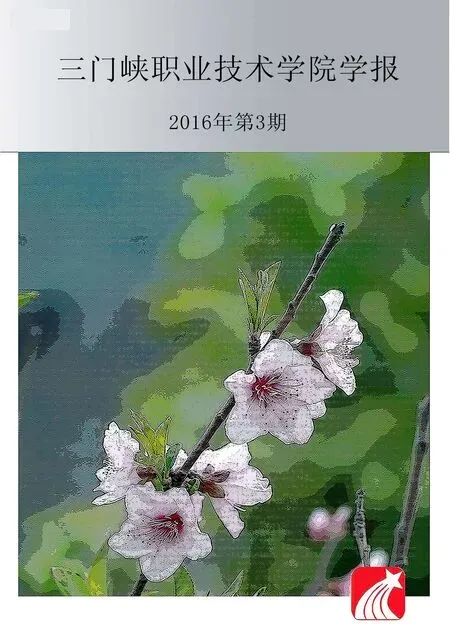穿越时空的心灵交汇
——前辈诗人对济慈颂诗意象审美特征的影响
2016-04-12张晓鹏金
◎张晓鹏金 燕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语系,河北 张家口 075000;2.河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400)
穿越时空的心灵交汇
——前辈诗人对济慈颂诗意象审美特征的影响
◎张晓鹏1金 燕2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语系,河北 张家口 075000;2.河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400)
约翰·济慈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颂诗以其鲜明的主题、令人陶醉的抒情、优美的格律形式和丰富的意象,被认为是其诗作中最重要和最成熟的部分。尤其是意象体现着丰富性、感性美和组合美的审美特征。对这些意象审美特征产生影响的除了浪漫主义思潮、济慈自身对美的追求和其丰富的想象力外,还有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这些前辈伟大诗人。
济慈;颂诗;意象;前辈诗人
约翰·济慈(1795—1821)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尽管他的生命只有25年零4个月,写作生涯也只持续了五年多一点,但是其诗作颇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在济慈所有的诗歌作品中,他的颂诗以其鲜明的主题、令人陶醉的抒情、优美的格律形式和丰富的意象而被认为是最重要和最成熟的部分。其中济慈颂诗中意象的丰富性又体现着丰富性、感性美和组合美的审美特征。影响这些审美特征形成的因素除了浪漫主义思潮、济慈自身对美的追求和其丰富的想象力外,还包括一些前辈诗人的积极影响作用。
英国著名的诗评家E·G·佩蒂特说过:“所有的年轻诗人,无论将来成就如何,最初的诗作都是模仿其所钦佩的诗人的作品。不同的是那些‘重要’的诗人能够从最初对范本的模仿中解脱出来,而那些‘次要’的诗人却永远不能超越模仿的阶段。”[1]纵观济慈的创作历程,其快速地跨越模仿阶段令人震惊。但是跨越模仿的阶段并不意味着济慈的诗作没有受到其他伟大作家的影响。许多伟大前辈作家的作品都滋养他的诗歌创作,影响着其颂诗意象的审美特征。而在这些前辈作家中,尤其以埃德蒙德·斯宾塞、威廉姆·莎士比亚以及约翰·弥尔顿为甚。
一、斯宾塞的影响
斯宾塞的《仙后》唤醒了济慈创作诗歌的天赋。济慈的挚友查尔斯·布朗(Charles Brown)曾经说过:“尽管生来就是一个诗人,但是他(济慈)直到18岁才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天赋,是《仙后》唤醒了他的这种天赋。他沉醉在斯宾塞的仙国里,在新的世界里呼吸,成为另外的一个人;直到倾心着那些诗行、尝试着去模仿,然后取得成功。”[2]
美国诺特丹大学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格雷格(Greg Kucich)在他的著作《济慈、雪莱和浪漫的斯宾塞主义》(Keats,Shelley,and Romantic Spenserianism)中讨论了斯宾塞对济慈的影响。他认为济慈的诗歌,尤其是早期诗歌受这位“伊丽莎白时代大师”的影响很深。济慈的第一首诗歌就是《模仿斯宾塞》(Imitation of Spenser)。而在济慈的颂诗中,斯宾塞也影响着其意象的选择和使用。如济慈在《心灵颂》和《夜莺颂》中对梦的意象的使用和描述。
Surely I dreamt today,or did I see
The winged Psyche with awakened eyes?
(Ode to Psyche,L5-6)
Was it a vision,or a waking dream?
Fled is that music……Do I wake or sleep?
(Ode to a Nightingale,L79-80)
根据著名的济慈研究家米利亚姆·阿洛特的研究,这些“梦”的意象正是受到了斯宾塞的诗歌《爱神》(Amoretti)的影响。
Was it a dreame,or did I see it playne,
A goodly table of pure yvory……
在《心灵颂》中,济慈用隐喻意象“长翅膀的男孩”(the winged boy)来描述丘比特,而这个意象来自斯宾塞的《仙后》,因为斯宾塞经常使用这个词组来修饰丘比特。“济慈在描写丘比特和赛姬时也许是记起了他 (斯宾塞)的描写 (K.may be remembering especially his (Spenser’s)use of it when describing Cupid and Psyche,The Faerie Queene III)”。[3]所以,在意象的选择和使用方面,斯宾塞影响了济慈颂诗意象的审美特征。
二、莎士比亚的影响
毫无疑问,莎士比亚是济慈最尊崇的诗人,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济慈在1817年4月15日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今天早晨用餐时,我觉得有些孤独,于是我开箱拿出了一本莎士比亚的书——此乃我之安慰也。”[4]两天后,在给雷诺兹的信中,济慈说:“我发现了一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莎士比亚的头像——他非常像乔治说起过的那样好,我非常喜欢他,把他挂在我的书的上方。”[5]
在《济慈与莎士比亚》一书中,莫瑞(John Middleton Murry)评论说:“莎士比亚影响的脉络是如此的接近济慈生命的中心,以至于我们用些许耐心就能看到这些影响已经渗入到他灵魂的最深处。”[5]莎士比亚不仅影响着济慈的诗歌理论、诗境及诗歌主题,而且在意象方面也影响着其诗歌创作。
如《忧郁颂》第三节:
Ay,in the very temple of Delight
Veiled Melancholy has her sovran shrine,
Though seen of none save him whose strenuous tongue
Can burst Joy’s grape against his palate fine;
(L25-28)
根据道格拉斯·布什(Douglas Bush)的研究,意象“the veiled Melancholy”who is“seen of none save him whose strenuous tongue can burst Joy’s grape against his palate fine”(被唯有咀嚼过欢乐之酸果味觉灵敏的人方才有缘看见的隐匿的忧郁)是效仿了莎士比亚的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
……What will it be
When that the wat’ry palates taste indeed
Love’s thrice-repured nectar?Death,I fear me;
Sounding destruction;or some joy too fine,
Too subtile-potent,tun’d too sharp in sweetness
For the capacity of my ruder powers……
在《忧郁颂》的最后两行中,“在白云碑上悬挂”(her cloudy trophies hung)的意象则来自莎士比亚的第三十一首十四行诗第十句:
Thou art the grave where buried love doth live,
Hung with the trophies of my lovers gone……
著名诗歌评论家米里亚姆·阿洛特(Miriam Allott),在《济慈诗歌全集》中对这两行作了注释:“济慈也许正想起了莎士比亚第31首十四行诗的第九句和第十句,因为在莎士比亚诗集中的这两行旁边,济慈标了边注‘巧妙的构思’(conceit)”。[3]其次,在济慈的颂诗中也可以找到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意象丛和意象组合的映射。在《夜莺颂》第五节中,济慈使用了花的意象丛,包括紫罗兰(violet)、麝香玫瑰(musk rose)、蔷薇(eglantine)等,使用了意象组合“夜的黑(darkness),芬芳(sweet)和荒野(wild)”。而这些意象丛和意象组合同样出现在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第二幕第一场249至254行。济慈从莎士比亚的花园里移植了鲜花,丰富着自己的诗园。无论是在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还是在济慈的《夜莺颂》中,这些意象、意象丛和意象组合都体现了相同的繁复性和组合美。
在《夜莺颂》的第三节中,同样可以找到来自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意象映射。在200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eats》一书中,苏珊·J·伍尔夫逊(Susan J.Wolfson)针对这一节评论道:“这总是使人想起莎士比亚的第73首十四行诗(This never forgets Shakespeare’s Sonnet 73.)在莎士比亚的第73首十四行诗中,一系列的隐喻意象‘in me behold……’,‘In me thou seest……’,and‘This thou perceivst’展现着济慈在这首诗中共有的心境 (reveal the shared mood that is but one of Keats’s moods in his poem)。”[6]而这种心境济慈也是通过一系列意象展现出来的:“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Where palsy shakes a few,sad,last gray hairs”,“Where youth grows pale,and spectre-thin,and dies”,“Where but to think is to be full of sorrow,And leaden-eyed despairs”,and“Where Beauty cannot keep her lustrous eyes,Or new Love pine at them beyond to-morrow”。无论是在《夜莺颂》中,还是在莎士比亚的第73首十四行诗中,都是用一系列的意象表现一个单一的情境,这正是意象繁复性的体现,由此可见,济慈颂诗的意象组合美特征受到了莎士比亚的影响。
另外,济慈的《秋颂》中也可以找到莎士比亚的影响。在《济慈与莎士比亚》一书中,约翰·莫瑞在涉及《秋颂》这首诗时评论道:“不难看出,这首完美的诗歌在丰富多彩的感觉情境上,在美丽宏达的场景方面深深地体现着莎士比亚的风格,像一幅令人窒息的画。”[5]莫瑞的评论显示《秋颂》中的意象所创设出的感性美是莎士比亚式的。
由此可见,在颂诗意象的选择、组合以及意象所创设的感性美方面,莎士比亚的作品给予了济慈很大的启发和灵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
三、弥尔顿的影响
约翰·弥尔顿这位伟大的新古典主义诗人对济慈的影响也是特别明显的。济慈将弥尔顿视作与莎士比亚一样的诗歌大师。在1819年8月14日济慈写给本杰明·贝利(Benjamin Bailey)的信中,他说:“我日甚一日地确信一个好作家(除了人性之友哲学家外)是世界上至真至纯的生灵—我越来越觉得莎士比亚和《失乐园》是了不起的奇观。”[4]
济慈在1819年8月24日写给雷诺兹的信中写道:“我日甚一日地坚信世界上顶尖之事除美行外便是美文,《失乐园》堪称更为伟大的奇观”。[4]米利亚姆·阿洛特在《济慈诗集》中评论说:“在济慈的诗歌探究中,弥尔顿是参照的标准”。[3]而当济慈读《失乐园》的时候,也认真地在书的空白处做了笔记。1819年3月19日,济慈在他的旅行日记中写道:“我反复地诵读弥尔顿的诗行,已经到了细细品味的状态,真是一种愉悦的感受。”[7]济慈对弥尔顿及其作品的爱与崇敬使他享受到了弥尔顿艺术之美,同时,在济慈的颂诗意象中,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弥尔顿影响的印记。如《心灵颂》:
O latest born and loveliest vision far
Of all Olympus’faded hierarchy!
Nor virgin-choir to make delicious moan
Upon the midnight hours
No voice,no lute,no pipe,no incense sweet
From chain-swung censer teeming;
No shrine,no globe,no oracle,no heat
Of pale-mouthed prophet dreaming.
(L24,25,30-35)
根据米利亚姆·阿洛特的研究,《心灵颂》第24、25及30至35行中出现的意象 “Olympus’faded hierarchy”,“no virgin-choir……”,“no voice……”,and“no shrine……”效仿自弥尔顿《圣诞颂》(The Nativity Ode)73至80行中的意象。
The Oracles are dumm,
No voice or hideous humm
Runs through the arched roof in words deceiving.
Apollo from his shrine
Can no more divine,
With hollow shriek the steep of Delphos leaving.
No nightly trance,or breathed spell,
Inspires the pale-ey’d Priest from the prophetic cell
(The Nativity Ode,L73-80)
约翰·莫瑞在《济慈研究》(Studies in Keats)一书中曾说:“济慈‘Olympus’faded hierarchy’意象的使用是因为他想起了弥尔顿在《圣诞颂歌》中古希腊众神在耶稣诞生日消失的描述。”[5]
除此之外,《夜莺颂》第33行“the viewless wings”的意象效仿了弥尔顿《热情》(Passion)中第50行的意象:“thence hurried on viewless wing”;而意象“divine melodious truth,Philosophic numbers smooth”效仿了弥尔顿《科马斯》(Comus)第467至第469中的意象:
How charming is divine Philosophy!
Not harsh,and crabbed as dull fools suppose,
But musical as is Apollo’s lute……
从以上的例证中可以看出,济慈颂诗中意象的选择、运用及其特点都受到了弥尔顿的影响。
济慈在创作中受到了这些前辈伟大诗人的影响,从他们的诗园中吸收着养分,但是济慈没有被他们的影响所禁锢而仅停留在模仿的层次上,而是超越了模仿,成为了一位拥有自己风格的伟大诗人。正如苏珊·J·沃尔夫逊在她所编纂的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eats中所评论的那样:“济慈已经拥有了他自己的郁郁葱葱。”
[1]E.G.Pettet,On the Poetry of Keats[M].London:The Syndics of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6.
[2]Sir Sidney Colvin,John Keats:His Life and Poetry,His Friends,Critics,and After-fame[M].New York: New York Scribner,1917:20.
[3]Miriam Allott,ed.,The Poems of John Keats[M].London:Longman Group,1970:516.
[4]济慈.济慈书信集[M].傅修延,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6.
[5]John Middleton Murry,Keats and Shakespeare:A Study of Keats’Poetic Life from 1816 to 1820[M]. London:Humphrey Mil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6:33.
[6]Susan J.Wolfso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eat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66.
[7]Elizabeth Coo,ed.,John Keats,The MajorWorks[M].New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0:464.
(责任编辑 倪玲玲)
I106.2
A
1671-9123(2016)03-0085-05
2016-07-22
张晓鹏(1976-),男,河北阳原人,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