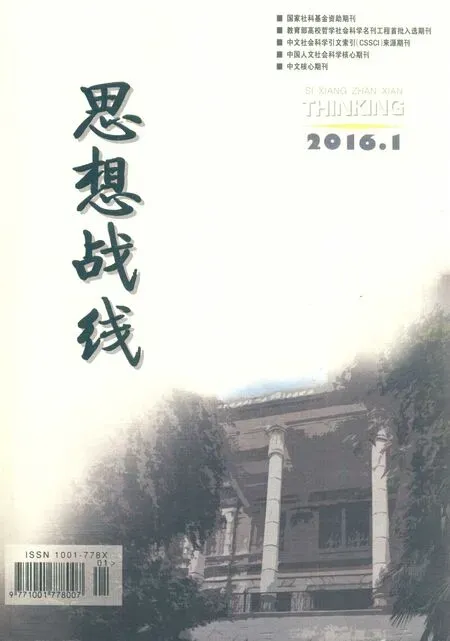“嵌入”的多重面向——发展主义的危机与回应
2016-04-11黄志辉
黄志辉
“嵌入”的多重面向
——发展主义的危机与回应
黄志辉①
摘要:在“跨越式发展”“参与式发展”等发展主义语境中,中国的乡村社会与民族地区出现了诸多发展主义的危机。这些危机均是以经济发展作为惟一目标而导致的“脱嵌”危机。而在当前构建巨型区域社会的发展战略下,亟须一种具有整合力的视野去回应这些“脱嵌”危机。由于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面向,能够涵盖空间、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嵌入式发展”模式,不仅能够规避诸如“跨越式发展”“参与式发展”的内在缺陷,而且能够良好地回应当代发展主义的危机。
关键词:“嵌入”;脱嵌;“嵌入式发展”;大转型;发展主义
一、引言:“嵌入”与发展议题
“嵌入”(embedment)概念源自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下称《大转型》)一书,该书5次提及“嵌入”,大意是指“市场经济是附属在社会体系之中的”。*[匈]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0页、第53页、第60页、第111页、第232页。在另外一篇名为《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之论文中,波兰尼又指出:“人类经济嵌入在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Karl Polanyi,“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in K.Polanyi and Harry Pearson(eds.),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Economics in History and Theory,Chicago:Henry Regnery Company,1957,pp.139~174.基于该观点,后来的许多学者围绕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频繁地引用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弗雷德·布洛克认为:“‘嵌入’是卡尔·波兰尼‘在社会思想上最重要的贡献。’”*弗雷德·布洛克为《巨变》2001英文版写的导论,参见[匈]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5页。此言不虚,但在笔者看来,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固然是“嵌入”理论的重要面向,但波兰尼赋予这一概念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笔者在本文中将展示 “嵌入”概念的多重面向,并依据“嵌入”理论的分析,回应当代中国发展议题中所蕴含的危机。
在《大转型》一书中,波兰尼提出的“嵌入”理论实际上是为了应对欧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发展危机。该书提出的首要问题是:为何贯穿19世纪的欧洲均衡发展体系,在进入20世纪初之后就被打破了?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原有的自由市场、自由政体、金本位制以及国际贸易体系四大要素无法继续维持世界秩序,*[匈]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6页。市场从社会中“脱嵌”出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从19世纪末以来,欧洲倡导的自由市场,导致了整个欧洲社会趋于崩溃、贫富阶级分化显著等问题。而在世界性范围内,由于自由政体与自由市场的扩张,使得殖民区域掀起了反殖民主义浪潮。不论是欧洲本土还是被殖民国家,贫困者、无产者濒于失去国家与社会的保护;同时,欧洲内部由于法西斯主义政治的崛起,使得自由政治的实践与整体社会结构之间也发生了“脱嵌”,等等。在这种背景下,波兰尼吁求一个能够实现全面整合的社会,将“社会”概念放置在分析的中心视野之中。
在最近十几年中,中国学界多次掀起了引用“嵌入”理论的热潮,每一波热潮都与当代中国的发展议题有关。尤其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或有关乡土中国的研究领域中,许多学者指陈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扩张过程如何造成了区域差异、城乡断裂、贫富分化等问题。例如,为了回应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王绍光、汪晖等人引用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分析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王绍光认为,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业、城乡差异以及社会保障失衡,都是由于盲目倡导自由市场而导致的,他用类似于波兰尼式的语调指出:“市场是必要的,但市场必须‘嵌入’在社会之中,国家必须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不能允许、也不可能出现一种‘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但是,王绍光一直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去继承波兰尼的理论,他所分析的发展议题充满了国家主义色彩,*王绍光:《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却忽略了“嵌入”理论中所蕴含的历史、空间以及社会整体面向。另一位学者汪晖也多次提及波兰尼的社会整体思想,试图呼应当代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脱嵌”问题。*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61页、第209页;汪晖《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载许宝强等《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页、第4~6页。不过,二位学者由于徘徊于批判自由主义市场与理论,未能兼顾“嵌入”理论的全部视野。
此外,许多中国学者结合当代发展议题去阐发波兰尼的理论。例如,为了应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产权纠纷,刘世定教授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阐发了“嵌入型关系合同”*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的分析策略;也有人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出发,指出“市场社会”与“市场性社会”的区别。*刘拥华:《市场社会还是市场性社会?——基于对波兰尼与诺斯争辩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但是,在笔者看来,从制度经济学理解的“嵌入”概念,继承的是格兰诺维特而非波兰尼的“嵌入”理论。格氏认为:“经济行动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Mark Granover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1,no.3,1985,pp.481~510.这一点与波兰尼所说的“经济系统嵌入在社会实体之中”有着天壤之别。前者将“经济行动”看做是与社会网络有关的行动类型,而后者从根本上就将“经济”看做是社会的特殊功能。有研究曾经指出,格氏的“嵌入”概念只是对经济学的市场分析进行修修补补,远不及波兰尼的内涵丰富。*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在本文中笔者将详细指出制度经济学如何简化了波兰尼的“嵌入”理论。而在经济人类学领域,不少学者强调波兰尼“嵌入”理论的重要性,认为,在分析少数民族经济变迁与社会转型时,要充分注意社会文化系统为经济发展赋予的规范性意义,倡导将“社会”或“文化”置于更为关键的位置,从而将经济发展议题转化成为一个社会、文化分析议题。*参见陈庆德等《中国民族村寨经济转型的特征与动力》,《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陈庆德《民族经济的理论溯源》,《民族研究》2009年第5期;施琳《经济人类学理论前沿综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黄志辉《无相支配——代耕农及其底层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此外,“嵌入”理论还与当代中国政府的总体发展战略密切相关。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到:“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政治局: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26/c_1110866377.htm。这是中共中央从民族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首次将“嵌入”概念纳入到民族社会治理的政治议题中来。与此同时,当前提出的有关“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蓝图,实际上是一个超越族群、民族、国家,“嵌入”了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巨型区域社会构想,这将重铸多样性的文明。而“嵌入”理论将有助于重新观察“一带一路”的历史与现实。
综上,依据“嵌入”概念所阐发的分析路径,均与当代中国的发展议题密切相关。然而问题是:为何要用“嵌入”分析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与危机?当下中国又面临了哪些发展主义危机?这些危机与“嵌入”概念的内涵是否一一对应?除经济面向之外,“嵌入”概念的内涵中还有哪些面向?当下倡导的“嵌入式发展”与以往的“跨越式发展”“参与式发展”等相比,又有哪些不同?这些问题只有在阐述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语境及危机,并全面描述了“嵌入”概念的多重面向之后,才能得到清晰的回应。
二、从“跨越式”到“嵌入式”:发展语境中的“脱嵌”危机
改革开放在取得瞩目成绩的同时,其发展过程中也酝酿了大量的“脱嵌”危机。为了应对这种“脱嵌”或“断裂”的发展危机,学界与政府试图通过阐释“嵌入”“再嵌”等概念,以求发现如何重建社会的方案。笔者认为,市场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危机与具体的发展语境密切关联。
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乡村或民族地区经历了数种发展话语的洗礼:即从“跨越式发展”“参与式发展”向当前的“嵌入式发展”模式的演变。但所谓“跨越式发展”或“参与式发展”,*参见牟本理《论我国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周大鸣等《参与发展:当代人类学对“他者”的关怀》,《民族研究》2003 年第5 期。都是以“中心—边缘”“落后—先进”“主导—引导”等作为认识框架的,有意无意地将对发展对象的分析塞入进化论的图式之中展开论述,*郭占峰:《走出参与式发展的“表象”》,《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且其轴心问题依然是经济的增长。虽然在“跨越式发展”或“参与式发展”之中,仍然会强调社会的重要性和文化的相对性,但以经济增量为向标的工业、市场实践,会将重建社会的倡导或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引向虚无。诸多讨论的最终目的,仍是将发展议题引向如何提高经济增量这一主题。因此,各种发展方案在面对工业和市场时,一方面将其视作手段,另一方面又视作目的,而不惜以毁灭自然环境、社会系统为代价。这样一来,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社会之间出现了一道裂痕。面对经济目的论,社会实体论、文化相对论在其中只是一个摆设,至多将文化习俗或社会关系转化为一种经济资本,纯粹变成了经济增量的来源。例如,在许多实证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在形式上尊奉布迪厄的资本分类方式,将文化或社会网络视为可以和政治、经济力量相交换的“资本”,从而泯灭了文化、社会的总体性意义。原本作为生活目的的社会文化总体事实,在跨越式、参与式的发展话语中,也被悄悄地转换成了诸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生存手段。此外,在一定的时期之内,政治实践的成功与否,主要也是以经济增量的指标作为衡量标准的,这使得国家政治与市场、工业保持更为暧昧的关系,从而使政治与社会系统之间出现了某种裂痕或“脱嵌”,政治代表性危机亦由此而生。
具体来说,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之中,以经济开发为主要发展内容的市场化、工业化进程,导致了以下三点“脱嵌”危机。相应的,也产生了三点重新“嵌入”的需求。
第一是社会的原子化危机。面对当代工业与市场的冲击,中国民族地区和乡土社会呈现出“原子化”裂变的倾向。*Helen F.Siu,Agent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乡村社会被市场、工业分解成许多亚群体或流散的个体,民族地区人口大范围流动(但在目前情境下,也有一些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等却减少了流动频次,*马戎:《中国人口跨地域流动及其对族际交往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6期。在某种意义上,同样造成了这些民族与其他民族、族群的隔离效应),同时出现了生活水平、经济收入上的分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整合能力下降。族群与族群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族群或阶层内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系纽带正在弱化。同时,由于利益、资源成为人们行动的核心导向,但主导利益、资源的公平竞争法则又未完全建立起来,群与群、个人与个人之间因此出现了频繁的冲突。原子化的趋势或个体主义的兴起,并不利于现代国家的建设和整体认同的塑造。因此,在政治或社会层面,要解决这一困境,就需要将各“原子”重新“嵌入”进一个统一的社会整体,而不论“嵌入”的黏合剂是公民身份、阶级成员还是夷夏传统。
第二是文化的断裂危机。30多年来,不论是儒、释、道、法和其他古典文化传统,还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传统,都面临市场经济或现代发展话语的冲刷。波兰尼的“嵌入”概念,其核心意义本来是指市场经济嵌入在社会文化体系之中的。但在发展主义的语境里,市场经济似乎已成为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独立发展方案。例如,新的消费主义正在取代传统的文化法则,重组多民族国家的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将此称为“生活世界殖民化”或“公共文化领域转型的危机”。*参见[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这样一来,后果便是传统文化体系的没落与终结,但新兴的消费文化、工业文化又无法维系整个社会体系的需求与运转,从而导致文化与社会的断裂。因此,急需类似甘阳教授所说的“通三统”*参见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或打通多个传统的视野,在文化领域将夷夏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现代文化嵌合起来。
第三是政治的“脱嵌”危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强势倒逼之下,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政治,在普罗大众的认识论层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危机,中国的乡村自治也因为社会本身碎片化导致了代表性的危机。*吴重庆:《“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在历史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民族政治体制,由于“去政治化”的呼声渐起,导致有关政治与新兴的社会文化模式之间出现了诸多“脱嵌”的讨论。此外,在就业机会、教育资源以及利益再分配等领域,一方面,由于确实存在诸如贪腐、庇护等不正当的政治实践,导致了人们的不满;另一方面,由于民族或族群之间存在制度上的分配差异,从而使部分人质疑当下民族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的合理性。因此,如何推动民族或族群、乡村与城市之间产生良性互动,并让政治治理与社会秩序之间实现良性嵌合,是当前政治治理的关键。
上述三种“脱嵌”危机,均无法通过坚持某种“跨越式”或“参与式”发展模式而得到解决,解决危机的关键,在于将对社会文化体系的重视提升到最为核心的位置上去,并重新审视这一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嵌合关系,鼓励“嵌入式”的发展路径。而所谓“嵌入式发展”,在笔者看来,是一种重视社会文化整体的发展模式,力图排除“跨越式发展”中的经济中心向度或“参与式发展”中的政治中心向度。在社会文化系统的内在视野之基础上,将一切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发展方式转而嵌入于社会文化的整体规范系统之中。相比“跨越式发展”或“参与式发展”两种模式,“嵌入式发展”模式试图排除进化论、经济中心主义或政治主导倾向,采取一种无中心或互为中心的发展路径。这种路径提倡社会的互动式发展,对任何霸权行径的发展主义都采取批判态度。
但是,笔者并非要贸然推崇这样一种发展模式,而是试图在“嵌入”概念的热潮之下,理性分析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获取这一概念的理论精髓。“跨越式发展”和“参与式发展”的关键问题,就是没有对“跨越”和“参与”等概念进行理性的学术分析,从而冒失地陷入了“发达—落后”“现代—传统”“主导—引导”“主位—客位”的窠臼与困境之中,最终导致对这两种模式的盲从。因此,提倡“嵌入式发展”,需要清理“嵌入”概念的真正内涵,规避任何发展模式的非理性狂热。接下来,我们将首先从这一概念产生的理论谱系之中,浮现其具体面向,然后再来回应当代中国的发展主义危机。
三、“嵌入”的多重面向及其理论谱系
波兰尼的“嵌入”理论是在应对欧洲的多重发展危机时发现的,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仅仅指向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而是存在诸多的面向。制度经济学、经济社会学以及经济人类学等研究领域,在提及波兰尼的“嵌入”理论时,都未曾系统梳理过波兰尼如何赋予这一概念以丰富的内涵。“嵌入”等相关概念之所以能够回应当代中国的多重发展危机,并可以用“嵌入式发展”替代“跨越式发展”和“参与式发展”,正是因为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嵌入”理论承上启下,连接了许多人类学的经典研究。因此,梳理这一概念的理论谱系,不仅可以获得一个分析现实发展议题的理论工具,同时,也可以呈现许多经典研究与“嵌入”理论之间的继承关系。
(一)朴素的隐喻:“嵌入”的空间面向
根据布洛克的观察,波兰尼很可能首先是从空间的隐喻中去阐发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的:“波兰尼借用了来自采煤业的隐喻……采矿的任务就是把嵌入矿井石壁中的煤炭分离出来。”*[匈]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页。而将煤炭分离之前,作为总体的矿床的自然状态,是各种矿质交融的状态,并互相给养、生长。因此,从空间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嵌入”既属于一种物理现象内含于另一种物理现象中的状态,又属于一种物理现象与其他物理现象交互生成的过程——“共生性”与“交互性”是空间“嵌入”的两个特征。
“嵌入”的空间面向中蕴含的上述两个特征,极其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社会分布格局。中华各民族的“嵌入式”分布,其特征是指各民族之间的共生关系与交互影响。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概念时,也不断强调民族之间如何共生与交互。*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在笔者看来,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5月指出的“嵌入的民族关系”,也指向民族之间的共生关系与交互发展。
在当前的发展情境下,大量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的广泛流动,从而构成各式各样的社群在城镇、工业区域的聚集现象,同样是一种空间“嵌入”的表现。但是要注意的是,仅仅是以民族、族群为单位的空间散杂分布,并不能定义为“嵌入式”的分布类型——真正的“嵌入式分布”,是民族、社群单位之间能够实现往来互动,社群、阶层之间能够实现平行或上下流动,并进行有效的交互渗透,才符合空间互嵌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必须同时满足共生与交互两个条件,才可称为“嵌入式分布”。
(二)“嵌入”的总体面向:作为实质性整体的社会文化系统
“空间”仅仅是“嵌入”最为朴素的面向。在“嵌入”的空间隐喻中,我们应该追问,作为总体的“矿床”指向何物?也就是说,要“嵌入”的总体是什么?波兰尼继承了“实体论”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一切政治、经济都是“嵌入”在作为总体的社会文化体系之中的,尤其是经济的运转,需要遵循社会自身的法则。与蔡雅诺夫一样,波兰尼一开始就拒绝了单一性的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他认为,一切经济都应该是社会的经济,而社会自身是具有差异性的,因此,经济形态也应各有不同。这种社会实体学说后来引发了一场有关实体主义经济学与形式主义经济学之间的论战。*参见李丹《理解农民中国》,张天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在人类学中,围绕东南亚农民经济行动的性质,斯科特与波普金二人也展开过类似的论战。*See James C.Scott,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Samuel L.Popkin,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Rural Sociaty in Viet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从理论的起源上来看,波兰尼倚靠人类学家的民族志,阐述了其社会实体学说。为了支撑社会实体论,马林诺夫斯基、图恩瓦尔德、戈登威泽、米德、里弗斯等人的经典民族志成果不断地出现在《大转型》的论述过程之中。例如,借助于马林诺夫斯基在美拉尼西亚的研究,波兰尼旨在阐述这样一些事实:“库拉圈”中的经济交换行为,都是“嵌入”在社会地位与荣誉体系中的;而在物质层面,社会共同体不仅分配物资,而且承担了使其成员免于饥饿的责任;相应的政治秩序依靠对称的互惠体系以及以部落头人为中心的再分配制度就能运转;原始共同体的政治权力是否巩固,有赖于权力义务的持续性履行。波兰尼对夸富宴的人类学研究也大加赞赏,认为这些研究表明:如果用荣誉符号以及仪式行动包裹的物资消费方式不能持续进行,头人的政治权力将受到质疑乃至颠覆。也就是说,由仪式及其体验、社会位置、互惠体系、家庭与亲属关系构成的实质性社会文化系统,包罗了政治、经济等子系统。这种社会实体学说认为:形式主义经济学在毫无道理的简化社会与文化。因此,应该从社会实体层面出发去看如何发展经济,而非从如何发展经济层面出发去看如何治理社会。
(三)一个关键的面向:经济作为“嵌入”社会的子系统
“经济嵌入社会”是波兰尼重点阐述的核心命题。他强调,发展市场经济应从社会整体出发,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旦无法因地制宜,便会出现发展的危机。他的社会经济理论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经济社会学完全不同。*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格氏更加强调个体或组织的经济行动(而非整个经济系统本身)如何“嵌入”在社会网络或社会结构之中的,并以此去修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Mark Granover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1,no.3,1985,pp.481~510.而波兰尼的意图是要颠覆斯密、李嘉图、边沁等人的古典经济学说,用“社会人”的假设去替代而非修正“经济理性人”的学说。
人类学家真正继承了波兰尼的经济“嵌入”理论。经典民族志总是追问:到底社会文化系统中存在怎样的经济?例如,萨林斯认为:对波兰尼“嵌入”命题的阐发可以创造“真正的人类学的经济学 ”。通过深度观察斐济、火地岛、夏威夷甚至美国本土的“经济”,萨林斯认为并不存在纯粹的利益交换关系领域。“经济作为一种文化范畴而非行为范畴,它与政治或宗教同属一类……经济不再是满足个体需要的活动,而是社会的物质生命过程。”*[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页。在《甜蜜的悲哀》一书中,萨林斯艰涩地指出了这种“物质生命过程”的历史相对性,并将其所在的西方本土文化中产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视为社会文化史的特殊产物,从而否定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全球普遍性。另一位人类学家斯科特更是直接宣称:“他(指波兰尼)对前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分析,促成了我自己的著作。”*[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7页。立足于对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的民族志观察,斯科特出版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隐藏的文本》等力作。尤其是有关“道义经济”的概念,是对波兰尼“嵌入”理论的直接阐发。斯科特认为,传统经济受道义伦理的钳制,当贫农、佃户受到饥饿的威胁,富农、地主有救助的义务,否则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这就是农民世界的道义经济与生存伦理。*参见[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在马来西亚的长时段田野调查中,斯科特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引入,首先破坏了传统道义伦理的经济基础,使得原本受社会保护的农民生存问题直接抛入了浩瀚的市场之中,而没有任何保障。*参见[美]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何江穗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斯科特的这些研究,与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分析的19世纪自由市场脱嵌史的过程相比,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而相比较起来,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要简单一些。与斯科特、萨林斯不同,格兰诺维特并非是要重创一个经济学的视角,而只是在提醒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忽略了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这一点常识,应将社会学的发现纳入到经济学的解释框架中去。如果说萨林斯、斯科特是在挑战主流经济学的解释范式,那么格兰诺维特则仅仅是在补充经济学的不足。前者才是波兰尼经济“嵌入”理论真正的继承者。
(四)被简化的一个面向:政治作为“嵌入”的另一个子系统
“嵌入”理论被许多读者简化为市场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关系,其政治面向被严重忽略。实际上,只需要看《大转型》一书的副标题“政治、经济的起源”,就可知政治命题的重要性。波兰尼认为,政治与经济是一对孪生的兄弟。19世纪的市场经济脱嵌史,同时就是一部自由政体为自由市场涤荡道路的历史,“通往自由市场之路的畅通需要中央政府来涤荡”。*[匈]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经济“脱嵌”的前提,是政治的“脱嵌”,而这必将遭致社会的全面抵抗。“社会不是受国家法律支配的,而是恰恰相反,社会使国家服从它的法律”,*[匈]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6页。国家应该为社会保驾护航,否则就是对社会的背叛。当政治力量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时,整体社会便会酝酿巨大的危机。20世纪出现的法西斯主义以及欧洲社会主义的实践,就是因为其政治实践脱离了社会整体而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因此,在当前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之下,应该提倡将经济、政治均“嵌入”在社会实体之中的发展策略,避免再次回到带有中心—边缘、引导和被引导的政治经济中心主义的发展路径上去。
詹姆斯·斯科特不仅继承了“嵌入”的经济面向,而且浓墨重彩地发挥了“嵌入”的政治面向。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斯科特猛烈批驳了那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单一性国家视野:极端的现代主义发展计划与独裁政权结合起来,就会导致对社会图景的简化、对治下社群的残暴,但最后一定会趋于失败。*参见[美]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按照斯科特的见解,政治实践的轨道必须铺设在社会现实之中,即政治应该“嵌入”在社会总体之中,否则,纯粹自上而下的政治实践将导致失败。此外,杜赞奇虽然没有明确阐发政治“嵌入”命题,但他在华北的人类学研究中,提出了两个命题与波兰尼的政治“嵌入”命题高度吻合:一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试图向基层社会组织全面渗透,这是政治“嵌入”在实践层面的努力;二是著名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这一概念认为,自上而下的政治蓝图必须依靠地方的社会文化组织才能得以实现。*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斯科特与杜赞奇在政治“嵌入”命题上的深度阐发,无疑将对当代中国民族政治实践路径与基层治理方式具有启发性意义。
(五)一个“过程论”的面向 :历史作为“嵌入”的分析视野
波兰尼对市场史的叙述表明,自由市场要存在,首先要创造一个市场社会。但新的市场社会与传统的、各种“嵌入”在社会体系中的市场模式并不兼容,所以需要一种强制性的力量链合无数个先前早已存在的贸易系统,并促成一个可以自由交易的市场。波兰尼认为,整个19世纪,自由市场通过船坚炮利在全世界不断铺展开来,但也同时遭到了社会的全面抵抗。在他看来,19世纪的社会史是一个钟摆式的运动史,自由市场对社会的侵蚀力量与社会的自卫力量不断交织。一方面,市场力量试图冲破社会藩篱反嵌社会;另一方面,各种社会自卫措施与政策所交织而成的保护性网络,抑制了人与自然的彻底沦陷。为了论证这一钟摆运动,波兰尼从历史过程的视野中叙述了市场与社会的“嵌入”关系。
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继承了波兰尼的历史“嵌入”观点,但是却对其历史描述的片面性做了批评与补充。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形形色色的交换》这一巨著中,布罗代尔认为,波兰尼所说的“大转折”实际上很早于19世纪就已经发生,但“波兰尼没有作任何努力去研究历史那具体而多样的实在”,*[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交换》,顾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230页。这实际上是在批评波兰尼仅仅关注了100年的历史。因此,布罗代尔详细的围绕“市场交换”这一主题,为波兰尼做了19世纪之前的历史注解。
波兰尼与布罗代尔的历史“嵌入”视野,对当今诸如“一带一路”这样的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具有巨大的参考性意义,研究者可以用一种历史性的互动观点去观察这些世界性的长廊。此外,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历史过程分析,*参见[法]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资本主义论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法]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与前述的社会实体论一旦结合,就能推出一个基本的结论: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的分析应该优于政治研究与经济研究——也就是说,在决定发展什么样的经济或实践什么样的政治之前,应该清楚发展对象的社会文化系统及其历史过程,然后才能弄清楚怎样发展、谁的发展等问题。
综上,分别是“嵌入”概念内涵的五个面向:空间、社会实体、经济、政治以及历史,每个面向都由人类学家或历史学者进行了深度阐释。其中,空间、实体以及历史三个面向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而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尤其是对发展的路径、方向、策略提供了启示。而政治与经济两个重要面向,则是“嵌入”在三个面向中的两种实践——不论是政治实践还是经济实践,都应将其发展图式铺设在社会文化的实体之中。总之,五个面向展现了“嵌入”概念的多重内涵,这也是它能回应各种“脱嵌”危机并被当今学界重新重视的原因所在。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如何在发展的语境中看待、使用这一概念是当下最迫切的理论工作之一。
四、“嵌入式发展”对发展主义危机的多重回应
根据上述五个面向的陈述和对“嵌入”理论谱系的概略清理,可以对“嵌入式发展”进行一个更为综合、精确的定义:“嵌入式发展”是一种尊重社会文化实体规范和历史延续性、并倡导共生与交互的政治、经济实践方式。这一定义的关键,在于它能够综合“嵌入”概念的所有面向。在这种定义下,“嵌入式发展”不仅能够规避“跨越式发展”和“参与式发展”两种模式的内在缺陷,而且能够良好地回应当代发展主义的多重危机。
首先,在空间层面,“嵌入式发展”更加认同共生、交互的多元一体空间格局,拒绝过度条块式、分割式的发展路径或治理模式。“嵌入式”的空间布局,需要坚持“共生性”与“交互性”两个特征。费孝通先生曾经在叙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概念时,*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既重视多元之间的历史共生性(“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又十分重视多元在一体之内的交互性成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有关多元一体的“嵌入式”空间发展格局的论述,还被费老使用到了区域经济的建设方案中。例如,在论述黄河中上游多民族市场建设时,*参见费孝通《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瞭望》1998年第33期。费老认为,这一区域的经济建设应该综合各民族、地区的特色,而不是以某一民族作为发展的主导。而在“跨越式”和“参与式”两种发展模式中,由于其已经设定了边界清晰的发展主体,同时又蕴含了先后、主次、中心或边缘等涉入价值评定的发展方案,从而无法从大的区域社会格局中汲取可供借鉴的交互性发展灵感,而且可能造成新的社会分化。
其次,在社会实体层面,“嵌入式发展”尊重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内在机理,以内发的视野展开系统性的建设。今天,在每一个主权国家内外,都已经形成了巨型的区域社会,如同海上和大陆丝绸之路的建设构想那样,“嵌入”了经济战略、政治理念以及各种宗教文化类型。在这些巨型区域社会中,每个社会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发现区域社会内外的普遍联系,尊重社会内部的特殊规则是“嵌入式发展”的基本准则。要强调的一点是,由于社会内部具有自身的自发性,因此,发展的方案首先是服膺于社会内在规范体系,而不是相反。通过重整族群与族群、城市与乡村、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联系纽带,推动社会进行自我重建。这种内外结合的“嵌入式发展”方式,将重新集结各种已被区隔、断裂、碎片化的个人、社群,重组多元一体的国家与社会。
再次,“嵌入式发展”并不拒绝“市场经济”,但拒绝只能代表部分人利益的市场经济,更拒绝给大部分人带来灾难的市场。在西部大开发的几十年时间里,民族地区与部分乡村、城镇地区,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及赶超型工业化进程,纷纷迈向“跨越式发展”道路。然而,过于密集而快速的发展模式,往往是以牺牲自然环境和社会公平为代价的,这一方面消弭了民族地区发展的内生系统(如传统的文化与自然),另一方面导致这些地区的后劲不足。如今,市场经济已经遍布全国的乡村与民族地区,确实带来了便捷的贸易、消费体系,改造了原有的生活世界、生活方式。如果重新将市场从中国社会中抽离,这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但这无法掩盖当下发展模式的不足。例如,市场分配的不平等;市场破坏了原有的道德体系,新的市场伦理却没有建立起来;市场的发展、工业的扩建、城市的扩张,将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等要素虚拟化为可以流通的商品,但却毁坏了自然与社会本身的内在机理,等等。这不禁令人追问: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市场?市场经济本身作为一个通往丰裕社会的方案,其引发社会灾变的根源在于以下问题没有得到良好回答:谁来设计、执行这个方案?谁来分配、享受或承担造成该方案的后果?如果按照波兰尼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市场的发展应该是在尊重地方社会文化体系的前提下进行的。至少应该建立一个尊重社会原有文化体系的市场,即“嵌入”性的市场,既不毁灭人性与自然,又能在利润、机会、教育资源分配上惠及绝大部分人的市场。
复次,“嵌入式发展”要求政治不能脱离社会系统。政治不能悬浮或“脱嵌”于社会之上,只有推动“嵌入式的政治”,才能实现“嵌入式”的发展。波兰尼指出,国家的命运与社会变革之间具有“共生关系”。*[匈]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页。不仅是经济,政治也应该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执政党十分重视将权力系统渗透进民族地方或乡土社会。*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学者提出的“政党下乡”*参见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送法下乡”*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都是政治再嵌进社会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通过近一个世纪的实践,成功地实现了将数亿民族地方或农村社会的人口整合到总体性国家中来,这是一种“嵌入式”的治理模式。但最近数十年来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以往的“嵌入”治理虽然带来了政党高效的整合力,但却造成了党政不分、党权过大的后果,同时出现乡村自治畸形化、民族区域自治产生了认同危机等问题,最终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脱嵌”现象。因此,国家权力要实现与民族地方、乡村社会的对接,实现上下有序的治理格局,前提就是推动中央权力或政党权力进行自我改善,将权力有序“嵌入”进地方社会的内部结构之中,这是一种“嵌入式的治理”。这种治理以国家力量作为乡村治理的后盾,但尊重民族地方或乡村社会的社会基础。基层政府如果悬浮在社会之外展开政治实践,*参见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必然导致“脱嵌式”的政治格局。
最后,在历史的内在视野之中推进“嵌入式发展”,在展开政治经济的实践之前考察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在民族地方或乡村社会,以往的“跨越式发展”或“参与式发展”是有向度的发展,但这种向度是外发型的,并不是出于社会内发的视野。例如,是否实现了“跨越”是以经济水平的外在目标作为比较对象的;衡量谁“参与”了发展则主要是在“政府—社会”间的合作模式中进行定位的。但是,“嵌入式发展”更注重社会内在的视野,而这种内在视野需要从历史的维度中去获得。当前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需要从历史中去叙述这一巨型区域社会具有长久的历史联系,而且需要叙述存在什么样的历史联系。例如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等层面是如何交融的。同时,在寻找这种内在历史视野的过程中,找寻有益于当下政治构想、经济战略的路径。任何政治经济实践,必须是在尊重社会历史生态的基础之上才能展开。也就是说,对有关社会变迁的历史思考应该先于政治、经济改革战略的制订。
综上,“嵌入式发展”模式吸收了波兰尼及其后的学者对“嵌入”概念五个面向的阐发,一一回应了发展主义在现实图景中呈现出的多重危机。这种综合视角对以往的发展方案进行了辩证的回顾。而“跨越式发展”或“参与式发展”都是以经济或政治为向度的发展图示,忽略了社会总体系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例如,已有的发展模式或“嵌入”视野将人拥有的社会关系也视为一种资源或一种社会资本,继而在市场上变现,这是无视地方性知识的历史与社会特性的做法。再如,有些学者倡导全面的国家管制主义,将社会纳入普遍的行政监管视角,这也将泯灭社会自发的特性。诸如此类的发展方案,远远背离了波兰尼本身的意图,波兰尼拒绝将社会性、自然的或人本身虚拟化、价格化、行政化。“嵌入式发展”将社会、文化及其历史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注重一种协同式的、整体式的、去中心化或互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与以往的发展模式不同,“嵌入式发展”要去除将一切经济化、行政化的做法,使人与自然回归其本位。这种发展理念与当前构建“一带一路”的亚洲区域社会是相契合的。如果能够以“嵌入”的历史或整体眼光透视“一带一路”区域内的民族关系,我们就能期待更加完善的大转型。否则,很可能会造就新的“脱嵌”政治、“脱嵌”经济或“脱嵌”的发展主义危机。
五、余论
“发展”与“如何发展”是当前中国民族地区或乡村地区的主要议题,如何发展或发展什么则是不同地区在现实层面的具体实践。过去20年,以发展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不论是“跨越式发展”还是“参与式发展”,均将中国乡村社会或少数民族地区推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型进程之中。工业与现代商品贸易市场链合了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区域与乡村社会,使其与更为广阔的多元一体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体系直接联系起来。一方面,这将赋予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概念以新的内涵;但另一方面,这一市场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含有乱象丛生的危机——原有的社会文化形态及其政治经济制度卷入到一个流变的市场格局之中去之后,必将引起文化与文化、社群与社群之间的龃龉。波兰尼所预言的市场灾变,在中国的现代化图景中也可见一斑。例如,工业化与市场化过程导致了劳动力、土地出现了虚拟化为货币的倾向,大量人口不断沦为相对贫困的境地,环境破坏严重;在土地流动和劳资合同的签订、履行时,出现了诸多纠纷;生活世界中的文化体系发生了断裂,人们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外来市场的殖民暴力;与此同时,乡村自治以及民族区域治理分别遭受了程度不一的质疑和代表性危机。
在种种发展危机面前,我们亟须一种新的发展视野。波兰尼曾经发现的“嵌入”概念具有内涵丰富的多种面向,由此概念衍生的“嵌入式发展”模式,能够一一回应所有危机。“嵌入式发展”是在新的大转型时期适时提出的社会发展战略,它所面对的是新的社会图景。这种新图景由新的、被现代工业与市场改造过的人、土地、商品构成。例如,乡村社群、少数民族群体与外部的联系,不再完全依赖传统的土司王权、宗教礼仪、联姻纽带或人民公社体制(虽然这些传统仍然在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市场、商品及格式化的物资消费方式联系起来,并不断重组其生活世界。在这种以经济大转型为目标的市场化进程中,由于工业与市场的标准化生产,导致了不同社群的人对物品的同一性使用方式,因此,乡村社会、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生活体系逐渐趋同(该潮流符合了现代工业与市场内在的“去相对主义”要求)。
但是,去相对主义的发展进程,试图标准化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网络,将造成对土地、商品与劳动力的相对简化,并消弭了原有的社会文化传统。例如,第一,在物资消费方式上,新的物资与商品琳琅满目,并被不断被赋予现代性的文化意义;新的消费观念、符号系统与传统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明,后者经常被资本与权力所重塑、激活、发明乃至新创,并不断被推向现代舞台进行展演。波兰尼大声抗议的原因,是因其不满于社会文化系统被单向度的市场经济所吞噬,后者应该是“嵌入”在前者之中并作为一个功能而存在的。第二,在土地使用方式上,土地被赋予了最高的“价值”,不断被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等“化”学进程所蚕食,农牧用地不断被转化为工业、建筑用地,自然环境不断被敲响濒临崩溃的警钟,但是,面对付出此种昂贵代价所换来的“利益”,在再分配过程之的分配法则与分配份额却并不明朗,且经常被质疑为不平等。第三,在劳动力的使用上,民族地区或乡村社会的人——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被建议朝向某种有“素质”的方向发展,通过教育、语言、技术、观念等现代行政治理手段,培养出与当代发展潮流相适应的人才,为工业、城市输送合格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者。这样一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土地、商品就被全面卷入至这场发展大潮之中去了。
全面卷入并非坏事,但是如何整合却是一大难题。“嵌入式发展”试图将上述的人、土地、商品重新整合进一体的社会中去。它不仅要求重新回到多元一体的历史空间中去思考,而且认为应该将政治、经济实践均“嵌入”在社会文化体系之中,呼吁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应该清晰明了社会文化变迁的具体条件之后才能展开。“嵌入式发展”模式认为,任何一个区域的“发展”,都不应该以一套纯粹的技术手段、制度规范、观念体系去置换已有的系统规范,发展的限度需要参照内外嵌套的社会文化体系。在这种发展模式中,重新复归人的人性与社会的自发性,是发展最为重要的目标。当重建人与社会的目标达到之后,发展才能算是合格的发展。
此外,“嵌入式发展”不仅试图在发展过程中,找回作为整体的人与社会,而且试图将“国家”带回其正确的轨道,使政治实践符合历史与现实,这将对少数民族地区或乡村社会治理的政治实践过程提供丰富的借鉴意义。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就是试图寻找一种与社会嵌合的政治,并将民族、社会的政治治理轨道铺设在社会体系之中。波氏认为,国家自始至终都应该和社会站在同一个队列之中的。不论何种发展,都应该符合民族地区或乡村社会自身文化机理的发展;不论发展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负面后果,国家都应有勇气承担这份责任。因此,社会与国家不是分立的,而应该是一体的。国家只要不僭越其自身法治的轨道,就可以与社会母体相辅相成。通过推动“嵌入式”的治理,继而能为“嵌入式发展”做好政治铺垫。
(责任编辑 甘霆浩)
作者简介:① 黄志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