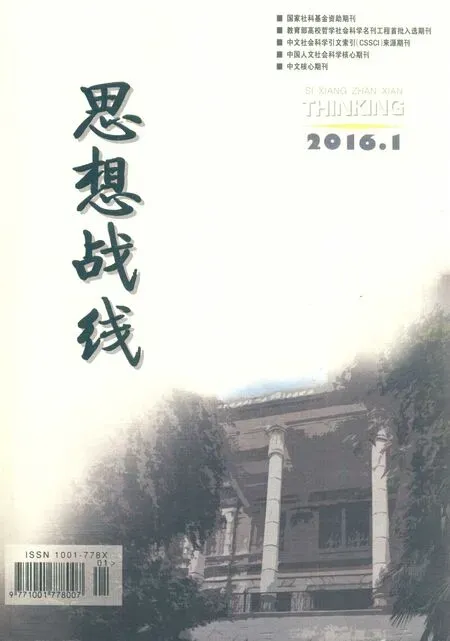人类学批评与当代艺术人类学的问题阈
2016-04-11向丽
向 丽
人类学批评与当代艺术人类学的问题阈
向丽①
摘要:人类学批评既是当代人类学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学展现其重构现实生活关系之能力的重要维度。人类学批评主要从“意识形态批评”和“日常生活批评”两个基本向度展开实践,为自由而多元的声音敞开诸种可能性。在走向反思的历程中,艺术人类学如何秉承人类学批评的传统,对于如何理解艺术;如何发掘艺术的地方性审美经验及其价值意义;如何理解和阐释文化交流中的艺术;如何考察和把握当代艺术的多元存在样态及其审美抵抗方式等问题,做出更富于智慧的解读与展演,从而真正开启了艺术人类学的诗学与政治学两个维度,无疑是当代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向度。
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类学批评;当代艺术人类学;问题阈
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学转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和学术思潮。并且,就在此种转向中,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被不断地催生出来并产生了极富于变革性的力量。就当代学科的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态势而言,诸如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应用人类学、感知人类学、象征人类学、城市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审美人类学以及艺术人类学等学科的产生,都在力图跨越自身的边界,通过人类学平台激活传统学科新的发展空间,甚至极大地挑战着学科权力的疆界,释放出跨界的快感与自足。然而,这远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事情在于,人类学早已不再只是一门学科,而是作为一种根本性的精神在其中发挥作用。此种精神不是别的,而是“批评”。
无可否认的是,在人类学走向自身反思的历程中,正是“批评”作为一种主导性的声音,能够让我们对于“常识”保持着足够的警觉,从而不至于深陷幻象的泥淖中而不自知。事实上,“人类学家已经试图——超越我们的翻译者角色——把我们的功能延展到去扮演曾属于批评家的角色……”。*[美]乔治·E.马尔库斯等:《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阿嘎佐诗等译,王建民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2页。在此,人类学批评既是当代人类学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学展现其重构现实生活关系之能力的重要维度。因为,“人类学作为一种有力的文化批评形式,是人类学者们早已对社会作出的承诺”。*[美]乔治·E.马尔库斯等:《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57页。尽管这一承诺至今依然尚未得到完全兑现,但人类学在与其他研究领域联合发展文化批评中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已不容忽视,在从“他者的目光”中提炼人们对于差异性的敏感度,从而发掘理论的洞察力的过程中,在保留对异域文化探求基础上回归本土文化反思和重构的转向中,人类学批评始终是在场的,并且,就在这些尖锐的声音中,一切关于文化和艺术的修辞学都将恢复其面对现实的真实质感。
在当代学科转型中,艺术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当代美学/艺术学、人类学领域中值得关注的学术发展动态。近年来,艺术人类学研究取得了较为卓著的成果,在关于艺术制品、艺术制作者、艺术行为、艺术观念及其共同编织的艺术网络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性进展,并引发了艺术人类学的当代转型。然而,在艺术人类学应建构于何种意义上的人类学平台之上;人类学如何介入艺术学研究;人类学介入艺术研究之后将引发何种艺术研究范式的转换等问题上,还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空间。在此种探讨中,人类学批评何为;人类学如何激活当代艺术人类学的问题域则,是这些问题的某种聚集形态,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
一、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与人类学批评的向度
20世纪80年代,乔治·E.马尔库斯(George E.Marcus)和米开尔·M.J.费彻尔(Michael M.J. Fischer)在其被人类学界誉为“后现代人类学”的代表作《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中提出,人类学应回归于文化批评,其重要的标志是,从对异文化的单纯兴趣回归到本土文化批判,从而建构一种更加富于平衡感的文化观念。*参见[美]乔治·E.马尔库斯等《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这是一种由关于对象知识生产到关于自我知识生产的转向,或毋宁说是一种反身性的建构。此种转向是人类学自身走向反思,从而对其与殖民主义相沾染的历史进行回溯与划界的必然结果。然而,这具历史的残骸并未曾就此退出现实的舞台,它常常以新的意识形态形式复活,或蜷于某个角落在特定时刻出其不意地重新站立起来。因此,在人类学思潮的更迭与演进历程中,批评始终作为人类学发展的精神内核,能够给予历史幻象一种响亮的撕裂。
批评是为区分与划界,人类学也正是以此不断超越其意识形态藩篱,并为其他学科研究范式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和发展契机。但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的,相反,它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而迂回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学能够作为文化批评展演其重构现实的力量,关键在于人类学能够将自身作为审视的对象。恰如麦克尔·赫兹菲尔德指出的,早期人类学家“深信自己的文化远比自己研究的对象优越得多,要是有人提出‘科学’也可以当做‘巫术’一样来研究,他们肯定会惊讶得合不拢嘴。他们并不明白巫术和科学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象征意义的不同,相反,他们认为二者之间的差异是理性的、真实的,不能加以任何夸饰”。*[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刘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页。这种不证自明、深信不疑的意识形态想象在古典进化论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而随着人类学家关于地方性知识的采集与经验,那些曾经被他们视为野蛮、低劣、未开化的民族所展示出的“奢侈的艺术”,让人类学家对于这些深嵌于各种权术政治的常识和西方自鸣得意的文明观发出了质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类学逐渐发展出民族志范式,对西方建构的文明进行着潜隐性的批评。概言之,这时期的民族志主要提供了三种广泛的批评:“‘他们’原始人保持了对自然的尊重,而我们已经丧失了人类生态的乐园;他们维持着亲密而令人满足的社区生活,而我们丧失了社区生活的经验;他们保留了日常生活的神圣意义,而我们已失去了心灵的视野。”*[美]乔治·E.马尔库斯等:《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81~182页。于此,“他者”及其所包含的原始激情被重新发掘并展现其作为文化救赎的可能性力量。而此种反向赞誊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艺术界掀起的原始主义风潮中就已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诸如高更、马蒂斯、毕加索等一大批艺术家,从大洋洲、美洲、非洲等地的土著部落艺术中汲取了新的艺术表现语言和手法,催生出了后印象主义、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诸多流派。在西方艺术中刮起的“黑色风暴”和“返祖现象”中,人们继续展开着“寻找原始人”的旷日持久的工作。在人们关于“高贵的野蛮人”的礼赞中,在对于“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参见Diamond,In Search of the Primitive:A Critique of Civilization,New Brunswich,New Jersey:Transaction Books, 1974;Robin Clarke,Ceofferey Hindley,The Challenge of the Primitives,London:Jonathan Cape,1750;Paul Radin,Primitive Man as Philosopher,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57等著述。的尊崇中,人们似乎在热情地建构出新的集体表象,以表达对原始文化的无限钦羡,一种新的审美意识形态得以滋长。
在此种美学重构的风潮里,原始文化不仅被重新定位,甚至被视为西方文明反思的新起点。这种转折无疑是巨大而令人振奋的,与过去将他者进行妖魔化的叙事模式相比较,它开启了一种新的关于“看”的方式。然而,这种美学神话叙事同时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原初的他者长期被遮蔽的存在得以显现,成为自我反思的镜像,从而磨砺出人类学“通过边缘理解中心的缺失”的特殊光泽;另一方面,在对传统范式中“文明/野蛮、高级/低级、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中,将其颠倒过来尽管是极富于革命性的,但重归于静态的对峙同样会产生一种新的二元对立幻象及其暴政。他者被无限地加以神秘化和美化,怀旧的悲哀并不因此得以消释,反而变得愈发不可收拾。庆幸的是,这种天真而拙劣的比较与激进的修辞学策略,在人类学自身走向反思的历程中也已获致重新审视。
事实上,许多更富于智慧的人类学家渐渐意识到,古典的文化拯救母题早已不再奏效,或至少它不再能够反映出充满着无数变量的当代社会的全部复杂性。差异是无所不在的,而绝不仅限于所谓自我与他者之间。于此,“他者”既非一种完全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也非自我的设定与外化,它只应是自身如其所是地显现。不仅如此,惟有当我们彻底摆脱了对于“他者”的自以为是的策略和经营,才有可能在“他者”的自行显现中真正发掘出其所蕴藉的批判潜能。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尽管“后”有其内在的模棱两可性,但它的一个重要向度仍然是对于现代意识形态的公开决裂:它揭橥了建构于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的独断性,以及总体性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暴政的源头之事实,从而充分肯定文化的多样性、不可表现性、游戏性、差异性、非中心性、零散化、不确定性、不可通约性、流动性等特征,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人类学反思的意识。在这一时期,人类学持续着关于所谓西方文明的纠偏工作,尽管关于“原始文化”的发掘与提炼仍然是其重要的精神来源,但关于他者的神话已不再那么诱人,人们对于他者的两副面孔以及蕴藉其中的权力运作机制,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与反思。尤其是,人们对于人类学本身的角色做出了更富于意义的界说与扮演。
从根本意义上讲,“人类学的任务就是透过那些自称为永恒真理的华丽辞藻去揭示隐藏其后的种种我们所熟知的实践行为”。*[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刘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页。亦即,人类学是对于不证自明的常识的批判,其中,意识形态的神秘性,权力自身所包蕴的“软化的新殖民主义”(soft neo-colonialism)*弗莱和威利斯指出,土著艺术被纳入市场营销和商品生产中可被视为一种软化的新殖民主义,土著社会传统的信仰和时间将根据西方市场逻辑进行重构,土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将变得零碎化而与自身传统相中断。See Fry,T.,and A.Willis,“Aboriginal Art: Symptom or Success?”,Art in America,vol.77(July),1989,p.116。这关系到如何看待土著艺术的本真性与交流性问题,本文也将着意于此种探讨。及其缜密的幻化机制,成为反思人类学的重要议题。为了通达这一目标,人类学批评基本采用“变熟为生”亦即陌生化的批评策略,从而使意识形态变得可见。然而,这毕竟是一个相当艰辛而漫长的历程,其困难之处不在于人们是否有与权力对峙的勇气,而在于其所面对的对象是隐秘而狡黠的。事实上,意识形态批评已成为当代人文学科共同介入的工作,并展现出不同的策略与设计。人类学民族志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设计中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具有远为广泛而深远的吸引力。在关于人及其行为复杂性的研究中,“民族志批评的任务在于发现个人和群体对他们共享的社会秩序进行适应和抵制的途径及其多样性。这是一种在一个空前均质化的世界里发现多样性的策略”。*[美]乔治·E.马尔库斯等:《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86页。于此,人类学批评的旨趣不在于描述,而是一种关于人与社会的真实链接,但它恰恰又能够在对文化的经验与描述中,捕捉到意识形态婉转的心思与逶迤的轨迹,从而提供了人们应对意识形态及其秩序的种种策略。
人类学批评强调反思在当代人类学和民族志中的作用,它带来了民族志研究与写作的新气象。例如,斯蒂芬·A.泰勒将后现代民族志定义为“一种合作发展的文本,它由一些话语碎片所构成,这些碎片意图在读者和作者心中唤起一种关于常识现实的可能世界的创生的幻想,从而激发起一种具有疗效的审美整合”。*[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等:《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66页。在泰勒看来,后现代民族志推崇“对话”而非“独白”,是对于碎片的拾掇与重构,其功能是“唤起”而非“再现”。因此,后现代民族志所要显现的只是一种自由的声音。在此意义上,后现代民族志即是诗,它凭借与日常生活的融入与中断,更能通达对于存在的揭示与洞察。
综上,人类学批评主要从两个基本向度展开实践,为此种自由而多元的声音敞开了诸种可能。这两种批评向度和类型可称之为“意识形态批评”和“日常生活批评”。其中,“意识形态批评”的要旨在于“去神秘化”,亦即揭示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及其缜密的运作机制;“日常生活批评”则是一种更富于经验性的研究,它将意识形态批评付诸日常生活的微妙之处,亦即探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意识形态策略的适应与抵制的种种方式。在当代社会,这两种批评类型实则是并置的,表现出解构与建构的双向维度。
人类学批评是持续而日益尖锐的,诸如对于强硬的殖民主义和软化的新殖民主义的批评,将殖民话语与实践作为民族志研究的对象,不仅对于这段历史进行回溯,而且研究历史是如何被表述和建构的,这使得人类学的自我批评成为可能。而重新审视分类如何可能及其蕴藉着的甜蜜的暴力,则是人类学意识形态批评的集中体现。此外,人类学在日常生活中发掘批评的力量,并取得卓著的成效。例如,威廉·拉伯夫(William Labov)通过对美国市中心贫民区语言的研究,捕捉居于权力社会边缘的人们对于权力抵抗的语言学策略;*See Labov, William,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2.保罗·斯托勒(Paul Stoller)则从感官切入,对于西方视觉主义至上的独裁与专横,提出了强烈的质询与批评。他主张人们必须重新调整和开放自己的感官,从而建构一种真正“有品位的”民族志,这提供了一种巧妙而有趣的人类学批评范式。*See Stoller,Paul,The Taste of Ethnographic Things:The Senses in Anthropology,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9.此外,20世纪80年代兴起并发展的新博物馆学,倾向于将公众理解为相异的、复数的、能动的而不是同质的和被动的群体。与传统博物馆学相比,新博物馆学对于博物馆中陈列物的含义如何被刻写,以及如何被阐释为“正确的”叙事给予了特别关注,并且植根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的变化,以及在博物馆公共空间内被承认的各种少数群体的推动,对于潜藏其中的权术政治发出挑战。*See Vergo,Peter,The New Museology, London:Reaktion Books,1989.
这些实践无疑都在表征这样一个事实:“当欧洲征服并统治非欧洲民众时,这些民众绝不仅仅是殖民势力被动的牺牲品。他们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回应殖民者的统治,最为重要的当然是各种各样的抵抗形式。”*[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刘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81页。尽管那段不堪的殖民历史或已成为历史,但殖民统治的传统依然存在,它总会以各种新的意识形态形式出现,甚至像幽灵似地游荡在人们对于胜利的沾沾自喜中。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划破历史的假象,如何找到制约“殖民”与“剥夺”的新的抵抗方式。有意味的是,随着人类学对于艺术及其经验的关注,随着艺术人类学的兴起与发展,这种新的批评与抵抗方式已渐至显现出来,并产生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变革。
二、走向反思的艺术人类学
在当代跨学科研究中,艺术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令人瞩目的,这不仅因为通过人类学研究理念和方法的介入,艺术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得以显现,而且,正是通过此种研究,艺术介入现实的能动性及其力量正在不断被开掘出来,这对于美学、艺术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学科都将产生新的震颤。在走向反思的历程中,艺术人类学秉承人类学批评的传统,对艺术做出了更富于智慧的解读与展演,这的确是一项严肃而兴味盎然的工作。
尽管目前艺术人类学正在不断显现其与社会现实链接的活力,然而,在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中,艺术却未能够被纳入人类学研究的视域中,或只能成为人类学的“剩余物”被放逐于人类学的边界之外。恰如贾克·玛奎(Jacques Maquet)指出的,“在关于艺术和审美领域研究方面,人类学做的工作非常少,除了研究‘原始艺术’之外”。*Jacques Maquet,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 Anthropology,Malibu:Undena Publications,1979,p.3.然而,即使是在“原始艺术”是否是“艺术”;“原始艺术”是否能够作为“艺术”而发挥功用等问题上仍有待商榷,事实上,“原始艺术”更多的只是作为描述社会生产方式、组织方式、交换、宗教等活动的介质而被轻描淡写地加以点缀,艺术并未能够作为艺术本身而显现,尽管我们对于“艺术”有了更多的理解。
那么,“艺术”为何难以进入人类学研究的中心视域?尽管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但它至少与人类学传统研究理念和范式,以及传统的“西方”艺术观脱不开干系,对于此种关联的厘清与反观,恰恰是艺术人类学自身走向反思的起点。学界对此有过诸多讨论,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值得深入思考:其一,艺术及其所包蕴的人类情感与经验是一种内在的难以描摹的存在,传统的民族志*主要指民族志发展的前两个时代所表现出的研究方式与旨向。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是一种随性的游记,第二个时代的民族志力图通过学科规范进入田野场,通过参与式观察与问询记录所研究对象的生活,虽则以“科学民族志”自我期许,但更多是一种记录而非对话。只有到了民族志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才开始了从反思介入民族志的再生产,在对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密切联系的重新审视中开启人类学批评的新图景。参见高丙中《〈写文化〉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代译序)》,载[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等《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通过观察与问询是无法捕获到其精神内核的。因此,人类学家不免在一种化繁为简的冲动驱使下,将艺术品当做“物”来看待,它产生的一个后果是,该物本身所包含的美学属性将直接被过滤掉;其二,人类学传统专注于对异文化的描摹与展演,往往自居于一种文化的傲慢感,这是西方中心主义审美意识形态长期以来盘踞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天然优越感。此种艺术制度将那些不能被西方美学原则涵盖和解释的事物加以分类,它们或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装饰品,或是被当做来自魔鬼方阵的异类排斥于西方艺术界之外。在这种分类逻辑的影响下,人类学家很难将其所面对之物当成艺术品加以看待和研究,“艺术前的艺术”因而成为了一种兀自弥散其光晕,却少有人问津的存在。
尽管如此,在人类学的发展中,我们仍然可以撷取到人类学关于艺术的诸多探讨,并且就在其探索轨迹中寻找到当代艺术人类学发展的向度与问题阈。诸如,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在《艺术与人类学》*See Raymond Fith,“Art and Anthropology”,in Jeremy Coote and Anthony Shelton (eds.),Anthropology,Art,and Aesthetic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p.20~22.一文中梳理了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脉络,概述了人类学对于艺术的关注与兴趣经历的三个主要阶段:
一是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人类家主要关注艺术的区域性风格和起源问题,图案设计的演化与传播,例如,阿尔弗雷德·C.哈登(A.C.Haddon)的《新几内亚装饰艺术》(1894年)和《艺术的进化:图案的生命史解析》(1895年),以及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在《北太平洋沿岸印第安装饰艺术》(1897年)中关于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印第安艺术的研究等,都是在这一向度上展开关于艺术的探讨。弗思指出,在一战前甚至在一战期间,人类学家对于艺术的兴趣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公众对于所谓原始艺术的关注主要源于其美感性和商业性的考虑,而非民族学的研究目的。*See Raymond Fith,“Art and Anthropology”,in Jeremy Coote and Anthony Shelton (eds.),Anthropology, Art, and Aesthetic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20.亦即,人类学家更多的是将异域艺术当成一种装饰品和商品来看待,而其中必然包含了意识形态的“筛选”与“变形”。
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由后印象派画家对于异域艺术的推崇,愈来愈多的异域雕刻制品(主要是面具和雕像)进入欧洲博物馆被加以收藏和展览,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为人类学专业性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关于原始艺术的研究,诸如博厄斯的《原始艺术》(1927年)结合自己在北美、南美多人种地区的实地考察及采集到的丰富的原始资料,对于绘画、文学、音乐、舞蹈等原始艺术类型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提出了“世界各民族尽管对美的鉴赏千差万别,但均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美的享受”*[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的观念。此外,雷恩哈德·亚当(Leonhard Adam)在其《原始艺术》(1940年)中,将史前史与现代原始艺术联系起来,对于农民艺术、儿童艺术以及欧洲艺术家与原始艺术的关联等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See Raymond Fith,“Art and Anthropology”,in Jeremy Coote and Anthony Shelton (eds.),Anthropology,Art,and Aesthetic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21.在弗思看来,亚当强调文化背景尤其是宗教对于理解原始艺术的重要性,然而,他对于艺术的“社会意义”的理解和论述仍有其肤浅性。*See Raymond Fith,“Art and Anthropology”,in Jeremy Coote and Anthony Shelton (eds.),Anthropology,Art,and Aesthetic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21.在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值得特别提及的,即朱利兹·E. 里普斯(Julius E. Lips)的《野蛮人打回来了》(The Savage Hits Back)(1937年),其中,图文并茂地展现出非西方社会的艺术家和手工艺人如何在他们的绘画和雕塑中描绘白人的形象,从看似平淡无奇的描绘到令人发笑的讽刺性漫画,表现方式不一而足。弗思评析道,该研究是关于殖民主义的较早批评。*See Raymond Fith,“Art and Anthropology”,in Jeremy Coote and Anthony Shelton (eds.),Anthropology,Art,and Aesthetic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p.21~22.其意义在于,它恰是通过对特定文化背景全部丰富性的探究,给予了异域艺术的特殊类型之产生及其意义以强有力的解释,并且,在此过程中发掘异域艺术中所蕴藉的审美抵抗力量,这对于我们探究艺术的审美抵抗与审美修复等当代美学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学关于艺术的研究进入了其相对繁盛的时期,诸如关于异域艺术的田野研究的激增,艺术的批评性分析更具穿透力,关于个体艺术家的风格创造力的敏锐而复杂的研究已经出现,人类学家对于比较美学,以及艺术作为交流的媒介和知识建构与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事实,表现出更为浓厚的研究兴趣等等。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批评性论文集,诸如卡罗尔·乔普林(Carol Jopling)主编的《原始社会中的艺术与美学》(1971年)、安东尼·弗格(Anthony Forge)主编的《原始艺术与社会》(1973年)等,而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Rober Layton)的《艺术人类学》(1981年)以及荷兰艺术史学者怀尔弗里德·范·丹姆(Wilfried Van Damme)的《语境中的美:关于美学的人类学探讨》(1996年)等著述则展现出了现代人类学对于美学和艺术研究所作出的丰富贡献。在这一时期,艺术人类学研究进入了反思和自觉的时代,对于原始艺术独特的表达方式及其美学价值,原始艺术对当代艺术的影响,以及艺术的批评范式等都有了较深入的探讨。
综上,人类学对于异域艺术的研究分别经历了从物到艺术品、从艺术风格到艺术行为、从艺术本身到艺术力量的转变,这也正是艺术人类学渐至显现其自身反思维度的重要转向。此种转向渗透着人类学对于殖民与剥夺的强烈质询与批判,对于西方艺术制度的解构与开启,以及对于艺术之于社会意义的不懈地探寻。于此,艺术的精神内核正在慢慢地向人们展露出其特殊的光泽,艺术人类学也由此逾越出其作为一门单纯学科的域限。然而,恰如霍华德·墨菲(Howard Morphy)和摩根·珀金斯(Morgan Perkins)在《艺术人类学读本》“导论”中所言:“在人们本该期待的地方,艺术研究却往往是缺席的。”*Howard Morphy and Morgan Perkins,“The Anthropology of Art: A Reflection on its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in Howard Morphy and Morgan Perkins (eds.),The Anthropology of Art: A Read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9.这是令人深思的,在当代,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艺术,我们为何需要艺术,我们应如何捕捉艺术自身所蕴藉的奇谲的想象及其向现实转换的轨迹,这些都需要我们结合当代情境给予一种新的解答。尤其是,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人类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悖论和困境,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远为复杂,由人类学和艺术学共同提出的社会问题,也将更为深刻地渗入人与社会的再生产之中。因此,在当代语境中,结合人类学的批评实践,将当代艺术问题聚集与再度开启,就成为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三、当代艺术人类学的问题阈
当代著名的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指出,马克思主义批评史迄今展示了四种基本模式:人类学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和经济批评。其中,伊格尔顿认为,人类学批评模式是四种批评模式中“雄心最大、影响最远的一种,它力图提出一些令人生畏的根本性问题”。*[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例如,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雄心:通过人类学批评挑战资本主义的基本信条,划破历史的幻象,在重新连结过去与未来两端的“现在”情境中解构审美与实践的对立。这是一种充满着革命意味的人类学,它力图在对既有权力和知识结构审视的基础上重构权力的边界。
而在当代社会中,尽管这种现代神话依然存在,但剑拔弩张早已不再成为常态,审美和艺术在治理实践中发挥着一种特殊的功能,或,艺术介入社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微妙的治理术。尤其是在审美资本主义时代,审美和艺术的因素已然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我们应当如何发掘艺术作为治理术的可能,对于艺术人类学而言,这是一个极富于挑战性的课题。它的问题实则在于:人类学批评之后,我们如何建构艺术研究的当代性?亦即,我们应当如何考察与把握当代艺术的新形式、新构型与新意义?我们如何在当代情境发掘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在人类学的意识形态批评与日常生活批评双重维度的建构中,当代艺术人类学的问题域已自行显现出来,它同时促使我们重新考量人类学的角色与意义。
首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艺术,这是艺术人类学的元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展开关于当代艺术人类学问题探讨的重要基础。人类学研究表明:(1)艺术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而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在场的存在。恰如墨菲和珀金斯强调的,艺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否则艺术人类学将不会生产出它的读者。*See Howard Morphy and Morgan Perkins,“The Anthropology of Art:A Reflection on its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in Howard Morphy and Morgan Perkins(ed.),The Anthropology of Art:A Reader,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12.于此,艺术不再是单数的大写的“Art”,而是一种复数多元的存在,也惟有放弃将艺术进行整体统摄的冒险,我们才有可能触摸到艺术的更为真实的存在。(2)艺术就其根本而言不是“个人的艺术”,而是一种社会表现。因为,“严格地说来,‘个人的艺术’这几个字,虽则可以想象得出,却到处都不能加以证实。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民族,艺术都是一种社会的表现,即使我们简单地拿它当做个人的现象,就立刻会不能了解它原来的性质和意义”。*[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9页。也正是在艺术的多元存在样态中,我们才更为深刻地感受到艺术与社会的互渗。(3)艺术具有其内在的审美属性,这是探讨艺术作为特殊意识形态之功能的认识论基础。在具体的人类学研究实践中,“对于艺术以及人类行为的审美之维的忽略通常会导致人类学无法理解或令人信服地显露出人们参与社会特定事件的效果”。*Howard Morphy and Morgan Perkins,“The Anthropology of Art:A Reflection on its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in Howard Morphy and Morgan Perkins(ed.),The Anthropology of Art:A Reader,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22.艺术绝不是人类生活的附带品或点缀,而是人类的自然组成部分,它几乎容纳并形塑着人类全部的情感、想象与需要,并通过诉诸人的身体与情感而发挥作用,这是任何其他“物”所难以企及和复制的。因此,对于艺术作为观念、行为、力量的同时考察与把握是切入当代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入口。
第二,如何发掘艺术的地方性审美经验及其价值意义。在人们沉浸于建构艺术的形而上学概念带来的快感之前,艺术首先是作为一种地方性经验而存在,并显现其丰富的“物质基础”。“地方”在此意味着艺术的在场与经验的融合,而地方性审美经验则是此种经验最微妙的表达。在全球化语境中,艺术的地方性审美经验变得愈发珍贵。因为,它保留和维系着人类同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的日益同质化,及其潜藏着的人类学暴力相对峙和抗衡的可能性力量。正是凭借着地方性的视角,来自他文化的艺术的特殊性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并获得应有的尊重。然而,对于艺术作为身体、情感、经验的聚集这一事实的忽略,以及对于这些内在的难以描摹的存在的望而却步,使得这一本该富于活力的探讨长久地被搁置起来。
格尔兹(Clifford Greertz)曾指出:“如果在人们发现的各个地方、各种艺术(如在巴厘人们用钱币来做雕像,在澳大利亚人们在泥土上画画等)确有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它们不能被纳入西方化的艺术程式,即艺术并不是为了诉求于什么普遍的美的感觉。”*[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在此,格尔兹强调了艺术的地方性审美经验恰恰是对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美学构想的一种疏离,而对于此种疏离的表现形态及其特殊价值,那些被美学宠坏的人们往往选择视而不见。事实上,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在人们“以什么为美”以及“如何表现美”的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以文本的方式书写,而且也是以政治经济体制、习俗、惯例、亲属制度、宗教、神话、艺术、禁忌、伦理、世界观、天文历法、祭礼仪式等社会生活中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地方性知识的文化书写方式写成。如果没有对这些地方性知识的考察和了解,我们如何能够理解那些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习得的常识十分相异的审美和艺术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常识性的地方性知识中,艺术作为审美差异的微妙表达方式,它同时也是建构和重塑地方性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然而,在文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艺术的地方性审美经验渐至呈现出肢解和“分裂”的状态,即随着市场的全球化拓展,许多地方性少数族裔艺术也纳入其商品化的逻辑之中,这一方面带来了地方性艺术展演的契机,另一方面,地方性艺术从其生产土壤中抽离之后,若省却对于其蕴藉的地方性审美经验的考察,符号化、拼贴化的市场挪用,将使地方性艺术成为一种抽象的标签,其包含着的原初情感甚至被严重误读。因此,对于艺术的地方性审美经验的解读与再生产,尽管是一件令人棘手的事情,但却是不可逾越的。
第三,如何理解和阐释文化交流中的艺术。该问题主要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中,土著艺术如何被表述、生产和再生产;艺术在文化交流中产生了怎样新的形式和审美经验;我们应当如何在文化交流中理解艺术的本真性与流动性。弗雷德·R.迈尔斯(Fred Myers)在《表述文化:土著丙烯画的话语生产》*See Fred Myers,“Representing Culture:The Production of Discourse(s) for Aboriginal Acrylic Paintings”,in Howard Morphy and Morgan Perkins (eds.),The Anthropology of Art: A Read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p.495~512.一文中分析了澳大利亚土著平图琵(Pintupi)丙烯画*这是一种在文化接触与交流中产生的新的艺术形式,是原初生活在澳大利亚西部沙漠的土著人群迁移到一个叫帕普亚(Papunya)的地方,并在与澳大利亚白人发生接触后,将伴随其丰富的祭祀仪式中出现的身体装饰和雕刻绘画等传统图案转化到用木板和帆布进行绘制而成。作为一种文化接触的产物所遭致的三种批评:(1)既然该艺术在西方社会文化中流通,就必须用西方艺术界的标准衡量它,而以此标准来看,它们代表了二流的新表现主义;(2)这些土著绘画因为受到西方形式的“污染”而无法代表真正的“他者”;(3)这些绘画被当做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会不可避免地遭到腐蚀而失去其本真性。不难发现,第一种批评是用西方艺术界的标准拒绝了丙烯画,而后两种批评则是从自我宣称的土著的角度拒绝了它们。在迈尔斯看来,这些批评都属于界定“高雅艺术”的隐性实践。在其中,自我与他者的界限被强硬地建构起来,关于他者的意识形态想象依然成为西方艺术界评价的“理论氛围”,于此,一种新的艺术批评的建构就成为亟待展开的工作,它呼吁的恰恰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细描”。事实上,恰如迈尔斯评价的,丙烯画的魅力在于它们在世界上仍然是有“根性”(rootedness)的和有“地方感”的。许多丙烯画家执著于在帆布上生产他们的身份,表达他们对神圣土地的固恋与梦境,并借由它来宣告土著对于土地的权利,这种艺术的“反利用机制”是西方视觉主义者所无法获悉的。在他们看来,白人不能完全欣赏这些诚挚的激情,他们购买的只是一种抽象的意义。这表明,地方感不等同于地方,艺术家完全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表达本土化的地方感,并同时有可能获得去地方化的认同与肯定,尽管其中包含着一定的文化误读。无论如何,这种“根性”对于理解和评价土著艺术都是非常重要的。
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应如何看待土著艺术的“本真性”?它是一种被制造的根性还是根性的自然延伸?无可否认的是,“本真性”在当代艺术市场中被推崇备至,其内在的奥秘与玄机的确值得好好揣摩。克里斯托夫·B.斯特纳(Christopher B. Steiner)在《贸易中的艺术:论非洲艺术市场中的价值生产与本真性》*See Clristopher B.Steiner,“The Art of The Trade On the Creation of Value and Authenticity in the African Art Market”,in Howard Morphy and Morgan Perkins (eds.),The Anthropology of Art:A Read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p.454~465.一文中指出,艺术品展演的关键在于营建一种发现的幻象(illusion of discovery)。其中,“做旧”成为“制造”土著艺术本真性的重要介质。诸如,为了慰藉西方人对于古老年代及其特殊美学品格的渴慕,复制神圣的古色,以保证其“不为西方人所接触”而保存的“纯洁度”,就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市场运作。在其中起作用的商品逻辑是,怀旧氛围成为一种审美对象,于此建构的审美幻象为“物”增值。在此,“旧”成为一种美学品质,并作为某物能够升格为艺术品的重要条件,这种“价值颠倒”的艺术事实恰好反映了人们对于“本真性”的膜拜。然而,极具反讽意味的是,斯特纳通过几个有趣的个案表明,言语暗示与物品的放置场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人们对本真性的判断和销售的成败,诸如一个美国买家在一乡村兴奋地买下了他曾经在古董交易市场上拒斥的同样一副面具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它足以令一切关于他者的自我想象与形式主义的梦幻遭致出其不意的一击。
迈尔斯赞同瑞克·麦克斯(Michaels)如下观点:把传统性与本真性用在当代土著绘画实践上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的判断。*See Fred Myers,“Representing Culture:The Production of Discourse(s) for Aboriginal Acrylic Paintings”,in Howard Morphy and Morgan Perkins (eds.),The Anthropology of Art:A Read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504.尽管本真性是艺术的地方性审美经验的某种聚集,但它绝非静止的标签,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考量艺术在文化的交流互渗与杂糅(Hybrid)中所具有的不同意义。莉恩·M·哈特(Lynn M. Hart)在《三面墙:地区美学和国际艺术界》*参见[美]乔治·E·马尔库斯等《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阿嘎佐诗等译,王建民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7~194页。一文中,以印度库蒙女性仪式艺术为例,分析了该绘画形式在印度传统仪式、市场以及博物馆中具有的不同逻辑与意义。其中,借助市场与博物馆的现代语境,非西方物品“通过变形”而摇身变成艺术名作,它的仪式意义被悬置起来,在特殊的交换中变成了高级拍卖会和高雅鉴赏制度的对象,获得了新的市场和尊重。在哈特看来,这种转变越来越常见,它是讨论表现的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的素材。该个案实则包含了两个需要同时考量的问题:一方面,土著艺术并不必然会被西方批评体系所拒绝;另一方面,在这种通过西方艺术界“变形”升格为艺术的过程中,断裂(disjunction)*这是弗雷德·迈尔斯在分析平图琵(Pintupi)丙烯画在其制造与流通中产生的问题时使用的一个术语。是一个隐秘而重要的问题。在迈尔斯看来,此种“断裂”主要指涉艺术生产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和描述与其作品在其他场合被制造的意义之间产生的鸿沟。因此,发掘“制造”意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想象,如何重新链接“物”的原初意义及其被制造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至少,这些研究再次凸显出了语境对于理解艺术流动性意义的重要性。
如上关于文化交流中的艺术的相关探讨,将当代艺术人类学研究引向了对于在文化交流中“物”向“艺术品”转换的变形机制;艺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流动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如何考察殖民主义、市场以及西方艺术界对于地方性美学原则的重新定义;如何避免地方性艺术中所包含的情感被误读;如何动态地考察全球化背景下艺术的生产与再生产及其意义等问题的关注,这对于打破关于艺术的静态式研究范式,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第四,如何考察和把握当代艺术的多元存在样态及其审美抵抗方式。在格尔兹看来,“艺术素以难以阐释而著称于世。似乎从‘文艺’这个词被造出来,它就像颜料、声音、石头和其他与文艺素无关系的东西一样,它自己本身早已成为了超话语研究的存在了”。*[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因此,将艺术当做一种事实而非抽象的哲学概念显然是对于艺术的较好注脚。在当代,人们对于艺术的兴奋与困惑几乎均来自于艺术的多元存在性,尤其是艺术在其中与权力周旋和博弈的方式。托尼·弗洛里斯(Toni Flores)指出,过去我们倾向于将审美形式视为一种似乎不与任何权力相关联的存在,近来这样的情况已有所改变。我们期待更多关于审美与权力(power)的民族志研究,并且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区分以下几种艺术形态:自治群体的艺术、被支配者的艺术(包括底层阶层的艺术、第四世界的艺术以及被征服者的艺术)、统治者的艺术(包括上层阶层的艺术和大众商品流通中的艺术)。弗洛里斯特别强调,希望在一种政治的和经济的结构中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人类创造物,他明确将这种希望表达为,“简言之,我所期待的并不是政治人类学,而是具有真实政治性的审美人类学(a truly political anthropology oaesthetics)”。*Toni Flores,“The Anthropology of Aesthetics”,Dialectical Anthropology,vol.10,(July),1985,p.35.
伊格尔顿曾向我们提出过这样一个看似常规性却令人深思的问题:“文学理论的要义(point)是什么?”在他看来,在“纯”文学理论的学术神话中,这似乎是没有必要去操心的,甚至会认为将文学与政治相连的任何念头和行为都暗含着必然的谴责。对此,伊格尔顿指出,“所有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而“政治”在他看来则是人们将自己的社会生活组织在一起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着的权力关系。因此,伊格尔顿强调,不是“把政治拉进文学理论”,而是“政治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参见[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6~213页。事实上,政治及其蕴藉的权力始终以其隐秘的运作机制渗透于社会分类框架之中,艺术也深嵌于此,并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成为对社会关系的微妙刻写。在这个问题上,弗思曾指出,通过艺术媒介使政治性言论起特定作用已不再是新奇的事。从历史上看,艺术有一种特意诱使人们理解和转变社会秩序的目的。弗思认为,这种“政治艺术”(political art)造成的后果不容易评估,例如,苏联现实主义或者中国关于农民斗争的壁画。*Raymond Firth,“Art and Anthropology”, in Jeremy Coote and Anthony Shelton (eds.),Anthropology, Art, and Aesthetic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p.35~36.再如,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在研究非洲文化时,对有意制造的丑陋艺术(intentional ugliness)给予了特别关注,他引入“反美感的”(anti-aesthetic)这一术语来讨论约鲁巴中有意制造的丑陋面具。他指出,严格地说来,“审美的”等同于“美的”,从该视角而言,有意制造的丑陋艺术就会被排除在美学研究的范围之外。*See Robert Farris Thompson,“Aesthetics in Traditional Africa”,In Jopling, C.F. (ed.),Art and Aesthetics in Primitive Societies, New York:E.P.Dutton,1971,pp.379~381;Robert Farris Thompson, Black Gods and Kings,Yoruba Art at UCLA, Berkeley,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Chap,3/4.这种排斥是应当避免的,例如,丹尼尔·比拜克(Daniel Biebuyck)用“丑陋中的美感”(aesthetic of the ugly)来表达莱加人(the Lega)有意制造的丑陋雕塑所具有的特殊的审美价值。*See Daniel P Biebuyck,“The Decline of Lega Sculptural Art”, In Graburn, N.H.(ed.),Ethnic and Tourist Art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 346.事实上,“有意制作的丑”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多方面的指涉和功能,荷兰学者范丹姆就以非洲面具为例,以丰富的个案和图片解析了“有意制作的丑陋面具”所具有的三种功能:表征不道德的品性;引起恐惧;通过模仿小丑特征缓解人们的痛苦,或通过戏仿和戏谑的方式,反讽当局者的可笑性与荒谬性以娱乐人们。*参见[荷]怀尔弗里德·范·丹姆在2015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10月24日~26日,江苏无锡)的大会主题发言及其提交的“Intentional Ugliness in African Masks”论文大纲。其中,第三种功能是极富于意味的,于此,艺术的审美抵抗功能及其意义是潜隐的而富于力量的。事实上,在当代艺术生产与消费中,尽管人们无法主导生产,但通过有选择地接纳与再生产艺术消费方式,在其对强势者文化的疏离、“变形”与重构中同样展现出令人生畏的精神性力量与社会变革契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于审美和艺术与政治/权力关系的厘清与超越,恰恰是艺术人类学向艺术致以的最崇高敬意。
概言之,人类学批评介入当代艺术人类学,倾向于从意识形态批评和日常生活批评两个向度切入,从而展开对如下两个主要问题的探讨:一方面,揭示非西方艺术在西方审美制度建构和维系中所遭遇的后殖民待遇并发出质询,弱势群体艺术的政治潜能的激发恰恰要建立在此种审美制度批判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阐释少数族裔、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艺术的独特表达方式及其与当代文化相交流中产生的价值意义,发掘它们背后的思想与激情,以丰富和发展后殖民批评与“弱小者话语”理论的研究,并积极探讨这些艺术本身所蕴藉的社会变革的力量及其实践机制,从而使“沉默”在当代获得新的言说方式。于此,如何开启艺术人类学的诗学与政治学两个维度,无疑是当代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向度。
(责任编辑 甘霆浩)
作者简介:向丽,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 昆明,650091)。
基金项目: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阶段性成果(15ZDB02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审美人类学的学理基础与发展趋势研究”阶段性成果(12CZW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