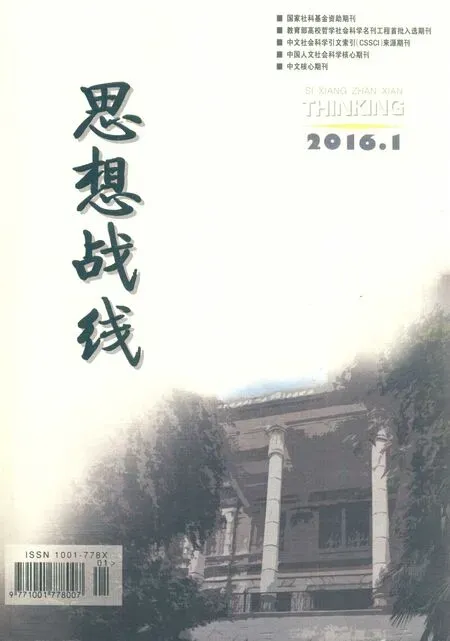“一带一路”观念对人类学文明研究的新拓展
2016-04-11赵旭东
赵旭东
“一带一路”观念对人类学文明研究的新拓展
赵旭东①
摘要:文明互动的机制并非受到文明核心区画地为牢一般的自我疆域界限的限制。文明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又重新进入到今天人类学家的视野之中,由此而使我们有机会把原来一种定点民族志的田野研究,放置到诸多形式的通道、流域、走廊以及道路的更为广阔的文明互动与流变的形成轨迹之中去考察,这便成为今日人类学视野新拓展的当务之急。需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做一种人类学的文明俯瞰,而非局限于传统人类学民族志所曾经训导我们的如何用匍匐于地上的眼光狭小的人类学。需要有与时俱进的胸怀去构建起真正人类学意义上的“一带一路”,从一种文明的关怀上去看待我们的人类学所一直孜孜以求的社会、个人与文化的那些复杂性的关系。这是人类学拓展新的研究空间之所需。
关键词:“一带一路”;文明;人类学
在现代世界一体化趋势的不断拓展中,以田野研究体现自身学科价值的人类学将面对来自一种文明观念的挑战,即宏观视野的文明观在向微观田野的研究者发出诱惑,接受还是拒斥这种诱惑,将体现中国人类学面对世界性文化转型的特殊智慧。人类学曾经自陷于某种形式的区域研究,并将其作为一种固化的研究范式,而不断推进到以民族国家为疆域范围的地域文化的国民性研究之中,而但凡超出此界限的内容,都一并概括和归类为是一种人类学的“海外研究”或“民族跨界研究”。由此而暗指民族国家之外以及超越了民族国家领土界限的那些研究对象,并不包括在人类学本土研究的范围之内。更为重要者,往往在这些超出民族国家领土范围的地域或边界的文化空间里,大多都会呈现出某种不同于其所研究的这一民族国家领土区域之核心地域的文化特征,如中国之中原文明,抑或黄河文明。而凡与此文明大有不同者,不得已都要作一种“屈尊就范”的另类处理,使之从更为抽象的概念上勉强符合于区域研究的接近主体文化特征的解释。这也就为人类学学科内部的分门别类的海外与跨界研究提供了其合法性的依据。很显然,本来可能是属于一个总体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在先入为主的内外之别的分类框架之下,被人为地区分为两个,即内部的民族国家下的文化与社会的研究,以及此一民族国家边界之外的所有其他民族国家或者文化区域的海外与跨界研究,或者是取巧于两者交界区域的独特性文化特征的研究,将其看成是内外之别的中间状态等等做法。但殊不知,所有这些划分,在人的整体性的以及连续性的活动意义上,都可能属于一种子虚乌有,人为构造的成分占多数,实际却并不存在。在这方面,中国人类学需要有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研究认识上的大突破,而借助偶遇的“一带一路”的新观念,或许可以使得这种突破变得可能并且生机盎然。
文明扩展的文化动力学
很显然,人们并不是以某个近代以来才逐渐清晰的民族国家的边界来划定和感知自己所认可的文化边界的,人们的活动是在更为宽阔的文化空间意义上不断延展开去的。这一点曾经为目光狭小的民族志学家所忽略,倒是一些早期的文化传播论者、演化论者,他们从来也没有这种国界或者跨国界的意识,只是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注意到人和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展和布局及其种种的形态的转化。很显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人类学要么机械地照搬传播论和演化论教条于中国文化的实际,要么就是完全地忽视了其存在。
而今日中国自身发展战略中所高调提出的“一带一路”观念,不仅巧遇了人类学的文明观,同时在一种文化主体性的意义上提出了自身文化与社会经济传播的取向和范围,而且还很明确地借助了“古代丝绸之路”的观念,从陆地与海上两个文化地理空间维度上,将作为并非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天下之中”的中央之国,脱胎换骨地与整个世界的文化疆域和全球一体化的努力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保持着一种和而不同的文明之间往来互动的姿态。中国因此而不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是更具世界意义的中国。中国意识的话语空间也不再是局限于有限的民族国家的国界范围之内,而是突破这个界限进入到了一种全球话语的文化表述空间之中,并与其他文明体系表现出一种彼此尊重、相互赞赏以及互利共赢的良性交往的轨道上来。*赵旭东:《中国意识与人类学研究的三个世界》,《开放时代》2012年第11期。
这种自主又包含了他者关怀的中国意识的新扩展,不仅是承载其文明的社会、个人与文化边界的拓展,同时也是其在原有基础之上的一种新的文明观的大发展,它要借此而实现的是未来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良性互动,而非那种欧美一般政治学观念所主张的文明之间的对抗性的平衡制约。这种国际关系上的抑制与平衡论的腔调,它并不是以文化包容性为前提,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文化或者文明之间的种种冲突,并使这些冲突不断地放大和模式化,进而激化为区域性的矛盾与对抗。而基于中国文化传统所构想出来的“一带一路”的观念,试图在超越“文明冲突论”上做一种勾连和弥合的努力,它的关注点肯定不是在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冲突,而是在于相互之间的互惠与往来。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在人类学遇到了“一带一路”的观念之时,它为向来以关注文明自身发展的人类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拓展视野的契机,人类学必然要成为这个时代一种新的文明观的发现者,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真实互动并彼此克服交流障碍,而实现彼此理解和相互和谐局面的完整呈现者。
很明确,人类学向来都会将人摆在其所研究的第一位,就像它的学科名称中所内涵的那个“人”(anthropo-)的要素一样。这门学科关注于人生活于其中的人类文明的全部面相,这当然不仅是指物质的,更为重要者还是指精神的;不仅是社会的,还是个人的。在文明的精神和文化的这一方面,人类可谓是占尽了先机;而在个人和其有机体的存在方面,人也不能离开其活动性而存在。换言之,人既是一种为自己创造出种种精神文化价值的存在,同时也是跟动物一般能够四处活动,并把这种文化的价值通过道路、走廊以及通道这些物质性的流通渠道不断传播出去的一种有机体的存在。很显然,作为一个身体和精神存在的个体,人们在一定的疆域范围内创造并适应了其生存的环境。随着人类命名系统的发展,我们会用某一种的类别概念来称谓这些人为某一个名称的群体,比如“汉人群体”。而作为这某一个有着自身名称的群体的人,他们自身往往又都是生活在某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范围之内的,尽管他们时不时地会有跨越这区域的活动存在。如果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画出其四处迁移的路线图,那一定是一件不大容易真正描画完整并在短期内完成的一项浩大学术工程。
并且,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在不同区域生活的人,其所构筑的文明的形态也会存在有彼此之间极大的差异,这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把与土地更为紧密联系的长时间形成的中国的乡土文明与西方世界更突出地跟海洋紧密联系的海洋文明之间进行粗略对比,便可作为例证。有着得天独厚的可以垦殖的广袤的黄土地,无意之中造就了一群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减少了四处迁徙移动的频率,并依附于这土地而生活的一种所谓乡土文明的出现和成熟;而生活在地中海、大西洋海岸边的人们,由于长期与海洋的接触,随着时间的流逝,很自然地会造就出来一种与海洋的形态密不可分的文明,这种文明不仅需要人去征服海洋,还要利用和适应海洋的种种生存环境。同样,其他的依随自然地理而形成的种种文明形态,其形成的过程也不出其右。比如,与山地的广泛接触与适应,也很自然地产生出来某种山地文明;生活于草原之上的人群,他们在长时间跟草原的接触过程中,创造出了一种跟草原生态环境极为融洽的草原文明。
但首先应该清楚的是,任何一种文明及其文化的形态都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自身往往会借助人的力量(这里既有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而不断地向某个核心文明以外的区域去做一种不间断的连续性的扩展。在这个意义上,文明的属性带有帝国的特征,即它内涵于其核心之中,只待适宜的土壤,便会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由此,它的无所不包的帝国属性,使其自身会向自己所属文明的核心地带的四周更为辽阔的区域不断地延伸出去。中国早期的“五服”观念里很自然地包含了这样一种意识,而这恰是文明并不存在一个真正边界的文化动力学的基础所在,即它不会因为种种的阻碍而停止其扩展的步伐。
不论是汉代凿通西域的“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抑或差不多同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连通,乃至今日“一带一路”观念的提出,都在暗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其自身存在的开放性。且因这种开放性而带来的交流的欲望和吸引力,从秦汉到清帝国从来都没有真正地中断过,尽管其间不乏宋代的边疆内缩以及明清短暂性的闭关锁国。但在这些政治与历史性的阻隔和封闭之后,必然又都会出现一种文化与社会交流上的开放和融通,并且可以看到一种文明与文化交流史上的闭合与开放在历史发展的轨迹当中是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赵旭东:《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发展——一种理解乡土中国及其转变的理论解释框架》,《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在一般性的认识中,作为一种闭合性而存在的中国乡村,不过是此一文明体其静态生活的一个样貌或者长程历史存在的某个瞬间,而真正能够使得这一文明体得以持续并充满活力的动力基础,恰在于其自身的核心文明特征对于其自身文明所能波及的疆域界限的不断开拓,以及在这其中主体文化在空间意义上的不断传播。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大量证据,似乎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国的文明观如果离开了这一点,也就无所谓作为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存续和发展,更谈不上由“一体”而分支、分化以及分离出来的“多元”文化形态。*赵旭东:《一体多元的族群关系论要——基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想的再思考》,《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从以黄河为中心所逐渐形成的黄土文明,进而向西南开拓而有与那个区域长期形成的山地文明的遭遇,这项工作在秦帝国或者先秦时代便已经开始,并逐渐进入彼此相互依赖和交流的状态。而历史上茶马古道的拓展,又在一定意义上将山地文明中的茶叶种植与加工,跟草原游牧文明的生活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两种不同文明之间借助一种互惠关系而构筑起来的一种依赖关系的绝好范例,并由此而维系了一条不同文明之间互通有无的文化通道的畅通,否则这条通道将归于沉寂或荒芜。
因此,文明之间的依赖或者往来互动的基础,在于相互之间互惠关系的形成。*赵旭东:《 新问题意识下的“新丝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文化转型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5年第2期。中国古代一直持续的茶马互市,其背后不仅是一种市场贸易的关系,更为重要的,它还是不同文明相互浸透而形成的彼此依赖关系下的一种良性的或者积极的互惠关系。即山地人群丰富的茶叶种植、加工与销售,以及草原丰厚草场所养育的良马资源为长期在山地生活之人日常运输所必需,反过来,经过发酵而可以长途贩运的特殊品类的茶叶,如云南普洱,安化黑茶,都成为了以肉食和奶制品为主食的牧民日常身体消化食物之所必须。这种不同文明生活样态之间关系的互惠沟通,成为了这两个不同文明之间,能够依生态环境的不同而各自保持独立,并能够长时间往来互动而未中断的根基所在。换言之,人类文明的存续一方面有赖于其不断向其核心区周边扩展的能力,也有赖于不同文明之间彼此依赖的互惠关系的养成和稳固,这一点对于理解文明的存在而言意义极为重要。但文明扩展的动力基础,是来自于人的移动性的能力,人并非是一个固定于一处的物种存在,而是四处可以去活动的并在活动中形成一种主体自我意识的存在。对于某种自然物的文化追寻,即使之在社会人群中被赋予一种价值,成为人的活动性可能的诱因,蒙古人对于金子的占有和追寻,*赵旭东:《侈靡、奢华与支配——围绕十三世纪蒙古游牧帝国服饰偏好与政治风俗的札记》,《民俗研究》2010年第2期。汉人社会对于玉石的欣赏和赞美,*叶舒宪:《草原玉石之路与〈穆天子传〉——第五次玉帛之路考察笔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5年第5期。都无意之中成就了一种游牧文明和玉石文明。在这一点上,今日的人类学更应该从人的移动性所促成的人的能动性的角度去看待人类的文明,其中就包括由此而成的道路、走廊、通道以及宽泛意义上的流域,而有关这种能动性的民族志的书写也需要在这一点上有所真正超越。
人的移动性与超越场所民族志
现代人类学自从将一种定点田野聚焦的民族志作为自己专业化模式的写作和思考的无可替代的经典范式之后,*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有两方面的忽视是为今日的人类学家所能够清楚地意识到的。这其中之一便是整体上的对于文明观的忽视,即宏观意义上的文化理解线索的缺失,即便不乏像马林诺夫斯基这样的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对于有关文明问题的种种讨论。*参见[英]马林诺夫斯基《自由与文明》,张帆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因为对于种种文明的整体而宏观的文化理解,实在很难跟有着一种固定边界的地域性的定点田野研究真正地联系在一起。很多时候,宏观的文明与微观的田野之间往往都是各说各话,顾此失彼。对于文明的研究者往往都是将自己置身于空中楼阁之中,而实地的田野研究者又无法真正跃出地域性微观视角的那种见木不见林的自我束缚和局限之外。
但很显然,对文明的理解一定是强调在地域之内却又是超越地域之上的那种辩证属性的存在。显然,一种尝试用自然实验室实验的物理学研究的范式,去理解社会中的人及其文明与文化的创造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现代人类学自马林诺夫斯基之后,选定点上聚集的民族志的做法作为自己研究的首选和惟一的方法,*参见[英]马林诺夫斯基《南海舡人》,于嘉云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它所因此而忽视的乃是那些并非能够聚焦于一个点上的对于具有文化启示性的线索追溯。*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但很清楚,人自身的可以动的行动能力,恰恰决定了其行动及意义制造的一种可追溯性。换言之,人的行动的完成,构成了其可以被追溯的一个行动轨迹,这种描记的技术在今天伴随着“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以及“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普及,已经变得轻而易举,即人的移动空间可以得到一种准确的记录和分析,微观的精细的描记成为了可能。借此,我们可以重新对人的活动或者其能动性给出一种文化意义的理解,而不再是僵化的在一点上去做缺少能动性的结构或者功能的分析。尽管人是生活在某一个确定的空间之中,但却毋庸置疑地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之间往来复去的移动,而作为有着一种行动能力的个人,他一定不会长时间地静止在某一个点上,这可能是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这种人作为动物之一所具有的移动性的属性,就像风所吹动的种子一般可以四处生根发芽,而所有的人造之物都会因为人的这种能动性,不断地由人所携带着并向四处播化出去,文明与文化的空间分布也自然离不开人的这种活动的能力和作为。
如果一个地方人迹罕至,这也便意味着它是一个没有人真正活动和居住过的地方,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文明可言,只有人存在的地方才会有某种文明并由人的移动性能力而将文明播化到其他地方。换言之,人可以通过其与生俱来的移动性而将某种文明的种子播撒到没有这种文明或者缺少这种文明的地方去。从古至今,这种通过人的行动能力而去传播文明的努力一直都未曾中断过,而这背后的根基性,就是一种人作为动物性的存在之一所具有的四处移动的能力。不论是旅行、探亲或者经商、出远门,乃至长距离的战争,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人生存所依赖的这种可移动性。但这一点往往为我们的古典的定点聚焦的民族志所忽视了。无意之中,熟悉并为聚焦民族志写作模式所规训的人类学家,把人往往无意识地界定成为是一个静止的存在,或者囿于一定有限疆域的被动地存在。似乎认为,他们属于是并没有任意行动能力的一个可以为他们所静态观察到的存在一般,他们生活在“那里”,而作为人类学家的“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任务不过是去“那里”去找寻“他们”的存在而已。而且相信只要是到那里,也就是到了田野之中,就一定能够找寻到他们,因为他们被找寻他们的人看成是永远固定地生活在那里的,即生活在固定的村庄、岛屿、寨子或者部落之中。在这方面,人类学家在注意到了人的静态的定居的能力的同时,实际上却忽视了其移动性的种种行动能力。
很显然,在人及其所构造出来的社会之中,这种人的移动性特征具备有人的本质属性,即可以肯定,一种没有移动性的人的存在是无法让人想象的。人及其所创造的文明,显然是不能脱离开此一人的本质属性而存在。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可能通过在一个点上的田野调查,而去把握作为整体的人及其社会构成的全部属性,那里只可能是我们对于人的认识的一个起点而不是其全部。针对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结构,相对而言是可以在一个有着其自身边界存在的社会中去加以定点的聚焦研究,但对于从来都是依附于人的活动性而存在的文明以及更具一般意义的文化而言,其对于借由人的行动轨迹而形成的某种文明与文化的线索的追溯,就可能会变得异常的重要。
在这一点上,文明与文化的存在显然是有别于作为结构性存在的社会的,后者如果是一种相对稳固不易撼动的结构性框架,并由此而可对其做一种超乎于个体存在水平之上的社会事实的静态结构功能观察和理性分析。那对于并非结构化存在的,且往往都是在一种流动性中演变的文明与文化而言,真正重要者,恰在于与人的移动性本质紧密关联的人造的文明与文化在人迹活动线索上的不断开拓、延展与分布,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一种人类学视野上的眼界开阔的追溯拓展,而不是极为狭窄的凝视聚焦。
“一带一路”与通道研究
恰恰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的观念,即基于一种空间拓展与线索追溯的不同文明与文化之间往来融通与纽带性的思考模式,便顺理成章地与人类学既有的文明观之间有了一种不谋而合的默契,并使得旧有的认识得到了一种新的相互具有契合性的理解,一个中国人类学的新时代恰可能因此而有一种崭新的面貌。*赵旭东:《迈向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也可以这样说,“一带一路”与“人类学”这两个各自有其自身历史传统和意义承载的历史转折关头无意之中偶联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人类学家新的理想图景的想象力空间。人类学原初的文明观念也由此而得到了唤醒和复活,并借此有了一种全新的拓展,它在当下以及可预期的未来,将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中国及其周边的世界诸种文明交织的范围之内。而传统人类学单一向度的场所聚焦的田野工作的形象,也会就此而有一种新的转变。这种转变强调在一种文明高度上去重新看待现代人类学过于将其既有研究的视野局限于“社会”本身这一维度之上的种种狭隘认识,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学自身对于人及其文化以及作为整体性的文明的种种受到后人批评且有自我反省的片面理解,这种转变同时也在人类学文明观的空间意义上的延展性上,得到了恰逢其时的把握和理解。
在一个人人可以觉知和表达的“后文化自觉”的时代里,*赵旭东:《后文化自觉时代的物质观》,《思想战线》2015年第3期。或者是一个“个体自觉”的时代里,*赵旭东:《个体自觉、问题意识与本土人类学构建》,《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我们确实有必要对每一个日渐觉醒的个体给予其周遭所处文明与文化的新解释,使他们成为既是文化的一个承载者和传递者,同时又是文化的一个发明者和创造者。文明在这样一种文化的发明和创造中,必然会得到一种新的发展和开拓,因为文明和文化一样,从来都不会停滞在一点上而驻足不前。而文化如果仅仅被认为是一种无人真正乐于去关照和体会的、死了的、僵化了的传统或遗存,那么它们的归宿,也只能是被人为地命名为“文物”而存留在静寂的博物馆中,只能是以被摆布出来的,以及固定化了的文明或者文化秩序形态而现身,所有这些最后都只能是作为一种非常片面的,对于文化与文明自身意义的理解。而且,应当清楚,文化与文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文化的文明和没有文明的文化同样都是不可想象的。与此同时,因为文化与文明与作为行动者的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紧密性的联系,那它们各自由于人的活动性存在,也一定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与形态转换之中。在此变动中,文明的种种新成就有可能被创造和发展出来,并叠加到既有的文明和文化的存在上去。而人类学家需要去真正考察和描记的,正是这一叠加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以及这种过程带来的文明与文化的后果究竟又是怎样的。
与人类学偶联在一起的“一带一路”观念,恰是在此意义上实现了对文化与文明的一种新理解,即今天的文明观念不再可能是一种对于自我封闭起来的文化边界的确认与保持,而是要在一种开放性的接受与扩展之中,去维护一种文明发展力量的强大底蕴。对此,人类学家不仅要直接去面对,而且还要迎头赶上,在一种文明拓展其自身边界的过程之中,去把握文明与文化的存在和意义,而非一般文明史学家的那种纸上谈兵的对于文明观念的怀旧式的理解,这种怀旧式的理解必然是一种对于文明和文化成长过程的带有偏差性的理解。以实际的观察为手段的人类学家,必然是要去看在这其中文化的转型以及文明形态的一些新的转变。
而文明其不同于社会之处恰在于,其各自所依附的核心媒介大为不同。就文明自身而言,它不同于社会学家从社会关系的分析里所透露出来的社会结构信息。文明与文化一样,它更多是借助于物而得以去表达自身。与此同时,还应当清楚,但凡人造之物,都必然会随着人的行动而处在一种不断的移动之中。这就决定了人类学者在研究文明之时,需要真正注意到人造物的存在,及其伴随着人的行动而发生的种种位置移动和存留轨迹。尽管之前的人类学不乏对物的研究,但那些物往往都被看成是一种近乎静止的存在,即便偶尔注意到其并非静止之物,也会因为社会整体性的理念而将其植入到社会中去,使其凝固化。而真正能够将种种的物放置在物借由人的活动而形成的移动轨迹的线索上去做考察的研究,可谓是微乎其微。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因为强调社会优先性而对于物的存在所作出的一种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判断,即并无怀疑地认为,所有的物不过是一个社会整体之中的一部分,并坚定地认为,物离开社会便似乎不能存在或者发挥其特殊的功用。但任何的物都会因为人的四处游走而处在跨越各种社会边界的游离状态之中,并且还会经过贸易、转让、赠予以及非正常的抢夺、霸占以及偷窃等的方式而频繁地易手他人或流出社会之外。
实际上,我们即便是凭借最为粗浅的观察,也可以看出诸多超出社会整体存在之物。它们要么是由世俗社会的平面结构脱逸出来而成为一种神圣之物,要么便是由社会之外作为某种神圣之物而被引进并逐渐融入到这一社会之中,成为一个社会日常生活特别的必需品或依赖品。这种物的文化意义的转化,首先使人跟物之间处在了一种专门的联系之中,也必然都会跟转运这些物品的通道和器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道在这个意义上担负起了物品意义及功能转化的媒介物功能,借一种通道连接的跨界或纽带而实现了一种文化观念的转变与勾连。
可以这样说,通道,或者更具一般意义的道路,它真正成为是实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连接与往来沟通的物质载体。它借助实实在在的物而充塞于此通道或道路之上,实现了此一道路的繁荣而非荒芜。今日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远古通道的荒废,无疑都是跟曾经的这些路上的物品因为世事的变化而不再能够充斥于这些通道之上有着密切的关联。*赵旭东,周恩宇:《 道路、发展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黔滇驿道的社会、文化与族群关系型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很显然,相比于过去的道路而言,今天汽车代替了马匹、高速公路取代了山间的羊肠小道、横跨江河两岸的桥梁取代了一个个在江河上承担运输和转运的渡口和码头。物品也被重新包装,通过极为便捷的物流体系而得到了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输送或转运。尽管现代世界体系经历有这种种的通道的改变,但有一点可能并没有真正的转变,那就是借助于各种形式的通道,物品在不同的文明体之间往来复去地被传送与消费。年鉴史学家布罗代尔对于地中海区域的各种形式道路与运输的研究足以说明这一点。*[法]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龙等译,吴模信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11~527页。如果说以前有很多东西都因为运输的困难和昂贵而成为我们社会中的奢侈品,比如茶叶、蔗糖和香料,今天这个通过运输而成为奢侈品的名目在逐渐减少,这种减少显然是仰赖于现代世界交通运输的便利和快捷。
从这个维度上去思考文化的问题,其最难于克服者,便是文化的物质性存在,它跟社会仰赖于彼此的结构关系而得以存在大为不同。很多时候,我们更倾向于将价值的观念加诸到文化之上,文化因此便被认为是某种附加上价值的精神性存在。但要清楚,这一存在其归根结底还是物质的,即文化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或者说大凡人造之物,都会在其上附着上某种的文化价值。因此,文化必然会透过物的表达而得以体现,这说到底不过又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且,凡是人造之物都会具备某一种的文化属性,即人造就了物品存在的意义。比如一幢房子,从来都不是钢筋、水泥和砖石的堆积,它背后富含有一个人对于什么是家庭的种种想象。
与此同时,人并不是孤立于这个世界的存在,他的行动坐卧、衣食住行,都会有赖于整个周遭世界的供给。人在对这个世界有某种物质性需求的行动表现之时,其也在将此一世界文化化了。文化在此意义上着实算是一套由人所装扮起来的华丽的伪装。而这伪装的基础,便是人对于分类概念的制造和转换,借此而试图去表明,但凡人造之物绝非此物本身,而是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并适合于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使用的物品。一把椅子,它是用红木制成的,我们更乐于称其为红木椅而非普通的木椅,因为红木相比其他的木材在这个社会之中被赋予了一种更高的价值,它为这个社会中的上流人士群体所青睐,所有围绕这一类器物的话语,也会从这个群体之中产生出来。坐在这把椅子上的人,总会虚幻性地以为,因为坐在它上面的缘故而着实会体认到自身存在的高人一筹。这是文化展示其魅力并能吸引人的关键所在,没有这种文化的物质性的存在,文化便无以真正去表达其自身。
因此而应该清楚的是,物从来都不是一种简单的物自身的存在。它对每一个人而言,必然是承载着某种的意义,或者经由一种转化机制而成为人们头脑之中的表征,并经由个人自我的表征加工转化而成为某种公共的表征。因此,就长途贩运的茶叶而言,它并非是简单地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经过某种加工方式而制成可以冲泡的饮料,同时它还曾经是某种在本地并不直接生产,必须要从远处不断运输进来的奢侈品。有关它的神奇功效的诸多传说,往往会引导着人们借助自我观想而去形成某种共同意识,它们直接地与人的饥渴满足的欲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湖南的安化县,那里的人们普遍在生产一种外销的黑茶,当地人实际上原本并不怎么喝这种带有奇怪味道的并非新鲜的茶叶,但是却因为其便于长期保存而能够远距离地行销到西北的游牧少数民族的社会之中去,这种茶便被称之为是“边茶”,这特别是用来指在新疆地区的茶叶贸易。据当地人说,没有这种茶的年度性的供应,那里的牧民的日常肉食消化都可能会出现问题。而安化县紧靠着湖南资江这条水系,过去发酵包装好的茶叶从安化资江的各个水运码头一直可以下到洞庭湖,再经过长江汉口而上达至汉中,由汉中再将茶叶运输和行销到整个西北地区。这条起自安化的通道也就是一条古代的边茶贸易的大通道,这里与云南的茶马古道同属于这一文明体,成为与其他文明体发生联系的必经之路。而这样的道路不计其数,人类学家能够真正辨识出来的,也不过是其中有数的几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明不是在遥远的有着固定化了的场所的那里,而是在一种由人的活动所带动的动态的通道线索之中存在着的,它们包括各种形式的人行走或者生活于其中的那些文化意义上的道路、通道和走廊。
要知道,尽管茶叶的饮用可以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质,或者说这种特质为中国的茶叶所塑造,但却并不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生产茶叶。对茶的认知和理解,往往是借助于文字和每天的饮茶习惯,使得这个文化中的每一个人,在很幼小的时候便知道茶叶对于他们的生活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是指用来冲泡的饮品,也可能是用以提神的兴奋剂;是用来交换的礼物,而且还可以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奢侈品。茶叶作为物品,它并不会因为某一个地方不生产此物而被人忽视,恰是对于茶叶的熟悉和渴求,带动了在某一个小地方生产的茶叶,可以通过一种通道打通的道路,运输而行销到渴求这种饮品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而这种对茶叶意象的塑造和熟悉,其所造就出来的一个无意文化的后果便是,凡是在中国的区域内,茶叶可谓是一种文化标志性的产品。即便是在不产茶的地方,同样能够喝到茶叶,体会到茶叶的味道。而且,这种喝茶的欲望,会因为其难于获得而表现得更为强烈和尊贵,彼此之间因品茶而产生的共鸣和观想也更为容易获得,而这些又都需要一种远距离的运输以及道路通道的凿通,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
因此,在造成这种共同性意识的诸多因素之中,对于茶文化而言,茶叶的运输一定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形成中国人茶文化认同的因素。运输使得物品离开其地方性的出产地,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区域之中得到消费、分布和被接受。而且,大凡带有一定奢侈性的物品,都使得远距离的运输成为可能。比如中国北方的茶叶大部分都从盛产茶叶的南方运来,而运到中国北方的茶叶再经过丝绸之路远去西亚、中亚乃至欧洲,而借助南方丝绸之路或者茶马古道,中国南方的茶叶又会远去东南亚以及借由“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南洋诸岛、中东及欧洲。又比如,我们今天生活里也很熟悉咖啡这东西,但这个名称不是跟中国而是跟欧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近乎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特征性的表征,在刻板观念中,就像中国人要喝茶而西方人要喝咖啡那样的泾渭分明。但要知道,咖啡的原产地显然并不在欧洲本土的任何一个地方,而是在东非埃塞俄比亚南部的卡法(kaffa)山区。在15世纪的时候,由于咖啡提神的神奇功效,商人们开始通过埃塞俄比亚北方古都贡德尔的大集市,将东非的咖啡大批量地转运到非洲西北部的苏丹,由此而进一步传入埃及以及地中海沿岸国家,并由此逐渐广播至整个欧洲。这种原本非洲的植物果实后来还跨越太平洋,在南美的巴西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咖啡由此得以在南美进行大量的生产和加工,这些无疑都是跟欧洲的殖民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布罗代尔的鸿篇巨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开篇就是谈论地中海区域的人们如何将从山巅运输来的雪保存起来,成为炎炎夏日里的一种奢侈的消费品。在这中间,意大利人学会了制作冰激凌,一位被囚禁的西班牙王子因为暴饮了雪水而毙命,还有摩尔人喜欢往菜肴上撒雪,就像威尼斯人在饭菜上撒糖一般。*[法]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龙等译,吴模信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6~27页。
但除此之外,如果没有现代便捷的运输,那就很难去想象一种外来的物品何以能如此范围广大地影响到整个西方世界的饮品文化。在西敏司试图要从阶级、身份以及宫廷文化上去理解蔗糖这种来自南美的舶来品,如何在欧洲社会中成为了奢侈品,进而成为了人们生活中最为普通的消费品的过程。他也许注意到了蔗糖的加工是从地中海盆地这个转运中心到达了北非、中东和欧洲这些地方,直到16世纪在美洲发现新大陆才衰落下去,他还注意到,以地中海为中心,蔗糖业广泛地传播到了西班牙的大西洋诸岛以及葡萄牙,包括马德里、加拿利群岛以及圣多美岛,最后才转移到了美洲。*Sidney W.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New York: Viking,1985,p.24.但他在这一过程中却可能一直忽略了现代航路通道的方便在蔗糖转运中所起到的作用,恰恰是这些新式交通运输和航路通道的开通,才使得这种变得有广泛人群的物品消费真正成为了可能并分出阶层。这是人类学的道路研究所需要去特别加以关注的。
文明及其超越性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物品运输的通道成为了某种物品可以进入到某一社会中去的一个重要的向度。很显然,一条通道可以将不同的社会形态联系在一起,它的亲和力以及融合力是其他任何一种形而上的文化融合观念都无法真正去加以替代的,并借助一条道路沿线区域性的扩展而可以找寻到不同文明体之间互惠性关系的存在。*赵旭东:《人类学与文明互动的三种形态》,《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
在此意义上,各种物品通过道路的运输与转运,又必然会是一种不同文明体其背后极为不同的文化价值存在的一种真正可去追溯的文化线索。这一线索的完整呈现,将会构造出来一种不同于人类学古典定点调查的那种聚焦的场所民族志新的民族志形态。场所民族志可谓是只有线索,而没有一种线索的完整而连续性的意义呈现,即存在一种线索民族志的缺失,而一种新的民族志,必然是在此静态的场所民族志基础上的一种动态的线索追溯的民族志。这需要我们有一种人类学空间视野的大转变,即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构造或社会关系结构的分析,而真正转向到更多从人因物的追求和转运而产生的特征性的行动轨迹的一种线索追溯上去。*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这种线索民族志的核心乃是基于启发式的问题解决而产生,它更为追求一种在动态之中的、有助于文化理解以及对于文明之间互动交流并有助推作用的诸多意义线索的发现。线索民族志更为在意多方位、多视角以及多主体地去看待世界各地彼此不同的文明与文化差异,特别会在意种种因生存环境的生态差异而形塑出来的差异性极大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宇宙观,即一种心态上的差异;注意到它们相互之间深层次的结构性差异以及外在表现上的因富于变化而表现出来的异彩纷呈的形态,并试图以民族志写作以及图像记录等多媒体的方式去呈现这些差异,并且更多是以文化和文明欣赏的姿态去展示这些差异的内涵。这种方法论的态度可以贡献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宏观战略,而且这种战略也必须是文化先行的,没有这一点做基础,文化的融通只能是转化为另一种的文化冲突。这显然并非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之中所追求的根本,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之间的融通,需要人类学家的先期走出去的田野研究,这在未来必将成为人类学家借“一带一路”之势而走出去的最为基础的努力方向。
如此,在人类学研究视野的新展开中,对于山川、河流、海洋等等,那些曾经阻碍人们去行动的自然障碍的克服所形成种种文明观念下的通道、流域、走廊以及道路的研究,就成为今日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当务之急。而一种曾经由英美主导的古典民族志的方法,无疑常规性地帮助我们找寻到了一个个细致的民族志意义上的社会形态的存在。尽管在这个方法之外,也有所谓区域或文化比较方法的存在,但经典民族志方法下的各个田野点,相互之间往往被看成是一种彼此孤立的存在,点似乎永远是点,而无法真正连成一线,更无法形成一面、一带或者一路。这显然跟人类学家的眼光,究竟匍匐在地上还是空中俯瞰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人类学的比较方法能够让我们找寻到它们彼此之间跨越一个一个孤立的点之上的某种共同性的存在,但却无法让我们看到它们之间文化意义上特征性的线索关联,以及彼此之间差异性共生关系的存在。而从一种道路与物品移动轨迹的视角去分析,这不仅可以保证一种在地的微观探究,同时也能够让我们不断提升视野,注意到更为宏大关系的存在,同时还可以真正使得我们有意识地去把握住不同文明之间隔绝、冲突以及互惠的多种存在形态的文化动力学的基础。由此,我们可能会看到传统的英美人类学的田野方法所一直习惯于忽视乃至于拒斥的宏大的文明观的视野,在这种文明观中,文明本身被理解成既是根基于一种地域文化的认同,同时又一定是要超出地域文化认同的种种限度,是在这二者的辩证之中体现其自身存在价值的。基于这样一种地方与整体的辩证,它根本上具有一种借助人的活动而向其四周不断辐射开去的能力。由此,我们才可以从所谓山地文明中见到草原文明的影子,从农业文明中又可见到游牧文明的痕迹,并且是彼此融合、相互构建起来的。而一种长时段的文明或者文化之间的往来互动、道路沟通、区域发展以及通道与走廊的打通,必然会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明互动的常态机制。
这种文明互动的机制并非受到文明核心区画地为牢一般的自我疆域界限的限制。无疑,文明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又重新进入到了今天人类学家的视野之中。由此而使我们有机会把原来一种定点民族志的田野研究,放置到诸多形式的通道、流域、走廊以及道路的更为广阔的文明互动与流变的形成轨迹之中去,而这便成为今日人类学视野新拓展的当务之急。换言之,我们需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做一种人类学的文明俯瞰,而非局限于传统人类学民族志所曾经训导我们的如何用匍匐于地上的眼光狭小的人类学。我们需要有与时俱进的胸怀去构建起真正人类学意义上的“一带一路”,即从一种文明的关怀上,去看待我们的人类学所一直孜孜以求的社会、个人与文化的那些复杂性的关系。在这样的研究空间的新拓展上,人类学家可谓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 段丽波)
作者简介: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重庆文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重庆 永川,402160)。
基金项目:①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费孝通思想研究:人类学视野的展开”阶段性成果(15XNL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