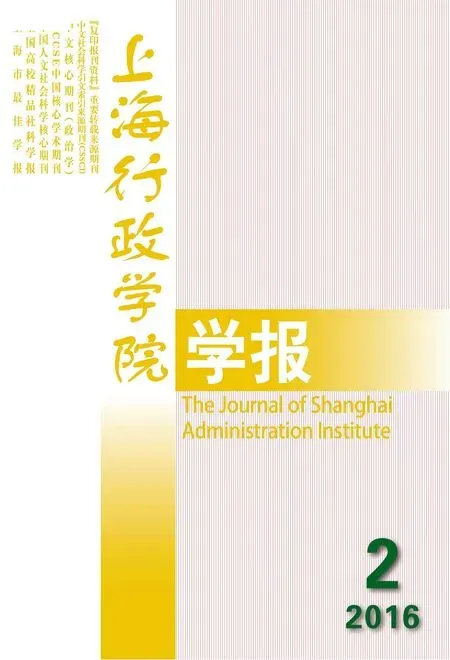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国际法路径*
2016-04-11宋瑞琛
宋瑞琛
(国家行政学院,北京100089)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国际法路径*
宋瑞琛
(国家行政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不断加深的全球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背景和推动力。全球化背景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内和国际问题相互交织,国家治理不仅需要重视国内法与国际规则的接轨,而且应该充分重视和利用国际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依据和保障。
关键词:全球化;国家治理;国际法
*本文系2014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省参与中国对下湄公河国家公共外交的路径建设研究”(项目编号:QN2014029)阶段性成果。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这一目标的确立是基于对中国当前的国内和国际实际做出的客观判断,是对中国与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做出的正确分析。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自由流转,世界市场深度融合,使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成为发展趋势。因此,既要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又要实现符合中国实际的国家治理,就不仅需要提升国家对国内社会的治理能力,而且需要提升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因而将国家治理置于全球化背景下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当前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最重要主体,但以往国家中心主义为主的治理模式,在全球化背景下却逐渐面临着难以触及和难以解决的治理危机,而国际法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际和国内双轨发展提供契合点和路径。国际法能够为国家治理走向国际法治化,协调国际和国内利益、整合国内和国际资源,从而促进改革提供思路和创造可能性。
一、全球化对国家治理的挑战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中国的国家治理是通过国际和国内两个轨道同时进行的:一方面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重新塑造国家与国内社会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缔结和制定国际条约,参与国际事务来发展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国际和国内事务的相互作用使国家的功能不再局限于对内管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成为国际仲裁的最终执行者和个人、跨国公司等参与全球治理的平台和唯一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化对中国国家治理的要求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合国际和国内资源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二是为中国发展国际关系提供制度和机制保障,而这种要求也是由全球化对国家产生的影响所决定的。
主权国家随着全球化深入而更加相互依赖,也使国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特点更加凸显。
首先,国内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增强。全球化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以及人口、资源、资金、信息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转;全球化增加了国内社会关系的国际因素,从而使国内的相关利益主体不仅从国内获益,而且能够从国际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利润;国内的跨国公司等由于活动突破国家界限,更加容易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甚至突破国家权力的限制。可以说,全球化不仅改变了国内社会关系的构成和影响因素,“也超出了国家权力的干预能力。”[2]
其次,国内问题高度关联国际问题,使国家行使主权权能受到限制。全球化使不同价值尺度和行为规则发生碰撞和融合,也使许多国内问题不断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首先,国内问题一旦产生国际效应,国家就需要在处理问题时兼顾国内影响和国际评价;其次,国内问题产生的国际效应,可能涉及多个国家参与、合作或需要调动多个国家资源,如气候问题或恐怖事件;国内问题的跨国外溢,不仅增加了问题解决的成本和难度,而且也超出了国家独立行使主权的范围,因而,一个国内问题如若处理不当,不仅会影响有关国际因素的利益,而且可能对国家间关系造成损害。
再次,国际责任和国家责任的矛盾,使国家统筹国际和国内的能力受到挑战。全球化使国家合作竞争的程度加深,其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通过双边、区域、多边条约确立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必须调动一部分国内资源用于承担国际义务、维护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等,因而也会改变国内利益分配格局;在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是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一方面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承担着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跨国行为或活动所产生的国际后果和效应,国家又必须为其提供最终保障,因而国家就面临着维护国内利益与承担国际责任的矛盾。
第四,国际因素对国家决策的影响,使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全球化使一国政府在对外决策或国际谈判中,首先会充分考虑国内利益诉求,但是也受到国际环境、国际舆论、以及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在该问题上的态度影响,以往国家在社会关系中起着引导社会价值、塑造社会文化的主导角色,但是国际因素对国家决策的影响作用,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对国内社会关系的主导地位。
要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这些问题,提高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就需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协调和整合国内资源,加强国内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发挥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地位,构建与世界的和谐关系,通过参与和制定国际规则,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
二、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中的国际法的作用
全球化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的共同特征具有跨国性质,而对这些问题的控制和解决已经超出单个国家的能力,需要国家与国家、与国际组织等一起共同应对,因而需要一套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引导国际社会中国家治理的方式和作用,而国际法具有这样的功能。
第一,国际法能够引导国家治理朝着规则化和秩序化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包括现实已达成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机制或框架,“如各种国际公约的谈判与缔结平台,以及为修改、完善和发展这些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导向机制或框架。”[3]国际法能够引导国家治理从以往注重“制度化”转向“法律化”,这种转变能够使国家治理有义务服从法律,这种服从的最终目的是要国家不管愿意与否,都应该在国际法框架下承担国际责任和解决问题。在国际体系中,国际法不仅确认并保护现状,而且建立并维持秩序、树立预期并导向该预期,国际法避免了使法律成为中心权力机构(国家)的执行工具,也在治理中增加了更多的话语主体。
第二,国际法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国际互动联系的框架。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面临着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因素影响扩大化诸多问题,因而就要求国家治理通过国际互动联系,调动国际和国内资源来解决。国际法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跨国互动联系平台和框架,并且塑造这种互动联系所追求的价值和目标,国际法所追求的公平和公正也因而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应有之义,同时也向各个国家展示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哪些价值值得提倡,哪些行为必须遵从国际规则,国家治理可以根据这种框架或思路调整国家内部利益和解决国内问题的国际化。
第三,国际法所追求的理想价值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思路。“法律在国际法上的自然延伸就是国际法治,而国家治理法治化也是国际法治的重要部分。”[4]国际法治所追求的“善治”包括:在立法上,注重专业和民主相结合的方式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不仅能够实现法治科学化,而且能够缓解不同参与主体矛盾,法律规范的至上性能够给予不同法律主体平等的参与和权利;在法律执行和责任上,所有的法律关系主体都应该遵守法律规范,积极运用法律方式解决问题和国际争端,“经过法律确立的归责原则与方法被严格遵守,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得以追究。”[5]首先,国际法追求“善治”,重视多元主体的观念能够改变以往国家治理认为国家全能的思维惯式,国家仍然是国家治理的首要主体,但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仅是政府现代化,而且应该包括社会各方面的现代化,应该关注国家、政府及社会相互之间的作用,体现国家治理的民主性,通过国际规则整合国际因素,也能够使国家主权权能在允许的范围内解决国内问题的国际化;其次,国家面对跨国问题时,国家行使主权的范围是有限的,要想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就必须注重问题涉及的国家、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主体,就必须通过国际社会这个平台,遵循国际通行规则,而善治所提倡的通过法律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各个国际主体都必须遵循法律规范的价值观念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相符合。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与国际法的内在逻辑
第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需要国际法。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是国际法的重要内容。国际法既包括国际法在国际层面的制订、遵守、解释和适用,也包括国际法在国家层面的遵守、解释和适用,因此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不仅是中国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践行国际法(条约、规则等)的重要内容,更是关系到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和维护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第二,国际法的目标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的目标一致。
首先,国际法提倡的民主是国家治理追求的目标之一。2002年《联合国千年宣言》中的内容就充分体现了国际法民主的价值取向,[6]这种民主体现为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决策程序和内容的科学性、更加透明的知情权和立法程序等,这些正是国家治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内在要求:“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7]在立法上要改变公民参与立法不够、社会组织作用不强的现状,推进立法工作民主化,在立法过程中征求各方面的意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立法,通过立法培育社会关系。
其次,国际法提倡通过法治途径实现发展、合作与共赢,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交和海外利益维护的重要路径。国际法治本质上是由充当普遍规则的国际法作为判断国际事务是非的标准,从而实现国际社会的合作共赢。“通过广泛和持续的努力创造共同的未来,才能使全球化充分做到兼容并蓄,公平合理。”[8]国际法的制定、解释和适用,都要有利于这些目标。而全球化要求国家治理应该发挥国家参与国际事务,提升统筹国际和国内事务的能力;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深入,使中国的国家利益外溢至海外,海外利益和国际利益平衡都需要通过国际法规来完成,用国际法来指导和厘定外交关系,应是国家治理在全球化背景中的发展方向之一。就是要“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9]
再次,国际法追求平等公平,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内在需要。国际法提倡通过国际法规制国际关系,实现国际关系的公平性。平等互利、和平解决国际争端、[10]共同承担国际责任、[11]主权平等[12]等国际法原则都体现出国际法追求平等公平的价值。中国的国家治理在对外交往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其宗旨就在于相互平等,维护国际法治,并且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及以事实为准绳的国际法为国家行为依据。
四、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国际法路径
全球化对国家治理的挑战,“凸显了国家在公共问题解决中的不可缺性,国家在全球交往中的整体性也更加突出。”[13]各个国家也主动或被迫地参与到国际体系中,并将国际关系因素纳入国家治理考虑的范围之内。对内,国家治理需要面对国内社会关系的异质性,根据国际因素对国内社会关系进行相应协调;对外,国家权力受到国际因素的挑战,国际因素在国家合法性构建中的影响更加明显,这就迫使国家更加注重利用国际规则对其国际资源进行整合。因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不能忽视国际法的作用,应该充分利用国际法增强国家治理的法治化程度。
一是参与国际法的制定。首先,在规则制定中应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资源与其他国家展开对话和沟通,区分不同的谈判对象,了解各方的共同利益和不同利益诉求,通过不同的谈判策略和方案,既要坚持自身原则维护本国应有利益,也要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其次,加强本国法律制度与国际规则的融合。加强国际法的研究与中国外交实践的联系,在对外实践中如对外投资、跨境服务、人口流动等领域适时在谈判文本中融入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利益诉求。如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中,中国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法律文本反映自身利益诉求。再次,提升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论贡献,增强中国在国际法治领域的影响力。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尽管中国也积极地参与着国际事务,但在国际法治价值、国际理念、国际规则的创设和引导方面仍落后于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应该注重提高中国在国际立法中的参与和贡献,注重提升中国在国际立法中的影响力,在国际立法中反映中国的利益诉求,通过参与国际立法的方式和坚持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思维,引领处理国际关系的规则、理念和秩序。
二是对国际法的践行。约定必守是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国际条约法中也重申了这一原则,联合国宪章序言中也明确要求,“缔约国应该尊重由条约和其他国际渊源引起的义务,因此各个国家有遵守和执行国际法的义务,但是国际法的遵守和执行必须依赖于各个国家的国内法体”[14]。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定和执行也不能与国际法相违背,从国际法实践来看,国内法的一些概念常常为国际法所采纳,如国际法上有关领土、条约等原则在不同程度上来源于罗马法;主要的国内法也可为国际法院或法庭所适用;在国际争端的解决中,国际法庭有时为了解争端的法律背景,首先会对相关国家的国内法进行研究,并在其国内法中寻找争端解决中可以引证的内容和原则。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需要将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联系在一起,“加强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建立定期评估修改机制,从而促进国际法在国内行政机构的有效实施。”[15]其次,运用国际规则解决国际争端和维护海外利益、协调国际关系。我国是诸多国际条约的缔结国,因而可以通过这些条约为国家对外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近几年美国常常以国际规则和国家安全审查为由,限制我国的海外利益拓展,而通过国际法途径维护国家利益也是对国际法践行的重要方式。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海牙公约、多方争端仲裁规则适用指南、联合国宪章、国际法院规约等都为国家解决争端、协调各国国家利益提供了依据;对国际法的践行,也是国家展开对外行为、解决国际事务能力的重要体现。
三是对国际法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需要国际法作为国家利用国际资源的触角,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能否准确和专业地制定和践行国际法,需要建立在对国际法准确和深入的认识上,以及培养专业的国际法人才。“提高国际法人才在行政、外交实务部门中的比重和作用,”[16]在政府部门、企业与教学科研机构之间构建畅通有序的渠道,推动形成国内与国际、官方与民间、企业与教学科研机构的良性人才培养的互动模式。
四是顺应国际社会重视司法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适度调整国家立场和策略。中国惯用外交形式解决国际争端,但是外交形式过于灵活,对国家之间的利益和关系的约束性较差,而国际法具有强行法性质,具有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公认不许损抑、不得随意更改的特性,因而对于解决国际争端具有较强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我国以往解决国际争端惯用协商谈判等外交形式,对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国际争端一直持审慎态度,而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也逐渐在区域和双边投资条约中加入了接受国际仲裁的内容,但是在实践中这些内容常常流于形式,中国应该适当地调整在适用国际司法的立场,用国际法作为衡量和评判国际争端的标准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保障。
五是在国内层面上建立和加强与国际法相适应的保障机制。与其他国家相比,尤其是在对外贸易关系中,国内法制建设与国际法的衔接还远远不够。例如,美国为维护其海外利益,国内制定了专门的《外国援助法》[17]、《经济合作法》[18]等法律,旨在为其公民或公司在对外投资中免受征收、战争、国内动乱等风险提供专门的法律保障,以衔接国内和国际法的要求,其次,在诸多国际条约中如《多边投资机构担保公约》[19]、《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20]等都有对外贸易和投资利益的法律保障和风险承担,中国也是这些国际条约的成员国,却极少利用其中规定和制度维护海外利益。在国内层面上,一方面,中国可以建立完善国内立法,对已经不合时宜的法律适度修订,加强国际法涉及但国内法还较为欠缺领域的立法建设;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等的沟通协作机制,尤其是发挥国际性社会组织在传播国内法律理念和规则,参与国家与全球治理事务,搭建国内和国际社会桥梁中的作用,使非政府间社会组织“与主权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一道成为了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角色”[21]。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国家治理,应该充分发挥中国在国际法治中的作用和影响,通过社会组织对国内法律体系的国际宣传,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优势,以及其在国家公共外交中、跨境环境治理等领域的作用,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等积极参与国内相关立法和国际事务管理,与主权国家一道成为国际法治的建设性合作者。
五、结语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中国家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全球化对国家治理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国家主权权能的内容和范围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处理能力与对国内社会关系的协调能力同样重要,甚至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处理决定着国内问题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但是在国家治理中,主权国家仍然发挥着社会组织和个人无法比拟的作用,仍然是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主体和国际规则与国际谈判的主导,任何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经过主权国家的同意;此外,国际组织的重大决策也需要通过作为成员国的主权国家的一致商议和同意,可以说,主权国家是国际组织作用和权力的主要来源,“国际组织如何发挥作用,发挥何种程度的作用,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都是由作为成员国的主权国家所决定的。”[22]因而,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中国家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
增强国家治理的多元开放是全球化对国家治理提出的内在需求。首先,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对外开放性。全球化直接导致了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但是这种互动关系是国家治理必须所处的基本环境,也导致了国内和国际问题的相互关联和作用。因此,国家治理既要为应对这些问题协调国内资源,又要为解决这些问题动员国际资源,需要承担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的责任。其次,国家治理在动员国际资源时必须在国际规则的框架下进行,才能够既符合国际社会的价值和标准,又能够为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的接轨提供保障和创造平台。其次,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多元性。国家治理可以是多中心的,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政府在治理结构中仍居于重要地位,但不是唯一的,国际和国内社会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都能够不同程度地为国家治理提供环境、资源和机制。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应该具有法治性。国内问题国际化需要综合利用国内和国际资源来解决,而国家的一切对外行为不仅要遵循国家的对外政策,也要符合国际规则的要求。因此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不仅需要更多地引进、吸收和借鉴,或者学习国际社会的规范和制度,服务于本国的法治建设,而且应该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时,国内立法上也需要与国际规则相一致,实现与国际法的接轨。
参考文献:
[1]参见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杨雪冬.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治理[J].理论研究,2014,(6).
[3]刘衡.国际法之治:从国际法治到全球治理[D].武汉大学,2011.
[4]何志鹏.国际法治:全球化时代的构建[J].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
[5]何志鹏.国际法治:现实与理想[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65.
[6]参见《联合国千年宣言》第25条内容:“做出集体努力,以促进更具包容性的政治进程,让我们所有国家的全体公民都能够真正参与。确保新闻媒体有发挥其重要作用的自由,也确保公众有获取信息的权利。”
[7]参见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8]参见《联合国千年宣言》第5条。
[9]习近平在2014年6月28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 0628/c1024-2521html,2014-06-28.
[10]参见《国际法原则宣言》中“一国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其与他国国际争端,避免威胁国际和平、安全和正义”,“国际争端应根据国家主权平等之基础并依照自由选择方法之原则解决之……”
[11]参见《国际法原则宣言》中“每国均有责任一秉诚意履行其在依公认国际法原则与规则系属有效之国际协定下所负之义务。”
[12]参见《国际法原则宣言》中内容:“各国一律享有主权平等。各国不问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性质有何不同,均有平等权利与责任,并为国际社会之平等会员国。主权平等尤其包括下列要素:(a)各国法律地位平等;(b)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c)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之人格;(d)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e)《国际法原则宣言》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f)每一国均有责任充分并一秉诚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
[13]杨雪冬.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治理[J].理论研究,2014,(6).
[14]王子妍、罗超、李何佳.国际法治的革新者——中国的角色转换与策略[J].五大国际法评论,2012,(14):1.
[15]王子妍、罗超、李何佳.国际法治的革新者——中国的角色转换与策略[J].五大国际法评论,2012,(14):1.
[16]王子妍、罗超、李何佳.国际法治的革新者——中国的角色转换与策略[J].五大国际法评论,2012,(14):1.
[17]美国的《外国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1961年通过,并且同年设置国际发展署,专职监督并执行美国海外援助和私人投资。
[18]美国的《经济合作法》于1948年3月31日通过,是美国政府专门提供货币兑换的担保法律。
[19]《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简称MIGA),1985年10月11日通过,1988年4月12日生效,中国是MIGA的创始成员国,依据该公约设立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是世界银行集团的成员和国际组织。该公约旨在鼓励成员国之间,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成员国融通生产性投资,并致力于促进东道国和外国投资者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为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私人投资提供担保,以加强国际合作。
[20]如《多边投资机构担保公约》中第2条(a)款中规定“一会员国从其他会员国得到投资时,对投资的非商业性风险予以担保,包括再保和分保”;第11条(a)款中关于承保险别的规定“本机构在不违反(b)和(c)款规定的前提下,可为合格的投资就因以下一种或几种风险而产生的损失做担保”。《国家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1974年12月12日通过)中第24条中规定“所有国家有义务在其相互间的经济关系中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特别是所有国家应避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第2条(c)款中规定“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在征收国有、征收或转移时,应由采取此种措施的国家给予适当补偿……”。
[21]曾令良.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J].中国社会科学,2011,(2):35.
[22]朱景文.全球化是去国家化吗——兼论全球治理中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6).
(责任编辑矫海霞)
The International Law Path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Song Ruichen
Abstract:The deepening glob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background and impetus of national governance.Globalization puts forward new challenges to the national governance.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are intertwined, national governancenot only needs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domest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but also should maximize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o that can provide an basis and security for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Keywords:Globalization; Nation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Law
作者简介:宋瑞琛女(1985-)国家行政学院科研工作站博士后
收稿日期:2015-12-2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6)02-0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