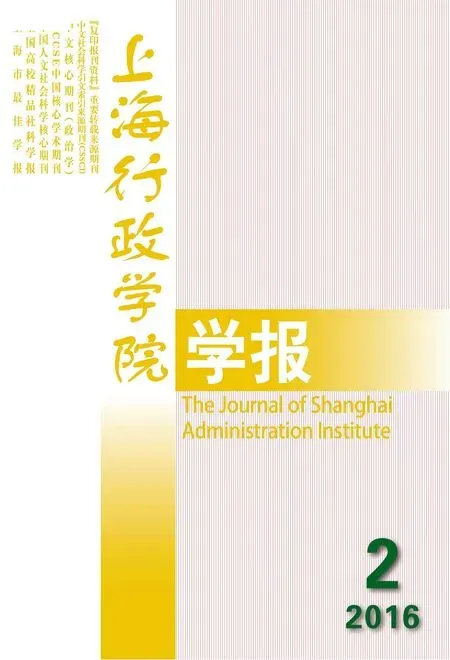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
2016-04-11郁建兴
关 爽 郁建兴
(1.清华大学,北京100084;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00721;2.浙江大学,杭州310058)
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
关爽1郁建兴2
(1.清华大学,北京100084;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00721;2.浙江大学,杭州310058)
摘要: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社会建设,促进社会转型,实现社会发展和良性运转,构成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通过分析和评估社会治理发展的政策脉络和演变逻辑,以及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治理改革与创新,可以看到,“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一发展模式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国家角色的转变与主动变革。当前,社会治理的发展已显现出制度化、法治化的趋势,但并没有真正成型。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缓兵之计”或“权宜之计”,而是兼具制度化与策略性。未来中国社会治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关键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转变,从而积累社会治理的积极因素,推动社会治理的有序发展与良性运行。
关键词: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发展模式;治理创新;法治
郁建兴男(1967-)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社会建设,促进社会转型,实现社会发展和良性运转,构成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考察2002年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党和政府不断更新执政和发展思路,从理念、价值、内涵、制度建设与政策设计层面,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推进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这构成了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问题重要的政策背景,表明党和政府已经开始从深层次上重视转型期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组织与制度环境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现实路径。当代中国正处于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的发展阶段,这种发展的阶段性表明社会治理发展的动态性、过程性与复杂性并存。[1]基于这一判断,本文旨在刻画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整体图景,致力于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变迁进行总体描述和概括性分析;同时,探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发展模式的特点。通过系统梳理社会治理的历史发展、政策演变与体制机制创新,本文提出“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以此概括和描述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与阶段性特征。
一、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发展模式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变迁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治理模式的热议,并从善治(good governance)角度评估中国治理绩效。在描述、概括与解释中国治理模式变化的研究中,由于关注点不同,已有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比如王绍光发现,随着公有制逐步退却,国家计划让位于市场力量,但与此同时,政府依然以制定标准、审查、监督和采取强制措施等“监管”方式积极介入国家的各种经济和社会事务;政府的控制模式并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改变,变成了一个新型的监管型政府。[2]与此观点不同的是,社会治理集中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合作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善治(good governance)等概念[3],用以描述当代中国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关系有助于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有学者认为“以社会和公民为本位,以公共服务为根本目标”、“市场化、社会化,与非政府公共机构甚至私人部门合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行为模式和政策手段[4]。还有学者系统考察了中国改革30年整体治理方式的变化:中国以治理为中心的改革,体现在从革命到改革、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政治协商到协商政治、从政治国家到公民社会、从政府统治到社会自治、从政府管制到公共服务、从集权到分权、从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从阶级斗争到利益协调、从传统决策到现代决策、从惩治腐败官员到监督公共权力等十二个方面。[5]总体而言,中国治理改革的目标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6]由于中国兼具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特征,同时具有广袤的国土和显著的地方差异,因此呈现出“治理的中国品格”,即国家主导的选择性品格和渐进演化的适应性品格[7]。
作为一种学术反映,国内外相关理论探讨为本项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背景。遗憾的是,当我们求解“如何认识与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领域的复杂性”这一议题时,已有研究成果显得并不充分。
第一,学者们尽管都从不同的侧面描述和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现实,但现有研究都无法全面展示中国社会治理领域的发展状况与复杂图像。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两重性和复杂性,即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8]。这势必会给中国的社会治理带来极大挑战与治理难度,也就决定了社会治理实践的复杂性、创新经验的丰富性与面临的现实挑战性。从社会治理实践来讲,各个政府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多有“各取所需”式的推行。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已有研究都难以完全捕捉、概括和描述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领域丰富的实践探索,也难以涵盖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实践的多样化、复杂性与发展的不平衡性。
第二,已有研究倾向于探讨国家与社会在社会治理某一具体领域的权力博弈,进而评估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与模式。然而,相关研究通过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行为解释为策略性互动,进而得出社会治理是国家维护政权合法性与社会稳定的“权宜之计”,这一方面忽视了近年来国家试图将化解社会冲突与推动社会发展纳入制度化框架的努力;另一方面,低估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对社会治理进步带来的深刻影响。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合作治理取向意识到二者确实存在着合作基础,但这种合作基础过于实用化。更重要的是,现有研究较多定位于研究社会治理对中国未来民主化进程的影响,而忽视了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的关注。
二、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
从历史演变与政策发展角度,梳理社会治理作为国家一项重要政策的发展脉络,目的在于分析社会治理的政策话语特点与演变的历史脉络。
(一)社会治理的政策脉络:从策略性运用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最早提及“社会管理”一词,并将其作为政府的一项管理职能。由于在这一时期,推动经济发展成为国家建设的首要目标,因此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管理”真正成为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的高频词,是在党的十六大之后。这时,国家强调通过创新社会管理,发展社会政策,协调不同利益群体间关系,并凝聚、吸纳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秩序,提供社会保障,激发社会活力。比如2011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系统提出了“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标本兼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社会建设目标;十八大报告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并强调以法治来保障社会治理主体间权责关系。此后,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表明党和政府开始重视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与组织结构支撑问题。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并在此目标下首提“社会治理”,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进而,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力图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可靠的法治保障,其中对“依法治国”的系统论述,不仅呼应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新目标,更推动了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和升级,为完善社会治理的法治框架奠定基础。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阐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努力方向,包括继续深化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等重要内容。进一步地,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可以看作是国家推动社会治理的发展将从宏观的制度安排、体制改革转向微观的、具有操作性的机制建设。
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主义盛行,市场转型与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不稳定、不公平的现象日益突出。为此,针对市场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国家必须回应这一挑战。因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成为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首要目标。这也就能够理解国家最初提出社会管理,其基本功能在于维持社会秩序,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由此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管理”一词的策略性运用。但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进而,随着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深入,范围更广阔的社会经济方案,如减少贫困、消除地区不平等、提供福利等会大大增加社会基层对资源和信息的要求[8]。况且,社会力量的成长已经凸显出其在协助政府履行社会职能方面的优越性。这些变化对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重塑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更要关注社会公平和社会建设,提高民生福祉,重建社会秩序,并为社会创造发展空间,以建立合法性的新基础。由此,国家不仅在政策文本首次以“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更将推动社会治理的执政目标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二)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治理改革与创新
通过梳理社会治理的政策脉络可以看到,新的政策导向表明社会治理成为国家发展与国家治理的战略性目标。国家自身有了自上而下推动社会治理的要求,由此社会治理成为中国新的政治话语。进一步地,通过梳理和评估近些年国家主要的治理改革与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行为,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路径。
1.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重新设定权力边界
2004年以来,中国行政改革聚焦于行政体系的法治化、规则化和标准化。然而,由于政府的行政范围过大,职能范围过宽,科层化的技术治理改革只触及了行政体制中的工具方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行政权力运行的布局和机制,[9]从而也就无法实现提升行政效率、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以及社会管理职能履行的改革目标。在涉及政府诸多行政体制改革的清单中,行政审批制度可谓是关键一环。作为国家治理与政府管理的重要方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转变职能和机构改革的基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涉及简政放权,通过科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行政审批程序,规范政府权力运作,并在此过程中协调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等多重关系。
这种“政府之手”无处不在的管理方式,经历了从取消到调整过多、过滥的行政审批事项,向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法制化建设深化,再向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三方权力边界、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建设的逐步深化等阶段。[10]并且,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行政审批改革项目日益多样化;地方政府也会在中央政府正式启动改革之前,率先突破制度阻碍,自发进行改革尝试,比如海南省海口市行政审批改革的“三制”,广东省深圳市、浙江省宁波和金华等地陆续建设的行政服务中心[11]。
在此基础上,职能转变是历次国务院机构设置变革的核心和亮点,其改革呈现出明显的两段论特色:第一阶段的重点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第二阶段的重点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12]由此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通过行政审批等行政体制改革,国家不仅重新设定了自身权力行使的边界,进一步创造、规范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制度空间,更通过政府职能转变,让社会力量承接一部分社会职能的治理方式,为其提供行动和发展的可能性。
2.逐步推进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为社会力量释放行动空间
此前,导致社会组织管理体制饱受诟病的当属“双重管理体制”。这种基于政治稳定与行政管控考量的管理制度,不仅在登记、监管等方面存在很大不足,而且极大地限制了社会组织的活动范围、行动空间与作用发挥,比如这种管理体制带来的过浓的行政色彩,使得在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政府简政放权的背景下,行业协会商会骤然承接政府“交还”的职能,往往并不具有相应的治理结构和组织能力[13]。
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在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制度、发展环境和监管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比如广东省社会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其超前性在于,社会建设要在省一级层面,协调各个部门,对社会组织进行全面培育和扶持、落实优惠政策,而不再局限于民政系统内部。[14]并且,中国政府在对社会组织的吸纳能力、对社会组织管理重点的分化、对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化水平、对社会组织管理手段多元化等几方面的监管水平有了明显提升。[15]针对社会组织在实际管理和功能发挥方面面临的困境,中央政府不仅吸取了地方层面的改革经验,更要求主动变革,随即而来的便是政策的出台、规章条例的修订工作,以及社会组织双重管理向直接登记转变:比如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更提出在2017年前形成这一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时间安排;十八大之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有了重大突破,即由原来的政府主管部门和民政登记部门的双重管理向直接登记转变。并且民政部正在修订《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将进一步消除社会组织直接统一登记的法律障碍。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这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来讲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外,除了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都已经得到较大改善,我们发现,国家开始逐步支持某些类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并逐步放宽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范围。比如2014年12月18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其重要意义在于这是我国慈善领域第一个以国务院名义出台的规范性、纲领性文件,并且鼓励兴办、大力发展各类慈善组织,以扶贫济困类项目为重点,加大政府财政资金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力度。
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92年,社会组织从无到有、从点到面、数量激增;第二阶段从1993年至今,是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和新的发展时期。[16]从数量上来看,这表明随着中国治理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进一步转变职能、推动社会治理发展的改革需要,国家已经意识到社会力量在治理格局中的重要性。
3.积极发展协商民主与合作治理,增强国家吸纳能力与社会参与能力
现代社会治理内在要求将公民视为治理主体。此前,社会管理制度的高度技术化以及对民众的区隔化使得社会碎片化严重,导致个体组织化以及组织化地参与社会管理及社会建设的能力必然萎缩。[17]近些年,国家逐步探索国家(政府)与社会主体进行多样性合作的可能空间,并建立或完善对于各类社会主体的支持和培育机制。比如国家对协商民主已有发展共识,例如十六大报告指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十七大报告指出:“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此外,国家通过政治吸纳,逐步增强体制的适应能力。比如国家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增强自身的吸纳与调适能力,借助协商制度实现对社会利益的整合。国家政治系统的开放性也使得公民或社会组织有机会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有研究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层民主,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公民协商呈现出积极发展态势,尤其是以温岭“民主恳谈会”为代表的中国基层、地方公民协商等协商民主机制,已经构成了协商民主经验的重要来源。[18]新近研究表明:中国会有意推动公民公开表达不满,增强信息传输功能,从而有助于公共政策的调整,维护国家的稳定性。[19]并且,近年来,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主要推动力的社会治理格局逐步形成,通过建立共治机制的方式寻求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治理的可能性,并提供相应的制度合法性与现实路径,比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的参与式治理等等,逐渐成为社会治理改革与创新的新内容。这就意味着,国家在试图探索制度创新,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治理过程,并积极培育社会主体的参与能力。
4.国家通过完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增强调解能力,为社会释放参与空间
由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和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和社会不稳定日益突出。这不仅需要国家建立和健全利益表达机制,进一步释放参与空间,听取民众诉求,还需要增强自身的调解能力。因此,可以看到,国家正在努力通过完善正式的调解机制和利益调节机制,利用和开放制度化沟通渠道和制度框架,修补碎片化的矛盾冲突解决机制,疏导社会矛盾,增强自身处理社会危机的调解能力。比如有研究指出:通过工会内部的上下联动、法律援助促成和解、劳动仲裁加强庭外调解以及法院鼓励诉前联调等调解机制创新与整合,2006年以来国家推动的大调解模式成为一种高度制度化和常规化的社会治理机制,显著地提升了国家对劳动争议的调解能力。[20]陈峰教授的研究指出:作为具有国家代理者和工人利益代表双重身份的工会组织在对待工人维权运动方面,也已经开始有选择地支持工人们的经济要求。[21]除了通过各种调解机制缓和社会冲突和社会抗争,研究发现,近些年,国家更逐步依据法律与法治的成熟来规范社会治理中的各种关系,以司法形式达到矛盾调处的目的。2014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要求健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努力形成依法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合力。这被认为是以法治方式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方式。由此可以看到,国家正在通过矛盾调解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正式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法治治理,增强自身调解和调适能力的同时,也为社会力量释放参与空间。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话语转变与政策演变,凸显了社会治理从策略性运用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变过程和基本特征。进一步地,通过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主要制度变革与体制机制创新行为,不仅推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积极互动,而且社会力量在参与空间、行动空间和发展空间都获得了扩展,从而推动了社会治理的发展。由此,在中国社会治理领域,国家的角色和作用也从改革前资源垄断的主导地位向以政策方针、制度建设引导为主的国家主导地位转变。并且,近些年,国家在政府权力、社会组织、公民参与以及基层自治等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进行治理改革;地方政府层面也出现一批旨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培育社会力量的创新实践。概言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其主要特色在于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以治理改革、制度建设与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等方式,推动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并且,地方政府推动的社会治理创新也逐步形成累积效应,进一步加速了走向社会治理的进程。因此,社会治理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中国应对社会问题的策略和政策工具,它已不再只具有工具意义。事实上,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发展,已在诸多领域通过调动社会自身的能动力量,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治理活动,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因此,认识和理解社会治理,应该突破社会治理的工具意义和价值目标理念。社会治理已经从政策走向现实。由此,我们将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概括为“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
三、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的特征
“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发展形态和发展阶段的描述和概括,其前提在于国家在社会建设中的角色演变,构成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驱动力,主要体现在:国家积极、主动推动社会建设,具有自上而下构建社会治理的要求;国家角色从直接控制社会转向制度提供者和协调者;国家适应社会发展趋势,在制度体制内追求变革,主动做出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转型;国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必不可少,它必须在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的前提条件下,对社会自治提供需要的资源份额与有效的制度供给[22]。因此,国家主导,从根本上讲是强调国家在制度供应和安排中的优先性地位,以及决策优势在社会治理中具有的关键性作用,从而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以及社会力量的成长提供合法空间。这除了要依赖于国家角色的转变,更依赖于国家提供社会治理发展所需要的宏观制度安排,不仅能够促成国家与社会在职能领域的有效合作,并且为培育社会力量提供相应的制度支持。“国家主导”社会治理的优势在于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力量推进的现代化发展和转型的国家,国家权力能够创造出权威、秩序与活力的内在统一[23]。这不仅使得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预设性,有助于加速社会治理进程,更确保了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这种模式的合理性在于,由于现阶段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较为欠缺,社会成长所需的组织和机制建设都不健全,影响社会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提升,因此还需要国家给予扶持和能力培育。
“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的治理形态表现为国家能够较好地回应社会诉求,允许并引导社会力量发挥更大作用,并且国家与社会在应对社会问题、履行公共性职能方面逐步确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且,政府有意引导和扶植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民众的参与,政府与社会开始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和格局。[24]基于此,“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在于国家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主导性作用,这种主导性作用一方面表现为国家不再直接控制社会以维护管制的稳定性和效率,而是通过国家建设、各种各样的政策、发展规划与社会治理改革积极回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挑战,并且从中央到地方都会出台层级不同、适用范围不等的社会治理目标与社会建设路线图。同时,国家承认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合法性与可能性,认可社会力量在承接政府职能、协助政府履行相关职能、满足公众需要方面优越性,允许社会力量通过正式的制度化渠道表达自身利益。“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强调了国家主导的优先性以及社会发展日益走向良性发展与制度化的趋向性。
然而,社会治理模式并未真正成型。原因则是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发展模式下,社会治理的特点在于兼具策略性与制度化,反映了国家在实现维持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之下,一方面要策略性应对社会的不稳定现象,对社会实施间接的控制与监管,也体现其致力于将社会冲突的解决和社会发展纳入国家正式的治理体系,以推动“积极的社会治理”①的实现;另一方面社会也在国家为其划定的制度边界和策略空间内积极与国家进行互动,从而实现自身目标。因此,“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并不排斥社会力量的地位及其积极行为:中国改革不仅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创造多元社会主体和复兴社会主体性的过程[25]。由此,国家与社会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然而,中国社会的成长过程“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压力下,国家不断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权而又以新的形式继续保持对社会的控制的过程”[26]。这反映在即使创新实践层出不穷的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并非完全自主,而是在政府划定的议题范围及特定环节中参与。[27]有些地方政府随意转移职能,不但没有推动社会组织力量的壮大与能力拓展,反而挤压社会发展空间,不利于社会组织成长。这也进一步说明政府与社会的互动缺乏有效的政策框架与法律框架的约束,难以形成法治基础上的有效的治理体系。而且,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关系并非预设两者的平等关系。即使最近几年被认为是社会治理领域重要创新的“大调解”模式,其调解的高度选择性以及柔性疏导策略的特点,导致这种模式走向“调而不解”的困境[28]。因此,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与国家并不处于平等地位。国家有意愿、有动力和有能力去推动一些治理创新,但同时也构建了一个由国家实施管制、进行监督的社会治理格局。
四、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未来发展: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转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治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中予以阐释,具有重大意义。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和国家建设是相辅相成、相互交织的过程。首先,从价值目标上来讲,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在于“让社会运转起来”,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有效对接贯通、良性互动的过程,[29]需要遵循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与运行逻辑。推动社会治理的发展,需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壮大,以及制度的整体设计和系统改革。这不仅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需要国家治理的支撑,更涉及国家如何融入到社会发展的问题。其次,从现实发展来看,在社会治理纳入国家整体规划与建设的当下,必须确立这一模式不是国家或政府对社会的单向、简单的管理和强行控制。社会治理的现实发展已经表明,社会治理不再是一种价值倡导,它在运行中已具有实际意义。社会治理创新与改革不仅呼应了国家层面对社会治理的支持,也在不同层面共同解释了中国的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紧密联系。再次,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市场模式还是社会模式,其发展都是不充分的。市场和社会模式的滞后同样会影响国家治理的良性发展。同时,在市场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形势下,国家模式的控制与包容能力会面临挑战。也即是说,国家不再推行全能主义的治理模式,但并未确立社会治理模式,但社会治理的积极因素已经构成国家治理模式转变的制度性基础。最后,中国的社会治理改革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共同转变,并且都在法治框架内予以实现,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创新社会治理的多种努力应建立在国家追求更为长期的有效治理模式和持续性的治理状况改善基础之上。社会治理不仅要不断回应社会诉求,还需要通过释放空间、法治框架以推动社会自身的成长与发展,并促使政府制度化地履行职能,从而跳出以社会管制维持社会稳定与合法性的效率思维,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和质量。
因此,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关键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转变,从而积累社会治理的积极因素,推动社会治理的有序发展与良性运行,以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注释:
①孙立平教授在《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中将“积极的社会管理”理解为以主动的建设和变革为手段,以改善社会的状况、建设一个充满幸福感的、更好的社会为目标。本部分研究借用孙立平教授的表述,并将“积极的社会管理”改为“积极的社会治理”,主要基于如下考虑:一是从根本上讲,孙立平教授界定的“积极的社会管理”,是从如何实现社会治理的角度进行探讨的;二是源于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并以“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三是更加凸显出国家与社会在某些职能领域中良好的合作关系。
参考文献:
[1]郁建兴、关爽.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J].探索与争鸣,2014,(12).
[2]王绍光.煤矿安全生产监管:中国治理模式的转变[J].比较,2004,(13).
[3] He, Q. A Volcanic "Stability".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3, 14(1), 66-72.
[4]燕继荣.变化中的中国政府治理[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6);刘厚金.我国政府转型中的公共服务[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5]俞可平、李侃如.中国的政治发展:中美学者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6]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3).
[7]敬乂嘉.治理的中国品格和版图[J].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11,(7).
[8]郑在浩.改革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评价过去25年.载熊景明、关信基.中外名学者论21世纪初的中国[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9]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10]唐亚林、朱春. 2001年以来中央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与优化路径[J].理论探讨,2014,(5).
[11]朱旭峰、张友浪.新时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回顾、评析与建议[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4,(3).
[12]周志忍、徐艳晴.基于变革管理视角对三十年来机构改革的审视[J].中国社会科学,2014,(7).
[13]郁建兴.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行业协会商会研究的新议程[J].行政论坛,2014,(5).
[14]朱健刚.社会建设的狂飙时代[N].南方都市报,2011-8-14.
[15]刘鹏.从分类控制走向嵌入型监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5).
[16]王名.社会组织论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7]李友梅.构建社会建设的“共识”和“公共性”[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6-14.
[18]郎友兴.软实力“现代化”与“协商机制”: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已无法维系[J].人民论坛,2014,(4).
[19] Chen, J., & Xu, Y. (2014).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with Public Communication, MIT Working Paper.
[20]岳经纶、庄文嘉.国家调解能力建设:中国劳动争议“大调解”体系的有效性与创新性[J].管理世界,2014,(8).
[21] Chen,F. (2003). 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r: The Conflict of Chinese Trade Unions' Dual Institutional Identity[J]. The China Quarterly, 176, 1006-1028.
[22]任剑涛.社会的兴起: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问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35页。
[23]林尚立.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对中国三十年政治发展的反思[J].公共行政评论,2008,(1).
[24]林闽钢.超越“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困境——兼论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突破点[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5).
[25]张兆曙.城市议题与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对杭州3种城市治理实践的组织分析[J].管理世界,2010,(2).
[26]李景鹏.后全能主义时代的公民社会[J].中国改革,2005,(11).
[27]杨宝.治理式吸纳:社会管理创新中政社互动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4).
[28]庄文嘉.“调解优先”能缓解集体性劳动争议吗?——基于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社会学研究,2013,(5).
[29]郁建兴等.让社会运转起来:宁波市海曙区社会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陶柏康)
State-Led Social Governance: The Pattern of Social Governance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Guan Shuang / Yu Jianxing
Abstract: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social governan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core policy issues in China today.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how to delineate and understand the recent development and complex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we analyze and assess policy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main reform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It suggests that state-led social governance is the key fea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formation of this model relies largel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the social governance reform of the government. Although the trend of social governance development is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under this mode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still needs more time. It implies that the model of state-led social governance should not be simply understood as a temporary strategy.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positive factors in social governance will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largely reli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le of state and socie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Keywords:State-Led Governance; Social Governance; Developmental Pattern; Governance Innovation;Rule of Law
作者简介:关爽女(1984-)清华大学与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6-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化研究"(13&ZD040)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8批面上资助项目(2015M58104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6)02-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