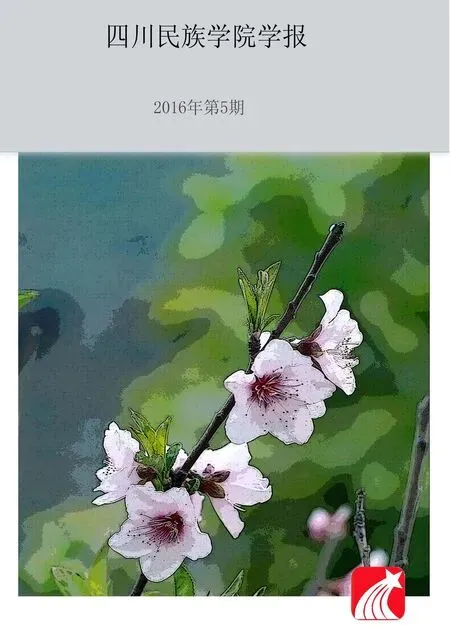唐卡的艺术元素解析
2016-04-11夏吾端智
夏吾端智
★艺术研究★
唐卡的艺术元素解析
夏吾端智
唐卡是藏族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构成和发展过程中不仅吸收了藏族本土的艺术元素,还不同程度地汲取了印度、尼泊尔、汉地、中亚等地区的艺术营养。
唐卡;艺术元素;解析
藏地与诸多地区相邻,与这些地域在政治、文化、宗教及贸易等领域的接触和交流对藏族本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藏族文化博大精深,素以十明文化著称。唐卡属于其中的工巧明,是极其独特的一种绘画形式。纵观唐卡的形成和发展,自然就能发现其中包含的诸多异域艺术元素。不同绘画元素在藏地相互交融之后,铸就了唐卡的丰富内涵和辉煌历史。“更何况将藏传佛教艺术归结为尼泊尔-西藏佛教艺术的名称本来就不符合藏传佛教艺术史的发展,因为自唐代以来,藏传佛教艺术从产生到发展过程中不仅吸收融化了尼泊尔艺术,而且还吸收了中原内地、印度、克什米尔和于阗的一些艺术因素”。[1]纵观唐卡的发展历史及艺术特色,不难发现唐卡从内容到形式,再到表现手法均受到了毗邻地区的影响,汲取了各地的艺术养分,进而丰富和完善了唐卡的艺术内涵。
一、本土艺术元素
吐蕃时期,佛教正式传入藏地,在赞普的支持和资助下,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唐卡艺术也在这一时期有了雏形。这时期唐卡之所以有了较客观的发展,是因为藏族本土的艺术因素起到铺垫作用,因此,在谈论唐卡的发展历史的时候,不得不论及本土艺术因素对唐卡形成所发挥的作用。
根据藏文早期文献《拔协》记载,桑耶寺竣工后,按赞普赤松德赞的要求,依据藏人的面孔特征塑造了佛像。虽然,这些是雕塑而并非唐卡绘画,但是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造像以藏人的体型为标准,而不是完全照搬印度人的体态。对藏人而言,看到具有自己民族的人体体型和面孔特征的塑像,无疑具有熟悉感和亲近感,为激发民众对佛教的信仰发挥推动作用。
在西藏阿里和青海德令哈等地发现了大量早期岩画,根据学术界的研究,这些岩画具有3000-4000多年的历史。换句话说,这些岩画最晚也是吐蕃时期之前刻制的,内容为牦牛、鹿、狩猎、迁徙场面、雍仲符号、各种宗教符号,以及表现当时生活的场面。西藏岩画的制作方法主要有凿刻和涂绘两种。凿刻类用线条技法来刻制,涂绘类是在石头上刻制各种造型之后运用颜料进行染色,多数为红色和黑色。“线条是唐卡的重要的艺术语言形式,线描的技法在很早的藏族古代绘画中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2]是藏族艺人经过早期岩画和摩崖石刻的实践创作中不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早在原始绘画中线条就用于造型,远古岩画中的各种形象,无不是用线条来界定的,不管是阴刻、阳刻、剔地、涂绘等手法,最终都是以线为轮廓界定。古老的陶器纹饰,青铜器纹饰、古老的佛像绘塑,线条都是极其重要的造型元素,也是审美的对象”。[2]线条即是刻制岩画和摩崖石刻的基本技法,也是唐卡的基本表现手法或艺术语言,唐卡的创作中线描的手法不仅能够使画工更加细致,还会表现各种形象的体态和质感以及善恶等相貌,使唐卡变得精美绝伦。古代岩画的线条显得较为硬直,变化也相对较少,但是“唐卡绘画的线条在西藏岩画线条的基础上更加复杂多变”。[3]因此,刻制凿刻类岩画的技法,即用线条来表现体态和物体,与唐卡中的线条的技法具有一致性和传承性。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唐卡以古代岩画的线条为基础,进一步丰富了完善了线条的表现手法,分为浊勾、叶勾、平勾、衣勾、云勾等五大类。
色彩是唐卡的一大特色,有些学者认为唐卡的色彩体系是在吐蕃时期形成的,这些说法忽略了早期岩画和摩崖石刻上的颜色。史前时期为各种造型染色的习俗已经流行,“涂绘的颜料一般是两种色相,红色与黑色。红色为最常见的色彩,红色颜料用动物血调上赤铁矿粉制作而成的。这种红色倘若涂绘在洞穴内的岩壁上,往往能够保持比较鲜艳的色彩,但如果绘在崖阴或旷野的崖壁处,其色彩氧化得更厉害一些,多呈赭色。除红色涂绘外,偶尔也能见到黑色”。[4]早期大多数本土岩画和摩崖石刻涂绘成红色,有些则涂抹成黑色,这一现象说明当时人们为了更准确和更形象地表现各种造型,探索了颜料和色彩的基本用法,至少存在色彩的初步体系。红色在古代岩画中极为流行,非常有趣的是,后弘初期唐卡中也大量使用了红色。虽然缺乏吐蕃时期的唐卡实物,但是从与其属于同一艺术门类的壁画的色彩分析,红色是吐蕃时期较为普遍使用的色彩。大昭寺早期壁画中有红色及深蓝色。此外,后弘初期的唐卡中红色的使用范围较广。早期岩画和摩崖石刻上的红色和黑色及染料的配制等经验可能为唐卡色彩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因此,古代本土岩画和摩崖石刻上的颜色与唐卡的色彩可能存在传承关系,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审美观念的传承。
构图,亦称空间布局,是唐卡的整个画面的布局。唐卡的构图分为中心构图、三界构图、棋格式构图、自然风景为主的构图以及主尊不在画面中心位置,而是在左部或右部等不同的构图方法。从空间布局上分析,学术界一致认为土著宗教苯教中的三界观对唐卡的空间布局产生了影响,“画面上部或上部左右为绘制上师、本尊等相,中部为主尊,下部为护法神,整个画面呈现出三界观的层次。”[5]这样的布局就有了地上、地面、地下的三界观,即上中下的层次感。这也是本土元素渗入唐卡的体现。
简言之,早期岩画和摩崖石刻在史前时期早已存在,唐卡是在吐蕃王朝时期开始形成的,从时间前后来分析,唐卡受到岩画和摩崖石刻上的造型的绘制手法及着色方法的影响是完全有可能的。藏族本土艺术为唐卡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从线条的技法,到红色的选用,再到构图均受到本土艺术元素的渗透。
二、 印度艺术元素
吐蕃王朝时期,西藏与印度在佛教文化领域的交流较为频繁,双方互派佛教学者,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吞米桑布扎奔赴印度学习梵文并创制藏文,莲花生大师和寂护大师来到西藏参与了桑耶寺的创建。这些举措对藏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吐蕃时期和后宏初期,借鉴和照搬了印度佛教中的许多做法,翻译了大量梵文书籍。在唐卡绘画艺术领域,印度对藏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能够找出印度艺术元素的诸多痕迹。
从图像学的角度讲,后弘初期,阿底峡进藏并弘扬佛法,培养了一大批学徒。他在西藏弘法时见到西藏唐卡的绘画技法不尽如人意,量度混乱的现象,故派遣学徒到印度的超戒寺带来唐卡的蓝本。“藏史记载,建噶当派不久,大师深感卫藏佛教艺术的粗劣不堪,造像、壁画及唐卡当中存在着诸多不规范的严重问题。大师曾命名弟子带书信给印度著名的超戒寺,请那里的印度画师作‘布画’三张带入西藏,作为壁画和唐卡的范例和蓝本,为噶当派绘画摹学之用”。[6]当时印度最流行的艺术风格是帕拉王朝的风格,也称波罗艺术风格,并传入藏地。藏人把从印度带至藏地的三幅唐卡作为艺术粉本,模仿绘制了此风格的唐卡,逐渐流行开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因此后人将其称为波罗艺术风格。阿底峡大师在后弘初期引进的东印度绘画风格对藏族唐卡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风格在当时成为藏区主要的绘画风格,并与之后形成的绘画流派有效融合。
唐卡的色彩是矿植物颜料研制的,是唐卡的一大特色,在印度早期艺术中也存在这种传统。康·格桑益西认为印度绘画的色彩对藏族绘画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艺术是此时期的重要代表。它的佛教壁画画法是先用朱砂勾勒,然后用当地的天然颜料涂色,最后用褐色或黑色勾勒形象。笈多式艺术风格对藏地佛教艺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西藏拉萨大昭寺壁画,阿里古格寺殿壁画中人物的一些细节描绘上,与印度笈多时期的阿旃陀石窟有许多相似之处”。[7]因藏区与印度毗邻,印度绘画色彩通过宗教和商业途径渗透藏区完全是有可能的。
从绘画量度理论上讲,藏人继承了印度的量度理论。《量度经》由四部经典组成,是印度绘制佛像的量度理论,对身体各个部位的大小和尺度做了严格的程式化规定。约公元11世纪左右,藏族译师雅砻扎巴尖赞同印度班智达达玛达热一起从梵文译成藏文,从此开始了佛像尺度和量度在藏地的不断发展。以此为基础,藏族学者开始著写了量度理论书籍。根据现有文献,最早著写佛像量度理论的学者莫属炯丹热比热智,他著写了一部篇幅很短的绘画理论书籍。对唐卡量度比例产生较大影响的理论家是曼拉顿珠,其著作《如来佛身量明析宝论》中明确规定了各种佛像的身体比例,成为藏族画师绘制唐卡时遵循的尺度比例。上述藏族本土量度理论文献均提及印度的《量度经》,说明藏族学者在撰写过程中不仅参考了印度的《量度经》,而且把其中的各种造像的尺度比例照搬到藏族唐卡造型上。
三、尼泊尔艺术元素
尼泊尔与卫藏地区接壤,早期隶属于印度。尼泊尔艺术对藏族艺术的渗透可追溯到吐蕃时期,据史书记载,尼泊尔艺术家参与了桑耶寺的修建与佛堂内供奉的雕塑的塑造。
此外,学术界普遍认为,尼泊尔绘画风格对藏族唐卡的影响始自萨迦时期,于公元13世纪,以阿尼哥为首的尼泊尔艺术家团队应萨迦派邀请来到萨迦,并进行了艺术创作活动,为藏区的绘画艺术增添了新的成分。尼泊尔风格在14-15世纪达到了巅峰。纽约大都博物馆的唐卡研究专家斯偍文·阔萨克(Steven Kossak)指出,“尼泊尔风格的绘画在13世纪早期首次在西藏出现,这些绘画与萨迦派是有关联的”。[8]大卫·杰克逊认为尼泊尔风格在藏族绘画历史演进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而且风靡一时,于14世纪早期至15世纪中期成为卫藏地区的主绘画风格。他专门为此撰写了一本著作《藏族绘画中的尼泊尔痕迹(The Nepalese Legacy in Tibetan Painting)》。书中这样写到,“大概从1360到1450的近一个世纪,东印度风格消失后尼泊尔画风发展成为西藏唯一的风格”。[9]1353年帕木竹巴推翻了萨迦政权,掌握了藏区的统治权,而尼泊尔风格继萨迦政权成为帕木竹巴赞助的画派。“颇为有趣的是,它在1350年或1360年左右替代波罗风格,因此,有意或无意当中成为帊木竹巴政权统治者统治期间所资助的唯一的风格”。[9]尼泊尔风格于公元13世纪初传入藏地,并于14-15世纪达到最高峰并成为藏区最主要的画派。藏人首先传承了这一画派,之后对其做了一定的创新,其表现为,齐乌岗巴大师以尼泊尔绘画风格为基础,创立了藏族本土的第一个画派,即齐乌岗巴画派。倘若没有尼泊尔流派作为基础和铺垫,就很难有齐乌岗巴画派的诞生,因此尼泊尔风格对唐卡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空间布局来看,棋格式布局是尼泊尔画风的主要特点。藏人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尼泊尔风格、齐乌岗画派以及曼唐画派的唐卡画面中,按照尼泊尔风格,在主尊的周围将上师、学徒、本尊等相关人物绘在棋格内,以左右对称的方式呈现。“在画面层次天地浑然一体不分明显的界限,风景不多,几乎没有山岩、树木或溪流的特点被西藏地区画派采纳,显现出轮廓结构优美之感”。[5]早期为数较多的唐卡中将主尊周围的佛和菩萨、上师、护法神等置于棋格中,并以对称方式出现,这是尼泊尔画风的标志,藏人将其吸收到藏族唐卡的绘画中。早期唐卡的主尊置于画面中央位置,并且所占比例巨大,这也是尼泊尔绘画的痕迹。这种风格是14-15世纪卫藏最为流行的绘画风格。
四、汉地艺术元素
雪域高原与汉地接壤,从历史文献和碑文记载来看,吐蕃王朝时期与汉地的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的高度。此外,虽然两地相隔之遥,但佛教在两地都成为正统的信仰,这一共同点为相互之间的接触铺垫了心理的基石,拉近了双方的距离,促进了更多的交流。吐蕃时期,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相继远嫁为吐蕃赞普王妃,前者带来了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随行中也有汉地工匠和画师,他们参与了大昭寺的建设之中,“当时主持大昭寺事务的蔡巴万户长委托艺术家们根据中原汉族的传统风格为大昭寺塑造了一些塑像。例如,寺内松赞干布和他的两位妃子的塑像以及佛陀释迦牟尼的塑像”。[10]此外,据说大昭寺内供奉的四大天王塑像也受到汉地艺术的影响。这可能是汉地艺术元素渗透藏区的始端。
在绘画领域,后弘初期,藏族僧人从汉地带回了唐卡,藏地的十六罗汉的形象也受了内地汉式艺术的影响,根据维塔利的研究,“后弘期著名佛学大师鲁梅·楚呈西绕(约十世纪人)访问内地时,带回了他在内地时根据内地十六罗汉粉本描绘的十八幅唐卡,其中还包括一幅释迦牟尼像和法护居士画像,在西藏广为传播”。[1]但是,笔者对维塔利的观点的正确性怀有疑虑,倘若后弘初期从汉地带来了唐卡绘画粉本并广为流传,那么为什么汉地青绿山水的风景画直到15世纪在曼唐画派中才正式出现呢?还有另一种可能,当时藏族画师只是接受了罗汉形象的描绘,而未模仿其中风景的绘制。这只是笔者的拙见,尚需进一步考证。倘若维塔利的观点能够成立,唐卡在早期发展阶段从题材到空间布局均吸收了汉地绘画的艺术养分。
藏族艺人吸纳了汉地的绘画营养,尤其是在帊竹时期和甘丹颇章时期这种倾向愈加凸现出来。曼唐派、噶赤派的唐卡中有大量青山绿水的风景内容,其中最为突出和引人注目的便是山清水秀、蓝天白云、花草树木、房屋建筑等自然因素作为佛和菩萨等的背景画到唐卡上。“在背景处施色浅淡而明快,中间部分及高山平川的接界处色彩尤为浅淡,还有众多的树木花草、山岩溪水、飞禽走兽等风景。背景空旷,每个神灵所占空间很小,神佛和人物成组出现排列紧密。”[5]这种背景处理拉近了佛和菩萨与众生的关系,给佛和菩萨等增添了自然属性。青山绿水的吸纳对唐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唐卡发展的历史来看,汉地艺术对唐卡绘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画面背景的描绘上,如山、水、树、云彩,尤其是花鸟,装饰等等方面”。[11]在噶赤画派中汉地风景描绘的痕迹极为明显,“尤其是该画派创始人南卡扎西将汉式绘画的风景布局或描绘,晕染和色彩运用等艺术风格引入了他的绘画作品中,甚至直接模仿汉式作品进行创作,形成了淡雅的色彩应用和淡影的风景技法的绘画风格”。[7]无可否认,汉地青绿山水的风景画及其浅淡的色彩处理方法极大地丰富了唐卡的构图和表现技法,更是拉近了画面中佛与人的距离,具有自然和谐之美感。
装裱是唐卡独具一格的特征,由贡夏、唐门、郭噶、唐帘、唐薪等组成。部分佛教艺术研究专家认为唐卡的装裱可能受到汉地绘画装潢的影响,谢继胜是代表性人物,他在《唐卡起源考》一文中指出:“唐卡这种形式并非来自印度,它的发展基本上与汉唐至宋元中原汉地卷轴画的发展进程相适应,它是在蕃汉交往密切的敦煌,沿着佛教绘画的轨迹,由吐蕃旗幡画演变而形成的”。[11]此外,唐卡收藏家和学者叶星生把唐卡的形制的起源与汉地的旗幡画联系了起来,“唐卡的形制是唐卡特色风格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识别唐卡的标识之一。其构成形式与汉地旗幡画、卷轴画极为接近,后来随着唐卡艺术的发展而形成鲜明的个性特征”。[12]于小冬分析了谢继胜的观点,认为“起源于汉地的根据主要不是从唐卡画面的内容,而是从型制上,即从汉族古代绘画的装裱方式上找到了确切的联系,从而解释了唐卡装裱型制的起源”。[6]谢继胜对比了唐卡的装裱和汉地的宣和装,其中,《四美图》是黑水城一幅著名的木刻雕版印画,这幅画的天头部位的惊燕与唐卡的飘带极为相似,而且,“唐卡画心的红黄边框、上下隔水、飘带等这些宣和装的形制特征在印度布画中截然无存,然而在11世纪前后的汉地卷轴画中无一例外地找到”。[13]黑水城出土的唐卡与汉地绘画的宣和装的装潢方式极为相似,所以,“从形制上分析,唐卡的装潢法基本上模仿的是宣和式装潢法”。[13]的确,从汉地卷轴画《四美图》的图像资料来看,它的形制与唐卡的装裱虽然并非完全相同,但是存在相似之处,因此,唐卡的装裱形制受到汉地卷轴画的影响是有可能的。
五、中亚艺术元素
中亚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特指某一国家,与西藏西部毗邻,由众多族群和地区组成,其中对吐蕃影响较大的莫属波斯、西域、于填、克什米尔等地。吐蕃与这些地区在早期已经建立了贸易关系,吐蕃的麝香、中亚的各种样式的器皿都是双方颇受青睐和喜爱的贸易交换物品。
杜齐教授指出,“无可怀疑的是,西藏(特别是西藏西部)在早期就与伊朗文化有着联系。这可能是出于迁徙和贸易的原因,艺术及装饰主题也随之从伊朗传入了西藏”。藏文史料文献中记载仁青桑布大师从克什米尔邀请多位艺术家在古格从事雕塑和绘画艺术活动,对藏区绘画和唐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植物纹样是鉴别唐卡风格的又一特征,唐卡的部分植物纹样是借自中亚的。“如当时有些唐卡和壁画中的植物纹样等是从西域传入藏区的,尤其在前弘末期和后弘初期从西域传入藏区的”。[7]西域与藏地相邻,从吐蕃时期就有宗教和商业领域的接触和交流,这些植物纹样从西域传入藏地完全是有可能的。
结 语
藏族文化是唐卡赖以形成和快速发展的土壤。唐卡虽然吸收了外地的各种绘画元素,雪域高原的艺术家是将其与本土艺术有效融合的促成者。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就很难促成唐卡的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吸收异域元素的过程中体现了藏族唐卡发展的一大特色,“藏族美术的一大特色是它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吸纳性,从它的先期发展历史开始就十分重视和善于学习借鉴周边地域和民族的文化艺术精华,并有着长期不断地和外域文化交流学习的良好传统”。[14]
[1]熊文彬.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白居寺壁画艺术研究[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p11、p156
[2]凡建秋.唐卡艺术解读[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p131、p130-131
[3]赵大军.解读西藏岩画和唐卡绘画艺术属性的相似点[J]. 西藏研究,2006年第3期,p55
[4]张亚莎.西藏美术史[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p36
[5]罗桑开珠.浅析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文化元素及其特征[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p154、p155-156、p155
[6]于小冬.藏传佛教绘画史[M].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年,p91、p100
[7]康·格桑益西:藏传噶玛噶孜画派唐卡艺术(上卷)[M]. 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3年,p33、p171、p42
[8]Steven M. Kossak and Jane Casey Singer.Sacred Visions Early Paintings From Central Tibet[M].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uem of Art,1998,p40
[9]David Jackson.The Nepalese Legacy in Tibetan Painting[M]. .New York: Rubin Museum OfArt, 2010,p131、p174
[10]扎雅·诺丹西绕著,谢继胜译.西藏宗教艺术[M]. 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p80
[11]谢继胜.唐卡起源考[J]. 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p109、p107
[12]叶星生.唐卡的起源与形制[J]. 收藏.2014年第23期,p113
[13]谢继胜、熊文彬、罗文华、廖旸.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上)[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p113 、p112
[14]康·格桑益西.藏传噶玛噶孜画派唐卡对汉地青绿山水技艺的吸纳[J].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p49
[责任编辑:王鹤艳]
An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Elements of Thangka
Xiawu Duanzhi
Thangka is a unique form of Tibetan art, and bears strong ethnic characteristics. During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angka has absorbed not only elements of Tibetan arts, but also painting elements of India, Nepal, and Central Asia, etc.
Thangka; artistic element; analysis
夏吾端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北京海淀,邮编:100081)
J229
A
1674-8824(2016)05-00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