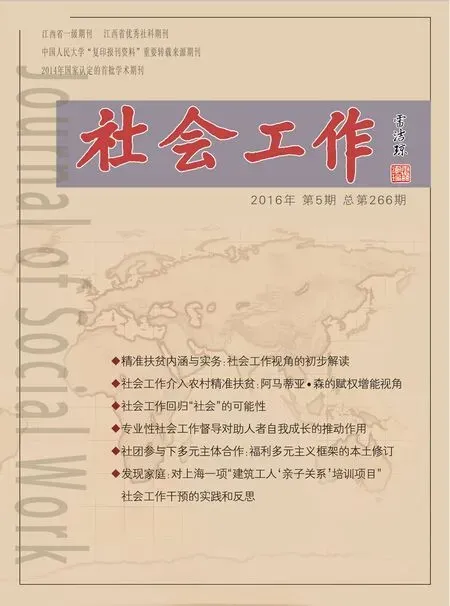社会工作增权视角下妇女庇护所防治家暴实践
2016-04-11吴清禄蔡惠敏
王 玲 吴清禄 蔡惠敏
社会工作增权视角下妇女庇护所防治家暴实践
王 玲 吴清禄 蔡惠敏
诸多实证研究发现,增权对提升受家暴妇女生活自主抉择权具有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回顾,探讨增权的定义、针对受暴妇女的增权,以及增权理论在妇女庇护所防治家暴服务中的运用。增权是目标也是一个过程,妇女庇护所不仅起着临时安全居所的作用,更要协助妇女调动内部和外部资源,完成其增权目标,并持续地评估进展,确保在此过程中没有出现新的失权。
增权 家庭暴力 妇女庇护所 受暴妇女
王玲,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博士研究生;吴清禄,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博士研究生;蔡惠敏,女,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助理教授,香港注册社工(香港 999077)。
一、问题的提出
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存在,并一直受到关注。联合国把“针对妇女的暴力”定义为:“无论是在公众场合或私人生活中,任何基于性别的,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体、性或精神伤害或痛苦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的行为。”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主要有亲密伴侣暴力、性暴力、荣誉处决、强迫婚姻和童婚、女性生殖器切割和贩卖妇女等(United Nations,1993)。亲密伴侣暴力和性暴力是最常见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类型。世界卫生组织与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及医学研究理事会根据八十多个国家的现有数据推断,全世界有35%的女性曾经遭遇过亲密伴侣暴力或非伴侣性暴力(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3)。在曾经有过亲密关系的妇女中,约有三分之一(30%)的妇女曾经遭受过由其亲密伴侣实施的身体和/或性暴力。联合国于2013年在亚太地区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项目“联合国男性与暴力多国研究”,在中国中东部地区一个县(包含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以随机抽样的方法访问了曾有或现有伴侣的949位男性和1022位女性。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曾有或现有伴侣的女性中,39%的人曾遭受过来自男性伴侣的身体和/或性暴力。在所有曾有或现有伴侣的男性中,52%的人曾向女性伴侣施加过身体(或性暴力)(Fulu et al.,2013)。在香港地区,根据社会福利署虐待配偶(同居情侣)个案及性暴力个案中央资料系统显示,2014年新呈报3917个案,其中83.3%的受暴人性别为女性(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2014)。由上面的研究回顾可以看出,针对妇女的暴力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针对妇女的暴力影响范围极广,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现有研究表明亲密伴侣暴力对受暴妇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身体、心理、性与生殖健康以及对其子女的影响。对身体的影响主要包括头痛、背痛、腹痛、胃肠功能障碍以及总体主观性健康状况不佳(Campbell et al.,2002)。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有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睡眠困难、饮食障碍以及自杀企图。对性与生殖健康的影响主要有意外怀孕、堕胎、妇科疾病和感染性传播疾病包括艾滋病毒,并会增加妊娠期间流产、死胎、早产和婴儿出生体重过低的可能性。亲密伴侣暴力和性暴力更会带来致命性的后果,如自杀和凶杀。当子女目睹亲密伴侣暴力后会出现行为问题和情感障碍,如社交技能低下、学习困难、抑郁或攻击性强(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5)。
以上的文献回顾表明,如何减少暴力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以及如何预防针对女性的暴力成为全世界面临的公共健康问题。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但防治家庭暴力体系还属于起步阶段,妇女庇护所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例如设施不健全、服务不完善、寿命较短、私密性差、缺乏多部门合作的防治家暴协调机制等(崔诗婉、罗婕,2013;吉朝珑,2009;张翠娥,2011)。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社会工作增权视角与妇女庇护所的文献进行回顾,探讨增权的定义、针对受暴妇女的增权,以及增权视角在妇女庇护所的防治家暴服务中的运用,以给我国妇女庇护所更好地实践防治家庭暴力工作提供借鉴。
二、社会工作的增权视角
(一)增权的定义
目前很多妇女庇护所都把增权作为服务目标。针对受暴妇女增权,是世界各个国家防治家庭暴力的核心工作(Cattaneo&Goodman,2015;Kasturirangan,2008)。虽然增权理论在各个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增权这一概念并没有统一的定义(Kasturirangan,2008)。如果对社会工作增权视角没有清晰的定义,就很难运用到防治家暴实践中。要了解增权(empowerment)的定义,首先要了解权力(power)的定义。有学者提出,权力的定义不应局限在心理层面的个人对周遭环境的控制感,更应包括一种真实控制资源的权力(Cattaneo&Goodman,2015)。真实权力的类型包括:对可获资源的实际主导权(power over),拥有自由意志的行动权(power to),抗拒他人影响的能力(power from)(Riger,1993)。我国学者陈树强(2003)把增权定义为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从而增加案主的适应能力和才能,使其能够控制环境,获得权力感。
(二)增权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核心任务
20世纪70年代,Solomon(1976)首次把增权理论运用在社会工作领域。《黑人充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一书中,Solomon把增权定义为一个过程,被耻辱化的社会群体通过实践个人影响力和担任出色的社会角色来发展出个人的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改革的力量。Solomon认为增权的起点在于一个社会不平等的环境,通过个人的、人际的、机构和社区层面的增权,去除对黑人少数民族的压迫、疏离、和无权感,增加黑人社区的自我、人际、经济和政治权力。目前,增权理论在社区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学科广受欢迎,有关增权的学术论文,截止于2016年5月,在PsycInfo数据库就有166,554条搜索结果。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FSW)和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于2014年7月在周年大会上通过社会工作专业全球定义:“作为一个以实践为本的专业及学术领域,社会工作推动社会改变和发展、社会凝聚和人民的增权及解放。社会公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差异等原则是社会工作的核心。基于社会工作、社会科学、人文和本土知识的理论,社会工作以联系个人和组织去面对人生的挑战和促进人类的福祉”(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2014)。因此,对民众的增权已经成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核心任务。
三、社会工作增权视角在妇女庇护所的防治家暴服务中的运用
针对受暴妇女增权是反家暴运动的核心目标(Goodman&Epstein,2008)。受暴妇女首先是失权的,被施暴者剥夺了权力。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权力与控制,施暴者通过心理暴力、性暴力、肢体暴力、经济控制等行为建立个人权力从而控制受暴者(Stark,2007)。女性主义理论也认为针对妇女暴力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父权社会结构下,男性的地位、资源、权力均高于女性(Dobash&Dobash,1979; Russell,1982)。因此,妇女受暴的经验可以理解为一个失权的过程,即妇女被施暴者剥夺了个人权力。针对受暴妇女增权,就是把施暴者剥夺的权力重新归还给妇女(McDermott&Garofalo,2004)。Cattaneo和Goodman(2015)指出,针对受暴妇女的增权可以被定义为通过社会生活中互动来获得权力的经验。增权是一个持续的、反复的过程。受暴妇女设定对个人有意义的增权目标。并调动内部资源(例如,自我效能感、知识、技能等)和外部资源(例如,社区资源与支持),积极采取行动,努力实现其增权目标。同时,持续地评估进展,并确保在此过程中没有出现新的失权(Cattaneo&Goodman, 2015;Goodman et al.,2015)。很多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工作增权视角对受暴妇女重获生活自主抉择权起到了积极作用(Cattaneo&Goodman,2010;Hague&Mullender,2006;Perez,Johnson&Wright,2012;Zweig&Burt,2007)。
(一)增权是目标
妇女庇护所一开始是一个发源于民间的妇女运动,如今妇女庇护所已经演变为一项社会福利服务,但妇女庇护所的核心目标始终是针对受暴妇女增权(Goodman&Epstein,2008),妇女庇护所更是促进挑战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中坚力量(Dobash&Dobash,1992)。目前大部分的妇女庇护所的防治家暴服务都运用社会工作增权视角,首要是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通过向这些边缘化的受暴者提供资源,减轻她们自身的无能感(Goodman&Epstein,2008)。例如,香港保良局妇女庇护中心的服务宗旨包括:为遭遇家庭暴力或严重问题的妇女及其子女提供安全短暂的住宿服务,解决即时危机;透过专业辅导,提升妇女的自尊感,协助她们拥有自我保护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好自我装备,日后更有效地处理个人或家庭问题;协助妇女建立“同路人”支援网络,透过互动及参与活动,发挥个人潜能,重拾自信;重视儿童身心发展,为他们提供危机介入辅导,防止家庭暴力蔓延至下一代;向公众宣传“零暴力”及和谐家庭信息,提高社会人士对家庭暴力之认识及警惕性,预防不幸事件发生①保良局妇女庇护中心,2016,《保良局妇女庇护中心服务宗旨》,引自:http://womenrefuge.poleungkuk.org.hk/b5_objective.html。
Johnson et.al(2011)在妇女庇护所的随机临床实验(a randomized clinical trail)结果表明,运用增权视角的辅导项目有着出色的治疗效果,比起没有参与辅导项目的受暴妇女,参与者的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与重复受虐风险显著减少。在此研究中,增权由个人进步量表修订版(The Personal Progress Scale-Revised)来测量,该量表测量的是十大女性主义治疗效果,包含积极自我评价与自尊,一个良好的舒适痛苦比例,性别角色和文化认同的自我觉察,个人自主权与自我效能感,自我滋养与自我关爱,高效的问题解决技能,自我肯定,享有多种经济、人际、社区资源、性别角色和文化认同的灵活性,以及参与有建设性的社会行动。
在增权视角下,受暴妇女应自己设定对个人有意义的目标,妇女庇护所的社会工作者只是担任协助者的角色,不能帮妇女设立目标,例如是要离开亲密关系,还是和施暴者复合,一位社会工作者回顾了她对案主所说的一段话:
我在这里不是要告诉你,你需要离开这段关系。我不会来判断你拥有一段什么样的关系。你必须自己来决定你要的是什么。你必须自己来决定什么对你是重要的,你想要一段什么样的关系。你需要意识到要一些事情改变的概率是很低的,因为这样的改变很难。并不是说没有改变的机会,而是关于要什么才能改变。案主显然不喜欢我所说的话。我继续说,你要知道,这是你的人生。你必须自己来决定。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要怎么做(Kulkarni et.al,2012;p93)。
(二)增权是过程
针对受暴妇女的增权是一个持续的、反复的过程(Kasturirangan,2008)。一个受暴妇女可能会为了自身的安全采取行动,并在行动后意识到行动带来的影响。她也许意识到需要更多的资源才能确保自身安全。因此会继续去努力获得这些资源,评估自己的进展,并进一步修改计划。在此情况下,增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包含多个步骤,通过不断评估进展来调整个人的行动(Cattaneo&Goodman, 2015)。由于每个受暴妇女的家庭环境、资源、困境、个人目标都不同,入住妇女庇护所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完成增权目标。因此持续的评估是家庭暴力危机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Kropp,2008)。妇女离开庇护中心后,不应视为完成了增权,而应持续地评估妇女的增权进展,重新制定增权目标,继续增权的过程。在处理家庭暴力的个案时,当施暴者未能反思和改变自己的行为时,受暴者也未离开这段关系时,暴力很可能会再次发生,一位妇女也可能会多次入住庇护中心。一位香港的社会工作者也提到一些案主在个案结束后还会再来寻求帮助。
当有社会工作介入,受暴妇女盼望有转机,更能够处理及解决暴力问题,不再受困。但可惜不是每个个案都可以在介入后便顺利地雨过天晴,解决所有问题……她们仍有很多“包袱”,包括经济问题、子女的将来、婚姻观念、传统思想、社交网络及亲友的压力。这些顾虑令她们未能勇于做出转变。……身为社会工作者,便要在她们处于人生道路上崎岖的部分时,不离不弃地在旁支持她们、扶持她们,令她们敢于转变和经历,继续创造她们的人生(和谐之家,2006;p63-66)。
(三)协助妇女获得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
Cattaneo和Goodman(2015)提出在增权过程中,协助受暴者调动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完成其增权目标。内部资源包括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知识(knowledge)、技能(skills)。自我效能感由班杜拉(Bandura,1982)提出,定义为一个人对完成个人生活中的某一行为的主观判断和自信程度。当自我效能感增加后,受暴妇女逐渐在心理上脱离了受害者的角色,而成为一名幸存者(Busch&Valentine,2000)。幸存者治疗(survivor therapy)(Walker,1994),整合了女性主义治疗与创伤治疗,专注于受暴妇女自我拥有的能力和复原力(resilience),去除受暴妇女的受害人心理(victimization),以及重新建构新的自我认同。庇护所向妇女提供多种辅导服务,包括个案辅导、危机评估、心理评估、妇女及儿童治疗小组、妇女互助小组等。辅导目的是帮助她们从暴力的阴影中走出来,提升自主意识和能力,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获得社交与心理的幸福感(杨陈素端,2005)。一位香港的受暴妇女参加完妇女庇护所的妇女治疗小组后,给出了以下的回馈:
治疗小组能够帮助我处理情绪困扰,让我逐步重新肯定自我的价值。回想发生家暴事件后,我失去了生存意义,缺乏自信,加上精神不能集中,对自己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在小组内,我透过不同活动学习分享及表达个人感受和情绪,起初难于启齿的我,从中发觉自己不再是孤单走路,跟其他组员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大家尽情地流露感受,最终放下忧虑和羞愧,互相得到鼓励。此外,我更认识到如何建立正面思考模式,从而带来正面的情绪和行为结果。情绪的改善不但令我用于接收转变,还会积极地面对将来,为自己制定人生目标,展开人生的另一页(蔡惠敏,2016:P6)。
知识是指理解达成目标所需要做的,不等于采取行动的能力。具体来说,知识是了解防治家暴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例如,受暴妇女想要获得经济独立,她需要了解有关职业培训或经济援助的信息以及获得的方法(Cattaneo&Goodman,2015)。妇女入住庇护所后,社会工作者首先协助妇女进行危机评估,增加她们对家庭暴力及其影响的认知,提升危机意识,制定相应的安全计划。同时向妇女提供有关资讯、介绍社区资源或转介服务。此外,向妇女提供有关反家暴教育,协助受暴妇女从社会文化、性别结构层面来理解伴侣暴力的发生原因、类型特点、和危险因子,例如用“权力控制轮”(power and control wheel)来说明施暴者的内在动力。当受暴妇女对自我经验重新界定后,便获得一种新的自我意识,从而勇于追求自我权益的保护、自主抉择的能力以及社会性别平等的意识(杨陈素端,2005)。
技能是指为实现目标所需的具体能力。例如,使用计算机的能力、就业的能力以及教养遭受家暴创伤子女的能力(Cattaneo&Goodman,2015)。为了协助妇女重建无暴力的家庭生活,需协助妇女认识自己的能力,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及各种所需的生活技能(例如,生活指导、职业技能培训、亲子沟通培训等),从而重拾自信,努力达成增权目标。
外部资源指的是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网络的支援,例如,朋友、邻居、同事、亲戚和其他福利机构等(Cattaneo&Goodman,2015)。一个受暴者个案的需求是多个方面的,需要多种社会、法律、经济和医疗等方面的资源。对受害妇女增权,不能单靠妇女庇护所力量去执行,还需要不同部门分工合作,才能协助受暴者获得多种资源,达成增权目标(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2011)。同时,妇女庇护所居住的经验,有助于受暴妇女之间接触,利于她们在组成互助团体后,逐渐脱离疏离和孤立状态,建立起互助支援网络。
(四)增权视角下社会工作者的角色
在社会工作增权视角下,介入的过程被重新界定为“分享权力”和“一道拥有权力”的过程,案主和社会工作者都是互为伙伴的角色。案主并不被看作为有问题,社会工作者也不被看作为专家、施恩者、指导者或权威者,而是被看作为促进者(陈树强,2003)。因此在增权视角下,社会工作者与受暴妇女之间是一种互相合作、互相信任的伙伴关系,社会工作者协助受暴妇女对家庭暴力进行重新认识,提高她们对权力的意识,调动资源协助妇女获得机会、信息和支持,共同致力于妇女重获被剥夺的权力,追求社会性别平等。相反地,一种权威式、施舍式、官僚式的介入模式将会破坏受暴妇女的自主独立和人格尊严(DeWard&Moe,2010)。
在一些资源匮乏的妇女庇护所中,社会工作者可能会面临员工倦怠(staff burnout)的情况。例如一位接听家暴热线的工作人员提到:
我认为这份工作是让人情绪紧张的,我也能理解这个处境。但我们需要采纳一些方式来减少压力。我们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在这里,但是明年有多少人会走,因为我们无法处理这些压力(Kulkarni et.al,2012;p93)。
减少社会工作者的压力,提高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幸福感将帮助社会工作者更好地协助受暴妇女,成为她们增权过程中有力的伙伴。因此,妇女庇护所应注重对社会工作者的培训和支持。
(五)实践中的失权
虽然很多防治家庭暴力的项目,致力于对受暴者增权,却在服务过程中,使受暴者面临失权,这也导致很多受暴妇女拒绝机构的服务(McDermott&Garofalo,2004)。妇女庇护所从一开始以女性主义为导向的民间运动,渐渐转变为附属于政府的社会福利机构,越来越官僚化,给受暴妇女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Goodman&Epstein,2008)。Goffman(1961)指出一个官僚化的机构中会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一方拥有决策和管理权,而另一方依赖于这个机构。一个官僚机构的运营需要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目的是控制其入住者和巩固等级制度,而违背制度的人必然会受到惩罚。
目前,由于政府或资助方要求机构拿出具体的业绩来进行考核,例如,多少受暴者离开了虐待关系,多少受暴者回去和施暴者复合等(Smyth,Goodman,&Glenn,2006)。这些指标并不能用来评估增权的进展情况,并导致妇女庇护所的服务目标越来越狭窄。同时,关注这些短期目标会使机构和工作人员忽略了长期目标,也忽略了每个受暴妇女的资源、困境和个人目标都不同。很多妇女庇护所为了交出令人满意的宿位使用率,不得不通过限定住宿时间,来保证人员的流动,而对住宿时间的限制对受暴者和社会工作者都成为一个无形的压力。
此外,妇女庇护所等机构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例如,为了保证妇女的安全,通常妇女入住的庇护所离她们居住的社区都很遥远,并且晚上回宿舍的时间都有严格规定(Goodman&Epstein, 2008)。这些规定使得受暴妇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需求来遵守机构的规定和制度。也有受暴妇女因为无法接受这样的控制拒绝了机构所提供的服务(Smyth et al.,2006)。这样的行政限制无疑就背离了增权的目标——即让妇女获得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权,使得妇女在增权过程中却面临失权的风险。对于妇女庇护所目前的发展,一位工作人员给出这样的评论: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种社会福利机构服务模式而非一种草根模式,即聆听受暴者,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及我们怎么做才能满足这些需求(Kulkarni et.al,2012;p96)。
社会工作增权视角能帮助妇女庇护所预防在服务中使受暴妇女面临新的失权。增权视角强调以受暴妇女的需求为服务导向,尊重妇女,倾听妇女,让妇女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并时时评估服务,确保完成增权的目标,预防出现新的失权。
四、结 语
在庇护的过程中,不能忽略社会工作增权视角作为导向的重要性。妇女庇护所的防治家暴实践,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庇护的目标并不仅仅为了给受暴妇女及其子女提供短期住宿,确保他们的即时安全,更要改变受暴妇女的失权状态,调动资源协助妇女获得机会与支持,激发案主潜能,协助其脱离被指责与被剥夺的状态,重新获得自主抉择和独立生活的能力。第二,庇护所增权的过程要尽可能地提高妇女对权力的意识,重视妇女的自主意念和自主选择的能力,而不是作为一个权威者来救助案主。案主始终是增权过程的主体,并承担个人责任,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做出种种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状况。庇护所需要尽可能地让受暴者直接参与到服务与政策制定的决策过程中来。第三,增权是一个持续的、反复的过程。由于每个受暴人的家庭环境、资源和困境不同,帮助受暴人制定出对个人有意义的增权目标,并进一步协助其修改其增权目标和行动计划。持续地评估进展,并确保在此过程中没有出现新的失权。第四,重视受暴妇女之间的互助关系,协助成立互助团体,帮助她们脱离疏离和孤立状态,共同努力实现增权目标。第五,妇女庇护所不仅在个人和人际层面进行增权,更要在社区层面进行增权。妇女庇护所的舍友可以成为社区增权的中坚力量。社区的参与可以为妇女庇护所提供多样的资源,同时亦能在社会上共同发声,倡导零暴力。
[1]蔡惠敏,2016,《晓晴小组:家暴创伤治疗妇女小组工作手册》,香港:保良局妇女庇护中心与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
[2]陈树强,2003,《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社会学研究》第5期。
[3]崔诗婉、罗婕,2013,《我国当前反家暴妇女庇护所的发展困境与未来出路》,《研究生法学》第5期。
[4]和谐之家,2006,《不要痛爱——给他明白你的心》,香港:明窗出版社。
[5]吉朝珑,2009,《家庭暴力受虐妇女庇护研究》,《河北法学》第9期。
[6]杨陈素端,2005,《家庭暴力:处理受虐妇女手册》,香港:和谐之家。
[7]张翠娥,2011,《妇女庇护所的发展现状与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8]Bandura,A.,1982.Self-efficacy mechanism in human agency.American psychologist,37(2),122.
[9]Busch,N.B.,and Valentine,D.,2000.Empowerment practice:Afocus on battered women.Affilia,15(1),82-95.
[10]Campbell,J.,Jones,A.S.,Dienemann,J.,et.al,2002.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physical health consequences.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162(10),1157-1163.
[11]Cattaneo,L.B.,and Goodman,L.A.,2010.Through the lens of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owerment in the court system and well-being fo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s.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25(3),481-502.
[12]Cattaneo,L.B.,and Goodman,L.A.,2015.What is empowerment anyway?A model for domestic violence practice,research,and evaluation.Psychology of Violence,5(1),84.
[13]DeWard,S.L.,and Moe,A.M.,2010.Like a prison:Homeless women's narratives of surviving shelter.J.Soc.& Soc.Welfare,37,115.
[14]Dobash,R.E.,and Dobash,R.P.,1992.Women,violence and social change.London:Routledge.
[15]Dobash,R.E.,and Dobash,R.,1979.Violence against wives:Acase against the patriarchy.New York:Free Press. [16]Fulu,E.,Warner,X.,Miedema,S.,et.al,2013.Why Do Some Men Us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How Can We Prevent It?Quantitative Findings from the UN Multi-country Study on Men and Violenc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Bangkok:UNDP,UNFPA,UN Women and UNV.:
[17]Goffman,E.,1961.Asylums:essays on the soocial situatio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New York:Anchor Books.
[18]Goodman,L.A.,Cattaneo,L.B.,Thomas,K.,et.al,2015.Advancing domestic violence program evaluation: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Measure of Victim Empowerment Related to Safety(MOVERS).Psychology of Violence,5(4),355.
[19]Goodman,L.A.,and Epstein,D.,2008.Listening to battered women:A survivor-centered approach to advocacy, mental health,and justice.Washington: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Hague,G.,and Mullender,A.,2006.Who listens?The voices of domestic violence survivors in service provis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Violence Against Women,12(6),568-587.
[21]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2014.Global 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Retrieved from http://ifsw.org/ get-involved/global-definition-of-social-work/
[22]Johnson,D.M.,Zlotnick,C.,Perez,S.,2011.Cognitive behavioral treatment of PTSD in residents of battered women's shelters:results of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79(4),542.
[23]Kasturirangan,A.,2008.Empowerment and programs designed to address domestic violence.Violence Against Women,14(12),1465-1475.
[24]Kropp,P.R.,2008.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Violence and victims,23(2),202-220.
[25]Kulkarni,S.J.,Bell,H.,Rhodes,D.M.,2012.Back to basics essential qualities of services for survivor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Violence against women,18(1),85-101.
[26]McDermott,M.J.,Garofalo,J.,2004.When Advocacy for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Backfires Types and Sources of Victim Disempowerment.Violence Against Women,10(11),1245-1266.
[27]Perez,S.,Johnson,D.M.,Wright,C.V.,2012.The attenuating effect of empowerment on IPV-related PTSD symptoms in battered women living in domestic violence shelters.Violence Against Women,18(1),102-117.
[28]Riger,S.,1993.What's wrong with empowerment.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21(3),279-292.
[29]Russell,D.E.,1982.Rape in marriage.New York:Macmillan.
[30]Smyth,K.F.,Goodman,L.,Glenn,C.,2006.The full-frame approach:a new response to marginalized women left behind by specialized services.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76(4),489.
[31]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2011.Procedural Guide for Handl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Cases.Hong Kong: Working Group on Combating Violence.Hong Ko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 page_family/sub_fcwprocedure/id_1450/.
[32]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2014.Statistics on Cases Involv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Reported by the Central Information System o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Cases in Hong Kong.Retrieved from http://www.swd.gov.hk/vs/chinese/stat.html
[33]Solomon,B.B.,1976.Black 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4]Stark,E.,2007.Coercive control:How men entrap women in personal lif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5]United Nations,1993.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85th Plenary Meeting.Geneva:UN(December 20,1993).
[36]Walker,L.E.,1994.Abused women and survivor therapy:A practical guide for the psychotherapist.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37]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5.WHO multi-country study on women's health and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summary report of initial results on prevalence,health outcomes and women's responses.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38]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3.Global and regional estimate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prevalence and health effect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non-partner sexual violence.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39]Zweig,J.M.,and Burt,M.R.,2007.Predicting Women's Perceptions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Assault Agency Helpfulness What Matters to Program Clients?Violence Against Women,13(11),1149-1178.
编辑/程激清
C916
A
1672-4828(2016)05-0080-08
10.3969/j.issn.1672-4828.2016.0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