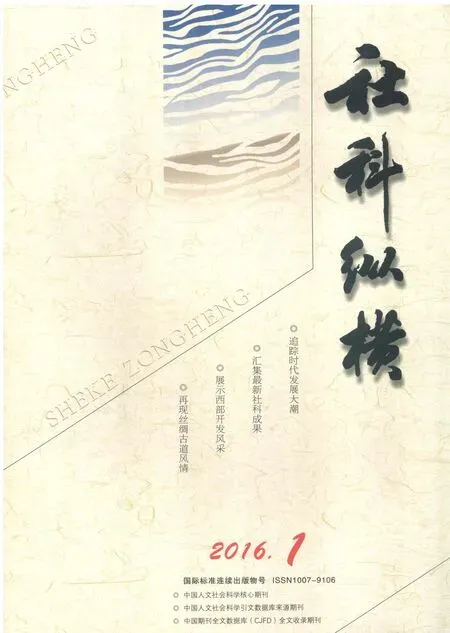刍议80后女研究生性别话语冲突及重塑
2016-04-10高成新邢亚菲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高成新邢亚菲(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刍议80后女研究生性别话语冲突及重塑
高成新邢亚菲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内容摘要】近年来,80后女研究生的择偶问题逐渐进入社会和学界的视野。本文从性别话语的角度指出,传统性别话语与现代性别话语的冲突是80后女研究生出现择偶困境重要成因。从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80后女研究生应该根据自身的择偶境遇重塑性别意识,在对传统性别话语与现代性别话语的颠覆与承继中寻求更为积极的主体性建构策略。
【关键词】80后女研究生性别话语冲突重塑
近年来,80后女研究生的择偶问题日益引发政府、社会和学界的关注,不一而足的择偶困境不仅影响着80后女研究生群体的健康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诚然,80后女研究生择偶困境的出现并非某种单一原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方因素导致的产物。本文对80后女研究生择偶困境成因的审视不在别处,而是着重聚焦于80后女研究生在择偶实践中所面临的传统性别话语与现代性别话语的紧张、错位和矛盾。正是传统性别话语与现代性别话语的内在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80后女研究生择偶困境的出现。为进一步消除80后女研究生所面临的择偶困境,她们应该在不断发展的市场化时代中重塑性别话语意识,从后结构主义视域着眼在对传统性别话语与现代性别话语的颠覆与承继中寻求更为积极的主体性建构策略。
一、80后女研究生的性别话语冲突
在福柯看来,“人类社会中的一切话语都是一种历史性和动态性的社会建构,经由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得以建构出来的话语对于社会秩序的调节及权力关系的排布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1]按照福柯对话语的理解与解释,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性别话语,其旨趣就在于籍由关乎两性之间的规范、制度、惯例等来完成性别场域中的权力安排及社会秩序的运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历史传统、文化制度、社会规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80后女研究生在内的整个女性群体始终呈现出“他者”和“第二性”的符号形象。当然,“他者”和“第二性”的符号的形成除却受到历史和现实的逻辑规约外,女性在身份认同过程中也先天性地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分裂。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个体在进行社会认同的过程中总是将自身所属的群体与其他群体做出比较,继而在主观层面形成所谓的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并在对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区隔中获得社会认同和自我满足。[2]也就是说,个体进行社会认同的结果大抵上应该是积极的,它既助于个体身份归属的识别,也可以实现个体的心理满足和自尊获得。作为社会认同的一个方面,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本应按照一般社会认同的逻辑理路提高女性的性别身份归属感,而实践层面的研究却表明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并没有沿循社会认同的一般逻辑,而是出现了某种错位和偏离,即女性并未因为自身的身份归属而感到自尊的提高和尊严的满足,反而在与男性群体的比较中对自身的性别身份产生了某种疑虑和排斥。[3]
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之所以与脱离出一般的社会认同逻辑,很大程度源于女性在性别意识层面的内在紧张:一方面,女性从思想意识和行为实践等层面可以显而易见地确定自我的群体归属,从而获得性别身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长期的文化制度和历史实践并未给予女性与男性相比肩的身份地位,这就使得女性不可避免地在与外群体即男性群体的审视中感受到自身性别身份的低下和不平等,从而滋生出一种相对负面的群体认同,尤其是在去性别化的市场时代,女性在性别身份认同方面的焦虑和紧张更是显得尤为强烈。她们既需要秉持自身的女性特质,寻求群体归属和自我认同,但又迫于林林总总的压力不得不竭力反抗、摆脱乃至消除自身的性别劣势,以男性化的角色规范要求自我。如此的性别话语建构之于高等教育场域内的80后女研究生而言内在性地蕴含着难以消解的矛盾,80后女研究生既要遵循所属群体角色规范和行为准则;但相对强势的文化资本和日趋激烈的社会现实又使得其不能单向度地完全依照女性的行为逻辑去进行展现自己,而是在一种去性别化的过程中弱化自身的性别身份,以更为普遍化的标准融入到社会结构中,正是这种内在的、先天性的“分裂意识”[4]折射出传统性别话语与现代性别话语的潜在紧张。
作为两种差异分明的性别话语取向,传统性别话语与现代性别话语有着旨趣各异的内涵与边界:传统性别话语主要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润和规训中建构起来的,众所熟知的“贤妻良母”、“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主外女主内”等民谚就是传统性别话语的朴素表达,从这些熟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传统性别话语的内核即在于男女两性基于自然生理差异所形成的社会角色分工,也就是说,男权制或父权制社会结构着眼,我们可以将传统性别话语视之为一种身体话语;作为与身体话语相迥异的话语建构,现代性别话语主要是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发展及西方文化的渗透所形成的话语取向,从本质上来看,现代性别话语的建构基础主要是以强调个体主义的效率原则或市场原则,其要旨在于忽视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在去性别化的社会景观中着重将能力和素质作为审视的标杆和维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现代性别话语可以理解为一种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形成的素质话语。
由此不难看出,传统性别话语与现代性别话语在女性形象的建构上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甚至对立的符号意义,传统性别话语基于男女两性的身体差异而将女性定格和描述为附属性、第二性的存在,这样的性别话语必然会内在地要求女性恪守女性的行为预期和角色规范,在传统的择偶、婚姻和家庭的场域内完成社会地位的获取及自我价值的实现,进而凸显自身的身体话语。而现代性别话语则宣扬为现代社会所推崇的独立、平等、尊重个体、实现自我的价值观,呼吁和主张女性应该摆脱自身的性别劣势,在去性别化的过程中凭借自身的素质和能力积极参与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这就要求女性必须遮蔽和弱化自身的性别意识,以男性化的方式介入到包括择偶、婚姻、家庭等在内日常生活世界和公共领域中。
二、80后女研究生性别意识的重塑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正是这两种壁垒分明的性别话语范式给80后女研究生带来不一而足的择偶困境,一方面,传统性别话语要求80后女研究生应该在择偶时强调身体实践,在行为表达和意识取向中遵循身体话语传统话语视域下女性身份塑造和家庭角色的完成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现代性别话语要求80后女研究生必须凸显出自身高学历教育说带来的素质和能力,在婚姻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弱化自身的性别身份意识,以与外群体即男性群体平等的性别身份意识进入到择偶、婚姻、家庭等各种场域中,正是两种性别话语的潜在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80后女研究生择偶困境的出现,使得80后女研究生的择偶实践呈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纠葛状态。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转换视角,从后结构主义的视域着眼,重新诠释和理解传统性别话语与现代性别话语,那么二者之间的紧张、错位和矛盾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消解,甚至可以将二者统一起来。
总体而言,后现代主义的解释之所以可以在化解女性性别身份危机、助益80后女研究生走出择偶困境方面有所作为,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并未将女性的性别身份视为一成不变的存在,所谓的传统性别话语和现代性别话语也只是在各自的历史惯习、文化传统及社会现实中所形成的性别话语范式,而性别话语形成的动态性和历史性向我们表明性别话语的建构总是处于流变的过程中,这就昭示出女性群体完全可以从传统性别话语与现代性别话语的二元束缚中解脱出来,根据具体的自我需要和社会样态来调整自身的身份建构方式,在对自我诉求与社会规范的综合考量中去实现性别身份的理解及重塑。
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阐述中,男女两性的性别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由后天的关乎性别的文化制度、社会规范、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建构出来的,换言之,男女两性之所以被呈现出不同的符号形象,并非完全是由两性的生理差异所导致的,而是由多种因素参与的历史和社会建构所规定的。因此,后现代解释向我们揭示出,“我们的社会性别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在自己履行的话语实践中占据了这些位置,如此我们作为个人的身份逐渐被建构出来。从这个观点看,我们的自我感知也不是固定的,这是一个过程,一种话语效果,因此也是可变的”。[5]正是在脱离本质主义的理解和言说中,后结构主义为新时期女性性别身份的主体性建构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启示,这就是性别身份的型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总是处于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女性对自我的社会认同与身份建构并不必然地总是在与外群体的比较中才能实现,而是可以依据不同的社会情景去不断调整自身性别身份建构的方式。
由此观之,迥异于传统性别话语和现代性别话语的二元解释模式,后结构主义的阐释无疑解构了男女性别角色的固定化和对立化,而将其性别角色作为一种动态发展的变化过程加以审视,强调性别身份的建构只是一种巴特勒所言的“操演论”或者“表演论”。在巴特勒看来,波伏娃的核心主张即“一个女人所以成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6]虽已开始强调性别身份的建构性,但还是囿于某种或传统或现代的性别文化霸权而无法真正有效突破影响深远的二元性别结构,因为波伏娃的观点暗藏着女性在身体实践与文化建构之间的断裂。为了彻底清算隐匿在传统性别话语与现代性别背后的二元性别论,巴特勒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性别表演论。巴特勒指出,性别身份并不是在自身的逻辑实践中建构出来的,而是受到权力分布的深刻影响,基于权力法则的社会规范、文化习俗等通过种种文化制度建构出我们的性别身份,所以“我们不能从性别关系来理解性别关系,性别关系在本质上完全是一种受权力法则所支配的社会规范,正是在一系列的管控、表演及规范中,我们的性别身份特征方才被创造和建构出来,因此,我们的性别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流动性状态中。”[7]
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有别于传统性别话语与现代性别话语的后结构主义理解为80后女研究生重塑性别意识继而走出择偶困境提供了相对有效和积极的选择性策略:一方面,80后女研究生可以在对传统性别的改造性理解中充分运用自身的女性气质或者身体话语去实现婚恋关系的缔结乃至家庭的建立,但这并不是简单复归到传统性别话语所指涉的附属性和第二性的性别身份,而是要在此过程中充分展现自身的素质话语;另一方面,当80后女研究生由于各种主观或客观因素无法借由自身的身体话语寻求到恰当的伴侣时,可以在对现代性别话语的重新理解中发挥自身的素质话语进入社会结构中,通过社会价值的实现来赢得择偶实践的顺利推陈,这并非是要完全淹没传统性别话语所张扬的身体话语,而是要在素质话语的不断践行中更好地融入到婚配市场中。当然,我们应该指出的是,至于80后女研究生选择何种性别话语作为走出择偶困境的策略,则应该根据自身的身体话语和素质话语而定,两种性别话语虽然旨趣各异,规范不同,但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却消弭了二者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在对性别身份表演性、流动性、可塑性的强调中既解决了80后女研究生在择偶中所面临的性别话语冲突,也为80后女研究生性别意识的重塑提供了积极的建构策略。
三、结语
一言以蔽之,80后女研究生的择偶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毋庸讳言,导致80后女研究生择偶困境出现的成因是众多的,本文对80后女研究生择偶困境成因的剖析主要聚焦于传统性别话语和现代性别话语的冲突。作为两种截然对立的话语取向,传统性别话语所强调的身体话语与现代性别话语所推崇的素质话语之间无疑存在着根本的断裂,身体话语要求80后女研究生遵守女性的思维意识和行为表达,竭尽其能在择偶过程中充分彰显自身的女性特质及身体价值,而素质话语则希冀80后女研究生遮蔽和弱化自身的性别意识,强调以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去赢得择偶实践的成功,这就使得80后女研究生在择偶过程难以寻求到最佳的平衡点。本文认为,从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传统性别话语与现代性别话语之间的对立可以在性别身份的表演性和流动性上统一起来,性别身份的形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情景要求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应该说,正是后结构主义对性别身份的再阐释与再理解为80后女研究生性别意识的重建提供了积极的重塑策略,性别话语的重建不仅有助于80后女研究生重新审视自身在性别话语结构中的话语位置,突破传统性别话语与现代性别话语的束缚,还可以根据自身的境况自由流动和穿梭于身体话语和素质话语之间,最终消解择偶困境。
参考文献:
[1][英]塔尔博特.艾晓明等译.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63.
[2]张莺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06(3).
[3]杨宜音等.性别认同与建构的心理空间:性别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互联网,转型时期的中国妇女[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Smith Dorothy.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A Feminist Sociology[M].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7:6- 7.
[5][英]塔尔博特.艾晓明等译.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56.
[6][法]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
[7][美]巴特勒.宋素凤译.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34.
*作者简介:高成新(1963—),女,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邢亚菲(1991—),女,山西大学哲学学院学生、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9106(2016)01- 0053-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