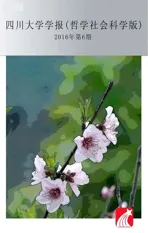从行政赋权到法律赋权:参与式治理创新及其调适
2016-04-07张紧跟
张紧跟
从行政赋权到法律赋权:参与式治理创新及其调适
张紧跟
近年来,为缓解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权力运行与权利诉求之间的紧张,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行政赋权发展参与式治理创新,既改善了治理又亲近了政民关系。但是,行政赋权推动的参与式治理创新却因其内在的弊端而难以持续和扩散。因此,应该适时转变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机制,从行政赋权转变成为法律赋权,使参与式治理创新既于法有据又可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公众参与;参与式治理创新;行政赋权;法律赋权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回应社会需求,创新性地向公众开放公共政策过程并建构各种公众参与地方政府主导的治理过程。尽管这种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①Archon Fung and Erik Olin Wright, Deepening Democrac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London: Verso, 2003,pp.23-25.创新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政府意图,但其赋权于公众参与的行为,不仅提高了治理绩效而且增强了治理合法性,因此赢得了广泛赞誉。②参见王锡锌、章永乐:《我国行政决策模式之转型:从管理主义模式到参与式治理》,《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赵光勇:《政府改革:制度创新与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治道变革的杭州经验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遗憾的是,从2007年被誉为“中国重大项目民主决策史上里程碑式事件”③《厦门PX事件:政府在尊重民意中学习现代执政》,《新京报》2007年12月21日。的厦门PX事件至今,类似的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创新不仅难以扩散,也难以持续。容易扩散的,只有那些概念较简单、操作较简便、短期效果较明显、采纳成本较低廉、获益群体广泛、相关阻力较少的地方政府创新。④吴建南、张攀:《创新特征与扩散:一个多案例比较研究》,《行政论坛》2014年第5期。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创新获益群体广泛、治理绩效显著,既不乏学术界和公共舆论的赞誉也赢得了执政高层认可,还利于自身利益与政绩最大化,⑤陈国权、李院林:《政府自利性:问题与对策》,《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却为何陷入了难以扩散和持续⑥刘伟:《社会嵌入与地方政府创新之可持续性——公共服务创新的比较案例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的泥淖?本文认为,除了中国式“人走政息”的常态因素外,更应该注意到多数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创新属于典型的行政赋权而不是法律赋权,⑦在《行政赋权与劳动赋权:农民工权利变迁的制度文本分析》(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一文中,蔡禾教授将地方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采取的对农民工的策略性赋权称为行政赋权。本文将法律赋权作为政府治理技术中与行政赋权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指通过法律制度确认公众参与地方治理过程的权利并构建有效的权利实现机制,从而提升其参与地方治理的实际能力。在行政赋权下,有关参与式治理的法律赋权虽然在规范层面上有一定彰显和体现,但过于原则和模糊而缺乏具体、细化的规范,公众缺乏可以依据的法律规则和程序来实现参与权利,主要表现为一种策略性治理技术,因此本文强调要实现从行政主导的赋权转向法律主导的赋权。或者说只是基于迫在眉睫的外在压力而被迫采取的应急性策略而不是制度创新。因此,要使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创新可持续发展,必须适时改变现行地方政府赋权机制,使创新发展于法有据。
一、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创新的产生
在当代中国,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既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党一再倡导的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实践形式。早在1982年,我国宪法第41条就赋予了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进入新世纪以来,扩展公民有序参与一再成为党的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与十八大报告关于新时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在此背景下,开放政府治理过程以吸纳公众参与也逐渐成为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性共识。*如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11条明确规定“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第15条明确规定要“增强公众参与实效”。但是,要使参与式治理有效运转起来,除了要求公众自身具有积极参与意愿之外,还需诉诸于地方政府主动向公众开放治理过程,建立健全制度化途径。换言之,在地方政府主导的治理过程中,参与式治理有赖于地方政府行政赋权。
在法理上,赋权与限权如影随形。因此,任何一项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创新措施,不可能只有权益增长而无利益剥夺,创新也不可能没有阻力存在。在地方政府治理实践中,虽然赋权于公众参与既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路径,也有助于遏制公共权力滥用并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与合法性,更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但是与公众分享地方政府治理过程必然意味着对地方政府自身权力运行的限制,因此不愿意开放公共政策过程是地方政府治理中的普遍现象。尽管执政高层一再倡导群众路线并要求“扩展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以及“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公共政策过程”,但是地方政府始终掌控着“水龙头的阀门”。最终,虽然专家智囊、新闻媒体、NGO和普通民众等开始对地方政府治理过程有了一定影响,*参见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A. Mertha,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2.0:Political Plur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Quarterly,2009,p.200;朱旭峰:《中国社会政策变迁中的专家参与模式研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但总体上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依然是较为封闭的精英决策,公众参与仍以原子化、非正式和影响政策执行为主要特点。*参见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Making in Post-Mao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Tianjian Shi,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于是,就形成了中国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权力运行与权利诉求的内在紧张性:一方面,公众参与诉求不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市场化和民主法治的日益完善以及法治教育和媒体宣传的启蒙引导,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走向公民权利的时代”,公众的利益表达能力、公共政策判断能力和行动能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公民懂得运用法律武器和社会舆论来捍卫其合法权益,要求党和政府给予更多权利保护——公民参与越来越主动、公民维权意识日益觉醒、公民强烈要求并熟练运用自由表达权、民众监督权的意识日益强烈。*卢文超:《公民导向:中国政府公共服务标准化的新理念》,《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近年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教育、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这四项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在2010—2014年分别为32.8%、36.8%、35.8%、35.6%,*《财政收入有多少用于民生》,《中国青年报》2015年3月7日。民生财政日益凸显,人民生活不断改善;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是从2008年最高位的0.491连续第7年下降,*《2015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2创12年来最低》,2016年1月19日,http:∥finance.sina.com.cn/2016-01-19/doc-ifxnqrkc6648457.shtml,2016年5月18日。。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得到遏止;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高层更加重视民生建设,2011—201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5221万人,2015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4%,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参保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中共十八大以来致力民生改善取得新成就》,2016年2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25/c_1118160162.htm,2016年5月18日。。所有这些数据为中国民众对党和政府的高信任度打下了坚实基础。于是,满足了基本经济需求的普通民众开始有了日益增长的参与诉求,在制度化参与渠道无法吸纳这种参与诉求时,非制度化参与不断攀升就不可避免。有学者推算2006—2009年每年群体性事件都超过9万起,*《群体性事件上升到每年9万起》,《羊城晚报》2010年2月27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透露,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万起,*陆学艺、李培林、陈光金主编:《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2014年的群体性事件总量高达17.2万起左右。*张明军、陈朋:《2014年度中国社会典型群体性事件分析报告》,《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2015年第1期。
民众日益增长的参与诉求,却面临地方政府治理排斥公众参与的常态化。一是地方政府对公众参与缺乏应有重视。或者是因体制型迟钝,地方政府对公众在合法渠道内的参与诉求置若罔闻。如2008年甘肃陇南“11·17”事件中,从当年9月底到11月这2个月的时间内,拆迁民众虽然不断到市委反映问题,要求政府保障其生计,但一直未得到正面回应。*《甘肃陇南事件仍未透明搬迁决策过程无权威说法》, 2008年11月29日,http:∥news.qq.com/a/20081129/001407.htm,2016年6月26日。或者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完全排斥公众参与,不愿公开或选择性地公开信息。如在2009年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中,地方政府不仅没有及时公开信息,而且完全将公众排除在公共决策之外。*王颖:《环境公共决策中公众参与问题研究——以广东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为例》,《新媒体与社会辑刊》第六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3-74页。二是使既有公众参与形式化。在地方政府治理实践中,公众参与缺少有效的、多样化的交流平台,往往只是地方政府网站刊登决策内容,或者召开座谈会、听证会等,参与方式缺乏应有的广度、深度和密度。有些公众参与机制甚至呈现出形式化、表演化态势,如听证会变成了“涨价会”,频繁上演“听证专业户”*《“听证专业户”为啥频频出现?》,《四川法制报》2015年11月25日。则折射出听证制度缺乏透明公正的代表遴选机制、对公众意见表达缺乏足够尊重。
最终,缺乏公众参与的地方政府治理不仅令长期“一统独大”的地方政府自身日益不堪重负,而且还因为缺乏民主法治约束的权力运行导致公众权益受损,进而引发权力运行与公众参与诉求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势下,被动回应和主动求变就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创新的基本动因。一方面,来自公众对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不作为”与“乱作为”的抗争,以及由此形成的越级上访、群体性事件等非制度化参与,导致局部治理危机倒逼地方政府赋权创新。如2007年厦门PX事件中,地方政府迫于公众的抗争压力,被迫开放政策过程。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主政官员的主动求变,也会推动地方政府赋权创新以适应大转型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如1999年,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在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中,基于农民已经厌倦传统单向灌输说教式思想教育模式,当地党委创新性地建立了民主恳谈的初级形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赢得了农民的积极参与,到2000年8月由中共温岭市委统一命名为“民主恳谈会”。*陈奕敏主编:《从民主恳谈到参与式预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4页。而杭州参与式治理的运作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时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与市长蔡奇的大力倡导和支持。*赵光勇:《政府改革:制度创新与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治道变革的杭州经验研究》,第191页。总之,面对公众日益增长的参与诉求,危机倒逼和主动求变都导致地方政府开放公共政策过程,通过建构新型公民参与路径,试图吸纳民意进入地方政府主导的治理过程。
二、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创新的实践及其成效
从近年来地方政府创新的基本实践来看,参与式治理创新主要体现在:
(一)参与式公共决策
由于由少数政治家、社会精英“自上而下”的传统“沙发式决策模式”日益不能适应这个“走向公民权利的时代”,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创新性地建构公众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的路径。从既有地方政府创新实践来看,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是开放式决策创新。如在杭州等地推行的“开放式决策”创新中,地方政府进行重大行政决策时,在充分公开相关决策信息的基础上吸纳公众以听证会、网络互动等形式参与决策全过程,初步实现了地方政府治理过程公开、透明以及政府与公众有机互动。从既有实践来看,“开放式决策”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有助于提升决策质量和政府公信力,促进了服务型政府建设。*胡业勋、叶睿:《开放式决策的合理性及其实现途径》,《光明日报》2013年8月10日。
二是行政决策咨询制度创新。如广州等地推行的“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要求由专业人士、利益相关方代表、市民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组成的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作为政府重大民生决策征询民意的制度形式,让政府在决策过程中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成为尊重并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载体和平台。这种公咨委制度作为衔接政府部门与公众的重要平台,一方面满足了政府了解民意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公众参与的意愿。
(二)参与式预算
作为一种民众能够决定部分或全部可支配预算或公共资源最终用处的机制,*陈家刚:《参与式预算的兴起与发展》,《学习时报》2007年1月29日。参与式预算使公众能够直接参与预算过程,讨论制定公共预算和使用财政资金,合理确定资源分配、社会政策和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并监督公共支出。推行参与式预算的直接动因是为了缓解地方政府与民众利益冲突、减少民生类信访、降低维稳成本。*陶永亮、林敏、李婕:《中国参与式预算改革的动力机制:基于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视角》,《制度经济学研究》2012年第3期。近年来,浙江温岭市、江苏无锡市、黑龙江哈尔滨市、上海闵行区、河南焦作市、四川巴中市白庙乡、安徽淮南市、广东佛山市顺德区、云南盐津等地方政府持续推进了参与式预算的创新试验。综观各地参与式预算,可区分为三种类型。
以焦作市为代表的参与式预算,通过信息公开、部门申报、财政汇审、民意测评、专家论证、社会听证、人大审查以及审计监督等8个环节的串联,打造出公众参与并与地方政府良性互动的环境和机制。*赵辉、孙善臣:《焦作打造参与式预算的区域样本》,《中国财经报》2011年9月21日。
而江苏省无锡市的参与式预算创新侧重于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项目建设,政府将拟实施的公共服务建设项目方案和预算草案向民众公布,由民众代表投票决定项目的取舍和优先发展次序,并全程参与监督预防腐败。
在温岭的“参与式预算”创新中,民众以民主恳谈为主要形式参与政府预算编制、人大审查与修改预算草案,使预算资金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包建永:《参与式预算:中国预算改革的温岭样本》,《台州日报》 2012年5月23日。
从既有创新实践来看,参与式预算使地方政府预算编制公开、透明、公平,强化了预算监督并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促进了公共利益最大化,客观上也有助于优化地方治理。
(三)参与式环境治理
在当今中国,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近年来,因民众环境权益受到侵犯而引发的环保类群体性事件呈几何级数增加,地方政府承受着严峻的维稳压力。为此,有的地方政府开始通过吸纳公众参与创新环境治理模式。自2011年起,浙江省嘉兴市政府创新环境治理,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搭建平台来发挥公众的参与作用,最终形成了由公众参与权与政府行政权之间互相配合的共治体系,即成立以环保联合会这一社会组织为龙头,市民检查团、专家服务团、生态绿色宣讲团等积极参与的政府引导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新格局。具体包括:建立公众与政府的“圆桌会”制度,通过协商和交流以达成共识并形成政策建议;建立“陪审员”制度,让普通公众做“环境法官”并参加环境问题听证会,维护环境决策和环境审判的公平性。*虞伟:《社会主体之间关系,主从还是平等?——基于环保公众参与嘉兴模式的思考》,《环境经济》 2015年Z4期。
嘉兴市环境治理创新的核心在于开放环境决策过程,吸纳公众有效参与环境治理的行政决策过程。*《从“嘉兴模式”环境公众参与到政府-公众-企业有效对话协商机制建设的探讨》, 2014年1月16日,http:∥www.chinaenvironment.com/view/viewnews.aspx?k=20140116132544968,2016年6月28日。如让市民参与环保审批、环境执法、环保监测等实际环境治理工作;开展让公众代表随机点名抽查企业,并与环保部门、公众媒体全程进行专项执法行动的“点单式”环保执法,围绕污染整治开展市民和专家代表“点单式”限期摘帽验收行动;向社会公开招募热心环保事业、具备一定环保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公众担任“环境法官”,对环保行政处罚案件在法律适用、自由裁量、违法事实等方面进行评议等。*朱海伦:《环境治理中有效对话协商机制建设——基于嘉兴公众参与环境共治的经验》,《环境保护》2014年第11期。其创新不仅有效地激励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而且能将因环境问题而导致的纷争矛盾冲突消弭于萌芽状态,维稳压力大为缓解。
(四)参与式政府绩效评估
近年来,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问题日益突出,而公众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价可以为公众与政府互动搭起沟通桥梁。*吴建南、张萌、黄加伟:《公众参与、绩效评价与公众信任——基于某市政府官员的实证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或者说,藉此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部门的管理效率,从而缓解经济增长引起的社会不满和矛盾,同时降低民主发展带来的潜在挑战。*Bennis Wai Yip So,“Civic Engagement i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Public Sector in China:Building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to Enhance Vertical Accountability,”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No.3, 2014, pp.341-357.为此,参与式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创新得到尝试。地方政府通过网站、电话、信函、入户调查、焦点座谈会、街头采访等多种途径来拓展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渠道。自1999年10月广东省珠海市正式启动“万人评议政府”活动后,类似的活动在杭州、南京等地不断被复制。当前,许多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注重引入公众评价,公众满意度评价占总体评价的比例逐步提高到30%以上,杭州市甚至达到50%;公众参与绩效评估的人数比例也逐步增加,如广东省鹤山市常住人口46万人,每年约有1.2万名社会各界人士参加镇级政府和市级部门的绩效评价,成为我国参与人口比例最大的县级市。*尹艳红:《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新趋势》,《学习时报》2013年4月22日。
地方政府开展参与式绩效评价创新,最大的亮点在于通过将公众评价纳入正式绩效评价机制当中而改变了传统“自娱自乐”的“凝闭式”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整改—反馈”机制通过构建外部评价而形成“压力机制”,进而驱动内部整改,有助于推进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回应公众诉求并推动地方政府绩效持续改进。*程晟:《公民导向:地方政府创新的路径——基于杭州的实证分析》,《领导科学》2015年第35期。
从既有创新实践来看,参与式治理创新通过地方政府赋权构建了畅通的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初步形成了地方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地方政府治理实现了从“维稳”向“维权”的转变,从而能够使矛盾纠纷在萌芽和酝酿阶段得到排解,为实现公民有序参与提供了实践可能性。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参与式治理虽然可能降低决策效率,但充分吸纳民意既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也会消解公共政策执行的阻力;而治理过程中的政民互动,不仅有助于促使地方政府合法、合理、规范地运用和配置权力,防范和克服专业偏执主义,而且还因为增进了公众对地方政府的理解而提高了地方政府公信力。对公众而言,参与式治理创新是地方政府对公众重大关切和基本利益诉求的主动回应,赋予了公众对于地方治理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公众可以通过一定程序与机制来影响地方政府治理过程,有助于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与参政能力。最终,参与式治理创新通过增进地方政府与民众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相互理解与信任从而重塑地方政府与公众关系,促进了地方政府与公众在地方治理中的协作共治。
三、行政赋权的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创新存在的弊端
参与式治理创新虽然主要是地方政府基于改善治理而进行的创新,但其主要内容却是政府赋权于公众参与地方政府主导的治理过程,其实质是“强国家弱社会”结构下的地方政府希望选择一定机制以吸纳伴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成长而日益增长的公众参与诉求。尽管这种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创新已昭示着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中国公民权利的成长,但是厦门PX事件至今,地方政府的反思性学习能力并未如预期般增强,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民意早期被冷落以至演变成中期的‘民议’和后期的‘民怨’”的通行版本依旧在各地不断被复制,标示着这种地方政府赋权创新并未改变公众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权利缺失的基本现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种参与式治理创新的赋权基本上是一个行政赋权过程。也就是说,公众之所以能参与公共决策、公共预算、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等,既不是因为他们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这一法理事实,也不是因为这是宪定权利,而是由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发展的特定需要而采取的治理策略。这种行政赋权性质决定了参与式治理创新中的赋权不是当然的公民权利,而是具有或然性的公民权利,这种或然性取决于地方政府的策略性选择。因此,从既有的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创新实践来看,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下问题。
(一)选择性运用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有效实施,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自身以外的政治力量、权威和压力的敦促与规范、监督和惩罚等刚性的外部约束来推动和保障。*胡宁生、戴祥玉:《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自我推进机制:动力、挑战与重塑》,《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2期。虽然参与式治理创新完全符合执政高层一再呼吁的“扩展公民有序参与”的发展方向,但并未成为中央政府统一部署下的“规定动作”,因此只能诉诸于地方政府的选择性自主和自由裁量。于是,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会存在明显的选择性运用。如在广州,在成功整治同德围交通出行难中发展出的以公众监督咨询委员会为平台而实现的参与式治理创新,*《专家呼吁推行“同德围模式”》,《新快报》2012年12月31日。并未自然延伸至稍后的白云山隧道议题上。*《广州暂缓白云山隧道项目 网友忧暂缓不是叫停》,《羊城晚报》2013年1月19日。而在杭州,自2007年起,按照“民主促民生”的要求,杭州市政府实施“让民意领跑政府”的“开放式决策”创新,不仅使民众与地方政府得到实惠,而且获得了学术界与公共舆论的普遍赞誉并在2010年荣获“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但是,2014年3月25日19时,经历过多次坊间传闻限牌和政府部门辟谣的“口水战”之后,杭州市政府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从次日零时起,在原有“错峰限行”基础上对小客车采取控制总量措施。*商意盈、张乐:《杭州“空降式”限牌引发强烈关注》,《中华工商时报》 2014年3月28日。这一缺乏广泛民调和公开征询而完全在封闭环境中生产出的限牌决定,俨然把“空降式”“半夜鸡叫”式决策当成“先进经验”,不仅让已经习惯于开放式决策的杭州市民感到突然,也令因开放式决策创新名满天下的杭州蒙羞。*《“双输”的杭州“限牌”》,《法制日报》2014年3月27日。即使在以“环境民主”闻名的浙江省嘉兴市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中,也存在着明显的选择性公众参与。其公众参与领域主要集中在协助政府环境执法方面而在环境决策方面却鲜有涉及,环保决策和环境影响评估的公众参与则主要集中在一些第三产业项目、小型工业项目审批之中。*朱海伦:《环境治理中有效对话协商机制建设——基于嘉兴公众参与环境共治的经验》,《环境保护》2014年第11期。
(二)叫好不叫座
在参与式治理创新中,地方政府主动开放公共政策过程,创新性地建构出公众有序参与的路径,但由于带有强烈的动员式参与色彩,因此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现象。动员式参与是地方政府基于某一特定政治经济或社会政策目标而动员公众参与地方政府治理过程的行为,很难被公众认可。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的参与式预算试水来看,尽管学界和媒体都对其评价甚高并寄予厚望,但由于立项与规划环节都由政府部门自行完成,公众参与仅限于审议环节,其参与式预算创新缺乏完整性,最终应者寥寥。*叶静:《《法治蓝皮书》披露广东顺德“参与式预算”模式探索》,《法制日报》2014年2月24日。而在参与式政府绩效创新实践中,因为参与者积极性受挫导致参与人数逐年递减,许多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活动在地方政府的激情动员、组织发动和声势浩大的评价运动之后往往陷入沉寂。如2003年11月,北京市政府考核督查发起“群众评议政府”活动时吸引了141634人参加,而2004年末当北京市政府再次发起同样的网民评价政府活动时,最终只有4000多人参与投票。*单士兵:《网民评政府陷入怎样的“沉默” 》,《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12月14日。2011年6月,东莞市为水价上调听证会邀请市民代表报名参加,却被曝公众“零报名”;而从2013年11月起,东莞市政府官网陆续挂出15份文件向公众征求意见,但半年多来,最多却只有1人参与投票,无人反馈意见。*《一些地方政府确实要补“公众参与”一课》,《现代快报》2013年7月14日。
(三)形式化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尝试通过广泛调研、书面征求意见、公布决策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方式“开门决策”,一定程度推进了科学治理和民主治理。然而,实践中公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很多“石沉大海”、一些遭到公众强烈反对或存在较大争议的条文依然原文保留、听证“专业户”频繁上演、只征求意见而不听取或只听取意见而不吸纳等现象,使参与式治理形式化。*《破解公众参与立法“走过场”困局》,《检察日报》2014年12月29日。一些重大规划与项目决策虽然多在形式上设定了公众参与环节,但在实际运行中往往表现为走过场。*陈丽华、李倩:《县域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公众参与》,《学习时报》2014年9月29日。在参与式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由于地方政府绩效管理过程客观存在着公众与政府部门的信息不对称,公众无法参与有效评估,因此很多“公民参与”往往沦为重形式轻效果的形象工程。*陈慧、祁凡骅、高璐:《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创新研究》,《行政管理改革》2013年第4期。而在参与式预算中,尽管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预算决策过程的某些环节或某些方面,但大部分公众参与只是提供咨询而非真正参与协商,地方政府主导预算过程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何包钢:《近年中国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试验评析》,《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在地方政府“开放式决策”创新实践中,常见的政府公示、座谈会、听证会、网络信息公开等形式存在传播范围狭窄或功能发挥有限等局限性,听证因其“逢听必涨”的基本套路已经让公众对之“审美疲劳”而无法对政府决策民主起到实质保障作用,而专家咨询往往基于行政机关决策需要进行“科学论证”而沦为“开放式决策”的“面子工程”。*胡业勋:《开放式决策法治化的困境与路径构建》,《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11期。
(四)既难以持续又难以扩散
从现有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创新来看,公众参与缺乏可持续发展机制。首先,公众参与地方政府治理存在着或然性。从既有实践来看,许多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创新是广大公众基于自身利益的集体关注而形成的“倒逼机制”与地方政府策略性反应的偶发性“合谋”,这种特定情景下的参与式治理可复制和推广的难度极高。其次,公众参与地方政府治理过程缺乏长效的保障机制。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愿意主动开放公共政策过程以吸纳民意,更多地体现了一些地方主政官员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前瞻,这不仅可能导致常态化的“人走政息”,而且还因为其创新带有非常明显的地方特色以及地方主政官员个性,甚至会因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行制度框架而增加可复制难度。如在广州同德围交通整治中一举成名的公众监督咨询委员会不仅因性质和定位不清引发人们质疑,而且缺乏有效运行的制度保障,以至公咨委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只能期待更多的“明星”级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加入。*《“三无”公咨委生存都很难》,《新快报》 2014年10月14日 。在参与式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创新实践中,许多地方政府只是基于特定政策性需要而开展公民评议,呈现出间歇性的“运动式”特点,没有建立长效机制并形成制度安排。*桑助来:《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模式及展望》,《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1期。即使是那些持续了较长时间且得到广泛认可的参与式治理创新也难以扩散。如历经10余年累积而日渐完善的浙江温岭参与式预算创新,虽然其设计者、执行者以及参与者均认为温岭经验能够在其他地方复制,也倍受公共舆论与学术界推崇,但却始终难以走出温岭。*《浙江温岭:参与式预算推广难点在于放权》,2014年7月22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722/12768350_0.shtml,2016年6月28日。因此,近年来虽然参与式治理创新层出不穷,都获得了上级首肯,但仍然主要停留在基层领域,较高层政策过程中民众参与程度仍然不高,而类似的参与式治理创新将来是否会拓展到更高层次也仍然属于未知数。*X. Yan and G. Xin, “Participatory Policy Making under Authoritarianism: The Pathways of Local Budgetary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olicy & Politics, Vol.44, No.2, 2016,pp.215-234.
四、走向法律赋权
追根溯源,上述种种弊端均因行政赋权式创新的内在机理所致。
一是践行执政高层政治目标的滞后性。在当代中国的多层级政府治理体系下,执政高层制定的政治目标必须通过各级地方政府来实现,但在此过程中由于中央与地方的核心关注点不同而充满了利益博弈。在革命战争年代,群众路线就被党确立为基本组织路线和工作方法;在1982年立宪中,公民也获得了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开始,扩展有序公民参与成为执政高层一再强调的发展目标。但是,在一线直面公众参与的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面对类似发展参与式治理这种软而非硬政策时势必会采取选择性执行策略。除了长期累积的官本位思想之外,地方政府普遍认为公众参与不仅会导致时间、效率等治理成本增加,而且还因为公众缺乏政府治理所需的知识和常识会降低政府治理质量并增加地方治理风险。因此,地方政府在发展参与式治理创新中的具体实践与执政高层的政治目标之间存在着差异性,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在发展参与式治理过程中必然滞后于执政高层的政治宣示,而自主地进行选择性赋权。有研究者对全国部分省份县级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制定重大政策时会经常征求群众意见者不足三成(29.9%),有时会者占49.1%,很少会者占20.2%,即使征求也是形式,而0.8%表示根本不会。*陈丽华、李倩:《县域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公众参与》,《学习时报》2014年9月29日。
二是刺激反应性。一般而言,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创新的启动是特定事件刺激的结果。现实中,由于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的权利实践存在着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的客观事实以及习惯性的“体制型迟钝”,地方政府对公众在制度化参与中所表达的利益诉求要么“管控打压”要么“无动于衷”。于是,事态逐渐升级,公众被迫选择制度外的渠道来表达利益诉求,暴力冲突开始加剧,引起社会舆论关注,上级政府施压“如期而至”,感受到上下压力不可承受之重的地方政府才开始“高度”重视并赋权于公众参与以尽快化解治理危机,从而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刺激—反应特性。这种反应性带有强烈的应急管理色彩,是一种治理技术而很难通过法律、法规规范为一种治理制度。可见,有些参与式治理创新非常注重怎样将眼前出现的公共问题暂时化解,其创新表现出较为浓厚的短暂性、临时性、权宜性色彩。
三是限权。虽然参与式治理创新是地方政府赋权于公众,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与行政自由裁量权使得地方政府很容易对公众参与地方政府治理进行“限权”。而在地方政府治理实践中,由于“对政策执行者容许的自由裁量程度的解释与有意无意的漠视规则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米切尔·黑尧:《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赵成根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这就为地方政府限权大开了方便之门。
1.政务信息公开中的限权。信息公开中的自由裁量导致各级政府信息公开普遍存在着避重就轻、报喜不报忧、信息效用低、获取困难等问题,于是赋予公众知情权的信息公开很容易异化成为对公众知情权的限制。
2.重大行政决策中的限权。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都出台相关文件明确“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必须经过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等步骤”,但是要么各级政府对什么是重大决策规定模糊,要么不公开重大决策的相关信息使参与式治理难以真正运转等。
3.增加参与难度。如在一些行政决策事项中,由于一些行政决定充满着太多技术性和复杂性问题,受到影响的公民必须克服很多困难和花费许多时间才能理解作出决定的过程,最终使公众不得不知难而退。*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7页。
4.压缩公众参与空间。如价格听证会变成“涨价会”后只是让公众来参与选择上涨幅度,城市小汽车“限牌”决策中公众能够参与的只是“如何限牌”的方案而已,参与式预算中公众只能参与审议由政府部门事先完成的立项与规划,而环境治理中公众作为“末端参与与事后参与”的角色固化后也难以真正参与环境政策的决策、执行和评估。
如此这般,行政赋权与行政限制往往是伴随在一起的,导致这种赋权具有不完整性、不稳定性和权变性。
综上,参与式治理创新中的地方政府行政赋权使公众始终处于被动和从属状态,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与行政自由裁量权使其既难以明确保障公众参与的法定义务与责任,又可以对是否吸纳公众参与进行自由裁量。在法理和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中,让作为行政主体的地方政府赋权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公众其实是一种天方夜谭。因此,行政赋权不可能使参与式治理从一种策略型运用的治理技术转变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治理制度。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改革创新都要于法有据,以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为此,应该适时进行调适,从既有行政赋权转变成为法律赋权,以时时回应“公众重大关切”,使作为组织路线和指导思想的群众路线有效运转起来。从行政赋权转向法律赋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赋权主体调适。公众参与地方政府治理作为一种宪定公民权利,由地方政府进行行政性规范是违背基本法理的,应该交由民选代议机关——地方人大来进行规范。因此,对于那些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创新,必须支持地方人大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及时通过法律、法规使其制度化,以保障地方改革创新于法有据。
二是赋权内容调适。首先,应该使参与式治理权利化。在行政赋权中,公众参与地方政府治理更多沦为一种行政治理技术;而在法律赋权下,公众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理所当然成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为此,作为一种法律上有效的、正当的、可强制执行的主张,*Samuel Stoljor,An Analysis of Rights,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4,pp.1-6.公众参与式治理不仅需要制度化成为法定权利并获得法律保障,而且还应该将纯粹法律文本上的“纸上权利”转变成为公众参与治理实践的“行动权利”。而要完成这种转化,不仅需要法律赋权能使公众积极行使权利,而且还需要参与和问责使地方政府能够在治理过程中履行尊重、保护和实现公众参与式治理的义务。*邓佑文:《行政参与的权利化:内涵、困境及其突破》,《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1期。因此,在法律赋权中,公众参与地方政府治理除了实体性规范外,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有完善的程序性规范。
其次,要完善参与式治理权利的内容。在行政赋权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选择性信息公开、随意选择参与主体、使参与机制形式化、压缩公众参与空间等来限制公众参与。为此,法律赋权应该使公众参与式治理成为一项内容完整的权利,对于应该吸收公众参与的事项,法律法规应当明确、具体地赋予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实施权、监督权等并规范公众参与式治理的机制与程序,以严格的法律责任和司法救济制度作为保障,这样才能使参与式治理落到实处。
最后,要明确地方政府保障参与式治理的义务。在行政赋权中,参与式治理虽然让公众进入治理过程,但只是把公众当作意见咨询和信息提供的对象;而在法律赋权中,要使地方政府承担对参与式治理有效运转的尊重、保障和实现义务。为此,法律赋权还应该明确地方政府保障公众参与治理权利实现的基本义务以及相应的义务履行机制。
结 语
参与式治理创新既反映了改革年代中国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后的必然诉求,也是实现地方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路径。因此,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创新无疑是对党和政府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尤其是近年来强调发展有序公民参与以及时回应公众重大关切的积极回应。但是,无论是地方主政官员的前瞻性改革还是偶发性地方治理危机倒逼所引发的参与式治理创新,都由于没有实现从行政赋权向法律赋权的转型,始终是“自选动作”而没有成为地方政府的“规定动作”,而且不少具有示范效应的创新举措渐渐因人走政息、改革动力不足而最终“了无生息”以及难以扩散,造成了“常使英雄泪满襟”而令人扼腕叹息的“创新浪费”。可见,如果不改变既有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创新机制,其可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因此,应该尽快实现从地方政府行政赋权创新转向法律赋权创新,使公众参与地方政府治理成为法定权利,进而明确地方政府的义务并保障公众有效行使其权利。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治国家的发展战略逐步确立,对传统凝闭型行政体制的改革也日益深化。党的十八大已经明确提出要保障公民参与权并把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确立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此背景下,完善现行法律、法规过于原则和模糊的参与式治理赋权规范也正在成为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要义。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和相信,随着法治与参与式治理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法律赋权将逐步得到全面确立,地方政府参与式治理必将走向规范化、常态化与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曹玉华)
From Administrative Empowerment to Legal Empowerment:the Innovation of Local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and Its Adjustment
Zhang Jingen
In recent years, som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introduc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rough administrative empowerment in order to ease the tens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appeal, improving the local governance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eople. However, the local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innovation promoted by administrative empowerment can hardly continue because of its inherent drawback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form the local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mechanism from administrative empowerment to legal empowerment, which will not only base local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innovation on law, but also contribute to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cal governments, public participation,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innovation, administrative empowerment, legal empowerment
张紧跟,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广州 51027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12&ZD04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港澳与内地参与式地方治理比较研究”(14JJD630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维权抗争治理中的民主建设研究”(12YJA810019)、教育部2013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D035
A
1006-0766(2016)06-0020-10
§国家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