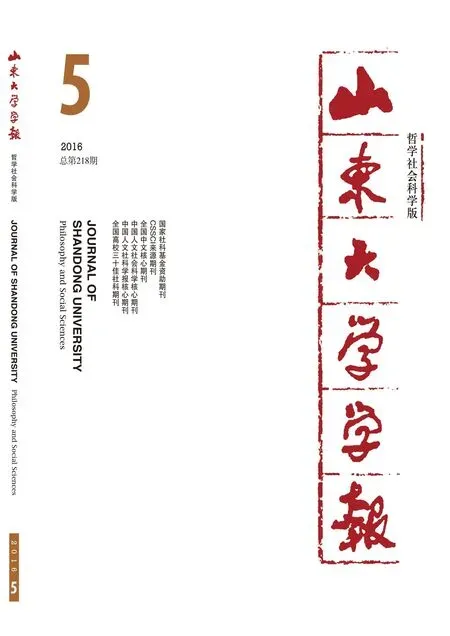社会控制视野中的社区治理及其协商民主指向
——以对济南市若干社区的现场调研为实证基础
2016-04-07魏治勋
魏治勋
社会控制视野中的社区治理及其协商民主指向
——以对济南市若干社区的现场调研为实证基础
魏治勋
随着基层社区传统权威的衰落和一元化社会控制的式微,中国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控制失范的危机,同时也蕴含着走向现代协商民主治理机制的契机。但当下基层社区普遍形成的“压力型体制”及其结合了传统中国统治技术的所谓“新治理术”,反而是走向协商民主的重大障碍。我们需要加强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为社区治理现代化创造良好氛围。
基层社区; 社会控制; 新治理术; 协商民主
近年来,中国正在城市和乡村建立起以“社区”为结点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通过颁布和实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等基层自治法律,城市和乡村社区治理都以走向民主法治化轨道为基本规划,且被认为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容。按照规划,中国基层社区的建设目标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体,如此则协商民主自应成为社区治理实践运作的基本逻辑。目前城乡社区的治理体系、治理机制和治理现状都明显存在与规范要求相脱离、相背反甚至异化的失范现象,支撑基层社区治理的所谓“新治理术”在某种程度上亦存在有悖民主法治要求的地方。因而,分析和诊断社区治理失范问题的背景、体制与机制成因,挖掘并阐明指示社区自治制度建设的协商民主路径,对于当下基层社区治理和社会控制殊具价值。
一、基层社区自治体的类型及其社会控制状况
中国当前广泛存在的以居委会和村委会为自治机构的基层社区,其前身分别是城市或乡村中的基层行政单位——居委会和行政村。虽然1954年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将居委会界定为“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但根据1962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为农村社区前身组成部分的“生产大队”被界定为农村最基层的掌管“生产工作和行政工作”的经济核算和行政管理单位。近年推行社区建设后,尤其在户籍制度弱化的背景下,城市中的“居”和农村中的“村”都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基层社区自治单位。基层社区是“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行民主法治制度建设的最具普遍意义的载体,也构成了广大中国公民民主参政的基本平台,理应成为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节点;同时,从国家实施社会控制的视角看,广大基层社区自然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推行其治理措施、达成社会控制目标的基本支点。由于各个社区所处地域的自然禀赋千差万别,人文社会条件各不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各有高低,这些基本差异必然影响到法制转型后的社区,无论在其内部构造、运行机制和外部特征上,都
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因而必然影响到社区在基本类型和治理方法方面的差异。因而,对中国社区自治制度性质的把握不可能脱离历史,任何制度类型的形成有其历史根源,而历史成为制度形成的真正渊源,历史也同时是理解制度的关键。
从我们调研所及的济南市三类典型的社区来看,其中每个典型社区都代表了社会控制的一种类型。这三个社区分别处于济南市城区中心、城乡结合部以及城市远郊,我们分别称之为Q社区、F社区和W社区。Q社区地处繁华的城市中心地带,直接由曾经的城市基层行政单位居民委员会转型而来;处于城乡结合部的F社区,虽然目前已被急剧扩展的城区包围,但原本是集体所有制的近郊行政村,因而其所有权性质并未因城市化而改变;而地处远郊的W社区,则是由农村行政村改组而来。历史渊源的差异和所处环境的不同,决定了这三个社区各自面临相当不同的社会控制对象和任务。Q社区管理机构惟一而单纯的任务就是对区内居民的行政管理,是当下纯粹的城市基层自治单位。近年来社区严格地执行了法定的社会控制任务,将犯罪率和社会纠纷数量都降到了最低水平,打造出了远近闻名的“模范社区”品牌。而F社区则有着复杂的成长背景,“城中村”的跨界特性以及“村改居”的体制转型,使得它必然背负更为复杂的社会控制任务:社区办工商业是社区居民的经济支柱——而对经济来源及其分配的控制,恰是社会控制的基本部分,社区无论在社区自治、行政还是经济分配上,都能够将社会控制主动权抓牢;长期聚居形成的共同体情感并未消泯,社区同时还是其居民的情感家园,因而甚至连居民的红白喜事、居民外出旅游服务,社区都无偿承包下来。社区各方面事务运转良好,其社会控制从表象看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就W社区而言,它原本就是一自然村落和基层行政单位,曾经承担了社区居民的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需求。但现实的发展却与这种预期多有偏离,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个人主义思想增长,农民原子化现象十分突出”*辛允星:《农村社会精英与新乡村治理术》,《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农村社会原有的“政社合一”结构基本解体。于是,广大农村面临再组织化和重建社会控制的问题,这是农村社区自治机构必须承担的首要职能。但包产到户的经营机制以及广大农民不再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现实状况,使得此类农村社区无法继续充当居民经济依靠的角色。更加突出的一个变化是,随着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并定居城市,居民原有的固定的情感与宗族纽带逐渐松弛乃至消失,农村社区不再具有“熟人社会”的凝聚情感功能,其情形正如学者所言的:改革开放以来,“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村庄公共权威经历了以‘私营化’为表征的蜕变,村庄从道义型共同体转向利益型共同体,农村社会精英逐渐成为具有排他性利益的独立群体”*宋蜻、杨善华:《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以苏南某村为案例》,《中国社会科学》2005第6期。。W社区展示的正是这样一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的整体景观,有着典型代表性。
可以说,三个不同类型的社区尽管在社会控制和社区自治方面各有特色,但也都表现出了共同的问题指向,那就是:“社区建设的各种活动主要是政府性的行为,而不是社区居民的自发自主的行为”*王小章、王志强:《从“社区”到“脱域的共同体”:现代性视野下的社区和社区建设》,《学术论坛》2003年第6期。。因而,随后的问题就是,在原有高度统一的社会控制衰退之后,如何在基层社区发展日益多元化、社区控制日趋松散化的情况下,按照宪法法律规定的社区自治目标取向,重构一个规范的、有活力的协商民主机制?这几乎是当下基层社区治理尚未实现而应当实现的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目标,需要在日益加快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予以探索推进。
二、社区精英与社区社会控制体制结构的塑造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亦在渐进转型中型塑着自己的体制结构与权力运作形态,这在我们前述三种社区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并以各不相同的权威形式在社区中建构并维持着相应的秩序状态。但其中各不相同的秩序状态共享着一种统一的本质内涵,那就是:无论它的具体形式有什么特殊性,它都是一种基于对权利和利益的承认、保障和协调基础上的社会控制形式。虽然这些具体的社会控制形式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宪法和法律,而是对前者的具体化和现实化,但是它至少在形式上不能与正式法律制度相对抗;各类社区的社会控制体制结构与权力形式总体上同样要服从于现有的法律架构。对于前述三种类型的社区而言,其微观体制结构和社会控制机制的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就不仅取决于现有的制度环境,而且必然深深地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利益与社会关系格局、社会权力网络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我们能够具体分析社区实施社会控制的体制结构与权力机制是如何完成其形态塑造的。
首先,这里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指古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传统中长期存在的基层治理结构和权力形态对当下社区体制结构与权力运作之构造的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传统唯一没有中断的国家,历史上的既有制度结构和文化传承对于现代中国的制度建设和社会控制会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某个国家的社会变迁离不开自己的历史,要在自己的历史基础上转变”*李善峰:《我国目前的乡村关系与社会控制:特别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这就是美国制度学派创始人道格拉斯·诺斯所言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就我们考察的Q、F、W三种不同类型的社区而言,“历史传统”方面却并无明显差异。原因在于,传统中国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控制方式,对于基层社会都意味着一种几乎一致的“同一性”:基层社会的社会控制乃是建立于以乡绅或士绅为主体、以统一的儒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为基础、以国家与社会分工为基本架构的一体化统治。这种家国一体化的统治形态为中国古代社会控制提供了三个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而且迄今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控制与形态,这三大构成要素是:其一是“目标性要素”,这是通过社会控制要达到的目标状态,主要是对理想的“差序格局”社会秩序的追求;其二是“规范性要素”,这是由各种制度、习惯和惯例构成的规范制度,其中浸透着儒家“亲亲尊尊”的价值和精神;其三是路径性要素,这是为了达至社会控制目标而应当采取的方法、手段和技术的总和*王鑫:《纠纷与秩序——通过纠纷解决所实现的社会控制》,《政法论坛》2010年第1期。在该文中,作者对三个要素的排序是规范性要素、路径性要素、目标性要素。。还应当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要素需要被提炼出来,这就是“主体性要素”,这一要素在古代中国表现为乡绅与士绅等地方名流,孔飞力称之为“士绅操纵”或“名流操纵”*参见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页。。在当代中国基层社区组织中,则表现为各种类型的“能人”,包括政治能人、经济能人、经纪人,当然他们一般要以合法的社区管理者角色的形式出现在基层社会控制的过程与功能展示舞台上。作为社区治理的掌控者,社区管理者不是任何单一职能的科层制干部,而是全面掌握和运作社区政治、经济、卫生、秩序的多面手,其内部分工则往往是暂时的和随机性的;尤其是从其掌控社区秩序的手段来看,更是多元的、复合的、富有策略性的,从而社区才能够负担起“单位”剥落之后的复杂社会功能,成为精微个体和庞大国家之间的必要中介,避免了社会中空的出现*王小章、王志强:《从“社区”到“脱域的共同体”:现代性视野下的社区和社区建设》,《学术论坛》2003年第6期。。就此而言,当代城市社区管理者多具有“政治能人”的特征,而与现代社会自治性治理机构的科层制职员相当不同。借助于符合现代法制的某种结合形式或嵌入路径,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精英们,已经成功地进入到社区社会控制的体制结构之中,成为政府管理与社区控制的“参与者”甚至“合谋者”和“主导者”,这一点与古代中国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状况颇为相似。

最后,社会权力网络是社区社会控制体制结构建构的基础性要素,同时也是贯穿于“历史文化传统”和“利益—社会关系格局”两大要素之中的勾连性部分。社会权力网络不同于杜赞奇所谓“权力文化网络”,“权力文化网络的一个基本功用,在于这种网络提供包括宗教信仰、家族情感和乡村人民所承认并受其规约的是非标准等象征和规范,它能够导致乡民对权威合法性的认同”*魏治勋:《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合法性分析范式》,《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相关论述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页。。可见,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本质上是一套权力合法性的论证系统,而社会权力网络则是社会权力存在与运作所形成的复杂系统。之所以说社会权力网络与历史传统相勾连,在于中国历史上久已存在的乡绅权力结构与当下社区权力结构之间,既有着历史影响关系又有着现实功能的近似性。其中,社会权力网络与“利益—社会关系格局”之间的勾连在于,前者是后者的载体,而后者构成前者的目的或本质。因而,社会权力网络就成为社区权力体制和治理体系的基础,社区权力结构体现的就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博弈过程和结果,并必然对社区的社会控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社区的社会权力网络,既可以从权力主体的角度予以分析,也可以从权力性质的层面作出区分。其一,从权力主体角度看,社区机关、社区居民、社区各类能人等构成了社区内部的权力主体,而乡镇或街道办事处则成为对社区权力格局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权力实体,社区社会控制目的的达成必须在这些复杂的权力主体间实现良好而均衡的秩序关系。应当说,对于Q、F和W三个社区,前述权力主体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只是在不同的社区类型其功能和重要性有所差异。其二,从权力性质来看,费孝通曾将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划分为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在当代城乡社区仍然可以找到其对应形式:对于横暴权力,费孝通认为,“它是压迫性的,是上下之别。……都是统治者的工具”*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页。。某些社区存在的黑恶势力显然属于非法的横暴权力,而当社区机关或其附属组织采用暴力或隐性暴力形式追求其社会控制秩序时,它也体现或多少沾染了横暴权力的色彩;社区居民以及其中尚未融合进社区权力机关的各类能人,则手握“同意权力”,他们的社会舆论评价和投票方向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社区机关及其管理者构成,一旦社区管理者被选举产生,则他们就掌握了“同意权力”,这是社区控制权力的核心力量;而社区机关尤其是其中的党组织和社区中有威望的长者,则明显的属于教化权力的类型,它们对利益方向的调整、对秩序的评价和对具体主体行为的规范,都明显具有教化权力的性质。这三种类型的权力既非完全融合,也非完全对立,而是在现实的社会控制过程中呈现出复杂关系。按照亨廷顿的相关理论,在民主政治的实践过程中,系统中各势力愈是均衡就愈能够达成民主性,系统的民主架构就愈加稳定,组织动员能力也就愈强,因而他主张:“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塞缪尔· 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73页。。国内学者亦指出,中国基层社会之所以在建立自主性模式中面临困境,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在基层社会权力系统中参与度不够且没有能够形成均衡的力量综合*吴思红:《论村民自治与农村社会控制》,《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6期。。就我们观察到的三个类型社区而言,仅W社区在宗族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表现出了较为合理的均衡性,但也存在暂时性和不稳定性的隐忧;而在Q社区则存在社会权力的行政化和外部化(更多的服从于社区权力结构之外的上级政权)的问题;F社区则存在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一体化从而可能压制社区居民所代表的同意权力的缺陷。事实上,三个类型的社区都无法达成社会权力网络长期稳定的均衡,从而必然影响其社会控制的过程、技术和效果。
三、社区社会控制机制与治理技术的变异
尽管当下中国基层社区社会控制呈现多元化发展状况,总体上仍然可以抽象出某些共性特征,其中又蕴涵或共享着某些关于中国基层社会控制机制、基本手段和技术,它们共同构成了学者们称之为“新治理术”*关于“新治理术”,学者们更多的是基于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控制手段和技术概括而提出的概念,名之为“新乡村治理术”。参见辛允星:《农村社会精英与新乡村治理术》,《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赵旭东、辛允星:《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的基本内容。深入描述、分析和界定这种所谓的“新治理术”,对于有效把握中国基层社区社会控制发展脉络并有针对地给出矫正性建议,将大有裨益。
从基层社区权力结构以及其基本构成部分的自身特性,我们可以一窥基层社区管理精英的某些基本特性:其一,社区精英和社区管理机构对于国家基层政权具有相当的依附性,并往往充当政府社会控制和社会治理“合谋者”角色。尽管村民自治法将社区明确为自治统一体,然而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社区不但总体上要承担“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职能,同时基层政权社会治理的所有指标都要分解到具体社区并由其实际完成;不仅如此,国家基层政权还紧紧地控制着社区选举的过程和结果,社区治理所需要的经济来源和政治支持也不可能脱离国家基层政权的掌控,这就使得基层社区事实上成为了国家基层政权的支部,具体承担着基层政权分解而来的社会控制任务,中国基层社区俨然处于一种承接上级行政管理任务的“压力型体制”*项继权:《短缺财政下的乡村政治发展:兼论中国乡村民主的生成逻辑》,《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3期。之下。但从表象上看,社区管理者产生于社区居民的民主选举,其行为目标和行为逻辑必须受制于全体社区居民的意志,这就使得社区管理者一旦面对基层政权和社区居民意志不一致的要求时,就会产生“角色冲突”和行为选择的两难。根据学者们的观察,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社区管理者和绝大多数社区精英都义无反顾地倒向了基层政权,从而充分地表现出其依附性和外生性特征,事实上成为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合谋者”。其二,社区精英和社区管理者相对于存在于其中并以之为服务对象的广大社区居民,越来越表现出疏离性的特征。产生这种疏离性的原因,一是相对于近代以来国家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的统一控制,当下的基层社区社会精英和社会势力发生了明显分化,社区管理组织不再是基层社会唯一的核心,其他社会权力对于社区社会控制形态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多方面影响力。二是社区管理组织对于基层社会本身发生了明显的抽离效应,严重弱化了其对社区的影响力。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社区管理组织仍然是社区的中心和国家权力的末梢,但其与社区居民的关系逐渐走向冷淡甚至紧张,“基层干部面临着社会权力持续弱化的现实”*赵旭东、辛允星:《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其三,基层社区的管理者们同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理性人”,社区管理者角色并不能抑制其逐利本性,尤其在经济能人成为社区管理者的情况下,其管理者地位和对权力缺乏监管的支配反而往往会为其经济利益的追求提供便利。基层社区管理者的这种逐利性特征,导致其对公益事业不够关心,且容易因与社区居民存在利益冲突而导致关系紧张,也必然会降低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其四,社区精英和社区管理者所具有的依附性、疏离性、逐利性特征,最终导致了基层社区权威的弱化,它使得相当一部分社区逐步丧失了形成“向心力”的价值观基础,导致了社区民众与社区管理者之间空前信任危机,其结果是基层社区越来越难以履行好其社会控制功能。
基层社区这种权威弱化趋势还在继续,但这并不意味着基层社区的管理者及其精英们在社区社会控制手段和技术或曰治理术方面在趋向弱化和式微。相反,基层社区的权威愈是弱化,其控制手段和控制技术就愈加需要发达和多样化。原因在于,只有借助于更加丰富多样的控制手段和技术,才有可能保证社会控制水平不致于明显降低。从现有的文献和调研材料来看,基层社区为了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较为普遍地使用着如下治理手段和技术:
其一,随着电子技术的发达和经济水平的增长,城乡社区普遍采取了较为严密的监控手段。从我们实地调研的三类社区来看,普遍都安装了较为严密的电子监控系统,尤其是位于城市中心区的Q社区,其电子监控设备已经做到了无缝对接,举凡社区居民的进出、交易、交谈等日常生活行为,都在监控之内。吉登斯曾经指出,居于权威位置的个人对另一些个人的直接活动实施直接督管已经成为社会监控的重要形式,对居民的监控、社会监控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在日益福利化的现代国家尤其如此,“现代国家的政府能力与它能否成功地维持监控的运作有关,而这种相关性只有在它们允许对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方方面面的监控时方可显示出来”*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73页。。可以说,从监控设备下对居民日常行为的监控以达成安全和秩序,到依赖于各种档案对居民生活状况和救济活动的监管以达成福利和安定,当代基层社区的社会控制已经无法脱离监控手段和技术的协助而独立运作了。并且,这种监控体系还必然带有“反思性再生产”的性质,既有的监控体系设计会不断被监控实践所批判和改进,反过来也是如此。可以说,就社会监控这一点而言,中国基层社区在社会控制技术上是大大超越于其经济发展阶段的,已然成为基层社会普遍依赖的”新治理术“的核心部分。
其二,只要社区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社区管理者普遍倾向于采取”父爱主义“的福利手段,以此换取绝大多数社区居民的服从。福利手段一方面可以看做是一种重要的监控技术,但它又不限于监控技术狭隘的物理特性,它同时是一种父爱主义的博取合法性的有效手段。类似于F社区,在大多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基层社区,社区管理者都倾向于以普遍的优厚福利换取居民的支持和服从,同时对福利政策的操控也使得对居民的社会控制达到了深入细微的境地。从总体上看,优厚的社会福利往往能够达成其它任何社会控制手段无法想象的社会控制效果。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基层社区中的经济能人如果能够牺牲一部分经济利益或者将其致富手段“无私”扩展服务于广大社区居民,则其往往能够以此为捷径成为基层社会权威;但同时,当其不正当地运用经济手段时,则往往会败坏基层社会的治理质量,当前基层社区的贿选现象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其三,在城乡结合部和城市远郊社区,传统的宗族治理手段复活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宗族势力一度作为负面因素受到打压而趋于消失,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基层社会社会控制的弱化,宗族势力在中国广大乡村甚至某些城市角落得以复活并成为影响当下基层社会控制的重要势力。在社区自治实施过程中,“他们往往利用血缘纽带关系,或者拉帮结派形成利益团伙,采取非正当手段控制村民选举,获取自治权力。一旦自治权力到手,就与乡镇政府分庭抗礼,乃至排斥村庄组织,而且利用族众或帮派的凝聚力和盲从特点及国家政策的有关信息,使乡镇政府工作非常被动乃至失去管理效能”*吴思红:《论村民自治与农村社会控制》,《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6期。。虽然有学者指出,在其调研过程中,并未发现宗族势力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明显影响*赵旭东、辛允星:《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估计与其择取样本的数量和合理性有关。宗族势力的复兴对于基层社区的治理和社会控制影响巨大,一个基本条件在于,在大多数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社区、城中村转化而来的社区,由于居民结构长期以来缺乏变化,往往形成大姓宗族对小姓宗族的压制和控制,它极易导致社区选举流于形式,从而最终使得社区自治归于无效。同时,在这类社区,包括小姓宗族和外来居民在内的“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往往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在现有选举结构和决策结构中,“少数人”的意愿和意见往往被“多数人”的决定所淹没*参见魏治勋:《全面有效实施宪法须加快基本权利立法》,《法学》2014年第8期。。因而对宗族势力与社区管理权力相融合的现象必须保持警惕。
其四,社区管理者亦会模仿国家基层政权,对社区控制指标进行分解,并适当引入协商民主机制促进分解指标的完成。从我们的调研看,多数基层社区在承担了基层政权的任务指标后,会对指标进一步分解,然后逐步落实到社区内部更加精微的结构中去。比如,Q社区就将可以分解的所有治理指标下达给社区的各个“楼长”,各个“楼长”都由本楼居民民主选举产生,对本楼的治安、卫生、收费、维修等多项指标负组织职责,结合本楼居民和社区共同完成对楼政的治理。在这里,在“国家政权末梢”的末梢,我们见证了近乎完全意义的协商民主的实例,从其实际运作的过程和效果看,都达到了相当理想的水平。
其五,在正常社会控制手段不能达成控制目标的情况下,社区也会采取隐性的横暴权力驯服秩序破坏者。基层社区管理层虽然并非完全基于民意产生,但在其实施社会治理和控制的过程中,总体上仍然比较尊重民意,否则一旦出现社区居民罢选甚至示威事件,相关管理层人员也很难得到基层政权的庇护而延续其管理生涯。因而,基层社区管理层必须尽力在基层政权的支持和民众的选票之间取得平衡,为此,尊重民意、为民谋利也必须成为其日常治理的重要选项。但是在日常治理过程中,总会有某些个别社区居民不服从管理甚至采取对抗姿态,这种情况下,如果其他柔性措施不能奏效,某些社区组织可能会寻机采取硬性的管控措施,包括教训、禁闭、体罚等非常手段。这些社区管理层就这样通过采取包括横暴权力在内的多种治理手段和技术的有机结合,在自身权威性普遍下降、社会转型日渐加速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大致维持社会治理的效能和社会控制的力度。
从以上论述可见,当前基层社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方面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怪相”——社区权威的式微和“新治理术”发达之间的明显失衡,其中既蕴涵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必须直面的危机,也蕴涵着走出治理危机的契机和方法,关键在于我们能够明确地洞悉什么才是社区走向“善治”的变革方向和必由之路,以及如何正确地区分和看待所谓“新治理术”的问题、合理性及其可能价值。在此前提之下,尽管现状并不乐观,但我们仍然可能把握一个相对确定的未来图景。
四、协商民主指示社区“善治”未来

以前述理论观照中国基层社区治理实践,我们发现:尽管基层社区之间差异较大,社会控制任务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被法律赋予“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一定位,则鲜明地揭示了国家为其设置的共同的目标方向。按照基层自治制度相关规定,社区是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目标,社区与基层政权之间是指导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从社会控制角度来看,“国家是在弱化外在力量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强化内源性自我控制,逐步建立一种适合农村社会发展的自主性治理模式”*吴思红:《论村民自治与农村社会控制》,《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6期。。这种治理模式有助于训练社区居民的民主素质和民主能力,有助于推进中国基层社区民主政治的发展。
但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却提醒我们,中国基层社区协商民主和法治建设的重大进步,在根本上必然与国家整体的民主法治进程相关联。因此,对于当代中国基层社区协商民主的确立和社会控制方式的根本转化而言,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建设,为社区治理现代化创造良好氛围;另一方面,政府必须主动培养具有市民精神和权利意识的新型社区居民,通过不断的民主实践锻炼他们的自组织行为实践能力,激活其民主法治意识,促进基层社区民主力量的发育;在遵循社会正义原则、“法的统治”与民主协商原则前提下,尽快推动社区治理及其社会控制走向健康稳定的现代制度之路。
[责任编辑:李春明]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he View of Social Control and its Tendency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EI Zhi-xun
(Law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As the waning of the tradi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declining of the unified social management model, the basic-level society in China is facing the crisis of disordering in social control, as well as the chance leading to moder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However, “Stabilization-orientation” in the basic-level communities at present and the so-called “new administrative strategy” correspondingly which embraces traditional governing technologies become the major barrier of promo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order to creat good atmospher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Basic-level Community; Social Control; New Administrative Strateg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2016-03-06
济南市软科学计划“商谈民主与城市社区现代治理模式研究——以济南为例”(20130215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法治文化的传统资源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14ZDC023)。
魏治勋,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