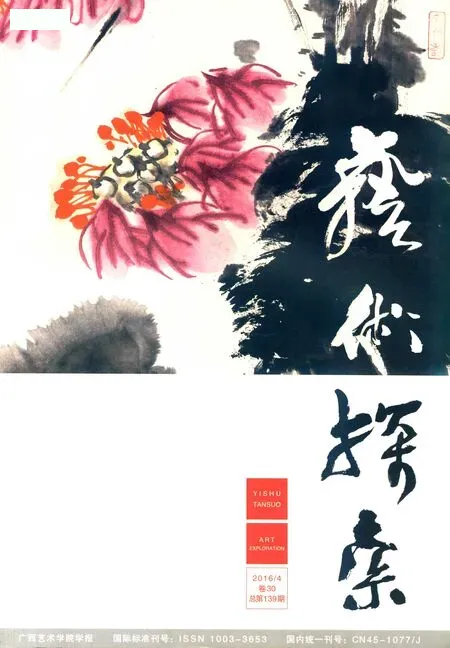隋唐以前艺术门类理论渊源考
2016-04-04韩刚
韩刚
(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隋唐以前艺术门类理论渊源考
韩刚
(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魏晋南北朝各艺术门类(诗、文、书、画等)理论异军突起,花团锦簇,变古则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盛况,主要是因为此前源远流长之乐论的奠基;之所以乐论能为其奠基,是因为“通感”这一深层艺术文化基因之奠基;之所以“通感”基因能为其奠基,是因为“中和”这一更深层文化基因之奠基。此外,当时随佛教文化东进的古印度艺术理论影响亦为渊源之一。
艺术门类理论;通感;中和
2011年3月,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把艺术学列为独立学科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艺术学理论旨在打通各门艺术之间的壁垒,通过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构建涵盖各门艺术普遍规律的宏观理论体系。不幸的是,该学科之设立及主旨颇为时人批评。笔者对此颇关注,始疑渐信。因为古代文化艺术中有大量与此相关的无尚家珍,只要静心读书,认真梳理,踏实研究,集腋成裘,“涵盖各门艺术的普遍规律的宏观理论体系”构建当不难期待。本文,引玉之砖而已。
一、隋唐以前文化艺术中的“通感”基因
考论隋唐以前艺术门类理论渊源,应从中国文化艺术中独具特色的“通感”说起。
“通感”英文为“synaesthesia”,源于希腊文。自钱钟书将“synaesthesia”译为“通感”并加以阐释后,“通感”便为文艺理论界认同与普遍使用。钱氏说:“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1];“寻常官感,时复‘互用’,心理学命曰‘通感’(Synaesthesia);征之诗人赋咏,不乏其例”[2]483-484;“寻常眼、耳、鼻三觉亦每通有无而意彼此,所谓‘感受之共产’(Sinnesgutergemeinschaft);即如花,其入目之形色,触鼻之气息,均可移音响以揣称之”[2]1073。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叙述法国象征派理论时也涉及此一问题:“他们又主张各种感觉可以默契旁通,视觉意象可以暗示听觉意象,嗅觉意象可以旁通触觉意象,乃至于宇宙万事万物无不是一片生灵贯注,息息相通,‘香气、颜色、声音,都遥相呼应’(用波德莱尔的题为《感通》[Correspondances]中的诗句),所以诗人择用一个适当的意象可以唤起全宇宙的形形色色来。”[3]
眼(视觉)、耳(听觉)、舌(味觉)、鼻(嗅觉)、身(触觉)之间的通感自古以来便存在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隋唐以前各类文献中更是俯拾皆是,说它是中国文化、艺术之深层基因应该是不会出现“于古不典”的情况的。
古人常将各种知觉相提并论,这暗示了它们之间可以通感。如“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国语·郑语》)[4]470-473;“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墨子·非乐》)[5]155;“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6]2749;“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荀子·劝学》)[7];“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
不共声,皆快于耳”(《论衡·自纪篇》)[8];“虽云色白,非染弗丽;虽云味甘,非和弗美”(《抱朴子·勖学》)[9]98;“哀弦微妙,清气含芳”(曹丕《善哉行》)[10]391;等等。
进一步地,古人并未满足于在各种知觉并置中暗示其间的相通性,而是对它们之间的通感进行了明确表述。如《左传·昭公二十年》提出“声亦如味”的重要观念,导乎先河,所用“如”字值得再三参详。又如《左传·昭公十一年》:“今币重而言甘,诱我也”[11]2060,《国语·晋语》:“又有言甘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4]270,其中“言甘”者,今所谓“甜言蜜语”也,这是以“味”说“言”之通感。《易·系辞上》:“同心之言,其臭如兰。”[12]79《孟子·告子上》:“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6]2749这是以家畜肉味之美说圣人经典中义理予人心的怡悦。此种通感后世引申甚多,如后汉蔡邕《被州辟辞让申屠蟠》:“安贫乐潜,味道守真”[13]871;西晋陈寿《三国志·魏志》裴松之注:“引身深山,研精味道”[14]1058;等等。《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太史公曰:“冯公之论将率,有味哉!有味哉”[15],《后汉书·郎顗传》谓黄琼“被褐怀宝,含味典籍”[16],《三国志·蜀志·杨戏传》谓刘子初“抗志存义,味览典文”[14]1148,此三者是以“味”说言论与典籍内容之通感。其他如晋陆机《拟西北有高楼诗》:“芳气随风结,哀响馥若兰”[10]688-689,是以声响说气味之通感,等等。
在文艺理论领域,各知觉之间的通感也大量存在。
就音乐而论,如《乐记》:“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17]1536-1537其中“象”“文采”“饰”等本为造型艺术概念,用以论音乐,系“通感”。三国魏嵇康《声无哀乐论》:“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13]1329以造型艺术术语“象”“形”论音乐亦属“通感”。
就书法而论,东汉崔瑗《草书势》是我国最早的书论篇章,“观其法象”是文中提出的重要理论命题。“法象”作名词指自然万物,如《易·系辞上》:“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12]82;作动词为效法、取法之意,如《论衡·雷虚》:“奉天而行,其诛杀也,宜法象上天”[8]65。“观其法象”乃观察草书由效法自然万物而来的艺术形象,即文中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中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兽跂鸟歭,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或点,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栗,若据高临危,旁点邪附,似螳螂而抱枝。绝笔收势,余綖纠结;若山蜂施毒,看隙缘巇;腾蛇赴穴,头没尾垂。”[18]3意为草书结体点划充满了有如自然万物那样的情态、生机与动态美。一般而言,书法乃静态抽象的空间艺术,却给人鸟振翅、兽踮脚想要“飞移”,狡兔突然受惊将要“奔驰”等动态意象与时间感。“山蜂施毒,看隙缘巇;腾蛇赴穴,头没尾垂”等则以自然物象为言进一步点出了草书笔划的曲折、回旋、流动之美。显然,无论是“观其法象”还是引文中涉及的“兽跂”、“鸟歭”、“狡兔暴骇”、“连珠”、“螳螂抱枝”、“山蜂施毒”(意为山峰间云气缭绕)、“腾蛇赴穴,头没尾垂”等自然形象,均当为绘画(或造型艺术)术语,崔瑗却以之论书,表明在其心目中,书和画是可以“通感”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谓《周礼》载“六书”之“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18]12。汉字衍化之初多源于“象形”,实则是以绘画方式提炼概括自然物象,此盖为“观其法象”说的基底。崔瑗《草书势》规范了后世书论的衍化方向,汉魏晋南北朝的书论都强调了这一方向。如蔡邕《笔论》:“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18]43其中“须入其形”“纵横有可象者”者,“观其法象”也。《篆势》:“字画之始,因于鸟迹,苍颉循圣,作则制文。体有六篆,要妙入神。或象龟文,或比龙鳞,纡体效尾,长翅短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缊。”[18]39这是在观象基础上提出了“要妙入神”的更高要求。钟繇《用笔法》:“繇解三色书,然最妙者八分也。点如山摧陷,摘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去若鸣凤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灿灿分明,遥遥远映者矣”。[18]51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就文学诗歌而言,如萧子显《文学传论》:“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19]1062,言文学、绘画、音乐相通。《文心雕龙》中颇多以“味”论文者,如《宗经》:“余味日新”[20]27,《明诗》:“张衡怨篇,清典可味”[20]65,《情采》:“研味李老”[20]415,《隐秀》:“深文隐蔚,余味曲包”[20]497,乃以“味”言“义理”;《情采》:“繁采寡情,味之必厌”[20]416,《声律》:“吟咏滋味,流于字句”[20]431,《总术》:“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20]530,《物色》:“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20]567,则是以“味”言文学写作手法。《物色》:“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彩附声,亦与心而徘徊”[20]566,则属文、画创
作手法相通之论;《声律》:“声得盐梅,响滑榆槿”[20]432,“榆槿”是古代作使菜肴滑润之调味品,故此是说文之声律与味觉之通感。钟嵘《诗品序》谓五言诗为“众作之有滋味者”[21]9,又谓“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21]7,是以“味”言诗歌审美。《诗品》中“指事造型,穷情写物”“润之以丹采”“雕文织彩”“朱紫相夺”等则表明诗与造型艺术(雕刻、绘画等)相通。
就绘画而言,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18]288,是以“味”说绘画形象的通感。南朝宋王微《叙画》:“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珪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18]295这是说音乐、宝玉予人之愉悦与自然山水牵动人之绘画情思可相通感。谢赫《画品》“陆杲”条:“传于后者,殆不盈握。桂枝一芳,足敷本性”[18]307-308,是以桂枝的芬芳气味说绘画作品的通感。姚最《续画品》“袁质”条:“曾见草《庄周木雁》、《汴和抱璞》两图,笔势遒正,继父之美。若方之体物,则伯仁《龙马之颂》;比之画翰,则长胤《狸骨之方》。虽复语迹异途,而妙理同归一致。”[18]330表明文学、书法、绘画之间可相通感。
二、隋唐以前文化艺术中“通感”基因之基底
古人不但明确表述了各知觉之间的通感,而且指出了发生通感的共同基底——中和。中和(中庸、和谐义)观念为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根基,据文献记载,起于上古尧舜禹时代,尧以“允执其中”云云命舜(《论语·尧曰》)[22]2535,舜又以之命禹(《尚书·大禹谟》)[23]。“中庸”观念最早由孔子提出,《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22]2749孔子之孙子思撰《中庸》作了详细阐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7]1625汉郑玄《目录》:“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又于“君子中庸”下注曰:“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17]1625。现在看来,“中庸”主要指折中、适当、不走极端。“中庸”即以中为用、取用其中的意思。[24]“中国”之名主要以此。
就文艺“通感”而言,如《左传·昭公二十年》提出“声亦如味”重要观念的语境便是在晏婴与齐侯论“和同”问题时:
公(齐侯)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11]2093-2094
约成书于战国初期的《国语·郑语》记载郑桓公与史伯之间关于“和同”的问答云:
(郑桓公问史伯)曰:“周其弊乎?”对曰:“殆必弊者也……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4]470-473
《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22]2482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正是中和之美的典范。如《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22]2469;《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22]2517(按:淫,过度、无节制、滥,非中和也。)
《老子》第十一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25]其中所谓“圣人”者,执持中道者也,之所以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难得之货令人目盲、耳聋、口爽、心发狂、行妨,是因为过度。
《孟子·告子上》:“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6]2749其中“理也,义也”者,中和、仁义之道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26],而尧命舜、舜命禹者,“允执其中”也。
《淮南子·齐俗训》:“今夫为平者准也,为直者绳也。若夫不在于绳准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术也。故叩宫而宫应,弹角而角动,此同音之相应也。其于五音无所比,而二十五弦皆应,此不传之道也。故萧条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27]180其中“萧条”“寂寞”者,中和境界也。如《淮南子·俶真训》:“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虚无寂寞,萧条霄雿,无有仿佛,气遂而大通冥冥者也。”[27]19
汉扬雄《法言·问神》:“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28]其中所谓“君子”者,“和而不同”之仁者也。如《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2]2508;《论语·里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22]2741;《乐记》:“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条畅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17]1535
三国魏嵇康《声无哀乐论》:“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13]1329“天地合德”之“合”可训为“和”,和睦、和谐、融洽义。如《吕氏春秋·有始》:“夫物合而成。”汉高诱注:“合,和也”[29]124;《吕氏春秋·古乐》:“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高诱注:“合,和谐。”[29]52
三、隋唐以前艺术门类理论之乐论渊源
魏晋南北朝各艺术门类理论繁荣之前,唯乐论独擅胜场,仅就此而论即不难知晓,在传统文化序列中,乐论当为诗、文、书、画等艺术门类理论之源。何以?
首先,在古人的心目中,乐是包罗万象的,诗、文、书、画等自然不能例外。如西汉司马迁《史记·律书》:“六律为万事根本”[15]100;《史记·乐书》唐张守节正义:“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岁有万物成熟,国有圣贤宫观周域官僚,人有言语衣服体貌端修,咸谓之乐”[15]95;等等。显然,这不但是由自古以来“礼乐”文化的性质决定的,而且在古代文化中,“乐”早于“礼”,“乐教”早于“礼教”。徐复观认为我国古代的教育是“以音乐为中心的”,他举《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为证并解释说:“成均即成调,乃指音乐得以成立之基本条件而言;是‘成均’一名之自身所指者即系音乐,此正古代以音乐为教育之铁证……又今文《尚书·尧典》,舜命夔典乐,‘教胄子’,以乐为教育的中心……日人江文也在其《上代支那正乐考》中谓中国古代以音乐代表国家,音乐的发达,较西人为早(原书四—五页),此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30]
其次,在魏晋以前的古人心目中,“乐”是可以包括诗、文、书、画等其他艺术形式的。如《墨子·非乐》:
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灸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5]155
不难见出,墨子“非乐”所表达的不仅是音乐、舞蹈等听觉、表演艺术,还包括“刻镂、华文章”(雕塑、绘画)等视觉艺术与“高台、厚榭、邃野之居”等建筑艺术。《庄子·天道》:“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之谓天乐”[31]128,则似将雕刻纳入乐范畴。“至乐无乐”为《庄子》文艺思想主旨,可《庄子》一书中涉及不少相关绘画和工艺美术故事,如“解衣盘礴”“梓庆作鐻”之类。而在《养生主》中,庄子谓庖丁“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31]55,则是认为“解牛”与乐舞是相通一致的。“去无用之乐”是先秦法家文艺思想的主旨,可在《韩非子》一书中却有“以象为楮叶”“墨子木鸢”“周君画筴”等精巧绝妙的工艺美术品制作故事。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说:“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岳),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32]郭氏是看到了这一点的。
是以,大致上可以说艺术门类理论尚不发达的魏晋(220~420年)以前的乐论是包含了各文艺门类的,乐论实际上相当于文艺理论,特别是艺术理论,“乐”的内涵与外延与现在所说“艺术”相当。亦正因为此,魏晋南北朝由于因缘际会,各文艺门类自觉建立自身系统理论时,之前高度成熟、源远流长的乐论
自然成为他们借用的共同资源。如《乐记》在论述音乐起源时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17]1527“心”为音乐之源,这一观点深刻地影响到此后各文艺门类理论源起观。如《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33]269;钟嵘《诗品序》:“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怀?”[21]12言社会、人事感荡人心从而产生诗意;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13]80,言文源于人之情应四季、万物的感荡;《文心雕龙·原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20]1,《物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诗人感物,连类不穷,流运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20]566,言文源于心应物色之感荡;宗炳《画山水序》:“余眷恋庐、横,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嶘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34]12,言“愧不能”重游的遗憾产生画意;王微《叙画》:“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此画之情也”[34]15,此言秋云、春风感动人心,产生画情;等等。《乐记》在谈音乐功能时最为强调与政治相通之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17]1527;“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7]1527;“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17]1534;“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17]1536;等等。此观点对后世各门类文艺理论功能论影响十分深刻,如《诗大序》开篇即谓:“《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33]269;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35];谢赫《古画品录》:“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36];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37]。等等论述,如出一辙。
魏晋以前文艺中,音乐与诗歌距离最近。因为当时乐、诗、歌混杂,诗为歌(乐)词,大都可以入曲和弦与歌唱。如《文心雕龙·乐府》:“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20]83。钟嵘《诗品序》:“古曰诗颂,皆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21]26。而《诗大序》中很多内容更是与《乐记》重合。萧子显《文学传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属文之道……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19]1062,乃借乐论文。《文心雕龙》第三十三篇则是论述声律的专篇,里面的几乎所有术语与观念均原属乐论,如“赞曰:标情务远,比音则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声得盐梅,响滑榆槿。割弃支离,宫商难隐”[20]432。南朝齐梁间袁昂《古今书评》:“皇象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18]204,系借乐论书法;谢赫《画品》“姚昙度”条“同流真伪,雅郑兼善”[18]307中“雅郑”即雅乐、郑声(俗乐),系借乐论画。
四、隋唐以前艺术门类理论之天竺文化渊源
无独有偶,天竺(古印度)艺术文化中亦有各艺术门类之间相通的观念,而魏晋南北朝古印度文化随佛教东来,深刻影响汉文化是大事因缘,虽然这不是隋唐以前艺术门类理论渊源的主要成分。如成书于公元4~7世纪的古印度《毗湿奴往世书》(Vishnupuana)的附录(Vishnudharmottara)第三部分《画经》(Chitrasutra)谓:“不知《舞论》,难解画经。”[38]160梵语“chitra”原义为绘画,兼指雕塑。《舞论》(Natyashastra)为印度第一部传统美学经典著作,相传是婆罗多(Bharata)所作,成书于公元2~5世纪。梵语“natya”原义为戏剧、舞蹈或舞剧,故《舞论》亦可译作《戏剧论》,相当于中国《乐记》。《舞论》全面论述了戏剧包括舞蹈、音乐等表演理论,其所倡导的“味论”,是印度传统美学的核心,被奉为印度艺术的圭臬和通则,不仅适用于戏剧、舞蹈、音乐和诗歌,而且扩展到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领域。《画经》指出:“绘画的原理适用于铁、金、银、铜和其他金属雕塑,也适用于石头、木头和灰泥制作的雕像”,“这些原理来源于舞蹈的原理,凡是在舞蹈中没有的原理也不会在绘画中使用”。[38]160-161
结语
魏晋南北朝以前,“乐”的内涵与外延与现在所说“艺术”相当,乐论即艺术理论。故魏晋南北朝各
艺术门类自觉建立自身系统理论时,之前高度成熟、源远流长的乐论自然成为共享资源。另外,西来的天竺艺术理论也当产生了部分影响。而这些之所以成为可能,端在于传统文化、艺术中的“通感”“中和”基因。
[1]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64.
[2]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90.
[4]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
[5]孙诒让.墨子闲诂[M].诸子集成(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6]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王先谦.荀子集解[M].诸子集成(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11.
[8]王充.论衡[M].诸子集成(7).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286.
[9]葛洪,撰.庞月光,译注.抱朴子外篇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10]逯钦力,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2]王弼,注.孔颖达,等.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3]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4]陈寿.三国志[M].百衲本《二十五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15]司马迁.史记[M].百衲本《二十五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243.
[16]班固.后汉书[M].百衲本《二十五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736.
[17]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8]潘运告.汉魏六朝书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
[19]李延寿.南史[M].百衲本《二十五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20]黄叔琳,注.李祥,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1]钟嵘,著.徐达,译注.诗品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22]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3]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36.
[24]孙钦善.论语注译[M].成都:巴蜀书社,1990:100.
[25]魏源.老子本义[M].诸子集成(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9.
[26]焦循.孟子正义[M].诸子集成(1).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186.
[27]刘安,著.高诱,注.淮南子注[M].诸子集成(7).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28]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M].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160.
[29]高诱,注.吕氏春秋[M].诸子集成(6).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30]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31]郭庆藩,辑.庄子集释[M].诸子集成(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32]郭沫若.青铜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187.
[33]郑玄,注.孔颖达,疏.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4]王伯敏,任道斌,主编.画学集成[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2.
[35]郭绍虞,王文生,编.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1.
[36]谢赫.古画品录[M].《画品丛书》本.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7.
[37]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1.
[38]王镛.印度美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校对:刘绽霞)
ExplorationofCategorizedArtsTheoriesbeforeSuiandTangDynasties
HanGang
Artistic theories onvarious artcategories,including poetry,prose,calligraphyand paintings,flourished and ushered in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atthattime.The extraordinarydevelopmentofartistic theories atthattime bloomed on the basis ofthe profound musicaltheories inherited over ancient times which fed on the underlying culturalelement ofsynaesthesia,which exerted its influence through the fundamentalChinese culturalelementofharmony.The thriving artistic theories in thatperiod alsodrewonartistic doctrines fromancientIndia introduced toChina togetherwithBuddhismatthattime.
Artistic Theories,Synaesthesia,Harmony
J120.9
A
1003-3653(2016)04-0053-06
10.13574/j.cnki.artsexp.2016.04.006
2016-04-15
韩刚(1971~),男,四川仪陇人,博士,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