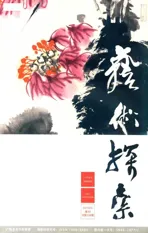油画写意:风格、形态或精神
2016-04-04郑工
郑工
(中国艺术研究院 美术研究所,北京 100029)
油画写意:风格、形态或精神
郑工
(中国艺术研究院 美术研究所,北京 100029)
写意在当下最重要的意义是对抗当今画坛流行的图像与观念,重新唤醒人心,张扬人的个性存在的价值,同时将形式纳入绘画本体的讨论中。就写意油画而言,其最重要的特征是让抽象的形式出场,实现现代主义的形式转向。我们需真正领会“写意”精神,以境界提升人格,以修持养成品性,同时将自我置入民族文化的历史,消解当代性与传统的对立,并以人为基点,在公共领域建立一个可以相互沟通的话语平台。
油画;风格;形态;书写性;写意精神
一
有人说:“写意不是风格,而是一种形态。”有人说:“写意不是形态,而是一种精神。”各有所指,各有道理。尤其在中国油画这一问题上,说到写意,总有一个上下文关系,在特定的语境里,你会明白其所蕴含的意义。若将“写意”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提出,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其意义的共通性,如何为其定义。刘骁纯说“写意在本质上是个性的”[1],正是从绘画主体出发,以为写意的意指不在对象的客观世界,而在于人的自我心境,在于个体立场与自我规范。他不说风格而说人,可布封(George-Louis Leclercde Buffon,1707~1788年)说“风格即人”①(法)布封《论风格》,转引自刘文立《布封及其名句“风格即人”》,《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期,第28页。,其文章笔法能恰如其分地表达人格规范,犹如人之“风骨”。于是,我们是否想到,从写意出发论其艺术,由此产生的所有评价均应回到人的问题上,比如创作意念中的合目的性问题,艺术表现中的合规律性问题,以及形式结构中的协调性问题,均见之于人的意志,故“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②(战国)商鞅《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石磊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然意志又是一种落实了的心理状态,无论是其动机还是所选择的方法与媒介,在行为的整个过程中都有意志的参与,控制与协调人的行动。
但这一“人”的概念肯定不是自然人,而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文化人,由某一文化所塑造的人,与自然的人性有关,与个体的人性也有关。自然、社会、个体,这三层关系在人的问题上混合交织在一起,我们只能在理论上加以区别。当我们的话语越靠近人的个体,其文化的差异性就不断地被释放出来,我们眼前的世界也就越丰富多彩;当我们的话语越接近人的自然性,其文化的共通性就不断地显露出来,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对话也就越容易进行,沟通也成为现实。我们谈文化,谈不同文化中的人,谈艺术,谈人的意志与个性,实际上都在不断地移动这一话语砝码,使其定位在某一点上。用中国古代的概念,就是“权”——权衡或权重,也可视其为权变。话语的阐释与开放度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人的主体谈写意。可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刘骁纯将写意置入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中,看到其如何从写实形态中分化出来。他没有受中西文化的局限,看到了共通性,并指出其历史之变的时间差,即宋代中国与19世纪中叶的欧洲;他也没有受材料媒介的局限,如绘画媒材
与雕塑媒材,而注重形态上人的审美感受的共通性,与手法、风格有一定的关系,如“删繁就简”“笔墨韵章”“离形得似”,却没有将某种手法或风格固化,不形成绝对的关联。至于他说“写意本质上是个性的”,我以为就超越了单纯的形态学论述,进入了与历史发展相关的现代性论述。他讲形态的历史性“分化”,强调创作中的“个性”,无不在说明“自由与民主”的现代意识,并直接指向一个“新的”世界体系,一个将个体的生存与奋斗纳入其中的新时代的出现。最让人关注的是,他将“写意”纳入对现代性的分析模式,以此讨论现代性起源。如中国宋代,“写意”与文人画、僧人画、水墨画在这一历史节点上的各种关系,一一进入他的视野。
二
如此这般,写意似乎又与手法、媒介、风格发生关系了。说到文人画缘起,必然谈到唐代的王维,其“一变勾斫之法”①(明)董其昌《容台集》(下),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王维以诗入画,以诗境开拓画境,诗画相宜,更何况他还参禅悟理,学庄信道,工于音律,这些在思想与精神上对绘画的转型均有助益,但根本之处还在笔法。所谓“写”之本义,就在笔法、笔道、笔性,这是中国画形式之本体。晚唐张彦远说“书画同体”②(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1,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1页。,用意亦在于此。虽然他还说“意存笔先”③(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1,第23页。原文为:“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但此“意”并不等于作品形式所负载的内容,不是19世纪中叶之前欧洲美学所表述的形式与内容之二元关系。
中国画所谈之“意”,是由用笔本身所生发出来的一种臆想或意象,是对笔的精神补充,与人的气息、气脉相连。故张彦远又言:“画尽意在”,“虽笔不周而意周也”。④(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1,第24、25页。原文为:“向所谓意存笔先,画尽意在也。……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象已生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北宋苏轼也说:“笔略到而意已俱。”⑤(宋)苏轼《东坡画论·跋赵云子画》,王其和校注,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至清代的恽寿平还说:“于笔墨不到处观古人用心。”⑥(清)恽寿平《南田画跋》,张曼华点校、纂注,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用心,即用意,心意相通。此处接近于19世纪后半叶西方形式主义美学观,但也不能完全等同,因为那“有意味的形式”,其意味在形式本身,而形式自产生之后便独立自在了,形式与质料(form and hyle)一起构成其本体性的存在。这在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中,成为其理论的支撑点,不仅是形式美学,也见之于材料美学,乃至影响到后现代艺术中的视觉观看与呈现,其角度或曰文化立场与中国不同。中国书画中的“形意”论,若依据于笔线、笔道,或直接称其“笔墨”,其物质性的因素是被不断忽略的,其精神性的因素是被不断放大的。故其笔墨形意,在审美上注重的是人的心理作用与精神品质,所谓意象森森,所谓气象万千,所谓意气风发,莫不如是。苏轼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⑦(宋)苏轼《东坡画论·又跋汉杰画山二则》。,说的是同样道理。这是中国书画笔墨的形式主义路线,或者叫做“形意模式”,其“形”不是指与物相关的外部形象,而是与用笔有关的内在形式。在这一点上,书与画不同。书法,尤其是狂草之书,可以将用笔之形式推向极致,可以抽象化,建立新的形式秩序。绘画之用笔,虽也引书入画,但只在形意,如苏轼《枯木瘦石图》,梁楷的《泼墨仙人图》与《李白行吟图》,或米氏云山,都没有将绘画笔线或笔道引向纯粹的抽象形态。元代的赵孟頫没有,明代也没有,无论是董其昌的山水还是徐渭的花鸟,无论那些画家如何讲究书法用笔或如何恣情任性,笔下的物象依然存在。究其原因,我以为是人的绘画意识在起作用,形意中的“意”在制约着用笔,其形式的纯化也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牵引出“意象”与“意境”。若言“意象”,则重点在“象”,注重的是由“意”所规定的“象”之品性;若言“意境”,则重点在“境”,注重的亦是由“意”所规定的“境”之品位。无论“象”或者“境”,都是主体观照的对象,只有“写意”立足于主体自身,反观自身,自修于身。
三
就中国当代写意油画的发展状况而言,其并没有突破形式对质料的限制,让质料自行出场,而是
“神遇而迹化”,在形式与质料所构成的各种关系中寻求各自的解决方案,让精神感化并沟通形式。在语言形态上,“笔触”与“痕迹”这两个概念较为凸显。回溯西方艺术史中,这一现象可在19世纪下半叶印象派绘画之后至20世纪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中寻得印证,而在中国艺术史中,却能从宋元以来的水墨画一路贯通。在画论上,可前溯南朝之宗炳,如“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2]。也包括谢赫“六法”中的“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①(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1,第13页。在思想根源上,可追溯春秋时之老庄。一如道与物的关系。老子曰:“惟恍惟惚”,“不自见”,“不自是”。(《道德经》第二十一、二十二章)庄子曰:“磅礡万物以为一”,承上德,广被四方。(《逍遥游》)二如心与物的关系。老子曰:“涤除玄鉴”,“明白四达”。(《道德经》第十章)庄子曰:“心斋”,“坐忘”,或“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引述这些文献的目的,意在将我们的视线从宋元穿过汉唐,直接与先秦的老庄思想相联系,梳理出绘画中“写意”一脉的历史渊源,进而想到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绘画的现代变革所抬举的传统是汉唐美术,且冠之以“写实”之名,而在打倒“王画”的背后,难道仅仅是“陈陈相因”“因循守旧”的问题吗?不是的,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处理,也可以看成文化的清理,即将文人画以及中国的“写意”精神一同搁置了,以为那是主观唯心之论,不符合科学的唯物主义,以此阻断与西方现代主义美术思潮的联系,阻断人的个体性以及其所阐发的自由精神。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后,“表现”与“抽象”的艺术观一度被屏蔽,形式主义美学遭到政治的批判,同样在“破旧立新”的现代话语中,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对传统的认识也扭曲了。中国画被改造,笔墨问题首当其冲,个性被限制在艺术手法或风格的范畴内,“写意”也就成了“意笔”,与“工笔”相对。“逸气”是不能谈的,“逸格”是被批的。但那时的中国油画,在民族化的思潮中使“写意”获得了一个生存的空间。尽管被限制在形式语言的范畴内,但毕竟通过“写意”,我们能够触摸到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批留洋的油画家回国后这么做了;五六十年代,有一批留苏的油画家也这么做了,包括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以及罗工柳主持的油画训练班,其教学思想以及学员们的毕业创作,都存在明显的民族文化意识与中国做派。画家的个体性一旦被融入到民族的集群文化中便合法化了,但“写意”再没有高调地存在。
四
“写意”,这一概念最富有中国表情。进入21世纪,中国的一批油画家为何在各种思潮的冲撞中重提“写意”,并在面对物象的写生活动中持续探索了十多年,其当代性意义何在?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对抗当今画坛流行的图像与观念,重新唤醒人心,张扬人的个性存在的价值,同时又对个性的养成提出要求,将形式纳入绘画本体的讨论中。
这几年,有关“书写性”的问题在中国绘画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甚至有人说“书写性”是中国当代绘画艺术转换的核心,“离开了书写性,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创造性活力”②夏可君《“书写性”十问》,《绘画的书写性——余像绘画第二回展》“前言”,北京通州区宋庄当代艺术馆,2011年7月17日。。可见,在当代艺术环境中,“书写性”就不单纯是毛笔的笔性以及相关的笔墨问题。或者,更简单些,书法用笔已不再是“书写性”的核心问题,只有创作主体的心气与意念,即“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庄子·达生》),才是我们寻问“书写性”的根本。凝神,不是凝视也不是凝听,与视、听感觉器官似乎切断联系(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与内在的心气、意念相关,而这一切又通过身体传达到手,由手及笔,最后集中于毫端。所以,中国画家讲究手性、笔性,也谈纸的性能,其感觉都在这几方面串通,且个体感觉的特殊性尤为突出。中国文人画家一再强调“胸有成竹”,并非其多么在意于外部的视觉形象,而仅仅将其作为先置条件,因为“胸有成竹”,画时才可将注意力全部投放在笔墨上,才知道自己要表现什么,故可“落笔倏作变相”[3];或“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4]。近代齐白石也说:“要写生而后写意,写意而后复写生,自能
神形俱见,非偶然可得也。”①齐白石《鱼乐图》(又名《雏鸡小鱼图》)题跋,原文为“善写意者专言其神,工写生者只重其形。要写生而后写意,写意而后复写生,自能形神俱见,非偶然可得也。白石山翁制并记。”又,“草野之狸,云天之鹅(鹤),水边雏鸡,其奈鱼何。三百八十二甲子老萍又题。”原图142cm×41.5cm,1926年作,北京画院美术馆藏。此意者何在,或此意者何解?我以为,此意是意图,也是意志,目的明确,但有幻想的成分,既涉及具体事物及其表象,又形成一种反思性的判断——“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是反思性的”[5]。反思判断是审美判断,是作为形式的感性判断,而对形式的探求与人的知性又发生关联。关于抽象的形式意念(Form)与具体质料间的关系,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年)说得更明白,如“质料应该消失在形式中,物体应该消失在意象中,现实应该消失在形象显现之中”[6],以此获得审美的真正自由。一百五十年后,席勒如果再看当代艺术界那些直接利用材料进行创作的现象,不知又作何言语。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对艺术问题的理解,多停留在黑格尔有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论述上,并受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影响,将各种技巧视为表现的工具和手段,形式不独立,技巧和手法也不独立,人的创作个性也难以独立,模仿与再现依然是我们的创作法则。所以,重提“书写性”的目的是破障,从技巧与手法的独立,寻得形式的独立,寻回自我的存在。举个极端的例子,如邱志杰的行为艺术《重复书写一千遍〈兰亭序〉》,前后花了五年时间,形式、内容与结果都不是他关注的,他注意的只是书写的过程,如何把握自我的心气与意念。或许这是中国式的解读,其中可能也存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年)的书写观念。或者,我们也可将其视为“书写性”的宣言,因为他将书写作为创作的核心理念,对“书写”这一现象进行直观的把握,在“踪迹”的问题上思考内驱力以及写出来的重量。
对写意油画而言,强调“书写性”最大的作用就是激发自我意识,但没有放弃对象世界,而是强化艺术的个性,也没有让感性的形式完全蒸发,而陷入空洞的概念游戏。其最重要的特征是让抽象的形式出场,实现现代主义的形式转向。书写,意味着主体的在场,现场感十分重要,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写意油画者们为什么热衷“写生”的原因。他们是让现实的存在于临场状态中敞开,同时也让自我的意识敞开,看到那些看不到的东西,因为他释放了形式对事物的压抑。书写是流动的,也是开放的,有着许多不确定性,包括方向上的不确定性。
五
范迪安认为,“写意油画”的本质支撑和内在学术理想是“写意精神”,也因此展现具有东方文化属性的语言特征。[7]戴士和也说:“写意既是指一种画法,也是指一种精神。”②戴士和《常写生更写意》,《库艺术》2013年第34期。他认为那是更高的境界,含有人格的力量,不是一般的生动能及。何为精神?一般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在生理学上,精神指的是“精气”和“元神”,是生物体脑组织所释放的暗能量。在哲学上,精神指的是过去事和物的记录及此记录的重演。回到“写意”问题上,把握“精神”对于一个族群的文化传承至关重要,对于一个创作个体的生命体现也至关重要。当代中国的写意油画,就肩负着这双重使命,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以外来媒材激活传统精神,在语言层面上实现跨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在个体性的艺术实践中寻求人的生命的普适意义,在公共性问题上将差异化再次推向前台。
主体性与差异化都是现代主义运动的流行话语,而公共性缺失又被人视为当代艺术的危机。那么,强调主体建构的写意精神在当代公共文化建设中是否具有消解作用?关于这一问题,金观涛与司徒立有一对话。金观涛认为这是画家的主体意识过于强烈所导致的结果,其涉及到个体偏好与“任意性”问题,也涉及到价值共享与个人消遣的矛盾冲突;而司徒立认为“公共性的丧失源于绘画中蕴含主体意识性质的变化”[8],如欧洲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或写实主义绘画,都存在公共主体性,表现为一种“公有现实”,尤其是写实主义绘画同样存在强烈的“主观建构”,只是其“公有现实”的取向不同罢了。他认为现代艺术与古典绘画最大的差别,是其主体性“更丰富细致”,社会性主题退出画面,社会化的“公有现实”不复存在。由于个别的主体性极度扩张,个体与
社会间的心灵沟通出现了障碍,强调多元的当代艺术被多元的价值冲突和疏离摧毁。但是,对于画家而言,他们都有各自的体验,寻求共相毫无意义,讲究写意或表现的画家尤其如此。可作品的感人之处及有效性如何体现?就在于其表现的意识,即“意”之所在,由“意”所建立的公共性。“意”对画之主体具有聚合作用,能产生共鸣或共振,这些都在形式意蕴中产生,与内容无关,或者说与“公有现实”无关。本质上个人化的主体精神是否具有公共性,与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与他所属的社会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因为那是接纳主体的价值构架。主体精神与意义表达是相辅相成的,在主体的意识中,意义是在人的想象中不断参与到绘画过程中,并超越于画面而焕发出来,而能够被阐释的,还是在文化、民族性及社会关注等公共性方面。
因此,对写意油画的个体性询问,有两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一是在多元文化结构中出现的个体性平庸;二是在公共性建构中隐含着重建个体理性与政治秩序的企图。前者直接削弱多元化,后者直接消耗个体性。我们需真正领会“写意精神”,以境界提升人格,以修持养成品性,同时将自我置入民族文化的历史,消解当代性与传统的对立,并以人为基点,在公共领域建立一个可以相互沟通的话语平台。
[1]刘骁纯.写意论[J].中国油画,2014(5):46.
[2]宗炳.画山水序[M]//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131.
[3]题画《竹》[M]//郑燮.郑板桥集详注.王锡荣,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373.
[4]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M]//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365.
[5]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4.
[6]论美[M]//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张玉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77.
[7]范迪安.文脉传薪:2015年中国写意油画名家学派研究展·序[N].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2015-09-27(4).
[8]司徒立,金观涛.当代艺术危机与具象表现绘画[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9.
(责任编辑、校对:关绮薇)
Styles,FormsandSpiritofFreehandOil-paintings
ZhengGong
The significance of freehand style of painting lies in its focus on characteristics of painters and the way they express them,which turns away from the prevailing worship of images and concepts in the fine arts circle nowadays. Freehand style painting is identified with the abstract form in expression,which can be identified as dawning ofmodernism in paintings.Painters must draw on the spirit embodied in the freehand style and practice self-cultivation,striving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radition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ofmodern spiritand develop a public platform forcommunications.
Oil-paintings,Style,Form,Writing,Freehand Style
J0
A
1003-3653(2016)04-0048-05
10.13574/j.cnki.artsexp.2016.04.005
2016-05-08
郑工(1956~),男,福建福州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