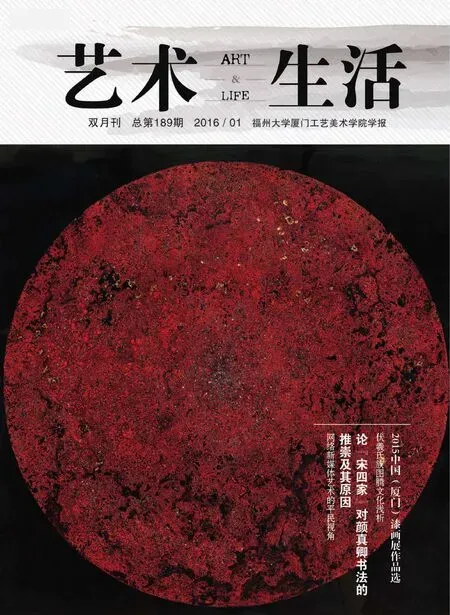陈宗光:不妥协的和解
——从无处安放的“癫狂老蔡”到量身定做的“标准配件”
2016-04-04王晓舜
王晓舜
陈宗光:不妥协的和解
——从无处安放的“癫狂老蔡”到量身定做的“标准配件”
王晓舜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快速城市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人口大量向城市迁徙、汇聚,改变了城市的产业结构。而具体到城市里生存的个体,不论从生活方式、伦理观、价值观、感知方式还是精神状态都随之发生剧变。多年以来,宗光一直关注和思考着城市与置身其中的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并将表达现代都市本质与城市中个人的内心感受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种长期持续的关注与思考在艺术家的精神世界里被物化为一个具体的形象。这个宗光早些年所创作的最成功或者说最被大众所熟悉的形象,是一个略带着几分自传意味的中年男子,这位男子总是显得敏感而又有点神经质,他精神世界的焦虑紧张通过扭曲畸变的身体和四肢得以外化,像是在进行一种无可奈何的尴尬挣扎,又像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挣扎完成一种宣泄或者自我疏导。这个被宗光命名为“老蔡”的家伙,总是留着最普通的平头短发,戴着象征着知识分子的小圆框眼镜,眉头深锁,紧张莫名。他裸露着自己苍白孱弱的身体,周遭一片压抑的灰暗。老蔡很疲惫,老蔡想过放弃,他想要从头再来,他甚至尝试决绝地揭下自己的面具和外皮,却无奈而悲哀地发现内里还是一个完全相同的面孔和身体。空间的挤压导致了灵魂的失重,老蔡在重重的压力下幻想着轻盈地漂浮在生活的上空,可到处都充斥着支离破碎的生活片段,所以老蔡的飞翔注定只能以跌跌撞撞的姿态来实现。老蔡努力摆脱着来着日常生活的万有引力又不得其法,所以他只能一面伤害着自己,一面尝试修复和缝补着自己,就像刚刚从一场叫做“正常”的事故中猝不及防地逃离出来之后小心翼翼地舔着伤口。画面中的道具和物件都是具象而真实的,可是由其拼凑构建的场景和空间却是虚拟而荒谬的。它们摇摇欲坠,仿佛随时即将崩塌。这场注定来临的崩溃是否就是作为一个人到中年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心灵危机呢?
2007年,宗光带着对城市和心灵的持续思考来到北京,在东南沿海二级城市生活了半辈子的宗光在北京这个国际化大都会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作。可想而知,当原有的小城文化记忆和思考遭遇中国政治文化中心最新最前沿的海量资讯的冲击时,艺术家会近乎本能地作出反应,而其个体的经验差异必将对作品产生深远的影响。德国社会学家齐奥尔格·希梅尔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书中说过:“都市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快速刺激而持续的变化。”21世纪的北京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巨变,作为一个外来的个体在面对一个陌生的巨兽般的城市时,脆弱感和渺小感不可避免地油然而生。当时宗光的工作室在费家村,而刚刚安定下来没多久,与费家村一墙之隔的索家村因城市规划发展的需要被拆除了,看着挖掘机效率极高地吞噬着索家村的断壁残垣,刚刚开始有些适应北京的宗光又一次强烈感受到城市和个体身心之间的矛盾和冲击。他回到不知还能使用多久的画室,将这种切身的困惑与敏感倾述在画布上。在北京的这段时期,宗光一共创作出200多幅老蔡系列作品,这个脆弱木讷却又不甘被现实裹挟而去的眼镜男不断地调整姿势延续着宗光的表达。
2015年对宗光来说又是很特殊的一个时间点,不知是因为回到了熟悉的福州进行创作,还是与宗光即将离开体制这个事实有关,从这一年开始,宗光新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呈现出显著的新面貌。首先从运用的材料上来看,不论是载体还是工具,都摆脱了原本一成不变的布上颜料操作。从厨房纸巾到拆迁遗留下来的旧家具;从刷墙用的滚筒到做蛋糕用的奶油瓶;从废纸皮到抽屉书架……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素材被宗光信手拈来,经过匠心独具的嫁接和杂糅,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其次从画面的构成来看,绘画语言更加趋向于纯粹,画面的空间感被有意识地压缩弱化,成为几近二维的平面。画面元素也因此更加扁平化,更加符号化。有些画面还配有零星片段的文字,让你感觉似乎意有所指可是又不得要领。看似简单随性的构成却有一种直抒胸臆的快感,让你能感受到宗光那种“逸笔草草”的洒脱。更为难得的是,画面结构单纯简洁但却依然充满各种丰富的可能性。在作品中,宗光阴险地将各种元素并置、排列、组合,却不直接设置好事物之间相互的关系,既不抒情也不说教,他只给出线索和暗示,联系由观者自己去建立和补充。而色彩,也从之前暧昧而压抑的灰色调转换成大量明亮的纯色。色彩明快响亮却不艳俗,反而有一种充满趣味的童真。
当沉重的责任感和现实的负担变得稀薄,老蔡身边那无法挣脱又如影随形的禁锢也明显地被弱化。之前隐喻和批判了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那种焦躁不安的分裂感弥散了。在这些新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了宗光的这些改变。如果说之前的老蔡系列中,宗光更多的是关注城市和环境对个体的异化,更多地带有某种自省式的隐喻和批判意识的话,那么随着近年来环境以及心态的不断调整变化,我们能感受到宗光正试图通过进入纯粹的图像而得以疏离现实世界的繁杂和沉重,用一个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应对这个世界。这些新作品依然延续着宗光对时代和环境对身体的作用和影响这个线索的针对性持续关注。但是形式与内容的比例产生了倒置。最显著的改变就是新作品的画面抽离了具体的情节和戏剧性的表达,简化为一种更为纯粹的符号化图式。经历了从整体到局部,从宏观到微观,从皮相到内里的改观,虽然围绕着对城市与身体的关注却依然没变,但是艺术家与生活之间混杂、暧昧的紧张关系却被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抹去,即便依然出现了疑似那样老蔡的人物形象,也被剥去了明确的标签和指向,不再是一个担负着重压,不停对抗和逃离的精神寄托。
在新作品中,宗光与城市和环境似乎找到了更合理的相处之道。也许他意识到,城市与个体将永远处于一种相互依赖也相互排斥、相互需要也相互伤害的复杂而矛盾的关系中。因为不仅是城市和环境改造了我们,我们也在改变着我们身处的世界,甚至可以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个微观的城市,千千万万个我们组成了我们身处的环境,那么选择针锋相对的抗争也许不是最好的方式,至少不是唯一的方式。所以宗光适时地改变了策略,他用一种不妥协的方式去实现环境与个体某种意义上的和解。他尝试着用嘲讽取代对抗,用调侃掩饰愤怒;用谐谑去完成追问。在轻松诙谐的嬉笑怒骂和含沙射影的指桑骂槐中,宗光就这样以一种“在野”的态度和方式完成了对现实和体制的戏说和解剖。
王晓舜,自由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