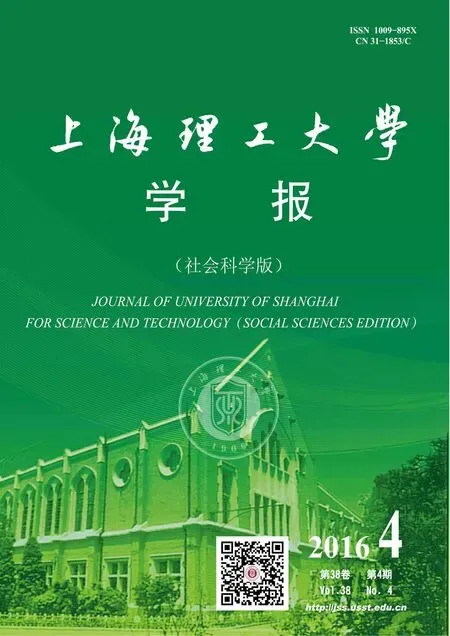死之“思”
——《蛙》与《时时刻刻》的比较阐释
2016-04-04褚萌萌
王 楠,褚萌萌
(1.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 2.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死之“思”
——《蛙》与《时时刻刻》的比较阐释
王 楠1,褚萌萌2
(1.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 2.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文学中,死亡母题是人类在现实中意识到人必有一死之后建构的死亡诗学。20世纪以来,随着死亡的艺术化处理和哲学思考进一步发展,中西文化中的死亡表达方式呈现“和而不同”的态势。莫言的《蛙》和迈克尔·坎宁安的《时时刻刻》便是一例。莫言把生死之际“此在”的可能性以“延生”的生育方式提供“向死而在”的“在”的可能性,坎宁安则通过三个历时共“在”的“向死”个体,表达个体濒死的能动性、选择性和责任感。虽然两个文本中主人公的畏死和濒死的体验不同,却在“延生”和“向死”的文学话语上表达了异质同构的“死”之思。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死亡永远处于“尚未抵达”的恒久状态,面对生命的绝对紧迫性,敞现向死而生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是人类生存状况的根本现实,是人类无法逃遁的难题中最为反思性的主题。
死亡;《蛙》;《时时刻刻》;比较阐释
死亡母题是中西作家创作中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死亡与文学在比较诗学视域中的基本立足点之一。尽管莫言的《蛙》(2007)和美国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的《时时刻刻》(TheHours,1998)在创作空间和时间上没有事实性的姻缘联系,并且对死亡的呈现模式、思考范式、具象寄寓等整体描摹中,两者创作的文学文化环境不尽相同,但是,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整体关注来看,两者都是后现代实验小说关注死亡在文艺创作上的一种特别的投射模式。本文试图在整理两者异质性和互补性的同时,把握中西文学中死亡母题在“向死而在”意义上的异质同构的“在”,以及现实的“在”和本体论上的“在”在文学和文化上的互证关系。
一、死与“思”
生与死是西方哲学中的重大问题。死亡作为与人类的核心体验相关的根本概念,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历史时期都被探索和讨论过。在现代医学的范畴内,死亡被公认为是每一个知觉个体生命的终结。然而,在哲学和社会学的讨论中,不同的文化却产生了不同的死亡观。如何理解死亡,把握今生,成为古今文化中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之一。苏格拉底和西塞罗都曾有言,哲学的定义是有关死亡的准备。如果没有死之思,恐其哲学就不成哲学了。早在古希腊时期,米利都学派、赫拉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等人就对死亡进行了脱离原始宗教的、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德谟克利特曾经反对那种相信“任何形式的生命都高于貌似公认了的邪恶的死亡”的观点;而伊壁鸠鲁在强调生的乐趣的同时,也指出对于死亡的恐惧是非理性的,因为“死亡比生活困苦要好”[1]。中世纪是苦难的世纪,也是基督教享有绝对话语权的世纪。在宗教神学的美化中,“为上帝而死和天国而生”成为人们“至上善举和最终归宿”[2]107。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诸多哲学家,在思考死亡问题的同时,认识到死亡的必然性,并进一步指出生命中的死亡因素,比如叔本华对于“意志”(will)的消极描写、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death drive)、尼采的“虚无主义”(nihilism)。从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再到福柯的生存美学,20世纪以来的现代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巨擘更以鸿篇巨制对存在与死亡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观点虽然对于死亡积极意义的认识有所不同,但都认可死亡的重要性,甚至认为死比生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注点恰好不同。中国哲学范围很广,既包括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又汇集释道两家的宗教哲学。但总体来讲,比起关于“死”的哲学,中国的哲学更多地是关于“生”的哲学。关于生死的问题,孔子主张“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即活在此生,守好为人的本分,“以生前现世为先,才能符合仁心人道”[3]。佛家的生死观是轮回观,其对于人生归宿的阐述——“从中阴而来,往中阴而去”——似乎赋予“死”较之“生”更深的涵义。然而,佛家所塑造的死后极乐世界,实则是要劝诫世人在现世积德行善,不坠入恶道,本质上也是对于“生”的强调。道家以“道”为万物的起点和终点,自庄子“息我以死”以来对于延生之道的强调,带有明显的“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的观念[4]。死亡既是回归自然,以非生命形式的再次延伸。儒、释、道三家的思想都描述了中国文化中对于生的关注。
作为两国文学中后现代小说的典范,莫言的《蛙》与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的《时时刻刻》虽然在谋篇布局、思考范式、具象寄寓、创作环境上相去甚远,但在表达对待生死问题的基本诉求上却成为中西文化中的典范。两者对于死亡问题的不同关照和不同呈现方式,由于自古以来相异的文化传统,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特征——“息我以死”与“向死而思”的异质同构的哲学思考。莫言的《蛙》虽然表面上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生育的故事,但实际上探讨的,还是人的向死而在的“此在”的“在”。这个此在的个体,专注于延生的问题和不死的可能性。正如庄子所言,死亡是对宇宙万物的皈依和顺附。自生至死的全部体验无不由着天地自然变化之道。这种自然之道是摆脱生死的企图和心理虚构,用以弥合生死之间的痛苦的阈界体验。莫言把生死之际“此在”的可能性做“延生”的方式提供“避死”的可能性,但是,“延生”也是以生的方式在“向死而在”的意义上正在死去。
这一点在坎宁安的小说《时时刻刻》中用濒死的体验表达了相同的诉求。坎宁安塑造了三位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她们敏感、独立,虽然地位、生活环境不尽相同,但死亡却是她们平静生活之下潜伏已久的“问题”。而三个女性的“此在”诠释了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的三种可能。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劳拉·布朗(Laura Brown)和克里莎·凡高翰(Clarrisa Vaughan)、无论如何竭力奋斗,时时刻刻会感受到死亡的临近。三段生命,由于畏死的心态,努力沉湎于世界(共在)的忙碌中,希望与世界的共在来消减死亡的威胁。她们向死而在的“在”,既不能死得无畏自由,也不能展示生命像未来开放的可能性和生存潜力。坎宁安通过三个历时共“在”的“向死”的个体,表达了一种对死亡的担忧和紧迫,即“此在”的最终和最深刻的可能性,同时也突出了个体濒死的能动性、选择性和责任感。不论《蛙》还是《时时刻刻》,似乎都在为究竟生命为何物困扰着。
由无数个体组成的整体的共在,以“畏”死为先,“畏”是“此在”先天就有的一种情绪。“畏的此在”是整体叙事结构的基本成因和特征,而向死而“思”是最为深刻的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思,这个“思”是以畏死和濒死的体验作为两个文本的写作逻辑的出发点:个体的生不是过去,死也不是尚未到来,死亡永远处于“暂时尚未”的恒久状态之中。但对作家来说,死亡则永远是开放而澄明的,是诗性的也是审美的,正是个性鲜明并勇于“向死而思”的作家们的存在,才使得“向死而在”从“人学”进入“文学”。“向死而在”,不仅成了人的存在方式,也成了文学的存在方式。
二、“避死”与“向死”
正如前文所论,如果说西方文化中更多的是“向死而思”的观念,中国文化则是“息我以死”的观念。一般意义上讲,中国哲学倾向推崇一种“安宁、快乐的人生哲学”观[5]。中国文化中乐生安死的传统“从根源上看,与古代中国人以自然为宇宙万物最高主宰,努力臻求与自然协调的生存意识有直接关系”[6]。在这样的文化思维之下,与“死亡”为本位的思想不同,《蛙》的世界观是以“生”为本位,因为“生”是自然的、协调的,是宇宙万物存在并具有意义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死亡”是对于因“生”而存在的这个自然体系的冲击和破坏。
《蛙》中“蛙”与“娃”(新生命)和“娲”(创造新生命)是同音;因此,高密东北乡村将“蛙”视为图腾,也就奠定了“生”是书中人物的共同信仰。在这样的背景下,背弃“生”而选择“死”,则是违背了为人的基本准则,走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书中的主人公“我”(蝌蚪)的姑姑(万心)最初是医学世家、名扬乡里的妇产科大夫。她首先为落后的东北乡村引入了新式接生法,在四年的生育高峰中,接生一千多次;那时候,姑姑是“活菩萨”,是“送子娘娘”,“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似乎有成群的蜜蜂、蝴蝶跟着她飞[7]22。而后来,姑姑做了计划生育小组副组长,劝说、威逼,用尽一切土办法对超计划怀孕的乡亲堕胎,这时的姑姑就成了活阎王,被之前爱戴她的人埋怨、甚至咒骂。在文末的话剧中,作者以超现实的笔法,描述姑姑遭遇青蛙袭击、而后通过丈夫郝大手的帮助捏泥娃娃,重新成为了生、而非死的象征,这时,人们对她的态度才得以改观。应该说,在国家特殊历史的选择与民间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之外,《蛙》实际上强调的是一种“生命的自在状态”,一种“生命强力”[8]。因此,死亡成为这种“生命强力”的对立,被“生命强力”最终战胜。这种“生”与“死”的对立,恰如中国戏曲中的人物脸谱化——相对于“生”而言,“死”是没有地位的,甚至是不道德的、终将被战胜的。这部关于“生”的小说,在自古以来“乐生恶死”的传统中,尤为突出地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对于“延生”的渴望与崇拜。众多因堕胎而未能来到人世的生命的死亡,是对东北乡村千百年来伦理道德、生活方式的破坏,而以张拳老婆、王胆两人为代表的产妇们的死亡,尤其是“我”的妻子王仁美在死之前说的一句“我好冷”,则被塑造为一种赤裸裸的不必要的牺牲,让人不寒而栗。
《蛙》用延生的方式获得的生命强力不是以死亡作为终点的人生意识,而是欲以一个生命的死替代和延续另一个生命的生的方式获得生死为一之“道”的永恒。在“向道而终”的过程中,每个个体的死亡只是幻化为一个时间片段。西方哲学“向死”之思则是以死亡作为起点,对在世的“此在”(Da-sein)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辨分析。这一点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中得以最为淋漓尽致的表达。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死亡是此在的终结。死亡是人生最为极端和真实的可能性。他认为,“此在在死亡中达到整全的同时就是丧失了此之在”[9]。这里的“此在”指的是“人的在”。海德尔格认为这个关于人的本体论将死亡看作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因为只要这个“此在”在“此”(生存着),就一定要承受这种死亡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当此在到达它自身的终结之时,当此在完全不存在之时,它的存在却因此被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此在也就完整了[10]。
《时时刻刻》中三位女主人公试图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向死”的欲望和体验,一种拥抱死亡、向死而生的意识(plunge toward death)[11]。作家伍尔夫在小说中的第一次登场即是一个走向死亡的形象:“她坚定地向那条河走去,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12]。而且,在赴死的过程中,伍尔夫还在关注身边的风景,好像死亡对于她来说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她在“做一件看来最应该做的事情”[12]2。应该说,对于伍尔夫来说,这种向死而生的意识并非一时之念。在伍尔夫的一天之中,她曾多次想到死亡。当她刚刚醒来的时候,就习惯性地躺在床上,想象自己是“一片有感知无形体的羽毛”,向往“一座阴间的公园”[12]3。而在当天下午,她与她的外甥们一起埋葬一只死去的小鸟之时,她十分严肃而认真地完成了整个葬礼过程;甚至后来,她的外甥女已经玩腻了这个“游戏”的时候,她还对此恋恋不舍。这实际上体现了伍尔夫对于死亡的欲求;在某种程度上,她甚至将这个给小鸟的葬礼当成了自己葬礼的预演,因为“她很想代替小鸟躺在那里”[12]7。这一天结束之前,伍尔夫尝试着从里士满出逃去伦敦。对于她来说,里士满是阴暗的、肃杀的,而伦敦则象征着“自由、亲吻、艺术的可能性和诡秘隐晦地闪烁着的狂热失常”[12]9。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伍尔夫渴望伦敦,虽然伦敦对于她来说也许意味着生命非自然的终结:“死亡……而她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希望深深地走入其中,直到永远找不到回来的路。”[12]139福柯的生存美学(aesthetics of existence)中提到了一个“末日训练”(the exercise of the last day)的概念。这种末日训练是将全部生活当作漫长的一天,以至于“当人到了一天里的夜晚时,他可以说是到了一生的夜晚,也就是即将死的时候”[13]497。福柯认为,这种死亡训练有两种好处:其一,让人“洞察当下,对生活的过程、活动的流程和表象的流变进行剖面分析”;其二,可以“对自己的整个人生投去一瞥”,使得一生的价值和真相呈现出来[13]118。
在第二个主人公克拉丽莎的故事中,死亡也是一个常见的概念。克拉丽莎经常想到死亡:她认为瘫坐在椅子上的理查德就像一个仍旧坐在宝座上溺死的皇后;她认为自家的走廊就像一个通向死亡国度的入口;当她与儿时的伙伴谈论起故地时,她提到的是希望在死去之后将骨灰撒在那里。同样地,死亡也似乎成为了克拉丽莎生活的一部分,她在这一天里也在不断地遭遇死亡相关的事情:在她晨起采办的第一站——花店——那里,店主芭芭拉就刚刚幸免于乳腺癌;她在理查德作品中的化身,结局是无缘无故地自杀了;和她有着复杂关系的理查德,在全书的最后,选择了跳窗结束自己病弱的生命。在上述所有与死亡的邂逅中,可以肯定的是,克拉丽莎濒死之前的镇定和皈依。然而,与伍尔夫不同的是,她并没有极端热切地向往死亡,而是将死亡当作生命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对待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克拉丽莎正是在进行一种关于死亡的训练。她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甚至将生与死混合在一起。在她看来,生,原本就是死,而死也就是生,因而“向死而生”在她这里被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
由于衰老(old age)是一个更接近死亡的时间点,福柯认为衰老具有更高的价值:“……正是老去构成了伴随个人或个人一生遵循的这一长期修养的肯定阶段、完成阶段和顶峰……摆脱了所有物质欲望,摆脱了他现在拒斥的所有政治欲望,获得了可能得到的一切经验,老年人将成为自己的主宰,而且能够让自己完全感到满意。”[13]45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十余岁的克拉丽莎,比书中的其他两个主人公——伍尔夫和布朗太太——更接近真正的死亡,也就在生死问题上更加泰然自若。
三、“息我以死”与“向死而思”
中西文化中,生死的问题都与“罪恶”有关系。并且中西方对于罪孽的不同看法加重了“避死”与“向死”的趋势。在中国文化中,“受罪”的本质其实是为了子孙或群体“造福”或者下辈子“投胎”能活得更好。在这个意义上,即使人已死去,其存在的意义也许并没有消亡,反倒以一种非生命的形式再次延伸。而在西方文化中,由于人生来是为了“赎罪”以便死后进入天堂,人活着其实就是死亡的预备,死亡被看作是人存在的最高阶段。因此,人虽然活着,其实正在死去。
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并一”[14]。这就是庄子所谓的生死之“道”。天地是与我同存的,万物是与我同一的,死亡等同于归返于自然。尽管“劳我以生”,生是受罪,使我劳顿一生,但是死亡是让我休息,“息我以死”[15]。因此,由生至死的过程是自然之道,对道家而言死无所恐惧*《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另,与庄子不同,佛教特别是小乘佛教对生死的深恶痛疾,有强烈的出离心。庄子也有出离心,但不像佛教那么强烈的沙门思想,庄子给自己留够了空间。。但是也不是西方本体论所讲,生死为客观对立物,以旁观者的态度对死亡这个客观实在物进行形而上的向死而“思”之解。因为庄子没有把死亡因个体的自主性提升到自然万物的高度,只是用自然之道弥合生死之间的痛苦,试图摆脱生死的束缚。
与中国哲学不同,人之所以受罪是由于因果报应。西方则不强调“罪恶”与“人的本性”之间的关系。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提出过对死亡的无知是最大的不幸,以及“逃避死亡并不难,真正难的是逃避罪恶”[16]。而基督教认为人生来就带有原罪,人生在世必须赎罪,死后才能进入天堂。及至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也认为人是有其罪恶和阴暗的一面,世界的荒谬性就在其罪恶。虽然基本理念不尽相同,但这些观点都帮助建立了西方文化中的“人本罪恶”的传统;以此为出发点,各家形成对待人性中罪恶成分的不同方式。
《时时刻刻》三段故事分别设置在一战、二战和社会飞速变化的20世纪90年代末。一战和二战是人类的欲望和无知带给人类社会的毁灭性灾难,而20世纪末的美国由于艾滋病、毒品、犯罪等社会问题亦是末世情怀。可以说,三位主人公都生活在由于人性之恶而带来的生存困境之中。对于她们来说,生活其本质就是空虚、惶惑、冷漠的;她们渴望死亡,因为死亡能够让她们远离这种生存困境。然而,她们又不能轻易地选择死亡,因为像正常人一样活着正是她们赎罪的过程,她们现世为人不能逃避的选择。
《时时刻刻》中的主人公之一劳拉曾经尝试自杀。她后来自杀失败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她抛下了家庭与责任,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从人的社会属性上来讲,劳拉这个人物可以算作是已经死亡了——作为妻子、母亲、女儿、邻居的她不复存在。然而,她虽然还活着,但却在生活中获得了死亡的意义——虽然还活着,但好像已经死去了——因此也没有必要再寻求死亡。1926年的伍尔夫是一位知名的作家,但她更是一个世人眼中的病人、一个受丈夫管制的妻子。可以说,伍尔夫已生无可恋;对于她来说,“死亡就是反抗,死亡就是一种与人交流的努力……死亡中有着拥抱”[17]。
与《时时刻刻》中预设的生存困境不同,《蛙》中姑姑面临的更多的是要不要终止生命的问题。在《蛙》的最后,姑姑接生了许多生命又扼杀了许多生命,她说:“一个人不能也没有权利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死去”[7]128。姑姑因自己曾经强制孕妇堕胎而愧疚,深感自己是有罪的,于是后半辈子她承受了所谓“现世报”自我谴责。《蛙》中许多死胎,总是变换着青蛙与娃娃两种形态出现在姑姑的幻觉或是身边;那些死去的人却好像“阴魂不散”,总是隐伏在字里行间。最终,姑姑通过老伴儿郝大手,以“捏泥人之手”来表达对那些没能来到人间的生命的歉疚。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突飞猛进,一些超生的方式也“与时俱进”在高密东北乡,袁锶以牛蛙养殖公司为幌子,组织了一批代孕女为那些想要生男孩的人代孕。而张拳老婆、王胆、王仁美等等因堕胎而死的产妇们,她们的命运似乎在代孕妈妈陈眉的身上得到了延续。陈眉不幸的身世、亲子被夺的遭遇,是这个瞬息万变的和谐社会中极为不和谐的一环。她的不幸仿佛也是在替之前那些死去的产妇们鸣冤。
四、“个体”之死与“群体”之死
死亡是个人事件。但是,因为人具有社会性,那么死亡自然也应该具有社会性。儒家思想中认为仁义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比人的生命重要。这其实就是将最本体的存在赋予仁义道德等社会伦理,而非肉体的生命。因此,这种情况下的死具有了一种社会价值——死虽然剥夺了人的肉体,终结了人的生命,但是却使得人的存在迎合了社会伦理道德,从而获得了最本质的存在意义。中国文化“比较注重和强调死亡的社会性和伦理意义”,相比之下,西方的死亡哲学,则更多地“关注死亡的主体性和个体性”[2]107,30。例如,尼采的“死的自由”强调死亡只有在我们自身愿意的时候才出现;而存在主义的海德格尔、萨特也强调人之存在的开放性、可能性和自由性。在这样的观念之下,死亡成为了《庄子·大宗师》中的“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另,与庄子不同,佛教特别是小乘佛教对生死的深恶痛疾,有强烈的出离心。庄子也有出离心,但不像佛教那么强烈的沙门思想,庄子给自己留够了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西方的死亡哲学在关注死亡的社会属性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但是,对于存在的社会属性的论述却不尽相同。西方哲学强调死亡的主体性和个体性,其实是重视个体生命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存在主义认为,“对死亡的承担就是此在把死亡这一最本己的可能性担当起来……死亡是使人的全部生活成为不可能的可能性,正视这种可能性并把它担当起来,才能展开本真生活的可能性”[18]。个体的死亡赋予个体生命以意义,因而使得整个人类社会有意义,是构成人类社会的积极因子。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中对于死亡的社会价值的强调,其实是重视人类社会中群体生命的作用。死亡终结了个体生命的存在,但却给予个体生命在社会道德意义上的存在。因此,社会作为一个群体的生命得以延续。试想,在儒家思想统治的中国社会,若非自古以来众多仁人志士在社会大义面前放弃个体的生命,以“仁”为本位的中华民族则必不能延续;反之,也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是崇尚仁义的民族,放弃个体的生命、延续群体的生存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蛙》就是一例。这部小说很好地诠释了族群生命繁衍的社会属性。诚然,众多胎儿的泯灭,是其自身生命的不幸,是其家庭的损失与悲恸。然而,堕胎更象征着一代人的消亡,是高密东北乡村传统的伦理秩序和生活习惯的断裂。另外,陈鼻老婆王胆,虽并非为仁义大义而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杀身成仁”,却是为了保护腹中的胎儿、为夫家传递香火而献出了生命。这在传统妇德思想仍旧盛行的乡村,也可谓是作为一名女子的大义。王胆腹中的孩子在计划之外生了下来,这象征着高密乡民的群体生命的抗争与延续;王胆虽死,但她的死是为了她所在群体的生。其他诸如张拳老婆、王仁美等产妇也都是为了群体的生命而献出了自身个体的生命。而后,这个计划外的早产儿陈眉,几乎像孤儿一样长大,又被一场大火毁了容。至此,她很难再拥有常人的人生,她的人生基本等于死去了。然而,她的社会意义并未消失:在最后的话剧中,“我”的妻子小狮子求陈眉代孕,为“我”生下了一枚男丁,延续了香火。陈眉母亲的生命在她的身上得到了最直接的延续,而她的命运也与母亲如出一辙。在新的发展时期,东北乡村建起了度假村、高楼大厦,似乎与过去的生活渐行渐远,那个乡民群体也似乎不再存在;但是,陈眉为“我”延续香火这件事,正表明着,过去的那个乡民群体其实还是活着的,虽然它的生命之火因外部因素而减弱,但却从未熄灭。
与《蛙》中对族群生命的延生愿望不同,《时时刻刻》中死亡与死亡意识,虽表面上看是不必要的,甚至无意义,但深层上讲,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应有之义。伍尔夫作为一位著名的作家,却没有办法为自己的生活做主,因养病的名义而被迫远离伦敦。甚至,在一些琐碎之事上,伍尔夫都要受到他人的规划。丈夫莱纳德陪伴她度过了身体状况最糟糕的时期,但却强迫她每天早上十一点必须喝一杯牛奶;另外,伍尔夫的姐姐瓦内莎提前来访,莱纳德仍旧坚持自己的时间规划,不愿为了伍尔夫而改变。作为主人,伍尔夫甚至对女仆娜丽也心存畏惧,怕被娜丽数落。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对于伍尔夫而言,死亡,与其说是一种解脱,不如说是一种自由的象征,是她对于生命掌控的证明。劳拉也曾有过自杀的想法。劳拉看似拥有幸福的生活、美满的家庭,但正是这种平庸让她感到窒息。她崇拜的那种伍尔夫式的“美妙的灵魂”、“悲伤”和“超验的愉悦”是她的生活所不能给予她的;她诉诸死亡,因为伍尔夫式的自杀是她所渴望的一切的可能。对她而言,死亡“可能给人以深深的慰藉”,“使人感到极度的自由”[12]121。同样,对于克拉丽莎而言,死亡也使得其个体生命的存在具有意义。如上文所言,克拉丽莎不惧怕死亡,甚至欣然接受、拥抱死亡。这样的死亡观带给克拉丽莎的是平静的生活态度——因为她了解死亡,所以她安然地面对生命,等待死亡,既不惧怕死亡,也不会不顾一切地追求自杀。
五、结束语
中西文化对于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有着不同的“思”。西方文化有“向死”的传统,更注重个体生命的社会意义;而中国文化“息我以死”,重视死亡的社会价值以及群体生命的延续。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诠释思维之下,同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时时刻刻》与《蛙》也展现了不同的生死之思。《时时刻刻》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生活在因罪恶而带来的生活困境之下,她们渴望死亡,却因种种原因无法轻易摆脱羁绊、放弃羁绊,可谓“向死而思”。相反,《蛙》则体现了高密东北乡民们对于死后余生的崇拜。在这样的寄托之下,他们作为群体的生命得以延续,那些死去的生命似乎也并未远离,可谓“虽死犹生”。
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中的死亡,是把人有意识有目的的生存活动在精神心理上虚构为天地间无意识无目的的自然运行。主观上此在意欲延生、超度,超越生死,客观上却更执着于心斋坐忘、形如槁木、心若虚空的存在,极力隐讳当面言死,力求在天乐人和中忘却淡漠死亡对于人生的制约与自省作用。孔孟儒学也有“未知生焉知死”的认知态度,立足于世间存在,更有“事死如事生”的实践理性要求。而西方的死亡哲学使人正视死亡,有一种向死而在的紧张与自由,不类庄子神人般的飘逸与至乐,更使人感到一种在的激动。这与中国哲学死学中的长生尽年思想、齐死生为一而以生为求的态度巧妙地互补呼应,组成了中西文化对死之“思”的异质同构的阐释。但不同于西方,中国哲学中的几近宗教却又非宗教,以及重人伦不重形而上的思考特征,构成了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朴素的心理情感世界。
[1] Warren J I.Democritus,the epicureans,death,and dying[J].The Classical Quarterly,2002,52(1):194-206.
[2] 段德智.西方死亡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7.
[3] 冯沪祥.中西生死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50.
[4] 庄子.庄子·养生主[M]∥庄子·内篇.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12.
[5] 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3.
[6] 陆扬.死亡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3.
[7] 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22.
[8] 张勐.生命在民间——莫言《蛙》剖析[J].南方文坛,2010(3):52-54.
[9]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286.
[10] Cerbone D R.Heidegger: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M].New 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8:81.
[11] Hughes M J.Michael Cunningham’sTheHoursand postmodern artistic re-presentation[J].Critique: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2004,45(4):349-361.
[12] 迈克尔·坎宁安.时时刻刻[M].王家湘,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
[13] 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97.
[14] 庄子.庄子·齐物论[M]∥庄子·内篇.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12.
[15]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
[16] 弗吉尼亚·吴尔夫.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布之屋[M].王家湘,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64.
[17] 孙利天.死亡意识[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145.
(编辑: 巩红晓)
“Thinking” on Death—A Comparative Study on Wa and The Hours
Wang Nan1,Chu Mengmeng2
(1.SchoolofForeignLanguagesandLiterature,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2.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Tsh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In literature,the motif of death has been constructed as “the poetics of death” when human beings came to realize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ir mortality in an early stage.As the aesth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conceptualization of death has evolved gradually,the western and eastern ways of expressing death has taken on the trend of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which is reflected in Mo Yan’sWaand Michael Cunningham’sTheHours.InWa,Mo Yan takes the state of “Dasein” between life and death as the “Possibility-for-Being”,which provides possibilities for the state of “being” in “Being-towards-Death”.While inTheHours,Cunningham tries to convey the individual’s initiation,selectivity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t the death-hour through three “Being-towards-Death” characters’ diachronic experience.Although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two texts have undergone different forms of “fear of death” and “near death” experiences,they make same claim of Thinking on death in their literary discourses.To the living,death is always in the perpetual state of “non-arrival”.Facing the moment of end of one’s life,we are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the “Possibility-for-Being” and impossibility of “Being-towards-death” are unavoidable.This predicament has remained a reflective and intractable topic in literature.
death;Wa;TheHours;comparativestudy
2016-04-2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阶段成果之一(SK22B2015024)
王 楠(1975-),女,副教授。研究方向: 西方文论、美国文学、性别理论。 E-mail:gracenanwang@163.com
I 106
A
1009-895X(2016)04-0349-07
10.13256/j.cnki.jusst.sse.2016.04.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