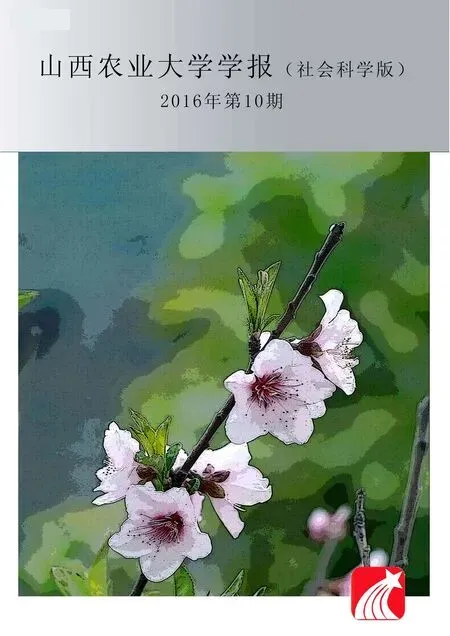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其完善
2016-04-04张晓云
张晓云
(1.安徽科技学院 法学系,安徽 凤阳 233100;2.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其完善
张晓云1,2
(1.安徽科技学院 法学系,安徽 凤阳 233100;2.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公众参与是环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程序正义。对于公众参与法律法规等虽有明文规定,但由于许多事实因素和法律因素,致使其规范密度不足而无法达到立法旨意。面对这一现状,在对环评中影响公众参与的相关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建议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的细节规定;对专家学者、专业人士和环保团体等人群的参加可以不受“存在利害关系”或受项目直接影响标准的限制;强化环评机关主动向公众征求意见的功能;将公众参与这一程序性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调整公众在风险决策中的地位,增进公众的实质参与。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影响因素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有助于我国环境问题不断地从“隐性”走向“显性”。在我国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越来越广泛,公众参与制度建设也正在经历一个由无到有,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有许多相关的衍生问题,如公众参与难且参与效果不佳,流于形式的也并不是个别现象,导致近年来,我国的环境群体事件层出不穷,而且环境群体事件以每年29%的速度递增。[1]公民参与在具体实践上,受到各种现实因素和参与者预期心态影响,导致参与程度的不足、意愿的缺乏。虽然公众自身也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之一,但是相关制度设计与安排显得更为关键,对于公众参与所产生的影响也远远高于公众本身,亟待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寻求解决之道。
一、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
随着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在1986年提出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相关概念与风险沟通的重要性日益获得重视,并有学者将风险沟通的理念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专家途径。即风险可通过客观的科学原理加以分析评估,而风险沟通则是将客观的评价结果传递给公众。因此,公众只是风险知识的被动接受者。二是协商途径。此类型源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强调在风险决策中应创造一个自由而平等的沟通环境,并让公众参与决策程序,扩大其参与的可能性。然而由于专家与公众不同的风险认知,导致公众在风险决策过程中仍可能遵从专家的知识霸权。三是风险评价与风险沟通一体。即整个风险沟通的过程就是在界定该具体事件的风险评价过程。此种理念并非否定政府与专家在决策过程中的地位,重点在于扩大参与界定风险的公众范围,将不同的立场与观点纳入风险的定义过程。[2]Beck针对当代风险科学管制,提出反思性科学及反思性政治的实践策略抗衡之。主张脱离狭隘实证科学理性,发展批判性、多元性与社会性的风险决策,让科学评价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科学判断或有限的解释。公众应积极投入科学决策,通过公众参与来进行学习与决定风险争议问题。即政府不再是公共事务运行过程中唯一的决策者与行为者,现代政府需要建立的是一种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相互渗透和共同参与治理的机制。[3]治理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政府应改变消极保守态度,主动去了解公众和社会的真正需求;另一方面,政府更应提供包含公民、第三部门、私人部门等参与的途径,使各参与者能从长期以来被告知角色,转变为对相关决策或风险知识主动积极的参与角色。
环境行政因牵涉广泛的利益冲突,以及行政决策于未知之中,在性质上,必须凭借公众参与来增强其决策的正当性。为弥补环境影响评价在环境决策上的民主正当性,所以特别设计公众参与制度,以确保审查程序能广泛地衡量各方利益,尽量做出最适切而得到最大公约的决定。环评过程中纳入公众参与是希望达成以下目标:1.环境决策中能充分考虑建设项目对当地的影响;2.促进替代方案,减缓措施的考量;3.确保重大的影响不会被忽略,并且将利益最大化;4.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能及早提出以避免冲突;5.将实际环境需求和现状反映给决策者,使环境决策科学、民主,符合现实情形;6.让决策通过并且避免信息过度不对称;7.使公众提高对环评制度的信任。[4]我国2002年的《环境影响评价法》首次确定了公众参与制定。2003年《行政许可法》规定了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的听证权。2006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规定环保部门应当在受理建设项目环评报告后,在其政府网站或采用其他便利公众知悉的方式,公告环评报告书受理的有关信息并公开征求意见。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详细规定了公众的知情权。2009年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细化了规划环评过程中公众参与的途径和公众参与的效力。2014年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在将“公众参与”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作为专章进行了规定,并特别规定了建设项目环评过程中必须进行公众参与。
二、环境影响评价中影响公众参与的相关因素分析
(一)公众的专业知识不足
公众决定是否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及参与行为的影响力,必须考虑公众需付出的成本,讨论议题的重要性,公众对特定议题的知识与能力,及其意见产生影响力的可能性。而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先决条件为具备高度的参政知识,以及对参与领域的专业知识有所了解。但是,公众却经常缺乏这两种知识。环境影响评价中污染的测量、评价标准与方法的认定,以及何等程度的污染可能造成的危害,都是非常专业的,非一般公众所能轻易理解,也非短时间所能获得的知识。因此,对于此种高度专业的技术性问题,公众似乎没有参与的能力。如垃圾焚烧处理项目,反烧者们最担心的是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噁英,知道它是致癌物,其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但对垃圾焚烧处理的具体技术和检测手段状况却一无所知。宁波镇海PX项目中,政府为处理炼化一体化中的污染问题,治污设备就投入36亿,但公众关注的是PX是有毒的。
(二)公众的理性思辨不足
公众参与制度的设计,通常都是假设公众是理性的,他们会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做出最好的选择。事实上,公众常常是理性经济人与非理性社会人的结合体,无法客观、理性的参与。最能说明公众不理性的就是邻避效应。所谓邻避效应是指公众以不受欢迎的态度,阻止经济活动或公共设施设置于自身周边区域,即使该活动可能直接或间接使公众受益;但同样地,若该经济开发活动或设施设置于它处,该公众则不会反对,甚至非常乐于接受。“邻避”是一种认知的态度,一种社会的运动,一种社会的病态,一种法律的失效,一种争论的范例。[5]如浙江杭州曾欲建老人临终关怀中心,最终因遭抵制被迫取消,而当地居民反对的理由仅仅是“觉得晦气”。“垃圾处理项目建设虽有必要但别影响我,选址请远离我家。”因此,只要有规划,就会引起公众的抗争。人们并不会理性考虑他们自身或其他人是否真的需要,借以改善公共卫生,提升环境质量,他们只会考虑到居住环境将被严重的侵犯,甚至导致消费经济衰退,房价滑落等负面影响。
(三)公众参与的方式不足
公众参与的方式一般有进行公众问卷调查、咨询专家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但是目前大部分的公众参与调查是以问卷调查为主,问卷的内容往往没有根据项目的特性进行设计,而且调查还经常“造假”,使公众参与流于形式。如2003年深圳深港西部通道在侧接线工程的环评过程中,环评单位——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只在工程沿线住有数十万居民的小区内发了50份调查问卷,就算完成对公众征求意见的程序。[6]2012年秦皇岛西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被披露环评的100份调查问卷全是伪造的。2014年5月,南京六合化工园区内南京荣欣化工有限公司新项目的环评调查中,调查问卷表上除了名字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项目负责人解释说:“我们是发动一些职工去调查的,承诺一份50元,究竟什么人来填,我们只负责提供这个信息,应该由环评公司来核实。”环评机构工程师表示:“我们只能核实一个有没有参与调查,第二支持不支持,其他的表上内容很多,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再去核实。”[7]
(四)政府机构本身的限制
目前行政机关在环评问题中的症结在于心态问题及公众沟通经验不足,行政机关是否愿意在政策决定过程中引进或开放公众参与,必须视公众参与的目标是否明确。如有些机关认为专家的意见已经足够,公众参与只是碍于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不为。因此,在环境决策过程中对于公众意见的采纳相对较低。此时,公众参与就会流于形式。同时行政机关也担心公众如涉入太深,导致其行政决策的困难或增加工作的不便,影响效率。
三、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完善
(一)完善多元广泛的参与途径
各国的环评参与方式大致有以下种类:公告;非正式小型聚会;一般公开说明会;社区组织说明会;咨询委员会;公众审查委员会;听证会;发行手册简讯;邮寄名单;小组研究;民意调查;全民表决;设立公众通讯站;记者会邀请意见;发信邀请意见;回答公众提问;座谈会等。[8]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了调查公众意见、咨询专家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公众参与形式。但环评中公众参与的选择,因公众本身能力、参与需付出的成本、公共议题的范围,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高低而有所不同。不同的参与方法有其相对的优势或弱点,在相互沟通程度、公共接触程度、处理特定利益的能力等性质上有所差别。因此,在公众参与途径上,应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的细节规定。首先要考虑多数公众参与的方便性,如参与的日期、时间与地点等。同时除登报、网站公告的程序外,还应通过各种传播媒体(如有线电视)及其他途径的公告,将举行的时间、地点及环评报告内容,事先公布,以提高公众参与环评的便利性。如印度尼西亚在通知过程中采取的是最便捷的简讯通知,即通过手机短信,将相关信息通知给当地的居民,以提高公众参与环评的便利。[9]其次,规定公众参与各种会议的出席率。为发挥公众在环评中的作用,立法应当规定公众出席会议的出席率,确保相关部门和建设单位积极举行公众参与的相关会议,通过此立法规定,也可让公众积极地了解环评项目的特性与影响。最后,在座谈会、论证会和听证会中,应规定有三分之二的学术专家或有实务经验的专家学者列席。
(二)扩大公众参与的主体
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是除建设单位及审查环境影响评价的机关外,其他相关机关、团体、地方政府、学者专家、当地居民等。在公众中,有两类人需要特别关注:一类是专家学者、专业人士和环保团体,例如律师、环境工程师等。另一类是低收入阶层等。前一类人群关注环境影响对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及生态等造成的影响,同时他们更倾向于让违法者以遵守法律的方式提出解决途径。如北京阿苏卫垃圾处理项目中,反建者主要是中国环科院研究员、大学教授、零废弃环保项目的发起人、环境律师等。其反对意见主要认为,污染物排放标准设计值低、担心后续监管不到位以及环评报告中的公众参与部分有造假嫌疑。后一类人群可能关注生存更胜于对周边环境的关注,也不愿意接受法律体系为他们提供的解决办法。他们更倾向于将项目建于他处,从而永久地避免可能产生的危害。如阿卫苏事件中,当地村民开始时强烈反对,将通往阿苏卫垃圾填埋场的道路堵住。而如今,村民代表会表示支持该项目的建设,究其原因是因为周边村庄将获得巨额的搬迁费用。因此,在环评公众参与范围上,对第一类人群的参加可以不受“存在利害关系”或受项目直接影响的标准的限制。只要该专业人士的专长与项目存在关联,他们就有权参与到程序中来。[10]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广泛考虑各方利益及不同立场,尽早发现潜在问题,避免冲突或解决纠纷。
(三)强化环评机关主动向公众征求意见的功能
政府应建构具有实质意义的公众参与机制,在接触或处理公众所提出意见前即已预设立场,并对参与过程中所呈现的公众意见或看法作出适当的处理与回应。具体而言:一是建立环评公众参与智库。公众参与环评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应汲取相关经验。早在 2009年时,北京市政府决定在阿苏卫垃圾填埋场的基础上,建设垃圾焚烧厂,然而这一项目因民意强烈反对而搁浅。2015年该项目重新启动,但同样遭遇了公众的激烈反对,这一项目又暂时被叫停。如今六年之后,一切都似乎还停留在原点。因此,相关环评机关应对历年的环评群体事件做详细的分析,以区分公众参与在各种类型案件中的性质及差别,并探讨公众参与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二是强调由下而上的事前沟通。行政机关应吸收新观念并转变心态,潜移默化终至身体力行,积累经验,切实担起公共责任,建立顺畅和开放的民意表达机制,经由公众沟通的过程凝聚当地居民的共识,实现多方共赢。三是规定环保部门的补充调查责任。环评报告不仅是公众获得信息的基础,也是环保部门审查时的依据。因此,环保部门如认为建设单位提供的环评信息有疑议时,应依职权主动调查,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四)强化公众参与程序的司法审查
从风险社会的角度来看,欲建构完整的风险规范体系,需要有司法机关的把关。即司法审查监督机制,应成为风险沟通的一环,调整整个风险决策过程中的权力互动。同时,也调整公众在风险决策中的地位,回应公民社会的发展。目前,除了环境公益诉讼以外,司法机关也在积极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以及“三审合一”的环境资源案件审判模式,从“硬件”和“软件”上为司法机关介入环境公共事务奠定基础。司法机关通过对公众参与程序的审查,有助于调整并强化公众在风险决策中的地位。一方面向专家传达应重视公众的主观风险感受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向公众传达其具有参与决策过程的积极地位。具体而言:一是赋予公众参与这一程序性行政行为的可诉性。行政程序本身即具有促进公众参与,保障公民权利等作用。所以,程序权利应具有非工具性的本体价值,它的作用及效果,不应完全附属于实体终局决定的结果。凡涉及限制或侵害公众法律上程序权利或利益的程序行为,若该行为可独立于实体决定之外,且其瑕疵无法或难于借由事后审查实体决定予以弥补时,则应容许当事人提前于终局实体决定作成前,即单独针对争议程序行为提出救济,以及时维护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程序上或实体上权利,从而促进实体决定的适当与合法。二是对公众参与程序进行实质性审查。目前,我国法院在对环评审批决策进行审查时,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现象,对公众参与一般只是进行形式审查。如伍权、陈权、黄用诉湛江市环境保护局一案中,原告诉称“‘107号批复’是在没有公众依法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的,环评报告所述调查了17个单位、250人,是虚假的”。但法院对这一诉求并没有做实质性审查,只是认为“被告受理《报告书》后,在湛江市环境保护公众网对受理信息进行了公告,公开环评报告简本,公告期限为10个工作日,公告期间被告没有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因此,程序上是合法的。[11]而最高院公布的十大环境行政案例中“正文花园业委会案”中明确指出公众参与程序是司法审查的重点,这也为法院以后审查此类案件提供了借鉴。[12]具体而言应审查:1.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在所选择的参与方式中能否被充分表达,不同意见是否能充分交流和辩论。2.环评过程中环评审批机关是否对公众提出的相关意见作出回应。对行政机关来讲以理性解释回应公众的疑问,这既是对行政决定理性内涵的揭示,也是对公众的一种负责任的回应。[13]
四、结论
环境风险的处理往往涉及复杂的社会沟通与决策过程。行政机关应通过法律制度性的设计,在尽可能提供相关信息的前提下,对各种可能选择方案进行公开及透明的辩论,并将公众的各种看法纳入决策机制。并衡量其对公众权利的影响程度,选择适当参与方式,以了解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观点和价值。理顺政府自身与企业、民众的利害关系,建立更为顺畅和开放的民意表达机制。同时,在环境团体的推动下,环境风险争议已逐渐进入司法系统中。未来可以从观察与调整风险决策过程中的权力互动,以及促进风险沟通的角度,将公众参与这一程序性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调整公众在风险决策中的地位,回应公民社会的发展。
[1]王姝.我国环境群体事件年均递增29% 司法解决不足1%[N].新京报,2012-10-27(05).
[2]Grabill,J.T& Simmons. M.Toward a critical rhetoric of risk communication: Producing citizens and the role of technical communicators[J].Technic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999,7(4):415-440.
[3][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85-190.
[4]Chaytor.B.The Potential of EIA Procedures to Enhanc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rade Policy Decision-making[J].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1995,15(6):507-522.
[5]李昕如.公共政策视阂下的邻避事件探析[J].决策与信息,2015,(5):98-99.
[6]金自宁.跨越专业门槛的风险交流与公众参与[J].中外法学,2014,(1):7-27.
[7]环评公众参与办法修订:须在网络和现场公示[EB/OL].(2016-04-15)[2016-04-20]http://news.sohu.com/20160415/n444250750.shtml.
[8]叶俊荣.环境影响评估的公众参与:法规范的要求与现实的考虑[M]//环境政策与法律,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3:223.
[9]Persada S F,Razif M,Lin S C,et al.Toward paperless public announcement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EIA)through SMS gateway in Indonesia[J].Procedia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14(20):271-279.
[10]汪劲.中外环境影响评价机制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6.
[11](2015)湛开法行初字第31号判决书[EB/OL].(2015-04-17)[2015-12-08]http://wenshu.court.gov.cn.
[12]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环境保护行政案件十大案[EB/OL].(2014-12-09)[2015-04-09]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 detail/2014/12/id /1519119.shtml.
[13]张晓云.环境影响评估审批决策中程序裁量的司法审查[C].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会议交流论文,2015:465-473.
(编辑:程俐萍)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its improvement
Zhang Xiaoyun1,2
(1.Literatureandlawschool,Anhuiscienceandtechnologyuniversity,Fengyang233100,China; 2.Lawschool,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210046,China)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IA is an integral part of procedural justice. Although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re expressly provided, it cannot reach the legislative purposes, because of many facts and legal factors. In the face of this situation, and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factors of influencing public's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judgment, the paper suggest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detail rul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llow experts and scholars, professionals and environmental groups to attend with no restriction from projects or the standards;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of the EIA agencies to actively soliciting public's opinions; Take public's participation into judicial review; Adjust the status of the public in risk decision to enhance the public's participatio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2016-04-27
张晓云(1979-),女(汉),吉林通化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法方面的研究。
江苏省普通高校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规划项目(KYLX15-0697)
C939
A
1671-816X(2016)10-073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