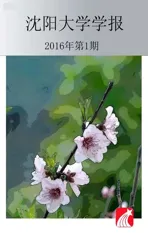甲午时李鸿章“一人敌一国”之说辨析
2016-04-03陈力
陈 力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甲午时李鸿章“一人敌一国”之说辨析
陈力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650091)
摘要:通过对甲午战争时期相关史料的分析和研究,探索了“一人敌一国”之说的起源及影响,认为甲午之败,非由“一人敌一国”所致,而是败于当时的中国在政治、社会等层面的落后。
关键词:南洋大臣; 甲午战争; 支援; 李鸿章; 一人敌一国
一、“ 一人敌一国” 之说的起源与其影响
甲午战争深刻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命运。战场上的失利,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对危机的应变能力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麾下北洋海军和淮军在水陆战场均一败涂地,更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在平壤和黄海大败后,李鸿章曾上奏为自己辩白,称失败非战之罪,实系孤军作战所累:“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1]。这种论调,非一时冲动之言,乃李鸿章内心真实写照。被解职后,其致信孙家鼐,强调战败缘于孤立无援:“东事愈棘,日久无功,中外谤议丛积,然使数年来海军能逐渐添购快船,水陆各军储有快枪快炮,何至于此?”[2]。
据吴永回忆,李鸿章晚年对甲午之役耿耿于怀,尝埋怨:“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3]
孙家鼐与李鸿章政见相类,皆为主和派,吴永为受业李府的门生,面对此二人,李氏自不必掩饰,尽可袒露心迹。
然而,史料有载,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廿九,李鸿章奏称:“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这说明了,并非清廷阻扰北洋海军添设军备,而是李氏自作主张,将丁汝昌等人的要求压下,根本没有上奏。户部亦称,下令各督抚停止购办军备,为期两年,期满后,各地纷纷请款购械,户部亦一一照办,唯独北洋未向户部请款[4]。
将慈禧视为一生之敌的梁启超,无视上述事实,反将李鸿章的怨言发扬光大。梁氏在《李鸿章》中大发感慨:“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以成此节制、敢死之劲旅,孤注一掷以向于我”,遂有“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之论。“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于是,梁氏慨叹:“以一人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5]
《李鸿章传》一书向来在学界影响甚广。王也扬认为,此书有新史学客观真实的色彩[6]。李润苍则察觉出,此书明显带有为李鸿章塑造英雄形象的意图[7]。书中所提倡李鸿章“一人敌一国”之说,亦因而广为传播:孙宝瑄尝借李鸿章“一人敌一国”故事,塑造章炳麟“以一人与一政府为敌”的英雄形象。李剑农亦受此说影响甚大:“李鸿章说他自己是以直隶一省,当日本全国。这并不是他掩饰自己过失的话,而是实在的情形”[8]。
“一人敌一国”之说倘若成立,那么,李鸿章非但不是罪人,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史可法式的悲剧英雄,此说关系着李鸿章的历史评价之褒贬,可谓牵连重大。
笔者经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发现在李鸿章担任统帅时期,北洋各军并非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事实上,南洋大臣为北洋方面提供了大量实质性的支援。这一大奥援对稳定战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这个重要史实,却被李鸿章“一人敌一国”之说所遮蔽,长期为学界所忽略。
二、 挽救危局:南洋援军之北上赴援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毅、奉、盛等军陆续进驻平壤,前线大军云集,堪称壮盛。李鸿章对局势颇为乐观,认为“各军皆系鸿旧部,练习西洋新式枪炮多年”,自信“当可无误机宜”。其在致友人的信中,甚至已在考虑战胜日本之后,该如何重振朝鲜藩务:“羊叔子有言,平吴之后,方劳圣虑。此时之胜倭或易,他日之保韩实难矣”[2]40。
前线诸军的统帅大权,独集于李鸿章手中。在得悉清廷有意委任吴大澂帮办东路军务时,李氏十分不悦:“鸿章在兵间四十年,亲见从前各路会办、帮办人员,大抵令其分剿一路,稍假事权,仍由统帅调度,……若两帅同办一事,则往往意见参差,徒增牵掣,贻误滋多;否则徒拥虚名,毫无实用”。
为证明吴大澂不宜帮办军务,李鸿章还举出中法战争的例子:“即如法越之役,吴清卿中丞奉命会办北洋,清卿本人平正,颇能和衷,惟平素不甚知兵,凡事悉由鸿章主持,未见赞助之益”[2]42-43。吴氏仅为帮办,但李氏对此反应甚为激烈,不惜再三反对。由此可见,李氏之所以专恃北洋,并非因为孤立无援,恰恰相反,而是他将北洋诸军视为禁脔,不容他人染指。
盛军为淮军精锐,尤善于使用新式洋枪,历来深为清廷重视,故派其驻扎天津,拱卫京师门户。此军调往朝鲜者,前后共十三营,约6 000余人,以致京津门户守备空虚。有感于此,清廷遂令李鸿章从各腹地省份抽调旧部填补防务。李鸿章却以“腹地等省兵勇,仅防本境,又少精械,似无可调之劲旅”为由,改派贾起胜、吴宏洛、姜桂题等人募兵补防。月余后,至八月初,募兵工作迟缓,仍有不少队伍还未募齐,未能形成战斗力。
清廷遂于七月初七传谕南洋大臣刘坤一,调时任江苏按察使陈湜募兵北上,以充实北洋诸军留下的防缺。随着形势愈发紧张,北方防务更形吃紧。七月廿七,军机处一日内连发三电至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处,要求其催促姜桂题、程允和迅速赴前敌;吴大澂、魏光焘、陈湜、程文炳迅速北上。
这时清廷的决策十分明显,在朝鲜和奉天前敌方面,主要依靠淮军。然而,朝鲜位于东三省侧隅,京津面临渤海,绵长的海岸线均可予日军登陆,如此一来,前敌与后方之别不甚显著,因此须厚集兵力以防万一,南洋援军负责填补淮军防务,且因应战情变化,作为预备队随时投入前线。
为节省时间,刘坤一从南洋防军中先行抽调三营,再招募三营,如此一来,便可在短期内迅速组建六个营,作为先头部队北上。其余各部,则分头招募,预期在八月成军。
此次遣军北上,需款甚巨,“共计库平银十四万三千两”,而南洋财政颇拮据,司库储备搜刮一空,亦无法凑足。惟有到处挪拨,“饬由两淮运司拨银五万两,江海关拨银六万两,镇江关拨银三万三千两”,方才筹得此数。军械方面,南洋亦先行筹足,“该军应用枪炮子药等件,均由臣据领,宽为拨给”[9]805-806。
然而,程文炳军的组建并不顺利,与陈军多系湘军不同,程氏系淮军宿将,其招募五千人亦多系淮勇,饷项营制均按照淮军标准,淮军的饷制,一向比湘军严苛。程氏得知南洋拨付陈湜三万金,“以为购办军米之用”,遂提出仿效此例,请求“另于行饷源之外,再请办米之费”。
其实,陈湜之所以获得优待,并非刘坤一心存派系之见,而是陈军组建迅速,可以“即日启行”,反观程军,组建工作相对迟缓,开拔无期,因而“不得不移缓就急”,先为陈军提供米款,亦是情理中事。但是,为了避免程军产生不满,刘坤一将予陈军购买米粮的款项,改为从其月饷抵扣,变相削减了陈军待遇,杜绝程文炳借机生事的籍口[10]2108。
南洋诸军中,湘淮并集,颇存芥蒂,刘坤一大义灭亲,在于防止程文炳因待遇不平而另生事端。程军到达天津后,仍不时要求南洋加拨饷银,刘坤一亦多照办。
由于“倭军均用快枪,亦多快炮”,李鸿章提醒,北上赴援的陈湜、程文炳两军,须“先利其器为要”。对此军情,南洋高度重视,江苏的库存枪械“本属无多”,但仍如数装备陈、程两军,此后已是“存项立罄”。因此,刘坤一通过驻英公使洽购军火以补充库存,拟购各式快枪11 000余支,弹药220万发,“各价约合银二十余万两”。对南洋来说,这又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在南洋全力筹措下,陈湜于八月十三日带领先头部队,兼程北上,程文炳亦于九月初在亳州集结北上。从七月初七接旨到起程,仅耗月余,南洋之反应,相比起后路淮军的募兵乱象,堪称可圈可点。
大举调兵北上的同时,南洋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饷款短绌。
据统计,陈、程两军耗费三十余万两,此外,补充新式快枪亦需二十万两,加上“自倭人肇衅以来,沿海各省均形吃紧,江南筹办防务,用款倍增”,南洋“以有定之度支,供无定之繁费,饷源日涸,益觉竭蹶不遑”。
刘坤一深知北洋战事正紧,清廷财政无力他顾:“臣等虽艰窘万状,而均饬由司关局库设法挪拨,未敢遽请部款者,亦知部臣持筹之苦,……外省少请一分之款,军需即可受一分之益”。因此,刘氏决定不向户部请款,而在辖境内开辟三个新的饷源:一是“官员倡率输捐”:“拟请饬令在任各官,除来年应扣廉银不计外,均各量力输捐,其充当差使之较优者,亦一体捐缴”;二是“劝谕绅富捐貲”:“听捐户自行报效,不准零星分派,致滋纷扰”;三是“派令典商捐息”。
刘坤一认为百业生计艰难,惟典铺一直获取暴利,“公家未尝资其捐助”,因而“拟请饬令各按实存架本,提出一个月息钱助充军饷”。前两者属于自愿性质,对于坐收暴利的典当行业,刘坤一则以强制手段收缴,体现出他对经济之熟悉,截富济急,尽可能减轻一般民众的负担[9]809-810。
尽管北上赴援免不了一番劳师动众,且对南洋财政造成空前压力,刘坤一仍坚决主战:“中倭既经开衅,不宜轻与议和,以申天威,而维国体。……现在我军厚集平壤,……新招各营,络绎北上,……以我理直气壮,士饱马腾,鼓行而进,直如摧枯拉朽!……责成李鸿章分饬平壤诸军,分道进攻,务将倭人尽逐回国,收复朝鲜版图,即以重兵驻防,使之不敢窥伺”。
三、战局相持的关键:南洋库存武备之应援
然而,被寄予厚望的四大军,在平壤之战中兵败如山倒,“纷纷相率渡鸭绿江”。将士丢盔弃甲,大批军火饷银均弃置不顾,据估计,“平壤军储甚厚,凡有大小炮四十尊,快炮并毛瑟枪万数十杆,……尚存饷银约及十万两”,“尽委之而去”,徒资敌手[11]。
开战前夕,李鸿章向清廷汇报北洋库存:“计军械局尚存毛瑟枪六千杆、哈乞开司枪九百杆、黎意枪一千三百杆,均每枪存子二百余粒”,另外还有火炮270余门,子弹1 000万粒,各种火药90万磅。
表面上看,存量颇多,似足应用。但“北洋沿海水陆淮练各军、东征前敌各军及新募各营,皆取供于此。……陆路行仗,炮尚可敷用,新式快枪、快炮不敷甚巨”,海军弹药亦“急须接济”,单靠北洋的库存,无法应付战事需要。
李鸿章遂向外国急购,无奈“各国以开仗守局外例禁运出口”,只能委托洋商以秘密途径购买,增加了货运的时间和成本。此时尚未宣战,北洋库存已捉襟见肘,只能依靠外购补充。俟战端一开,北洋库存之窘况,可想而知。
果不其然,据前线指挥叶志超电报,平壤各军一路溃退之后,已是“军装不全,子药俱罄”,“带有枪回者不过十之六七,所有枪子每枪不过数颗,锅帐炮位等件遗失净尽”[4]114。
败军渡过鸭绿江后,总算惊魂甫定,在九连城站住阵脚。此时,“九连城各处分驻各军,枪炮子弹,均二百数十出,备粮亦甚艰难”,稍好一点的“东沟一带”,“奉军枪炮子药均不足三月”[4]131-132。枪械亦严重缺乏,叶军、铭军、毅军“惟后门枪仅存数百杆,顷查前门来福亦仅数百”。前线不但汇聚平壤败军,还有东三省募集急需装备的五十余营防军。武器弹药的缺乏,为前线面临的最大问题。
八月廿六,李鸿章向清廷告急,称北洋库存已尽,无以为继:“嗣新募各营到津、及晋、豫调到各营纷纷请领,业将存枪及七生半过山炮领发殆尽,又电恳粤督借拨毛瑟枪四千枝,顷又发尽,宋庆添慕多营,无枪应付,正深焦急。”[12]375-376
当时中国南北诸军中,枪械种类繁多,新旧杂陈,俱有优劣之分:上等有快利、毛瑟、马梯尼、哈乞开司、黎意;中等有英国马梯尼、云者士得;下等为林明敦,中国能自造,易走火炸裂,难堪大用。可与日军所用快枪相衡的,仅有毛瑟、哈乞开司、马梯尼等上等枪。
既然外购需时,缓不济急,那么北洋补充军火最快捷、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通过国内各军库存来调配。故此,清廷指示李鸿章向两广、南洋借调。
李鸿章遂向两广求援,前后总计借枪6 000余枝,基本耗尽库存,尚不敷所需。与此同时,肃州镇总兵田在田回山东募兵六营,过天津时,向李鸿章“请发精枪”,李氏因库存见空,无法满足,因该六营负责北上拱卫京畿,事关重大,于是请求南洋拨林明敦枪2 400枝,交田军使用[12]388。
早在此前,七月廿七,清廷令张之洞麾下的吴大澂、魏光焘率军北上。魏军惯用林明敦枪,该种枪械北洋从未用过,亦无储备相应弹药。朝廷催兵北上的电旨“急如星火”,张氏对此一筹莫展。在张氏请求下,南洋向魏军配发了大量枪械,“魏藩司光焘六营,枪炮大半取资于此”[10]2111,确保其如期赴援。
可见,在北洋库存耗尽的情况下,南洋库存成为前线、后援各军的重要军备来源。
面对李鸿章的要求,南洋复称,原有10 000枝哈乞开斯,连同黎意和马梯尼,新式快枪约有13 000枝,其中3 000枝拨解海军衙门,其余枪械,用以装备陈湜、程文炳两军,以及各防军后,已所剩无几,仅林明敦枪尚余5 000枝,“若尊处合用,多少照拨”[12]390。南洋虽设有上海制造局,惟其制造能力相当有限,每月仅能造枪150枝,远不能满足战需。由此可见,南洋库存并不比北洋宽裕。尽管如此,南洋还是凑足了1 000支哈乞开司,拨付北洋,这令李鸿章喜出望外,即命盛宣怀派人设法运至天津。此外,田在田所需枪械,南洋亦全数拨付。
张之洞接任南洋大臣后,曾在十月十二日派人清点南洋库存,发现“南洋哈乞枪一万,今年解北洋四千,陈臬、程提二军二千数百,余发营防,久已无存”。而南洋向英国订购的枪械,预计最快也要十一月中旬才能到达上海。
换而言之,在南洋库存13 000枝新式枪械中,将近7 000枝都用于支援北洋,超过总数一半;在库存的老式枪械中,也有将近半数都调拨给北上援军;导致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南洋库存只有2 000余支老旧的林明敦枪。
清廷于十月初五召刘坤一入京,命张之洞署理南洋。张之洞在十月十一日到任后,对南洋库存作过统计,发现“南洋械本不精,加以北上诸军领去太多,仅剩快利精枪六百枝,岘帅此行尽行带去,一扫而空。弟到之次日,已派员到军械局逐一点清,尽是破铜烂铁”[13]5841。尽管如此,在刘坤一向英商所订快枪运抵镇江后,张之洞还是将其中5700枝拨付北洋,应付战需[14]5877。
四、湘淮易势:南洋全力增援下战局之 演变
日军推进到义州后,形成隔江对峙局面。清军新败,士气低落,加之军备紧缺,惟有坚守待援:“只要长甸、蒲河、九连城、大东沟数处稳扎不动,倭必不敢过江,即过亦不敢深入。能固守到十月中,冰冻潮合,到十一月初,后队渐集,守局可站稳矣”。
为此,清廷大举调集各地援军源源北上,甚至还从陕西、甘肃调集骑兵增援,用人无分远近,求兵心切可见一斑。
南洋作为湘军重镇,自为清廷所倚重,遂再令李光久率湘军5营,“随带枪械,迅速北上,听候调遣”。此前陈、程两军北上,刘坤一出力甚多,曾上奏荐书,可谓主动请缨,但李光久之北上,刘坤一心境却有了较大变化。首先担忧“湘勇于北地不甚相宜”;其次,“南洋自有防务,筹兵、筹食,昕夕不遑”;最重要的是,“此间饷械拨发一空。近复奉旨调李健斋五营北上,又须如数招补,不知如何措手?”[10]2114-2115
陈湜、程文炳本不领兵,其部队多由募集而成,到北后须经整训,方能接敌。李光久军则不同,该军驻江宁下关炮台,属拱卫省城的精锐,拥有很强即战力。此军一去,意味着南洋防军失一支柱。尽管如此,南洋还是迅速拨齐枪械弹药,使李军顺利成行,从九月初三接旨,到九月十七日起行,堪称迅捷。
刘坤一指示北上各军:“目下敌焰方张,主上之所倚赖,天下之所仰望者,惟此湘、淮两军。……朝庭必慎选专权以出之,俾湘、淮联为一气;即使分道扬镳,亦应共抒同仇敌忾之忱,未可稍存此界彼疆之见,盖将帅参商,为兵家大忌也,……纵或奉令派在赞襄,但以杀贼为主,不必问统帅是否湘产。”此时统帅为李鸿章,前敌指挥则是宋庆。湘军北上,必隶其麾下,因此刘坤一要求各军“不惜自屈以求有裨于当世”[10]2121,正是为了战事大局着想。
九月廿七,日军渡江突袭九连城,同时,在旅顺后路花园口登陆。一时间,各路防线被轻易突破,旅顺岌岌可危。
目睹前线连遭败绩,京畿形势急转直下,清廷继续调兵遣将。九月廿八,电谕南洋:“在辖境三省防军之内筹拨五六千名,带足枪械子药,拣派敢战将弁,迅速统率,附搭商轮来京。朝廷明知江防重要,难以抽调;但畿疆尤为切近,不得不移缓就急。该督当仰体此意,赶紧筹画办理,不得稍有推卸,致误事机”[4]161。
此电颇值得注意,其一,要求南洋援军以海路北上,海路虽较陆路迅速,但在失去制海权的情况下,此举相当危险,但清廷仍令取海路,可见形势危急,只好铤而走险。其二,清廷深知南洋防务吃紧,但为保全京畿,宁可牺牲南洋。
九月卅日,南洋回电称,决定抽调刘光才五营,“即日带械北上”,连同之前调拨的李光久军,“该两军共五千人,保卫京畿,似可同当一路”。刘军本驻镇江,扼守长江咽喉重地,亦属南洋防军之精锐。
十月初一,刘坤一基于“北路能多一营究得一营之力”的考虑,决定派安徽提督宋朝儒率军1 500名北上支援,之所以选择宋朝儒,“该提督与前湖北提督程文炳同是淮人,似可合扎”。
十月初二,刘坤一续派驻镇江刚勇营提督申道发率三营兵力,即由瓜州启行,又派曹文元率一营由江西东上,一并遵陆北上。
清廷的要求,南洋皆尽力满足,在接旨5日内,共从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调集5 800余人北上支援。惟因上海招商局“仅有三船在沪”,“且船中执事华洋人等均不敢冒险装运,各国公司商船又坚守局外之例,不肯揽载”,所以只能从陆路开拔。
南洋不遗余力的支援,造成自身防务空虚。刘坤一对此忧心忡忡,由于饷械不足,各军北上后,南洋已无法进行兵力补充:“必须招募填扎,临事方可策应,而饷械无出,焦灼殊深”。另外,库存被北上诸军搜罗一空后,刘坤一曾两次通过驻英公使密购快枪,由于“枪件奇贵”,需资巨大,高达八十余万两。如此一来,南洋“从前节存防费”,自此“提拨一空”。
可见,南洋为了支援北洋战事,在兵力、装备、财政三方面皆近枯竭,刘坤一为之浩叹:“有来日大难之势,为之奈何!”[10]2111-2123
此时,预计陆续北上的南洋援军,总数已达37营2哨(陈湜10营,程文炳10营,李光久5营,刘光才5营2哨,宋朝儒3营,申道发3营,曹文元1营)约19 400人。连同由两湖北上的30营,赴援湘军超过50营之数,可谓声势浩大。
淮军为主,湘军为辅的局面,随着南洋各军的北上,已悄然发生变化,连李鸿章心腹盛宣怀亦不得不承认,战局“舍湘军实无可望”[13]5812。情势改变的原因在于南洋大臣的无私应援。
五、 总结:“一人敌一国”并非历史真相
综上所述,本文着重考察了南洋大臣在李鸿章担任统帅期间大力支援北洋战事的史实,澄清了梁启超所谓李氏“一人敌一国”之说,考诸史实,可知此说失之偏颇,并非真相。
本来,湘、淮两集团的畛域之别,举世皆知。清廷不但没有弥缝双方嫌隙,反加以挑拨,以此制彼,坐收渔利:“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驾驭人才正要如此。似宜留双峰插云之势,庶收二难竞爽之功。否则偏重之迹一著,居奇之弊丛生”。
但在甲午战争中,南洋方面在民族大义下,却能摈弃门户之见,倾全力支援北洋。“湘淮互制”已然转变成“以湘助淮”,使得中国在前线精锐损失几尽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京畿地区稳定,避免了首都沦陷的局面。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最高目标在于:“攻占北京,擒获清帝。自不待论,此乃最佳手段”。为达目的,其策略是切断中国南北各军的联系:“使长江以南之兵不得北上,对长江以北之地,骚扰威胁其背后,以使之不能北上,……使进攻北京之兵专心致力于进攻”[15]213-214。
纵观战争期间,日本始终未能实现通过“直隶平原决战”夺取北京的意图。究其原因,正是包括南洋在内的援军大批驰援,厚集兵力于京畿,打通了南北联系,使孤立北京的计划彻底破产。在北洋各军屡屡速败的情况下,战事却形成相持的局面,这无疑要归功于各路援军的及时赴援。与此同时,在精兵强将大多北上赴援后,南洋防务大为削弱,张之洞曾为之感叹:“出色将领大率皆已北上,有事万不可恃”[13]5842。南洋这种窘境,恰恰印证梁启超所谓“各地疆臣袖手旁观,不肯出一兵相救”的荒谬。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事实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非如李鸿章所言,单纯系双方兵力差距所致。比如清军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四次围攻海城而不得,反映出军事思想的彻底落伍,“还想靠在国内镇压农民起义的一套办法打现代化战争”[16]。其实,在当时而言,李氏亦心知中日之间的差距,根本在于近代化进程的落后,即倾全国之力,亦毫无克敌制胜的希望,“将来非添造铁舰及大快船十数艘,并扩充制造机器厂局,断不足制倭”。
事实证明,即便在湘军大量增援、前线兵力大为厚集的情况下,中国最终亦未能扭转战局。与奉行“和魂洋才”的日本相比,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在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中,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因此,战后中国的有识之士,痛定思痛,由此掀起了针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浪潮,诸如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乃至其后的清末新政,均聚焦于上层建筑的重构。时人对甲午之战的这种反思,更印证了甲午之败,非由李鸿章“一人敌一国”所致,而是败于当时的中国在政治、社会等层面的全方位落后。
参考文献:
[1] 顾廷龙,戴逸. 李鸿章全集:奏议十五[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423-424.
[2] 复工部正堂孙(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M]∥李鸿章全集(信函八),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59.
[3] 吴永述,刘治襄记. 庚子西狩丛谈[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07.
[4] 户部奏遵议李鸿章奏东征倭寇筹费为难各情请饬覈实办理折(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三日)[M]. 中日战争(第三册), 177-178.
[5] 梁启超. 李鸿章传[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196.
[6] 王也扬. 康、梁与史学致用[J]. 近代史研究, 1994(2):216.
[7] 李润苍. 浅论梁启超的史学[J]. 近代史研究, 1981(1):259.
[8] 李剑农.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130.
[9] 筹解湘军行营月饷片(光绪二十年七月三十日)[M]∥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刘坤一遗集(第二册). 北京:中华书局,1959:805-806.
[10] 复奎乐峰(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六日)[M]∥刘坤一遗集(第五册). 北京:中华书局, 2108.
[11] 姚锡光. 东方兵事纪略[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30.
[12] 李鸿章全集(电报四)[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375-376.
[13]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 张之洞全集(第七册)电牍[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5841.
[14] 张之洞全集:第八册[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5877.
[15] 山本四郎. 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方略》趣旨[J]. 抗日战争研究, 1995(1):213,214.
[16] 戚其章. 甲午战争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261.
【责任编辑李美丽】
Argument about Huai Army during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ChenLi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the origin and influence of “fight a lone war” are explored. It considers that, the failure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is not due to “fight a lone war”, but because of China’s backwardness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evel at that time.
Key words:the Nan yang minister;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support; Li Hongzhang; fight a lone war
中图分类号:K 25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464(2016)01-0065-06
作者简介:陈力(1987-),男,广东广州人,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