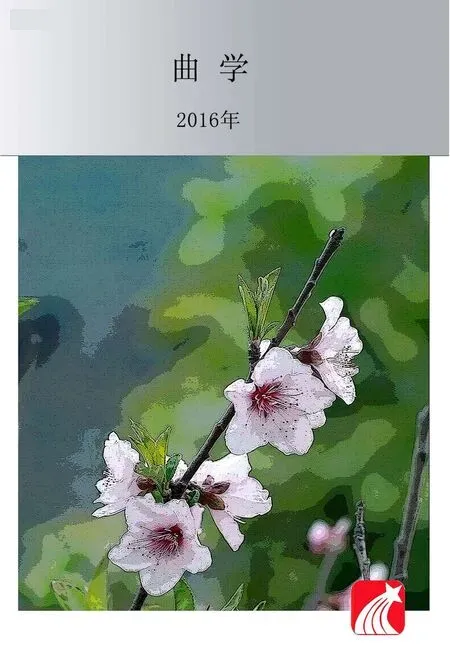读曲与二度创作
2016-04-03叶长海
叶长海
《曲学》第四卷
读曲与二度创作
叶长海
一
真正的戏曲家,他所作的剧本不仅是为提供案头阅读,更是为提供剧场演出,故而很注意剧本的“戏剧性”、“动作性”。剧作家写作剧本有时直接提示“舞台动作”,有时却并不直接提示,而只作“暗示”,由演员与观众发挥想象力,共同完成了某种舞台动作。读者、演员与观众通过创造思维,将案头的戏曲想象为演出的样式,或直接将其搬到舞台上进行演出,这就是对原作品的二度创作。
先举一个有作者提示舞台动作的例子。《牡丹亭·惊梦》的一支曲:
[山桃红](生)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小姐,和你那答儿讲话去。(旦作含笑不行,生作牵衣介)(旦低问介)那边去?(生)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旦介)秀才,去怎的?(生低介)和你把领扣松,衣带宽,袖稍儿揾着牙儿苫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旦作羞,生前抱,旦推介)(合)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蚤难道这好处相逢无一言?(生强抱旦下)
作者汤显祖在这一曲十来句曲辞间,写明了剧中人的行为动作。演员只要能按提示表演,即可把杜丽娘的这个美妙的梦“立”在舞台上了。所以明末茅暎批点这一出戏时曾说:“此折全以介取胜。”*明泰昌元年朱墨套印本《牡丹亭》第十出《惊梦》茅暎眉批。见《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第九函,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年影印本。
即使像这样的剧本,作者已有许多提示,但读者在阅读时的想象或演员在演唱时的表演,还是会有不同的“发挥”的。如梅兰芳对《游园惊梦》的表演就有许多创造性的表演创作,他还专门写了两篇文章——《我演〈游园惊梦〉》和《〈游园惊梦〉从舞台到银幕》,记录了他的许多二度创作。
古人亦留下不少舞台表演的记录,说明“导演”或演员的创意。
清后期所编的《审音鉴古录》是昆曲剧目的演出选本,这里记录了许多演出的动作设计。如上面所引《惊梦》[山桃红]的最后,原作者汤显祖的提示是“生强抱旦下”。《审音鉴古录》中则改作如此提示:“又近,小旦笑推急走介;小生提衣急趋;小旦远立凝望,转身先进;小生紧随下。”这是更为细腻、含蓄的动作设计。
再看《牡丹亭·离魂》一出,《审音鉴古录》编者作眉批提示:“此系艳丽佳人,沉疴心染。宜用声娇、气怯、精倦、神疲之态。或忆可人,睛心更洁;或思酸楚,灵魂自彻。虽死还生,当留一线。”本子中对舞台动作有明确的指示。如其中一曲[集贤宾]:
(小旦[杜丽娘])海天悠,问冰蟾何处涌?(两咳)看玉杵秋空,(作两抢咳)恁谁窃药把嫦娥奉?哎呀甚西风(贴[春香]误听: 嘎,敢是怕风么,待我去闭上了罢)(小旦)吹梦无踪,(陡作精神)人去难逢,(珠泪双流,自言自语式)须不是神挑鬼弄。(贴: 小姐,你是病虚之人,不要伤感罢)(小旦)在眉峰(一咳,皱眉科: 哎唷!),(贴: 小姐,为什么为什么吤!急状态)(小旦)心坎里别是一般哎呀疼痛。(作难过状,双手揉胸口,双手直垂于桌,痛晕,睡桌介)(贴: 哎呀不好了,老夫人快来!……)
引文括号内的文字,即是对演出者的动作设计或说白补充。编者还专为此曲作眉批云:
春香最难陪衬。或与小旦揉背拭泪,或倚椅瞌睡,或胡答胡应,或剪烛。支分依宾衬主法,方为合式。*(清) 作者佚、王继善订定《审音鉴古录》,中国书店,2012年影印道光十四年(1834)刊本,第六册。
编者在眉批中还提示,虽然同为丫环,《牡丹亭》中的春香与《西厢记》中的红娘性格有所不同,演员要加以分别:
春香、红娘,当加分别。盖红娘事事引逗,春香语语含糊,作者析之。”*(清) 作者佚、王继善订定《审音鉴古录》,中国书店,2012年影印道光十四年(1834)刊本,第六册。
有时,作者的情思在剧本中寄寓很深,读者不易发现。如有一则记载云:
相传临川作《还魂记》,运思独苦。一日,家人求之不可得;遍索,乃卧庭中薪上,掩袂痛哭。惊问之,曰;“填词至‘赏春香还是旧罗裙’句也。”*(清) 焦循《剧说》卷五,《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第181页。
“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是《牡丹亭》第二十五出《忆女》中的一句。这是丫环春香在整理旧物,看到小姐杜丽娘送给她的“旧罗裙”而“睹物思人”时所说的一句沉痛之语。为什么汤显祖在写这一句时会有如此异常的伤感动作呢?我的理解是,汤显祖写《忆女》一出,实际上是在写他自己对夭亡的爱女的深切忆念。不难看出,整部《牡丹亭》中充溢着作者的亡女之痛,而且表现了作为父亲的某种自省与自责。
有时作者之用心在此,而读者之用心在彼。作品给读者留下了很多想象空间,有可能产生多种不同的解读。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绵搭絮]曲中有一句“他不偢人待怎生”,清初金圣叹少年初读《西厢》读到这一句时有激烈的感受。见于他在作“金批《西厢》”时的记录:
记得圣叹幼年初读《西厢》时,见“他不偢人待怎生”之七字,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此真活人于此可死,死人于此可活,悟人于此又迷,迷人于此又悟者也。不知此日圣叹是死是活,是迷是悟。总之,悄然一卧至三四日,不茶不饭,不言不语,如石沉海,如火灭尽者,皆此七字勾魂摄魄之气力也。*(清)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之四,清顺治贯华堂原刻本。
对于平常的七个字,金圣叹当时却感到它有“勾魂摄魄”的大气力。他为什么有如此异常的反映,以至于三四日“废书而卧”?一定是少年金圣叹曾遭受他人的“不理睬”而难过。那么,这个“他人”是何人呢?是师长,还是亲邻?数十年过去了,他还清晰地记录了此事,可见他一生都有这种感觉,总是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深深,难以理解,难以沟通。那么,在作“金批”的此时,那个“他人”又是何人呢?皇上?友人?恋人?总之,“他不偢人”这样的事总是不时地触动他心底的某种情结。
20世纪60年代,戴不凡所著《论崔莺莺》中,讲述读《西厢记》的一些新体会,令读者大开眼界。如他在《自序》中,以《联吟》折一段为例:
(旦云)有人墙角吟诗。
(红云)这声音便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那傻角。
(旦云)好清新之诗,我依韵做一首。
(红云)您两个是好做一首儿。(从弘治本)
戴不凡对这一段文字有他个人的独特理解。他说:“如果是用读小说甚至是读话剧的眼光来看,这明明是莺红在对谈张生,是红娘在对莺莺说俏皮话。可是,在并不存在的第四面墙的戏曲舞台上,一个剧本这样写着,是否就意味着只能够这样解释呢?不一定。如说,第一番话是两人的对谈(这是无伤大雅、不失分寸的话);莺莺说要和诗是她的内心独白;红娘的俏皮话是她一面暗中以手指莺莺,并呶着嘴儿,转着眼儿,向观众示意……这又何尝不可呢?——从上述人物关系来看,我以为这里不但是可以,而且应当是这样解释才恰当的。这样,人物的心情既得到了真实的表现,而且戏也出来了。”*戴不凡《论崔莺莺·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第8、9页。在《论崔莺莺》中,像这样的细读文本例证还很多,这就成了此书的最大特色。
戴不凡从“戏曲的导演或演员”的角度来解读《西厢记》,就能从剧本的文字之外,“寻找”到一些舞台动作,“设计”出一些富有戏剧性的场面。这些舞台构思,有的也许是作者的“初心”,但更多的是读者的二度创作。戏剧的二度创作,不仅丰富了文本涵义,而且把案头的文字“立”到舞台上,使“戏剧”得以真正的“完成”。
二
有些戏曲剧本,只记下了唱词,而省去了说白。可以理解为,说白处“留白”,让演出时即兴发挥。今见元代原刊的杂剧本子,有一些就是如此。如关汉卿的《闺怨佳人拜月亭》,全剧的曲词俱在,但许多处说白、动作则只作一两语要求,并无具体内容的提示。其第一折的两支曲子:
[天下乐]阿者,你这般没乱荒张到得那里?(夫人云了)(做意了)兀的般云低,天欲黑,至轻的到店十数里。上面风雨,下面泥水。阿者,慢慢的枉步显的你没气力。
(夫人云了)(对夫人云了)
[醉扶归]阿者,我都折毁尽些新镮鏸,关扭碎些旧钗篦,把两付藤缠儿轻轻得按的揙玭,和我那压钏通三对,都绷在我那睡裹肚薄绵套里,我紧紧的着身系。
(夫人云了)(哨马上,叫住了)(夫人云了)(做惨科)(夫人云了,闪下)(小旦上了)(便自上了)(做寻夫人科)阿者!阿者!(做叫两三科)(没乱科)(末云了)(猛见末)(打惨害羞科)(末云了)(做住了)不见俺母亲,我这里寻里。(末云了)(做意,末云)……*(元) 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8页。
在这里某某“云了”,究竟说了什么,可以由读者(或演者)想象补充。又有“做意”,究竟做什么意,亦有赖于二度创作。
关汉卿另有《关张双赴西蜀梦》,元刊本只有全部的曲词,连“云了”“做科”的提示都舍去了。试看其第二折的前半折:
[南吕一枝花]早晨间占《易》理,夜后观乾象。据贼星增焰彩,将星短光芒,朝野内度星正俺南边上,白虹贯日光。低首参详,怎有这场景象?
[梁州]单注着东吴国一员骁将,砍折俺西蜀家两条金梁。这一场苦痛谁承望?再靠谁挟人捉将?再靠谁展土开疆?做宰相几曾做卿相?做君王那个做君王?布衣间昆仲心肠。再不看官渡口剑刺颜良,古城下刀诛蔡阳,石亭驿手挎袁襄。殿上帝王,行思坐想,正南下望,知祸起自天降。宣到我朝不若何当,着甚括声扬!
[隔尾]这南阳排叟村诸亮,辅佐着洪福齐天汉帝王。一自为臣不曾把君诳。这场勾当,不由我索向君王行酝酿个谎。*(元) 关汉卿《关张双赴西蜀梦》,《元曲选外编》(第一册),第2页。
全剧都是这个形式,既不标出角色行当,亦无一字动作提示。这使二度创作者(读者、演者等)需下更多的功夫,以“完成”完整的戏剧。当然,这种无“提示”的剧本,也少了限制与规定,有可能释放出更多的想象与再创造的自由。
像元刊本《西蜀梦》这样的曲本,实际上只是四个代言体的套曲而已。代言体的套曲,在散曲中亦有,如元代杜仁杰的《庄家不识构阑》、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就是这一类。所以,读元刊本《西蜀梦》就像是在读四套散曲,曲辞之外的人物动作(包括内心动作与外部动作)全凭读者的想象。
三
于是,有学者就在寻找,历代的韵文中,是否还有类似于戏剧的“代言体”曲辞在。王国维在《戏曲考原》中引录了许多歌辞,用以考索戏曲之“原”。其中有一篇宋人杨万里的《归去来兮引》,全篇共十二支曲子如下:
侬家贫甚诉长饥,幼稚满庭闱。正坐瓶无储粟,漫求为吏东西。
偶然彭泽近邻圻,公秫滑流匙。葛巾劝我求为酒,黄菊怨冷落东篱。五斗折腰,谁能许事,归去去来兮。
老圃半榛茨,山田欲蒺藜。念心为形役又奚悲。独惆怅前迷,不谏后方追。觉今未是了,觉昨来非。
扁舟轻飏破朝霏,风细漫吹衣。试问征夫前路,晨光小恨熹微。乃瞻衡宇载奔驰,迎候满荆扉。已荒三径存松菊,喜诸幼入室相携。有酒盈尊,引觞自酌,庭树遣颜怡。
容膝易安栖,南窗寄傲睨。更小园日涉趣尤奇。尽虽设柴门,长是闭斜晖。纵遐观矫首,短策扶持。
浮云出岫岂心思,鸟倦亦归飞。翳翳流光将入,孤松抚处凄其。息交绝友堑山溪,世与我相违。驾言复出何求者,旷千载今欲从谁。亲戚笑谈,琴书觞咏,莫遣俗人知。解后又春熙,农人欲载菑。告西畴有事要耘耔。容老子舟车,取意任委蛇。历崎岖窈窕,丘壑随宜。
欣欣花木向荣滋,泉水始流澌。万物得时如许,此生休笑吾衰。寓形宇内几何时,岂问去留为。委心任运无多虑,顾遑遑将欲何之。大化中间,乘流归尽,喜惧莫随伊。
富贵本危机,云乡不可期。趁良辰孤往恣游嬉。独临水登山,舒啸更哦诗。除乐天知命,了复奚疑。
《诚斋集》卷九七“乐府”栏目中收入此篇,题为《诚斋归去来兮引》*见《四部丛刊》初编杨万里《诚斋集》卷九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则作卷九十八,见台湾商务印书局,1982至1986年影印,第1161册第291、292页。。“乐府”栏目中除此篇外,还有[念奴娇]、[好事近]、[武陵春]、[水调歌头]各一首及[昭君怨]两首。另有一首为“集句”。其中[念奴娇]、[好事近]、[昭君怨]、[武陵春]、[水调歌头]均为词牌,于是后人往往将[归去来兮引]亦看作是词牌。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即收此篇。近年出版的《杨万里集笺校》于“笺证”中还特别说明:“诚斋归去来兮引,《归去来兮》为词牌,诚斋为词题,右词咏诚斋者。”*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七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3742页。其实,宋人词调[归去来]与杨万里此篇完全不同*(清) 万树《词律》卷二有[归去来]调,49字,选柳永“初过元宵三五”一首为例;其《词律拾遗》卷二又有[归去来]调,52字,选柳永“一夜狂风雨”一首为例。此后王奕清等编纂的《钦定曲谱》卷七亦有[归去来]调,将49字作为正体,而将52字作为“又一体”,所选例词亦是柳永的此两首,并作说明云:“此调祗有柳词二首,无宋元词可校。”。《诚斋集》“乐府”栏目中并不都是词,除此篇外,另一首“集句”亦不是词。
杨万里此一篇《归去来兮引》,在形式上与宋代“大曲”略似,而又独具风貌。故王国维《戏曲考原》全文辑录此篇,并云:“杨诚斋之《归去来辞引》,其为大曲,抑自度腔,均不可知。”王氏又云:“此曲不著何宫调,前后凡四调,每调三叠,而十二叠通用一韵,其体于大曲为近。”*王国维《戏曲考原》,收入《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180、181页。后来王易著《词曲史》则谓:“以今考之,则其第一、第四、第七、第十调为[朝中措];其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调为[一丛花];其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颇难确定为何调,似[唐多令]而后半不合,似[南歌子]而首句用韵不同,末亦多一句,惟与谱载无名氏之平韵[望远行]较近,然俱不用换头,且纯为代言体。”*王易《词曲史》,上海书店1989年《民国丛书选印》影印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第311—312页。
这一篇《归去来兮引》,若作为诗、作为词,则无多精彩处,故历来不大受人重视。但自王国维将其作为宋人的“曲”提出,其意义就不同一般了。后来刘永济编《宋代歌舞剧录要》,将此篇编在“鼓子词”中,与赵令畤之《商调蝶恋花·会真记》归为一类*刘永济辑录《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67页。。这篇曲的内容是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所述情境改为由曲来表现。所以其所咏者并不是诚斋,而依然是陶渊明,只不过此处是杨万里为陶渊明“代言”而已。将“辞”体改为“曲”体,就可以演唱了。若演唱起来,陶渊明就成了登场人物。
如此曲首段“侬家贫甚诉长饥”四句,其内容即是《归去来兮辞》的序言:“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59页。以下诸段内容,大都来自陶渊明的原《辞》,并吸收了《晋书》、《宋书》陶潜传中所述的一些片断。如首调第二叠“偶然彭泽近邻圻”七句,即是将史书陶潜传的叙述内容改为陶渊明的“自咏”。其首二句“偶然彭泽近邻圻,公秫滑流匙”,事见《晋书》:“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晋书》卷九十四《隐逸·陶潜》,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1页。接着两句:“葛巾劝我求为酒,黄菊怨冷落东篱”,事见《宋书》:“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着之。”*《宋书》卷九十三《隐逸·陶潜》,中华书局,1974年,第2288页。后三句“五斗折腰,谁能许事,归去去来兮”,事见《晋书》:“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晋书》卷九十四《隐逸·陶潜》,第2461页。
《归去来兮引》全曲就是这样的形式,将陶渊明作品中以及史书中所述及的有关情节,化成陶渊明的“登场演唱”。所以王国维称此曲“已纯用代言”。并云:“虽前此如东坡[哨遍]檃括《归去来辞》者,亦用代言体,然以数曲代一人之言,实自此始。要之,曾(布)、董(颖)大曲开董解元之先,此曲则为元人套数杂剧之祖。”*王国维《戏曲考原》,《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81—182页。
四
闻一多则把目光投向《楚辞》。他认为《九歌》是一种“歌舞剧”。他在《什么是九歌》中写道:“严格地讲,二千年前《楚辞》时代的人们对《九歌》的态度和我们今天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差别。同是欣赏艺术,所差的是,他们在祭坛前观剧——一种雏形的歌舞剧,我们只能从纸上欣赏剧中的歌辞罢了。在深浅不同的程度中,古人和我们都能复习点原始宗教的心理经验,但在他们观剧时,恐怕和我们读诗时差不多,那点宗教经验是躲在意识的一个暗角里,甚至有时完全退出意识圈外了。”*闻一多《什么是九歌》,《闻一多全集》(5),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1、352页。闻一多把我们读到的《九歌》看作是一部歌舞剧中各个角色的唱辞。至于舞台景观与舞台动作,则可以想象添加。闻一多就专作《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一文,构想当时的演出样式,通过想象写出环境布置、歌舞场面、动作表情等。且看他对《九歌》第一幕《迎神曲》的演出设想:
黄昏时分。从四面八方辐辏而来的鼓声,近了,更近了,十分近了。“神光”照得天边通亮。满坛香烟缭绕。男女群巫,和他们所役使的飞禽走兽以及各种水族,侍立在两旁。楚王左带玉珥剑,右带环佩,率领着文武百官,在庄严肃穆的乐声中,鱼贯而出,排列在祭坛下。坛右角上,歌声从以屈大夫为领班的歌队中泛起。
男音独唱: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
[楚王上前三步,依次举行着祭祀的仪式。
女音独唱:
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献玉有司奉上一张草席,王接过来,铺在坛上。有司又奉上一块宝石,王接过来,压在席上。]蕙肴蒸兮兰藉[荐牲],奠桂酒兮椒浆[奠酒]。
[王和百官向着远天膜拜,五色瑞云中微微的现出东皇太一的身影。大家连忙伏下。金鼓大作,远近人声欢呼万岁。
合唱:
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
[群巫纷纷起舞。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君欣欣兮乐康,君欣欣兮乐康!
[云层中的东皇太一渐渐隐没,“神光”渐暗,乐声渐小,幕徐下。*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闻一多全集》(5),第397、398页。
《楚辞》中的《九歌》,虽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但都赞同这是一组祭祀鬼神的乐歌。因而,总是与宗教有关,与歌舞有关。不过,读者或研究者的视角不同,其侧重点也就有异。有的偏重其文学性,有的偏重其宗教性,有的偏重其歌舞性。明代杨慎的说法值得注意。他在《女乐本于巫觋》一文中说:“观《楚辞·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悦神,其衣被情态,与今倡优何异?”*(明) 杨慎《升庵集》卷四十四《女乐本于巫觋》,收入陈多、叶长海《中国历代剧论选注》,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他分明已意识到《九歌》歌舞有似于明代的“倡优”表演。近人王国维则率先明确地从戏剧的视角考察《楚辞》,认为《九歌》中的所谓“灵”,实则是“以子弟为之”的装扮“表演”。“《楚辞》之灵,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词谓巫曰灵,谓神亦曰灵,盖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而视为神之所冯依: 故谓之曰灵,或谓之灵保。”他进而指出:“至于浴兰沐芳,华衣若英,衣服之丽也;缓节安歌,竽瑟浩倡,歌舞之盛也;乘风载云之词,生别新知之语,荒淫之意也。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页。闻一多在王国维的认识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他不只是把《九歌》看成是“后世戏剧之萌芽”,而是视为实实在在的“歌舞剧”,并把《九歌》“改编”成一部有景观、有角色、有歌舞、有贯穿动作的“剧本”了。但不知何故,闻一多的“悬解”,在相当长的时段间响应者寥寥。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古代文化学者知“文学”者众,而知“艺术”者稀。
不过,近数十年间,闻一多的“知音”渐多。还有人循着闻一多的思路,在《诗经》中寻找“戏剧”的足迹。
《礼记·乐记》的“宾牟贾篇”中曾记录孔子议论《武》乐的演出情景:“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礼记·乐记》,《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542页。对于孔子的这段话,我们曾予试释:“这是孔子对《大武》内容的解释。全剧共分六场: 第一场写武王大会诸侯,誓师伐殷;第二场表现武王统领的军队在牧野与殷军会战,并击败殷军,占领殷都朝歌,殷亡;第三场、第四场是描写周军继续向南进军,平定了南方的边疆地区;第五场表现周公、召公分别统治东方和西方;第六场表现周军班师还朝和对武王的崇敬之情。《大武》全剧的‘脚本’保存在《诗经》里,一般认为,《诗经·周颂》中的《我将》、《武》、《赍》、《般》、《酌》、《桓》等篇即是。”*叶长海、张福海《插图本中国戏剧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1页。多年前,陈多、谢明两位先生还曾对《诗经》的这部分诗篇作了“悬解”。这里抄录其“第一场”:
镐京(今西安附近)城郊,舞台是一个圆形祭坛。
数十人的管弦乐队在祭坛一侧,演奏员或跽或立。乐器有打击乐大鼓、小鼓、鼗、敔、钟、磬、柷、铎,管乐笙、竽、匏,弦乐琴、瑟等。
第一场: 北征
柷声一作,随之鼓乐齐鸣,其声震天。一队队士兵手执干(盾)戚(斧),在将帅带领下整齐地走上祭坛;左右站立,稳重如山。一阵欢呼声中,武王(演员扮演的,下同)左手拿板斧,右手执白旄,立于战车上,左右拥立着周公、召公、太公,缓缓登场。武王和三公下车,立于“军社”(战争时专门载着神位随军而行的一辆战车)前,礼拜、宣誓。士兵合唱起,管弦乐齐奏。
合唱: 上天发下命令, 文王武王担承。 为王业不贪安稳, 日夜奔驰,为着百姓康宁。
武王: 啊!前途光明、宽广,宽广、光明。 大家努力用心, 天下永享太平!
——《诗·周颂·昊天有成命》
武王、三公登上战车。武王用白旄指挥,鼓声大作,将士们挥舞干戚,如潮水般向前冲去。队形不断变化,表现出浩浩荡荡出征的景象。
第二场: 灭商
鼓声紧密,表示与敌人遭遇。武王用白旄指挥将士冲杀。舞队作奋勇杀敌动作。战斗胜利结束,阵阵欢呼。欢呼声中,武王由三公簇拥下车;拜舞,承受天命代殷。庄严的管弦乐起。
合唱: 伟大的武王, 功劳盖世无双! 把文王作为榜样, 继往开来向前闯。 随着文王的步伐, 打败殷纣,阻止他把人民杀伤。 啊,武王!你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百世流芳!
——《诗·周颂·武》
(《昊天有成命》原诗: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
(《武》原诗: 于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陈多、谢明《先秦古剧考略》,陈多《剧史新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2、53、56页。
陈、谢两位先生还将《诗经·野有死麕》视作歌舞剧,其绎述如下:
野有死麕(歌舞剧绎解)
(郊外,一位少女,跳着采摘野菜的舞蹈。她时而停下来四处张望,像是在等待什么人)
青年头戴草笠,身背弓矢,手持狩猎来的野鹿上场。
青年: (唱)打到了小麋鹿满心欢快, 用白茅仔细地包裹起来。 (少女远远地看到青年,会心地唱)
少女: (唱)女儿家心意里春潮澎湃, 好一个青年人逗引女孩。
青年: (唱)森林里有袅袅小树, 野地里打来了一头麋鹿。 用白茅将它好好包住, 姑娘你好似美玉明珠。 (青年将鹿送与少女。欲拥抱少女,她羞涩地避开)
少女: (唱)慢慢啊,缓缓呀, 别把我的围腰拉, 小心狗叫惹人家。 (两人携手歌舞下)
——剧终
(《诗·召南·野有死麕》原诗: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陈多、谢明《先秦古剧考略》,陈多《剧史新说》,第61、62页。
其实,把《大武》看成戏曲,古已有人。明代王守仁就曾说过:“《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明) 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8页。此处“戏子”,实特指“戏曲”。至于《野有死麕》,陈多、谢明先生认为这可能就是《礼记·郊特牲》中所说的“罗氏致鹿与女”这类故事*《礼记·郊特牲》:“罗氏致鹿与女,而诏客告之,以戒诸侯。”《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454页。。而宋代苏轼早就指出:“猫虎之尸,谁当为之?置鹿与女,谁当为之?非倡优而谁?”他显然是把“置鹿与女”看成是倡优的表演。*(宋) 苏轼《东坡志林》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第26页。
五
1974年于新疆发现了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这个剧本约写于公元6世纪至8世纪。其样式是韵文散文结合,形式上与印度古代叙事文学如《五卷书》之类没有区别,亦即与中国的“说唱文学”相似。但其书名即自称“剧本”,书中使用“幕”、“退出”等舞台术语,因而,季羡林先生断言其为剧本,并指出:“《弥勒会见记》剧本流行于中国唐代,它比戏曲繁荣的宋、元要早得多。《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发现对中国剧史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弥勒会见记”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第270页。《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发现,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历史上曾有过一类戏剧文本,其“代言体”与“叙事体”常常难以严格区分。这种戏剧,与西方近代戏剧大不相同,故而季羡林特别指出:“吐火罗文剧本,无论是在形式方面,还是在技巧方面,都与欧洲的传统剧本不同。带着欧洲的眼光来看吐火罗剧,必然格格不入。”*《季羡林全集》第十一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近年来,有更多的学人在关注中国古代“诗歌”与“戏剧”之间的关系。不仅关注《楚辞》与《诗经》,而且关注到乐府与敦煌曲子词*如钱志熙《汉乐府与戏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戚世隽《中国古代剧本形态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张长彬《敦煌曲子伎艺形态初探》,《曲学》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也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戏剧史开辟了新园地,拓展了研究视野。
同样是古代的诗歌,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同的解释呢?闻一多的一段话很有启发性。他说:
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闻一多《匡斋尺牍》,《闻一多全集》(3),第214页。
把文艺作品“当文艺看”,本应是天经地义之事,但历来因某种习惯或某种意识形态之故而常常被忘却。闻一多此一提醒很重要,他是要拨正人们在赏读文艺作品时的视角。闻一多本人多才多艺,他既是诗人、学者,又是画家、戏剧家,故而独具只眼,能从《楚辞》中看出许多奇妙的上古艺术。
另外,还有一个戏剧观念的问题。也就是要回答“什么是戏剧”的问题。“戏剧”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既具有历史的规定性,又具有历史的流动性。同时,还有个地域、民族的差异问题。在世界历史上,曾有过各种各样的“戏剧”。古代戏剧与近代戏剧不同,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不同。不能用西方近代戏剧的标准去看待中外古今的各种戏剧。但“戏剧”又有它不同于“诗词”、不同于“音乐”、不同于“舞蹈”的独特品格,那就是,它具有综合各种艺术元素的特性。尤其是上古戏剧,往往具有高度融合“诗”、“歌”、“舞”的总体性的特征。不过,古希腊戏剧是以“诗”为本位的总体性表演艺术,古印度戏剧是以“舞”为本位的总体性表演艺术,古中国戏剧是以“乐”为本位的总体性表演艺术。只有别具“大戏剧”的慧眼,才能更好地读懂并识别世界上的各种戏剧。基于此,我们在读中国古代的“曲”时,可以有我们自己独特的二度创作方法,而不必为西方近代戏剧的“定义”所格范。我们的独特方法,恰恰可以丰富与拓宽“戏剧思维”,从而促使“戏剧观念”的更新。
2016年,205— 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