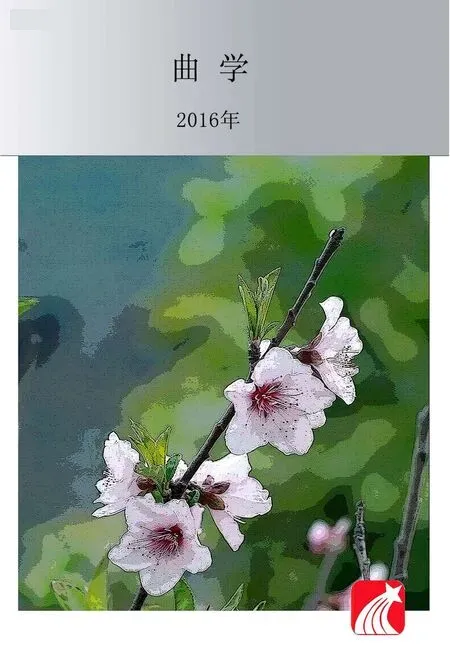顺治、康熙二帝的文化取向与戏曲的南北交流融合*
2016-04-03赵山林
赵山林
《曲学》第四卷
顺治、康熙二帝的文化取向与戏曲的南北交流融合*
赵山林
在封建时代,由于帝王的特殊身份,他们的文化取向和相关言行,对于宫廷戏曲乃至整个剧坛的状况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拟以清初顺治、康熙二帝为例加以初步探讨,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
顺治七年(1650)摄政王多尔衮逝世,顺治八年(1651)正月,顺治帝开始亲政,时年十四岁。对于这位年轻皇帝的言行,王公贵族不时援引太祖、太宗的遗训,加以引导和规范。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上奏:
太宗文皇帝缵承大统,绍述前猷,亦时与诸王贝勒大臣讲论不辍,且崇奖忠直、鼓励英才。录微功,弃小过,凡下诏布令,必求其可以顺民心、垂久远者,然后施行。又虑武备废弛,不忘骑射,时时亲行较猎,曾有诸王贝勒等置酒宴会,优人演剧为乐。适值驾还猎次,克勤郡王以闻,太宗怒曰:“我国肇兴,治弓矢,缮甲兵,视将士若赤子,故人争效死,每战必克,以成大业。朕常恐子孙弃我国淳厚之风,沿习汉俗,即于蹈淫。今汝等为此荒乐,欲求国家兴隆,其可得乎?”*《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十九。
对于济尔哈朗反对“演剧为乐”的上奏,顺治帝是不是作了明确的表态,笔者目前尚未看到有关史料记载。但从顺治帝始终喜爱戏曲的态度来看,他当时并未把戏曲与道德教化严重对立起来。*赵维国《论清代“淫词小说”禁毁管理的法律化》,《中国小说研究》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顺治帝关注明朝历史,也就附带关注描写明朝历史的戏曲作品,他阅读过《鸣凤记》传奇,或者还看过《鸣凤记》的演出。由明入清、官至工部侍郎的程正揆(1604—1676)在《孟冬词二十首》之一中写道:
传奇《鸣凤》动宸颜,发指分宜父子奸。
重译二十四大罪,特呼内院说椒山。*(清) 程正揆《青溪遗稿》卷十五。
由此可知,顺治帝对《鸣凤记》很感兴趣,对严嵩、严世蕃父子奸邪当道表示愤慨。他特别关注杨继盛的事迹,并且由此引出了同一题材的再创作,事见郭棻《蚺蛇胆表忠记序》:
忠愍大节,如日星海岳,弇州题碑,中郎之诔有道,无愧辞矣。后人敲音推律,被之管弦,以其腴而易传,婉而多风也。曩如《鸣凤》诸编,亦足劝忠斥佞,独是以邹、林为主脑,以杨、夏为铺张,微失本旨。今上几务之暇,览观兴叹,思以正之。相国冯公、司农傅公相顾而语曰:“此非丁野鹤不能也。”于是札属殷重。野鹤受书,屏居静室,整衣危坐,取公自著《年谱》,沉心肃诵,作十日思。时而濡毫迅洒;午夜呼灯;时而刿心断须,经旬搁笔。阅数月而兹编成,曰《蚺蛇胆》,志实也,曰《表忠》,扬美也。缮写装演,质之二公。会有以《后疏》一折,借黄门口吻,指前代敝政,搢绅陋习,过于贾生之流涕,有如长孺之直憨,复属笔窜,慎重如告。微词著书,大臣体应如是。无如野鹤五十年来,目击时事发指眦裂者。非伊旦夕,尝以不能跻要津,职谏议,忼忾敷陈,上规下戒,比于魏徵、陆贽,往往见之悲歌感叹。兹幸从事编纂,得少抒积衷,方掀髯大叫,辗然以喜。乃欲令之引嫌避忌,顿焉自更,野鹤然乎哉?于是敛稿什袭,拟付名山。才人之志,亦复如是。是亦足以见出与处之难与易矣。噫嘻!凌云褒美,扬雄之赋以传;枕秘藏书,王充之论未泯。立言不朽,要自有万丈光芒在。矧表章忠义,非所埒于鞶绣之辞者乎!野鹤之文可传,其不欲必传之心尤可传也。*(清) 郭棻《蚺蛇胆表忠记序》,蔡毅《中国古代戏曲序跋汇编》(三),齐鲁书社,1989年,第1523—1524页。
丁耀亢(1599—1669)《表忠记》成于顺治十四年(1657),顺治刊本,二卷三十六出,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据上引郭棻序言,可知此剧写作缘起是顺治帝览观《鸣凤记》,不满该剧以邹应龙、林润为主,以杨继盛、夏言为辅,认为有失创作本旨,希望重新创作。相国冯铨、司农傅维麟于是推荐丁耀亢改写,丁耀亢呕心沥血,数月而成,“专用忠愍为正脚。起孤忠于地下,留正气于人间”*《丁耀亢全集佚名题词》,张清洁校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13页。,突出杨继盛的刚直忠烈,亦直斥嘉靖朝政治的黑暗,其《后疏》一折借黄门长篇道白,冷嘲热讽,以五十年来目击时事发指眦裂者,“指前代弊政,缙绅陋习,过于贾生之流涕,有如长孺之直憨”,“读黄门一折,阅之生悸,两疏风霜昭大节,一编户牖惊真气”*丁存守[满江红]《日照》,张清洁校点《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15页。。冯铨、傅维麟二人以此出言激烈亢直,命耀亢修改,“乃欲令之引嫌避忌,顿焉自更”,耀亢不改,此剧遂以措词违碍未能进呈顺治帝御览*参见丁淑梅《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8— 299页。。
按同时奉命创作的同一题材戏曲尚有《忠愍记》,作者为吴绮(1619— 1694)。据杨恩寿《词余丛话》,“吴园次奉敕谱《忠愍记》,由中书迁武选司员外郎,即以椒山原官官之”*(清) 杨恩寿《词余丛话》,《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51页。。吴绮本人诗中不止一次写到此事,对此是颇为自豪的,如《入署拜椒山杨先生祠》:
排云宁计九重赊,犹剩清风满署衙。
触佞角应同獬豸,驱奸胆不借蚺蛇。
当年臣节何须补,异代君恩更有加。
欲谱遗忠难握笔,先生原是古夔牙。时奉命谱椒山传奇
留将正气与乾坤,俎豆千秋此地存。
筹国不堪言已验,捐驱益信舌难扪。
谁夸龙比为僚友,已见鸾嵩少子孙。
苹藻托交吾未敢,圣朝无事赋招魂。*(清) 吴绮《林蕙堂全集》卷十七《亭皋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龙比”,指关龙逢、比干;“鸾嵩”,指仇鸾、严嵩。
又如《入署偶吟》:
新换头衔骑省郎,终朝驱马看人忙。
铁花绣尽黄密钥,赢取残书迭印床。
平明初下紫宸班,锦署无营昼掩关。
闲拂案尘摊好句,一杯凉雪祭椒山。*(清) 吴绮《林蕙堂全集》卷二十二《亭皋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可见《忠愍记》之作,与《蚺蛇胆》同时受命,而吴绮改本称旨,加官晋爵,丁耀亢改本则以措词违碍,未能进呈。“两剧奉旨而作,而命运判然两别,可见清初统治者的戏剧创作取则。”*丁淑梅《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9页。然而时至今日,吴绮《忠愍记》已佚,而丁耀亢《蚺蛇胆》尚存,这也是当时人始料未及的。
明末清初有一位著名曲师陆君旸,名曜,嘉定人。初从吴门范昆白习北曲,弹三弦,曾为《董西厢》谱曲。后又擅南曲,善吹笛。徐珂《清稗类钞》记载清兵下江南之时:
会大兵入吴,遁于三江之浒者若干年。世祖闻其名,御书红纸曰:“召清客陆君旸来。”既入,御便殿赐坐,令弹。陆乃弹元词《龙虎风云会》曲,称旨,赐之金。自是,贵邸巨室争邀致之,无虚日。或欲使隶太常,弗屑也。年七十,尚能作遏云之逸响。宋荔裳按察琬赠以诗云:“曾陪铁笛宴宁王,吹笛梅花满御床。几度凄凉春草碧,不堪重过斗鸡坊。”
时松江提督马进宝亦缿首下狱,人不敢问。进宝故善君旸,君旸任侠,直入狱具饷。台臣闻者皆大駴,各起谋劾之。华亭张法曹急往告,君旸忼忾曰:“吾何难仍遁之三江间耶!至尊若问我,道我病死。”言讫竟行。后上果问及,如其言,上为叹息。当是时,君旸名藉甚。初本名曜,君旸者其字。至是,以上称君旸,遂以字行,凡长安门刺往来奏记,皆得直书陆君旸以为荣。*(清) 徐珂《清稗类钞》音乐类十。
按《龙虎风云会》即罗贯中所作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演奏此曲明显带有歌颂顺治帝之意。这个戏,顺治帝之前的明天启帝,之后的乾隆帝,都是喜欢唱的。上引宋琬诗为《赠陆君旸七首》之六*(清) 宋琬《安雅堂未刻稿》卷五,清康熙间刻本。。又当时人董俞亦有《春从天上来·赠陆君旸》一词:
白发花卿。向梨花皓月,绿醑同倾。宫商自谱,乐府新声,骊珠一串分明。看轻拢慢捻,掩抑无限深情。正魂消,渐曲终人散,斗转参横。 当年禁廷宠召,喜子夜瀛台,天语峥嵘。汉代延年,唐时幡绰,风流今古齐名。旋南驰叱拨,春江路、蟾白螺青。掩柴荆,蒲团茗碗,蝶梦初醒。*(清) 董俞《玉凫词》,《清名家词》第三卷,上海书店,1982年,第35页。
“当年禁廷宠召,喜子夜瀛台,天语峥嵘”,写的就是陆君旸奉召为顺治帝演奏、得到好评的这番遭遇。
昆山诗人叶奕苞(1629— 1686,字九来),在与堂兄叶方霭(?—1682,字讱庵)的唱和诗中亦写到陆君旸。其《春夜同讱庵兄观剧三叠前韵》之三云:
共叹龟年侍帝宸,霓裳几叠梦相亲。
调移凤管迷新曲,影侧乌纱俨旧人。
笛里残梅消岁月,杯中浮蚁隔风尘。
欲知沧海三迁事,邀取麻姑细指陈。*(清) 叶奕苞《经锄堂诗稿》“倡和诗”,清康熙间刻本。
以天宝年间李龟年比拟顺治年间陆君旸,其立意可以参看叶方霭《观剧和九来》四首之三:
曾听箫韶奏紫宸,钧天余响自情亲。
阿谁优孟真佳士,若个何戡是旧人。
环佩清宵犹望幸,鱼龙甲帐久生尘。
茂陵园寝闻歌吹,玉碗传来事已陈。
庚子春侍驾南海子,得见内廷诸秘戏。*(清) 叶奕苞《经锄堂诗稿》“倡和诗”附录,清康熙间刻本。
叶奕苞、叶方蔼的唱和诗作于康熙元年(1662),其时叶方蔼正因“奏销”案中欠银一厘而革职家居。时传“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咏的便是这位顺治十六年(1659)一甲第三名进士*陆林《清初戏曲家叶奕苞生平新考》,《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唱和诗是追念顺治朝之作。诗中小注提及的“庚子”即顺治十七年(1660),可见那一次宫廷演出的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顺治一朝宫廷戏曲演出记载较少,但实际上仍可发掘,这组唱和诗可为一例。
陆君旸对昆曲音乐的贡献是得到公认的,乾嘉时人舒位(1765— 1815)《论曲绝句十四首,并示子筠孝廉》其六云:“便将乐句赠青棠,腰鼓零星有擅场。协律终怜魏良辅,安弦定让陆君旸。”*(清) 舒位《瓶水斋诗集》卷十四。将其与魏良辅相提并论,可见其影响是不小的,而这影响,与顺治帝的召见恐怕不无关系。
顺治帝不但喜欢看戏、听戏,而且喜欢与人谈论戏曲。据《北游集》载,福临曾与浙江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忞禅师(1596—1674)谈文论艺:
上一日持一韵本示师曰:“此词曲家所用之韵,与沈约诗韵大不相同。”师为展阅一过。上曰:“北京说话独遗入声韵,盖凡遇入声字眼,皆翻作平上去声耳。”于是上亲以喉唇齿舌鼻之音调,为平上去入之韵,与师听之。又言:“《西厢》亦有南北调之不同,老和尚可曾看过么?”师曰:“少年曾翻阅,至于南北《西厢》,忞实未辨也。”上曰:“老和尚看此词何如?”师曰:“风情韵致,皆从男女居室上体贴出来,故非诸词所逮也。”师乃问上:“《红拂记》曾经御览否?”上曰:“《红拂》词妙,而道白不佳。”师曰:“何如?”上曰:“不合用四六词,反觉头巾气,使人听之生趣索然矣。”师曰:“敬服圣论。”*《北游集》卷三。
谈话内容涉及词曲声韵、戏曲作品评价。顺治帝对张凤翼《红拂记》的评价切中肯綮,可以看出他具有相当高的鉴赏水平。由《西厢记》,二人又谈到金圣叹:
上曰:“苏州有个金若采,老和尚可知其人么?”师曰:“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上曰:“正是其人。他曾批评得有《西厢》、《水浒传》,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师曰:“与明朝李贽所谓卓吾子者同一派头耳。”*《北游集》卷三。
顺治帝对金圣叹的评价也是切中肯綮的。对于金圣叹的评点,顺治帝还有一段评价:“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事见金圣叹《顺治庚子正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口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具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七律八首,其第一首云:
绛县涂泥不记春,江南梅柳漫惊新。
忽承帝里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
合殿近臣闻最切,九天温语朗如神。
昌黎好手夫何敢,苏轼奇逢始信真。*(清)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
顺治帝所见的《才子书》,就是崇祯十四年(1641)问世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顺治十三年(1656)问世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邵兰雪即邵点,金圣叹友人,是一名滞留京城的太学生。顺治帝对《才子书》的评价,当是新科状元、昆山人徐元文(1634—1691)等近臣转述,被居京的邵点耳闻,传回苏州的。*参见陆林《清初邵点其人及与金圣叹交游考——兼论金诗〈春感〉八首的创作心态》,《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2期。可见金圣叹当时对自己的作品受到皇帝青睐,是何等喜出望外。庚子年是顺治十七年(1660),其后一年,即顺治十八年(1661)五月,金圣叹因“哭庙案”惨遭杀害,妻儿充军,其结局也是当时人始料未及的吧。
金圣叹之外,状元徐元文的业师尤侗也是受到顺治帝好评的:
上一日慨叹:“场屋中士子多有学寡而成名,才高而淹抑者,如新状元徐元文业师尤侗,极善作文字,仅以乡贡选推官,在九王摄政时复为按臣参黜,岂非时命大谬之故耶!”师云:“忞闻之: 君相能造命,士之有才,患皇上不知耳。上既知矣,何难擢之高位。”上曰:“亦有此念。”因命侍臣取其文集来,内有《临去秋波那一转》时艺,上与师读至篇末云:“更请诸公下一转语看。”上忽掩卷曰:“请老和尚下。”师云:“不是山僧境界。”时升首座在席,上曰:“天岸何如?”升曰:“不风流处也风流。”上为大笑。*《北游集》卷二。
尤侗以时文体所作《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引《西厢记》之意而申之,顺治帝十分感兴趣,在经筵上向翰林院学士王熙(1628—1703)索览,亲加评点,赞赏不迭,连称“才子”*(清) 尤侗《西堂集》卷首。,这里又与木陈忞同读,可见兴致不浅。尤侗《读离骚》一剧,亦“曾进御览,命教坊内人装演供奉”*(清) 尤侗《读离骚自序》。。这都是尤侗引为荣耀的,当然也是他的学生徐元文引为荣耀的。
顺治帝对尤侗的眷顾,后来被木陈忞写进了《世祖章皇帝哀词》十首之三:
洞开四目舜诸瞳,天鉴高垂度亦洪。孝重鲰生翻埜纪(忞进孝子黄尚坚万里寻亲纪,上极嘉叹,即命词臣译为满字,以便御览),才怜下士念尤侗(上一日出名士尤侗集示忞,因叹其才高不第,位居下僚,复为上官论斥,李广数奇,岂不诚然。忞言君相能造命,上既知侗,何难擢用。上曰久有此心)。间谈思庙长挥涕,因说嘉鱼亟叹忠(明臣熊鱼山,讳开元)。惠我生民须哲后,堪嗟莫挽鼎湖龙。*(清) 释道忞《布水台集》,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30册,第43页。
诗中写到的明清间人物,都是顺治帝与木陈忞当日宫中对话所谈到的,尤侗之外,还有三位:
“孝重鲰生翻埜纪”,指苏州孝子黄尚坚,他不顾关山阻隔,抛妻别子,独行万里,前往云南寻找明末在云南为官的父亲黄孔昭,历尽艰险,终于全家团圆。黄向坚寻亲事,他本人著有《寻亲纪程》、《滇还纪程》,归庄《黄孝子传》、顾公燮《消夏闲记》中亦有记载,其事被“苏州派”作家李玉写成了传奇《万里圆》,亦名《万里缘》,为干戈遍地的明清易代之际留下了一幅写照。
“因说嘉鱼亟叹忠”,指在明末被廷杖,入清后弃家为僧,隐苏州灵岩以终的熊开元(1599—1676)。他所作的《击筑余音》套曲,是与贾凫西《历代史略鼓词》类似的作品,都表现了对于明清易代、天地反复的沉痛之情。
“闲谈思庙长挥涕”中之“思庙”,乃崇祯帝谥号。顺治帝与木陈忞曾经谈及崇祯帝:
上曰:“御河之南有台,明称南台,朕今改之,所谓瀛台也。宫城之北有山,明称煤山,朕今改之,所谓景山也。煤山即崇祯帝投缳之所。”语毕潸然,复歔欷叹息曰:“崇祯帝亦英主,惜乎有君而无臣,不幸为李闯窘迫,毕命于此,殊为可恨。”*《北游集》卷三。
另一次则从书法谈起:
上笑曰:“朕字何足尚,崇祯帝字乃佳耳。”命侍臣一并将来,约有八、九十幅,上一一亲展视,师时觉上容惨戚,默然不语。师观毕,上乃涕洟曰:“如此明君,身婴巨祸,使人不觉酸楚耳。”又言:“近修明史,朕敕群工不得妄议崇祯帝。又命阁臣金之俊撰碑文一通,竖于隧道,使天下后世知明代亡国,罪由臣工,而崇祯帝非失道之君也。”师曰:“先帝何修得我皇为异世知己哉!”*《北游集》卷四。
顺治帝对于崇祯帝的评判,当然首先是为了论证清灭李自成、张献忠是为明复仇,进而论证清代明而兴是“天命所归”,这一评判不仅为《明史》的修纂确定了基调,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戏曲中崇祯帝形象的塑造。且看《铁冠图·观图》中崇祯帝的道白:“自临御以来,从无失德;不料流寇猖乱,海宇分崩,近日秦关失守,边疆吿急,眼见兵锋渐近神京。那些文武大臣,并无一人能建奇策,为国家灭贼退兵,岂祖宗王业将终于此乎,使朕寝食不安,如何是好。”在王承恩禀报“奉旨向勋戚大臣借银助饷,答应者寥寥数人。其余尽推贫乏,不肯捐助”之后,崇祯帝唱道:
[解三酲]叹臣僚勋爵坐享,山河誓簪笏绵长。更有那系姻亲的结契在椒房上,岂忍见邦家多沦丧。却怎生忘情任逐秦家鹿,袖手傍观歧路羊。还思想,笑纡朱拖紫,讵少忠良。
《铁冠图·煤山》中崇祯帝绝命词中所写的“德薄承天命,登庸十七年。朕非亡国主,误国是谗奸”,也是同样的意思。
《桃花扇》第十三出《哭主》中,崇祯帝死后,左良玉失声痛哭:
[胜如花]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其后左良玉领众齐拜,举哀:
[前腔](合)宫车出,庙社倾,破碎中原费整。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又哭介)这恨怎平,有皇天作证: 从今后戮力奔命,报国雠早复神京,报国雠早复神京。
这些地方对崇祯帝的描写,都能够看出顺治帝评价的影响。
(二)
与顺治帝相比,康熙帝的文化取向显得比较成熟而稳定,他在注意了解南北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以大一统的思维,促进南北文化包括戏曲的交流与融合。
顺治年间,宫中演戏主要由隶属礼部的教坊司女优承应。到康熙年间,除教坊司女优外,还新设了隶属于内务府的演剧机构——南府,收罗大批民间艺人,培养训练年轻的太监和艺人自己的子弟来承应演出。无论教坊司还是南府,艺人大多来自民间特别是江南。康熙三十二年(1693)六月,李煦就任苏州织造,到任不久,就挑选了一批女孩子,准备让她们学习弋腔,进宫演唱;但苦于找不到好的弋腔教习,后来还是康熙帝专派宫廷教习叶国桢到苏州加以训练*《康熙三十二年李煦送进女子戏班奏折及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中国书店,2007年,第9页。。杨士凝《捉伶人》一诗则写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江南织造“搜春摘艳供天家”即捕捉民间艺人以扩充南府演剧机构的情况*《芙航诗襭》卷十一。。康熙帝南巡时,也由“江苏织造臣”组织著名戏班“承应行宫”,然后“每部中各选二三人,供奉内廷,命其教习上林法部”,即担任南府的教师。*(清) 焦循《剧说》卷六引史承谦《菊庄新话》,《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中国戏剧出版,1959年,第201页。这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南北戏曲的交流与融合。
康熙帝以上举措,基于他对戏曲史的了解,和对戏曲声腔特点的认识。懋勤殿旧藏《圣祖谕旨》中有这样的话:
魏珠传旨,尔等向之所司者,昆弋丝竹,各有职掌,岂可一日少闲,况食厚赐,家给人足,非常天恩,无以可报。昆山腔,当勉声依咏,律和声察,板眼明出,调分南北,宫商不相混乱,丝竹与曲律相合而为一家,手足与举止睛转而成自然,可称梨园之美何如也。又弋阳佳传,其来久矣,自唐《霓裳》失传之后,惟元人百种世所共喜。渐至有明,有院本北调不下数十种,今皆废弃不问,只剩弋阳腔而已。近来弋阳亦被外边俗曲乱道,所存十中无一二矣。独大内因旧教习,口传心授,故未失真。尔等益加温习,朝夕诵读,细察平上去入,因字而得腔,因腔而得理。*转引自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第6页。
这表明康熙帝对昆山腔十分重视,要求南府认真组织排练,精益求精。他对于“梨园之美”的概括十分精到,先从“曲律”着眼,继而要求“丝竹与曲律相合而为一家”,进而要求“手足与举止睛转而成自然”,可以说包括了戏曲表演之美的各个要素,完全是行家之言。
康熙帝这里还谈到弋阳腔,实际上他的视野扩展到整个北曲,从唐代歌舞谈到元明杂剧,要求“因字而得腔,因腔而得理”,探其精要,存其本真。
他的这种见解,还写进了诗歌,见其《偶观演剧作》:
雅颂不能传,诗词降作调。
唐人歌舞精,元曲选声妙。
若曰得仙音,究未探其要。
暂为遣见闻,寄此发长啸。*《圣祖文皇帝御制文集》卷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依据以上认识,康熙帝对乐书的编纂极为重视,有关问题也乐意向行家请教,懋勤殿旧藏《圣祖谕旨》中有这样一段:
问南府教习朱四美: 琵琶内共有几调?每调名色原是怎么起的?大石调、小石调、般涉调,这样名色知道不知道?还有沉随、黄鹂等调,都问明白。将朱之乡的回语,叫个明白些的,着一一写来。他是八十余岁的老人,不要问紧了,细细的多问两日,倘你们问不上来,叫四阿哥问了写来,乐书有用处。再问屠居仁,琴中调亦叫他写来。*转引自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第7页。
朱四美,康熙三十年左右满文档案中有弹乐教习或教授弹琴的教习朱之清,可能即此人。四阿哥即日后的雍正帝胤禛,“乐书”即当时编纂的《律吕正义》*参见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第7页。。
对于剧本的改编,康熙帝也很重视,《圣祖谕旨》中有这样的话:
《西游记》原有两三本,甚是俗气。近日海清,觅人收拾,已有八本,皆系各旧本内套的曲子,也不甚好。尔都改去,共成十本,赶九月内全进呈。*转引自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第7页。
于是康熙年间宫廷内部就有了《西游记》的改编本,到乾隆年间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升平宝筏》的宫廷大戏。
康熙帝下江南,注意感受江南文化。康熙二十三年(1684)首次下江南,所作《南巡笔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十月)二十三日,抵维扬,市肆繁华,园亭相望。游平山堂、天宁寺,百姓持香夹道,意甚诚敬。平山堂乃宋臣欧阳修所建,修以文学侍从之臣,出知扬州,为政之暇,优游谈宴,传为佳话。故朕诗有“文章太守心偏忆”之句。
(十月)二十八日,回銮,过虎丘。山不甚高,亭榭阑槛,布满其上。千人石,高下可容千人。传为生公讲经处,故旁有点头石。剑池,在夹崖中,殊可观。平远堂,俯瞰虎丘之背,田畴林木,望若错锦。苏民仍列酒坊、茶肆,各安生业。管弦竞奏,觉有升平景象。然从事纷奢,罔知务本,未若东北风俗之朴实耳。夜坐舟中,与侍臣高士奇谈论古今兴废之迹,或读《尚书》、《左传》及先秦两汉文数篇,或谈《周易》,或赋一诗,每至漏下三十刻不倦,日以为常。盖诗书意味深长,不似耳目之好,易于烦厌也。*《南巡笔记》,《圣祖文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可见康熙帝南巡,欣赏江南风景名胜,对其中的文化蕴涵尤感兴趣,同时也留心考察南北风俗的差异。
以上两则笔记的日期之间,即十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康熙帝看了不少戏。姚廷遴《历年录》记载,十月二十六日康熙帝来到苏州,不住预先安排的行宫拙政园,提出要住苏州织造祁国臣的工部衙门:
工部妻子出来朝拜,拜毕即抬出小饭来。上曰:“不必用你的,叫朕长随来煮。这里有唱戏的么?”工部曰:“有。”立刻传三班进去,叩头毕,即呈戏目,随奉亲点杂出。戏子禀长随哈曰:“不知宫内体式如何?求老爷指点。”长随曰:“凡拜要对皇爷拜,转场时不要将背对皇爷。”上曰:“竟照你民间做就是了。”随演《前访》、《后访》、《借茶》等二十出,已是半夜矣。上随起,即在工部衙内安歇。*(清) 姚廷遴《历年录》(稿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9—120页。
这天演出的剧目是康熙帝亲自点的,包括《浣纱记》的《前访》、《后访》,《水浒记》的《借茶》等二十出。第二天上午,又接着看戏:
次日皇爷早起,问曰:“虎丘在那里?”工部曰:“在阊门外。”上曰:“就到虎丘去。”祁工部曰:“皇爷用了饭去。”因而就开场演戏,至日中后,方起马。*姚廷遴《历年录》(稿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0页。
到虎丘,拜佛、观塔之后,便坐在大殿上观看演出:
传苏州清客打十番,打完,上曰:“好,果然好。但是只晓得南方的音,还不晓得我北方的音。叫小番来,打一番与你们看。”即刻飞传舡上小番来,俱十五、六岁俊俏童子,一样打扮,俱穿酱红缎衣,头戴红纬貂帽,共一十六个。各持乐器上山,在大殿前两旁边立,打一套十番,果然好绝,姑苏极老班头,亦从未闻见者。约有一个时辰方毕,时已黄昏矣。*同上。
康熙帝从大殿出来,看见下边百姓拥挤,塔上俱点红灯,照耀满山,看者不肯散去:
上曰:“上边百姓都已听见了,下边的还没有听见,再打一套去。”随坐千人石上,打起十番。上自动手打鼓,后乃连打数套,逐件弄过,直打至二更时方完。*同上。
这里康熙帝感兴趣的十番,是集打击乐与管弦乐为一体的变响音乐。其打击技法别具一格,自成一家锣鼓经。其管弦乐的乐曲,多取元曲及昆曲的曲牌选段或选句*浙江遂昌十番以演奏《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长生殿》《浣纱记》的昆曲曲牌,在各地十番中别具一格,称为“遂昌昆曲十番”。。明沈德符(1578—1642)《顾曲杂言》曰:“又有所谓《十样锦》者,鼓、笛、螺、板、大小钹、钲之属,齐声振响,亦起近年,吴人尤尚之,然不知亦沿正德之旧。武宗南巡,自造《靖边乐》,有笙,有笛,有鼓,有歇、落、吹、打诸杂乐,传授南教坊。今吴儿遂引而伸之,真所谓‘今之乐犹古之乐’。”*(明) 沈德符《顾曲杂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217页。
按十番和昆曲一样,在当时的苏州都很流行。康熙朝大学士张英(1637— 1708)《吴门竹枝词二十首》中间有两首写道:
虎丘待月中秋节,玉管冰弦薄暮过。
山畔若教明月上,便愁无地驻笙歌。
挝鼓一通多逸气,老年白相坐当中。
四围弦索清歌绕,争和祢衡白发翁*(清) 张英《文端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前面一首写的是昆曲,后面一首写的是十番,二者共同营造了浓郁的艺术氛围。十番南北多地皆有,康熙帝这次在苏州特地点听并且高度赞美江南十番,又特地点演并且亲自演奏南方民众不易听到的北方十番,南北十番并奏,明显带有促进交流之意。
康熙二十八年(1689)第二次南巡,接驾的仍然是苏州织造祁国臣。此时苏州戏曲更加繁荣,“时郡城之优部以千计,最著者惟寒香、凝碧、妙观、雅存诸部。衣冠宴集,非此诸部勿观也”,而寒香部净角陈明智尤享大名,被称为“甪直大净”。这次祁国臣“以寒香、妙观诸部承应行宫,甚见嘉奖。每部各选二、三人,供奉内廷,命其教习上林法部,陈特充首选”*(清) 焦循《剧说》卷六引《菊庄新话》,《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第199— 201页。。这是戏曲南北交流,并且进入宫廷的一个生动例证。
康熙朝,演剧活动频繁,且以昆曲、弋阳腔为主,被戏曲史家经常提及的有两次。
一次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三藩之乱以后的庆祝演出。董含《莼乡赘笔》记载:“二十二年癸亥,上以海宇荡平,宜与臣民共为宴乐,特发帑金一千两,在后宰门架高台,命梨园演《目连传奇》,用活虎、活象、真马。先是江宁、苏、浙三处织造各献蟒袍、玉带、珠凤冠、鱼鳞甲,俱以黄金、白金为之。上登台抛钱,施五城穷民。彩灯花爆,昼夜不绝。”后宰门,即今地安门。
另一次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为庆祝康熙帝六十寿辰举行大规模戏曲演出。根据宋骏业、王原祁、王奕清、冷枚、邹文玉、徐玫、顾天骏、金昆合作完成的《康熙万寿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描绘的图景,从紫禁城神武门至海淀畅春园,共设戏台四十九座,其中可见剧中人的有二十余座,根据朱家溍先生的描述是:
西四牌楼庄亲王允禄府外大街搭设戏台,所演为昆曲《安天会·北饯》。
新街口正红旗搭设戏台,所演为昆腔《白兔记·回猎》。
东四旗前锋统领等搭设戏台,所演为《醉皂》,昆腔、弋腔都有这出戏。
都察院等搭设戏台,所演为昆腔《浣纱记·回营》,另一台为昆腔《邯郸记·扫花》。
西直门内广济寺前礼部搭设戏台,所演为昆腔《上寿》。
正黄旗戏台,所演亦为《上寿》。
西直门内崇元观西大理寺等衙门搭设戏台,所演为弋阳腔戏《列宿遥临》,福禄寿三星登场。
内务府正黄旗搭设戏台,所演为昆腔《单刀会》。
西直门外真武庙前巡捕三营搭设戏台,所演为《金貂记·北诈》,昆腔、弋腔都演这出戏。
广通寺前长芦戏台,所演为昆腔《连环记·问探》。
长芦另一台,所演为昆腔《虎囊弹·山门》。
四川等六省祝寿戏台,所演为《刘海戏金蟾》。
浙江省祝寿戏台,所演为昆腔《邯郸梦·三醉》。
苏州府棕结戏台,所演为《玉簪记》中《问病》或《偷诗》。
直隶鳌山戏台,台上有二捡场人,尚未开戏。
又一直隶戏台,所演为昆腔《西厢记·游殿》。
茶饭房祝寿戏台,所演可能为《双官诰》。
最末两座是直隶的竹式戏台,一台堂桌左右二椅,一椅坐一官员,顶戴袍褂,一椅坐一女子,梳两把头,这出戏可能是演当代故事,所以着时装。
另一台所演可能为《鸣凤记》*朱家溍《〈万寿图〉中的戏曲表演写实》,朱家溍《故宫退食录》,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643页。。
综观以上剧目,显示出昆、弋并存的特点,这与前述康熙帝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康熙帝认为《万寿图》也画得很好,在回答王原祁奏折时表示满意:“《万寿图》画得甚好。无有更改处。”*同上,第636页。
有清一代戏曲的两大名作《长生殿》与《桃花扇》都产生在康熙年间。这两个戏都曾引起康熙帝的注意而进入内廷。孔尚任的《桃花扇》定稿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六月。问世以后,北京的王公士绅纷纷借钞,一时大有“洛阳纸贵”之誉。就在这一年的秋夕,康熙帝派内侍向孔尚任索要《桃花扇》,要得很急,而孔尚任的誊清本一时不知流传到何处,孔尚任无奈,只得赶紧向张平州中丞家找到一本抄本,连夜送进宫中*孔尚任《桃花扇本末》。。相传康熙帝对《桃花扇》非常欣赏,一段时间甚至“内廷宴集,非此不奏”,每次演到《设朝》(十六出)、《选优》(二十五出),常常皱眉顿足说:“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吴梅《顾曲麈谈》第四章“谈曲”,《吴梅全集》理论卷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当然对于《桃花扇》,康熙帝的态度可能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可以从明朝灭亡的前车之鉴中取得有利于巩固满清统治的历史教训,并且进一步论证满清政权取代朱明政权是“天命所归”。另一方面,由于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歌颂了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等明朝的忠臣,谴责了刘良佐、刘泽清、许定国、田雄等降清将领,甚至对改换满洲装束为新朝效命的徐青君给予“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元老缩龟头”的辛辣讽刺,这就很可能引起康熙帝的不快。就在《桃花扇》剧本进入内廷的第二年,孔尚任就因一件疑案的牵连而被罢官。有人怀疑这是《桃花扇》剧本引起康熙帝不快的结果,这样的揣测看来是不无道理的。
洪昇《长生殿》,也曾传入内廷。洪昇的好友,同时也是孔尚任好友的金埴(1663—1740)《题〈桃花扇〉后二截句》其二云:
两家乐府盛康熙,进御均叨天子知。
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清) 金埴《巾箱说》,《不下带编 巾箱说》,中华书局,1982年,第135页。
关于《长生殿》的流行过程,近代曲学大师吴梅先生说:“初登梨园,尚未盛行,后以国忌装演,得罪多人,于是进入内廷,作法部之雅奏,而一时流转四方,无处不演此记焉。”*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卷下三“清人传奇”,《吴梅全集》理论卷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2页。吴梅先生这一描述的准确性,现已无法作更严密的考证。但洪昇因《长生殿》而得祸,《长生殿》也因此祸而更为流行,却是真实的情况。这是一桩颇具戏剧性的事实。
总之,顺治、康熙二帝的文化取向和相关言行,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促进了戏曲的南北交流与融合,对于清代宫廷戏曲乃至整个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6年,187— 203页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戏剧通史”(项目代码10jzd000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