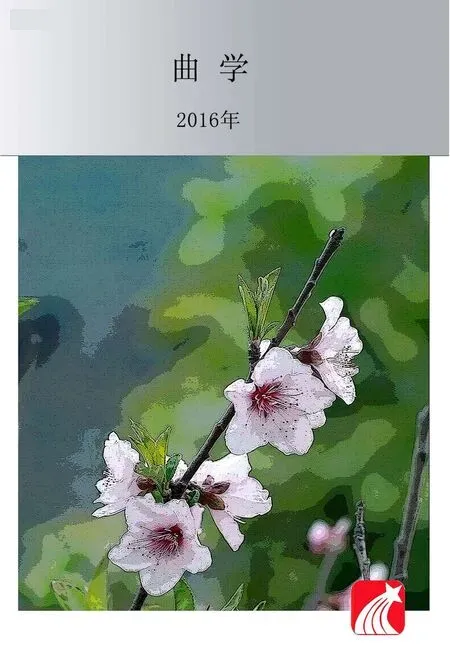挽歌流变考
2016-04-03解玉峰
解玉峰
《曲学》第四卷
挽歌流变考
解玉峰
引 言
挽歌作为送葬歌曲,在中国古代丧礼中使用极为普遍,因为挽歌不论对下层社会、还是对上层社会而言,都有其特殊的功用,故能历数千年之久。汉代以后挽歌的仪式化、制度化,对挽歌诗的创作则有推动之功,并最终使得挽歌(诗)成为中国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挽歌的普遍使用,最终导致职业性挽歌郎的出现,职业挽歌郎和业余唱家们,则为中国古代的歌唱艺术增添了新的艺术品类。故挽歌源流变迁的梳理,或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理解数千年中古代中国在礼仪、风俗、文学、音乐等方面的文化传统。
关于挽歌的研究,学术界过去主要集中于两方面: 一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文人所作挽歌(诗)思想意蕴的解读,二是关于挽歌产生年代或起源的考证。*前一类论文主要有卢苇菁《魏晋文人与挽歌》(《复旦学报》1985年第5期)、王宜媛《六朝文人挽歌诗的演变与定型》(《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吴承学《汉魏六朝挽歌考论》(《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欧阳波《汉魏六朝挽歌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后一类论文主要有齐天举《挽歌考》(《文史》第29辑)、丘述尧《〈挽歌考〉辨》(《文史》第43辑、第44辑)、何立庆《早期挽歌的源流》(《文史杂志》1999年第2期)等。由于前一类研究有相当多的成分为主观阐释,也难求共识,所谓“诗无达诂”,故本文无意卷入诉讼。后一类研究对挽歌研究的深入展开而言有着极重要的意义,是其他研究得以展开的根基和前提。但在笔者看来,挽歌作为民间葬礼中的一种仪式,其形诸文字的时代必远远落后于其实际存在,故今人只能对挽歌的产生年代做出概貌性推论,而不可能有精确性判断,结论愈求精确,距离事实真相可能也愈远。如果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其在后来历史中的变迁,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察考挽歌在历代礼乐、风俗、文学、音乐等方面实际影响和作用,其意义或胜于某一历史起点的推定。
过去关于挽歌研究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挽歌”概念的无限泛化。我们认为,挽歌应基本界定为送葬歌曲,即牵引灵柩前往墓地时所歌之曲,而古代或近代各种临尸而歌(存世文献中多称之为“丧歌”或“哭丧歌”)都不宜归为挽歌。正是因为对挽歌缺少基本的界定,致使有的研究者在挽歌产生年代问题上无限前移*如丘述尧先生《〈挽歌考〉辨》文(《文史》第44辑)即将挽歌上溯到原始社会,中华书局,1998年,第 219页。,如此对挽歌各方面的论述也不能做到有的放矢*“丧歌”或“哭丧歌”的形态、功能各异,而挽歌大都是“一倡众和”、“以齐众力”(详后),对中国古代葬礼及中国文学、音乐有实际意义的也正是此类“挽歌”。。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挽歌为送葬之曲这一基本界定下,从礼乐制度、风俗时尚等方面考察挽歌的源流变迁,努力还原中国古代挽歌的生存图景,进而考察其对中国文学、中国音乐的意义。疏陋之处,敬祈宏达之教正。
一、 挽歌的起源
关于挽歌的产生时代或起源,众家结论不一,概括说来主要有起于先秦、起于汉初田衡、起于汉武帝等三说。涉及挽歌的产生时代或起源的文献资料,主要有以下数条。
《左传》哀公十一年(前484),吴伐齐,“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晋杜预(222— 284)注云:“虞殡,送葬歌曲,示必死。”孔颖达(574—648)疏曰:“杜云送葬歌曲,并不解虞殡之名。礼启殡而葬,葬即下棺,反日中而虞。盖以启殡将虞之歌,谓之虞殡。歌者,乐也。丧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盖挽引之人为歌声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唐)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79年,第2166页。
《庄子》“逸篇”有:“绋讴所生,必于斥苦。”晋司马彪(?—306)注曰:“绋,引柩索也。斥,疏缓也。苦,用力也。引绋所以有讴歌者,为人有用力不齐,故促急之也。”*(南朝宋) 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张驎酒后,挽歌甚凄苦”注,转引自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407页。

东汉末经学家谯周(199— 270)《法训》有:“有丧而歌者,或曰:‘彼为乐丧也,有不可乎?’谯子曰:‘《书》云:‘四海遏密八音。’何乐丧之有?’曰:‘今丧有挽歌者,何以哉?’谯子曰:‘周闻之: 盖高帝召齐田横,至于尸乡亭,自刎奉首。从者挽至于宫,不敢哭而不胜哀,故为歌以寄哀音。彼则一时之为也。‘邻有丧,舂不相’,引挽人衔枚,孰乐丧者邪?’”*(南朝宋) 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刘孝标注,转引自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407页。
西晋崔豹《古今注》卷中“音乐第三”曰:“《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还复滋,人死一去何时归!’其二曰:‘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晋)崔豹《古今注》卷中,辽宁教育出版社标点本,1998年,第8页。
综合以上诸种文献看,笔者认为,挽歌的产生时代似以先秦说较胜,至于产生于西周、还是春秋战国时代,则较难判定。周人重礼,“吉、凶、军、宾、嘉”五礼中,丧葬之事甚被看重。厚葬在上层阶级或富贵阶层往往流行,棺椁则相当沉重,十数人或上百人执绋引柩乃属常见。故《礼记·曲礼》有“助葬必执绋”。郑玄注云:“绋,引车索。”*(清) 阮元《礼记正义》卷三,中华书局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979年,第1249页。何东山云:“天子千人,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同上注,第1298页。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同声协力的必要。《庄子》“绋讴所生,必于斥苦”,正是指出了挽歌用以齐众力的功用。挽歌在先秦时,是否已施用于上流社会,《仪礼》、《礼记》等文献未载,难于考实,但其施用于民间当无可疑。有些挽歌曲调在民间应非常流行,故公孙夏率兵伐齐时,命兵士唱挽歌,以示必死之心。宋玉《对楚王问》中说歌唱《蒿里》,“和者数千人”;歌唱《薤露》,“和者数百人”。但先秦时,挽歌歌辞可能随用随弃,不必为精心制作,而汉初田横门人葬田横时所歌《薤露》、《蒿里》二章,则情真辞切,故备受后世文人瞩目,这应是后人将挽歌源起归至田横时的主要原因。
二、 挽歌的制度化
从文献记载看,上流社会葬礼中用挽歌,至迟应始于汉武帝时代,所谓“《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按,宋玉《对楚王问》中说歌唱《蒿里》“和者数千人”,而歌唱《薤露》“和者数百人”,或可说明早在战国时代挽歌已有雅俗贵贱之别,当时挽歌使用已有礼制因素,唯文献阙如,我们暂且将挽歌的制度化归于汉武帝时。。至此,挽歌的使用乃成为汉家制度。汉初百废待兴,汉家制度仓皇未备,至武帝时礼乐制度大兴,故挽歌作为一种新型礼制进入丧礼,也在情理之中。当然,挽歌作为一种新礼,也不断遭遇到守旧士人的反对。如东汉儒士刁雍作《行孝论》,训诫子孙曰:“轜车止用白布为幔,不加画饰,名为清素车。又去挽歌、方相,并盟器杂物。”*(北魏) 魏收《魏书》卷八十四《刁冲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1858页。汉末经学家谯周也不赞成用挽歌,认为挽歌乃田横门人“一时之为”*见前引《世说新语》“任诞”篇刘孝标注。。甚至直至西晋摰虞时,也仍有人认为挽歌“非经典所制,违礼设衔枚之义”。但摰虞认为,“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挽歌因倡和而为摧怆之声,衔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众。虽非经典所载,是历代故事”。*(唐) 房玄龄《晋书》卷二十《礼志中》引虞挚《挽歌议》,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626页。故从西汉以后的文献看,相关挽歌的文献记载已非常丰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武帝后挽歌在日常社会中的制度化。
当挽歌被上层列入丧制之后,下层社会的挽歌与上层社会的挽歌开始有日渐显著的差异,其差异应不限于所歌曲调的不同(所谓“《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礼以别异”,不同身份等级的人,所用挽歌亦有异。《通典》“挽歌”条云:

按,唐代宗遗制中关于其丧礼(包括挽歌)的规定,固然反映了中唐时的情况,但必前有所本。《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二引《晋公卿礼秩》有:“安平王葬,给挽歌六十人,诸公及开府给三十人。”*(宋) 李昉《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五十二礼仪部三十一,《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第3333、1085、2580、2076页。检《晋书·司马孚传》,安平王司马孚(180—272)之葬“皆依汉东平献王苍故事”。按,东平王刘苍为刘秀之子,司马孚即司马懿之弟、晋武帝司马炎之叔祖,二人皆帝室宗亲,权势倾盖一时。《晋书·桓温传》说桓温死,“一依太宰安平献王、汉大将军霍光故事”,“赐九旒鸾辂,黄屋左纛,輼輬车,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晋书·谢安传》说谢安死,“依大司马桓温故事”。如史家记述,霍光、刘苍、司马孚、桓温、谢安等葬皆同一等级,据此我们可认为,霍光等葬可能皆应给挽歌六十人(所谓“挽歌二部”)。而次一等级的“诸公及开府”(“三品以上”)则给挽歌三十人(所谓“挽歌一部”)。如《宋书》卷五一《刘道规传》:“及长沙太妃檀氏、临川太妃曹氏后薨,祭皆给鸾辂九旒,黄屋左纛,輼輬车,挽歌一部,前后部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梁) 沈约《宋书》卷五十一,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1475页。这便是次一等级的情况。
从《唐六典》、《通典》、《唐会要》、《五代会要》、《通志》、《续通志》、《续通典》等文献看,“挽歌”作为葬礼仪式的一部分在隋唐以后各代中皆有相应之规定,虽世有变革,但仍可见其一贯性特征,如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编成的《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十八“挽歌”条有:
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命翰林学士李昉等重定士庶丧葬制度,昉等奏准后唐长兴二年诏,五品六品常参官丧,舆舁者二十人,挽歌八人,明器三十事,共置八床。七品常参官,舁者十六人。挽歌六人,明器二十事,置六床。六品以下京官及检校试官等,舁者十二人,挽歌四人,明器十五事,置五床,并许设纱笼二。庶人舁者八人,明器十二事,置两床,悉用香舆魂车从之。*(清) 嵇璜编《续通志》卷一百十八《礼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53页。
对照前《通典》所载,我们不难看出其大多仍循前朝故事。挽歌的这种制度化,为挽歌在上流社会的生存提供了较可靠的保障。数千年来,民间社会婚丧礼俗大多崇奢尚厚,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更兼风俗传统的惯性使然,挽歌在民间社会也一直绵延不绝,直至近代。从明清及近代各地方志看,民间葬礼用挽歌者仍很普遍。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湖南《清泉县志》有:
舁柩者或多至三十六人,下至十有六人,舁者作邪许声,有词唱相导,盖古《薤露》、《蒿里》之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547页。
又如光绪十年(1884)刻本江苏《六合县志》亦云:
发引日,用僧乐、挽歌以导輀车,亦有陈列纸帛人物、祭章、亭幔及用方弼方相者。*《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65页。
自先秦以来,中国对周边地区的朝鲜、越南、日本等风俗文化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唐宋以来,随着航海等交通技术的发展,这种影响更为显著,葬礼中用挽歌应很早即及传至这些周边国家。承韩国汉阳大学吴秀卿教授相告,直到今日,在韩国一些农村地区葬礼中仍有使用挽歌的。韩国学者李素罗《韩国丧歌中厄避邪歌和wu ya huol huol》文中也谈到,在韩国挽歌多称“行丧歌”。据李文介绍,韩国的丧歌有六种: 1. 行葬礼之前夜的歌, 2. 葬礼之日的早上,把棺材从房间往外抬时唱的“避邪歌”, 3. 发靷(祭供桌前的祭祀)和路祭中吟唱的“告祱”, 4. 把棺材运往墓地时唱的“行丧歌”, 5. 下葬时唱的“踏墓歌”, 6. 葬礼后,回家途中演唱的歌。以上的1和6都很少见,3是朗诵调,属于全国性的多。2在过去曾广泛流行,但现在知道的人已很少。*李素罗《韩国丧歌中厄避邪歌和wu ya huol huol》,《艺术探索》1997年第6期。
故从挽歌的变迁来看,汉家礼乐制度始备的汉武帝时代,的确是一个值得瞩目的一个阶段。若从挽歌的制度化而言,后世有挽歌起于武帝说并非不可思议。因为在这一阶段,在易为文人瞩目的上流社会,挽歌的仪式化、制度化色彩更加显著。同时,挽歌的这种仪式化、制度化,也催发了文人挽(歌)诗的制作。
三、 挽歌诗的制作
如前所述,挽歌在民间丧礼中其使用虽可能很普遍,但其歌辞的制作一直不被重视,随意为之,也随用随弃,故田横门人为田横制作的挽歌诗才能流行一时,为人瞩目。但当挽歌走向制度化以后,情形便大不一样了。既然送葬时例需有挽歌,请文人学士为亡者制作挽诗乃成为必然之趋势。
从存世文献看,两汉时未见有文人写作挽诗的记载。两汉时文学尚未自觉,诗歌写作尚未成为文人风尚,两汉诗歌除少量乐府诗外,今存者甚少,故汉诗中未见挽诗似亦在情理之中。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两汉文人写作挽诗应未成为常例,即使偶有尝试也属率意为之,自家他人皆不珍视,故今日未见汉人挽诗流存。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代。三国时曹操(155—220)有《薤露行》、《蒿里行》各一首,曹植(192—232)有《薤露行》一首。从诗的内容来看,我们不能说曹氏父子以《薤露》、《蒿里》为题的诗是专为送葬挽歌所作,但我们可以认为,《薤露》、《蒿里》二挽歌曲调当时非常流行,故曹氏父子如后世词曲家一样倚曲填词,曹氏父子之诗在当时皆可倚曲而歌。魏人缪袭(186— 245)今存挽歌诗一首。晋人傅玄(217— 278)今存挽歌诗四首(其中三首似不完整),陆机(261—303)今存挽歌诗七首(其中三首不完整),张骏(306— 346)有《薤露行》一首,陶潜(365— 427)今存挽歌诗三首。魏晋时代流传至今的挽歌诗外,除陶潜三首因为是为自家写的挽诗,有明显的个人化色彩,其他挽歌诗都看不出是专为某人写作的。又,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引陆机挽歌诗时有“王侯挽歌辞”、“士庶挽歌辞”、“庶人挽歌辞”等三种标题。由此来看,魏晋文人已开始参与挽歌诗的写作,但此时的挽歌诗大多是公用性质的,专为某人写作挽诗似未成为主流。魏晋以后,文人专为某王公贵戚、亲朋好友贡献挽诗或受命、受他人之托写作挽诗,则渐成一种传统。
据逯钦立先生所编《先秦汉魏六朝南北朝诗》、《全隋诗》,南北朝文人所作挽诗今存者有宋颜延之(384— 456)《挽歌》一首,宋鲍照(415?— 470)《代挽歌》一首,宋江智渊(418— 463)《宣贵妃挽歌》一首,北魏温子升(495— 547)《相国清河王挽歌》一首,北齐卢询祖(生卒不详)《赵郡王配郑氏挽词》、北齐祖珽(生卒不详)《挽歌》、北齐卢思道(约531—582)《彭城王挽歌》、《乐平长公主挽歌》。单从数量上来说,南北朝时文人所作挽诗今存者并不算多,但南北朝时可能有相当多的挽歌诗未能被保存下来。如《南史》卷七十二《丘灵鞠传》:“宋孝武殷贵妃亡,丘灵鞠献挽歌三首,云:‘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赏。”*(唐) 李延寿《南史》卷七十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1762页。而丘灵鞠所献三首挽歌今无一存。又,《隋书》卷五十七载北齐著名文人卢思道事云:“文宣帝崩,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阳休之、祖孝征等不过得三首,唯思道独得八首,故时人称为‘八米卢郎’。”*(北魏) 魏徵《隋书》卷五十七,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第1397页。不但魏收、阳休之、祖孝征等“当朝文士”所作挽歌诗今皆不存,即使卢思道大为时人称颂的八首挽诗也无一存。前代挽歌诗之亡佚,于此可见一斑。
唐宋以来,文人为亡人奉献挽歌诗的现象,似更普遍。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下载咸通九年(869)同昌公主丧事云:
(同昌)公主薨。上哀痛之,自制挽歌词,令百官继和。及庭祭日,百司与内官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之庭,家人争取其灰,以择金宝。*(唐) 苏鹗《杜阳杂编》,辽宁教育出版社标点本,2000年,第24页。
宋朱熹(1130—1200)《晦庵集》卷九《孝宗皇帝挽歌词》前《序》云:
阜陵发引,诏许近臣进挽歌词,熹恭惟盛德大业,不易形容,方将摅竭鄙思以效万一,冥搜连日才得四语。*(宋)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第119页。
据任半塘先生统计,《全唐诗》中以“挽歌”、“挽词”、“挽歌辞”为题者二百五十四首*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24页。。唐骆宾王、王维、岑参、杜甫、白居易、韩愈、李义山、刘禹锡、温庭筠等,宋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陆游、朱熹等著名文人,皆有相当数量的挽歌诗。
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以来,文人之所以有挽歌诗的写作,因为挽歌诗有其用: 这些挽歌诗很可能在送葬时即交付歌郎歌唱。如《新唐书》卷八十二《承天皇帝倓传》,述大历三年(768)肃宗子李倓迁葬事云:
(代宗)遣使迎丧彭原,既至城门,丧輴不动。帝谓(李)泌曰:“岂有恨邪?卿往祭之,以白朕意,且卿及知倓艰难定策者。”(李)泌为挽词二解,追述(李)倓志,命挽士唱,(李)泌因进酹。輴乃行,观者皆为垂泣。*(宋)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十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3619页。
又,《新唐书》卷七十七载代宗皇后独孤氏葬事云:
大历十年薨,追号为皇后,上谥。帝悼思不已,故殡内殿,累年不外葬。……又诏群臣为挽辞,帝择其尤悲者令歌之。*(宋)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七七,第3497页。
又,宋金盈之编《醉翁谈录》载: 唐艺妓颜令宾,殁前向相识之士大夫求挽词:
寻卒,士夫持至数封。其母拆视之,皆哀挽之词,掷之于地曰:“能救我朝夕耶?”其邻有张□□因取挽歌数篇,教挽柩者唱之,声甚悲怆。*(宋) 金盈之《醉翁谈录》卷八,辽宁教育出版社标点本,1998年,第36、37页。
近些年来,在唐宋新出土文献的整理和利用方面,有些研究者注意到唐宋时在墓志盖上镌刻的挽歌。*如陈忠凯、张婷《西安碑林新藏唐——宋墓志盖上的挽歌》(《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金程宇《稀见唐宋文献丛考》之《新见唐五代出土文献所载唐人诗歌辑校》(中华书局,2008)、胡可先《墓志新辑挽歌考论》(《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5期)。值得指出的,这些挽歌与《全唐诗》等传世文献所载挽歌有不同的特征: 一是其文字一般较为浅俗;二是普遍存在文字相互因袭的现象;三是其作者皆不可考,非出自当时有名望的文人;四是这些挽歌所歌咏的即墓主,均非显达人士。这些特点恰恰反映了这些挽歌可能曾作为民间通用性的歌辞被歌郎演唱。凡此,皆可见当时文人所作挽歌诗交付歌郎歌唱之风尚。
正从上述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汉武帝以后挽歌的仪式化、制度化在客观上推进了文人挽歌诗的制作。
四、 挽歌的娱乐化和职业化
在指出挽歌始终具有的实用性功能(“以齐众力”)以及其在走向制度化以后拥有的“礼以别异”的功用之外,我们也应当指出,挽歌既然是一种歌唱,也自然有一定的艺术性、娱乐性,故自起产生之日起就可能用以娱乐,而不必一定用于送葬仪式中。从史料来看,至迟在汉末,挽歌用为娱乐的现象已很普遍。如东汉应劭(约153—196)《风俗通义》云:
灵帝时(168— 190),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儡,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儡,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国家当急殄悴,诸贵乐皆死亡也。”自灵帝崩后,京师坏灭,户有兼尸,虫而相食者。魁儡、挽歌,斯之效乎?*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568、569页。
又,《后汉书》卷六一《周举传》:
(永和)六年三月上巳日,(大将军梁)商大会宾客,讌于洛水,(周)举时称疾不往。(梁) 商与亲昵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太仆张种时亦在焉,会还,以事告(周)举。(周)举叹曰:“此所谓哀乐失时,非其所也,殃将及乎!”(梁) 商至秋果薨。*(刘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2028页。
又,《晋书》卷二十八《五行志》:
海西公时,庾晞四五年中喜为挽歌,自摇大铃为唱,使左右齐和。又宴会辄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悲切。时人怪之,后亦果败。*(唐) 房玄龄《晋书》卷二十八,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836页。
又,《晋书》卷八十三《袁松传》:
山松少有才名,博学有文章……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初,羊昙善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谓“湛屋下陈尸,山松道上行殡”。*(唐) 房玄龄《晋书》卷八十三,第2169页。
又,《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
元嘉九年冬,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弟广渊,时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宿广渊许,夜中酣饮,开北墉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左迁晔宣城太守。*(刘宋)沈约《宋书》卷六十九,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1819—1820页。
正是因为挽歌的歌唱有一定的艺术性或技术性要求,挽歌郎必然要有一定的技术训练才能称职,并非如一般挽士一样易于获得*有研究挽歌的学者以为,挽歌郎常为官宦子弟或优秀人才,实是将挽郎与挽歌郎混而为一。前引《通典》“挽歌”条关于挽郎与挽歌郎的区分甚明白,此不赘述。。故挽歌郎的职业化可能很早即已发生。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四有云:
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车为事。有挽歌孙岩,娶妻三年,不脱衣而卧。岩因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毛三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59、160页。
又,唐白行简《李娃传》传奇写到世家子弟郑生为挽歌郎歌唱时,有非常精彩的描绘:
又,唐李亢《独异志》“李佐”条所载也多传奇色彩:
李佐,山东名族,少时因安史之乱失其父。后佐进士擢第,有令名,官为京兆少尹,阴求其父,有识者告,后往迎之于鬻凶器家。归而奉养,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谓曰:“汝孝行绝世,然吾三十年在此党中。昨从汝来,未与流辈谢绝。汝可具大猪五头、白醪数斛、蒜虀数瓮、薄饼十拌,开设中堂,吾与群党一酧申欵,则无恨矣!”佐恭承其教,数日乃具。父散召两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即列坐堂中,久乃杂讴。及暮,皆醉,众扶佐父登榻,而《薤歌》一声,凡百齐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宋)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四库全书》本,第670、671页。

宋元以来,随着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社会各类职业划分更趋细密和成熟,远非前代可比,故挽歌郎作为一种特殊职业也应比此前更成熟。从《水浒传》、《连城璧》等小说来看,“棺材出了门,讨挽歌郎钱”(意谓为时已晚,自找晦气),乃是宋元以来的民间谚语。《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卷二十一有:
(阎)婆惜冷笑道:“你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儿般捉弄,我便先还了你招文袋这封书,歇三日却问你讨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我这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快把来,两相交割。”*《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2000年,第227页。
又如李渔《连城璧》申集:
殷四娘看见大势已成,恐怕众人到了一处,大家和好起来,说出两相情愿的话。这个和事老人就不但无功,反有过了,“棺材出门之后,去讨挽歌郎钱”,那里还得清楚,所以两边终日催促要想完姻,殷四娘故意作难,只是延捱推阻,直等那三主谢仪陆续收完了,方才与他成事。*清康熙写刻本,第158页。
谚语中的“挽歌郎”当然都是专事此业的。宋末元初人燕南芝庵《唱论》述及唱曲题目有云:
有曲情,铁骑,故事,采莲,击壤,叩角,结席,添寿;有宫词,禾词,花词,汤词,酒词,灯词;有江景,雪景,夏景,冬景,秋景,春景;有凯歌,棹歌,渔歌,挽歌,楚歌,杵歌。*(元) 燕南芝庵《唱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60页。
按,燕南芝庵为宋末元初人,生平不详,其所著《唱论》实为当时民间唱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唱论》既将“挽歌”列为“唱曲题目”之一,亦可见挽歌对当时职业唱家的重要。吴敬梓(1701— 1754)《儒林外史》从很多方面反映了清中叶时的社会风习,小说第二十六回写到鲍文卿葬事时,有云:“这里到了出月初八日,做了铭旌。吹手、亭彩、和尚、道士、歌郎,替鲍老爹出殡,一直出到南门外。”*(清) 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点校本,1962年,第315页。这里的“歌郎”,显然也是职业性质的。
汉末以来,挽歌被用为娱乐以及挽歌职业化发展,都说明挽歌不仅有实用性或制度性功用,而是一种有特殊风味色彩的歌唱艺术,故历代才会有如此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人们耽爱挽歌。《李娃传》中挽歌唱的描绘令人神往,作为小说家言其中不免过多夸饰和渲染,但仍促使我们试图对挽歌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五、 挽歌的歌唱:“文”与“乐”
挽歌唱首先是一种“相和歌”,即一人倡之、众人和之。关于挽歌这种一倡众和的歌唱形式,多种文献可为佐证。如前引《风俗通义》云:“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晋书》说“自摇大铃为唱,使左右齐和”。《李娃传》说西肆挽歌人“拥铎而进,翊卫数人”,《独异志》写道李佐父“薤歌一声,凡百齐和”。宋郭茂倩(1041—1099)《乐府诗集》将挽歌诗归为“相和歌辞”一类。朱熹(1130—1200)《朱子语类》论及《诗经》时说:“如《清庙》一倡三叹者,人多理会不得。注下分明说:‘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譬如今人挽歌之类。今人解者又须要胡说乱说。”*(宋) 朱熹《朱子语类》,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第2065页。
挽歌唱是一种“相和歌”,文献俱在,无可疑议。作为“相和歌”,挽歌唱是一种究竟应当何处用“和声”?历代文人所作挽歌诗多为整齐的五、七言诗(中唐以前多为五言,中唐以后始见七言*笔者所见最早的七言挽诗为白居易《元相挽歌词三首》。,但仍以五言为主流),这些挽歌诗在交诸歌郎演唱时是否会有改造?
上述问题对我们总体上理解挽歌诗甚为重要,可惜相关的文献资料甚少,下面让我们研读以下几条较珍贵的资料。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六“寒食诗”条引《王直方诗话》云:
(苏)东坡云与郭生游寒溪,主簿吴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发声,坐为凄然。郭生言恨无佳词,因改乐天寒食诗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词曰:“鸟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路,尽是死生离别处。冥寞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每句杂以散声。*(宋) 魏庆之《诗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78年,第343页。
按,《王直方诗话》的作者王直方(1069—1109),算是苏轼的后辈,其所述或有所本。其所谓每句后的“散声”应即是“和声”,不过此处唱挽歌唯郭生一人,故“和声”也只能由其一人歌唱。
《缀白裘》为苏州人陈德苍于清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763—1774)陆续编成的著名的折子戏选本,内收源自戏文《幽闺记》的《请医》一折,其中有庸医一家四口唱《蒿里歌》一段表演,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挽歌的功用及歌唱形式(念白为苏州方言):
(净)是我里家主婆、小儿、儿媳哉,扛子棺材,我里家主婆说道:“喂,老个,我里又心好哉,唱介只《蒿里歌》,接接力罢。”我说道:“使得个!”我就第一个来哉,说道: (唱)“我做郎中命运低。蒿里又蒿里!”(白)我里家主婆来哉,说道: (唱)“你医死个人儿,连累着妻。蒿里又蒿里!”(白)唔猜我里个强种拿个扛棒得来,对子地下一甩,说道: (唱)“唔医杀子胖个,扛不动。蒿里又蒿里!”(白)我里儿媳妇好,孝顺得极,走得来,对子我深深里介一福,说道:“公爹,(唱)从今只拣瘦人医。蒿里又蒿里!”*(清) 陈德苍编《缀白裘》第十二集,中华书局点校本,1955年,第228页。
按,“请医”一折所保存的《蒿里歌》,应当反映了下层民间挽歌的演唱,其歌辞有明显随心编造的特点,但其每句后合唱“和声”的形式,应当是所有挽歌的共同形式。值得注意的明乐天大笑生辑笑话集《解愠编》所收与《请医》显然有渊源的一则笑话,《解愠编》卷三“拣瘦者医”条有:
一庸医不依本方,误用药饵,因而致死病者,病家责令医人妻子唱挽歌,舁柩出殡。庸医唱曰:“祖公三代做太医。呵呵咳。”其妻曰:“丈夫做事连累妻。呵呵咳。”幼子曰:“无柰亡灵十分重。呵呵咳。”长子曰:“以后只拣瘦的医。呵呵咳。”*(明) 乐天大笑生编《解愠编》,中国戏剧出版社点校本,1999年,第12页。
今日昆曲之折子戏多是明中叶后因舞台演出而不断打磨加工而成,其最终定型基本上可认为在清乾隆中叶。《请医》一折在原戏中本为极为简短的过场戏,后来被艺人加工成可演出长度约三十分钟左右的折子戏。故笔者认为,《缀白裘》所收《请医》中歌唱《蒿里歌》一段表演当主要据类似《解愠编》所载嘲笑庸医类的笑话加工而成。两相比较,其不同主要是: 一、《解愠编》中唱辞为整齐的四句七言诗,《请医》中唱辞长短不齐;二、 “和声”部分,《解愠编》为“呵呵咳”,《请医》为“蒿里又蒿里”。对于后者,较易解释。从一般情况看,凡用“和声”的歌曲,其“和声”部分的音乐旋律一般有相对稳定的特征,“和声”部分的主要意义也在“乐”,不在“文”,故“和声”的“文”可用无实指意义的虚词(“呵呵咳”或“邪许哟”)或者虚指的“蒿里又蒿里”,故郭生唱苏轼改造的寒食诗,也应是每句后另加“蒿里又蒿里”一类的虚指辞。
挽歌郎歌唱时一般是严守原诗,还是在本辞基础上有所增益?齐言之诗(五言诗或七言诗)是否一定要变为长短不齐的杂言才能歌唱?对这一问题,若单纯依赖相关挽歌的文献材料则无从回答,我们只能依照常例去推定。从乐府诗歌唱的一般情况看,乐人或唱家往往要对原辞进行一番改造的。《南齐书》卷十一《乐志》有:“侏儒导舞人自歌之。古辞俳歌八曲,此是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摘取之也。”*(唐)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195页。其实,乐人或唱家对原辞的改造并非仅限于“摘取”这一种形式,以下仅取二例以说明之。魏武帝曹操《苦寒行》为很著名的乐府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三并载其原辞以及其被晋乐演奏时的歌辞,我们现在将其并列如下:
本辞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阪诘屈,车轮为之摧。
晋乐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一解
本辞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晋乐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道啼。二解
本辞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晋乐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三解
本辞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道正徘徊。
晋乐 我心何拂郁,思欲一东归。何拂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道正徘徊。四解
本辞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晋乐 迷惑失径路,暝无所宿栖。失径路,瞑无所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五解
本辞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
晋乐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六解
两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到,晋乐演奏曹操《苦寒行》时,对原诗改动极少(仅将“迷惑失故路”改为“迷惑失径路”、“薄暮无宿栖”改为“暝无所宿栖”),但歌唱时却大量使用叠唱(如叠用“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等),使得原来纯粹的五言诗中加入少数三言诗句,入乐后的歌辞篇幅明显超过原辞。
又如魏眀帝曹叡的《歩出夏门行》,《宋书》卷二十一、《乐府诗集》卷三十七并载其在魏晋时演唱的歌辞:
步出夏门,东登首阳山。嗟哉夷叔,仲尼称贤。君子退让,小人争先。惟斯二子,于今称传。林钟受谢,节改时迁。日月不居,谁得久存。善哉殊复善,弦歌乐情。一解
商风夕起,悲彼秋蝉。变形易色,随风东西。乃眷西顾,云雾相连。丹霞蔽日,采虹带天。弱水潺潺,落叶翩翩。孤禽失群,悲鸣其间。善哉殊复善,悲鸣在其间。二解
朝游清泠,日暮嗟归(“朝游”上为艳)。蹙迫日暮,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风雨,树折枝摧。雄来惊雌,雌独愁栖。夜失群侣,悲鸣徘徊。芃芃荆棘,葛生绵绵。感彼风人,惆怅自怜。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之说,嗟哉一言。(“蹙迫”下为趋)
按,这段署名魏眀帝的歌辞,实际上除采用曹操《短歌行》“乌鹊南飞”数句外,又取曹丕《丹霞蔽日行》全篇(略易数字),将“丹霞蔽日”到“悲鸣其间”六句插到第二解,又以“月盈则冲”以下四句放在篇末。
余冠英先生曾一语中的地指出:“古乐府歌辞,许多是经过隔截拼凑的,方式并无一定,完全为合乐的方便。”*余冠英《乐府歌辞的拼凑与分割》,见余冠英《古代文学杂论》,中华书局,1987年,第157页。我们认为,唐前挽歌诗的演唱与一般的乐府诗无根本差别,故唐前挽歌诗的演唱也应有很多文辞的隔截拼凑。沈(佺期)、宋(之问)之后,随着文人律诗(包括挽歌诗)的成熟,挽歌在歌唱文人所作挽诗时,随意隔截拼接文辞的现象应当明显减少*古体诗本无严格的格律限制,近体诗则不然,隔截拼接文辞很容易导致不合律。,故唐宋以后也有可能存在按照原诗演唱(每句后加“和声”)的,前引《诗人玉屑》郭生唱寒食诗即应是这种情况。
以上我们对挽歌唱的探讨,主要就其“文”(辞)而言,其“乐”究竟如何?相关挽歌的音响资料,笔者仅见两种: 一是前文提及的《请医》中的《蒿里歌》,二是韩国新编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一段挽歌表演*新编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韩国首尔艺术团音乐剧2008年10月26日上演于南京文化艺术中心。。《请医》一折,今日国内江苏省昆剧院、浙江昆剧团等院团尚能演出*《异同曲集》第四集二十二卷下册、《拜月亭全记曲谱》卷三及《幽闺记曲谱》下卷第一部分等皆载其乐谱,因上述乐谱皆用工尺谱,录入不便,故本文未引录。。
从共通点来看,这两处的挽歌唱都是无板眼节奏的徒歌,这一点也可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如清佚名撰《异闻总录》所载某农人为鬼唱挽歌事亦可说明:
方子张,家居秀州魏塘村,其田仆邹大善刀镊。尝有人唤之云:“某家会客,须汝为歔。”邹谢曰:“吾所能只唱挽歌尔,何所用?”曰:“主人正欲闻此曲,当厚相谢。”邹固讶其异,然度不可拒,密携铃铎,置怀袖以行。既至,去所居甚近,念常时无此人家,而屋又窄小,且哀挽非酒席间所宜听,益疑焉。将鼓铎而歌,坐上男女二十余人同词言曰:“吾曹皆习熟其音调,无唐□人相混也。”乃徒歌数阕。皆击节称善,欢饮半酣。……审其处,榛棘蒙盖,盖一古冢耳。*(清) 佚名撰《异闻总録》卷四,清康熙振鹭堂据明商氏稗海本重编补刻本,第26页。
从文献记载来看,挽歌歌唱的伴奏乐器主要是“铎”,即一种借撞击而发音的铃类乐器,许多文献皆可说明此点。如唐姚思亷《梁书》卷五十《谢几卿》传有:“(谢几卿)肆情诞纵,或乘露车历游郊野。既醉,则执铎挽歌,不屑物议。”*(唐) 姚思亷《梁书》卷五十,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第708页。唐萧嵩《大唐开元礼》卷一百三十九《凶礼》“陈器用”有:“铎者,以铜为之,所以节挽者。”又云:“铎,每振,先摇之,摇讫三,振之。”*(唐) 萧嵩《大唐开元礼》卷一百三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页。伯2662号写本《书仪》叙述柩车发引,有:“以帛两匹属轜车两边,以挽郎引之,持翣振铎,唱《薤露》之歌。”*转引自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258页。以铎伴奏唱挽歌的例证甚多,不具引征。《史记》卷五十七《周勃世家》说周勃早年“常为人吹箫给丧事”,唐司马贞《索隐》曰:“《左传》歌虞殡,犹今挽歌类也。歌者,或有箫管。”*(汉)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七,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2065页。司马贞以为挽歌唱伴以箫管,显然有误解。
不是用可以表现音乐旋律的管弦伴奏,而是以简单的打击乐器伴奏,也从另方面说明了挽歌唱为徒歌式的吟唱。
述及挽歌演唱,也许有读者会有兴趣想知道: 假如春秋战国时代即已有挽歌唱,除文献普遍载录的《薤露》、《蒿里》两曲调外,人们歌唱挽歌时是否还使用其他曲调?战国时代的《薤露》、《蒿里》,是否会历两千年之久一直有相对稳定的唱腔或旋律被传唱至后世?换言之,李延年时代的《蒿里》与折子戏《请医》中的《蒿里》是否有继承性?
上述问题,实际都可以归结到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 挽歌唱是否有确定的调高、调式、节奏、节拍以及确定的旋律腔调或唱调?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触及了中国韵文歌唱“文”与“乐”的相互关系问题。按照笔者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笔者认为,(20世纪前未受西洋音乐观念影响的)中国式的歌唱,其首要目的是传辞,故其“乐”从根本上来看是为“文”(文辞、文意)服务的,“文”为主,“乐”为从。中国式的歌唱主要是方言入唱(也有可能尽力用官话或者尽力向官话靠近的方言),方言的字读语音语调对乐音旋律高下有根本性影响(今日各地民歌、地方戏犹然)。从“乐”的角度看,某一唱调一开始可能会有相对稳定的旋律腔调,歌者也可以借用这一相对稳定的旋律腔调去“套”唱文字形式相同或相近的“文”(辞),但由于方言(或者努力“打官腔”的方言)的局限,而方言语音又始终处于变迁之中,更兼古代中国长期缺少较准确可靠的记谱符号和技术,这样即使产生了相对稳定的旋律唱调,这样其稳定性也势必有很大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人去乐亡的现象普遍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说,时间跨度数百年或上千年,《薤露》或《蒿里》能始终保存其原始的旋律腔调,哪怕是部分保存,都是几乎不可能的。
故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说: 虽然从文献记载看,《薤露》和《蒿里》两调的歌唱被历代文献广泛载录,但西汉李延年之歌《薤露》,其唱调肯定不同于西晋之袁山松,也肯定不同于北宋之郭生。历代的挽歌郎可能曾经创造和使用了无数不同旋律腔调的挽歌,这些当然挽歌也有共同的特征——皆为“摧怆之声”,可令听者“歔欷掩泣”——故称“挽歌”。
六、 挽歌的案头化与挽联
自先秦直至近代,挽歌演唱虽一直绵延不绝,但我们也应指出,挽歌(诗)也有日益文学化或案头化的一面。魏晋以前,挽歌诗的写作不为文人关注,但魏晋以后,与中国文人诗歌的日益成熟和精致同步,挽歌诗的文学水平也日渐提高。挽歌诗同其他类诗歌一样,也成为文学品鉴的对象,成为文人学士才学修养的重要表现。而且有许多挽歌诗都是在王公贵人亡故后,文人学士们应旨同时奉献的,这就使人们咀嚼辞藻、品评高下成为可能,也为文人们展现才艺提供了特殊机缘。北齐“八米卢郎”的佳话,已可见时人对卢思道才情的无比艳羡,后代亦然,如北宋陶岳《五代史补》载五代时石文德献挽歌事,云:
石文德,连州人,形质矬陋,好学,尤攻诗。霸国时屡献诗求用,文昭以其寝陋,未曾礼待文德,由是穷悴。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于门下。其后文昭知之,亦兼怒王宅,欲庭辱文德而逐之。居无何,秦国夫人彭氏薨,文昭伤悼,乃命有文学者各撰挽词,文德乃献十余篇。其一联云:“月沉湘浦冷,花谢汉宫秋。”文昭览之大惊,曰:“文德有此作用,吾但以寝陋而轻之,乃不如南宫小儿却能知贤耶?”于是始召文德而愧谢之,未几承制授水部员外郎。*(宋) 陶岳《五代史补》卷三,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刻本,第18页。
又如欧阳修《六一诗话》载宋初名儒李昉(925— 996)为宋太祖赵匡胤(927— 976)进献挽词事云:
李文正公进《永昌陵挽歌辞》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楼三度纳降王。”当时群臣皆进,而公诗最为首出。*(清) 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年,第264页。
由此可见,挽歌诗特殊的写作背景,使得挽歌诗极易为人瞩目,也促使文人学士为其文字用心雕琢,精益求精。像丘灵鞠、石文德辈因献挽诗而获升迁,名利双收,自然也是令时人艳羡之事。
但事物总是相反相成,当文人们为挽歌诗精心雕琢、不断提高挽歌诗的文学水平时,其“乐”(由于主要是由社会底层的职业歌郎承担)则并未相应地不断进步,“文”的艺术水平远远高过“乐”,这必然导致挽歌“文”、“乐”这一对组合关系中愈来愈偏向“文”,乃至最终“文”成为“挽歌”的全部,人们主要关心其文字如何,至于其是否最终被付诸歌唱则无关紧要。由于汉字特有的属性以及中国文人对文字的情有独钟,中国文学在魏晋时代即已相当成熟、精致,故魏晋时挽歌“文”与“乐”这一对组合关系中偏向“文”实际上已经发生,愈至后来则愈为突出。五代以前,文人挽歌诗仍多称“挽歌”或“挽歌诗”、“挽歌辞”,五代以后则多称“挽诗”、“挽辞”或“挽章”,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文”的提升和“乐”(歌)的降低。五代以后,虽然文人挽歌诗的写作仍在持续,但已主要是文学之事。
挽歌诗出于悲悼亡者之意,多“述其行谊”、“美其功伐”,故孝子贤孙或门生弟子将所得之挽诗搜集成册以表其孝义,元明以来亦渐成风尚。元著名文人许有壬(1287—1364)《特进大宗师闲闲吴公挽诗序》云:
至正六年十月七日,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闲闲吴公薨于大都崇真万寿宫承庆堂。中朝士大夫骈呇走吊,莫不哀伤,哀伤之不足,又形诸歌辞,诸弟子裒为卷轴,征序其首,以倡嗣音,以广其哀焉。*(元) 许有壬《至正集》卷三十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207页。
又,明永乐时名臣杨荣(1371—1440)《待诏滕公挽诗序》云:
姑苏滕公用衡,年几七十,承召至京师,仕为翰林待诏,凡五年,无疾而终。朝之士大夫相与赋哀挽之诗,于今又十年,积为巨帙,公之婿凌浩求予言以为序。*(明) 杨荣《文敏集》卷十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7页。
对挽歌诗,从“择其尤悲者,令挽士歌之”,到将其裒集成册、以广流传,显示了挽歌诗的又一变迁,也可以说是挽歌诗日益案头化的必然结果。
挽歌诗日益案头化的另一结果,便是挽联的日益流行。自魏晋时代起,偶对精工的诗句即很受人青睐,挽歌诗亦然,故丘灵鞠挽歌诗句“云横广阶闇,霜深高殿寒”,深得宋孝武帝赏识。五代以来,随着对联写作之风的兴起,挽联写作也应始于此后不久。今人多以北宋人苏颂(字子容)(1020—1101)为韩绛(字康公)(1012—1088)所写“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为现存最早的挽联。梁绍壬(1792—?)《两般秋雨盦随笔》“挽联”条云:
挽联不知起于何时,古但有挽词而已,即或有脍炙二句者,亦其项、腹联耳。(叶梦得)《石林燕语》载:“韩康公得解、过省、殿试,皆第三人。后为相四迁皆在熙宁中。”苏子容挽(辞)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此则的是挽联之体矣。*(清) 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六,清道光振绮堂刻本,第193页。
梁绍壬有关挽联起源的这段话,梁章钜(1775—1849)《楹联丛话》曾全文转录,梁氏于此未加评述,这或即是今人将挽联归于苏颂的文献依据。然笔者颇疑苏颂所撰“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仅为其挽诗中之一联,因此联概述韩绛生平事迹,颇为精工,故为时人传诵。但同为概述亡者生平事迹、功业,如前引李昉挽赵匡胤时所撰“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楼三度纳降王”显然亦为“挽联之体”,且早苏颂百余年。在笔者看来,今日若想对挽联产生之年代做出确定判断,是非常困难的。但无论如何,考虑到文人诗中“联”的相对独立性,由挽诗的“联”进而变为“挽联”,可谓顺理成章之事。
五代以后,当挽歌诗已主要是一种案头文字,而不一定交付歌郎演唱时,其作为文字的功用(“述其行谊”、“美其功伐”)实际上也可基本上由挽联取代。*我们这里说“基本上”,主要是因为挽联还不能完全取代挽诗,挽诗比之挽联有更久长的历史传统,故挽诗的写作比之挽联更显郑重,同时由于挽诗有较长篇幅,可以有数章,故可包括比挽联更丰富的内容。明清以来,对联写作更为风行,这种风气必然对挽联写作有更大的推动。同时,由于挽联常可悬挂于灵堂(近世或用殡仪馆)供参加丧事者的观瞻,故在整个丧事活动中挽联比之挽诗更易为人瞩目。凡此种种,使得挽联的地位,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有与挽诗并驾齐驱之势,甚至最终超越挽诗。这就使得现代的人们,大多知挽联而不知有挽诗,知挽诗而不知挽诗之用、挽诗之变。
小 结
两千多年来,发生在挽歌中的变迁甚多,这些变迁可从以下几方面稍加概括:
从民间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关系而言,挽歌本为流行于民间社会的一种有具体实用功能的仪式,汉武帝以后开始为主流社会所接纳和吸收,最终成为上层社会礼仪制度的一部分,挽歌也成为个人身份等级的标志之一。这一点恰反映了数千年中国传统礼乐文化强大的吸收力和同化力。
从风俗时尚来看,挽歌初起时即作为送终之礼而用于丧事,有其特殊的使用情境和功用,唯“凶”事才用挽歌,但汉末以来即用于“宾婚嘉会”,成为人们娱乐游戏之一种,许多任诞之士更痴迷于挽歌,置流俗非议于不顾。挽歌的职业化也大概发生在此时,降至后来,挽歌歌唱乃成为职业唱家们才情修养的一部分,职业唱家们所作“摧怆之声”,当然是有意为之,不必出于真情实感。
从文学与音乐的关系来看,挽歌的文学化历程也印证了中国各类韵文演进的基本规律: 其初始阶段,“文”与“乐”彼此依存,“乐”的地位相对突出,“乐”在客观效果上推动了“文”的制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学)的日益提高,“乐”的地位则相对日渐降低,乃至无足轻重,导致“文”最终脱离“乐”,案头化的文字几成为全部。故“挽歌”一变为“挽歌诗(辞)”,再变为“挽词”、“挽诗”、“挽章”和“挽联”。从现象上看,古人留给今人难以尽数的挽(歌)诗、挽联,而其乐则几无一存。
2016年,123— 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