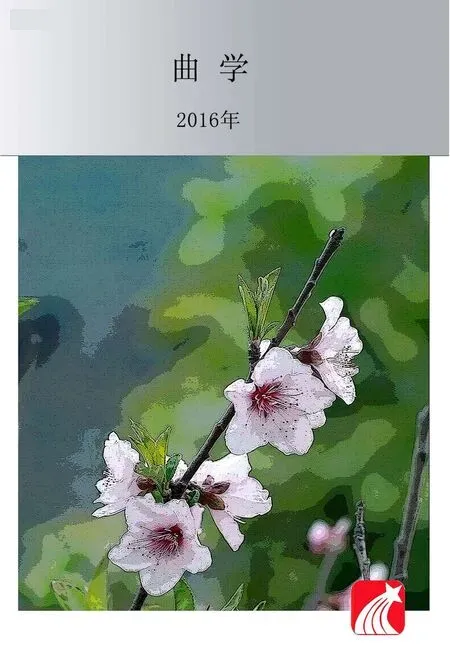论板腔
——兼论戏曲音乐创作
2016-04-03庄永平
庄永平
《曲学》第四卷
论板腔
——兼论戏曲音乐创作
庄永平
“板腔”曲式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音乐领域内容与形式上的最佳结晶之一,也是中国传统音乐最主要的乐曲结构形式之一。“板腔”曲式常被称为“板腔体(制)”,它在中国音乐曲式结构中的形成是比较晚的。在它之前中国传统音乐的曲式,几乎是“曲牌体(制)”的一统天下。然而,正因为形成得较晚,它不仅继承了曲牌体许多优秀的成果,更主要的是突破了曲牌体制于音乐发展上的一定壁垒,因而所体现出的音乐艺术成就更高,更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精髓。可以说中国音乐相比于西洋音乐所具有的特色东西,在板腔体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因此,研究板腔体就是寻找中国传统音乐的特色,总结中国传统音乐的成果,使之在今天接受和借鉴外来音乐方面,不至于失却自己的立足之本。同时,也能寻找与现代音乐相结合的可能与切合点,使之蜕变为一种现代的,富于民族特色的结构形式。
“板”“腔”与“板腔”释义
“板腔”就字义上来分析:“板”字,《辞源》解释是:“片状的木头。后片状物皆称板,如铁板、石板等。”*《辞源》,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542页。《说文解字》中“板”作“版”,这个“片”字旁就是释“板”字为“片状物”的来源。而后改为“木”字旁显然先是引申指的是木板,然后才扩大至其他物质的片状物。“板”字用于音乐是与一种木制乐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乐器就是魏晋以来的“拍板”。《辞源》引《景德传灯录(二七)〈善慧大士〉》:“大士登坐,执拍板唱经,成四十九颂。”*同上,第1244页。“拍板”一词的“拍”字原是动词,“板”字是名词,最早就是指一种击节的动作,即“拍着板”,后来两字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节奏乐器的名词。因此,在“拍板”成为一种乐器名称之前,“拍”字的出现比“板”字要多得多,也早得多,这是因为“拍”字已由动词转为乐曲的一种结构名词了。早在东汉(约公元208年左右)蔡琰《胡笳十八拍》之“拍”,就是一种宽大的拍,大约相当于文章中的“段”或“章”,可称为“段拍”或“章拍”。还有如我国现存记谱年代最早的琴曲《碣石调·幽兰》,全曲四个乐段就称为四拍,到了唐时才缩小到以句为拍。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中对“拍板”作的解释是:“拍板本无谱。明皇遣黄幡绰造谱,乃于纸上画两耳以进。上问其故,对:‘但有耳道,则无失节奏也。’韩文公因为乐句。”*(唐) 段安节《乐府杂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58页。宋张炎《词源》也说:“众部乐中用拍板,名曰齐乐,又曰乐句。”*(宋) 张炎著、蔡桢疏《词源疏证》(下),中国书店,1985年,第14页。以乐句为拍就被称为“句拍”。我们从现留存的《敦煌乐谱》*庄永平《琵琶、古谱、戏曲音乐——庄永平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194—230页。中可以发现,有众多的“囗”符号,而且,每两“囗”之间的谱字数都是相等的,或六个谱字或八个谱字,甚至四谱字不等。还有唐乐流传到日本后产生的乐谱,如《仁智要录》、《三五要录》、《博雅笛谱》*叶栋《唐代古谱译读》,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等中有“百”字(“拍”字的通假字或简笔字),每两“百”之间的谱字数也都是相等的。这就说明那时不仅在实际演奏中是用“拍板”来分割乐句,起到节(制)拍的作用,而且更进一步化为谱面的节拍符号了。当然,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中又说:“鼓,其声坎坎然,其众乐之节奏也。”*(唐) 段安节《乐府杂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第58页。这个节奏显然是指的如今天乐曲的旋律进行,包括小拍(如以四分音符为一拍的单位拍),至于大拍(如一小节中有四拍的4/4拍的小节)就是用“拍板”来分割的。可见,那时它们并不是经常组合在一起指乐曲的节拍形式。唐代“拍”的组词很多,如大曲中的“拍序、序拍、破拍、催拍、促拍、歇拍”以及“拍弹”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那时“拍”就是节拍的最小单位了。因此,即使拍被分解了,也只能称为“破拍”或“曲破”,至于“破”到何种程度,我们从日本传自唐代的《三五要录》等乐谱上,表示[破][急]段的,大致相当于今天的8/4、6/4、4/4拍的都有,4/4拍大概是最小的节拍形式了。看来,它们有的仅是一种速度上的差异而已,“破”与“急”就是其名称。另外,以《乐府杂录》的说法,那时拍板打不打无所谓,旋律(包括节奏)照样可以进行下去,但它作为乐曲的乐句分割也就必须打的。可见,那时的“拍”还很宽大,还没有真正介入到旋律节奏之中去。后来,拍板的“板”的作用才逐渐凸显出来。虽然那时“板”字仅与“拍”字连在一起,但至少为今后“以板代拍”埋下了伏笔。到了宋代基本上也还是保持“拍”或“拍板”的称呼,如宋张炎《词源》中写有“拍眼”一节,大多是言“拍”不言“板”的,有“拍眼、待拍、拍板、应拍、乐拍、按拍、无拍、均拍、前拍、后拍、艳拍、花拍”等。提到“板”的如:“王感化善歌讴。声振林木。系之乐部,为歌板色。后之乐棚前用歌板色二人。”*(宋) 张炎著、蔡桢疏《词源疏证》(下),中国书店,1985年,第14页。所谓“歌板色”就如现在唱京韵大鼓的演员,一边演唱一边自己执板打鼓;“色”者,即今行当角色之分类。宋王灼《碧鸡漫志》中也提到“曲拍”“花拍”等。*(宋) 王灼《碧鸡漫志》,《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第132—133页。可见,用“板”字最早可能与宋元时的说唱形式有关连,但真正大量出现以“板”替代“拍”或“拍板”的,大约要到明代了。首先,是出现了各种“板”的打法,如明魏良辅(约1522—1572)《曲律》中就有“迎头板、彻板、绝板”等名称。其次,出现“鼓板”与“板眼”两词。明魏良辅《曲律》提到“南曲之鼓板”,又讲到:“拍,乃曲之余,全在板眼分明……其有专于磨拟腔调,而不顾板眼;又有专主板眼而不审腔调,二者病则一般。”*(明) 魏良辅《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五),第5—6页。之前,在宋张炎《词源》中称为的“拍眼”,现被“板眼”一词所替代。由于注重拍板的实际操作,大概当“拍”变为乐谱符号,“板”就成为拍板乐器的简名了。而且,拍板乐器本身也由最早的九或六片双手操作,减为三片单手操作了。那么,首次较完整地为昆曲曲谱点上板眼节拍的是明沈璟(1553—1610)的《南曲全谱》。他在蒋孝的《南九宫谱》基础上增订并圈定了板眼。另一方面,魏良辅只是论到“板”而未能论及“眼”。后明王骥德(?—约1623)《曲律》为“板眼”下了确切的定义:“盖凡曲,句有长短,字有多寡,调有紧慢,一视板以为节制,故谓之‘板’‘眼’。”*(明) 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118页。而且,他在推崇沈璟点板眼的做法时,提到了“鼓”与“板”两种乐器的互为作用:“词隐于板眼,一以反古为事。其言谓清唱则板之长短,任意按之,试以鼓、板夹定,则锱铢可辨。”*同上。这样,我国传统音乐最富于特点的板眼节拍形式,不仅在实际操作中,而且于谱式上就此基本肯定了下来。因此,“板”字于传统音乐中的涵义,不仅是“板”(檀板)乐器本身,它还引申为板的打法以及各种节拍形式,等等。这些,当然主要是指声乐歌唱方面,但要做到节拍的定性与定量也不易。不过,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现在人们常常过分强调我国音乐的特点,是所谓的“韵律性节拍”特征,也就是不定性、不定量的节拍形式,这似乎是有些以点概面了。实际上从唐代的《敦煌乐谱》等古谱来看,那时的节拍是基本定性、定量的,而且有时还很严格的。例如,两“囗”之间是八个谱字,如果多于8个谱字,就要运用“火”字将多余谱字合在一个谱字节奏单位之中;如果少于8个谱字就要运用“引”“T”等符号,增加谱字节奏单位使之合于既定的拍数,也就是“拍”是以谱字为“节”的,这可能与唐代近体诗严格的字数、句式格律有关。而所谓的“韵律性节拍”是后来进入词与曲的时代,尤其是在声乐的说唱音乐方面才凸显出来的节拍特征。由于我国历来声乐占了音乐的主导地位,因此,给人以中国音乐节拍特征是不定性、不定量的。其实,今天从整个民族音乐来考察,事实上规整节拍与韵律性节拍都是存在的,只是前者器乐曲中多些,后者声乐曲中多些。因此,我们在指出这些特征的同时,是不应以偏概全的。
那么,关于“腔”字,其涵义则更是广泛了。最早“腔”字就是指人和物体内的空处。*《辞源》,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563页。对于人体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口腔”这一空处,它是人们讲话和歌唱的重要器具,也是使用最为频繁且最为外显的人体空处了。首先,讲话和歌唱的发声源“声带”就在口腔之中,这是口腔排在诸腔之首的最直接原因。其次,口腔中由于有牙、齿、舌、唇、喉等器官,借以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传统发声法上总结出的“五音四呼”,就涉及声母的“牙、齿、舌、唇、喉”五类与韵母的“开口、合口、齐齿、撮口”四类,这些都是歌唱发声最主要的部位与口型。除此之外,起发声共鸣作用的还有鼻窦腔、蝶腔、头腔、胸腔等腔体部位。因此,我国古代用“腔调”一词来指音乐的旋律曲调,确实是十分高明的,也是非常经典的用词。因为毕竟音乐的旋律曲调是从口腔中发出来的(唯鼻音例外,但不能成字)。因此,“腔调”一词不仅强调了发声器官和音乐曲调的种种关系,而且更突出了我国的音乐历史一直是以声乐为主的,声乐的特点也就成为我国民族音乐的主要特点及来源。然而,到了器乐开始发展繁荣起来之后,用“腔调”一词来指音乐的旋律曲调就不很合适了。所以采用“旋律”,即活动(旋)着的各音(律)之意,以及借用词曲的“曲调”(曲的调名),来指乐曲实质性各音高低连接线条的进行,且以“旋律”与“曲调”来互为释义。其实,“旋律”一词是借用于东瀛日本,“曲调”一词则是我国古代词曲名称的重新定义。*庄永平《简论我国音乐的旋律及特征》,《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正由于此,传统上以“腔”字组词的极多,如“声腔、腔调、唱腔、板腔、腔体、腔格、腔句、腔节”等声乐全称与结构方面;“高腔、梆子腔、皮黄腔、西皮腔、二黄腔”等腔系或腔调方面;“嚯腔、豁腔、叠腔、垫腔、带腔、撮腔”等曲调装饰及演唱技巧方面;还有音乐处理方面的“橄榄腔、顿挫腔、喇叭腔”等,甚至引申出“油腔滑调”“荒腔走板”之类的生活用语,可以说在那时凡是涉及旋律曲调进行与演唱、演奏技巧及音乐处理等方面,一切以“腔”字囊括之。另外,还可注意到,20世纪奥地利音乐学家霍恩博斯特尔曾将全世界乐制分为中国、希腊和波斯—阿拉伯三大体系,那么,中国体系就可以用“腔”字来囊括。笔者曾撰文提出以“腔格、音格、拉格”*庄永平《音格·腔格·拉格》,《音乐探索》2001年第4期。与此三种体系相对应,其“格”指的就是音乐上特定的规范,而“腔、音、拉”三字就是指的他们音乐旋律与结构上各自特点的集中表现。
总之,“板腔”一词,顾名思义就是“板”与“腔”的结合。“板”就是指节拍、节奏,“腔”就是指唱腔的旋律曲调。也就是唐时以“鼓”的坎坎然之声,泛指旋律节奏的进行,加上以“拍板”乐器的节拍来操控歌唱与乐队。后来就以一人操作的“檀板”与“鼓”,来具体指挥演唱、演奏的进行。为什么我国传统的演唱、演奏要用“板、鼓”从头至尾打入,而西洋音乐的演唱、演奏“则合自然之度”而不用?其实,这是与我国节拍、节奏概念的生成与结合密切相关的。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我国音乐发展到后来,以“板”与“腔”结合成“板腔”一词,以“板”在前引领“腔”,说明“板腔”体制十分强调节拍、节奏的重要性。这种节拍、节奏与旋律曲调的关系,即所谓“以腔生板、以板节腔”,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腔词关系与发展机制,最终成为我国传统音乐最为成熟的一种曲式结构。
板腔体的起源与板式形成
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称为的板腔体曲式结构,它的起源并不是以“板”为节拍、节奏乐器而来的,之所以称为板腔体是后来当这种曲式结构较为成熟时,用“檀板”来操控指挥演唱与乐队后的称谓。实际上板腔体首先是来自西北的梆子腔,梆子腔是以梆子乐器击节而得名的。梆子与檀板是两件不同的乐器,北方梆子称为北梆子,是由两根长短、粗细不同的檀木棒互击,其发音高脆、坚实,后来才有了用于南方戏曲的“南梆子”,乐器及音色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正是由于梆子腔的兴起,打破了曲牌体于音乐上的一定壁垒,使传统音乐发展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梆子腔”最早起源于明代的“西秦腔”、“甘肃调”或“琴腔”。清吴长元《燕兰小谱》(1785序)载:“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肃调’,名‘西秦腔’。”《金台残泪记》说:“南方人们谓‘甘肃腔’为‘西皮调’。”*转引自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983页。秦腔,据清李调元《剧话》载:“俗传钱氏《缀白裘》外集有‘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蜀谓之‘乱弹’。”*(明) 李调元《剧话》,《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第47页。后来最先演变而成的,也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陕西同州梆子和山西蒲州梆子(今蒲剧),之后随着不断的流布形成了庞大的梆子腔系统,包括陕西同州梆子、秦腔、汉调桄桄;山西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河南梆子(豫剧)、河北梆子、老调梆子;山东梆子、章丘梆子、枣梆;安徽淮北梆子,等等。还有后来在进入了其他腔系中,成为多腔系剧种中的一部分,如“皮黄腔”中的“西皮腔”以及川剧中的“弹戏”、滇剧中的“丝弦腔”,还有浙江绍剧中的“二凡”,等等。由于我国北方语所占的人口与地区比例最大,虽然内部有北方、西北、西南等次方言区之分,但与南方的方言相比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大,所以腔调结构上较为一致,故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庞大而单一的声腔系统(腔系)。那么,对于“梆子腔”的结构而言,它并不是在曲牌体结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仅从唱词方面就可以明显发现,不仅与曲牌体运用的是“曲”的长短句结构不同,它是运用整齐的七、十字上、下句结构;而且这种整齐句体与唐代整齐诗体也是不能同日而言的,这倒不是在具体唱词结构上有多大区别,主要是音乐上节拍、节奏等方面已与唐时大不相同了。正是由于唱词结构的变化,也引起了唱句结构的变化,比较突出的就是曲牌体唱腔是不用过门的,而板腔体唱腔在各腔节乐句之间,插入大小不等的器乐间奏与过门,致使二者的旋律结构就明显的不同了。在乐器运用上,“梆子腔”所用的梆子击节也仅于板位上,眼位一般是不打的,因此常常也无从区分板与眼。例如,所常用的主要板式[流水板]就无眼位可言。后来梆子大概在其他腔系如“皮黄腔”中率先被檀板与鼓替代,很可能是受了昆曲等曲牌体制的影响。因为一方面檀板与鼓听起来比梆子雅致,而且,更主要的是檀板与鼓是既打板位又点眼位,这对唱腔的板眼节拍厘定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以板替代梆子也就为板腔体制立名了。
另一方面,对于板腔体各板式的形成,先从戏曲所表现的情感上看,像昆曲那样明显是突出了它的音乐抒情性。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曲”,经过魏良辅等音乐家的加工,出现了像[赠板]那样极其缓慢而抒情的唱腔。我们今天感到昆曲听起来是那样的优美动听、悠扬雅致,其实就是这种极慢速的[赠板]唱腔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因此,昆曲在达到曲牌体声腔的巅峰之时,它在戏剧(戏曲)三要素即抒情性、叙事性、戏剧性中,后两者明显是先天不足的。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其他快的曲牌及大小唱段的调剂,因而唱腔的叙事能力不强,戏剧性则更是不足。例如,它还没有产生出后来板腔体中的[流水板][快板]等颇具戏剧性效果的板式来。甚至像明王骥德在《曲律》中认为:“今至‘弋阳’‘太平’之滚唱,而谓之[流水板],此又拍板之一大厄也。”*(明) 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119页。我们知道,真正向快的板式方面发展,正是由板腔体制来推动完成的。当然,曲牌体中后来出现了[流水板]的滚唱,确实也是一种对曲牌唱腔体制的突破,其实也是受了板腔体的影响而产生的。但是,很显然这种突破已不可能在成熟曲牌体制的昆曲上进行,而是在“青阳”“石台”“太平”等当时一些新兴崛起的曲牌声腔上开始的。那么,板腔体在戏剧(戏曲)三要素中,显然首先是来源于它的叙事性,这种叙事性实际上与民间说唱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于唱句上它是以上、下句结构,落音通常相差大二度为主的,例如,京剧中主要的[西皮]唱腔,上句落2音、下句落1(或 6音),构成宫调式或羽调式;[二黄]唱腔上句落1音、下句落2(或 5音),构成商调式或徵调式。这种上下大二度音相差的叙事乐句结构,确实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大发明,追其源大概与语言唱词结构上的平仄对应关系有关的。当需要抒情性时可以加大上、下句落音的对比;当需要戏剧性时又可以节奏的变化来驱动。这样,在整个戏剧(戏曲)中它比曲牌体结构要灵活得多,表现力也就更为丰富了。其实,像“梆子腔”开始时都是些[流水板]之类的板式,腔情亦即“繁音激楚、热耳酸心”是也。后来[慢板]等板式的产生,可以想见最早可能是受了昆曲的影响而发展形成的。而且,在“梆子腔”“皮黄腔”等板腔体的[慢板]与[流水板]之间,又衍化出快慢不等的其他板式,加上曲牌体上已有的[散板],以及发展出的一些特殊板式,如[摇板][快板][垛板]等,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成套板眼曲式体系。这种套曲结构而后也就成为我国民族音乐最主要的曲式结构,显然这是板腔体制的一大功劳。至于板眼节拍的厘定上面已有所谈及,其实早在曲牌体的昆曲时代,已有所谓北方多用活板,南方多用死板的说法,虽不免有点过头,但实际上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看来这又是与运用不同的方言联系在一起的。大致北方言婉转即可成腔调,旋律伸缩性较大,因而不易控制板眼节奏,所以被称为“活板”。而南方言声调调值不明显,常要靠旋律来引申其语言字调,因此节拍较易固定,眼位节奏也被逐渐细化,最终形成一定的较为固定的板眼节拍形式,这就是所谓的“死板”。实际上这也说明了固定板眼的节拍,是于南方的昆曲腔调上开始的。但昆曲阶段仅是厘定了慢节奏板式的板眼,至于后来戏曲中整个板式系统的板眼,却是由“梆子腔”及后来的“皮黄腔”等板腔体制,在吸收了曲牌体制板眼基础上,产生出一系列快慢不同的板式才大有建树的。
板腔体各板式的特点与功能
正如上述,板腔体结构的最主要特点,是产生出一系列板式来。“板式”一词原有两种涵义:
1. 下板方式,这在昆曲的曲牌体结构中已经有了,也就是以“板”来指示旋律曲调的节奏。在魏良辅《曲律》中已提到: 字随板出的[迎头板];后半拍出字的[腰板];一句唱腔唱完后下的[底板]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板”看似下得各各不同,但实际上都是下在相对于反拍的正拍位置上的,其功能就在于指示旋律节拍节奏的不同方式而已,它不可能来替代旋律本身的进行。正如今天指挥的打拍那样,通常也是打在正拍上的,仅有时为了突出节奏或其他方面,偶然也打在反拍上。不过,这也说明到了明代,“板”(节拍)至少已经缩小到了能介入一定的具体旋律节奏中去了,这在唐的“句拍”时代是做不到的。另一方面,我国后来的记谱方式,如工尺谱就是以这种板的指示为依据的,因此对于音乐的记录来说,它只能是一种粗略的规范,还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详细记录旋律曲调节奏的要求。
2. 板眼形式,简称板式,这是板腔体结构的一大特征。由于板腔体结构是以一对上、下乐句为基础,以节拍、节奏的变化为主线,同时带动旋律的变化,产生出一系列快慢不等的腔调样式,这就是板式的产生。这种方法的特点: 一是由于其他板式都是由[原板]发展而来,因而从音乐素材等方面来讲是比较统一的。当然,少数腔系也有可能是以比[原板]慢或快的板式为基调的。二是常根据由慢至快渐层发展的节拍、节奏原则加以组合,形成结构较为庞大的套曲,成为板腔体中表现力最为丰富的结构形式。
例如,京剧中[西皮]的[导板][回龙][慢板][原板][二六][流水][垛板][散板]等组成大型的成套唱腔,表现力非常的丰富。一般来说,[原板]与[慢板]的关系,结构上常就是2 ∶1的关系。也就是[原板]采用2/4拍,[慢板]采用4/4拍,后者速度约放慢一倍而已,在此基础上旋律可以进一步加花撑开。[原板]与[快三眼]犹如指挥打整拍与分拍那样,是一种反过来1 ∶2的关系。前者采用2/4拍,后者采用4/4拍,但它们采用同一个速度,其趣味就在于节拍的打法上,表现出不同的抑扬顿挫感觉来。除此之外,[原板]与[二六][流水]等快板式的关系,结构上常就不一定是这样较严格的对应关系了。这是因为唱词的字位节奏关系发生了变化,因此腔调上也有所变化。而[原板]与[垛板]等更是由于字位节奏关系的变化,联系上就不那么直接了,但它们都是一种总体上的紧缩或放大(多叠)。正如上面所述的,从叙事性与戏剧性方面来讲,上、下句结构的叠置就是为了戏剧中的宣叙而形成的,它与西洋歌剧中的宣叙调功能相类似。这种结构我们在说唱音乐中可以大量见到,实际上它就是由历史上的宝赞、变文及唱赚、鼓子词、诸宫调等形式发展而来的。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根据叙事的长短,任意叠置多少对上、下句均可,这种叙事部分常处于唱段头、尾部分外的[平板]结构部分。一般而言,上、下句结构不如昆曲的曲牌体抒情性那样强。因为曲牌体可以换用一个同宫调的曲牌,而板腔体只能在原有腔调基础上发展而有所限制。但是,这显然不是绝对的,前者即使换用曲牌情绪的变化常也是不大的,而板腔体结构由于易于分解与综合,它可以运用拖腔(扩展)与垛句(紧缩,但可叠置)两大利器,来发展变化它的腔调旋律,因而驰骋的余地也就更大了。例如,在上、下句落音上加以变化,就能发展出四句式的起、承、转、合乐段,这就打破了上、下句的落音关系,使通常偏向于叙事性的结构,朝着抒情性方向转化。有时运用长大的拖腔使其情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这在板腔体的[慢板]中常得到集中的体现。至于戏剧性主要表现在较快的板式上,如运用[垛板][快板]或整、散板的交叉等使情绪阵阵上推,产生出强烈的戏剧性效果来。如果说昆曲的曲牌体“水磨腔”结构,使唱词字调与音乐腔调的慢速配合上,达到异乎密切的程度,那么,板腔体结构不仅在[慢板]中吸收了昆曲[赠板]的做法,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且它又开发出[垛板][快板]等快的板式,把汉语单音节的连接速度,推进到了无以复加的快速程度,能造成极大的情绪波澜,使它的表现功能大大超过曲牌体结构,特别是在叙事性与戏剧性方面的能量更大。如果从语言的根本点上讲,只有汉语这种单音节词根占多数的语言,才能产生出如此强烈的、戏剧性的效果。这种现象外国音乐家们有时虽然感到中国戏曲音乐“显得不优美、粗笨、生硬和喧闹的”,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合乎天生禀性的、充满生命活力的音乐的印象”。*〔德〕 费里茨·波泽著,范额伦译《非欧洲诸民族之音乐》,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安徽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音乐与民族》,内部资料,1984年,第98页。外国人认为中国戏曲音乐的诸如缺点,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而它原有的禀性特点则越来越鲜明、突出。
相比西洋语言的多音节结构,轻、重音节似搭配好的互相制约,因而不可能分拆开来表述的。即使是他们现在的“饶舌歌”,也不可能像我们戏曲唱腔中那种极快的板式节奏。它只能加快单位拍内的音数,如两个八分音符转为四个十六分音符那样,即使这样也达不到汉语绕口令的速度。而汉语还能加快单位拍本身,如1/4拍转为分解的1/8拍那样。因此,如果使用汉语而不运用这种节拍形式,这不就放弃了中国最富于戏剧性表现的工具了吗?除了[垛板][快板]之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板腔体结构中还有一个强大的利器就是[摇板]的运用,这种板式也是以汉语单音节词根占多数为基础的,它是一种独一无二且十分奇特的音乐结构,那就是以无板的散唱与有定板节奏的伴奏相结合的一种板式。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奇特的板式?实际上也与汉语的单音节结构有关。因为单音节(字)之间可以灵活地组合在一起,又可以灵活地拖音,这样一来,如在拖音时伴奏又是有衡定节奏的,这就成为了一种看似散拍节奏,又是有定次节奏的组合体,这样,就形成那种内紧(伴奏)外松(唱腔)特点的[摇板],富于强烈的戏剧性效果和独特的表现功能。一旦形成了这种结构,各剧种唱腔上又可以各自加以发挥,形成丰富多彩的形式。如京剧的[摇板]、越剧的[嚣板]、沪剧的[快板慢唱],等等。想必西洋多音节语言是不可能产生出这种奇特板式来的,试想如果用西洋多音节语言来演唱[摇板],这不成了“疙瘩腔”了吗?要么几个音节挤在一块儿,要么一个音节硬拖在哪儿显然是不行的。因此,音乐上很多有特色的东西都是语言所使然的,不仅不容易改变它而且更应该很好地利用它发扬它,这才是民族特色的所在。
板腔体的创腔手法与特征
板腔体是我国传统音乐最高级的曲式结构,因而它也集中了我国传统音乐创腔手法最精髓的部分。虽然我国戏曲创作特征之一,就是其“创作是在本剧种戏曲腔调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民族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第215页。,然而,板腔体与曲牌体创作不同的是,曲牌体基本上是一种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倚声填词”的创腔方式,它注重的是文学唱词的方面,而这种局面从板腔体开始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正如我们今天不会认为创作设计京剧唱腔是一种“倚声填词”,说明板腔体于唱腔音乐方面已有了更大的创作回旋余地,认识到这一点是颇为重要的。这也是我们说板腔体制在现今的形势下,还可以被充分利用和发展的原因所在。下面将板腔体的创作手法简述如下:
1. 节拍、节奏的变化,也就是上面已经分析到的各种板式的产生,其特点是以二之幂的进行来划分的。这在运用板腔体的各个腔系剧种发展上是并不平衡的,但总体上已经发展得较为俱全了。例如,相当于今天1/4拍的有板无眼;2/4拍的一板一眼;4/4拍的一板三眼及散、摇板等。其间,值得注意的是,1/4拍的有板无眼节拍,是比较能体现与语言紧密关系的拍式。因为汉语的单音节(字)本身就是一个单位,因此形成有板无眼的1/4拍是极其自然的。比字再小的单位势必割裂了字是行不通的,因此,即使运用比1/4拍小而快的1/8拍,它必然又会以1/8拍为字单位了,这是典型的以一元起步的节拍形式。在我国民族音乐中凡是节拍上有翻拍之感时,均可用有板无眼的1/4拍来解决。正如杨荫浏所举的锣鼓曲《下西风》*杨荫浏《语言音乐学初探》,载《语言与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第72页。的例子,来说明用1/4拍的曲调也不全是强拍的,它有与小节节拍轻重规律相符合的地方,也有不相符合的地方。而西洋音乐中由于语言的多音节关系,常是一轻一重或一重一轻,即称为“抑扬格”或“扬抑格”的组合,因而音乐上常就是以二元节拍起步的。他们的一拍子运用是极少的,如果出现翻板现象,那肯定就是节拍本身没有搞好平衡。其实,西洋音乐也有类似我们板式的东西,它们的板式是以速度来表示的,例如,每分钟多少拍称为[慢板],多少拍称为[行板]等;如果还不够清楚时只能加上文字的表达,如“不太快的快板”之类。只是我国的板式除了速度上的一些区分之外,更着重强调旋律发展上的同一性。另外,为什么传统板腔体没有产生出3/4拍的一板二眼板式?这也是因为汉语在组词上,从《诗经》开始就是以成双的二字词组、四字词组为多。三字词组是不稳定的,中间一字靠前靠后均是可以的。更重要的是,三字词组各字往往没有轻重的区别,因此,不很适应3/4拍这样的拍式。相反,西洋语言的轻重音组合特别适应3/4拍,因为3/4拍本身是强、弱、次弱的轻重节奏特点,与西洋语言的轻重特点甚为吻合。正由于此,他们一度认为三拍子是完全的拍子,而二拍子或四拍子倒是不完全的拍子,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当然,现在只要唱词提供一定的条件,完全可以开发出这种一板二眼板式,但要特别注意中西语言上的这种异同关系。
2. 旋律变奏手法的运用。在曲牌体上较多运用的是变形手法,在板腔体结构上已有所突破。现代音乐上“变形”与“变奏”是有所区别的。〔苏〕 玛采尔在《论旋律》中讲到:“变形大多被用在悠长的抒情歌曲中,允许旋律的动机可以较自由的变化,特别是音和音调的节拍移动和动机一般长度的改变,等等。”“变奏较常出现在快速歌曲、民间舞曲和器乐曲的旋律中,变奏在节拍的重心上不改变动机基本要素的相互关系。”*〔苏〕玛采尔著、孙静云译《论旋律》,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第184页。由于我国音乐多用五声或七声音阶,有时就不太可能运用较严格的音程模进变奏关系,因而只能采用不很严格的变形手法。现代的模进、分裂、倒转等手法就常需要音阶的细分如十二声音阶,在传统五声或七声音阶上运用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因此,所谓变形者多用于声乐曲,如上述所谓的悠长歌曲;变奏者多用于器乐曲,器乐旋律不受唱字的牵连变化可以自由得多。因此,曲牌体唱腔多用变形手法是与它们的腔词关系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虽然在板腔体中还是运用着大量的变形手法,那就是“依字行腔”原则所带来的。但是,它已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而有所突破,尤其是它有着“拖腔”这一利器,运用变奏手法就更为自由了。因为拖腔旋律大都脱离了与唱字的关系,具有纯器乐般的音符连接。当现今在进入更高级的创腔阶段,在处理腔词关系上出现运用诸如“特性主题音调”等手法,就是把变形与变奏二者结合起来,既可用于“拖腔”的纯音调的部分,也可巧妙地用于腔词关系密切的腔格部分上。总之,可以说“变形”与“变奏”也不是绝对的,只要处理得恰当任何变化发展都是可以运用的。
3. 各行当唱腔的形成,当然与旋律曲调的发展有关的。从曲牌体最为成熟的昆曲唱腔来看,虽然已有行当唱腔的一定区别,但还没有解决好男女声的音域、音区问题。例如,唱腔上经常出现八度的翻唱,也就是应该下行落音的,但由于音区太低只能将此音翻高八度来唱,这就造成了整个旋律线的跳动与断裂,令人听来就很不舒服。这是因为男女声的音域、音区大致相差四五度,男女演唱同一曲牌必然会产生那种男高攀、女不就,或女高攀、男不就的情况。然而,在比较成熟的板腔体如京剧唱腔中,就根据五度或四度的旋律移位法,形成同一宫调上的“同调异腔”解决了这一难题。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在男女声各自分唱的基础上,给予人物音乐形象上的特定性格等,形成各行当的唱腔,这就更具有当今戏曲音乐作曲设计的意义。从这一点上讲,行当唱腔在音域、音区运用上,具有类似西洋男女分声部演唱的特征。因为像青衣用小嗓,老旦用大嗓演唱,说明有一定分声部的因素。不过,这还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洋的女高音与女中音等的划分。因为行当只是一种戏剧角色上的划分,并不是演唱曲调包括音域、音区上的划分,女高音与女中音之类才是从音域、音区出发来划分的。当然,行当划分似乎也有比西洋声部划分有所优越的一面,例如,青衣与老旦或老生与净的区分,特别是演唱方法上的不同,对角色的创造是十分有利的。
4. 调性、调式的进一步发挥运用,这是音乐上有力的表现手段之一。首先,各种调式变化及暂转调等手法的运用,是旋律曲调充分扩展的标志之一。例如,“梆子腔”系统中早就有了旋律上“欢、苦”音的运用,由于改变了调式的结构,从而形成调式色彩的变化。还有后来“皮黄腔”大量的暂转调与双重调式性的运用,如以“变宫为角”“去工添凡”“以变为宫”等造成调式色彩的变化,给人以一定的音乐新鲜感。其次,在调性、调式变化的基础上,创造出反调唱腔来,这确实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是板腔体旋律结构发展的又一功绩。
在曲牌体唱腔上常只能集合同一宫调的曲牌,偶有所谓的“犯调”运用,但总体上它还没有能意识到反调及其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音乐发展动力,而且曲牌的旋律结构本身常也不能提供这种调式变化的可能性。而板腔体上一旦反调唱腔成立以后,它又可以拓展形成各种板式,从而大大加强了唱腔的表现力。例如,京剧的[反二黄],越剧的[弦下调]等等,使剧种的腔调更为丰富。一般而言,“梆子腔”系统中就很少运用反调唱腔,这是因为它本身唱腔上运用“欢、苦”音的调式对比,具有综合调式性七声音阶的变化,这就不太适合反调的调性对比运用。相反,在“皮黄腔”等板腔体唱腔上,既可以运用旋律中的“欢、苦”音的调式对比,又可以采用幅度更大的调式对比手法,以致产生出反调唱腔来。而且,反调唱腔不仅是拓宽了旋律的发展,更是造就了音乐性格上的一种变化。如果说西洋声乐上的音乐性格,常是另起炉灶作曲而成的话,中国传统声腔上采用的就是类似反调唱腔的手法,其特点就是音乐素材上较为统一,同时常形成一种特殊的旋律情感色彩。
5. 板腔体的具体创作手法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式:
(1) 加帽,句首的扩充,常用于句首第一词组。主要来自“句前衬字”,这在曲牌体中已常运用。从性格上讲,有偏于叙述性与偏于抒情性两类。从结构上讲,有单、复式之别。
(2) 插腰,唱腔句中扩充手法之一。主要也是由唱词的“句中衬字”引起的。从性格上讲,也有偏于叙述性与偏于抒情性两类。
(3) 加垛,泛指在段式或句式内加(夹)用“垛句”形式。常由唱词的“垛句”直接引起,用于唱腔句式之前、中部,加用由若干规整性的乐型或乐逗排比构成。有句前加垛、句中加垛形式;根据落音有单、复垛等结构。
(4) 搭尾,唱腔句末扩充手法之一。主要功能是补充基本句式叙述的不足,增强表情分量,加强句式结束的圆满与稳定。有偏于叙述性与偏于抒情性两类;有单、复式之分。
(5) 加腔,加用“拖腔”的简称。在板腔体中加腔常以句末加用无词(字)乐汇的“拖腔”著称,其表情的功能非常突出。
(6) 伸腔,即伸长唱腔基本句式的全部或局部的幅度,唱腔句式扩充手法之一。也就是扩大有词乐汇的节奏时值,常仅是拉长音的幅度,并不具有旋律高低的变化。
(7) 缩腔,即缩短唱腔基本句式的全部或局部的幅度,唱腔句式紧缩手法之一。也就是缩短有词乐汇的节奏时值,常仅是压缩音的幅度,并不具有旋律高低的变化。
(8) 减腔,指裁减唱腔基本句式的某一部分,唱腔句式减缩变化手法之一。即把基本句式局部(包括其腔格旋律)裁减掉。
(9) 综合运用上述变化手法。*于会泳《腔词关系研究》(任珂、陈应时、沈庭康编辑、校对),据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系1963年油印教材翻印,第201—260页。
板腔体的推陈出新与现实意义
板腔体作为我国传统音乐的最佳曲式,是我国传统音乐精华的积淀,也是我国传统曲式链上最终端与最重要的一环。因此,直到现在还是有着它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人类有很多本质性的东西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存在着很大凝固性的,时代的变迁不可能促使它们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例如,语言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像汉藏语系单音节特点可以说自古以来没有多大变化,因此,仍然维系着它与音乐方面的特定关系。像西洋印欧语系多音节语言的情况也是同样。正如早在一千五六百年之前,人们就发现那时天竺(印度)的梵音(属印欧语系),就“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即表音文字)、“梵音重复,汉语单奇”*(南朝梁) 慧皎《高僧传》,引自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第159页注1。,那么,这种现象可以说直到现在仍无多大改变。我们仍可以发现今天的汉语与英语互译,显然是英语长而汉语短。在古代由于运用文言文,这种现象想必就更为突出了。因此,只要现在人们仍然使用着各自的语言,历史上那种对声腔音乐的种种影响都还是存在着的。板腔体制在今天仍然具有它强大生命力的深层原因,就应该归功于根本上由汉语所带来的影响。但是,问题是涉及音乐腔调具体的曲式结构等方面,它们则是在不断演变进化着的。我们只要看看传统曲式链上两大壁垒的曲牌体与板腔体结构,就可以非常明确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来。例如,曲牌体主要是直接受词、曲结构形式的影响,其音乐唱腔曲式就十分偏向和依赖于文学唱词结构。这种结构正如诸文体及自身之间的区分那样,你若是要改动一些原有的规律,那它的结构也就发生了动摇。例如,《蝶恋花》词,它的格式是双调、六十字;前后段各五句、四仄韵。如果取消了哪怕上述四个条件中的一个,它就不能成为《蝶恋花》词了。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各词调之间,它就是以这些条件作为区分你我的,如果抹杀了这些条件,它们也就类同了。当然,实际上也可以有些小的变动,但大的变动那时就称为“又一体”,也就是已不同于原来的体式,产生出又一种新的体式了。这种新的体式要么或许与其他词调多少有些类同,要么就成为一种新的形式。但是,由于新形式常容易模糊与原有词调的界线,而且往往也不一定成熟。因此,声腔音乐发展到曲牌体结构,它已有了较严格的自身条件,如果你变动了它的立足之本,就很难说这是[山坡羊]那是[风入松]了。其次,正由于曲牌体结构的特殊性,现代音乐发展的很多手法,就很难运用到它的结构上去,这样,也就谈不上进一步来推动它的发展了。例如,从句式上看,词、曲音乐因受文学上句子押韵的影响,多用“换头”的变化手法。因为二者结尾已经有了相对的约束(押韵、落音),只能变化句的前部与中部了,这种体式也深深影响了器乐曲的结构。我们只要听听《阳关三叠》、《梅花三弄》等古琴曲的旋律,大都具有这种“换头”结构的特点。还有如围绕中心音旋转的手法,像《夜深沉》等乐曲大都出现由不同旋律线进入相同的落音,实际上也是一种“换头”手法的运用。后来词曲音乐逐渐过渡到板腔体时代,音乐上“换尾”结构才多了起来,由此,我们现在可以较明显地来区分这两种结构,也可来大致判断乐曲产生的时代。板腔体上、下句大二度的不同落音,既是为了唱词宣叙的需要,也是出于唱腔音乐上发展的需要。因为乐句、乐段的尾音不同,落音上就有了对比,以致造成调式等更大的变化,这是音乐腔调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中国历来的诗、词、曲文体,是只讲究字调而不甚讲究句的语调的。因此,造成昆曲等曲牌体上的字调旋律设计得非常缜密,各种腔格的腔、词表达几乎达到了异常紧密的程度。相反,对于句的语调因整体结构较涣散,句子的跨度又过于长大,几乎就体现不出各种语调的区别来。实际上在腔词关系的各要素中,乐句长短的不规则和其对应的腔调,与音乐发展手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和现代音乐发展手法运用与否的矛盾也最大。可以说曲牌体结构是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要在曲牌体结构上改革发展,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除非造就一种新的不伦不类的结构形式,但人们就不认为这是某某曲牌,那或许也就另当别论了。历史上昆曲作为曲牌体结构的典范,在取得辉煌成功后的几百年来,总体上这种“雅部”腔调却一直是呈式微趋势的。从大的方面讲,其中自然有艺术盛衰的规律和原因在内。然而,音乐曲式结构上的羁绊看来是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否则就很难理解它会被板腔体结构的“花部”腔调所取代的事实。虽然后来人们一直对曲牌体改革发展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但似乎收效甚微。现代以来这种改革尝试也作过不少,即使像20世纪50年代《十五贯》的排演,被誉为“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但也仅是较多从剧情、表演等方面而言的,至于体现戏曲特征及成功与否的唱腔音乐方面,与传统的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如唱功戏等),戏曲改革的根本乃在于音乐上。正如西洋的歌剧成功与否,主要不仅是剧本、表演、舞蹈、舞美等方面,而更在于音乐创作与表演(唱和奏)的方面。从这一点上看,西洋把中国的戏曲看作是犹如他们的歌剧,确实是有同一的地方,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因此,曲牌体制作为一种历史积淀主要是传承保存下去,给后人留下一种参考的结构样式,至于板腔体制应该可以在传承的基础上,做到与时俱进、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那么,为什么说板腔体制可以做到与时俱进呢?这应该首先还是从它的结构特点上来谈。可以说我国戏曲声腔发展到以板腔体制为主,说明事实上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现了曲牌体结构上的极大弊端。事实上我国的文学艺术,一方面文学的诗、词、曲(元曲、南北曲)发展到后来,逐渐趋向于散文体了,如散文小说的出现与繁荣就是最好的证明。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已经在不断地打破曲牌体森严的格律规范,到了现代随着提倡白话文,曲牌体的整个结构也就被边缘化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在腔调上随着板腔体制的崛起,也说明了在传统声腔中的腔、词关系,开始由历史上以腔词一方为主,转到以腔调一方为主的局面。虽然,真正打破这种局面的是近代学堂乐歌的兴起和西洋音乐等一系列形式的引进。但是,从曲牌体与板腔体结构的异同,即可发现这种局面的打破,首先是来自传统声腔的内部,是传统音乐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声腔中腔词关系开始发生逆转的契机,其次才是对外借鉴所起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说板腔体制不仅汇聚了传统音乐的很多精华,是现今体现我国民族特色的主要方面,而且,它也具有与现代音乐创作手法接轨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板腔体基本整齐对称的乐句结构,对于音乐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现代音乐的本质是趋向于乐句的整齐对称;结构的便于分解与综合,这样有利于运用各种模进等旋律发展手法。就是像西洋音乐发展到后来,也是放弃了以前那些不整齐的结构而归结为所谓的“四方形结构”*〔苏〕 玛采尔著、孙静云译《论旋律》,第199—201页。,就很能说明问题。曲牌体之所以式微就是因为它是长短句式,特别是它的偶数唱句常常拉散了结构,这对音乐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历史上如词调中慢词的产生,可以说就是因为偶数句的节律所导致的结果。而板腔体的上、下句乐段结构,一是唱词相对集中,如七字句是4(2+2)+3的形式;十字句是3+3+4(2+2)的形式。虽然它对唱句语调的体现仍是比较薄弱的,但相比曲牌体上几乎涣散和平均排比的唱词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二是在各词逗间插入大小不一的过门,这对调剂音乐是有很大功能的,而曲牌体唱腔是不用过门的。沈知白认为:“过门是中国音乐中的特点,这特点是中国文字的特性和歌曲的结构造成的;研究民间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的人,都应该重视这一点而作分析的研究。西洋音乐有和弦终止法,所以不必用类似中国音乐的过门来划分乐句的起讫。”*沈知白《中国音乐、诗歌与和声》,姜椿芳、赵佳梓主编《沈知白音乐论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4年,第71—72页。事实上中国文字的特性和歌曲的结构,正是板腔体制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其中“中国文字的特性”带有文学艺术根底的性质,板腔结构则是这种性质的部分反映。说是部分反映说明它还可以有更多的反映,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开拓创造。另外,板腔体中还可以运用拖腔及垛板等形式,造成乐句结构上长短方面等更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仍是反映出文字的单音节结构在组合上的极大灵活性,反映在腔调上就是沈氏认为的“加的节奏”,它与西洋的“倍的节奏”有着较大区别。*沈知白《节奏的基本原则及类别》,同上,第116页。因此,如何来平衡这两者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事实上这两种节奏以致引申到结构方面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很多传统唱腔都经过“点板眼”的匡正过程,其实也就包含有二者合一的可能性,也就是所谓“强弱”与“尺寸”(长短)尽可能的同一。总之,板腔体结构变化的可塑性还是很强的,只是以往我们对它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像沈知白那样有卓识远见的音乐理论家还太少。当然,传统的板腔体制还有很多不适应现代音乐发展的方面,例如,有过于程式化的倾向;乐句规则与不规则的调剂平衡;[散板]与[摇板]运用的过于“水化”(俗语的“水”就是运用上太随意、太随便之意);[垛板]的运用还可以进一步增加它与其他板式的对比性,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努力加以改进与发挥的地方。因此,如何充分发挥板腔体制的优越性,又大力借鉴现代音乐创作的诸元素,不仅对传统戏曲改革,而且对创立中国式的歌剧,均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现代京剧音乐创作给我们的启示
对于戏曲的改革与新歌剧的创作,实际上也已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了。近代以来,所谓的“旧戏改造”也曾经轰轰烈烈过,但那时大都是一些能人志士的义举,很少有总盘全局上的考虑。当然,艺术的改进也不必来总盘考虑,“百花齐放”才是成功之路。问题是限于那时艺术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在其他一些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等还不能提供较为成熟的条件下,真正的戏曲改革本身几乎是谈不上的。至于歌剧的创作则更是刚刚起步,能谈得上经验总结的东西更是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戏改造才真正走上了一条较为踏实之路。但是,又由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一些干扰,其间反反复复充满着艰辛与颠簸。首先,音乐对于戏曲的功用方面,长期以来是认识不足的。外国人认为中国的戏曲就如他们的歌剧,那歌剧就应该以音乐创作及唱、奏表演为主的,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旧戏中的理念。因此,现在仍有必要来再认识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不少提倡剧本决定制,导演主导制、名演员支撑制,等等。这些当然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但对戏曲音乐方面仍有着莫大的忽视。例如,像理论上论及诸如度曲四声字音时,没有同时结合旋律曲调来谈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也不可能把问题讲清楚;还有像宫调的问题,必须结合乐器、乐谱才能具有说服力,等等。自然,其间也有传统的音乐记谱、传统音乐创作方式等方面明显不足的原因,但正由于此,现今就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使得现代京剧的音乐创作有了一定的发展机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方面是脱颖而出的、杰出的音乐创作人才的出现,这不是说能出现就能出现的,它本身就有着很大的政治、文化等方面集聚合力的原因,也是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个别音乐主创人员政治地位的上升,在整个戏曲创作中占有主要地位,这就无形中使得戏曲创作出现重视以音乐为主导的局面,这恰恰又是符合现代戏曲及其音乐创作规律的,也为历来外国歌剧的成功创作所证实。问题是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认真地加以总结,不管什么原因这种总结对于整个戏曲创作上的得失乃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说是我们避免重蹈戏曲改革反反复复走老路的覆辙的有效途径。跳过这种经验的总结,来奢谈今天的创作及作品,往往是不着边际、不得要领,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来的。再者,从技术层面上讲,戏曲音乐创作的成功经验,并不局限于现代戏本身,它同样可以用于新编传统戏等创作。也就是说,创作手法的创新等也仅是一种技术手段,虽与内容有一定的联系,但技术就是技术,古今中外作品内容均是可以运用的。
除此之外,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现代京剧的创作成功又开辟了中国歌剧创作的一条新路。歌剧这种形式是外来的,从引进到中国来之后,也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然而,在创作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理念: 一种是几乎全盘接受西洋歌剧的形式,从旋律到曲式等各个方面都按照西洋的格式办事,仅语言是使用汉语而已。这些歌剧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很难入乡随俗,很难被中国人所接受。因为声乐作品与器乐作品不同,它必须更深入地适应中国人的生活习性、审美观念和欣赏习惯。直到今天还有人兴致勃勃地想创作出成功的准西洋歌剧的作品来,其初衷是好的、富于理想的,但往往资金耗费巨大,没有演出几场就刀枪入库了。就是因为这些作品常常洋味十足,不仅受众面极小,而且在观众中几乎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实际上以中国观众欣赏角度来看,西洋歌剧的抒情性、叙事性、戏剧性三者,在运用上常也有割裂之嫌。要么咏叹调,要么宣叙调,戏剧性效果(主要是节奏方面)有时也不够强烈。而且,把它们连成一片好像还是比较困难的(西洋歌剧中基本没有语言对白),但这是他们歌剧艺术创作的观念与欣赏习惯,无可非议。问题是他们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在我们来看则未必,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中国戏曲那一套,尤其是戏曲音乐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常常会在声乐创作与观赏中顽强地表现出来。
另一种就是仿照西洋歌剧的模式,打造出民族化的歌剧来,从《白毛女》到《洪湖赤卫队》、《江姐》等,也已走过了几十年的创作历程了。这种理念的立足点就是,在创作上大力吸收中国戏曲有特色的成分,来打造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歌剧,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为,虽然歌剧形式是外来的,但内容是中国的,不管怎样形式多少是要为内容服务的。而且,你的观赏对象是中国人,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如何为中国人所欣赏、所接受的问题。虽然这种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但也应该是慢慢地、自然地、循序渐进地变,如果突然来一个大转弯,那就必然要翻车。问题是能否可以另辟蹊径,既完善我国的戏曲,又消化外来歌剧的形式,把二者统一起来呢?我们从现代京剧改革的成功,可以看出另一条走向中国歌剧的成功之路,那就是通过戏曲改革,突破原有的戏曲音乐形式,实际上不就成为一种新颖的中国歌剧形式?可以说民族歌剧与现代京剧的创作发展,必将成为一种殊途同归的艺术之路,事实上它们二者均为中国人所喜爱,如果发展下去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崭新的声腔形式,既是中国现代戏曲,又是中国的歌剧,具有更强烈的现代气息和鲜明的民族风格特点。我们从以前走过的道路,可以发现现代京剧的一些唱腔比起歌曲化的中国歌剧腔调,不仅具有表面上的那种优美、顺畅,而且更具有一种民族音乐的内在张力,因而听起来更有劲,也更耐听;更熟悉,又更有新意。其实,这就是民族板腔体制的旋律结构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对于戏曲音乐改造和中国歌剧的创作,板腔体制仍具有极大的潜力。这种潜力既集中了这种结构所代表的中国音乐特色元素,又在于它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与现代音乐接轨的可能性。总之,现代京剧及其音乐对我们的启示,具体地来说是多方面的,这里也不可能一一来加以分析,只是简要地加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 选择京剧作为戏曲及其音乐改革的突破口是十分明智的。不仅因为京剧本身的艺术成就在我国戏曲中是最高的,而且从使用语言上讲受众面也是最大的。其次,传统京剧的语言用所谓的“中州韵”和“湖广音”,但之所以成为京剧,除了运用“京音”的行当之外,即使是老生、青衣等这些行当的念唱,从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京音”的成分。也就是说实际上可视为是在京音基础上,扩大“阴、阳”声调值的对比,“上、去”两声作各种变化插穿。*庄永平《京剧中州韵辩正及声调研究》,上海艺术研究所《戏曲音乐资料汇编》,1986年第3期,收入《琵琶·古谱·戏曲音乐研究——庄永平音乐论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390页。问题是虽然传统的这种用韵确实能加强戏剧(戏曲)语言的音乐性特征,但毕竟与现代社会有了一定的距离,正如“中州韵”形成本身与现在的用韵已产生距离一样。因此,“京剧完全可以改用普通话的声调系统,而不会失掉或破坏其原有风格基调。这里因为: (1) 其阴平和阳平字与普通话的调值本来就很吻合。(2) 上声可以用上趋腔格,去声可以用下趋腔格,因此与普通话的调值也能吻合”*于会泳《腔词关系研究》,第33—34页。。这就是选择京剧作为改革戏曲及其音乐,与开创中国歌剧新路所具有的优越性。因为歌剧之用国语(普通话)与京剧改用京音(亦可理解为普通话),可以说就是殊途同归的,为新的声腔音乐创作奠定了基础。
2. 把传统的板腔体制不断推向前进。这里涉及很多方面,只能涉猎一二。例如,创造新的板式这是最主要的成就之一。例如,《海港》中的[排板][吟板][宽板]等,像[吟板]的清唱样式,在其他的剧种板腔体中早已存在,特别是南方的声腔如越剧、沪剧中已有。但是,作曲家之所以称为[吟板],更着眼于各板式及演唱方式上的对比。《海港》的“忠于人民忠于党”唱段中,[吟板]唱句就是放在前后处于强大动力的[摇板]之中,板式对比极为强烈,极大地提升了[吟板]唱句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把传统的[摇板]赋予如此强烈的情感,这是任何传统唱腔及民族歌剧中所没有的。这种只有汉藏语系才有的节奏形式,才真正体现出我国民族音乐的特色。因此,[摇板]的有定节奏与[吟板]的散唱,强烈的节奏紧松对比,富于情感的旋律沁人肺腑,把主人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情感阐发得淋漓尽致。试想,在西洋歌剧中有如此戏剧性效果强烈的唱段吗?有如此能打动中国人心的唱段吗?另外,像“细读了全会公报”的[宽板]唱段,可以说就是一种全新的板式,其出新的程度相当高,完全可以认为是一种新颖的歌剧唱段。但是,由于有了京剧音乐的底子,这种歌剧唱段就更富于民族化、现代化了。除此以外,引进西洋歌剧的“特性主题音调”,结合唱腔旋律的出新,这是借鉴西洋歌剧的成功做法。还有对原有行当唱腔的突破,结合对新的声腔音域、音区的划分,吸收和创造新的腔调,以及对调式对比的充分扩张,等等,*庄永平《于会泳的京剧音乐创作》,《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都不仅仅是对传统京剧唱腔的革新,也可看作是开创中国歌剧的一条新路。
3. 对传统京剧乐队的革新也是极其重要的。我国传统戏曲乐队虽然有简练多用、以少胜多的特点,但是,这只是传统场面用法的最低要求,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今天戏曲音乐的需求了。像传统京剧乐队中偏向于武场乐器,有过于喧嚣之嫌。这是历史上散乐、百戏中遗留下的,实际上在整个舞台音乐中,它主要并不是来合作音乐,增加音乐表现力的,它是为了配合念白、动作与舞蹈的,似乎就这样硬是闯进了音乐的领域。因此,如是要真正成为音乐的一部分,要进行精心的设计才行。沈知白认为:“旧戏中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用大锣大鼓时,丝竹就停奏,而用丝竹时,锣鼓也停奏。我以为锣鼓、丝竹同时并用是值得提倡的。”*沈知白《怎样改革旧戏的音乐》,姜椿芳、赵佳梓主编《沈知白音乐论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4年,第48页。那现在《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很多现代京剧中已基本上做到了同时并用,且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效果。相信外国人听了不会有以前那种“不优美,粗笨,生硬和喧闹的”印象,而是犹如他们交响乐队中金鼓齐鸣式的乐队全奏音响。现代京剧中采用中西混合乐队,不仅富于中国器乐的音色特点,而且,增加了乐队的厚度,丰富了织体,极大地提升了乐队的综合表现力,这是现代京剧音乐非常成功的一方面。像《智取威虎山》第五场“打虎上山”的前奏;《海港》第四场的前奏,是如此打动观众的心弦,完全可以与西洋歌剧的前奏曲相媲美。*庄永平《论现代京剧中西混合乐队的组建与功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结 语
综上所述,板腔体制是继我国传统声腔音乐曲牌体制后,产生的又一最佳的乐曲结构形式。板腔体制是以节拍、节奏的发展变化为纬线,以旋律曲调的变化发展为经线,编织而成的一种充满活力与发展生机的曲式结构。这种结构体制就是以“板”的样式,简称“板式”为标志来体现的。也就是“以腔生板,以板节腔”成为它不断发展的既定原则,以板式变化来带动旋律曲调上的一系列变化。因此,板式囊括了我国几乎所有的传统音乐精华,如节拍、节奏上二之幂的发展进程;旋律上的变形与变奏;曲式结构上曲牌与板腔体制的变化;腔词关系的对应与变式,等等。可以说正是由于板腔体的这些特征,即使是在今天,只要还是使用汉语歌唱,那传统音乐历史上产生与总结出的原则就不会过时。因为这种优势就是在于与语言密切相关的、具有最本质的民族音乐特征和特别适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要说变化,也仅在于本质基础上的腔词对应及其形式等方面。正是由于板腔体结构上的优势,在现代音乐的氛围下,它还是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在发展中很多东西是要经过再平衡的,例如,“加的节奏”与“倍的节奏”的关系;单旋律与复调的关系;旋律发展的变形与变奏关系,等等,常常会产生出矛盾来,这就要看在处理上如何来平衡了。总之,如果说要创作出我国新型的民族歌剧甚至音乐剧等,板腔体制的很多东西,如长大套曲(相对于歌曲的短小只曲)等方面,还是具有相当优势的。可以这么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能超过板腔体成套唱腔表现力的歌曲长套体制。相信,无论是戏曲音乐改革还是民族歌剧创作,当它们殊途同归时,很可能就产生出一种既符合中华民族欣赏习惯,又富于时代特征的新戏剧来。
2016年,1— 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