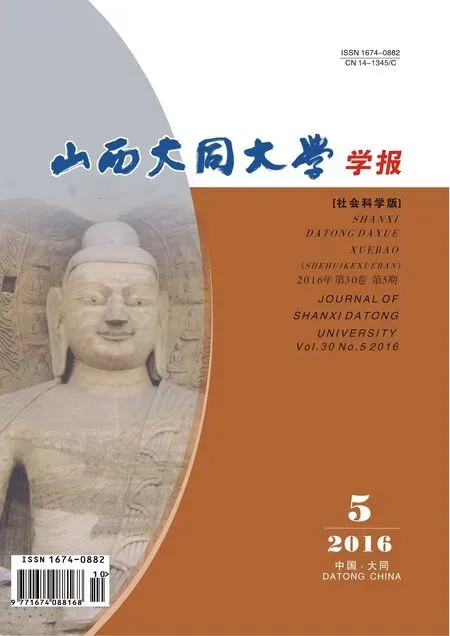严复翻译“三原则”评价中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之维
——兼驳“信、达、雅”抄袭说
2016-04-03师杰
师杰
(山西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大同037009)
严复翻译“三原则”评价中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之维
——兼驳“信、达、雅”抄袭说
师杰
(山西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大同037009)
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严复翻译理论的“信达雅”抄袭了英国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但这种说法忽视了严复翻译理论提出时的中国文化背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因素,是仅靠简单的形式比对进行片面的主观评价。实际上,严复“信达雅”和泰特勒“三原则”之间有三大差异:前者强调信达雅的一致性,而后者强调三个原则的差异性;前者秉承了中国文化的经世致用观,而后者继承的是西方文化的求真思辨观;前者产生于中国历史上的西学东渐热潮时,而后者则产生于西方译论的前科学时代。
严复;信达雅;泰特勒;三原则;相似性
时下,比较译学研究越来越受到翻译理论界的关注。应该说,对中国译论和西方译论的很多方面进行共时的比较研究,找出其中异同,得出有益的启示,以促进我们对翻译的认识,是一种非常有建设性的工作。然而,比较译学研究中也有些研究只是对中国译论和西方译论某一方面做简单的比附,由其中相同的部分而轻率地得出结论,实在令人遗憾。近年来有学者撰文称严复的“信达雅”系抄袭英国翻译家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即属此列。笔者认为,翻译理论研究者对于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应当认真梳理,在虚心学习国外先进译论的同时,要善于总结自身经验、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在对传统译论做出现代阐释时要能确认传统译论的价值,而不要歪曲经典译论,因而妄自菲薄,失去自己的文化自信。
一、回到本初——原典分析
英国翻译家亚历山大·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1747-1814)于1792年出版的《论翻译的原则》(Essays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是西方翻译理论的第一部专著。该书阐述了完美翻译的三大原则:传达原作的思想、复制原作的风格、显现原作的流畅。
泰特勒对完美翻译(a good translation)作了一个界定,并提出三项具体的原则:
First General Rule: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Second General Rule: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in a translation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Third General Rule: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1](P102-103)
我们注意到泰特勒的三条原则中三次出现translation和original,因此其实际上论述了译文忠实于原文的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即思想、风格及行文。泰特勒深受18世纪浪漫主义诗派的影响,十分注重精神上的相似,这一特点接近傅雷的“神似说”;他特别偏重文体与风格,在诗歌翻译论述方面有开创之功。
泰特勒提出的忠实、风格一致和通顺的这三原则,因其全面、概括性而深入人心,成为许多翻译家遵循的信条,并对19到20世纪西方的翻译理论产生了积极影响。
时隔100多年之后的1898年,我国思想史上译介西方学术思想之第一人严复(1854-1921)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明确提出了堪称“译事楷模”的“信达雅”,并详加申说: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2](P136)
“信”要求译文意义忠实于原文;“达”指译文语言流畅,读者易解;“雅”乃严复顺应士大夫阶级的阅读习惯而选择的汉以前的写作文法。
历史证明,“信、达、雅”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实践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且由于它简明洗练的诗化语言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心理,在译坛一直被奉为圭臬,它不仅获得了最广泛的接受和认同,而且“获得了衡常价值和普遍意义”。[3]
二、比较之维——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
应该说,严复的“信达雅”和泰特勒的三原则之间确实有很大的相似性。大体看来,第一条相当于“信”,第二条相当于“雅”,第三条相当于“达”。然而这样简单比附,是否可以据此得出结论说严复的观点就一定是“抄袭”早他一百年而诞生的泰氏之三原则呢?严复晚于泰氏一百年而生是事实,但这一点是否一定就证明“信达雅”本于泰氏理论呢?笔者认为,关于“信达雅”与泰氏三原则是否有承继关系,恐怕不能单纯以作者出生之先后与二人观点之间表面的相似性而做出“抄袭说”的结论,妥善的做法是考察他们理论的各自内容与所指,更重要的是,要梳理其源流,找出他们各自的理论渊源,以便正确认识每种理论发生及发展的道路。
尽管严复的“信达雅”和泰特勒的三原则貌似如出一辙,但仔细分析起来,二者却有诸多差异。
首先,这两种理论产生的文化背景有巨大差异,二者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严复与泰特勒生活于不同的国度,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其理论自然也带着各自社会文化的深深烙印。严复所处的时代,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危机催生了康梁发动和领导的戊戌变法。而文化上,甲午战争之后,庞大的留学生群的出现,成为西学输入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西学东渐真正的翻译热潮是从维新派开始的。而从1895年到1911年,因朝野学习西方之需,成就了翻译一时之盛。
曾留学英国、精心研读过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著作的严复,甲午战败后痛感时事弥艰,连续发表政论,极力倡导维新变法,力主变法图强;同时开始致力于译著,欲以西方科学取代八股文章。他翻译西方著作的目的,决不在“其形下之粗迹”,[4](P576)而是要直探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脉所在。因此,严复高举“西学”旗帜,本着“西学中用”的治国思想,一方面要使人们在船坚炮利之外,更多地了解西洋各国强盛之根本,即社会政治思想;另一方面则要将西方学术著作中最切合中国现实状况者,视其先后缓急和时势之需要介绍给国人。
严复的翻译活动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进行的,他的“信达雅”翻译思想反映的也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需要,这与严复的学术思想和治国思想是浑然一体、不可割裂的。
随着1792年泰特勒的翻译理论专著《论翻译的原则》的出版,西方翻译理论的第一个时期也宣告结束。这第一个时期被后人贬为“前科学(pre-scientific)时代”或“前语言学(pre-linguistics)时代”。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集中反映了直接来自实践的经验,[5](P34)也就是说,泰特勒是西方遵循“经验”途径探索翻译问题的最后一人。泰特勒的翻译理论是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关于翻译的全部思考、观察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因此作为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代表了18世纪末以前西方翻译理论的巅峰。
与泰特勒大致同时代的许多知名翻译家和翻译思想家(如Dryden、Pope、Cowper、Campbell等)论述翻译问题时也大多以经验为本,规定一些译者和译文应严格遵守的所谓“原则”或“法则”。在这漫长的时期里,从事翻译的人直接根据自己的实践对翻译做了初步的分析和论述。
其次,二者侧重点迥然不同。中国的译论大多见于译家的感悟式随笔。秉承这一传统,严复也是在他所译之书的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的。所谓“译例言”,是译者对他译书过程中的艰辛与乐趣所做的解说,旨在交代成书过程以及译后的心得感悟,并非专为阐述其理论而写。而西方译论则截然不同,它秉承西方学术传统,注重理论的阐述。《论翻译的原则》是英国近代的一部翻译理论专著,泰特勒所提的翻译三原则“整体上思维严谨,表述清晰,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学术精神和品格”。[3]“信达雅”与“三原则”二者的出发点不同,因而侧重点也有本质的差异。
如前所述,泰特勒的三条原则中多次出现translation和original,显而易见,“三原则”分别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阐述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而于此三原则中,泰特勒更注重三原则的差异性,即三个不同的方面。因此,赵巍、石春让认为,泰特勒三原则的阐述“贯穿着强烈的主客体意识,具体表现在对客体即原文的尊重,反复强调译文应以原文为旨归,突出原文的重要地位,字面上也交代得一清二楚”。[3]
严复则比较侧重“信达雅”的一致性,着重从意义的角度忠实于原文,在诠释原文意义和译文的表达中强调译者的悟性。“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句话既表明了“信”和“达”的关系,也说明了严氏在“信”和“达”之间更强调“信”,“达”的目的也是为了“信”。严复对于“达”和“雅”的论述既点明了“达”和“雅”的关系,也表明了在“达”和“雅”之间他更强调“达”,“雅”是方式,“达”才是目的。由此看来,在严复所谓“信达雅”中,“雅”为的是“达”,而“达”为的是“信”,三者有着一致的目的。“信达雅”三者依其重要性渐降排列,三者中,严复侧重“信”,而“雅”和“达”皆以“信”为依归。
以上是从两种理论内容之侧重点得出的结论。若是就两种理论中每一条进行对照分析,则可以明显地看出,泰特勒的第一条中强调的是complete,即译文要完整再现原文的思想,不使译文中出现漏译现象,即所谓“欠额翻译”;而严复的“信”讲的则是译文“不倍本文”。笔者认为,如果说泰氏的第一条是从“量”的角度来对译文做出规定,那么严复的“信”是从“质”的角度对译文给予把握。再拿严复的“雅”来说,严复所谓“汉以前字法句法”实则是为了在士大夫阶层的读者群里获得言说方式的认可而采取的策略选择,这一点当属严氏基于当时国情的创见,绝无丝毫抄袭泰特勒三原则的嫌疑和可能。
最后,二者的分野反映出中西方不同的学术价值观。中西方译论有各自的学术传统,所以泰氏“三原则”和严氏“信达雅”的提出也各有其学术渊源,不能因其相似而将其混为一谈。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经世致用,有一种功用至上的倾向。所谓“六经注我”讲的便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的经世致用观。从严复对所译西方著作的取舍中,便能看出他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贺麟在谈到严复选择原书的精审时说,“[他]处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空气中,……根本认定西方各国之强盛,在于学术思想,认定中国当时之需要,也在学术思想。”学术之目的不在学术本身,而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深受这种文化氛围熏陶的严复译介西方思想著作也并非出于对翻译本身的兴趣,而是为了赈世济民,富国强民。他翻译《天演论》旨在将科学进化论引入中国;翻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又将逻辑归纳法和演绎法介绍到中国。其翻译实践如此,翻译思想亦当如此。散见于其译著译例言的翻译思想,旨在说明译书之背景、艰辛及心得,因此其表述缺乏西方翻译理论专著的精当论述和缜密的逻辑推演,而是多了一层强调译者/读者悟性的成分,更强调译者/读者的学养积累,少了对所译客体的条分缕析式的认识及对翻译实践就事论事式的科学态度。
西方文化从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更多关注认知本身,其价值在于满足人性自在的思辨兴趣,不在于征服自然的实用目的,所以更注重逻辑分析和理论的演绎,在语言表述上具有条理性和层次性,理论更具系统性。西方文化这一求真特质决定了西方译论多以理论专著的形式出现,尽管西方翻译理论也是源于翻译实践的,但是与中国译论纯粹发端于译家个人的翻译经验而见之于译著“例言”及它所反映的中国人治学之“经世致用”特点不同的是,西方译论可以单就理论说事,多了一种“就事论事”的因素,也就是说可以抛开具体的文本翻译实践,只在理论层面进行探讨和阐述。泰氏“三原则”秉承了西方学术文化的求真思辨传统,着重阐述原文的特质应在三个不同的方面——思想、风格及流畅程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它所论及的这三个方面虽然也本于翻译实践,但译论本身则可自成一体。
三、评价坐标——源于民族文化的提炼与创新
说到理论之共同点,无独有偶,历史上有多位翻译理论家都提出过与泰特勒“三原则”相似的翻译理论。举凡费道罗夫的“等值”、奈达的“等效”、纽马克的“文本中心论”、卡特福德的“对等翻译”,都与严复的“信达雅”有相通相契之处。尤其是泰特勒的“三原则”和罗森斯坦的“Triness”(三个“ness”即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gracefulness),相通之处就更多。应该说,身处不同地域的学者通过各自的学术实践得出相似或相近的理论,这恰恰说明学者们对翻译活动有着共同的认识,或者说翻译活动在不同的双语对译中进行转换时体现出相似或相同的规律。如果我们根据严复”信达雅“与泰氏“三原则”之间存在的相似性,便得出结论说严复的理论系抄袭泰特勒的理论,那么,我们是不是更有理由说罗森斯坦的理论抄袭了泰氏理论呢?罗氏的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gracefulness岂不正合于泰氏的第一、第二、第三条原则么?
事实上,早在泰特勒之前,英国翻译理论家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1719-1796)便首次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1)准确地再现原作的意思;(2)在符合译作语言特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移植原作者的精神和风格;(3)使译作像原作那样自然流畅。坎氏的“三原则”和泰氏“三原则”无论从文字表述,还是从理论渊源上都比严复的“信达雅”与泰氏“三原则”之间更具相似性,然而西方人没有据此得出后者抄袭前者的结论,反倒是我们中国人通过简单的比附得出严复“信达雅”抄袭了泰特勒“三原则”的结论,这个事实本身是否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呢?
从中国翻译史的纵向来看,严复的翻译思想是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土壤,继承了前人的理论并提炼而成。罗新璋认为,“严复的译例言,客观上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一方面,集汉唐译经论说之大成;另一方面,开近代翻译学说之先河。”[2](P6)严复是我国近代的翻译家,其理论与我国古代译论一脉相承,同时对古代译论又有所发展,属于我国自成一体的翻译理论体系。
笔者认为,既然中国译论和西方译论客观上曾经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在进行中西译论的比较研究时,就应当实事求是地对二者进行剖析,要正确对待中西译论各自的优缺点,这样就能做到既敢于肯定中国传统译论的学术价值,又不盲目跟风,人云亦云,混淆是非,人为地丧失了文化自信。
当然,实现这一转变的前提是我们要有历史和文化的视野。只有将观点置于大历史的坐标体系,尤其是本民族文化演进的谱系中,观点才会鲜活,才会释放出张力,也才真正能还原理论本身应该具有的学术地位与世界意义。
[1]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2]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A].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3]赵巍,石春让.比较译学的个案研究引发的思考——从严复的“信达雅”与泰特勒的三原则说起[J].外语学刊,2005(05):96-100.
[4]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5]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庄绎传译.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An Avoidance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An Argument against the Contention of Plagiarism on the Part of Yan Fu's“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SHI Ji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This thesis expounds on the three important discrepancies between Yan Fu's“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and Tytler's Three Principles:while the former stresses the consistency of 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the latter lays emphasis on the dissimilarities of the Three Principles;the former has proclaimed the idea of“Putting What is Learned into Practice”in Chinese culture,whereas the latter has been a continuation of“Seeking the Truth through Speculative Thinking”in western culture;the former has grown out of he upsurge of western culture be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but the latter has come from the pre-scientific age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By analysing the above thre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the paper aims to disprove the plagiarism on the part of Yan Fu's Three-Character Principle.Also it is made clear in the paper that great caution must be taken against such research abus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Yan Fu;“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Tytler;the Three Principles;similarity
H059;I046
A
1674-0882(2016)05-0077-04
2016-06-25
师杰(1971-),男,山西浑源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西对比与翻译。
〔责任编辑 裴兴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