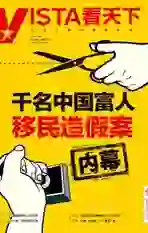北京西海边,收集遗落的“文明倒影”
2016-03-29沈佳音
沈佳音
姜寻将雕版称为“文明的倒影”,不仅因为雕版上面的字是反的,而且它们身上有时光的痕迹,忠实地反映了逝去的文化生活
一个年轻人在台灯下低头凝视,右手半握拳握住刻刀,左手四指并拢摁住木板,大拇指推进。他遵循前辈的教导,“伐刀要快,干净利落,挑刀要准,不偏毫厘”,汉字的一笔一画在坚硬的木板上慢慢凸显。
案边摆着几块刚刻好的雕版,等待着水印师为其刷上墨汁,付诸宣纸,然后再手工装订成册。这是起于隋唐年间的雕版印刷术,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印刷形式。
两千年后,在码洋以亿计的二十一世纪,这种古老的印刷术在北京西海边、一家名为“煮雨山房”的工作室里延续。去年,他们应诺贝尔博物馆的邀请,为莫言的小说《大风》定制了274册木刻雕版线装书。
姜寻是这里的主人,作为中国收藏雕版最多的人,他还有三万多块雕版长年封存在几个库房里,无处展示。而去年,韩国已经将一批雕版打包申遗成功了。
众里寻他
“煮雨山房”还是一个小型雕版博物馆,一些明清时期的雕版陈列在书架上。一进工作室就能看见墙上挂着《草窗韵语》卷一首页的整幅雕版拓片,长1.8米,宽1.3米,这是姜寻的至爱。而另一块宝贝明万历雕版《五台山佛教印刷版》则被他固定在一个可旋转的木架上,供人翻看两面精美的雕刻, 一面是“婆罗宝树之图”,一面是“西方圣境九品往生图”。
1916年,宋代孤本《草窗韵语》一经出现便引起藏书家争相抢购,因为全书字画均依作者周密的手稿真迹临摹,被人称作“妖书”、“尤物”,“纸墨鲜明,刻书奇秀,出匣如奇花四照,一座尽惊”。大藏书家蒋汝藻是民国丝绸富商,他以1500大洋的高价力压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将其收入囊中。
拿到书后,蒋汝藻欣喜不已,以其为镇库之宝,将原藏书室“传书堂”改名为“密韵楼”,又延请董康依照宋本原样翻刻。然而这本书刚二校蓝印数十本,还没来得及正式出墨印本,蒋家便破产了。宋本《草窗韵语》从此不知所踪,200多块雕版也各自流落天涯。
升入初中时,姜寻从父亲手中接过人生第一张雕版。那是一张木刻戏曲雕版,“民间唱本的一组插图,像连环画一样”。年幼的他只是觉得很美,一直到上世纪末到中央美院壁画系读研究生后,他接触到一些名家,才对藏书文化有了系统的了解,也因此发现了雕版的文字之美。
姜寻倾慕蒋汝藻,2004年曾特意到其老家浙江南浔寻找“密韵楼”,千辛万苦才找到旧址,却已经破败不堪。回来后,他花了三四年时间,从私人藏家和拍卖会购买过4次,才集齐了这套《草窗韵语》的雕版。姜寻对这套雕版甚为钟爱,他女儿的名字便出自于此,唤作“语儿”。
收藏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稍纵即逝。
2000年,那块《五台山佛教印刷版》出现时,古董商给姜寻打电话,说收到一块大型佛经雕版。在外出差的姜寻赶回北京后却得知已被买走。于是几年间,他经常给这个古董商打电话,希望其牵线搭桥,请那个买主转让此物,但一直未能如愿。姜寻的朋友都知道他的这个遗憾。在一个画廊里,他的朋友偶然看到了这块精美雕版,便赶紧告诉姜寻。这一次,他终于如愿以偿。
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姜寻收藏雕版已经二十年了。这依然是个小众收藏,很多收藏家觉得这不过是些黑乎乎的木料。但姜寻却将其称为“文明的倒影”,不仅因为雕版上面的字是反的,而且它们身上有时光的痕迹,忠实地反映了逝去的文化生活:可以看到大悲咒佛经,可以看到《长生殿》的戏曲本子,可以看到门神年画,可以看到清算地主的历史记录,可以看到类似“大富翁”游戏的升官图……
雕版上的文字也透露着很多有趣的信息。国力强盛时,字迹工整大气。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奉康熙皇帝之命主持刊刻《全唐诗》,集全国之能工巧匠,做得尽善尽美。从嘉庆时期开始,刻字就开始歪扭,而到了光绪时,雕版上的字已经完全扭曲了。
姜寻随手从墙角抽出一块元代的雕版《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现在是没有人去做研究。比如公元 868 年的《金刚经》,它的墨是现代技术无法研制的。如果我们从古代的雕版上提取积墨进行成分分析,会对现在墨汁的生产提供一些参考。”
2009 年,姜寻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将其一间食堂改造成文津雕版博物馆。他挑选了一万余片雕版做展览,免费对公众开放。“这些雕版曾将文明硕果大量复制,广泛传播。它们历代延续下来,像古老的山脉一样,可能动不了,但成为一种原始的存在。”
来自诺贝尔的订单
书籍付梓出版之后,很多雕版就如废料一般被遗弃,来到姜寻手中之前,有些曾被用作菜板,后背刀痕累累;有些曾被用作鸡笼猪圈,污秽堆积;有些曾被用作门板窗户,容颜斑驳,有些被劈成碎片残渣……
开设雕版博物馆那些年,姜寻便组织工匠对部分散失、腐朽、损坏的雕版做一些修补工作,尽量将其补齐。
《草窗韵语》也不例外。姜寻想将其刊补完整,接续蒋汝藻当年未竟的事业:“这是藏书家的潜意识里将收藏、研究、出版看作自己的职责。古代的藏书家收到一些孤本善本,就会把它翻刻出来,流传后世,要不然这书没了就没了。”
他多方打听才找到扬州雕版印刷国家级传承人陈义时担此重任。“扬州曾是南方雕版印刷的中心,陈义时出身雕版世家,把《草窗韵语》完美地补齐了。”姜寻也不得不承认这一行已经衰落了,“我这里曾经有四个刻工,但是现在只剩下两个了。虽然我们提供的薪水还可以,但也不可能太高,熬不住就走了。如今全国刻得好的不超过十个。”
2009年,扬州雕版印刷技艺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依然很少有人愿意再学这门手艺。陈义时的儿子无论如何都不肯子承父业,他只好打破“传男不传女”的老规矩,逼着女儿接了班。
在机器的流水作业前,手工作业无疑如龟速般前行。一个熟练的刻工一天刻二十多个字,而一块雕版一般刷800到1200次为宜。姜寻每年只做几本书,每本印数也不过几百册。
与姜寻一样,留在这一行的都是真正爱雕版的人。2010年,24岁的山西男孩赵乙屾放弃了所学的法律专业,循着古籍上的名字“广陵古籍刻印社”来到扬州,拜入陈义时门下。“雕版上有各种各样的字体。古人读书是单纯地沉浸在一种阅读体验里,读的时候有时候会欣赏一下字好不好看。而这个时代的人可能会省略这个程序,现在的人读书,我感觉就是为了获取一些信息,一些数据,只要是一种格式化的字体就行了。”
2013年,陈义时把赵乙屾介绍到“煮雨山房”工作,因为这里是全国为数不多还能有活干的地方。赵乙屾一来便开始刻民国奇女子吕碧城二十页的手稿《晓珠词》,这是姜寻的老师杨成凯最喜欢的一位女作家。赵乙屾每天平均刻十几个字,已经刻了十多页,预计今年可以印刷出版。遗憾的是,杨先生去年去世了,最终没有等到。
刻版需要长期久坐,赵乙屾不仅不以为苦,却认为这是一种放松。他沉浸在木头、墨汁、宣纸交织的气息中,怡然自得。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汉学家艾思仁也热爱中国的雕版印刷。他一直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国版刻之美的书。
去年,艾思仁的老伙伴、古籍与版画收藏家冯德保以诺贝尔博物馆的名义邀请姜寻为莫言1984年的小说《大风》定制了木刻雕版线装书。从2009年开始,诺贝尔博物馆每年都会邀请两个国家的设计师来为书籍做装帧设计。
姜寻为《大风》选择了雕版《草窗韵语》里的字体。他从里面把字一个个摘出来,没有的字就找字根造字。他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电脑上反复调整每个汉字的结构比例,保证全书字体的和谐统一。排好版,然后刻板。接着请天津杨柳青的水印师把汪六吉手工宣纸附上刷版,最后手工穿线装订而成。
这部书全球发行274册,每一册都有编号。在斯德哥尔摩亮相后,后50册放在中国销售。这也是姜寻这些年收到的唯一一笔木刻雕版线装书的订单:“我还做很多其它的设计,来补贴雕版这部分的支出。”
书籍的母体
今年46岁的姜寻自号“大来”,因为他收藏的第一部明版书是“大来堂”版《史记》,一开始只买到上半部,时隔几年后又遇到了下半部。他也曾一掷千金,在翰海拍卖会上花138万买下一张唐代刻本《陀罗尼经》,令藏书家韦力刮目相看。
如今,古籍善本已是炙手可热的拍品,姜寻另辟蹊径,发力雕版收藏,“雕版是书籍的母体,具有唯一性和稀缺性,现代人更应重视其技艺传承及旧雕版的保护问题”。
2012年,文津雕版博物馆因拆迁而仓促关门,一直没再找到合适的场馆。姜寻有一次去韩国,一下飞机就看见几个女人在刷版:“中国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雕版是什么了。”
去年,韩国将64226块朝鲜李氏王朝时期(1392-1910)的《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打包,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成功。韩方在申报材料中说,这些古籍木刻板中有一些已经遗失,有一些有破损,但正是这些遗失和破损,更应该唤醒一种意识,那就是保护这些古代经典的载体,让它们得到更好传承。而姜寻的3万多块雕版中,仅明代就有3000多件。
韩国的同行为姜寻的收藏估出天价,但姜寻不以为然:“你不能用别人给你的估值,来判断自己的文化价值,文化是无价的。只有真心热爱,文化才有温度。”
这些雕版,姜寻一块都不肯卖掉。“好多人不理解,说你买了这么多雕版,为什么还在买。这就像人的成长一样,有了阅历的积累才有思想力。你有一块雕版的时候,你没法分类,你有一百块的时候,你知道大致的类别了,你有一万块的时候,你整个类别很清楚,雕版分三大类,一个是书籍雕版,一个是佛经雕版,一个是版画雕版,然后再细分。有数量才能选精品。”
作为读书人,姜寻又特别偏爱书籍雕版,在他的收藏中,有两万多块是诗文类的。 他同时也是一位装帧设计师,他设计的书曾三度获得“中国最美的书”图书奖。其中一本是他自己的诗词集《姜寻诗词十九首》,依然是木刻雕版线装书。每一页纸都是手工抄的千年古宣,还是毛边纸,用麻绳装订。最特别的是其封面装帧着一块清代早期的雕版残片。这样的书每一本都是孤品,因为每一块雕版残片都是不一样的。而这本集子的字体来自他收藏的1958年的雕版《毛泽东诗词二十一首》,也是他自己一个汉字一个汉字地拼出来的。
在他的太太邢娜看来,姜寻对雕版的热爱,其实源于他对汉字的痴迷。姜寻一直酷爱金庸,小时候曾经看到一本金庸的港版书里有一篇前言,变成简体版后就没有了。于是他拿出一本父亲民国时的老字典,从中找出每一个字,剪下来拼成一篇前言。“所以,他现在干的还是小时候酷爱的那件事,一模一样。”
在姜寻身上,时光似乎停住了,犹如那些已坚硬如石的老雕版,而版上那些汉字的笔画又衍生出无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