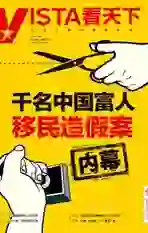苏联解体后,“红色人类”和他们的二手时代
2016-03-29沈佳音
沈佳音


在《二手时间》中,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了
在前苏联地区看到的数位“红色的人”。对于本书在中国出版,她曾向译者吕宁思表示:“我希望知道中国读者是怎样读我的这些书的。”
“俄罗斯文学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是唯一能讲述一个大国实施一场实验的文学。”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写作中,她创作了一套“红色百科全书”。她写了五本书,试图重现苏联如何想在地球上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历史。
《二手时间》是最后一本,被她称为《红色人类的终结》。1991年,苏联在泪水和咒骂声中轰然倒塌,然而美好的自由生活并没有如约而来。从那时起,阿列克谢耶维奇便开始游历整个苏联地区,她看到“红色的人”——苏维埃人仍然无处不在,在混乱的新时代里挣扎。“充满希望的年代被充满恐惧的年代所取代。这个时代在转身、倒退。我们生活在一个二手时代。”
今年,《二手时间》在中国翻译出版,自此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这五本书都与中国读者见面了。在二十世纪,两国的历史进程互为参照,而在世纪末,两个大国走上了各自的道路。《二手时间》里那些主人公提起中国心情复杂,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向该书的译者吕宁思表示:“我希望知道中国读者是怎样读我的这些书的。”
如何不靠伟大思想活下去
1992年秋天,一位77岁的二战老兵在布列斯特要塞卧轨自杀。五十一年前,他曾和苏联战友们一起在这里抵抗了希特勒军队的进攻。老人身上有一份遗书,痛斥叶利钦-盖达尔政府,因为他们造成的屈辱和贫困的生活,也因为他们对伟大胜利的背叛。
“他没有留给我们一张纸片。只给国家、给陌生的人们写了遗书。”他的妻子无法理解他。有一次他下班回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让我们去参加伟大的建设吧,祖国在召唤。”然后,他就带着妻女参加了贝阿大铁路建设工程,去建设共产主义……
然而,苏联的共产主义一夜之间就没了,调头奔向了资本主义。这些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却留在了原地,成了所有人的笑料。有一个主人公说:“我们都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甚至到现在我们仍然喜欢人贴人地拥挤着排队,有一种团结的感觉。”
书中记录了好几个自杀者的故事,他们不愿意改变,因为那意味着否定自己的一生。“国家成了他们的宇宙,取代了他们的一切,甚至生命。他们无法摆脱伟大的历史,无法和那段历史告别,无法接受另外一种幸福,不能像今天的人们这样,完全潜入和消失于个体生活中,把渺小看成巨大。”
阿列克谢耶维奇自己也是“红色的人”,她剖析俄罗斯民族身上的奴性。她还记得,放学后他们全班同学一起去开垦荒地,他们鄙视那些不去的同学。“我们会为了自己没有参加过革命、没有经历过战争,而难过得哭出来。”
这几年,大陆引进了一些关于苏联历史的作品,比如《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古拉格:一部历史》等作品都用惊心动魄的故事告诉人们那些年的真相。阿列克谢耶维奇此前几部作品也是如此。
而《二手时间》除了揭示历史真相以外,还着重于记录知道真相之后。“帝国的没落令所有人忧虑:人们为日常生活发愁,拿什么买东西?怎么活下去?相信什么?这次要喊什么口号?如何学习不再依靠伟大思想活下去?最后一个问题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因为从来经历过这样的生活。”
比如一个成长于斯大林时代的女孩知道了大饥荒和大屠杀之后却选择了逃避真相,因为“没有那种生活,我就会双手空空;失去一切,我就会像个乞丐!”她的母亲是个美女,来自贵族家庭,1917年革命爆发前嫁给了一位军官,屡遭调查,但她母亲对斯大林爱到头脑发昏。她的父亲是个共产党员,却遭到党内残酷镇压,在监狱里打掉了牙齿,打破了脑袋,被开除党籍,但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傻瓜?天真?不,这都是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妈妈读莎士比亚和歌德的原著,爸爸毕业于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
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苏联解体后的十几年,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首先是一个大时代被偷走了,然后是他们个人的时间被偷走了”。
没用一枪一炮,超级大国就分崩离析了,然而依然血流成河。历史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人群中潜伏着魔鬼的激情,热衷于种族屠杀、暴力掠夺。熟悉的邻里立刻变成了互相残杀的敌人。
断裂的叙述
一个八十七岁的老共产党员在激烈地缅怀着苏联时代,他曾是列宁的信徒,后来又成为斯大林的信徒。“乳臭未干的小丫头!我才不是奴隶呢!……那是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将来再也不会生活在那样强大的国家中了。”他给大儿子取名“十月”,还想给女儿取名“柳波列娜”,取自于“我爱列宁”。他妻子也列下了一系列中意的名字:马克思娜、斯大林娜、恩格斯娜……都是当时最时髦的名字。
不过,讲着讲着,老共产党员的讲述出现了裂缝。在一次全市党代会上,宣读了对斯大林致敬信,与会者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光荣属于斯大林同志,我们胜利的组织者和鼓舞者!”掌声持续了十五分钟,持续了半个钟头。所有的人都站着,互相观望,没有人敢第一个坐下。他不知道怎么就坐下了,完全是下意识的。这时两个便衣就过来问他:“同志,您为什么坐下了?”他马上跳起来,就像被烫着了一样。他和妻子都曾被邻居偷听检举而遭到残酷审查,并含冤坐牢,被打得肚子里的东西都流出来了。在监狱里,他遇到了因为各种原因坐牢的人,最奇葩的一个是因为他长得太像斯大林了。但出狱之后,打开香槟,第一杯仍然是“为了斯大林”,拿回党证后他觉得幸福极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向他表示不可理解,他发火了:“你们不能按照一般的逻辑法则来审视我们,不会像会计师那样计算!你们必须明白,能够判定我们的只有宗教法则!这叫信仰!你们还会羡慕我们吧!……您也认为,就像现在报纸上写的那样,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用密封的车厢从德国带来的传染病吗?一派胡言!是人民站起来了。”

1992年3月16日,正在进行“去苏联化”运动的俄罗斯街头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关掉录音机后,他说出了心中最隐蔽的秘密。十五岁的时候,一群红军来到他们村征兵:“红军在挨饿,列宁在挨饿。富农把粮食藏了起来,要么烧了。”他当时是共青团员,他知道自己的舅舅把好几口袋小米运到森林里,挖坑埋起来了。他想起自己入团时的誓言,于是夜里就找到红军,带他们到了现场,红军装了整整一车。早上,他被妈妈的哭声惊醒,舅舅家着火了,舅舅被红军战士用军刀砍成了碎片。
七十多年后讲起往事,他用双手蒙住眼睛哭了。在他死后,他把市中心的一套三室公寓留给了他“最热爱的共产党”。
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了这个故事,因为“这是属于一个时代而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二手时间》里有二十多个人的完整故事,曾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德国媒体称赞该书摘取的是最为细小的马赛克,却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图画。
复调的历史抒写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采访历时二十年,她向人们询问的不是关于某种主义,而是关于爱情、嫉妒、童年、老年,关于音乐、舞蹈、发型,关于已经消失的生活中成千上万个细节。“实际上,在一个人的身上会发生所有的一切。”
因此,文学界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一直有争议,尤其在她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认为她写的是文献,不是文学。在获奖演讲中,她说:“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没有界限,它们相互流动。见证者不是中立的。讲故事时,人们会进行加工创造。他们与时间角力,他们是演员,也是创作者。在我的书中,他们讲述自己的历史,更宏大的历史也从中显现。我们没有时间来理解已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说出来。”
诺奖对其作品最为推崇的“复调书写”在《二手时间》里随处可见。“从写作风格上看,她的复调特点是多种第一人称交叉(包括作者本人、被专访的主人公和群体采访的各类人物),多种语境的交叉(回忆、描述、片语、意识流)和多种环境和时间的交叉。” 阿列克谢耶维奇并不直接评判,不过吕宁思还是读出其世界观的复调,“不仅仅是创作手法的复调风格,其实在她的作品中更揭示出复调式的人生,一个人从语言到思想到感情都具有多面性,甚至于一个人的身份和世界观都是复调式的,本书主人公们讲述的故事中,就展现出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复杂性。”
在那个卧轨老兵的葬礼上,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了他的战友关于战争的不同记忆和关于现状的不同评价。而在与老共产党员的交谈中,老共产党员的讲述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分叉。他的孙子一直坐在旁边沉默不语,只用几个政治笑话表明态度。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在一个火车站里,挤着好几百人。一个穿着皮衣的人绝望地在人群中寻找着谁。可找到了!他走到另外一个穿着皮衣的人跟前:“同志,你是党员还是群众?”“我是党员。”“那么请你告诉我,这里有公共厕所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坦承:“当面对人的多重层次,面对生活的复调,我自己都呆住了。” 她还采访了一对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友谊的闺蜜。两人的故事中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除了都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的名字。两人心中都有各自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有她们自己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她们从大学时就约定不谈政治,不涉及这些话题,只谈论孩子和孙子,只谈论谁的别墅栽种了什么东西。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到现在。

1991年8月,在莫斯科街头进行民主集会的年轻人
在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故事的最后,阿列克谢耶维奇特意采访了一位十九岁的大学生。他不知道这个苏联解体前自杀身亡的元帅:“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我喜欢斯大林……”
阿列克谢耶维奇发现在新世纪又出现了对苏联的向往,对斯大林的崇拜。在大街上,她遇到了身穿印有铁锤镰刀和列宁肖像T 恤衫的年轻人,“但他们真的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吗?”
明年就是1917年十月革命一百周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写道:“一百年过去了,未来又一次没有到位。出现了一个二手时代。”
在全书的末尾,她附录了一个小人物的讲述。这个六十岁的老妇人,生活在远离莫斯科的偏远农村里,苏联强大了,苏联消失了,都与她无关,什么也没有失去。“我还是住着一个没有任何设备的小房子,没有水,没有下水道,没有煤气,我就是这么生活的。我一辈子就是老老实实工作。耕地,干活,从不闲着。我的收入一直很微薄。”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普京,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白军和‘红军都是一回事。反正要等到春天才能种土豆……”
安娜·依琳尼奇娜:
这虽然是不久之前发生的事,但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国家了……我们的天真和我们的浪漫都留在那里了。
我当时是立刻就爱上了戈尔巴乔夫!现在他们都谴责他:“苏联的叛徒!”“戈尔巴乔夫为了比萨饼就出卖了国家!”但我还记得我们当时的惊奇和震撼!我们终于有了一位正常的领导人。我不为他感到羞耻!那时候大家彼此传颂戈尔巴乔夫如何在列宁格勒叫停了保安随从的阻挡,走到人民中间,还在一个工厂拒绝了昂贵的礼物,在一个传统的晚宴上只喝了一杯茶,等等。他总是微笑,讲话从来不念稿子,年富力强。我们没人会相信,就在商店里出现香肠的时候,就在人们不必为了购买进口胸罩而排上几公里队伍的时候,苏维埃政权却竟然终结了。
那时候人们对报纸杂志的激情简直无可描述,远远超过读书。那些厚厚的刊物动辄发行量突破数百万册。从早到晚在地铁上总是同样的景象:全车乘客,坐着的、站着的,都在阅读。素不相识的人们也都互相交换报纸看。我和我的丈夫订阅了二十种杂志,一个人的工资全花在订杂志上了。我一下班就跑回家,换上浴袍开始阅读。不久前我妈妈去世了,她说过:“我会像一只垃圾场中的老鼠似的死去。”她那个一居室的住房简直就是一个阅读室:从书架到壁橱,从地板到走廊,堆满了杂志、报纸,其中有珍贵的《新世界》《旗帜》和《道加瓦》……到处是装剪报的盒子。
那时候的信仰是真诚的,也是天真的……我们都相信:时候到了,停在街上的公共汽车把我们载去参加民主集会。我们憧憬着住进美丽的房子,而不是赫鲁晓夫的灰色建筑中,我们会建成高速路取代破旧的公路,一切都将变得美好。但谁都没有去寻求合理的证明。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证明。但是为什么还要相信?因为我们是用心去信,而不是用理智去信。我们是用心去投票站投票的。谁都没有具体说应该做什么,反正自由就是一切了。如果你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电梯里,那么你的梦想就只有一个:打开电梯门。而当电梯门开启时,你就会感到幸福,无比幸福!这时你还不会去想自己此刻应该做些什么……因为你终于能够畅快地呼吸了,你只是感觉到快乐!我的女友嫁给了一个在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的法国人。那个人只是听她说啊说:“看看吧,我们俄罗斯人现在多么有干劲。”可是他问她:“你能告诉我,这种干劲是要做什么呢?” 其实不管是她还是我都不能对他说清楚。我只是这样回答他说:干劲就是攻击力,就是这样。我看见周围都是生气勃勃的人,生气勃勃的面孔。那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美丽!这些人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啊?昨天他们都还不存在啊!
我们家里的电视机从来都不关,每小时都要看整点新闻播报。那时候我刚刚生了儿子,每次抱着他到院子里,也一定要带个收音机。居民们连外出遛狗时也要带着收音机。现在我总是要拿儿子开玩笑:你和我们在一起,生来就是政治家。可是他对此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整天就是听音乐,学习外语,想去看外面的世界,过另一种生活。我们的下一代完全都不像我们,他们到底像什么人啊?在我说到戈尔巴乔夫时,我的丈夫必须补充一句“戈尔巴乔夫……还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时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总书记的妻子,从来没有为她不好意思。秀美的身材,漂亮的服装,他们夫妇相亲相爱。有人给我们带来一本波兰杂志,上面写道:“赖莎,是一种范儿!”我们为此多么骄傲啊!人们没完没了地参加集会,街道都被传单覆盖了。一个集会结束了,另一个又开始了。人们都像赶场一样奔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要去得到某种启示。这正是正确的人寻找正确的答案的时刻。前方还有未知的生活在等待我们,它吸引了所有人,就好像我们已经到了自由天国的大门口。
但是生活却变得越来越糟糕。很快,除了书籍,什么都买不到了。货柜上只剩下书籍了……